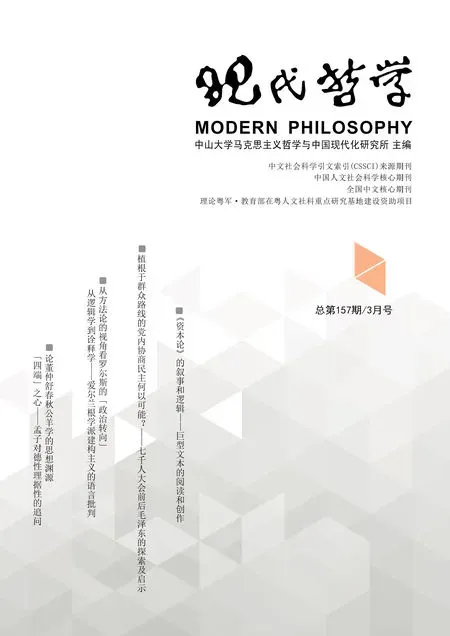卫生与政治:1950年代前期西南土改卫生工作队研究
李飞龙
1951年5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颁布了《关于动员组织卫生工作者到农村去配合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强调“为了配合分配土地的改革任务,全区应大力发动各级医协组织土改卫生工作队”*《关于动员组织卫生工作者到农村去配合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西南卫生》1951年第1期。。1951年下半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共组织了9200名卫生人员参加土改卫生工作队。他们深入农村,一面协助土改,一面进行卫生宣传教育、防治疾病、训练初级卫生人员、建立基层卫生组织。*《西南区三年来工作的成就》,重庆:西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05页。不过,此为配合土改而组建的卫生组织并未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仅发生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所管辖的三个省、四个行署区、一个直辖市以及西藏*时西南局管辖的范围为云南、贵州、西康三省,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署区,重庆直辖市及西藏,人口7650万。参见四川省档案馆编:《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1949-1954)》,内部资料,2000年,第141页。,从而使西南土改卫生工作队具有某种特殊意义,即不仅要保障土改队人员的身体健康、开展卫生防疫,还要配合土地改革、增强西南民众的国家认同。
这种将卫生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的组织并非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出现,始于20世纪初的现代卫生观念和公共卫生制度就已经预示着国家权力的介入。20世纪前,即便是大城市也仅采用传统方式来解决卫生问题,晚清以前不论是富贵之家还是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排泄物的处理基本没有卫生、便捷的污物处理系统。*杜丽红:《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现代卫生观念和公共卫生制度的确立得益于国家对卫生管理的介入,广州即是通过民国时期的市政改革才创立了现代卫生制度,虽然城市厕所的改变是有限的,但政府成功地塑造了一套对厕所和如厕文化的新准则,以及改变人们对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构想。*潘淑华:《民国时期广州的粪秽处理与城市生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9期,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8年,第67—95页。换言之,从20世纪初开始,以国家权力的介入为标志,现代卫生观念和公共卫生制度才得以建立,从此卫生与政治便密不可分。但是,近代中国政治对卫生的影响毕竟有限,尤其是远离现代文明的农村和边疆民族地区,民众甚少感受到来自国家的力量。晚清一位来华传教士曾对中国人的自由如此评价:“中国人丝毫不像受压迫民众,世界上再没有比他们更不受官方干扰的了。”*[美]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以磅礴之势解放大西南后,西南地区的民众即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卫生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日渐紧密。
目前,学界对卫生与政治的研究多集中于近代中国*如余新忠的《晚清的卫生行政与近代身体的形成——以卫生防疫为中心》(《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刘岸冰的《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初探》(《史林》2006年第2期),杜丽红的《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成果是此方面的代表。,而且研究表明近代公共卫生制度对下层民众而言,往往是“费而不惠”。*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25页。当代卫生防疫亦有论及,但主要是宏观层面的政策梳理,或地方实践的静态叙述*例如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艾智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清洁卫生运动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9期;肖爱树:《1949-1959年爱国卫生运动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胡克夫:《新中国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和防疫体系的创立与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等等。;而对卫生防疫在政府职能和权力的日渐具体化和不断扩张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所起的作用如何,目前还未见专门的讨论。鉴于此,本文拟以西南土改卫生工作队为例,试图分析1950年代前期西南地区的农村社会状况,以及卫生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解放前西南地区的农村社会
土改卫生工作队仅发生在西南地区,既与其恶劣的卫生防疫条件有关,也是其独特的政治环境所致。即便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地处西南的农民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仍旧薄弱,尤其是少数民族存在严重的“我族”与“他族”之分,加之近代西南边疆的列强入侵以及传教士的文化渗透,使得西南地区的农村对国家的认同度很低。这或许就是西南局卫生部派遣土改卫生工作队的深层原因和背后逻辑。
首先,解放前的历代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农村都仅限于间接管理,无法实质性地控制基层社会。自秦朝设置西南三郡开始,中央政权就将西南地区纳入了控制版图,并推行“天下一统”之理念。不过,无论是应对边疆及更远地区民族的“羁縻治策”,还是元代以后制度性特征明显的土官土司制度,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仅仅停留在对当地蛮夷首领的政治控制上,以土官治土民。明清的“改土归流”虽然对强化国家的直接控制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却因19世纪中期开始的列强威胁、蚕食以至入侵而被迫退让。不论是清朝还是中华民国都未能经由政治一体化和文化同化完全达成直辖西南边疆的预期成效。*吴启讷:《民族自治与中央集权——1950年代北京籍由行政区划将民族区域自治导向国家整合的过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5期,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第81—137页。1917年春,云南省政府试图进行禁烟,曾派一个营的军队到云南省澜沧县佧佤山中课、班庆禁种鸦片,结果少校司令沈某被击毙,部队溃败,几乎全军覆灭。*云南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41页。有些居住在边境的少数民族甚至举家离开中国,1936年前后,“仅腾跃龙陵沿边一带,近年来每年迁出界外的夷民平均有二三千户之报”*江应樑:《抗战中的西南民族问题》,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1938年,第14页。。抗日战争时期,受到国民政府重心西迁的影响,国民党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力有所增强,西南地区的主动参战也使得族群建构与国家整合联系起来,中华民族化得到增强。不过,除中央系进驻四川、贵州外,西南地区基层社会一直游离于中央政权以外,即便是国民党中央政权进驻贵州并经营多年,“但多系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上层,而县以下广大的农村仍为地方实力派所把持”*贵州省委:《工作报告(1950年1月9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馆):《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0)》,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76页。。可见,解放前夕的大西南,特别是民族地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仍需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仍无法实质性控制基层社会,一些地方割据和列强入侵甚至有分离边疆的危险。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地区农村并没有广泛的基础,革命力量不强。解放前西南地区曾拥有一定数量的党组织和党员,但基础薄弱,发展缓慢。近代以来,以龙云、卢汉、刘湘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对共产党一直采取高压态势。从云贵川三省中共地下党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看,三省的地下党发展规模有限,组织活动主要集中于城市和县城;革命根据地的区域不大,常年战争,最后被迫转移;红军长征转战贵州、四川、云南边界地区传播革命理念,但并未建成稳定的根据地。在此环境下,西南地区农民的动员工作很难说是卓有成效的。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区域看,中共的工作中心也不在西南。因地理位置与苏联比邻,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东北、内蒙古、西北等地就一直是中共动员少数民族政治基础的重点。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所主导的蒙古民众抗战、将回民抗日武装收之旗下、对新疆民众的动员都是边疆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在川、滇、康、黔、桂等西南地区,除了少数族群上层的统战工作外,并无“激发少数民族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之举措*吴启讷:《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江海学刊》2015年第2期。。直至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前,云贵川三省的革命力量仍旧不强,时四川、贵州共有地下党员九千名,云南地下党员稍多,也是九千名,以及解放战争后期发展起来的两万人游击队,而西南人口达到七千万*邓小平:《克服西南工作困难要掌握好三个法宝(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6页。,革命力量比例仅为0.054%。1950年1月,中共贵州省委报西南局的《工作报告》中亦称,贵州“广大群众在过去革命锻炼较少”,“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贵州亦未形成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贵州省委:《工作报告(1950年1月9日)》,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贵州省档案局(馆):《建国后贵州省重要文献选编(1949-1950)》,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76页。。可见,解放前西南地区农村党组织力量薄弱,党员数量偏少,大部分农民并未直接感受到革命的力量。
最后,西南地区民族关系极为复杂,各地自成一方,互不相统,对执政党的认同度不高。将西南地区与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比较,封建王朝尤其是清朝更加重视后者,而对前者,因未对政权构成威胁,往往遭到忽视,比如苗族。对汉人而言,苗人不外乎落后与野蛮,加之汉人不断迁徒与侵扰,更加导致苗人生活的艰难与物质文化的落后。*谢辛芸:《近代中国苗族之国族化(1911-1949)》,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习硕士论文,2011年。即便如此,控制与反控制、模仿与拒斥一直是中央王朝与西南地区的主流关系。在此关系之下,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极为复杂。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汉民族和彝族的历史矛盾和隔阂,使得汉彝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受到很大限制,尤其是凉山地区,“汉人素以炎黄华胄自豪,四夷民族,即为蛮夷。而罗彝亦以曲布之子孙自傲,黄天贵胄,舍我无他”*马长寿著,李绍明、周伟洲等整理:《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上)》,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5页。,甚至出现了“汉到夷走”的情况*王文光、龙晓燕、陈斌:《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序言第11页。。不仅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十分低下,农民生活水平日渐贫困化。至解放前夕,西南少数民族仍保留着原始的生活状态。当时的民族学者岑家梧曾对西南地区这样描述:“过去政府施行了征讨羁縻的政策,迫使这些民族困处山地,社会经济,异常落后,渔猎、畜牧、锄耕的生产方法;图腾、氏族、奴隶等制度,至今仍然保存。原始的宗教巫术,支配了他们整个的生活。”*岑家梧:《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广州: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9年12月,序言。在这种情况下,对由汉人为主体组成的新政权,少数民族很难不抱有敌视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国家对民族地区的统战工作已经开始,但摇摆不定和敌视新政权的少数民族上层仍大量存在。从凉山地区彝族上层的基本情况看,彝族上层对新生政权的政治态度即是如此。比如威望很高、号召力强的花打木机对汉人仇视很深,素来就极不愿与汉人往来,甚至认为和汉人说话都是低人一等,如果靠拢政府,深恐其他家支说他投降汉人而削了自己的面子。*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乌抛日铁情况介绍(1954年1月31日)》,四川省档案馆:建川48-77。素来被称为打冤家能手的乌抛日铁因其父普果古哈曾于1929年带领彝民人枪千余,烧杀三河口及雪口山等汉人居住乡镇,解放后惧怕人民政府算老账(他认为人民政府是汉人政府),疑惮甚大,不肯外出。后受国民党周开富的影响,对新政权的态度由犹疑转变为对立。*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乌抛日铁情况介绍(1954年1月31日)》,四川省档案馆:建川48-77。在峨边小凉山彝族中威望甚高,被称“硬都都”的黑彝木干(汉名郝孝忠)曾于1950年和1951年两度与解放军发生军事冲突,后潜入凉山挖里挖,怀疑和恐惧心理十分严重,继而与峨边甘家克斯木切及马边乌拋家乌拋日铁等有威望的黑彝上层喝血酒盟誓,组织攻守同盟。*中共四川省乐山分工委办公室:《甘木干维谷情况介绍(1954年1月31日)》,四川省档案馆:建川48-77。可见,受西南地区复杂的民族关系影响,少数民族上层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并不高。
纵观解放前的大西南,游离于中央政府以外的政治结构和复杂的民族关系,成为此地区有别于它地的原因。为了增加西南地区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配合土地改革顺利的推进,诱发了西南土改工作队的派出。此外,在各种因素的考量中,也要注意到西南各地1950年年初的匪乱。在这次匪乱中,西南地区即有65万之众,占全国武装土匪的一半以上,邓小平甚至说“西南恶霸不当土匪,不搞武装斗争的很少”*邓小平:《1950年主要工作情况(1951年2月20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345页。。虽说这次匪乱的原因与征粮、禁银、禁毒的“三股水一起流”有关*王海光:《贵州接管初期征收一九四九年公粮问题初探》,《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3期。,但如此大规模的匪乱亦说明西南地区的民众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并不是很强,面对突然到来的新政权,很多民众都持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
二、卫生防疫的恶劣条件与工作队的派出
解放前中央政权对西南地区农村的控制力不强、中共在农村并没有广泛的基础、民族关系复杂以及对执政党认同不高只是派遣土改卫生工作队的内在因素,直接的原因还是卫生防疫的形势所迫。
解放前,西南地区农村的公共医疗状况极其恶劣,各种疾病广泛流行,尤其是性病、疟疾和妇女儿童疾病的蔓延,造成人口逐年锐减,严重威胁着西南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生存与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最普遍的疾病是肠胃病(因饮食粗劣)、风湿病(因衣服少房屋坏)、眼病(经常烤火)、皮肤病(劳动擦伤)和甲状腺肿大(缺盐或缺碘,西昌德昌县肿颈患者最高到90%);地方病也普遍存在,如藏族沿交通线的花柳、滇西滇南黔东南的疟疾。云南有30余县(主要在傣族)存在严重的疟疾,有83%的人血液里含疟疾虫,一般脾肿指数为64.97,疟蚊多至23种。1919年思茅原有6万人口,到1938年只剩1万余人。滇西1950年疟疾横行,有的地方严重到无人收割庄家的地步。云南患麻风病者约有3万余人。*《解放前西南少数民族的卫生状况》,《西南卫生》1951年第1期。云南边疆芒市等地被称为“超高疟疾区”,由于疟疾的流行,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有的村寨十室九空,芒市原有傣族5000多名,但到解放前只有1800多人。*沈其荣编:《民族工作手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6页。历史上曾有120万人口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解放前只剩20万人口。民众对这些地方极为恐惧,称之为“瘴疠之区”*李德全:《我国少数民族卫生工作》,《民族团结》1959年第10期。。婴儿死亡率极高,贵阳花溪某村15个妇女生了95个孩子,死了50个;黄平东坡乡25个妇女生了144个孩子,死了68个。一岁以内死亡的婴儿,普遍超过50%。*《解放前西南少数民族的卫生状况》,《西南卫生》1951年第1期。个人卫生习惯也极差,直至建国初期,贵州丹寨的少数民族农民仍长年喝生水,妇女头发用猪油擦而不洗。*贵州省土改卫生工作第五队六分队:《丹寨县土改卫生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5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贵州省从江县部分少数民族的饮器、碗杯、饭橧都积上一层垢膩,一年之中只洗两次,一次是6月6日,另一次是除夕。*《从江县人民政府卫生院1952年度卫生工作总结报告(1953年1月25日)》,黔南州档案馆:51-2-285。他们“生了病至多吃点草药,一般的依靠祭鬼念经来解决。山头(景颇族——作者注)、彝族、傈僳等族,生了病先杀鸡祭鬼;不好,再杀羊,杀牛,常常把家产耗尽,牲畜杀绝”*《解放前西南少数民族的卫生状况》,《西南卫生》1951年第1期。。苗族患病的民众普遍相信鬼师,一般用鸡鸭狗猪牛等祭祀,有着多年的历史,并演变为一种风俗习惯。*贵州省土改卫生工作第五队六分队:《丹寨县土改卫生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5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如此恶劣的卫生条件,不仅危害着西南民众的生命与健康,对土改工作人员也是一样,大理地区的一支土改工作队刚到农村不久,即全部病死于烈性传染病。缘此,土改卫生工作队呼之欲出。
1951年5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颁布了《指示》,正式要求各地派出土改卫生工作队,还特别强调了工作队发动群众和配合土地改革的目标指向,“深入发动群众,加速分配土地的改革,是西南区1951年的中心任务之一”,“各级人民政府都在为这一中心任务而努力”,因此“全区应大力发动各级医协组织土改卫生工作队,在各地土改工作团的统一领导下,以满足农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对医药卫生的迫切要求,保障农民健康”*《关于动员组织卫生工作者到农村去配合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西南卫生》1951年第1期。。《指示》强调发动群众和配合土地改革而派出土改卫生工作队,恰是客观环境使然,此举正好印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卫生防疫要面向工农兵的原则。在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提出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面向工农兵的方向问题、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问题、中西医团结的力量问题,其中面向工农兵是最基本问题,是卫生工作的唯一出发点。*《贺诚部长总结报告(1950年8月19日)》,重庆市医务工作者协会出版部编:《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重要文献》,重庆:重庆市医务工作者协会出版部,1950年,第57页。如何达到面向工农兵,派遣卫生工作队直达西南地区农村社会的最底层,或是最好的实践形式。
同时,派遣工作队也可弥补第一期土改工作之不足。在第一期土地改革中,包括17个整县、30个县的一部分以及3个市郊区(重庆、万县、南充)被涵盖在内,如以乡为单位计算,约有1512个乡(占全区总乡数的11.43%)13137733人(占全区总人口数的15.61%)参与了土地改革。*张际春:《西南区第一期土地改革工作总结》,《西南政报》1951年第12期。不过,在第一期土地改革中,问题颇多:贵州省镇远地委在“土改中群众发动不好,政策未为群众所了解、接受,群众情绪不高”*《中共镇远县委副书记吴肃关于第一期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贵州省档案馆编:《解放初期贵州土地改革档案文献选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7页。;清镇县“贫雇农阶层发动不好,组织上入会,政治上思想上未提高,最难发动的老帮工老佃户未能很好发动(占50%左右)”*《中共贵州省委关于秋收前第一期土地改革总结会议向西南局的报告》,《解放初期贵州土地改革档案文献选编》,第110页。;三类村中(如绥阳县桑木乡四村)贫雇农有很多尚未参加农协*《吴肃在贵州省秋收前第一期土地改革总结会议上关于斗争地主问题的发言》,《解放初期贵州土地改革档案文献选编》,第128页。;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土改中“本族内部团结很紧,有当匪的或是坏家伙都是包庇”*《蔺伐夫在贵州省秋收前第一期土地改革总结会议上对少数民族工作发言》,《解放初期贵州土地改革档案文献选编》,第124页。;划阶级时,有的少数民族认为“少数民族的地主是劳动地主”*《中共贵阳地位副书记常颂在贵州省秋收前第一期土地改革总结会议上关于第一期土地改革情况的发言》,《解放初期贵州土地改革档案文献选编》,第134页。。可以说,在决策者看来,西南地区的群众动员和第一期土改都存在很大不足。为此,邓小平要求“第二期土改必须做得更加仔细一些,宁肯做得少一些,不可使之粗糙”*邓小平:《土改、镇反工作必须做得更加仔细一些(1951年7月10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前揭书,第421页。。因此,西南卫生土改工作队从创建开始,就坚持秉承发动群众和配合土改的目标。
三、工作队的组建与实践
《指示》颁布以后,各地纷纷制定组建工作队的具体方案,进入实施阶段,比如《贵州省1951年下年度土地改革卫生工作计划》*《贵州省1951年下年度土地改革卫生工作计划》,《西南卫生》1951年第6期。、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卫生厅的《1951年下年度土地改革卫生工作计划(草案)》*《川西人民行政公署卫生厅1951年下年度土地改革卫生工作计划(草案)》,《西南卫生》1951年第1期。。土改卫生工作队基本按照军事化编制在整个大西南铺开。在贵州,设立了“土改卫生工作团团部”,在卫生厅厅长领导下,负责全面掌握、指挥、督促、坚持土改卫生工作的推行。“土改卫生工作团团部”下设11个“土改卫生工作队”,每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人,队员40-60人,且要求番号统一,一律用“土改卫生第×工作队”。其中,遵义为第一队、第二队,贵阳为第三队,安顺为第四队,独山为第五队,毕节为第六队,兴仁为第七队,镇远为第八队,铜仁为第九队,卫生厅组织第十队赴贵阳区,第十一队为机动使用。*《贵州省1951年下年度土地改革卫生工作计划》,《西南卫生》1951年第6期。土改卫生工作队下设若干分队。黔南地区(独山地委、第五队)下就设7个土改卫生工作分队,在土改县份每县设1个分队,分布于平越(1953年7月改为福泉——作者注)、麻江、三都、丹寨、都匀、平塘、独山等县。*《土改卫生第五工作队及分队工作计划》,黔南州档案馆:51-2-98。在土地改革初期,西南地区的基层行政网络并未广泛建立,此时进行军事化的单位设置显然有助于土改卫生工作的推进。
工作队组建以后,即围绕卫生宣传教育、防治传染病、训练初级接生员、创办卫生机构、保障土改人员健康等内容,在乡村社会动员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各项工作。
(一)宣传动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将根据地时期的宣传动员手段和方法快速植入到新解放区,很快取得了成效。工作队到达土改地区后,即着手调查环境卫生、疾病规模、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实际情况,并通过干部会、小组会、贫雇农会、民兵会、妇女会等各种会议进行卫生知识的宣传。麻江县第四区隆昌乡一至六村,共召开宣传大会18次、小组会162次、儿童姐妹会8次、妇女会5次,其中大会听众为1585人次,小组会听众为5100人次,儿童姐妹会听众为568人次,妇女会听众为230人次。*《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麻江)分队工作小结(1951年10月9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仅这6个村庄,就召开各种会议192次,听众达到7483人次。在隆昌乡七至十一村,亦召开了宣传大会、小组会、儿童姐妹会、妇女会183次,听众达7933人次。*《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麻江)分队七——十一村工作小结(1951年11月)》,黔南州档案馆:51-2-98。土改卫生工作队通过召开宣传会议、发放宣传品、张贴标语、讲演、家庭访问等多种形式,将卫生防疫思想传播到乡村社会的最底层。在独山专区第一期土改卫生工作中,丹寨县召开宣传会议80次,听讲人数11404人,发放宣传品7种214张,张贴标语184张,家庭访问618次454户;独山县发放宣传品90份,张贴标语90张;麻江县宣传162次;平塘县讲演16次,听讲人数4629人,张贴标语75张,发放宣传品110张。*《独山专署土改卫生工作队(第五队)第一期工作总结(1951年)》,黔南州档案馆:51-2-98。广泛的宣传动员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西南地区民众对新政权的敌视,起到了发动群众的目的。
针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的特点,工作队的宣传方式和策略灵活多样。麻江县第四区隆昌乡在会议讨论时采取漫谈的方式,如说笑话一样进行,群众不受拘束,可以随便发表意见。针对少数民族长期喝生水的习惯,隆昌乡农民提出利用竹筒盛开水带到山上去喝,还创造了用烤烟叶的烤枬和蒸饭的甑子来灭虱的办法。*《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麻江)分队工作小结(1951年10月9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由于工作队与少数民族之间存在语言交流的障碍,影响了宣传工作的正常进行,工作队创造了多种方式进行沟通。丹寨县的土改卫生工作队以会说汉话的少数民族作翻译,来与少数民族交流。*贵州省土改卫生工作第五队六分队:《丹寨县土改卫生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5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平塘县则让工作队人员学习一些简单的少数民族语言。*《平塘县土改卫生工作第三分队第一期工作总结报告》,黔南州档案馆:51-2-98。在宣传动员中,工作队还动员民众将卫生工作编成山歌来唱。麻江县第四区隆昌乡第五村农会主席田景光就创作了一首卫生歌:“土地改到长江村,卫生同志随时跟,预防人民身染病,宣传农村讲卫生,屋前屋后常打扫,妇女时时记在心,早上起来须洗脸,头上头发要理清……”*《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麻江)分队工作小结(1951年10月9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西南地区流行的金钱板*金钱板是流行于四川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形式,它的唱腔是前辈艺人在川剧高腔一些曲牌的基础上加工、改革而成。早期(清代)的演出方式都是“跑乡场”、“扯地圈”。后来进入茶馆、书场演唱,逐渐流传到云南、贵州两省。也被用来作为宣传媒介,在《歌唱两年来的西南卫生建设》(金钱板)中就有这样的唱词:“土改卫生意义长,卫生人员同下乡,双重任务要担当,治病给药搞预防。”*重庆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委会、新中国科学建设成就卫生宣传计划委员会编:《新中国卫生建设成就·宣传资料汇辑》,内部资料,第47页。灵活多样的宣传形式成为土改卫生工作队与西南民众的沟通交流的重要途径,也为新政权其它政策的推行提供了群众基础。
(二)组织动员
组织动员也是卫生土改工作队实践的重要内容,通过新型的组织网络可以改造原有社会关系、重组社会结构,并再造农村社会基础。在近代西南农村,基层卫生组织十分薄弱。1938年贵州省开始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1943年县级建立医院达到78家,不过乡村级的医院几乎没有。*吴鼎昌、贵州省政府编印:《黔政五年》(1943年),第94页。因此,在土改卫生工作中,贵州省独山地委将“建立区乡村群众性基层卫生组织”视为土改卫生工作队的重要内容。*《土改卫生第五工作队及分队工作计划》,黔南州档案馆:51-2-98。实际上,正因土改卫生工作队的存在,才使部分地区建立了新型的卫生组织。川西平原西部边缘岷江中游的灌口区(灌口镇)卫生协会,就是1951年在土改卫生队的协助下建立的。*《灌口镇志》编纂组编:《灌口镇志》,内部资料,1983年,第177页。
在土改卫生工作队的帮助下,农村基层逐渐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卫生组织机构,并以此为中心,汇集大批乡村权威人物,进而将乡村社会的多数人纳入其中。丹寨县杨武、金钟两乡的基层卫生组织由村卫生委员会和卫生小组构成,行政村的卫生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由农协主席兼任行政领导,副主任委员1人,专门负责业务领导,下设卫生员1至2人,防疫委员1人,宣传委员2人,调查统计委员1人,文书委员1人,一般以行政村的分布大小来决定人数的多少;卫生小组是自然村及行政小组为单位,在卫生委员会的领导下每组或自然村为单位选举组长1人,副组长1人。杨武、金钟两乡共组建了16个行政村的卫生委员会(共有卫生工作人员145人),73个卫生小组。*贵州省土改卫生工作第五队六分队:《丹寨县土改卫生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5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在基层行政组织尚待完善的情况下,卫生委员会和卫生小组成为新型乡村政治权威的汇集地,村卫生委员会聚集了乡村社会中的主要骨干,卫生小组则要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每户都要参加。在麻江县,村卫生委员会由农会主席、妇女会主席、学校校长、当地卫生工作者及当地热心卫生工作的积极分子、儿童团长、姐妹团长等充任。卫生小组的组长由行政组长兼任,副组长则选组内热心卫生工作的积极分子充任,每户指定1人为卫生组员。*《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麻江)分队工作小结(1951年10月9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在独山专区第一期土改卫生工作中,工作队帮助各土改地区普遍建立了基层卫生组织,共计建立1个区卫生委员会,31个村委员会,216个卫生小组,这些基层卫生组织为卫生防疫步入常态化提供了基础和准备。*《独山专署土改卫生工作队(第五队)第一期工作总结(1951年)》,黔南州档案馆:51-2-98。在这些卫生组织中,汇集了以乡村干部为核心的新型乡村政治权威,再由他们将农村中的家家户户组织起来,共同组建了一张乡村卫生网络。
(三)实践动员
第一,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的治疗为西南农村民众提供了生命和健康的保障,拉近了国家与西南农村民众之间的距离。1951年,在丹寨县杨武、金钟两乡均发现了麻疹、天花、麻风病、天花等传染性疾病。在杨武乡的瓦厂村和金钟乡的小羊村,工作队到达时恰逢麻疹流行。因此,土改卫生工作队将麻疹、天花、麻风病等疾病作为重点进行诊治,讲解了霍乱、伤寒、疟疾、回归热等传染病的预防方法。针对金钟乡数十年来从没有中断过麻风病的情况(金钟乡有麻风病8人),土改卫生工作队采取了隔离的办法。交圭行政村也在工作队讲解麻风病的传染途径后,决定替麻风病人在深山里造一间房子,把他们迁移在里面(村民愿意供给他们粮食,但是不准麻风病患者出来,这也得到了病人的支持)。此后,羊甲小村、羊甲大村、排谈村等有麻风病者的村落均照此方案进行隔离。*贵州省土改卫生工作第五队六分队:《丹寨县土改卫生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5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在土改卫生中,工作队治愈了大批传染病和地方病的患者。麻江县第四区隆昌乡一至六村共治疗164人次,其中麻疹肺炎30人,痢疾24人,疟疾35人,肠炎31人,百日咳9人,外伤3人,感冒8人,其他24人。*《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麻江)分队工作小结(1951年10月9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黔南地区在第一期土改卫生工作中,共治疗各种疾病2957人次,其中都匀739人次,麻江164人次,三都227人次,丹寨742人次,独山426人次,平塘659人次。*《独山专署土改卫生工作队(第五队)第一期工作总结(1951年)》,黔南州档案馆:51-2-98。
对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的有效治疗,有利于增强民众对执政党的认同,大量典型实例的言传身教更有助于民众的接受。柔远村六十多岁的杨老太因去女儿家,被传染恶性疟疾,病的很重,被人抬回来,儿子都已经买好棺木衣服等准备后事。土改卫生工作队闻讯后赶到,经过一天一夜的诊治,杨老太病情得以转好。六七天后,完全康复。她指着门前放着的棺木对村民说:“如果不是人民政府毛主席的领导,为我们人民做事,我早就在那里面去睡了。”*贵州省土改卫生工作第五队六分队:《丹寨县土改卫生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5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羊浪行政村长王国思的妻子生孩子六小时,胎盘都没有下来,用鬼杀猪狗鸡鸭以后,仍未解决问题。土改卫生工作队赶到后,当即给她取出,并告诉他们胎盘不下来的原因,说明消毒接生的好处。之后王国思结合他家的事实逢人便讲:“现在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了身,分了田,还要我们讲究卫生,现在如果不是卫生同志下乡,我也没有儿子,老婆恐怕用鬼早就用鬼完了。”*贵州省土改卫生工作第五队六分队:《丹寨县土改卫生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5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塑造典型以其运作成本低、生效快等优点,适应了当时宣传的需要,更以情感教育和心理动员为特色,将“思想教育”蕴含于其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各项宣传和实践的重要法宝。
第二,种痘员和接生员的培训不仅为西南农村卫生工作提供了人力支持,还能有助于为国家培养社会主义的卫生队伍。由于缺乏种痘员和接生员,西南地区的婴儿死亡率很高,都匀县第三区基长乡平定村在调查时发现,此地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该村有母亲140人共生产婴儿778人,但死亡436人,死亡率达到56%。*《独山专署土改卫生工作第五工作队第五分队总结报告(1951年9月20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丹寨县杨武乡莫文英、肖功琴、朱月英、李兰英、马文熙妻子都有小孩死于脐带病,她们得知土改卫生工作队培训接生员后,主动找到队长要求学习。*贵州省土改卫生工作第五队六分队:《丹寨县土改卫生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5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在接生员培训讨论会上,女学员石文风说:“我生了六七个小孩,都是坐板凳生的,生出来都滚在地上,有三个几天就死了,现在卫生工作同志教了我们新法接生,我回家去一定要他们用新法接生。”*《独山专署土改卫生工作队(第五队)第一期工作总结(1951年)》,黔南州档案馆:51-2-98。麻江县第四区隆昌乡第一村第四组妇女张妮氏生了病找人打瓦针(用碎碗碴刺患处,放淤血——作者注),正值土改卫生工作队女同志去做妇幼卫生调查,给她药后就病愈了,不久她就参加了接生员的培训。土改卫生工作队利用张妮氏这个实例做宣传,加之张妮氏也主动参与,使得该村群众很快认识到打瓦针、用神用鬼都是不科学的,只有吃药才是最好的治疗方式。*《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麻江)分队工作小结(1951年10月9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培训的种痘员和接生员为西南农村防治天花和提升婴儿存活率提供了人力支持。
同时,这些新培养出来的种痘员和接生员很快成为社会主义卫生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在对新式接生方法的认同,而且其政治思想与新政权也日渐吻合。1951年4月4日,政务院批准和颁布的《卫生部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的决定》曾要求“各地专署与县(市)人民政府在条件许可下,应开办初级卫生人员训练班”,“作为工矿农村的基干队伍”*《卫生部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的决定》(1951年4月4日政务院批准,同日公布),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编:《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1年)》,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593页。。显然,西南土改卫生工作队在培训种痘员和接生员时也是基于此方面的考虑,所以在培训中特别注意种痘员和接生员的年龄,工作队规定种痘员在16岁至35岁之间,接生员在25岁至40岁之间。种痘员和接生员的年轻化既有助于快速的学习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容易接受新政权的理念和主张。期间,麻江县第四区隆昌乡一至六村共训练接生员36人,种痘员34人。*《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麻江)分队工作小结(1951年10月9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根据相似的方法,隆昌乡七至十一村共训练接生员45人,种痘员49人。*《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麻江)分队七——十一村工作小结(1951年11月)》,黔南州档案馆:51-2-98。在第一期土改卫生工作中,都匀、麻江、三都、独山、平塘等五县总计训练种痘员323人,接生员256人。*《独山专署土改卫生工作队(第五队)第一期工作总结(1951年)》,黔南州档案馆:51-2-98。这些种痘员和接生员成为新中国卫生人员中的“基干队伍”。
第三,公共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改善不仅被视为现代文明的发展,也可看作国家权力对个人自由的触碰。西南地区农村公共卫生环境和个人环境普遍落后,丹寨县杨武乡和金钟乡90%以上少数民族的居住方式是人畜杂居;村寨里污水塘堆积垃圾,长达数年之久;水井多半不合卫生条件;厕所过少或者没有,仅有的厕所也是距离厨房太近。*贵州省土改卫生工作第五队六分队:《丹寨县土改卫生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5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土改卫生工作队在动员群众的基础上,对村寨公共卫生进行了整治。他们发动群众进行大扫除,从事打扫室内外、清洁铲除路边的杂草、迁移厕所、整修水井等工作。杨武、金钟两乡共清理垃圾1959挑,厕所加盖191个,厕所迁移66个,水井修理44个,水沟修理31个,水塘改善8个。*贵州省土改卫生工作第五队六分队:《丹寨县土改卫生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5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麻江县第四区隆昌乡一至六村参加清扫的农民达到632人,共清理垃圾数1387市石,迁出牛粪715市石,清理水井6个,铲除青草67丈,填塞污水池塘2个,疏通阴沟76个。*《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麻江)分队工作小结(1951年10月9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隆昌乡七至十一村参加清扫的农民达到555人,共清理垃圾数500市石,迁出牛粪550市石,清理水井15个,铲除青草100丈,填塞污水池塘10个,疏通阴沟46个。*《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麻江)分队七——十一村工作小结(1951年11月)》,黔南州档案馆:51-2-98。在独山专区第一期的土改卫生工作中,麻江县共清洁大扫除垃圾1957市石,清扫牛粪715市石,改良水井6座,疏通阴沟46丈;丹寨县共清洁大扫除垃圾1959市石,改良厕所157座,水井修理41座,水沟修理31条,水塘改善8个;平塘县共调查厕所194座;独山共清洁大扫除垃圾6338斤。*《独山专署土改卫生工作队(第五队)第一期工作总结(1951年)》,黔南州档案馆:51-2-98。公共卫生环境和个人卫生的改善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发展。
不过,这种现代文明的发展也使得国家权力触碰了个人自由,个人逐渐陷入国家的监控之下,比如喝生水的问题,少数民族一直有此习惯,不过在工作队的劝导之下,麻江县第四区隆昌乡的民众逐渐认识到喝生水的坏处,普遍开始喝开水。*《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麻江)分队工作小结(1951年10月9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从饮水卫生的角度看,喝开水肯定有助于身体的健康,但从个人自由的角度看,行政的干预却直接影响了民众的生活习惯。家庭卫生也是如此,丹寨县金钟乡柔远村50多岁的雇农王老太,首先自己搞好了家里的卫生,之后带头动员本自然村其他农民,耐心地讲解,“毛主席为我们好,叫我们讲卫生,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做,大家都减少病,生产也才好,对得起毛主席”,经过他带头及耐心的宣传,全村每家的室内外均打扫的十分干净。*贵州省土改卫生工作第五队六分队:《丹寨县土改卫生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10月5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将家庭卫生与生产劳动,甚至与“党中央毛主席”联系起来,卫生与政治的关系一览无遗。
从土改卫生工作队的组建看,其本身就是具有军事组织的性质,目的是借助于军事化的单元设置以求快速迅捷的推行。从土改卫生的实践看,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和策略,较为完善的卫生组织机构,保障民众生命和健康的疾病治疗,种痘员和接生员的培训,公共环境和个人卫生的改善都使得土改卫生工作队的成效斐然。据统计,独山专区土改卫生工作队第五队分别在都匀等7个土改县开展土改卫生工作,三个月共治疗病人2957人,培养训练种痘员323人,接生员246人,建立基层卫生委员会284个,卫生小组647个。*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卫生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页。1952年底,西南地区“89%以上的县份有了县医院,15.8%的县属区有了卫生所,联合诊所也建立了1000多个”*《西南区三年来工作的成就》,重庆:西南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05页。。在土改卫生工作队的配合下,西南地区第二期和第三期土地改革最终顺利完成。第二期土改于1951年6月开始,到9月底结束,参加地区有50个整县,105个县的部分乡以及2个市的全部郊区,合计28645个乡,占全区总乡数19.31%,土改地区人口24845073人,占全区总人口数26.07%。*四川省档案馆编:《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1949-1954)》,内部资料,2000年,第141页。第三期土改于1951年10月开始,到1952年6月结束。加上第一期和第二期土改,全区共完成12000个乡7300多万人口(占西南地区总人口超过81%)。*四川省档案馆编:《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1949-1954)》,内部资料,2000年,第178页。第三期土改的完成,标志着西南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
四、结 语
坚实的政治基础有助于卫生疾病的有效防治,卫生防疫也能促进民众的政治认同,两者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1951年下半年创建的土改卫生工作队即具有促进政治认同的功能,其所从事的宣传动员、组织动员和实践动员有效改善了历代中央政府在此区域直接管理不足的问题,夯实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增强了少数民族对国家和执政党的认同。从土改卫生工作的组建开始,独山专区特意将“医务工作者必须大力配合土地改革这个政治中心任务”写入《土改卫生第五工作队及分队工作计划》中。*《土改卫生第五工作队及分队工作计划》,黔南州档案馆:51-2-98。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麻江)分队在1951年8月13-15日的集中学习时也强调:“土改卫生工作队不是单纯的治病”。*《独山专区土改卫生第五工作大队第二(麻江)分队工作小结(1951年10月9日)》,黔南州档案馆:51-2-98。中共中央西南局卫生部在制定工作队方案和规划时,还明确规定各工作队以救治一两种疾病为主,“参加扑灭当地流行病及治疗足以妨碍土改的多发病”,“治疗病类力求专一,有重点的治一两种妨碍土改或生产的病和疫病,否则治不胜治反而失去应有的作用”*《关于动员组织卫生工作者到农村去配合土地改革工作的指示》,《西南卫生》1951年第1期。。此类论据大量存在于文献之中,甚至土改卫生工作队员也要亲身参与到土改中,比如黔南地区的土改卫生工作队就做了大量协助查田评产、划阶级的工作。*《独山专署土改卫生工作队(第五队)第一期工作总结(1951年)》,黔南州档案馆:51-2-98。
实际上,国家权力在西南地区的推进充满着艰辛与险阻,1949年底出现的大规模匪乱即是明证。因此,在国家权力渗入基层社会的过程中,用相对柔和的手段和策略,更容易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相处。1950年5月,邓小平在复电西康区委时指出:“目前切不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企图去进行政治的或经济的改革事宜,但你们应该指示贸易机构在进行与彝区的贸易工作中使彝民获得好处,及教育卫生部门能与彝民治病等,这将大大帮助对于彝民的团结与争取。”*《关于做好彝民工作的意见(1950年5月12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第144页。1950年7月,他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也强调:“在当前来说,文化工作首先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卫生工作作用很大。”*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前揭书,第200—201页。在土改卫生工作队进入农村后,他们通过卫生宣传、建立组织,将农民普遍动员起来进行传染病和地方病的治疗,集中起来进行种痘和接生的培训,组织起来进行公共卫生的扫除,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培养了农民的政治热情,增强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绵阳专区的干部说:“我真想不到农民欢迎卫生人员比欢迎土改人员还热烈。”*何正清:《大力组织医务工作者到农村配合土地改革,开展卫生防疫建立卫生组织的基础》,《西南卫生》1951年第4期。相对于疾风暴雨式的土地改革,从医疗出发的土改卫生工作队显然更容易为农民所接受。
需要说明的是,西南地区的土改卫生工作队只是临时性的组织,它在西南的卫生实践未使农民形成一种自觉性的卫生习惯。其实即便是后来的爱国卫生运动都未达到彻底清洁农村之目的,农民的卫生习惯并不会随着运动型的卫生治理而改变,卫生治理的更大作用可能是以改善环境为契机,发动群众,稳固政治基础。同时,随着现代化卫生行政的建立,国家对农村医疗卫生介入的程度也在逐步加深,虽然国家已意识到,但并未停止卫生制度隐含的这种权力关系,而是建立起了严格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这一点在现代卫生医疗体系中依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