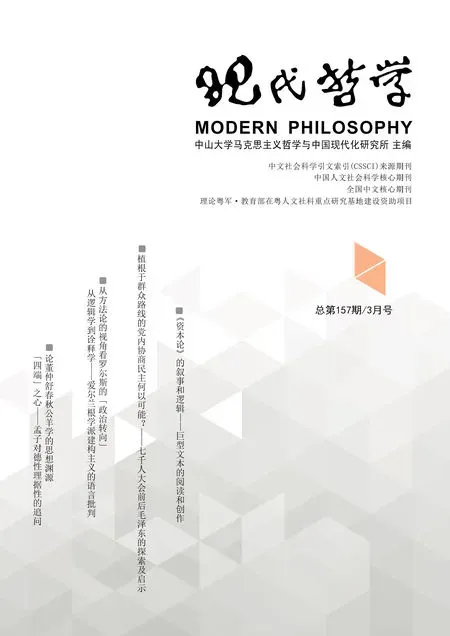重申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柄谷行人的经济学-哲学理论
周 阳
一、引 论
尽管作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批判理论家,柄谷行人在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文学研究领域受到普遍关注,但是由于国内研究者很少从柄谷文本的内在逻辑出发去系统地考察其理论体系,因此出现了不少脱离语境的批评。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柄谷思想来源的博杂性是造成我们误解柄谷的一个重要因素。柄谷有很深的日本宇野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背景,他对马克思的许多理解(譬如对价值形式论的诠释)直接来自宇野弘藏。其次,柄谷在不同时期又不同程度地卷入与几乎所有当代重要激进思想家(德里达、福柯、拉康等)的思想对话,这也导致我们不能准确把握柄谷思想的轮廓。再次,柄谷在借用前人思想资源时其实已加入自己的理解。例如,柄谷对价值形式论的简化,虽然在宇野学派内部颇受非议*柄谷从流通论中直接引出“信用论”的做法,更接近宇野派中小幡道昭一系的主张,但这并不为山口重克等人所接受。;柄谷的四种交换方式论,虽然处处都有拉康《研讨班17:精神分析的另一面》中“四种话语”论的影子*拉康在那里明确指认了剩余快感与马克思剩余价值的关联,并且和柄谷一样批评资本家是只进行购买而不支付代价的人。,但在对精神分析基础概念的理解却与拉康有不小差异。最后,柄谷非但常常抱有这种“六经注我”的态度,更不惜以今日之我非难昨日之我。例如,他从《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时期的解构主义的门徒,变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时期的福柯派拥趸,再变为《跨越性批判》时期更贴近拉康化风格的理论斗士。柄谷这种多变的思想立场,的确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更为丰富多样的视角,但也确实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
本文之所以主张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去理解柄谷《跨越性批判》中“重建共产主义形而上学”,也是考虑到了上述这些因素:尽管像巴迪欧、朗西埃、奈格里、齐泽克等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一样,柄谷重建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论旨趣也是试图建立更为普遍的政治联合,对抗资本主义的专政,但柄谷将政治经济学作为其共产主义论的基础,这种更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使他与其他人的工作具有鲜明区别;而相比于他自己在其他文本的论述,柄谷的共产主义论在《跨越性批判》中得到最为充分的展现。
二、柄谷对“劳动价值-形而上学”的批判
柄谷的工作是对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重建”,在这之前的首要工作,就是对旧有的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拆解。柄谷指出,旧有的共产主义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是最普遍的联合,即劳动生产者的联合,所以其理论基础就是传统理解的那种“劳动价值论”,即认为商品无须藉由交换就具有价值。在他看来,传统劳动价值论不仅在理论上违背了马克思的教导,而且在现实当中被革命实践无情地证伪了。
柄谷指出,这里的首要问题在于廓清马克思的价值论到底是指什么。在柄谷看来,马克思的主张是“一个商品只有被其他商品所交换才可能有其价值”,“商品首先对他人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否则不成其价值”,也就是说“马克思重视的是使用价值”*[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赵京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53页。,更准确地说是商品交换当中的使用价值-经验,即这种使用价值-经验必须包括“对他人的使用价值-经验”在内。这种交换当中的使用价值的经验是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成立的必要条件。因此,传统劳动价值论被柄谷轻而易举地排除在马克思的价值论之外:传统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根据在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时间”,这种劳动时间是在商品交换之前就已经确定下来的;而在商品交换给他人之前,其使用价值是根本不可知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商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2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3页。转引自[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152页。。在柄谷看来,传统劳动价值论其实还停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水平上,恰恰是为马克思所批判的东西。
可能有人会认为,即使传统劳动价值论可能不大符合马克思本人的理解,但由于它将价值的根据安置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时间上,而这种劳动时间是可以不受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影响的,因此它具有普遍性的优点。对此,柄谷指出,就传统劳动价值论不依赖于使用价值-经验而言,它的确具有普遍性的、形而上学性的品格;但是,由于传统劳动价值论将商品交换的问题排除在外,于是就脱离了“社会性”的领域,而只有在“社会”当中,才能讨论真正的普遍性*[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154页。。即使在在劳动时间的问题上,也只有进入社会交换领域,才能讨论对价值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否则就只能是某一经营体内部的劳动时间,它并不比某一商品的使用价值更具有普遍性。因此,就真正的形而上学必须是普遍性的而言,传统劳动价值论即使算一种形而上学,也只能是一种武断的形而上学。
在柄谷看来,如果说这种理论上的批判还并不能说服所有人的话,那么建立在传统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旧共产主义论及其实践即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也该为人们敲响警钟了:苏东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与违背马克思的教导、严重忽视使用价值、忽视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并不是没有关系的。
三、柄谷对“使用价值-经验论”的批判
在柄谷看来,仅仅诉诸使用价值-经验同样不能为理解经济现实提供出路。柄谷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商品理论就是试图从使用价值-经验论出发推导出一切经济范畴,而物物交换——物品所有者通过对商品的使用价值-经验(即效用)的衡量、排序建立起交换的尺度从而展开交换——就是这种商品理论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新古典经济学归为某种使用价值-经验论。但柄谷指出,如果接受使用价值-经验论的前提,则物物交换在逻辑上是无论如何不能成立的,因为要求这物品持有者在交换之前,不仅要对他自己手中的物品的使用价值有经验,还必须对他将要交换到的、他人手中的物品的使用价值有经验。但所谓对一物品的使用价值的经验,在享用该物品之前是无论如何不能获知的。因此上述两个条件显然是荒唐的:交换之所以是可能的,前提就是双方都不使用自己手中的物品;而交换之所以是必要的,前提就是双方在交换前都不能使用对方手中的物品。更重要的是,物物交换在经验上也没有验证:“商品的关系体系并非各种商品直接发生关系,而是由和一般等价物的一商品之关系构成的。”换言之,根本不存在不以货币为中介的“等价交换”关系:“所有的商品只有在货币的媒介之下才能相互产生关联。”经济事实与这些使用价值-经验论者所说的恰恰相反,“实际的市场中买卖并非同时进行的,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通过将货币当成本钱”,买与卖是分离的,商品并不是“直接”与另一个商品发生关系,而是“首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仅仅”与货币发生关系。*[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162、163页。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是现实中唯一存在的交换经验。
物物交换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它在经验上是得不到验证的。因此,使用价值-经验论者建立在物物交换基础上的交换论根本不能成立,而就使用价值-经验论者对经验(即不存在物物交换,而只存在商品与货币的交换)之“视而不见”而言,他们只能算是伪经验论者。
这些伪经验论者为掩饰自己在理论上的窘境,也曾乞灵于康德哲学:对于将要交换到的、他人手中的物品的使用价值,对于这种未发生的事实,我们是无论如何不会有经验的。伪经验论者不愿承认他们的失败,于是搬出“习惯”概念。他们认为通过“习惯”,就能对这种未发生的事实有所经验,甚至自作主张地给这种“习惯”套上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使用的术语“共通感”。柄谷甚至指出,阿伦特、利奥塔、哈贝马斯等人之所以把“回到康德”狭隘地理解为回到《判断力批判》的康德,也是出于上述目的。但伪经验论者始终无法自圆其说的是,“习惯”无论如何都只是过去的事实,它与未来毫无关系。
柄谷把这种伪经验论的立场称为“策略性”的立场、相对主义的立场:它只关注的自己的、特定的经验,而不关注他人的经验,这种相对主义本身其实是违背经验论原则的。但是伪经验论者由于相信只有自己才真正关注了经验,反而更坚信这种“策略性”立场才是“实践性”立场、“现实性”立场。柄谷指出,由于伪经验论者不关注他人的经验,却又不得不承认他人的经验也是现实的一部分——他们之所以求助于运用“共通感”概念,就是因为他们也承认他人的存在——所以,伪经验论者的“策略性”立场其实并非“实践性的”,而是“非现实”的,即 “思辨性”的。
就一般意义所理解的“思辨性”是指与现实无关而言,“思辨性”立场本身与现实是不会产生关系的,也就谈不上对现实有危害了。事实上,即使伪经验论的理论本身破产了,伪经验论者本人还是在从事商品与货币的交换活动。因此,在柄谷看来,对交换过程给出真正合理的解释,一方面是理论上对交换论的机制加以澄清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一种实践的要求:解释伪经验论的交换论这种理论上根本是错误的理论,在现实中仍然能产生影响、造成危害的原因。
四、柄谷对“货币-信用-经验论”的批判
正如柄谷在对使用价值-经验论的交换论的批判中所指出的,现实交换过程是且仅是物品与货币的交换。柄谷提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物品与货币交换中的经验并不是对物品的使用价值的直接经验,而仅仅是一种信念、一种“相信”,“相信”我们有对物品的使用价值的经验。建立在“相信”-经验之上的经验论才是真正的经验论。
关于这种建立在真正经验论基础上的交换论是如何运转的,柄谷给出了自己的说明。这种交换论的逻辑是这样的:第一步,物品的持有者对他手中的物品的使用价值并没有直接的经验,但他“相信”它具有使用价值。我们可以把这一位物品持有者称为A,把他这一环节的“相信”称为“相信1”。第二步,货币的持有者“相信”A手中物品的使用价值会与另一位物品持有者手中物品的使用价值相等,即他“相信”等价交换这一事实“应当”存在。我们把这一位并没有直接登场的物品持有者称为B,把货币持有者在这一环节的“相信”称为“相信2”。第三步,货币持有者希望A也“相信”“相信2”,为此他向A提供了保证,也就是他手中的货币。第四步,A“相信”了“相信2”,接受了货币,同时也交出了他手中的物品。我们可以把这一环节A的“相信”称为“相信3”。整个交换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第四步,因为“相信3”的成立根本不需要任何经验上的保证,也不可能存在经验上的保证——A不可能对货币持有者手中的货币的使用价值有直接经验——“相信2”根本只是“相信3”自身预设的内容而已。
可见,在柄谷的解释中,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交换实际上仅仅是一种信贷关系,货币仅仅是一种信贷的凭据:对于A来说,货币是否具有使用价值根本无关紧要,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明明知道货币的物质形态在流通中会损耗*甚至有的货币根本就不具有“物质形态”,譬如电子货币,它仅仅是账户上的虚拟数字。,还是仍然当它是足值的在使用。在整个过程中,只有“相信1”、“相信2”与“相信3”相互之间的信贷关系,使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从未出现;商品与货币之间的信贷关系所保证的,就是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直接交换未来一定会发生,而且他把这种“相信交换某种将要发生”当成“交换已经发生”。
真正的经验论者用商品与货币的信贷关系偷换掉了商品之间交换关系,柄谷认为这一“信以为真”和康德论证知识的普遍性的逻辑是一致的:1.经验是知识成立的必要条件; 2.而普遍性顾名思义就是指在无论何种时空条件下都存在的性质,具体地说,现在存在,过去存在,未来也要存在;3.但是,就经验是总是主体在事实发生过之后对该事实的感知而言,主体对未来的事实根本不可能有经验;4.所以,知识的普遍性本身不可能靠经验来保证。真正能保证知识的普遍性的是信仰,或者说所谓“理论之信”*[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21—23页。:信仰不是妄想,妄想是无事实根据的想象,而信仰是一种“相信”,“相信”未来的事实会发生,并将此“相信”本身计入已知的经验中,简单地说,就是把“相信”某事实未来会发生当成该事实已经发生。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的普遍性得到了保证。用康德的话说,货币既非一种可直接经验的实体,也不是对经验的事后记录,货币“是通过货币交换对所有生产物的价值关系进行调整的东西。因此,货币乃是作为所有商品的关系体系之体系性,即超越论统觉X而存在着的”,货币即所谓“超越论假象”(“信仰”)。*[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261页。正是通过作为“超越论假象”的货币,商品体系全称命题得以成立:商品体系的普遍性恰恰是通过货币来保证的,因为主体正是通过货币将未发生的交换当成已经发生了的交换,由此建立了交换的“一般性”,即交换的普遍进行。
更重要的是,在柄谷看来,尽管这种以真正经验论为基础的交换论揭示了交换的现实运作机制,但这种揭示仍然有其局限性,即它并没有揭示出上述现实运作机制自身的界限:通过将未发生的事实当成已经发生的事实这样一种“相信”的机制,交换过程的“一般性”得以成立,这种“一般性”扮演了“真正的普遍性”的替代物。所谓“真正的普遍性”是指必须“如期所是”地面向每一个事实本身,把未发生的事实当成未发生事实本身,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就是面对商品之间的直接交换从未发生这一事实*[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三章3.单独性与社会性。。但这种扮演并不是每次都成功:当“资本家手中的已被生产出来的商品”与“被雇佣者手中的货币”的交换时,这一交换总是充满了危险,一旦失败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182—183页。
五、柄谷重建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工作
在柄谷看来,只有那种把交换的现实运作机制及其界限都考虑在内的理论才算是真正普遍的交换理论,也只有这样的理论才可以算是真正的交换的形而上学,即建立在普遍性经验之上的交换理论。他进一步指出,要重建这种形而上学,首先就要像康德那样将“个别性-一般性”与“单独性-普遍性”这两对概念区分开来。
个别性与一般性之间并不能直接相互转化,转化如果要实现还需要一种中介机制,即“相信”的机制:1.个别性向一般性的转化:某一个体通过将对其他个体的经验的“相信”、超越论假象直接转化为其他个体的经验本身,从而建立起诸个体之间的一致性、普遍性。柄谷指出,德国浪漫派、黑格尔主义者的民族国家理论正是上述一般性理论在政治哲学上的反映:民族国家(nation)并不单纯是上层建筑,不是对经济事实发生后的观念记录,即不是对经济基础的机械反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论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表象(观念),它是靠教育和文学等来强化的,这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理;更重要的是,民族国家作为表象来说,它与货币的运作机制是同构的,也是一种“超越论式的假象”*[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62、167、241—242页。,或者更准确地说,民族国家形成就是货币交换的产物。2.一般性向个别性的转化:某一个体认为在自己的“相信”、想象中就能把握其他个体的经验,因此真正去面对其他个体的经验就显得不必要了,由于有了这种“相信-现实”机制的保障(更具体地说,就是民族国家的保障),伪经验论者才心安理得地呆在他们的“思辨性”立场上,为他们自己的特殊经验辩护。这自然无法撼动现实的秩序,因为伪经验论者的“思辨性”立场本身就是现实秩序的一部分。例如,柄谷所提到的“新社会运动”(“女性、同性恋者、特殊/少数族群等运动”),就因诸运动本身对特殊性的强调,而陷入相互对立的境地。这样,拒绝中心化和被别人代表的运动,不是被民族国家权力之一翼的政党所代表,就是只能停留在不痛不痒的抵抗上。*[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267页。
与“个别性-一般性”的逻辑相反,单独性和普遍性的相互转化是直接的。在单独性和普遍性之间,即单一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不存在“相信”机制,不存在超越论假象,个体之间直接交往,这种直接交往状态才是真正的普遍性。*[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60—62页。这种普遍性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物品之间的互酬交换。互酬交换不同于商品交换:商品交换的标准是建立在对物品使用价值的经验上的,但在商品交换中,人们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能直接享用物品,一方面个体不能享用自己手中的物品,而只能“相信”这一物品能被享用;另一方面在交换时,个体也不能真正享用他人手中的物品,因为他也只是“相信”他人也“相信”自己手中的物品能被享用。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都被一种“相信”所隔断。与之相反,互酬交换则将人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障碍彻底打破了:互酬交换一方面是一种纯粹的赠予,作为一种赠予它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以“相信”机制为基础的算计,这种算计就是把他人当成我,而不把他人当成他人本身;另一方面互酬关系也取消了人与物之间的障碍,被赠予者可以真正享用他的物品,当然,所谓真正享用就是指普遍享用,即与他人一起享用,这还是赠予。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赠予才能成为相互赠予,才符合所谓互酬的定义。在柄谷看来,这种互酬交换就是共产主义了:共产主义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普遍交往。
在柄谷看来,互酬交换并不是空想理论,它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的运动。首先,这种互酬交换的原始形式在商品交换之前就已经存在,柄谷将之命名为交换形式A,使之与作为商品交换的交换形式B相区分。再者,在商品交换出现之后,这种互酬交换也没有被商品交换所彻底瓦解,它仍然残存于家庭、共同体之中,作为对商品交换的消极限制而存在。商品交换“不能使家庭市场经济化,而只能依存于家庭。另外,农业等也是无法彻底资本主义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有关人和自然的生产方面,仍然只能依靠家庭和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本是以非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因此,不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全球化了,这些形态还残留着”*[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169页。。更为重要的是,互酬交换反过来还能作为对商品交换的积极限制而发挥作用,即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构成因素而存在。当“资本家手中的已被生产出来的商品”与“被雇佣者手中的货币”的交换时,商品与商品的使用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即不能被“相信”关系所统摄)就直接暴露出来了,一旦作为消费者的工人普遍地拒绝购买,则整个商品交换体系就崩溃了。最后,通过拒买克服商品交换之后的、新的互酬交换,就是柄谷所认为的共产主义的交换形式。这种新的互酬形式的主体在拒绝购买资本家的商品时,已经将商品交换中人的复杂性考虑在内,即理解“相信”并非单纯的幻想,而是现实的运作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抵制“相信”机制。这种考虑其自身的复杂性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在这点上它不同于交换形式A中那种原始的人(原始的人并没有考虑到“相信”机制运作的条件),这种真正的人的联合才是共产主义。
六、结论:我们对柄谷的批判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柄谷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阅读本身是透过宇野经济学、精神分析理论等理论透镜进行的,因此要对柄谷“重建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论工作给出总体的评价,首先需要全面考察柄谷在多大程度上“误读”了宇野经济学、精神分析理论,这种“误读”是否具有积极意义。限于主题与篇幅,本文仅以死亡本能与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关系为例,来说明柄谷的“误读”并非总是带来积极的效果:由于柄谷对死亡本能概念的误读,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理解,即认为在柄谷那里并立地存在着两种形而上学,一种是基于“资本的本能”(即货币积蓄本能)而产生的“货币的神学/形而上学”*[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176页。,另一种是共产主义形而上学,柄谷所主张的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因而受到了限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如果柄谷正确理解了死亡本能概念,共产主义形而上学本身的普遍性原本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首先,对柄谷来说,货币形而上学到底算不算是一种形而上学。尽管与其在《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的看法不同,在《跨越性批判》中柄谷不再将货币的魔力归因于货币自身,而将其归因于积蓄本能-形而上倾向*[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导论第6页。。他认为,就像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死亡驱力,death drive)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倾向超越了快乐原则(principle of pleasure)一样*[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83、180页。,资本家——马克思称之为“理智的货币贮藏者”,即守财奴——的积蓄本能也是形而上的,它不遵从快乐原则,即不是以一般的快乐、使用价值为其目的、动机,积蓄本能毋宁是将追求交换价值(货币)本身视为其唯一目的。因此,资本家的确是韦伯所谓禁欲的新教伦理的践行者,这种为赚钱本身而赚钱的精神,似乎很接近康德的绝对律令。更重要的是,由于柄谷将积蓄本身与死亡本能相关联,“死亡”这个根本意义上的“他人的经验”的视角似乎也被包括进来了。而上文已分析,柄谷认为真正的形而上学之所以是形而上学的、普遍性的,就在于它能将他人的经验(尤其是死者的经验)纳入进来。*[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85、173、175、180、85页。综上所述,在积蓄-形而上学本能基础上构建一种货币的形而上学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
但柄谷是否真正理解了死亡本能的问题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正如拉康所指出的,只有与快感(jouissance)相关联,我们才能把握死亡驱力。与柄谷的理解不同,快乐原则的作用本身就在于限制享受,它就是命令主体享受越少越好的法则,所以“超越快乐原则”带来的并非更多的快乐,而是痛苦,这种“痛苦的快乐”(painful pleasure)就是快感。而所谓死亡驱力,指的就是主体这种不断地想突破快乐原则,获取超出(excess)快感的欲望。*[英]伊凡斯:《拉冈精神分析辞汇》,刘纪蕙等译,台北: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152页。简单地说,超越快乐原则的驱力并不像柄谷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对快乐的抑制,驱力的关键在于与快感的复杂关系。
进一步,拉康也承认,守财奴的确不享用他所积累的财富,而毋宁是把自己当成财富的工具,当成财富积累其自身的工具*Jacques Lacan, The Other Side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Russell Grigg, New York: Norton, 2007, pp.82-83.。他认为这其实是性倒错的心理结构,倒错主体就是把自己当成快感(jouissance)的对象和工具,当然,这个快感并不是倒错主体自身的而是大他者的①。倒错主体却总是“假想着存在着大他者快感的纯粹客体-工具”,从而用这种工具(哪怕这种工具就是他自身)“取代、构成了主体性之分割”②,即倒错主体通过把自己当成快感的工具的办法,躲开了快感本身。这就好像守财奴也是通过把自己当成财富积累的工具的方式来回避财富积累、创造本身。③柄谷也注意到守财奴与性倒错的关系④,但他并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因此,如果我们接受柄谷的基本逻辑,即只有将死者的经验考虑在内,在死驱力的基础上才能建构真正的形而上学,那么由于积蓄本能并非死驱力,建立在积蓄本能基础上的货币的所谓“形而上学”其实并不符合柄谷本人对真正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假使柄谷正确理解了死亡本能概念,共产主义形而上学的普遍性、唯一性原本是可以得到保证的⑤。
① [英]伊凡斯:《拉冈精神分析辞汇》,前揭书,第234页。
② [斯洛文]齐泽克:《实在界的面庞》,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③ Jacques Lacan,TheOtherSideofPsychoanalysis, trans. Russell Grigg, New York: Norton, 2007, p.82.
④ [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前揭书,第173页。
⑤ 与死驱力相关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工人的生产与被剥削问题,这是拉康的一个重要主题,柄谷并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个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受到齐泽克的批评。(Jacques Lacan,TheOtherSideofPsychoanalysis, trans. Russell Grigg, New York: Norton, 2007,pp.78-83;[斯洛文]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