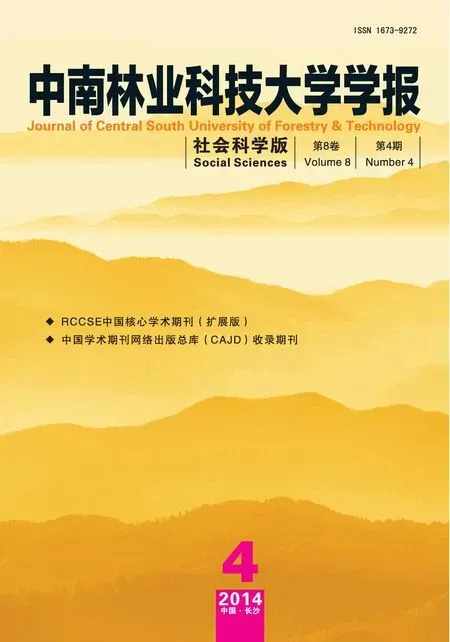《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观之内在逻辑
訾 阳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观之内在逻辑
訾 阳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然观的可分为自在自然、对象自然和人化自然三个层次,它们之间是发展的关系而不是对待关系。从三分的发展逻辑这一视角出发,我们能够对自在自然、对象自然和人化自然的内涵进行重新的解读,并发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逻辑演进过程。
马克思;自然界;自在自然;对象自然;人化自然
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中的自然观,一般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将自然界划分为“人化自然”以及 “自在自然”;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自在自然”根本不在马克思自然观的视野之内。这两种观点都把马克思的自然观的内在结构和丰富内涵简单化了。笔者认为,在马克思的自然观中,存在着“自在自然”、“对象自然”、“人化自然”发展的三个逻辑层次,而且这三个层次是内在地紧密联系着的;以此为视角,我们会发现马克思自然观更加丰富的内涵。
一、自在自然
马克思在《手稿》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在自然”的概念。单从概念上理解“自在自然”(Natur an sich)如下含义:自在自然是在自身,与自身直接同一的自然,是处于潜在状态尚未展开的自然;同样也是以自身为根据的自然。
(一)作为直接同一自然界的“自在自然”
首先,“自在自然”尚未展开的,与自身直接同一的自然。马克思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存在着的存在物”[1]。因而,马克思认为人作为存在物是分层次的,即自然存在物与自为的存在物两个层次。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与作为自为的存在物的人并不直接等同。因此,经由人身作为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自然存在物,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同的自然界,一是作为人本身的自为的自然界,一是直接的自然界。
当“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时,与其他具体的自然存在物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时候人同自然的联系完全是自然同自身的联系,而“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1]。自然界作为人的身体只是“人为了不致死亡”[1]而必须与之交互的自然界。因而,人作为单纯的自然存在物时,人淹没于自然之中;自然中并没有人,自然在自身之中与自身同一。自然对人的意义仅仅是自然对于一般动物的意义;人对自然的关系也至多是动物对自然的关系。
(二)作为双脚立地自然界的“自在自然”
其次,笔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中,“自在自然”同时是以自身为根据的自然,因而是作为独立实体的自然。
在黑格尔那里,自然界只不过是释放出来的绝对理念,其实质是在感性形式掩盖下的抽象概念;自然形式对于本体的抽象思维而言具有相对的外在性。自然的这种外在性虽然是一种体系上的必要;但对于抽象的思维而言,同时又是一种缺陷,自然必须扬弃自身。被绝对理念设定的自然界只能是作为主体的绝对理念证明自身的工具。
因此,黑格尔的自然蕴含着“关于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存在物;自然存在的根据还不在自身;“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它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1];因而,黑格尔的自然并非“自在自然”。
(三)与传统逻辑框架中的“自在自然”的商榷
因此,笔者认为,在《手稿》中马克思赋予了“自在自然”以深刻的意义。首先,在“自在自然”作为在自身尚未分化的方面,马克思肯定了人直接作为自然存在物,并且肯定了这个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存在于其中的自然界对于人“不至于死亡”的自然属性的意义。其次,在“自在自然”作为依据自身而存在的方面,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自然观,并且赋予自然独立的存在地位。
笔者认为,以人类实践活动划分“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边界,在与“人化自然”相对立的关系中讨论“自在自然”在事实上和理论上都难以成立。首先,人的活动边界就是人的认识边界,而人的活动在现实性上不可能有边界;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的活动具有无限延展性,另一方面人的活动只涉及人类活动范围之内,而活动之所及只能是活动的内部领域而非边界,因而为人的活动所规定的人的意识,并不能触及所谓的边界。其次,如果通过在与“人化自然”的对立关系中规定“自在自然”,使“自在”始终与某物相对立,“自在自然”就会失去其“自在”的内涵。“自在自然”本身是人之空场的自然,因而还不具备与“人化自然”相对的根据。因此,“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的摆置是在预设人与自然相异的隐性前提下产生的,是在预设了“人化自然”和直接同一的自然之瓦解的基础上谈“在自身并以自身为根据的自然”。再次,由于这种摆置方式,“自在自然”也只能通过“关于已被加工过的自然范畴来加以直观和理解”[2],其必然导致“自在自然”不存在的论断。因而,将“自在自然”从马克思的自然观中驱逐出去,实际上也是简单地对自然进行二分的必然结果。
但“自在自然”还不具有历史性,仅具有内部空间的差异性。正如费尔巴哈强调的,自然物永远只是完全确定的、感性的、个别的事物[3];自然的概念指向的是具体的自然物的集合,而不是自然物本身的共性的抽象实在。由于自然中存在差异着的具体自然物,这就使“自然界”内部具有空间的分割。从而具体自然物和具体自然物在其之间的分殊关系中,确立起了对象性原则。自然作为对象自然出场。
二、对象自然
在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看来,每个自然存在物必须是感性的、具体的,相互之间存在着差异的,空间上是相互外在的;具体的自然存在物,在“自身之外有对象、自然”[1],因而自然物是对象性的存在物。
(一)作为直接自然存在物对象的自然
马克思指出“一个存在物如果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1]。因此,所谓对象性存在物,即是说一个存在物自身之外有对象;是通过对象确证自身的存在和本质的存在物;与之相反,“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一个存在物必须是对象性存在物,其存在才有意义,才有根据,才能得到确证。对象性存在物本身就是自然界;一切自然界存在物都处于对象性关系中。人直接作为自然存在物,当然也必须与其他存在物处于对象性关系之中。需要指出的是,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发生的对象性关系,只是人作为一般的肉体存在物,一般的自然存在物与对象发生的关系,即自然与自然本身发生的关系。
(二)作为自为存在物(人)对象的自然
但是,人不仅是自然存在者,更是“für sich selbst seiendes Wesen”[4](中央编译局译: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这个存在物,一方面能够为了自己存在,而首先他必须对于自己存在。同时,这种存在强调其存在是依靠自己的存在。综合理解共有三个层次,第一,这个存在物对于自身而且能够对于自身存在;第二,这个存在物的存在是为了自身而且能够为了(目的性的为了)自身的存在;第三,这个存在物的存在是由自身为之,是根据自身的存在。人作为这样一种存在者可以把自己的活动作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来对待。把活动作为人意志的对象,表现了人能够为了我存在;活动作为意识的对象,表现了人的存在能够对自己存在。具备了这两方面的条件,人的活动具有自由自觉性,人们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自我展开,自我实现。
人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物在展开自身活动时,必然要与对象处于另一种的关系中。这种关系即是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的关系,又是我“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1]。人与自然物这种对象性关系已经不是自发的,而是自为的关系;它不是自然直接规定的对象性关系,而是人主动地构建起来的对象性的关系。原本非人的自然界成为了自为地存在着的人的对象,从而本身对人而言也是自为地存在着;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界在作为人的人的域场内,都是自为存在着的自然存在物。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的性质,以及在人的对象性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存在样态,相比齐一的自然状态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三)人与作为对象的自然相互关系的三个层次
人把自然当做对象与其发生对象性关系的基本方式,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第一,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这是与人作为直接的自然存在物密切相关的一种人对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表现为自然界为劳动者肉体生存提供生活资料。第二,自在的自然界“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1],因此人类必须通过劳动对自然进行改造。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活动构建起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层面,即人对自然依赖基础上的能动关系。
第三,人与自然在互动基础上形成的彼此依赖关系。一般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只有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不存在自然对人的依存性。在此,就人作为直接的自然存在物的逻辑前提下进行的思维。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当人作为人同自然发生关系时,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自然界现在“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者那样对我而存在”[1],这意味着自然的存在和现实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只能是对人的存在和现实性。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说“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1]。人的感觉和激情能够确证外部对象的存在并且外部对象以何种方式存在也证明了人在何种意义上存在,因而在这种关系中,“是互为根据或本质的”[5],人与自然相互确证。
当作为人的人与作为自然的自然相互对待,当自然以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并且作为人的人以人的方式同作为对象的自然发生关系,更广阔的逻辑框架会出现在我们面前,即“人化自然”。
三、人化自然
传统视域认为人化自然是通过人的实践打上了人的烙印的自然。这种定义仅仅抓住了人化自然的一个规定性。笔者认为《手稿》中关于人化自然的思想内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人化自然”是被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中介了的自然。第二,“人化自然”是人本的自然界,是被人的社会中介了的自然。第三,“人化自然”是历史性的生成过程。
(一)生命活动中介的“人化自然”
首先,“人化自然”是在“对象自然”基础上的,被人的活动中介了的自然界。这个层面上的“人化自然”最接近于“对象自然”,它仅仅意味着“对象自然”是人通过生产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进而被创造的世界;自然,只要一经成为人的对象,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人化自然”。
人有通过改造作为对象的自然界,才能使自然界“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1]。没有人的实践活动,没有实践活动中以及在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理论活动人类本质的对象化,没有与对象自然的交互,“人化自然”不可能生成。而人类实践活动所触及的自然之所以同人作为动物意义上展开活动所形成的自然有所不同,因为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三个独特的性质,分别是自由性、普遍性、自觉性。
但仅仅通过自由自觉的普遍的实践,通过改造对象世界,是不是就必然生成“人化自然”呢?笔者认为并非如此。虽然马克思肯定了“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但可以看出,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所形成的自然界,是“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1]的。异化的框架下的各种人的活动的特性都呈现出非人的性质,因而异化形式是必然要被扬弃的。因此,仅仅在实践意义上谈人化自然是不充分的,实践仅仅是人化自然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二)人本性质的“人化自然”
只有在“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基础之上,即以共产主义为前提,建构起真正的人的社会,“人化自然”才有具有真正的现实性。而“人化自然”在上述前提条件下,就具有了鲜明的人本色彩;“人化自然”也就是“社会的”“人的”自然。
共产主义通过扬弃私有财产,进而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像自身、向社会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它解决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是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有机统一。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性质是社会性质;社会的性质不仅仅要从事实的社会联系和交往来理解,这里的社会还包含着价值的维度,即社会中的人应当是本质丰富的人。而仅仅当人性复归后,只有当人作为人的人产生后,“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对人而言才存在。在社会条件下,自然界是直接体现一个人个性的对象,因而同时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因此,扬弃了私有财产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贯彻到底的人道主义同时也是贯彻到底的自然主义。这时相互对待的人与自然凝结成了更广义上的人或者说更广义的自然;大写的自然等于大写的人,大写的人也就等于大写的自然。
(三)历史性质的“人化自然”
“人化自然”是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因而具有历史性。然而“人化自然”作为历史而形成的过程绝不是“自然发生说”所阐述的“生命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1]的过程,历史场域中的自然界的历史性不同于发生的过程性。
“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意识到的历史”[1]。马克思在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一,一般自然物质有形成过程,但没有历史。第二,人和自然物一样是形成的,但人形成的过程是历史。[6]由于人具有精神类能力的存在物,他自觉到自己的生命活动,因而他可以不断扬弃自身的生命活动;这种有意识扬弃自身的生命活动构成了历史。自然界之所以具有了历史性,乃是因为自然界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并通过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被扬弃了。而且只有把采取独立形式的自然对象直接扬弃,自然对于人才有意义,才是被人肯定的。因此,自然界就人发展的过程而言才是历史,才被纳入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
历史作为自然史,自然史作为历史,即是人不断改造自然的过程,又是人通过改造自然从而扬弃异化,使人向人复归过程。第一方面是前提性的,第二方面是目的性的;前者渗透着后者。首先,历史是“自然界对于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这一历史过程有赖于人的劳动,并生动地体现在“工业的历史”中,“因为全部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1]。工业是人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人在工业中把自己本质力量对象化于自然界,因而工业是自然界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其次,“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做准备的历史”[1],但要使意识成为人的感性意识,需要成为人的需要,同时使人成为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的对象,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因而,人对自然的改造的过程即是异化产生的过程,又是扬弃人的异化和并使自然真正复活的过程。
(四)“人化自然”内在的逻辑层次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在逻辑结构上有两个层次。一方面,当自然作为人的对象,与人发生关系时,它当下必须是人化自然,不是“人化的自然”就不能作为人的对象;人化自然和作为人对象的自然是同时发生,人化自然只能是人的对象。另一方面,“人化自然”是人与自然的统一,自然就是人,人就是自然,自然不在人之外,人也在自然之中;在大写的自然=大写的人的视域中,人与自然的分别仅仅是视角的问题,但两者在本质上也是一体不二的。这时的“人化自然”在逻辑结构上即不是与“自在自然”相对的自然,也不是与“自然化的人”(客体主体化的结果)的对待的那个自然。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手稿》关于自然观是由三个发展着的逻辑环节构成的,即“自在自然”“对象自然”“人化自然”。对于马克思《手稿》中的自然观不能简单地从“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对立的逻辑框架中加以理解;在对立统一的对待逻辑中理解“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只能得出如下结果:人化自然是打上人类烙印的自然,而自在自然则相反;从而必然导致,一,不能理解“自在自然”,甚至否认“自在自然”;二,片面理解“人化自然”,以至于隐藏了马克思自然思想的丰富内涵。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07,105,57,56,91,106,86-87,140,58,89,81,206,92,88,90.
[2]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吴仲昉,欧力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6.
[3] 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425.
[4] Karl·Marx.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erste Abteilung Band2,Dietz Verlag Berlin, 1982:409.
[5] 舒远招.西方哲学原著精义选讲[M].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 426.
[6] 刘兴章.感性存在与感性解放[M].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9.
Internal Logic of the View of Nature in Economic &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in 1844
ZI Ya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Marx’s view of nature in Economic &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in 1844 can be in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namely nature in itself, nature as object and humanized nature. The relationships of these levels are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treating.It’s the logic of development. Form the view of development logic of three levels, we can re-interpret the conceptions of nature in itself, nature as object and humanized nature, and fi nd out the natural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Marx; nature; nature in itself; nature as object; humanized nature
B82
A
1673-9272(2014)04-0056-04
2014-05-19
訾 阳(1988-),男,山东高密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编校:徐保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