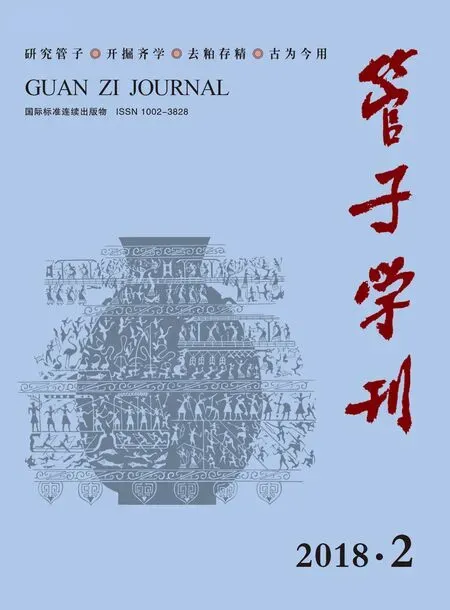《史记·孔子世家》再探微
陈 曦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军事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十几年前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时,曾写过一篇研读《史记·孔子世家》的论文[1]。近年来,虽因教学需要不断搜检《论语》,但《孔子世家》却长时间未再触摸。最近有幸参与张大可先生主持的《史记疏证》工程,促使我再次捧读,更深地感受到了司马迁对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敬之情。作为孔子第一篇传记的《孔子世家》,堪称司马迁与孔子两位文化巨人的心灵碰撞,反映了“史学之父”司马迁对孔子形象的独特解读。而这,在此篇传记一些颇有争议的笔墨中,表现得尤为明晰。
一
若举出《孔子世家》最重要的史料来源,毫无疑问当首推《论语》。韩兆琦先生通过比对《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的素材来源,认为“《论语》是被《史记》按原文取用最多的先秦著作,它总共一万来字,差不多都被司马迁引用尽了”[2]250。《论语·述而》有言:“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世家》一字不差地引用了这段话,表明司马迁是认可这种记述的。除了《论语》,太史公还采录了先秦汉代的诸多典籍,如《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国语》《韩诗外传》等。笔者注意到不少学术名家针对《孔子世家》采录《国语》的如下两则材料,指责太史公既已承认“子不语怪、力、乱、神”,又记述其大谈“怪”“神”:
定公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
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禹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在他们看来,上引文字实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岂不是对“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否定?如崔述曰:“《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果有此事,答以‘不知’可也。乃获一‘土怪’,而并木石、水之怪而详告之,是孔子好语怪也,不与《论语》之言相刺谬乎?桓子鲁之上卿,获羊而诡言狗以试圣人,何异小儿之戏,此亦非桓子之所宜为也。且土果有羊怪,则当不止一见,如水之有龙然。苟以前未有此事,则古人何由识之;既数有之,又何以此后二千余年更不复有穿井而得羊者?岂怪至春秋时而遂绝乎?是可笑也!”[3]277再如顾颉刚的指责:“《孔子世家》中,既从《论语》,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又集录《国语》中的许多关于孔子的神怪之谈,好像他真有二重人格似的。这都是他碰到了冲突牴牾的材料时,不懂得另择而只懂得整齐的成绩。这样做去,旧问题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来了。”[4]195又如李长之的议论,口气虽不甚严厉,但也认为司马迁的记述有问题:“在《论语》中,孔子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可是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中,孔子却就懂得木石之怪,山川之神,以及三尺的短人,三丈的长人了。这说明着什么呢?这是说明司马迁已经把孔子浪漫化了,或者说,他所采取的孔子,已不是纯粹的古典方面了。”[5]68无论以上三位学术名家的批评态度或激烈、或含蓄,但均认为司马迁的记述前后抵触,自我矛盾。这俨然已成定论。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包括《孔子世家》在内的整部《史记》,的确存有不少史实错误,但像这种在一篇文章中前后论断不一的却很少见。司马迁是否犯下如此“低级”失误?笔者认为非也,理由有三:
其一,上引《孔子世家》的两段文字不能证明孔子对弟子“语”了“怪”论了“神”。
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是孔子的某位弟子对其平时讲授内容的概括。“不语”,正如钱穆先生的解释,是“先生平常不讲”[6]183的意思。从上引两段文字的语境来看,均非孔子向弟子传道授业的场景。上引第一段文字是季桓子有意测试孔子的学问,原本“(缶)中若羊”,却对孔子说“得狗”,以此观察孔子的反映,看孔子是否博学多识。上引第二段文字则是吴国使者因“得骨节专车”而请教孔子“骨何者最大”,这说明孔子在当时诸侯国间已有巨大声望。孔子向弟子讲学时“不语怪、力、乱、神”,但遇到社会上有人向他咨询此类问题时,他会调动其丰厚的学养储备而给予解答,更何况季桓子的询问实含有测试孔子学问高低的意图在内,孔子焉能不答?
其二,两段文字只能说明孔子曾“语”了“怪”,但并未论了“神”。
何谓“怪”?何谓“神”?在古代文献中,这两者的界限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如《礼记·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而孔子显然是将“神”与“怪”看成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内涵正如钱穆先生的如下解释:
(怪力乱神)此四者人所爱言。孔子语常不语怪,如木石之怪水怪山精之类。语德不语力,如荡舟扛鼎之类。语治不语乱,如易内蒸母之类。语人不语神,如神降于莘,神欲玉牟朱缨之类。力与乱,有其实,怪与神,生于惑[6]183。
可知“怪”即自然界的“怪异”物象,而“神”则指宗教学或神话学意义上的具有人格化特征的神灵,正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所记“降于莘”的“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便具有洞察世事、识别善恶的能力。依此定义阅读上引《孔子世家》的两段文字,可知第一段的确出现了“怪”的内容,所谓“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云云,但第二段则既未见“怪”的踪迹也未见“神”的影子。
读者可能会质疑:此段不是明明多次出现“神”的字眼,所谓“禹致群神于会稽”“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吗?怎能说未见“神”的踪影呢?答案是此“神”非彼“神”。《孔子世家》此处的“神”,指的是各地的诸侯。《史记集解》引韦昭曰:“群神,谓主山川之君。为群神之主(祀者),故谓之‘神’也。”吴国使者不明白为何将各地的诸侯称为神,“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两句便是孔子的解释,意谓古人认为山川的神灵可以主宰天下,因而把那些主管祭祀山川的诸侯也叫做“神”[7]3207。这种称谓,并不是孔子的发明,而是在孔子之前便已形成。因年代久远,这一说法已被时人遗忘,但“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的孔子却了如指掌,每遇他人咨询,便能对答如流。
至于说这段文字中的“得骨节专车”,是说吴人伐越时,在会稽挖出了一具人体骨骼。吴人觉得这具骨骼与当地人不同,尺寸很大,其中一节相对完整的骨架(如从头骨以下到尾骨)便装了一辆车。河南陕县上村岭出土有春秋时期的车子,颇能说明当时车子的结构形制,其1051号车马坑1号车,箱(舆)广 100厘米,进深 100厘米[8]116-117。吴国使者所说的这具人体骨骼,如若运载时使人体骨架保持完整,大概当需两辆车子,由此可以推断此人身高应在2米以上。这么高的个子固然属于少见,但却不属“怪异”范畴;孔子推测这具骨骼是防风氏,也是依据他的古史知识做出的判断。这段文字涉及的只有三尺的“僬侥氏”最矮者,其身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0.7米;如何认识“长者不过十之”的长翟人最高者?“十之”,不应理解成“十倍于”三尺高的僬侥氏最矮者,而应是“十尺”的意思。古代的“十尺”约等于现在的2米3。由此印证那具骨骼应属防风氏,孔子的推测并非凌虚蹈空。吴客曰:“善哉,圣人!”当是对孔子学识的由衷钦佩与高度赞赏。
其三,两段文字不能说明孔子迷信怪、神。
为他人在涉及“怪”“神”的问题上答疑解惑,就能说明他迷信鬼神、宣扬超自然信仰吗?如果认可这种逻辑,就可论定大学课堂上讲授宗教学的教师,均为信奉宗教者。事实自然并非如此。当然,有较真者,会说这些教师亦或不乏崇奉某家宗教者,故而还是有必要解读上引《孔子世家》的文字,考察其中所折射出的孔子对“怪”“神”的态度。鉴于第二段文字既无“怪”也无“神”,故而特别需要考察的,只是第一段文字而已。
这段文字描述季桓子在其父死后,继其父任,担任鲁国的上卿。他家凿井时挖到一个“缶”,外表画有类似羊的图案,告诉孔子时,却说的是“狗”。孔子答道:“据我所知,应是羊的图案。我听说,古人祭祀木石之怪,画的是‘夔’‘罔阆’的图案;祭祀水之怪,画的是‘龙’‘罔象’;祭祀土之怪,画的是‘坟羊’(即大羊)。”《周礼·考工记》有“山以章,水以龙”的说法,用龙的形象来象征水怪。故而古人用“羊”“夔”“罔阆”等来象征土怪、木石之怪,亦当可以理解。
一般注家在解释这段话的“中若羊”三字时,往往理解成“缶”里装有一只羊。然而“缶”不同于“缸”,它的形状口小腹大,是盛酒浆、水的器皿,怎能盛一只羊或狗呢?孔子依据其古代文化领域的广博知识,推测出从地下挖出的“缶”,当为古人祭祀土怪的祭品,故而断定上面画的应是羊。季平子为考验孔子的学识,故意说成是狗。孔子未被迷惑,不但认定是羊,还依据自己对古人风俗、信仰的深入了解,对何以是羊,做出了清晰透彻的解释。这段话只能说明孔子学识渊博,对关于土怪、水怪之类的古人信仰有着精深的研究,但却不能因此而说明他本人迷信怪异。至于对“鬼神”的态度,尽管《孔子世家》这两段文字未出现“鬼神”,但从孔子“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的话语,可知其尽管并非完全否定“鬼神”的存在,但在日常生活中,他除了对弟子“不语”之外,还采取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明确声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这说明孔子并不是一个迷信鬼神者。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把源自《国语》的两段文字,放在“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之后,非但未与“子不语怪、力、乱、神”构成矛盾,反而表明已届“不惑”之年的孔子,学识渊博,见解卓越,能不被怪象邪说所迷惑,不厌其详地为人解疑释惑,已被视为“圣人”,在诸侯国间享有良好声誉。
二
司马迁客观、大胆地描述了孔子的出身情况,从中可透视其不为贤者讳的“实录”意识,以及勇于挣脱儒家教条的可贵精神。
《孔子世家》云:“(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清人梁玉绳对此记载颇不满意,批评道:
“古代婚礼赖重,一礼未备,即谓之奔,谓之野合,故自行媒、纳采,纳徵,问徵、问名、卜吉、请期而后告庙,颜氏从父命为婚,岂有六礼不备者?……野合二字,殊不雅驯。”(《史记志疑》卷二十五)
其实,梁玉绳所谓“颜氏从父命为婚”之语,本于甚不可靠的《孔子家语》①《孔子家语》云:“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于颜氏徵在,从父命为婚。”,岂能作为立论的根据?看来,确实如人所言,“孔子的出生是一个谜”[9]。而解开谜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正确理解看似“颇不雅驯”的“野合”一词?唐人司马贞的解释很有影响,他说:
今此云“野合”者,盖谓粱纥老而徽在少,非当状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史记索隐》)
司马贞认为孔子父母之结合“不合礼仪”,原因是夫老妻少,年龄悬殊过大,而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从他声称颜氏“从父命为婚”的记载“其文甚明”(《史记索隐》)的话语中,便可知晓其立论的根据仍是《孔子家语》。再者,“先秦文献中关于老年男子纳少女为妻妾的例子并不鲜见,且均不以为不合礼仪,也末见称其为野合者”[9]。看来,孔子父母当初有不合礼仪的行为是不假的,古代学者一般也都意识到了,但由于有为贤者讳的思想在作怪,故都没有揭示出事情的真相。当代学者李衡眉依据人类学的观点,认为“野合就是一种较为自由的婚姻缔结形式,至今在一些民族中还以不同形式的风俗存在着”。他又考察婚姻发展史,认为“野合不过是杂乱婚制在习俗中的残存,这可以从古代民族中有‘节日杂交’的习惯为例证”。因之,他推断道:“叔粱纥与颜徵在的‘野合’不会像上述各民族那样浪漫,他们的所谓‘野合’,很可能是指的没有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即非明媒正娶,而是自由结合的。”[9]结论坚实,颇为可取。
明晓“野合”的含义之后,回过头来,我们不禁要问:司马迁选用“野合”一词,是否是对孔圣人的不尊重?答案是否定的。他并不以男女自由结合为大逆不道,在《司马相如列传》中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私奔,该篇也因而被视为“我国后代浩如烟海的才子佳人小说的滥殇”[2]522。当然,类似的故事早就频频见于先秦典籍,但故事的主人公一般都遭到了批评与诅咒。如《国语·周语上》记密康公跟从周恭王游于泾上,“有三女奔之”,密康公之母劝戒并警告道:“必致之于王。……小丑备物,终必亡。”密康公不从,“一年,王灭密”,果如其母所验。以记载纵横家言行为主的《战国策》倒是有不少与儒家思想相忤逆的故事,如作者以肯定的态度描述了齐太史敫女怜慕其家仆而私自以身相许,而此家仆竟是避难于民间的齐湣王之子法章,也即后来的齐襄王。太史敫之女慧眼识珠,得以成为齐国王后。《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以同样的态度转载了这个故事,表明太史公在恋爱婚姻观方面勇于挣脱礼教束缚的可贵精神。是故,他不会认为孔子父母的“野合”是淫贱可耻的,更不会认为此事会有损于孔子人格及思想的伟大。
退一步讲,即使司马迁鄙弃孔子父母的“野合”之举,以他作史之严谨,也是不会不录的。纵观《史记》全书,太史公对自己喜爱的人物从不偏袒,总是写出他们的瑕中之疵,如《项羽本纪》既刻划了项羽龙飞凤翥的雄姿,又交待了他的鼠目寸光及暴戾凶残,此点已为人们所熟知。甚至是对世人所顶礼膜拜的“圣人”周文王,司马迁也敢于揭示其绝不崇高的行为。在《孟子》等儒家经典中,文王为王道乐士的开辟者,“以德行仁”,行事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但司马迁却多次言及周文王及其股肱大臣吕尚对殷纣王施展阴谋手段,如:“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史记·殷本纪》)“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史记·齐世家》)有学者责难道:“德非倾人之事,岂阴谋所能为,信如此,则古之为德,乃后之所以为暴也。迁并言之,未可与论知德矣。”(《习学纪言序目》卷九)“此特战国辩诈之谋,后世苟简之说,殆非文王之事……迁不能辩其是非,又从而笔之于书,使后人怀欲得之心,务速成之功者,借以此为口实,其害岂小哉!”(《困学纪闻》卷十一)而实际上,军事集团之间在你死我活的斗争过程中,施以诡计蒙骗对方,剿杀异己势力,是再常见不过的事,自古以来莫不如此。况且,“商周非君臣名分,实质方国军事联盟之关系”[10],文王不可能、也没必要遵从后来儒家所设计的为臣之道去效忠殷纣。应该说,太史公对周文王也是满心景仰的,但绝不隐讳其难以登大雅之堂的行为。从他对周文王的写作态度中,可推知他即便不齿于孔子父母的“野合”,也必定会不为贤者讳的。西汉大学者刘向、扬雄均钦佩《史记》的实录精神,“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汉书·司马迁传》),当为千古定评
参考文献:
[1]陈曦.孔子神韵的独特演绎——《史记·孔子世家》探微[J].郑州大学学报,2000,(3).
[2]韩兆琦.史记通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3]崔述.崔东壁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三联书店,1984.
[6]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
[7]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8]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9]李衡眉.孔子的出生与婚俗[J].孔子研究,1988,(4).
[10]王慎行.文王非纣臣考辩[J].历史研究,1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