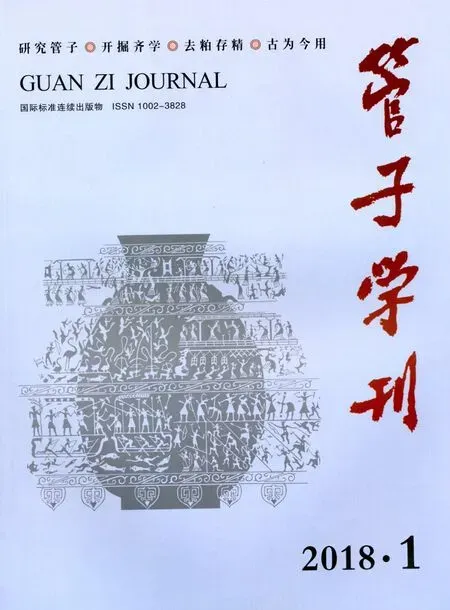论“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与齐文化研究的深入
——“多重证据法”和东周齐国殉马坑等的研究
印 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一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即“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1]。“二重证据法”一经提出,便在学术界畅行不衰,至今在古史研究领域仍颇具影响力。通过运用“二重证据法”,王国维先生在对商王世系和殷墟的确认以及甲骨文研究等诸多方面的学术实践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二重证据法”成为他对学术界的一大贡献。虽然王国维先生对于地下出土的只提到了甲骨文、金文,实际上是表述了在古史研究中历史学与考古学的相互关系[2],客观上点明了将地上传世材料与地下所发现的材料相结合的重要学术研究方法。因此,“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既包括(狭义)历史学者以考古资料来补正历史文献,也包括考古学者以历史典籍来解读、印证考古发掘资料。随着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从地下科学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早已不胜枚举,远不只是甲骨文、金文等文字材料,以久负盛名的临淄齐国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3]为例,该殉马坑是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属于春秋晚期,其墓主的认定就是借助于传世的历史文献。东周齐文化的研究亦包括地上的传世文献资料与地下发掘出来的考古遗存,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传世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古资料相互印证和补充,这样就能够加深对东周齐文化的认识。
二
王国维先生所提出并在学术研究中予以运用的“二重证据法”实际上是时代的产物,他关注地下之新材料,其实这应与当时现代考古学的传入存在相当大的关系。早在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前,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对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同年,中国猿人北京种在北京房山周口店被发现,这些在今天看来已属于学术常识的东西,在当时却是震撼性的事件,不可避免地对上千年来皓首穷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带来了观念上的巨大冲击,使得他们面对这些新方法、新事物不能不进行思考并做出反应,王国维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所以,从历史的高度来考察,“二重证据法”的出现并非仅是王国维先生“妙手偶得之”,而应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东西方学术交流、碰撞的结果,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属于时代的产物。
“二重证据法”自诞生后,其具体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与完善,而考古学的进步是推动其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田野考古工作无论是发掘的范围还是研究的深度都受到很大的局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考古事业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伴随着大量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大批田野考古资料的发表,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在复原古代社会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早已不限于“补正纸上之材料”了。随着“二重证据法”的发展,在原始社会史研究中,考古学发挥着主力军作用,在夏商周古史研究中,考古学发挥生力军作用,特别是对东周史的研究,东周时代所包含的春秋战国时期既有一定数量的传世历史文献,又有丰富的考古遗存被发掘,十分有利于考古资料与传世历史文献的相互印证与补充,恰好是“二重证据法”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
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与相互渗透,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是“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合成作战,组成多重火力网,联合攻关,实施重点突破。在对东周齐文化的综合研究中,可以由历史学学者根据历史文献、历史地理等多角度地开展工作;考古学学者系统研究与其密切关联的考古遗存,并确定相对年代序列与分期,同时为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测定绝对年代提供层位关系清晰、文化性质确切的测年标本。在测年技术上,常用的是碳十四测年方法。如果做高精度的测量,夏商周时期标本的碳十四年代误差一般可达到20至30年左右[4]。这样的多兵种合成作战无疑是“二重证据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该方法具有历久而弥新的魅力。
三
作为“二重证据法”新发展的多学科合成研究对于夏商周时期的古史研究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便于进一步理解这种新发展的具体作用,下面就通过三个例子来予以说明:第一个是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第二个是陕西长安沣镐遗址;第三个是东周齐文化的殉马坑。其中的第三个例子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些,而前两个例子可算作是“它山之石”,能提供一些借鉴。
(一)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
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包括城址及墓地两个部分[5],是已发现的唯一既有城址又有诸侯墓的西周早期封国遗址,该城址亦是已知唯一始建于西周早期的一座西周时期城市遗址。在该遗址中,城址、居址、墓葬俱全,这在西周遗址里并不多见。以1996年对该遗址的田野发掘为例,该次发掘不但进一步揭示了其自身年代分期、文化内涵、城市布局及建筑特色,其中的一个重大收获是有字卜甲的发现。此次发掘所发现的108号灰坑(Hl08)坑内的堆积分为3层,其中第1层出土的有蚌刀、卜甲、石片等。此次发掘所获遗物中包括数十片卜甲(三片刻字),标本H180①:4属于腹甲甲首部分,正面刻有“成周”两个字。该标本残长是7.1厘米、残宽为10.4厘米。“成周”卜甲不仅为该遗址的分期与断代提供了新的根据,还与该城址年代等其他重大发现一同为对该遗址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琉璃河遗址的发掘提供了西周早期等有明确背景的系列测年样品,通过年代测定,测年技术专家们根据该遗址的考古学分期断代及测年数据,经拟合计算,为西周早期年代等的确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另外,在1986年秋冬季对琉璃河遗址所进行的发掘中[6],该遗址的西周早期墓葬1193号墓(M1193)是第一代或者第二代燕侯的墓葬,该墓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其保存较好的棺木样品,以树轮系列进行高精度碳十四测定,通过拟合计算,结论是其最外轮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011士20年,这就是其年代的上限[4],又根据该墓出土的青铜罍、盉上的铭文,进而把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上推至距今三千年前的西周初年。
(二)陕西长安沣镐遗址
沣镐遗址位于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沣河两岸,是西周的都城遗址。该遗址1997年的田野发掘以其所发现的确定商周分界年代的界标而备受学术界瞩目[7]。该次发掘的Tl原为一条长10米、宽2米的探沟,后来向西扩方长8米、宽2米。据Tl的西壁剖面,其地层分为四层,第1层为表土层;第2层是晚期扰土层;第3层是灰土层,年代是西周中期;第4层则是黄土层,年代大约是商周之际。该层叠压于18号灰坑(H18)之上。18号灰坑在Tl的中部,该灰坑堆积很厚、内涵也极为丰富,其南北宽为4.5—3.5米、东西长度大约6.3米,深度较大。坑里的堆积分成四个小层,其四小层的陶片相互间经常可以拼兑到一起,各层的包含物看不出早晚分期特点,所以发掘者推断该坑整个坑内的堆积形成于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从该次发掘的分期来看,第一期的典型单位有18号灰坑等;第二期典型单位有T1的第4层(T1④)等。第一期遗存是沣西地区几十年以来考古发现的最早周人文化遗存,该期的年代被推定为文王迁丰到武王伐纣之间的先周文化晚期;第二期的陶器群具有明显的由先周文化至西周文化的过渡特点,其年代被推定为西周初年武王到成王前期。该次发掘为“断代工程”中的武王伐纣与西周列王的年代研究提供了由先周至西周晚期有明确背景的系列测年样品,通过年代测定,“断代工程”专家们根据以上考古学分期断代及测年数据,经拟合计算,得出了武王伐纣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的结论。
(三)齐国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
下面以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为例。该大型殉马墓在山东淄博临淄区齐故城大城东北部,墓向是10度。墓圹底中部有生土台,台东西宽是18.1米、南北长为20.7米。沿墓室的四周有相通的“沟”。发现了斜坡墓道,上口残长为14.7米,坡的残长是18米。石椁室南北长度是7.9米、东西宽度为6.85米,因被盗扰,棺椁的形制不清。器物库东西长度为8.2米、南北宽度是3.8米,是在椁室以北2.5米处。在距离椁底以上3米处的填土里,发现了一批用来殉葬的狗、猪及其他家畜、家禽骨胳,这些动物是被放置在椁顶上面填土里的。按头骨来计算,计有三十只狗、两头猪以及六只其他的家畜家禽。殉马坑位于大墓的东、西、北三面,呈曲尺形,西面长度是70米,北面残长为54米,其东端已遭破坏,复原后大约长度为75米。坑的宽度在4.8米左右。坑中的殉马排列从西面南端开始,由南向北,由西向东,排成了两列。马皆呈侧卧状,昂首,头向外,前左腿压于前马的身上,右腿蜷曲,显然是按照一定的葬式摆放的。马龄大多是六、七岁口。骨胳上下有席纹及乱草的痕迹。除了位于西面南端的五匹马脖下有小铜铃之外,其余都无随葬品。该墓及其殉马坑基本被认定属于齐景公。该墓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座能与历史文献记载相对应的经过科学考古发掘的春秋时期齐国国君的墓葬。
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的殉马数量非常庞大,据发掘者判断,该殉马坑的殉马总数可达到600匹以上。相比之下,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殉马坑、新郑郑国祭祀遗址春秋时期殉马坑以及淄河店二号战国墓殉马坑不论是单坑殉马数量还是殉马的总数都远远少于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8]。东周齐国单坑殉马数量偏多的葬俗由春秋时期延续到了战国时期,这个结论之得出是依据继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之后的淄河店二号战国(早期)墓殉马坑的发掘资料,淄河店二号战国墓殉马坑单坑殉马数量(殉马69匹)也是当时最多的。根据种种迹象推断,东周齐国殉马方式的一个重要特色便是先使殉马昏迷过去,随后再放进坑里摆姿势,由此形成的这种殉马的方式与传统意义上的活埋和杀殉是有所区别的[9]。不过,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就需要有兽医学乃至生物学、化学等多方面的鉴定,也就是需要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介入,另外,东周齐国殉马坑也需要更具体的绝对年代数据,这样才能充分开发该遗存的潜在价值,进一步深化对东周齐文化的认识。
由于考古发掘出的丰富的东周殉马遗存,临淄一带东周殉马遗存在自身范围内就可以形成纵向序列,仅春秋晚期的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与战国早期的淄河店二号战国墓殉马坑在时间上就可以形成该地春秋战国时期的随葬殉马坑序列。通过研究随葬殉马,不仅可揭示墓主人的社会地位,而且马与车皆属于交通运输工具,在经济领域中有重要作用,另外学术界公认东周时期在军事上是由车战向大规模骑兵部队转变的重要转折期,因此对于执掌权柄的大贵族来说,是随葬车马还是单独大规模殉马,也在一定意义上暗示出军事方面从车战向骑兵部队演变的进程,所以当时的殉马能够昭示出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社会发展情况。通过对随葬殉马坑中殉马数量的研究与骨骼等的鉴定,可以发现临淄东周齐墓殉马的马龄及体质变化,甚至能揭示出品种来源与饲养方式和养马业的发达程度等方面的情况,而要圆满完成以上的研究,达到预期效果,就需要通过甚至包括DNA的提取与鉴定技术及统计学等在内的多方面的介入来获得多重证据以进行全方位的探索。
在“二重证据法”中,运用传世历史文献与地下发掘资料进行相互印证与补充是最传统也是最典型的,该传统方法在对东周齐文化的研究中仍然大有用武之地。例如,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虽然严重被盗,不过除了其殉马坑之外,仍可用“二重证据法”对该主墓所承载的历史考古信息予以搜集和分析。春秋晚期齐国国君墓的发掘暗示出了当时齐国殉死之风的嬗变。考古发掘资料反映出在经科学发掘的春秋初期周王墓里就已经不见人殉现象了①这座周王墓位于洛阳体育场路的东侧,在东周王城外。该墓是带有四条墓道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亞”字形墓),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两周时期的唯一一座该种形制的墓葬。该墓墓向是1°。四条墓道都是斜坡墓道,其中南墓道坡度相对较缓,是主墓道。墓室的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墓口部稍大于墓的底部。墓室的长度约是7.5米、宽度约为6.7米、深度是13.1米。在墓底的四周发现了熟土二层台,由于该墓被严重盗扰,仅残存了局部。葬具与葬式皆不明。此墓出土了200余件器物,包括铜器、玉器、骨器、蚌器及石制品等。墓葬的年代应该属于春秋初期,发掘者初步推断该座墓葬是周平王之墓。(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5期)。东周时期的齐国是东方大国,齐桓公乃是“春秋五霸”之首。在发现于临淄河崖头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里,即齐国最高统治者齐景公的墓中,虽然在殉马坑里随葬了大量殉马,可无论主墓还是殉马坑中,都没有人殉的现象。这个考古发现的结果可以从考古学的角度揭示出到了齐景公时期即春秋晚期阶段,齐国人殉之风应当是已经衰败了。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等齐国的“勇力之臣”为齐庄公殉死,而晏婴却通过自找理由不去为齐庄公殉死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踰墙……遂弑之。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引自《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六,见《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83页)。关于“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皆死”,杜注:“八子皆齐勇力之臣”(引自《春秋左传正义》卷三十六,见《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83页)。,这一方面反映出该时期在齐国从死之风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亦暗示出当时的殉死之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强制性变得比较低了,当事人已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去殉死。鲁襄公二十五年即公元前548年,该时间属于春秋晚期的偏早阶段,而齐景公是死于公元前490年,这离齐国晏婴自己找理由不去为齐庄公殉死之事仅过了58年,由此揭示出在这半个世纪略多一点的时间里,齐国殉死之风的衰落速度竟是如此之快。西周时期周人墓的人殉现象就已经较为罕见了,这与殷遗民墓是不同的。在姜齐贵族执政的春秋时期,齐国没发现姜齐贵族墓的人殉现象,姜齐贵族虽非姬姓,但实际上是从属于姬周贵族集团的,并深受姬周贵族集团的影响。至于战国时期执政的田齐贵族,则是通过推翻姜齐贵族统治之后上台的,并不听命于姬周贵族集团。战国齐墓的人殉现象或许和田氏代齐存在一定的关系[10]。以上例举了在对齐故城春秋时期大型殉马坑的主墓——齐故城五号东周墓主墓的研究中,除了使用历史文献来与考古发掘资料相互对比从而基本上认定其墓主是春秋晚期的齐景公之外,该主墓的一些葬制如没有人殉的现象亦可通过运用传世历史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资料来相互补充并予以解读,而且应结合齐国当时的社会历史乃至春秋时期齐国以外的如洛阳王畿地区等的历史考古资料予以深入探讨,以揭示凝聚于墓葬之中的社会历史。
综上所述,运用“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能够深入揭示东周齐文化,对东周齐文化的深入研究应是由包括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来共同进行的。这样不仅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汇集相关各学科的人才优势,而且其结论也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学术界的共识。随着历史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对于东周齐文化的研究中的某些具体结论当然也有可能需要重新再认识。毋庸置疑,作为“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包括(狭义)历史学、考古学及相关自然科学等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关于东周齐文化的深入探讨会是通过多重证据以研究东周齐文化的成功范例。“多重证据法”是“二重证据法”在新时代的进一步发展,“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能够大力推进对东周齐文化的研究。
[1]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2]李学勤.“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3]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齐故城五号东周墓及大型殉马坑的发掘[J].文物,1984,(9).
[4]仇士华,蔡莲珍.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碳十四年代框架[J].考古,2001,(1).
[5]琉璃河考古队.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J].文物,1997,(6).
[6]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J].考古,1990,(1).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0,(2).
[8]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淄河店二号战国墓[J].考古,2000,(10).
[9]印群.论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的特点——与郑国祭祀遗址殉马坑等对比[J].管子学刊,2016,(3).
[10]印群.东周时期秦齐殉人墓的比较研究[C]//东方考古(第9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