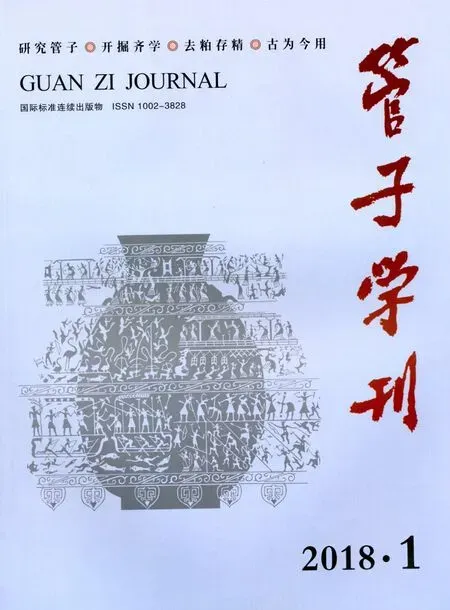《管子》赏罚思想的五项原则及其当代价值
王义忠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MBA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管子》[1]是先秦时期一部划时代的鸿篇巨著,而赏罚则是其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之一,“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管子·君臣下》,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所以它将其视为为君治国的两柄利器,并由此形成了明确公开、理性适度、遵循法度、论功过是非、赏信罚必等五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形式上是彼此独立的,实质上是相互联系且具有一定内在逻辑的。其中明确公开是前提,理性适度是要求,循法赏罚是保障,是非功过是重点,赏信罚必是关键。
一、五项原则
(一)赏罚要明确公开
《管子》认为,明确公开是其赏罚思想的前提。所以“赏罚之数,必先明之”(《立政》)。唯有如此,才能使得赏者愉悦、受罚者信服,进而使“赏”赏出吸引力、感染力、带动力,使“罚”罚出惩戒力、震慑力、影响力,这也是其开篇便提出“开必得之门”“明必死之路”(《牧民》)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赏”是激励民众、调动民众、发动民众的法宝;“罚”是使民祛恶从善、改邪归正、匡正辟邪的锐器。所以无论是明赏还是明罚,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都是有益处的。
1.明赏可以提升国家发展的正能量。《管子》认为,对于成绩突出者,应“赏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君臣上》),这样他人就不会有攀比羡慕的心理。所以它在《山权数》篇明确提出,对“能明于农事”“能蕃育六畜”“能树艺”“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育”“能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能医民疾病”以及能“知时”之民,都给予“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的奖励。此外,它还重视将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以国策十分之一者树表置高,乡之孝子聘之币”(《山权数》),同时辅之以免除服兵役的奖励,“孝子兄弟众寡不与师旅之事”(同上)。这种在农业、畜牧业、林业、园艺业、医药、时令、桑蚕等方面奖励有突出才能者,特别是“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权修》),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发挥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乘马》)、“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止”“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山权数》)。故《管子》强调,“赏”时要大张旗鼓,旗帜鲜明,营造积极的氛围,用明赏“赏之于其所善”(《禁藏》)。而“赏善”则可以引导民的正向积极行为,从而使民运用其聪明才智为国家发展提供更多的正能量。所以《管子》还对懂诗、懂时、懂春秋、懂出行、懂占卜的特殊贡献之民,给予土地、衣服奖赏。“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山权数》)。《管子》还将这类奖励用于战事准备,在预测越国要来偷袭齐国时便成功使用了这种方法,从而使民众自我提高游泳技能,“能游者赐千金”,但是还没有用去千金,“齐民之游水,不避吴越”(《轻重甲》)。
2.明罚可以减少社会进步的负能量。《管子》认为,对于成绩差且有过错者,“罚之以废亡之辱、僇死之刑”(《君臣上》),他们也不敢有疾恨抱怨的情绪。在政令执行方面更是如此,它明确指出,“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重令》),而且这五种情况都是“死而无赦”(同上)。这样国家推出的爱民之道、益民之略、安民之举、成民之法、利民之策、富民之方等民本治国方略才能真正得到有效落实。因为国家惠民政策的执行者不敢截留阻滞,民众就能够从国家发展中得到真正的实惠,自然不会滋生社会进步的不和谐因素。它还进一步指出,百姓不受刑罚处罚的原因,主要在于明罚的震慑作用。“于下无诛者,必诛者也”(《禁藏》),而不是“有诛者,不必诛者也”(同上);百姓之所以遭受刑罚处罚,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坚持明罚,没有明“罚”的威慑作用。所以《管子》强调,“罚”时要声势浩大,扩大影响,涤除消极的余孽,用明罚“罚之于其所恶”(同上),并致力于使百姓不受刑罚,“功之于其所无诛”(同上)。
总之,赏罚公开是德政的最高体现,“赏罚明,则德之至者也”(《枢言》)。因为公开行赏不仅能有效激活民众的创造潜力,而且能有效节约费用,“明赏不费”;而公开处罚不仅能有效震慑潜在犯罪分子、递减社会发展的负能量,而且还能切实减少刑杀,“明罚不暴”。因此,要确保明“赏”与明“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相得益彰,切不可重赏轻罚,也不可重罚轻赏,从而使赏罚达不到预期效果。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明“赏”还是明“罚”,都只是治国理政手段而不是目的。因为赏罚的真正目的在于让一切有利于思想创新的花朵争相怒放,让一切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有利于社会和谐的要素充分涌流。
(二)赏罚要理性适度
理性适度是《管子》赏罚思想的基本要求。唯有如此,才能使君保持威势、使受赏者满足、挨罚者信服,从而真正达到赏罚的根本目的。为此,它阐释了这样做的理由,并描述了赏罚理性适度的具体情况。
1.理性适度的原由。它认为,如果君奖励过少,那将燃不起民众奋力竞取的激情,唤不起民众垂涎三尺的欲望,更无法全面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如果君奖励过多,容易“致赏则匮”(《君臣下》),毕竟国家财富是有限的。“夫赏重,则上不给也”(同上),同时还会引起民众对奖励的过度苛求,易引发极为严重的徇私舞弊,导致奖赏本应达到激励民众、树立模范标杆的目的而发生偏离甚至背离。这样就会演绎因奖赏过多而导致国家财力衰微甚至灭亡的情况发生。为了验证这种思想,它讲述了一个国君因征战而奖赏亡国的故事:每次国君都将夺来的土地财物尽数分给了有功将士,致使最后将士的实力、地盘超过了国君,导致了弑君惨状的发生。它还认为,如果惩罚过轻,那将对民众特别是奸邪之徒没有任何震慑力。“诛罚轻,罪过不发,则是长淫乱而便邪僻也”(《正世》)。不仅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难以维系,而且会激起他们铤而走险去触犯法律的“钢丝”,无法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这样的轻罚看似有爱民之心,实则是伤害百姓;如果过分处罚,超出了民的承受能力,就会导致国家法令过于残暴,“致罚则虐”(《君臣下》),而“罚虐,则下不信也”(同上)。所以无论是财政匮乏,还是施政残暴,都无法得到民心,而只会失去民心,“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同上)。因此,无论是“严威不能振”,还是“惠厚不能供”(《君臣上》),都是由于奖赏名义与实际情况不符造成的。所以《管子》强调,对于那些做好事的人,应“不留其赏”,这样民就不会考虑私利;对于那些有过失的人,应“不宿其罚”,这样民就不会抱怨刑威(同上)。为了使“罚”具有威慑力,《管子》明确规定,触犯了死刑的要“罪不赦”。至于赏罚理性适度的标准,韩非子给出了明确答案:“威足以服人”“利足以劝之。”[2]330这与《管子》“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正世》)有异曲同工之妙。
2.理性适度的贯彻。《管子》认为,“赏“不代表对臣民的爱护,”罚”也不代表对他们的厌恶。“货之不足以为爱,刑之不足以为恶”(《心术下》),“赏”与“罚”都不过是爱、恶的微末表现而已。“货者爱之末也,刑者恶之末也”(同上),所以它也不是一味地施行重罚。对于那些不是触犯“铁律”的情形,它主张根据处罚对象的实际情况,灵活适当惩罚,这样既保持了赏罚的适度性与完美性,又使“赏”的影响力、“罚”的震慑力发挥至最大程度。在《小匡》中它对不同民的犯罪情况就运用了这种思想,充分体现了其爱民的民本情怀。一是针对犯小罪的民,它提出以一钧半的铜赎罪,“小罪入以金钧分”;二是针对犯轻罪的民,它提出以兵器架、盾牌、皮胸甲、两支戟赎罪,“轻罪入兰、盾、鞈革、二戟”;三是针对犯重罪的民,它提出用兵器、犀牛皮甲和两支长戟来进行赎罪,“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肋、二戟”;四是对于那些犯轻微过失的民,仅缴纳半钧铜以示惩罚,“宥薄罪入以半钧”;五是对于那些无冤而喊冤诉讼的民,经过官员三次劝阻而仍坚持要诉讼的,也仅交一束箭以示惩罚,“无坐抑而讼狱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一束矢以罚之”。虽然这五种抵罪的做法不一定科学,但是由于《管子》旨在减轻罚罪,赢得民心,所以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最主要的是它还解决了齐国“富国强兵,称霸诸侯”所需的戈、剑、矛、戟以及斤、斧、锄、镰、锯、欘等器具铜材料不足的问题,“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锄、夷、锯、欘,试诸木土”。《管子》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措施,是因为它认为过重的“刑罚不足以畏其意”,过多的“杀戮不足以服其心”(《牧民》)。诚然,“刑罚繁而意不恐”,就会造成“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直接导致“上位危矣”。
此外,《管子》还列出了赏罚的特殊情况。对于那些急躁而又行为邪僻之民,“赏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因为“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正世》),所以对这样的民“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同上)。因此,设立民不以为利的轻赏,想要役使他们做事,是不可能的。“赏不足劝,则士民不为用”(同上),即使勉强而为之,也不肯尽力;规定民不以为惧的轻禁,想要禁止他们作恶,也是不可能的,“刑罚不足畏,则暴人轻犯禁”。这样法令即使颁布,民众也不会听从。
(三)赏罚要务必循法
《管子》之所以强调赏罚务必要循法,是因为不循法而滥施赏罚之君并不罕见。为此,它列出了君主观、随意赏罚的情况,指出了其害处,同时明确了依法赏罚的益处。
1.肆意赏罚的表现。为了警醒国君循法赏罚,《管子》描述了三种不循法赏罚的情形:一是依据君之权臣赏罚。“臣有所欲赏,主为赏之;臣欲有所罚,主为罚之”(《明法解》),这样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君“废其公法,专听重臣”(同上),从而成为“听主”;“臣有所爱而私赏之,有所恶而为私罚之”,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君“倍其公法,损其正心”,从而“专听其大臣”(《任法》),进而成为“危主”。二是根据君之喜怒赏罚。《管子》强调,君应“喜无以赏,怒无以杀”(《版法》)。倘若反其道而行之,因喜而赏,因怒而杀,就会民怨升腾、政令废弛,直接导致“民心乃外”,一旦这种情形出现,君必将“外之有徒”“祸乃始耳”(《版法解》)。三是凭借君之爱恶赏罚。《管子》指出,君如果“爱人而私赏,恶人而私罚”,那么就会“倍大臣,离左右,专以其心断为中主”(《任法》)。《管子》强调,这三种情况都是丧身亡国之君的做法。所以它要求,作为治国理政之君,绝不能依据个人的亲疏、远近、喜怒、好恶来肆意赏罚,而应是“爱人不私赏,恶人不私罚”(《任法》),依法赏罚。倘若不如此,就会“赏禄加于无功”(《权修》)。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就会“民轻其赏禄”,从而“上无以劝民”,直接造成“令不行矣”(同上)的情状。同样,如果“常令不审”“官爵不审”“符籍不审”“刑罚不审”,就会“百匿胜”“奸吏生”“奸民生”“盗贼生”(《明法》);如果国君“刑赏不当”,那么即使“断斩虽多”,也会“其暴不禁”(《禁藏》);如果依私意行事,那么“赏虽多士不为欢”(同上)。毋庸置疑,如果赏罚率性而为,那么就会背离法度,从而失去奖优罚劣、奖勤罚懒的功效,有时甚至会出现得赏的人莫名其妙,挨罚的人鸣冤叫屈。
2.赏罚依法的益处。《管子》认为,法应像尺寸、绳墨等标准器具一样,并称“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七法》)。它强调,依法就能够判定民众行为的是非曲直,就可以起到震慑矫正作用。因为“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七臣七主》)“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县命也”(《禁藏》)“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法解》)。正因为如此,《管子》强调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施行,而且是不折不扣地循法而行,“置仪设法以度量断者为上主”(《任法》)。这样君遵循法度而又以法治理之,那么就会“身无烦劳而分职”(《明法解》)。指出,国君都应依据法令与赏罚治理国家,“人主之治国也,莫不有法令赏罚”,在国家法令明确、赏罚规定得当之后,君循法赏罚,才能“主尊显而奸不生”(同上)。否则,就会出现“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党而劫杀之”(同上)的惨况。所以它特别强调,“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基于这种原因,《管子》主张一切都要“以度量断之”,这样依法治罪,“则民就死而不怨”(《权修》);依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同上)。所以,倘若“以法制行之”,就会“如天地之无私也”(《任法》),它还进一步指出,“明主之治也,审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明法解》),赏罚更是如此。它认为,倘若君按公法行事,那么民“罪虽重下无怨气”。所以国君依法赏罚,就会使境内之民如丝之有纪、网之有纲,这样民就会“去其不善言,学君之善言;去其不善行,学君之善行”。针对《管子》循法赏罚的情状,韩非予以高度评价,“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辑也,乘之者遂得其成”[2]140-141。并据此称赞“管仲得之,齐以霸”“桓公得管仲,立为五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2]141。
(四)以是非功过论赏罚
1.保持赏罚公正。《管子》认为,“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七法》),且“有过不赦,有善不遗”(《法法》)。所以它要求明君“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不赏也;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明法解》)。这样就会出现“法度行则国治”的情状,从而使赏罚都能保持公正;而昏君则“不察臣之功劳”“不审其罪过”。只要“誉众者”,就“赏之”;只要“毁众者”,就“罚之”。这样一来,就会形成“邪臣无功而得赏,忠正无罪而有罚”(同上)局面,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功多无赏者“不务尽力”,行为忠正而受罚者“无从竭能”。这样就会出现“私意行则国乱”的境况,从而使赏罚失去公正。因此,只要“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那么群臣就会“举无功者,不敢进也;毁无罪者,不能退也”(同上)。同时辅之“以前言督后事”,“所效当则赏之,不当则诛之”,这样就会达到“张官任吏治民,案法试课成功”(同上)的目的,并将“爵人不论能,禄人不论功……以贵富荣华以相稚也,谓之逆”(《重令》)。荀子也强调,“无功不赏,无罪不罚”[3]158。韩非子指出,民该得赏还是该受罚,都应由其行为来决定,“赏罚随是非”[2]288。王安石也认为,“是非明而后可以施赏罚。”[4]243这样才能真正保证赏罚公正。
2.保证赏罚公平。《管子》指出,如果赏功不公平,“位虽高为用者少”;如果赦罪尺度不一致,“德虽厚不誉者多”(《禁藏》)。所以,它主张君对各级官吏要公平地以功过论赏罚,并设置官吏督察,“吏啬夫任事”“论在不挠,赏在信诚”(《君臣上》)。根据吏啬夫、民啬夫的职务和职责,“乘其事,而稽之以度”(同上)。由于是按劳绩授予俸禄,“则民不幸生”;按功过治罪惩罚,“则下无怨心”(同上)。所以《管子》要求国家在冬季对三老、里有司、伍长等进行年度考核,“使各应其赏而服其罚”(《度地》)。它还特别强调,治国理政切忌不可“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七法》),“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同上)。因此,君欲治国理政,必须做到公平赏罚,“有功必赏,有罪必诛”(同上),这样方可长治久安。因为“罚有罪,赏有功,则天下从之矣”(同上)。假如朝廷没有政令,“则赏罚不明”;而赏罚不分明,又不按功过赏罚,“则民幸生”(同上)。为了保证赏罚公平,《管子》指出,明君治国体现为分清职务而考计功劳,“有功者赏,乱治者诛,诛赏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与焉”(《明法解》)。对于应当奖赏的,“群臣不得辞也”;对于应当惩罚的,“群臣不敢避也”(同上)。如果客观成果能够证实其主张的,就给予赏赐;不能证实的,就给予惩罚,“功充其言则赏,不充其言则诛”(同上)。所以对所谓有智能的人,“必有见功而后举之”;对所谓有恶行败德的人,“必有见过而后废之”(同上)。
《管子》还指出,如果君丧失了公正、公平之心,那么就会无功而赏、有功却罚,最终导致身死国亡。“如此,则悫愿之人失其职,而廉洁之吏失其治”。所以它非常愤怒地指出,“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而以毁为罚也”(《明法解》)。
(五)要确保赏信罚必
《管子》认为,行赏贵在信实,处罚贵在坚决。“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九守》),赏信罚必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法法》)。
1.赏信罚必的必要性。《管子》认为,只有奖赏信实,才能对得赏者有激励力,而“赏罚不信,则民无取”(《权修》);只有奖赏坚定,才能使有功者得到鼓励,“赏庆信必,则有功者劝”(《八观》)。因此,只有奖赏保证诚信,才能赢得民信于境内、昭大信于天下。所以《管子》强调,对于那些政事做好且有政绩的,“君予之赏”;对于那些政事做的不好且犯错误的,“君予之罚”。所以它指出,只有惩罚务求必定,才能使国家的法律真正具有威慑力、震撼力。只有禁律与刑罚威严,才能使那些无视法纪者规规矩矩,“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同上)。因此,《管子》特别强调“罚必”。例如,在封山方面,“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地数》),这样人们就不敢随便开采了,“然则与折取之远矣”(同上);“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同上),这样人们就不敢触犯禁令了,“然则其与犯之远矣”(同上)。所以“罚恶”可以使民言有所顾忌、行有所舍弃,从而为构建和谐、安乐天下的理想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3.赏信罚必的好处。《管子》认为,无论是赏还是罚,对于那些亲眼目睹、亲耳所闻的民众都有影响力,对于那些非身临其境的民众也有潜移默化作用。“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则其所不见莫不暗化矣”(《九守》);“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权修》)。可见,“赏信罚必”有着“畅乎天地,通于神明”的力量,甚至对于奸邪之民也具有感染力(《九守》)。所以《管子》认为,赏罚只有信实坚决,才能使民坚信不疑,“赏罚莫若必成,使民信之”(《禁藏》)。因为“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法法》)。只要国君按照臣民提供的劳动成果给予赏罚,“则不劳矣”。“圣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修理,故能长久”(《九守》)。《管子》还指出,如果君能始终坚持赏信罚必,那么他就能“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心虑”,从而达到“无所不见”“无所不闻”“无所不知”的最佳境界。试想,治国理政达到如此的“辐凑并进”,国岂能不昌?民岂能不富?因此,作为国君必须“行赏信必”,长此以往,“则善劝而奸止”(《版法解》)。所以《管子》强调,“必诛而不赦,必赏而不迁者”(《禁藏》),这不是因为君主喜欢赏赐和乐于杀人,而是要为百姓兴利除害的缘故,“非喜予而乐其杀也,所以为人致利除害也”(同上)。显然,这对于养老扶幼、保全万民来说,没有比这更可贵的了,“于以养老长弱,完活万民,莫明焉”(同上)。由此可见,赏信罚必还有益民的成分蕴含其中。
《管子》还特别指出了赏罚不信实的危害。认为良田不赏给战士,3年就会兵力衰弱,而“赏罚不信,五年而破”(《八观》)。此外,《管子》之所以特别重视赏罚必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赏罚不信实严明,民众就没有廉耻之心,“赏罚不信”,则“民无廉耻”(《权修》)。然而,“廉、耻”是国之四维中的“两维”,而“两维绝则危”(《牧民》)。对此,战国纵横派独传子书《鬼谷子》也强调,“用赏贵信,用刑贵正。”[5]94商鞅也指出,“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罚,则奸无端。”[6]110所以《管子》强调,赏功应有信,罚过应审明,“信赏审罚”(《幼官图》)。
二、当代价值
《管子》是我国古代一部治国理政的“百科全书”。通过潜心研读,我们可从中洞察出它对赏罚问题认识的独到与深入,其赏罚思想不仅原则明晰具体,而且内容翔实丰富,是现代社会治国、治企甚至治家不可多得的参鉴宝典。虽然有些内容不合时宜,打上了时代烙印,但是它的五项原则却具有普适价值,奠定了后世赏罚思想的基础。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审视,它仍熠熠生辉,光芒四射。尽管赏罚的内容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由于多年来人们较多地聚焦了对《管子》经济甚至真伪问题的研究,从而影响了学界对其赏罚思想的深入发掘。但是,一旦拂去历史的尘埃,洗尽时代的垢印,其赏罚思想的五项原则便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因为它是一套严整而又系统的理论精华,是当时齐国富国强兵、成就霸业的重要权杖,是从明确公开、理性适度、循法、论功、赏信罚必中生发出来的思想精髓,所以《管子》赏罚思想的内在价值是非常丰富的。就文本解读而论,五项原则各具特色,都可以单独构成赏罚思想的经典;就内在逻辑而言,它们具有一定的递进关系,共同构成了赏罚思想的支柱;就赏罚效应而言,它是基于对当时民众的具体情况,获得了社会普遍认同;就赏罚效果而论,它既实现了士农工商“四业”发展的单项突进,又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霸业的整体推进,还保障了国家的安定、社会的祥和、人民的幸福。因此,赏罚思想犹如一枚璀璨夺目的宝石镶嵌在《管子》一书中,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并没有因某个朝代、某个时期甚至某个君王的退位而退出、消逝而消逝,因为历朝历代总会或多或少地具有上述赏罚思想五项原则的影子。特别是它为确保按功过是非赏罚,并设置了督察的官吏,后世乃至当代仍在借鉴使用,但是它的监督仅停留在官府层面,没有社会监督,无法保证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不相互勾结,从而难以真正保障赏罚的公正与公平。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能有这种思想已是颇为难能可贵了。
尽管如此,赏罚也不是治国理政的终极目的,而只是《管子》达到“富国强兵、称霸诸侯”的重要手段,“赏罚明,则勇士劝也”(《兵法》)。因此,国君只有综合运用上述五项原则,才能使“赏”,赏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罚”,罚出民的能动性、自觉性、规避性。这样才能使二者都能够成为国家发展的驱动器、社会进步的加速器。
时至今日,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如何用创新的赏罚思维“引领新常态”,“用赏”激发那些干事创业之人“初恋般的热情”,从而加速驱动创新,进而推动社会快速发展;“靠罚”清除那些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之徒“磁铁般的意识”,从而将礼、义、廉、耻“四维”灌注到他们灵魂的深处,全面维护公平正义,营造社会和谐。在推进“一路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对那些积极参与且项目进展较快的国家或地区,可以予以奖赏,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而对于那些虽然已经参与到“一路一带”建设中,但是仍处于消极观望或项目推进缓慢的国家或地区,可以施以惩罚,由AIIB提供正常利息甚至高息贷款。这样既可以使有关国家或地区早日分享“一路一带”带来的益处,又可以加快“一路一带”的建设速度。此外,在AIIB内部可设置这种“赏罚“的监督机构,对“一路一带”贷款实施应用情况,除了加大内部督察外,还可以引进一些非成员国进行社会监督,从而确保“一路一带”项目建设的公平、公正、公开。这样既可以将AIIB成员国凝聚在中国的周围,又可以将非成员国汇集到中国描绘的美好蓝图中来,从而达到让全球更多国家参与到“一路一带”发展中来,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加油助力!
[1]张小木.管子解说[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张觉,等.韩非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2.
[4]王安石全集:28[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5]岳阳注译.鬼谷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6]张觉.商君书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