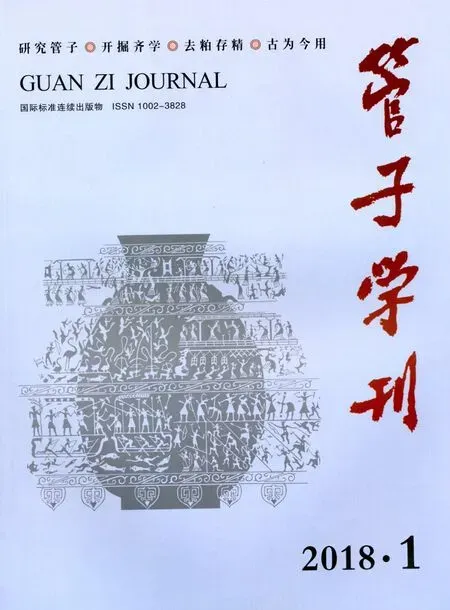管子战略思想研究
廖吉喆
(中共中央党校 战略哲学教研室,北京 100091)
美国著名战略家约翰·柯林斯曾说:“如果说在某个领域,通才比专才更为可取,那么这个领域就是战略。”[1]260在古代中国,管子绝对可堪称为一位具备通才素质的伟大战略家,其思想涵盖之广,通识之深远,功勋之卓著,为古今俊杰所钦服。孔子赞誉:“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苏洵、苏轼、苏辙在同题文章《管仲论》中,对管子均予以高度评价;梁启超誉其为“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2]3。管子相齐近40年,定民意,修内政,振经济,强军事,展外交,用时7年先富而后强,继而“尊王攘夷”向外拓展,最终成就齐国从一个贫弱地偏,内乱不断,外忧不止的国度一跃晋升春秋第一霸主宝座。纵观那段历史我们发现,齐国霸业卓越功业的背后所蕴藏的是一代名相管子丰富、务实和深远的战略思想。例如:强调道义、民本,“人与天调”目的性思想;强调“三本”“四维”“四固”“五事”“五辅”的全局性思想;强调“与之为取”“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知量,知节”的辩证性思想;强调先富后强的过程性思想。最为值得一提的是管仲在那个年代对经济发展问题以及发动“经济战”包括采用“尊王攘夷”战略时所采用的具有创新性意义的思想,特别是其战略思想比其它战略家更接近大战略结构的特征等。这些成功实践为后来者们提供了一笔巨大的战略精神宝库。直至21世纪的当代,管子战略思想依旧闪耀着其耀眼的价值光芒。对管子战略思想进行研究也有助于加深对管子本人以及管子学派在认识、思考、研究和处理战略问题时的思维方式和特点的理解;从大战略视角对中国先秦时期的战略特征进行梳理也有助于进一步分析管子战略思想的历史地位,同时对大战略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中的萌芽和发展也会有新的反思和认识。
一、管子战略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利义并重”是其战略指导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战略思想史上利义关系一直是战略家们极为重视的议题。利义关系实质上涉及当代战略哲学研究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如何权衡的问题。一方面,“利”更多地涉及战略手段的效用问题,如何做到有利有效是工具理性必须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义”更多地涉及正义等价值目标的问题,是价值理性必须面对的问题。段培君教授在论述当代大战略形成和发展的特征时指出:战略思维的当代形态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某种统一。这个结构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们正是基于此对战略思维的本质得出了当代的新概括。在传统战略思维中,存在着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不同强调而形成的不同流派。但是,从传统战略思维向当代战略思维转变的历史进程表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发展趋势更加清晰地展现了战略思维的本质[3]。就这一点来说,管子的“利义并重”的战略原则对于大战略思想的萌发有着重要的意义。
先秦时期的利义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重义轻利,秉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以孔孟学派为主,他们将“义”作为至上的道德追求,崇尚的是“舍生取义”,认为“义”的精神追求要高于一切物质利益的攫取,获取“利”必须要采取正当的手段,要符合“义”的要求,否则就是小人。这一派更为重视价值理性的方面。荀子认为国家和个人一样需要“先义后利”,否则国家就会遭致灭亡,其论著《管子·王霸》(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篇就以齐国为例讲述了国家治理中秉持“先义后利”原则的重要性,认为:“掣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紊之而亡,齐阂、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弛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拙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稿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它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荀子·王霸》)
另一种利义观则是重利轻义,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以法家作为代表,他们反对儒家所谓的“仁义治国观”而极力倡导“功利强国观”。他们鼓励人们追求功利效果,追求物质利益,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法家的“贵诈利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的观点体现了重利轻义的倾向,是以工具理性的考量作为立足点。
与上述义利观不同,管子则以“利义并重”做为其战略的基本指导原则。这种战略的指导原则首先与当时齐国的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密切相关,管子出任齐相后为齐国确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实现“霸王之政”。管子将国家权力进行了层次划分,其实质是对国家的战略目标进行了层次划分。如表1所示,第一层目标为“霸”,第二层为“王”,第三层为“帝”,第四层为“皇”[4]37。实现“霸王”的目标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这些条件不仅包含权利因素还包括道义因素,是对整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考量。因此,在战略指导上必须保持力量的综合平衡发展而极力避免力量的单维扩张,所以单强调“义”或单强调“利”都是不足取的,必须采用“利义并重”的原则。
其次,采用“利义并重”的战略原则是基于现实的考虑。管子极为崇尚功利,这种对功利的崇尚不仅源于其强烈的富国强兵的理想,还源于其对人性的准确洞察。他认为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所在,只有先了解人民的这种本能才能够更好的调动人民的力量为统治者所用。在《形势》中有这样的论述:“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这就是说,老百姓总是得利则喜,失利则怒,他们以财物为重并唯利是从,所以要崇尚利才能使之不招而来。但是光有利还不够,还需要以“义”做为倡导和教化,因为“夫民无礼义,则上下乱而贵贱争”(《版法解》)。所以,“利义并重”是周全的原则,在“利”与“义”两股力量的结合下民众才得以调动,民力才得以挖掘,财富才能聚集,齐国才具备利向外攻伐的基础。外交上也是如此,通过各种手段“亲邻国”以提升国际威望是“义”,通过军事“伐不服”扩其地兼其民是“利”,两者结合使齐国既拥有“矛”又拥有“盾”。
(二)辩证权衡是其战略思想的基本方法
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评价管子说:“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5]721这种因祸为福,转败为功的卓著能力体现了管子在战略管理方面的辩证方法,其基本特征是善于分析权衡祸与福、败与功、轻与重,并能够实现其转化。

表1《管子》关于大国权力层次与道义层次对照表[4]
辩证权衡的方法首先体现在对全局与局部的把握上。管子战略的全局性思维展现出其宽广宏阔的视野与举重若轻的政治智慧,他指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霸言》)。强调君王要明悉天下大势而非斤斤计较,如此才能收获人心。又如,“减,尽也。溜,发也。言偏环毕善,莫不备得,故曰减溜大成。”(《宙合》)即:减,是全部之意,溜,是发展之意;做到全局与局部的完善周全而且无不处理得宜,就可称之为“减溜大成”[6]77。管子对全局与局部辩证把握凸出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在横向方面将中原内外一并纳入考虑,形成中原内外一局棋的局面;二是在纵向方面以时间作为标尺将客观整体视为一个有机延续、不断发展的全过程,形成“国富兵强天下平”的三步走战略;三是“任大道不任小物”,以抓大放小执简御繁的方式实现“垂拱而天下治”的治理目标;四是立其大不夺其小,以“事先大功,政自小始”(《问》)的举措将全局与局部有机统一起来。
管子战略思想的辩证权衡方法也体现在对机遇与威胁的前瞻上。管子的战略前瞻是人类欲图前瞻危机把握命运的一种尝试。这一前瞻性思维上体现了权衡中的统一性思想。首先,对立转化构成了其哲学基础。管子的前瞻思维“效夫天地之纪”,包含大量的朴素辩证法规律。例如,“奋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日极则仄,月满则亏。极之徒仄,满之徒亏,巨之徒灭。”(《白心》)这些所强调的是物极必反之规律,告诫为政者要“不平其称,不满其量,不依其乐,不致其度”(《宙合》)。指出“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权修》)。这些对立转化的哲学思辨为其前瞻性思维奠定了基础,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转化的辩证前瞻,才使得管仲在相齐40余年中以其敏锐的眼光“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其次,因果参患是其原由分析的基本路径。管子的危机前瞻是建立在对祸患产生的因果关系的洞察上,认为“誉不虚出,而患不独生,福不择家,祸不索人”(《禁藏》)。因此,要瞻察因果以求避祸之良方。《参患》中,提出有猛毅的君主与懦弱的君主容易被颠覆,原因在于“猛毅则伐,懦弱则杀”。同时,还强调君主需要向他人借鉴以洞悉因果规律而自我警戒,“上观绝理者以自恐也,下观不及者以自隐也”,即既要从违背常理的人身上吸取教训以自我戒律,又要从行道不足的人身上获取借鉴以自我鞭策。再则,防微杜渐的内因防患成为其应对危机的重要方法。管子的防危避患尤其重视“微渐”的预防。在《权修》中提出“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即大邪大恶的根源的在于微小的邪恶,假如微小的邪恶得不到禁止而希望大邪大恶不伤与国家,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注重“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这才是治国之根本。同时,管仲还极为注重内因的防患。如在《禁藏》中强调“禁藏于胸胁之内,而祸避于万里之外。”强调“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禁藏》)因此,提醒君主首先应谨言慎行,而后才能推己及人;官员首先严于律己,方能治理百姓。
管子战略思想的辩证权衡方法还落脚于战略的具体施策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顺天者有其功”。“道”即事物的发展规律,机遇蕴藏其中,只有洞察发展全过程,才能把握“转机”“症结”“中枢”之所在。“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形势》)必须把握天道,顺应天道才能探知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才能在发展规律中探寻质变的契机,进而把握机遇而实现飞跃。假使背离天道,暂时之功最后也终将失去。楚汉相争,项羽七十余战,攻必胜,战必取却未能切中“枢机”;刘邦屡战屡败却能顺应天道紧扣胜利的脉搏,故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使天下归汉。这也是“得天之道,其实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同上)其次,“知予之为取”。取予之道可上升为战略哲学范畴,其运用范围广泛而深远。如在军事上“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7]131,取予之道在此便是诱敌、动敌之法;在政治上,“将欲去之,必先固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将欲灭之,必先学之”(《道德经》)。同时,在经济上、外交上同样有着重要的运用。管仲的“取予之道”主要在于取民,因为“争天下者必先争人”(《霸言》),争人需要得其心,欲得其心还要从其所欲,“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因此首要在于“佚乐之、富贵之、存安之、生育之”而后民才会“为之忧劳、为之贫贱、为之危坠、为之灭绝”(《牧民》)。所以,先予后取,国家发展强盛之机遇就蕴藏于其中了。《小匡》中也阐述了管仲对当时的邻邦小国“钓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进而达到“不称动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的目的。可见,机遇就藏在“给予”之中了。第三,“攻坚则轫,乘瑕则神”。“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制分》)即用兵之法在于避实而击虚,攻击敌方虚弱之处,其坚固的部分也会遭到削弱;若攻击敌方坚固之处,其薄弱环节也会加强。这也如同《孙子兵法·势》所说的精通“虚实之用”,那么军队进取之所向,便如同以石头去碰击鸡蛋一般,攻必胜、战必取。屠牛坦一天能解剖九头牛,但他的刀却仍能够削铁,是因为其刀刃是游刃于空隙之间的缘故。两军对垒,敌方的弱点就是我方战胜的机遇所在,因此,机遇须在“弱”中求。第四,“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霸言》)。一个国家的危险处境正是别国意欲作为的时机所在。如《三十六计·趁火打劫》“敌害在外则劫其地,敌害在内则劫其民,内外交害则劫其国。”管仲尤其强调“人者有道,霸王有时”,对这种时机的把握是建立在两个基本条件之上,一个是“国修”,即本国的政治清明;另一个是“邻国无道”,即邻近的敌对国家混乱无道。回顾历代先贤圣王,其卓著功业往往是得利于敌国的不当之举;但这只是显现的机遇,更重要的是首先将己立于不败之地,如兵圣孙子告诫的那样“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7]100要谨防自己的弱点,使敌人无隙可乘,在此基础上仔细观察敌方的不当之举,进而抓住时机,一战而胜。第五,“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权修》)。机遇不仅需要等待,更需要创造经营。这种创造经营仍是建立在对未来精确的把握上。“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同上)人才的培养需要百年的苦心经营,然而其效用却是“一树百获”,其对国家未来命运的影响是无比的深远。因此,需要立足长远,在“远”中求机遇,在“近”中求经营。
(三)“遍知天下”是其战略筹划的重要基础
战略筹划是战略形成的必备环节,而战略筹划的方法直接决定了战略的质量。不同的战略主体其筹划方法、方式、特征也不尽相同。管子战略筹划中最为凸出的特征就是其“遍知天下”的方法,此种方法不仅涉及情报学的范畴,更重要的是它为战略筹划提供了一套系统的分析统筹模式,对战略客观、全面、务实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
管子将“遍知天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的战略高度,他将“聚财”“论工”“制器”“选士”“政教”“服习”“遍知天下”“机数”称为“兵未出境而无敌”的八项要素,指出“为兵之道,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七法》)。管子“遍知天下”的筹划方法具有三重特征:一是“全知”,不仅要对敌对双方做到知己知彼,更要对天下的各方面情况作全面的了解;不仅要对军事信息进行掌握,更要对各国的经济、社会、外交、民情等等内容有全面的把握。二是“先知”,要做到先敌而知,因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唯有比敌人先知道相关的战略信息才能迅速的捕捉机会,才能做到“早知敌则独行”(《兵法》)。三是“深知”,管子还将“知”从深度上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知形”“知能”“知意”三个层次,最高的层次就是要“知意”,即要深刻的了解敌人的战略意图,掌握敌人真正的战略思想、目的以及出兵的方向[8]。“知意”是建立在“知形”和“知能”的基础上的。所谓“知形”就是了解敌人的军事布阵情况、工事、装备等等有形比较稳定的既有状态;所谓“知能”就是要了解敌人军队的数量、实力以及军队将领的才能、各级军官的指挥素质、士兵的士气等等主观的情况。
管子“遍知天下”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建立在客观全面的方法上。正如《孙子·用间》中所述:“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即,想要做到“先知”,需要切实的调查研究而不可通过祈求鬼神、夜观天象等不务实际的方法去取得。《管子》尤其强调人事的、全面的调查对前瞻的作用。如《八观》中所言及的八观——“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只有通过这八方面的实际调查才能得出敌我国情的真实状况,才能预测出“国之存亡”。同时,《管子》采用的是联系的而非孤立的,整体的而非片面的思维去统一考量国家之安危。如《立政》先预告危机,即“国之所以治乱者三;国之所以安危者四,国之贫富者五”,对这些危机因素进行分析之后,对君主做出了要求或更确切的说是预防危机发生的措施:“君之所审者三……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君之慎者四……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君之所务者五……”。由上可见,无论是对危机的预测、对君主的提醒以及对危机防范的要求都是整体的、相互联系的。
在“遍知天下”的基础上,管子最终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战略设想,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齐国的目标定位问题。一个国家在制定战略目标时,往往会出现两种偏向,一种是“没有抱负”,放弃了本是力所能及的目标;一种是“野心过大”,而现有的条件无法支撑其实现。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述,“好的政府一开始就必须做两件不同的费脑子的工作。首先,它必须选定其对外政策的目标和方法。作出这种决定时,必须考虑到能最有把握地以现有力量保证其实现”[9]。管子在制定齐国战略目标时,能够极好的避免两种偏向,制定出合理可行的战略目标,并且在第一个目标“霸政”实现后,保持极高的警惕,务实权衡后选择“持盈保泰”而非“既霸再王”的战略目标。
首先,霸政诸侯,正当其时。《小匡》中,管仲为齐相后,在论百官时提出,“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为也。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这次对话,其实就是管仲提出“霸王”目标的宣言书。管子“欲霸王”,即先“霸”后“王”两步走的战略规划。“霸政”是第一阶段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王政”的战略手段。经过一系列励精图治,齐国终于实现其第一阶段的“霸政”目标,接下来是按照原有设想更进一步实现“王政”,还是持盈保泰稳固“霸政”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抉择。其次,既霸欲王,其不可也。《小问》中,齐桓公问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即齐桓公在管仲、鲍叔牙等大臣的辅佐下实现了霸业,其想更进一步,就“王业”的战略目标向管仲咨询其可行性。管仲将此问题推于鲍叔牙来,而鲍叔牙又将之推于宾胥无;最后宾胥无告诉齐桓公“古之君王,其君丰,其臣教。今君之臣丰。”意思是说,古代能够成就王业的君王,其威望智识都高于他的大臣,而今天齐国的情况却恰好相反。言下之意就是劝桓公认清现实,打消称王的念头。齐桓公思虑之后说道“周公旦辅成王而治天下,仅能制于四海之内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观之,则吾不王必矣。”这次君臣对话,其实质就是对齐国战略目标的一次再分析,这种分析是基于对齐国客观实际的考量,表面上是说齐桓公的德才智识不足,实质上是出于对齐国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尊王攘夷”的国家间新秩序的深层考量而得出的结论。以此作为立论基础,齐国很难达到实现王业的目的。假若强行为之,将很有可能重新陷入贫弱内乱的窘境中去。因此,打消“称王”这一妄念,符合了齐国的国家利益。在这里,管仲等人的务实明智也正暗合了李德·哈特在《战略论》中的警示:“在决定一个目标时,要学会面对事实,通过调整目的来配合手段,坚决避免‘咬下的分量超过你可以嚼烂的限度’这种愚行的出现。”[10]290
(四)“小征大匡”是其战略实施的主要运作机制
战略其本质在于“经世致用”,战略思想必须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是务实的而非空洞的,是践行的而非玄想的。正如布罗迪所明示的那样:战略思想家的参考架构是纯粹实用的(pragmatic)。他不像科学家是以发现最后真理为目的,而是志在帮助军事和政治领袖来准备他们的心灵和装备,以便能有效和成功地应付其敌人[11]46。务实性的战略思维源于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制定合价值的、合规律的、合实际的战略目标,采用适合的、可行的、可受的战略手段,并以实践成果来检验战略规划的成败。因此,在战略领域的“一厢情愿”与“玄想空谈”正是一种致命的无知。管子的战略思想的务实性就体现在其“小征大匡”的战略实施机制上。“小征大匡”即对很小的征战也要有足够充分的准备与警惧,“小征大匡”最重要的标准在于它的实效性,即所采取的手段是否能够确保既定目标的实现。这种机制内在的具备三重属性,一是充分性,即手段的采取应该足够的充分以确保目标的实现;二是节制性,即所采取的手段应注重“勿过”,手段的滥用既是对本国权力的消耗,也会造成物极必反之势;三是灵活性,即手段应“不拘一格”,做到“因地制宜”“因敌制胜”。
1.“小征大匡”的充分性:“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重令》)正如上言,管子极为强调手段的充分性,若一个国家的在德行上无法荫庇弱小,在国力上虚弱无威,在军事实力上无法臣服诸侯,这样的国家想“求霸求王”是不可能的。管仲相齐之后修内政、展外交、重农商、整军备其实都是为了实现“霸政”这一目标,为了增加手段的“充分性”而进行的。
2.“小征大匡”的节制性:“天下乘马服牛,而任之轻重有制。”《乘马》中将治理天下事喻为驾马驭牛,驾驭者要对牛马的负重能力有所了解,并对承载负担有所限制,若不顾实际过度承载只会物极必反。同样“用力不可以苦”,即征用民力时不能太过头,那样会造成“民苦殃,令不行”即民众疲惫,政令无法施行的结果。又如,管仲尤其重视法治,认为“凡国君之重器,莫过于令”,但反对滥用刑杀之法,那样会造成“令重下恐”的不利局面,而应做到“刑德合于时”,春要“解怨赦罪”,冬要“断刑致罚,无赦有罪”。可见,管仲对治国理政手段使用的节制与运用。
3.“小征大匡”的灵活性:“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乘马》)在讨论营建国都时提出,要利用自然资源,依靠大地之利,所以建造城墙不一定非要符合方圆规矩,铺设道路也不一定要平直如准绳。在军事上,应做到“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这也正如孙子所述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地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7]155即强调作战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式,就如水流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要能根据敌情变化来制定策略,如此才能制胜,才能称为“用兵如神”。管仲这种灵活务实的手段择取贯穿其思想,也正是因为这种灵活与务实才能令齐国“因敌制胜”,开创了春秋的霸政。
二、管子战略思想的结构要素
管子战略思想的突出特点是结构的相对完整。它不仅包含“和合能谐”的政治战略,而且包含“轻重之术”的经济战略;不仅包含“慎谋保国”的军事战略,而且包含“尊王攘夷”的外交战略。在这方面,管子似乎比其它的战略家更要接近当代大战略“全”的结构特征。这是本章对此做具体分析的原因所在。
(一)管子战略思想的政治谋略——“和合能谐”
“和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与理想境界,它不仅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一个社会的稳定、进步、繁荣、昌盛的重要保障,可以说“和谐”既是目标又是手段,是价值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历来重视“和谐社会”的构建并留下了大量关于“和谐”理论与实践的宝贵财富,“和谐”思想也已深植于国人心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
1.“和谐”思想释义。诸子百家对“和谐”的释义与倡导各有表述,如儒家提倡的“中和”“以和为贵”“和而不同”,道家的“法自然”,以及墨家的“兼爱非攻”“兼相爱、交相利”。总之,“和谐”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辅相成、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2.管子的“和合能谐”理念。管子的“和谐”思想非常丰富,内容涵盖国家的各个方面,但它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将“和谐”提高到了政治高度并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实现方案。管子“和谐”思想所要达到的是“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形势解》)的理想状态,要达到这种状态则应做到“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徳,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兵法》)即要“以人为本”,用道、德来蓄养之则老百姓才能和睦,和睦才能团结,和睦团结便可协调一致,全国上下协调一致便可无敌于天下了。管子不仅在社会层面上强调和谐,在自然观上更是强调“人与天调”的和谐思想,认为人类只有按照自然规律去行动,与自然规律保持协调一致美好的事物才能生长出来,即“天地之美生”(《五行》)。具体来讲管子从政治的高度对“和谐”进行展开,力图通过相应的战略手段达到君民和谐、君臣和谐、自然和谐、社会和谐以及天下和谐的目标。
3.管子为实现和谐目标的战略举措。通过“爱民富民”实现君民和谐。管子相齐,其内政治理方略尤为重视“爱民富民”,并将其作为齐国的基本价值进行贯彻实施。首先,“爱民富民”是君民和谐、政权稳固的首要前提。“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牧民》)。因为民众“恶忧劳”“恶贫贱”“恶危坠”“恶灭绝”,君主若能“佚乐之”“富贵之”“存安之”“生育之”。那么百姓就会愿意为君主而忧劳,为之忍受贫贱,为之赴汤蹈火。只有“爱民富民”才能富国强军。只有重视民本才能富民,在此基础上才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同上)。因此,只有重民,才能富民;只有富民,才能富国,富国乃是强军的基础。只有“爱民富民”,才能使“远者自亲”。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个重视民生发展的国度才能使万民来赴,使本国疆土得以充分开垦,兵源得到及时补充,进而才能更有力的推动富国强军目标的实现。从漫长的历史征程中我们不难发现,骄奢淫逸,重负盘剥,不顾人民死活的政权很少有能长久的;而那些重民重本,藏富于民,节制勤俭,深得民心的政权很少有不成功的。
通过“朝有经臣”实现君臣和谐[12]。君臣之间的和谐是国家职能得以顺利运转的重要条件,管子对君臣间的关系也有着深入的见解,认为“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形势解》)。即只有君臣之间相亲上下之间和睦才能保证政令通畅。在如何实现君臣和谐问题上管子提出“朝有经臣”的方案。所谓“经臣”是指“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重令》)。这在道德、品行、能力、忠诚等多个维度对“经臣”进行了量化描述,朝廷需要以这些标准去选拔人才;同时还推行“乡里察举”“察问”制度,希望能将国家的秀才良将选拔到朝廷中来为国效力。要实现“朝有经臣”的目标除了做到“择之有法”还需要“任之有术”,这首先便对君主自身品行提出了要求,君主需要有水一样的品质做到“仁、精、正、义、卑”即仁慈的、分明的、正直的、恰当的、谦卑的,这是达到君臣和谐的基本条也是招揽和使用人才的必备素养,在此基础上君臣要各司其职不得越俎代庖,因为“主行臣道则乱,臣行主道则危。故上下无分,君臣共道,乱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则乱”(《明法解》)。即在君臣职能上要有明确的界定,君主要做的是“兼而一之”,人臣要做的是“分而职之”;君主要能“善用其臣”,人臣要能“善纳其忠”;君臣之间要做到“上明下审,上下同徳”(《君臣上》)。这样一来君臣之间才能和谐共处,国家行政才会清明高效。
通过“人与天调”实现自然和谐。管子的自然和谐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人与天调”的思想上。《五行》中记述:“固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通若道然后又行,然则神筮不灵,神龟不卜,黄帝泽参,治之至也。”意思就是通过对规律的把握与应用,所制定的治理目标才能到达很好的效果。“人与天调”的思想与《周礼》中“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以人法天”的思想相吻合。人与天调首先是人与“四时”的和谐,《四时》篇中开篇即讲“令有时”,意思就在强调政令的发布与实施必须强调时节,因为“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即政令适应四时则获得福祉,违背四时则产生祸患。在《四时》篇中,着重阐述了如何根据春夏秋冬的具体特征来发布行政目标与措施。其次,人与天调是人与“五行”的和谐,《五行》篇中总结了天地万物因“五行”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规律,认为金木水火土每一“行”都具有其德性,并在一定时间主宰着世间万物,因此政府颁布的法令政策要依照五行的性质进行施政,如此才能合乎天道,顺应规律从而避免灾患进而获取成功。人与天调还表现在人与“水地”的和谐,《水地》篇中对水的特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主要思想在于君王如何根据水所显示出来的特性来提升自我修养,因为帝王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战略的抉择与实施。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多如牛毛,例如三国时期那个“扶不起的阿斗”,任凭诸葛亮如何高超的战略运筹,还是无法弥补愚蠢的君主所带来的拖累。其次,《水地》篇还把水性与人性相联系,认为人性与水性是相对应的,只要掌握了那个地区的水的特性,就能了解这个地区的人性,进而采用不同的治理方法。这种看法,现在看来是有点不合宜的,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管仲人与天调的思想。
通过“礼法并举”实现社会和谐。社会治理是每一个政权所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因为具体时代背景以及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差异,所以在社会治理的方法举措上也会有所不同。如同中国古代法家崇尚的是严刑峻法,儒家推崇的是道德教化,管子则采取了“礼法并重”的社会治理方案。管子将“礼、义、廉、耻”称为国之“四维”,国家如果失去其中的一条就会发生倾斜,失去其中的两条就会出现危机,失去其中的三条就会被颠覆,而四条全部丢失国家也就灭亡了。“礼”的教化能够使百姓不逾越节度,“义”的教化能使人们不妄求进取,“廉”的教化能使百姓不欺瞒罪恶,“耻”的教化则可使百姓不从流合污。“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牧民》)因此“四维”的礼制教化是安国固本实现社会和谐的的重要手段。管子对和谐社会的治理还有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即“以法治国”,认为“威不两错,正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明法》)管子在立法和执法上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如要“有法必行”“执法无私”“法必有常”,这都为齐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打了的很好的基础。总而言之,“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权修》)。即只有“礼法并举”才能实现国家安定,社会和谐。
通过“尊王攘夷”实现天下和谐。天下和谐可以说是管子“一匡天下”的梦想,而“尊王攘夷”不仅仅是个响亮的口号而是现实这个梦想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尊王”是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权威以结束中原各国纷争不断的局面;“攘夷”是为了解除中原的外部威胁以换取和谐的外部环境。具体内容详见第四节。
(二)管子战略思想的经济谋略——“轻重之术”
管子的经济战略思想集中在《轻重》篇中,这对当时乃至日后中国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其经济调控思想不仅包含了对本国经济的调控,还包括对国外经济的调控,这种调控其实可视为早期对他国发动的“经济战争”。例如,《侈靡》篇倡导奢侈性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无论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提倡奢侈。这样一来,“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即富人进行奢侈的消费,穷人才有更多谋生的机会,如此一来,百姓才会振奋而有了生业。再则,《轻重甲》还提到通过设立倡导鬼神祭祀的活动来间接增加国家税收,而非采取直接征收的方式;因为祭祀需要的祭品价格会在节日时得到大幅提升,因而也不必从房屋、粮食等处征收税项了。《地数》篇中还提出,通过对盐的季节性操控对他国进行“进攻”。因为楚国可以产黄金,齐国和燕国可以产盐,而其他国家无盐可采或产量很低,君主可以先趁机下令砍柴煮盐,等到阳春播种的季节发布禁止民众煮盐的政令,如此一来食盐供不应求,盐价必定上涨40倍,君主可以将已经上涨40倍的食盐运出卖给梁、赵、卫等国。如此一来君主可以通过盐价的季节性调控换取天下的巨额财富,进而使他国的财富锐减而没有充足的财力对我国进行损害行动。在那个时代,已经有了经济战争的雏形,真是令人叹为观止[6]77。管子经济战略中最为影人瞩目的就是他的“轻重之术”。
1.“轻重之术”的含义。“轻重”一词最早出现在《国语》一书,《史记》在《管晏列传》《齐太公世家》《平准书》书中都有管子使用“轻重之术”来辅佐齐桓公的相关记载。然而“轻重”理论最为集中和系统出现的是在《管子》一书,书中直接以“轻重”为题的有7篇,简介涉及和论述的有12篇,合称《管子·轻重》19篇。“轻重”在含义上有多种解释,但就《管子》中“轻重”的含义可解释为关乎“钱”的问题,“轻重之术”是关于如何通过对商品流通和货币价格的调控来实现国家财富积累与流通的方法,即马非百所解释的“封建国家应通过运用‘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的供求规律,实行‘敛轻散重’的物价政策,以达到‘无籍而赡国’即‘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财政目的。”[13]53
2.“轻重之术”的作用。管子非常重视“轻重之术”的运用,认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国蓄》)。“通于轻重之数,不以少畏多。”(《山权数》)“不通于轻重,谓之妄言”(《山至数》)。即国家的统治者如果不通于“轻重之术”则不能很好的留住老百姓,不能做到调整疏通民利,更谈不上通过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的大治;如果君主通晓轻重之术,就不会因为自己的钱财少而惧怕资财多的国家,这是一个国家理财的重大政策,不可以不谨慎小心。就战略而言,“轻重之术”对国家有两大作用:其一“轻重之术”可以使国内以及国家间的人、财、物得以顺畅流通,并通过“轻重之术”的各种手段来实现国家财富聚敛的作用;其二,“轻重之术”可以对相关国家发动经济战争,通过供需、货币等手段扰乱并破坏敌国的经济秩序,使敌国陷入失衡状态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3.“轻重之术”的实施。“轻重之术”的实施需要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首先,本国必须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则谈不上经济调控,更谈不上运用大量货币去操控敌国的供需关系。即“国有十年之蓄”方能答到“尽有之”的目标(《事语》);其次,必须寻找到不同敌国的经济要害。在当时而言,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定的首要因素,因此也成为了遭到攻击的首要目标。但是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所以攻击的目标、方向、层次都有所侧重,但基本上会围绕各国不同的经济资源来展开,例如食盐等;再则,“轻重之术”的运用没有固定不变的法则,而是需要根据变化着的实际做出适应性调整。如《轻重甲》所记载的:“齐桓公问管子:‘轻重有数乎?’管子回答说:‘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这也意味着“轻重之术”的成功实施有赖于决策者高超的权变能力。
“轻重之术”的实施围绕“战衡,战准,战流,战权,战势”五种基本方式来展开[14]。管子所说的“五战而至于兵”(《轻重甲》)即通过这五种战略方式的灵活运用便能达到兵不血刃的效果。这五种方式实质上是在经济的供求、价格、流通、权术、形势五大领域的具体展开[14]。“战衡”就是通过操控供需,使二者失衡从而达到“低买高卖”的获利方式。“战准”就是以价格作为杠杆通过进出口贸易以获取重要物资的手段。这种形式的盈利方式又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如国际贸易平衡的情况下应该采用“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的指导原则进行商品定价,这样能够保持本国商品与各国商品价格的一致,从而避免“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情况的发生;如果本国急需但是生产滞后则应采用“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的原则抬高所需商品的价格以使国外相应资源的大量流入;而当本国生产的产品出现盈余时,则采用“天下高我独下,天下重我轻”的方式将富余产品以低价的方式输出他国从而获利。“战流”主要是针对国家重要物资在流通领域所采取的“谨守重流”政策,这种政策通过严守高价来确保本国重要物资的储备。“战权”则是指在与各国的经济博弈中通过权术、谋略的使用使敌国在经济上自造障碍而陷入危机的方法,如《轻重戊》所记载的“服帛降鲁梁”就是“战权”的一个经典案例:鲁国和梁国擅长织绨,经过管子的精心筹划齐国上下一律穿绨服并禁止本国生产,所有绨服全部从鲁国和梁国高价进口,在利益的诱惑下两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放弃农业生产而转移到织缔业上来,一年后管子探听两国的情况便让齐桓公带领百姓改穿帛料衣服并封锁关卡与两国断绝贸易往来,如此一来两国绨服大量滞销并且粮食缺乏,两年后两国大量百姓归属齐国,三年后两国国君也正式降齐。这种通过利诱的手段使敌国放弃自身的基础产业,并在适当的时机通过经济绝交的方式使敌陷入危机,进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权”法确实让人惊叹。《轻重戊》中的“买鹿制楚”“买狐皮降代国”所采用的方法同属此例。“战势”即在经济领域要善于捕捉有利的时机与形势,通过因势利导来打击敌国。管子的“战势”思想几乎贯穿其战略始终,“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轻重丁》)的思想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是涵盖了其在政治、军事、外交中的战略。
(三)管子战略思想的军事谋略——“慎谋保国”
军事谋略是管子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对军事战争的态度不同于尹文的“寝兵”,孔子的“去兵”,墨家的“弭兵”,也不同于商鞅的“苦忍好战”,而是采用了非常清醒务实的“节制之兵”[15]。这种对军事战争的节制态度源于两种认识,一是清醒的认识到军事战争对国家与君主的重要作用,认为“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王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参患》)。二是对战争的危害性有着明确的认知,认为“夫兵事者,诡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失谋而攻,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兵法》)。总而言之,管子对待军事战争这把既具有重要性又具危害性的双刃剑采取的是“慎谋保国”的总态度。
1.“慎谋保国”之理义。如李德·哈特所述:“一个良好的理由(师出有名)是一把利剑,同时也是一块防盾。”[10]278管子在实施“慎谋保国”的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总是为齐国寻求道义上的根据和支持,并且善于将道义化成权利。管子在对敌使用军队时必定是以“正义之师”的角色出现在战场上,这种“举之必义”的做法与其对战争性质的划分有着紧密的联系。管子认为“成功立事,必须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七法》)。即做任何事情想要获得成功则必须使行为出于道义。管子将军事战争分为正义的和不义的两大类,正义之战是“案强助弱,禁暴止贪,存亡安危”(《幼官》)的;而不义之战则“贪于地”,这种不义之战无法令人信服也无法从根本上战胜敌人。《霸言》中论述到一个国家想要实现霸政,必须具备很多必要性的条件,而最根本的就“国修而邻国无道”。即首先要使本国政治清明,民富国强,整军振武。但即使拥有这些条件还不足以实现霸政,还需要等待时机,这个时机就是邻国的“无道”,在这里敌我双方的道义则演变成了衡量胜负的重要手段。管子还有一套完整的“制人论”,认为“凡国有三制: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佚亦佚,进退劳佚,与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枢言》)。即一个国家只有“德盛义尊”才能制人,可见其对国家德行与道义的重视。因此,在实施“慎谋保国”的战略中管子首先便为齐国树立起“尊天子,攘夷狄”凛然道义的形象,在主持正义、维护礼制的国家形象使齐国对他国的征伐变得师出名门并且使他国对齐国的侵扰失去了道义上的支持,形成了“攻守兼备”的态势。在塑造国家正义形象上管子采取了以下步骤,首先进行一系列内政革新为齐国树立起内政清明、国富民强的形象;其次采用“不以勇猛为边竟”(《枢言》)的政策达到“边竟安”“邻国亲”的局面,甚至还让出自己的土地为灭亡的小国进行复国和保护,这些举措为齐国在国际上赢得了诸侯国的赞誉与信任奠定了非常扎实的基础;再则便提出“尊王攘夷”的国际号召,在中原各国群龙无首、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这种号召下为齐国带来了空前的威望。正是管子将“理义”与“权力”的完美结合,使齐国常年不受到外国的进攻并在无后顾之忧的保持向进攻的战略态势。因此,管子在“慎谋保国”中采用的“竞德”优于“竞兵”的思想为齐国建起了一座坚固却又无形的防护墙。
2.“慎谋保国”之备战。现代著名的战略家约翰·柯林斯认为“力量的优势是确保和平的最好手段……侵略国面对这种压倒的优势很可能在进行侵略前就放弃其侵略意图了。”[1]140管子在“慎谋保国”的过程中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态度,认为“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以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重令》)。即只有国富兵强敌国才不敢随意来侵犯,因此积极备战则成为了管子军事战略的一个重要任务。管子采取了多种办法进行强军备战。首先,在制度上采用“寓军于政,平战一体”的政策将军事与政事、将平时与战时有机统一起来。在具体做法上是将齐国分为三部分,每部编为一个军并分别由桓公、高子、国子掌管,三军下设乡,乡有行伍,由当地的长官通过狩猎演习的方式训练老百姓让他们熟悉军事战争,训练好后“令不得迁徙”,让这些军士固定下来不得随意的迁徙,并做到“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小匡》)。在平时主要从事农事,战时则拿起武器进行战争,“平战一体”的政策能使之“守则固,战则胜”[16]。其次,重视武器装备的升级改造与管理。中国的兵学有“重人、重道、轻器、贱物”的传统[17],即在战争中对人和战略理论的重视远远超过对武器装备的重视。但是管子却认为“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参患》)。即认为论兵首先就要讨论武器装备的问题,只有“审器”才能“识胜”。因此管子对兵器的改造升级可以说极为用心,要求军队“求天下之精材,论百工之锐器”(《幼官》);除了要求军队不断创新武器装备外管子对武器装备的管理问题也极为重视,要求建立严格的武器管理制度,建立齐军的武器装备库,对质量低劣的武器不予以入库、对破损的残缺的武器要及时修缮、对军备的出库入库要实行登记制度,这种分工细密流程明晰的军备管理制度可以说在当时具有非常创新性的意义;管子对军队后勤保障也极为重视,认为战争必定会产生大量的物资耗费,物资的能否及时补给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所以对兵员、粮食、兵器、城寨都有明确的规定使齐国“甲兵大足”,拥有了与世界争霸的器物基础。其三,管子对士兵的技能与素质的提升注入了大量的心血,认为“万乘藏兵之国,卒不能野战应敌,社视必有危亡之患”(《重令》)。管子将能战与否视为军队训练的首要目标并为这个目标提出了明确的量化标准——“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困”(《七法》);其练兵从选兵开始,要求以严格的标准“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同上);选兵后则以严明的军纪、艰苦的训练、军队武德的淬炼、奖罚分明的催促进行规范,最终为齐国练就了一支极善搏杀的无敌之师。如《荀子·议兵》所谈及的“齐人隆技击”、《汉书·刑法志》所述的“齐人以技击强”,高超的军事技能成为了齐军百战百胜的重要基础。总而言之,管子从制度、军备后勤、士卒训练三方面为国家的安全保障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17]。
3.“慎谋保国”之攻取。以武力对敌国进行攻取是“慎谋保国”思想中层次最低并直接应对战争的阶段,由于这个阶段的暴力性、惨烈性以及不可逆转性让战争的指导者不得不更加“慎谋”。管子在指导战争的慎谋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极为重视情报的收集与分析工作,认为“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七计》)。即不注重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却想举兵行军就如同没有船只樯橹却想渡过险滩一样是难以成功的。在情报工作上管子强调要做到“遍知”“先知”,要在正式出兵前将敌我双方及其余邦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将帅等要素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并且还要求通过敏锐的洞见力“先知”,“早知敌,则独行”(《兵法》)。即只有先敌而知才能迅速捕捉战机并在战场上寻得主动权。“遍知”“先知”实质是为“慎谋”打下了深厚的信息基础。第二,主张对发动战争的时机有深刻把握,认为“时之处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固曰,今日不为,明日亡货。昔之日已往而不来矣!”(《乘马》)因为时间与空间有着不同的性质,时间的单维性和不可逆转性致使战机转瞬即逝,一旦错过将悔之莫及。第三,采取积极灵活的战略战术,认为“无方,胜之机”(《幼官》)。即战略战术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战场上也没有一成不改的打法,而是必须根据敌我双方的现实情况做出适应性的调整,在战争指导中只有做到“无设无形”才能够达到“全胜而无害”的境界。第四,不主张蛮力硬拼的作战方式而提倡“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霸言》)的“乘瑕”思维。即要寻找到敌方的薄弱点发动进攻,这样的进攻才具有很高的效率,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对敌国“瑕”或者说薄弱环节的寻找与判断也构成了“慎谋保国”的重要基础。
(四)管子战略思想的外交谋略——“尊王攘夷”
战略家更为重要的目的在于引领历史,开辟未来。因此,不能仅满足于适应与应变,而须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精神进行战略创新,因为“战略创新是最好的战略发展,它使战略主体处于最有利的战略格局中,往往是最有效的战略导向”[18]98。管子所处时代背景与前朝不同,然而他却能做到“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正世》)。做到不盲从于古人,不拘泥于今人,而是根据新形势,提出新战略。管子的战略创新最精彩的莫过于“尊王攘夷”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这个战略创新让齐国一跃成为春秋首霸,而后一直被春秋乃至战国各诸侯所沿袭。“尊王攘夷”战略可以说是管子战略思想的一项伟大创见,“尊王”符合春秋道义,“攘夷”符合中原诸侯的整体利益。道义与利益为齐国“尊王攘夷”霸政的实施进行了正名,通过“尊王攘夷”的外交手段加速了齐国“一匡天下”梦的最终实现。
1.“尊王攘夷”取得成功的原因。“尊王攘夷”战略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生命力原因在于:首先,“尊王”是切合实际的。周平王东迁后,周朝天子大权旁落,各路诸侯各自为政,对东周政权既不理会也不上贡,但没有哪一家能够有足够的实力兼并所有诸侯进而建立一个匡扶四海的政权,因此,东周政权名义上还是“最高政权”。齐国认清这个事实,提出“尊王”的口号,“尊王”的口号为齐国霸政提供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诸侯国不尊重周王室,齐国便会领兵讨伐。反而言之,各路诸侯不遵从齐国,就是对周王室的不尊。实质上讲,齐国在“尊王”的号召下代周行王事。其次,“攘夷”是获得普遍拥护的。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常常受到来自边境民族武装的滋扰,“北戎”南下,“西戎”东进,“南蛮”也是跃跃欲试向北扩张,中原各国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滋扰。因此,齐国的“攘夷”政策其实是找到了各诸侯国之间的共同利益——生存。“研究大战略的人有必要找出那些与国家安全特别有关的利益。最最重要的国家安全的利益是生存,即国家的生存……各国负责的领导人都愿为那些涉及国家存亡的重大事件而献出自己的生命。”[1]11齐国正是找到了各诸侯国间的共同利益——生存,在生存利益的号召下进行会盟是齐国霸政的又一块铺路石。最后,“尊王”与“攘夷”是相辅相成的。“尊王”是为整个同盟找到共同的领导者,周天子虽然是名义上但又是“最好的领袖”。“每一个成功的国际安全联盟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只要利益一致,合作就继续下去;合作一旦终止联盟也就垮台”[1]12“攘夷”正式找到了这个切中要害的共同利益,为由齐国主导的同盟找到了共同的事业,有了共同的事业才能有协调性的行动,才能推动齐国霸政的真正确立。总而言之,“尊王”使齐国能代王行政、师出有名;“攘夷”使齐国获得协调统御中原各诸侯的真正权利。
2.“尊王攘夷”实现的主要方式。“尊王攘夷”战略主要是通过“会盟”的方式来实现。管子时期共进行了9次大规模的会盟,其中武装会盟3次,和平会盟6次,并且每一次会盟都是齐国迈向霸主地位的重要节点。管子所推动的“会盟”可以说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个目标。其方式大致为号召诸侯,缔结盟约,加强团结,抵御外辱[18]86。齐国的会盟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目标与侧重点并不相同。第一个阶段是齐国早期借会盟的名义剿灭异己扩大威望,如对谭国、遂国的剿灭即为此例;第二阶段是齐国以会盟的方式号召中原各国对夷狄发起进攻以保障各国的共同利益,如联合宋国、曹国营救被狄人围攻的邢国以及联合鲁国、宋国、陈国等八国联军对楚国发起遏制;第三个阶段则将会盟当成一种政治手段,用于解除对峙实现边境安定,最后与楚国的和解与同盟即为此例。管子时期的“会盟”又可以分为“兵车之会”与“乘车之会”。尹知章注解说:“兵车之会,谓兴兵有所伐。”即“兵车之会”是各国带领军队的联合作战;而“乘车之会”则是不带军队的和平会盟,据《大匡》记载:“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请事,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飨国四十有二年。”这意味着当时管子所采用的会盟方式主要以和平会盟为主,也表明“管仲在执行此种政策时,几乎是完全依赖外交手段的微妙运用,至于武力则尽量保留作为后盾,或最多只是作有限度的使用而已”[18]88这种不滥用武力与杀伐的会盟在当时乃至当今都是难能可贵的。
3.“尊王攘夷”所采用的行进路线。“尊王攘夷”战略采用的是“先易后难,先北后南”的行进路线。“先易后难”的路线主要是针对中原诸国展开的攻势,期初齐桓公以报收纳公子纠为借口于公元前684年对实力强大的鲁国发动进攻,鲁庄公在曹刿的辅佐下在长勺打败齐军,而后齐军再次联合宋国攻打鲁国但还是无功而返。两次军事行动的失利也让齐国转变了进攻方向,在管仲的建议下,齐国将目标转向实力弱小的与齐西邻的谭国(今山东济南东),以其不尊重齐桓公为借口发动了进攻,贫弱的谭国很快被消灭,齐国国土得到扩张;随后在公元前681年进行北杏会盟,因为邻国遂国(今山东肥城南)被邀而未参加,管子趁机出兵消灭遂国以提高齐国的威信力;实力较强的鲁国看到齐国已将不服号令的谭、遂两国剿灭,再加上战场上的连连失利便同意会齐国在柯(今山东东阿西南)会盟修好,此次会盟齐国可谓达到了阶段性胜利,从此齐鲁之境再无大战;此后又以同盟的手段对背叛齐国的宋国发动进攻,胜利后又对四分五裂的郑国、发生内乱的鲁国进行会盟调停,最终中原各国纷纷屈服于齐国,在公元前667年齐国在宋国的幽发起会盟,周天子代表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原诸侯国都参加了此次会盟,齐国至此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先北后南”的路线则主要针对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展开的,北方的山戎、狄,南方的楚国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中原发动进攻,中原边境各国不堪其扰便向盟主齐国求救,针对出兵方向和先后问题,管子向齐桓公提出了“先北后南”的战略方向,认为必须趁燕国被犯而求助于齐国的机会出兵北方,只有将北方安定了才能更好的号召中原各国对付实力强劲的南方楚国。在武装平定了山戎、夷狄后,齐国则以“救郑抗楚”的名义邀请中原的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组成联军南下与楚国形成了军事对峙,由于实力相当楚国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而齐桓公、管子也无意用武力与强大的楚国直接冲突,最终双方同意结盟,从此南北军事对峙的局面结束,中原两面强敌的围攻也得到了解除,这也是管子采取正确的战略路线所取得的成果。
三、管子战略思想的历史影响与当代价值
(一)管子战略思想的历史影响与局限
管子战略思想对历史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实践上,管子的战略思想成功指引了齐国的发展,通过各种切合时宜的改革终于使齐国走出了贫穷、内乱的困局。7年的苦心经营让齐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综合实力大幅增强,齐国的面貌与桓公初即位相比可谓焕然一新,随后又以“尊王攘夷”为号召采用多种手段北战南征,平定中原各国的内乱、解除中原南北的威胁,实现了“一匡天下”的梦想。在理论上管子战略思想一直为后世所承袭或重视。例如,《管子》一书是以管子战略思想为基础而著述的,而后来西汉淮南王刘安所倡导构建的治国理论体系《淮南子》和管子战略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代表管子战略思想的《管子》也是后来历朝历代英雄俊杰所研究的重要著述。
当然,管子战略思想有其局限性。首先,管子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制度人事安排帮助齐国逃出“人亡政息”的厄运,致使管子去世后齐国立即陷入大乱,齐桓公更是惨死奸臣之手,管子苦心经营的政治遗产没有得到继承,并随着他的去世而灰飞烟灭。也有学者总结了《管子》中的君主模式论,认为其缺少君主机制的论述,只强调通过君主人格道德修养,君主自我监督、自我反省、自我完善的方法达到理想政治的境界,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19]。国家的体制机制问题值得后来人的深思。其次,管子的战略具有某种不彻底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没有从根本上实现中原各国的融合与团结,没有彻底改变中原国家“群龙无首”的局面。“尊王攘夷”仅仅是权宜之计,这种战略既没有在根上重新确立和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地位,也没有使齐国横扫诸国实现统一,而仅仅是建立在强国政治的基础上的。一旦主导团结的国家陷入衰颓,这种表面的团结就会被撕成一张碎纸。第二,这种不彻底性还表现在对中原南北两面强敌的措施上。管子所采用的是“击退”而非“击毁”,所以北方的夷狄虽然遭到军事重创而被迫迁徙,但是由于后续的军事外交手段跟不上,导致夷狄政权休养生息后又卷土重来。对待南方的楚国也是如此。楚国只是迫于中原联军的威势而形成与齐国的会盟,它并没有持久性。所以,春秋五霸之首为后来的乱局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再则,管子夹杂着很多的朴素思想。例如,他直接把水的不同性与各地民众的特性进行对等显然是不妥当的。水质浑浊苦涩地区的人民就一定狡猾、巧佞、贪财好色?显然不甚妥当。当然,以当今的视角去评价管子战略思想的缺点并非要苛求古人,管子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它也应当得到历史的理解。
(二)管子战略思想的启示
管子战略思想对当代的战略仍有着巨大的价值和启示。本文最后对管子战略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从大战略的角度进行了总结,认为当代战略的理念与实践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有大战略的整体架构。管子战略思想的结构要素在今天依然具有价值,包括“和合能谐”的政治战略、“轻重之术”的经济战略、“慎谋保国”的军事战略和“尊王攘夷”的外交战略。他的更加注重“非战”手段运用的思想也具有启发性。梁启超先生在评述管子经济思想时称“管子言五战然后至于兵,则军事似非其所甚重。”[2]96认为管子实际上是把军事手段放到了次要地位,且更加注重以非军事手段来达到目标。这种结论是有现实依据的。如管子在战略实施中和平会盟的外交手段远远超过实际的军事行动,值得一提的是管子更注重运用经济手段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些思想也为当今大战略思想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定依据与思路。安德烈·博福尔将大战略视为是各种战略的汇集,是“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它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1]112。大战略思想的鼻祖李德·哈特则进一步将大战略的整体构架比作一个金字塔结构,大战略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并指导从属于它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等具体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这种比喻我们认为是合理的,人类发展至今,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出现使战争变成来一种极度危险的达到政治的目的,或者说战争已经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工具。所以,在接下来的战略博弈中需要更加注重挖掘和使用多元的非军事手段。同时,不仅要从静态表征的视角还要从动态协调的视角来看大战略的整体结构,大战略思想包括了“大目标”“大手段”以及“大协调”,“大目标”“大手段”是静态的战略结构表征,而“大协调”则是动态的战略结构表述,是对子战略间、战略内部要素之间的合理协调与安排,是保证“大手段”能以最优组合实现“大目标”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在当今日趋复杂的战略环境背景下,凸出整体构架的动态“大协调”观显得尤为重要。
二是要有大战略的长远视野,把握战略机遇,避免战略的短视和执行上的不到位,从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上走出“人亡政息”的轮回。这方面,实施机制的重要值得今人进一步思考。管子的战略从近期看是成功的,其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立足齐国、眺望中原、胸怀华夏,完成了那个时代其他人无法完成的任务;但从长远看又是失败的,因为管子的战略遗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安排,并在其去世后连同管子一道埋入了泥土中,“人亡政息”让齐国苦心经营的盛世局面瞬间灰飞烟灭。这种短暂的成功并没有换来长久的和平,从根本上讲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是战略的短视,因为没有看到“战后的和平”。在战略实施的机制上管子战略也表现出了某种不彻底性,管子战略只给中原带来了短暂的安宁,既没有从根本上确立周朝的权利基础,又没有使齐国成为取代周王朝的新一代政权;既没有彻底击毁北方夷狄,又没有与南楚建立真诚的联盟关系,而只是在灰色地带求得一时安宁。当时的齐国是最有实力开辟新王朝的国家,就是因为战略实施机制上的缺陷让齐国失去了这样一个绝佳的机遇期。就当前的战略形势而言,战略的视野需要摆脱陈旧狭隘的战略观而放得更加长远,应以大战略的视野更加注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加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更加注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加注重挖掘新的有效管控人类分歧的手段、模式机制,更加注重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科学性、艺术性及可持续性。这需要以战略哲学的价值论与认识论为基础去重新审视,在战略的范围、结构、模式、机制以及战略优势等要素上作进一步的梳理和研究。
三是要深刻理解当代战略思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特点,并由此把握管子“利义并重”思想的难能可贵,进一步深化对战略本质的理解,并在实践上推动战略的文明转型。如上文所详述的,管子的战略思想一直遵循着“利义并重”的原则,而且这种“利义并重”不仅把“利”变成“权”,而且善于把“义”变成“权”,即把道义完美的变成了权利,这种利义的完美融合使齐国既拥有了尖锐的矛又拥有了牢固的盾。其实所谓的“利义并重”就是当今哲学术语所倡导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价值理性是战略的价值追求、道德追求,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驱动力和道德约束力,而工具理性是达到这种目标所采用的手段、方法,为价值理性提供可行的现实路径,二者在逻辑与效用上相辅相成,但在战略实践中又常常相互分离,走向极端。例如,马基雅维利将“利”或“工具理性”凸出强调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认为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这种野蛮的丛林法则让人遗忘了最初的价值追求,就像李德·哈特所说的那样“人类历史打了无数次战争,但大都是劳而无功”[20]383。又如,国际政治中的理想主义学派常又将“义”或“价值理性”予以过度强化,使之超脱了现实的政治理念,体现了人类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与向往,诚如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21]106。但理想主义缺乏实证的精确研究与手段支撑,容易导致战略上不切实际。因此战略家们应该抛弃片面的、单维的价值理性观或工具理性观,将二者统一回归战略的考量,从而进一步促进当代战略的文明转型。
[1]约翰·柯林斯.大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78.
[2]梁启超.《管子》评传(诸子集成本第六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
[3]段培君.“战略思维理论和方法”,中央党校讲稿,2016年3月17日.
[4]王日华.《管子》的霸权思想及其现代化——兼与西方霸权理论比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3).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李山.管子译注[M],中华书局 2009.
[7]任俊华,赵清.孙子兵法正宗[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8]王崇.谈《管子》中的情报分析思想[J].学理论,2015,(8).
[9]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利斗争与和平(第七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李德·哈特.战略论:间接路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1]Brodie,B.(1973).WarandPolitics.London:MacmillanPublishersLimited.
[12]杨国宜.《管子》和谐治国理念的现代诠释[J].合肥学院学报,2014,(3).
[13]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王珏.轻重之术:管子的经济战谋略[J].管子学刊,2011,(4).
[15]杨永林.《管子》的兵学思想简论.管子学刊,2009,(1).
[16]邵先锋.论管子寓军于政、平战一体的军事思想.管子学刊,2009,(2).
[17]张颂之.试论《管子》兵学技巧——《管子》兵文化学之一[J].管子学刊,1995,(2).
[18]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M].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
[19]谷玉梅.《管子》君主模式浅析[J].齐鲁学刊,1992,(6).
[20]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1]奥斯卡·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