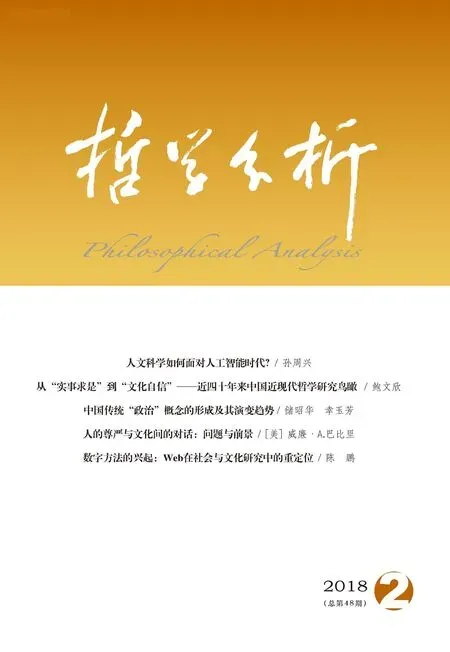价值相对主义就是价值虚无主义
——苏格拉底论正义与定义
安希孟
一、价值相对主义
我们必须反对价值相对主义、价值怀疑主义、价值不可知论和价值虚无主义,反对二元论、多元论、多中心或无中心论价值观,反对“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立场。相对主义认为:真理并非绝对的,只能根据其他事物加以判断;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因立场不同、条件差异而相互对立的观点。真理和正义都是价值,否则就不会有“为真理而斗争”。当代世界的“正义”与“社群”之争,当然首先要伸张正义——正义在先,才有社群。正义就是符合定义、合乎标准、中规中矩。社群应按正义办事,否则不能成群结伙。社群服从于更大共同体,方能走出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自留地,方能推进全球文明与多元文化的协调发展。多元以全球文明之一元为前提,多元归于一元,这个共同之“元”是普遍标准、共同价值。
普遍的价值指那些不分畛域,超越信仰、民族、国家,出于人类的良知与理性之价值观念。价值相对主义则认为,价值评价与价值规范无法形成普遍价值,因而否认了价值一般。价值相对主义源于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主张道德观念的多样性、文化的差异性、道德的不确定性和情景的变异、多元化,并不一定排斥价值的确定性。例如,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涂尔干等所主张的“文化相对主义”,推崇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允许道德或价值无标准和杂乱。再往前追溯,古希腊哲人不承认民族、种族、宗教的差别,追求普遍性与永恒性,这恰恰是哲学的本质所在,它与相对主义水火不容。近代则有康德,他提出人为自然界立法,认为道德是绝对的,道德律是一种绝对命令,它不允许随心所欲,而是要做符合准则的事。行动者要遵守道德准则,即“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这种绝对命令是普遍必然的,是先验 的。
相对主义在逻辑上就站不住脚。相对主义把“价值相对主义”奉为圭臬,然而一旦成为“主义”,便绝对了,即以相对为普遍。“主义”者,“主”张一个“义”,就不是相对的。“价值相对主义”否认普遍价值和价值一般,只讲价值的相对性、随意性、流变性、短暂性和主观性。相对主义诡辩论本质上属于虚无主义。价值相对主义则与价值虚无主义互相定义,其共同结果就是不辨是非。我们应该走出价值相对主义中隐藏的虚无主义泥淖。价值不是自封的,不是相对的,而是公认的、普遍赞成的;它是一般性的,是规律。
二、价值与定义
价值哲学的兴起,表明普遍价值受到追捧。抽象价值、绝对价值和普遍的价值、价值一般,是社会生活秩序的要求。全球秩序的建立,需要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也需要有价值一般和明确规定性。价值的普遍性,需要确切的规定性和明晰性。价值论的相对主义、模糊哲学,是模棱两可、缺乏明晰定义的。要走出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误区,哲人们诉诸价值的本体论诠释,给出先验的、绝对的规定性。
人类交流,必须有共同的认知。定义(definition),就是一种获得共同认知的重要方法,它是对事物的本质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做出说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探寻普遍定义,是苏格拉底的功劳,也是柏拉图“相”论的理论来源。苏格拉底的哲学主要是为道德的相关概念正名,探求合乎逻辑的定义。他的对话往往是为各种美德概念正名,是直接针对智者学派相对主义发声的。智者学派认为,概念是约定俗成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确切的意义。苏格拉底则力图揭示同类事物共同的本质属性,要求概念的确切内涵。苏格拉底反对把特殊事例作为定义,正如不能列举“圆形”“三角形”“梯形”例子来定义“形状”,列举不能代替定义。他主张从特殊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共同本质,达到“辞事相称”。作为同类事物的本质和共相的“善”“美”理念贯穿于人类思想史,超越各民族特殊利益,乃“天下之至理”“古今之通义”,它们都需要定义,而不是相对主义式的游移不定。苏格拉底打破砂锅问到底,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其主要方法就是所谓的“苏格拉底问答法” (Socratic elenchus),亦称苏格拉底反诘法,是通过一系列问答、相互质疑来重建信念。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的问题” (Socratic question),指的是如何过值得过的生活。一个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在苏格拉底那里就是要追问“什么是虔诚(正义、勇敢、节制,等等)”,要在“殊相”中找到“一般”,找到定义。他认为,提供定义是获得知识的途径,而美德是知识,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善,就会做正确的选择。苏格拉底寻找普遍价值,寻找普遍正义和正义本身,寻找正义的定义。具有明确定义的“正义”表明,存在着高于族类的共同价 值。
古希腊人注重研究事物的本性,也探讨美德涉及的基本原理,如智慧、正义、节制、勇敢、友爱、虔诚等道德问题。前苏格拉底希腊哲学主要是研究宇宙本原的“自然哲学”,苏格拉底开始研究人本身,研究伦理,如正义、勇敢、诚实、智慧、知识、国家,等等。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家是热爱智慧的人,而不是有智慧的人。他研究伦理问题,寻求普遍的“善”,因为善是最高、最普遍的本质。普遍的本质即共同性,是永恒不变的。善,就是一切普遍本质应该具有的,是最高的本质,具有本体论性质。阿尔弗雷德·韦伯认为,在伦理学上,苏格拉底的功绩就是从特殊找出一般,从个别找到普遍,从个别过渡到共同体,从个别物上升到共名。他引导思想去推论,去下定义。他给每个词一个清晰的定义,澄清思想上的混乱。重要的是给名词下定义。①阿尔弗雷德·韦伯:《西洋哲学史》,詹文浒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51页。例如,《美诺篇》讨论德性的定义、德性是否可以传授。美诺提出德性的许多“定义”,却被苏格拉底一一否定。苏格拉底要寻求的是关于德性的一般性定义,美诺没有满足这一要求,他是以具体的、特殊的例证来回答德性问题。这里讨论的对象不是个别行为,不是具体事例,不是个别感性事物,而是指向本质和定义,即一般理性。②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页。
在此先从苏格拉底讨论的“虔诚”的概念切入,来谈论普遍价值与正义、规则、定义。苏格拉底在定义中探求普遍性,寻求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特征,而不是表面相似(《美诺篇》,72B①本文所引柏拉图著作皆于文中标注篇名和标准编码。中译文参见:柏拉图:《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2007年版;《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他说:“我们要阐明的名词是指事物的本性” (《克拉底鲁篇》,422D)。共同的本质使一事物成其为该事物,它对事物的存在而言具有因果必然性。苏格拉底要驳斥的是智者学派,智者们强调个人感受,主张相对主义。苏格拉底提倡理性,认为通过理性获得的真理具有绝对性,而智慧或者专业知识(expertise),是有明确定义的(definitional)知识。
普遍定义,就是“相”的雏形。探讨普遍定义,是苏格拉底的功劳,也是柏拉图“相”论的来源。“相” (eidos,idea),指谓普遍本质,最早见于《游叙弗伦篇》。《游叙弗伦篇》是苏格拉底对多神教的批判,反映了他对普遍和一般的追求。通过对虔诚的探讨,他使得宗教转向理性。苏格拉底请教游叙弗伦虔诚是什么,以便作为范式,因为关于虔诚的智慧和定义,将保证获得关于虔诚的正确判断。一个知道虔诚定义的人,不会在“何为虔诚,何为渎神”的问题上犯错误。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游叙弗伦篇》没有教条,只有探究,不是尽善尽美的成果,而是探究过程,虽然这个过程并没有以完满的结论告终。
在该篇中,游叙弗伦认为父亲杀了人,如果不揭发,就是不虔诚——苏格拉底后来也被控告不虔诚。苏格拉底要求游叙弗伦说明什么是虔诚(《游叙弗伦篇》,4A-5C)。游叙弗伦给虔诚下定义说:“让神喜悦的就是虔诚”,“让神憎恶的就是不虔诚” (《游叙弗伦篇》,7A)。苏格拉底对此反驳说:不同的神,见解各不相同,同一种行为可能既虔诚又不虔诚,同一个神也可能喜怒无常、朝令夕改,所以这个定义不能成立(《游叙弗伦篇》,7B-8B)。于是,游叙弗伦再次修改定义说:所有的神(all gods)一致赞同的行为,就是虔诚。所有的神一致反对的行为,就是不虔诚。苏格拉底认为,这是倒因为果——人因为虔诚才被神喜爱,被神喜爱是虔诚的结果,而不能用来定义虔诚。如果把被神喜爱当作虔诚的定义,当作虔诚的本质,那就是本末倒置。苏格拉底认为,被神喜爱,只是虔诚的一种属性(《游叙弗伦篇》,9C-11B)。“原因”是使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本质规定性,这就是绝对的“相”,其“结果”仅是偶然的属性。苏格拉底认为虔诚的定义高过虔诚的行为,他也反对以举例说明的方式来获得虔诚的定义,反对以特殊代替一般。应该说明的是使一切虔诚的行为之为虔诚的那个本质的“相”,它可以作为标准或模型——与之相似的,就是虔诚,相反的,就是不虔诚(《游叙弗伦篇》,6D-E)。
苏格拉底坚信游叙弗伦对于虔诚必定了然于胸,否则不至于起诉其父,故希望他不吝赐教:“你说的虔诚和不虔诚是什么?难道任何行为中的虔诚不都是同一的,而不虔诚总是相反,而和自身相同吗?因此在每个不虔诚的行为中,都可以找到一个不虔诚的‘相’(idea)。”“我并不是要你告诉我虔诚的一两个例证,而是告诉我使一切虔诚的行为成为虔诚的那个‘型’(eidos)。我相信你会承认有一个‘相’(idea),由于它,一切不虔诚的事物成为不虔诚,一切虔诚的事物成为虔诚。请您告诉我这个‘相’(idea)是什么。我就可以把它当作标准(paradeigma),其他行为,与之相似的,就是虔诚,与之相反的,就是不虔诚。” (《游叙弗伦篇》,6D-E)
“型” (eidos)和“相” (idea),就是同类事物普遍的共同的本质。每个“型”和“相”自身同一,是同类事物存在的原因,是判断事物的标准。虔诚的“相”,既是判断虔诚的标准,也是判断不虔诚的标准,因而无需不虔诚的“相” (标准)。不虔诚是虔诚的阙如,犹如“非存在” (non-being)是“存在” (being)的阙如。“存在”是判定“存在者”存在的标准,也是判定“不存在者”不存在的标准。正如“非存在”不存在,恶(evil)不存在,存在的是善(good)。恶是善的匮乏。善是判断善之为善的标准,也是判断恶之为恶的标准。由是观之,否定依附于肯定,消极依赖于积极,被动依附于主动,否定性不独立存在。前者是后者的欠然、阙如。这就是所谓的“存在是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尺度”。“型”或“相”,就是普遍原则、原理、一般,而非个别、特殊、偶然。这是科学、哲学和宗教所寻求的。
三、正义与形式问题
凡正义者,皆可定义。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这里的道,可以理解为正义,只不过孔子没有给出定义。在古代中国,“正义”的意思是义理考据章句注疏之学。例如《五经正义》,乃鉴于儒家典籍散佚、文理乖错、师出多门、章句杂乱,为适应科举之需应时而出。概念、界定、定义则始于近代西学输入。正如梁启超所说:“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之。”
普遍的价值有明确的概念定义,才有正当的正义。当今的全球文明以正义为基础。没有正义,就不会有社群。推进全球文明应该在国际社会伸张正义,而不是混淆视听、抹杀是非、袒护邪恶。寻找正义和定义,就不是搞相对主义诡辩论(sophistry),也不应抱持怀疑论和悲观主义的态度。关于正义的问题,仍以苏格拉底为例——他为什么拒绝越狱?因为既然生活在这个城邦,就不可以不服从城邦法律,即使判决有失公允,他也要服从法律。法律具有普遍性,他敬重法律、正义和法庭,至死不渝。早期希腊城邦制度,是根据神的法则建立的。人们纷纷立法,树立法律权威,以确立正义。
《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在雅典大街上和路人玻勒马霍斯讨论正义。苏格拉底批评了若干流行的关于正义的定义。有人说,正义就是言行诚实,偿还宿债。苏格拉底说,对于疯子,你能偿还兵器吗?又有人说,正义就是损敌利友——这当然也不对。关于“正义”的讨论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苏格拉底和攸昔德谟斯(Euthydemus)讨论“正义”和“非正义”。苏格拉底依次问:说谎、欺诈、偷盗、贩卖人口,应该归入哪一类?攸昔德谟斯答:非正义。苏格拉底说:将军带领部队去奴役一个敌对城市,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他作战时欺骗敌人,是正义的。他盗取敌人财物,是正义的。原先归入非正义的,也可以算作正义。欺骗敌人是正义的,失利时谎称援军就要到,这种欺骗可归入正义。孩子生病,父亲骗他吃药,这种欺骗可归入正义。某人绝望自杀,朋友偷走剑,这种偷盗行为也归入正义。攸昔德谟斯不得不说:“我错了。我把原先说的话收回”。①张树栋:《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在这两个对话场景中,苏格拉底询问“正义”究竟是什么,引导对话者给所讨论的对象下定义,但并没有指出下定义的形式规则。可以明确的是,他不赞成枚举正义行为的例证来以代替定义。他认为,正义行为既然被称为“正义的”,就必然有其共同特点。共同特点才是定义的要件。
在《理想国》中,有一种说法是,正义就是秩序与和谐,“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每一个人严于律己,这才有秩序与和谐。苏格拉底的理想国需要通过智慧(wisdom)、勇敢(courage)、节制(temperance)带来正义(justice)。他按照正义的原理设想理想国,正义就是和谐万邦。
苏格拉底说:“正义是最大的美德。”思考正义,使我们看到人类的一些原则具有非正义性。“我确信,凡合乎法律的就是正义的。”他还为抽象的正义找到相对抽象的标本——法律。正义是立法的标准,是立法的共同本质,法律是正义的体现。
在《游叙弗伦篇》中,苏格拉底还谈到虔诚(piety)和正义的关系。一切虔诚的事,都是正义的。但不能说一切正义的事,都是虔诚的。虔诚只是正义的一部分,正义还有别的部分(《游叙弗伦篇》,11E-12A)。所有的美德都是正义的、正当的,虔诚只是其一。节制、勇敢也是正义。正义概念的外延,比虔诚宽泛。关键是探讨:虔诚是正义的哪一部分?(《游叙弗伦篇》,12A-E)苏格拉底主张把握真理,而不是轻易相信头脑中偶然的意见。我们必须澄清自己的观念。
实际上,苏格拉底也没有提供关于正义的准确定义,尽管如此,他通过论辩、举例、反诘来不断地探寻,正义的实质就逐渐在对话者的意识中浮现出来。人生的目标就是追求正义,舍生取“义”。如果正义就是凭借人们固有的良心、良知办事,或者“善恶之心人皆有之”就可以不去寻求善恶的知识,那就不对了。如果仅仅认为良知未泯就有正义,那法律、社会管理、教育、慈善机构、舆论媒体就都是多余的了。这不是哲学的思考结果,因为那样就会有无数个正义,多元论、无政府主义、相对主义、诡辩论、怀疑论就会满天飞。对于正义,人不能单凭良知良能,也不能凭“源洁则流清,形端则影直” (王勃《上刘右相书》)的期许,还要有关于正义的哲理、法理,或者说,具备关于正义的知识,才能行正义之事。
苏格拉底追寻一般规律,追寻道德的一般原理和基础,寻找普遍定义,追寻绝对和超验。苏格拉底的理想国是正义的城邦,追求正义是个过程,“追求”自身就有意义。正义比勇敢、自制、虔诚更为抽象,属于较高层面,也许做到了诸般道德,就是正义了。定义或概念是舶来品,向为中国哲学所阙如。在西方哲学中,定义或概念之明确始自苏格拉底。哲学寻找定义,而不是正义,它寻找正义本身、寻找正义的定义或正义一般,而不仅仅是寻找正义的例证和具体行为。正义就是符合正义的定义。正义定义,就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规则可能是单纯形式,但不可或缺。借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苏格拉底追求绝对知识,寻找形式正义(formal justice)。形式正义有别于实质正义。在希腊神话里,正义女神被蒙上眼睛以求不偏不倚,这不是说她能做出实事求是的判定。培根《新工具论》指出,形式与性质不可分割:“形式,不是别的,正是支配和构造简单性质的那些绝对现实的规律和规定性。”形式是性质的内在基础和根据,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本质力量。认识和掌握了形式,就可以抓住自然的统一性,认识真理,得到自 由。
这和寻常徒具形式、走过场的形式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古希腊哲学重视形式,形式正当、形式合理,就是正当和合理。对于形式的重要性,贝克曼(James Beckman)指出,苏格拉底否定形式下潜藏的动机,在于超验的和终极的形式。由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形式取代诸神而成为最高价值标准。①James Beckman,The Religious Dimension of Socrates Thought,Waterloo: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1979.
让我们再次回到前述《游叙弗伦篇》。对话指出,存在着完全同一的“形式”,即虔诚。一切虔诚的行为由于这种形式而成为虔诚。这里被称为“形式”的,还只是概念或词的意义,而不是客观实体。《游叙弗伦篇》的确包含着“形式”的思想,但尚未达到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相分离。现实世界是“原型”的摹本,是可感知的对象;理念世界是不可感知的无形体的世界,是理性可以把握的形式世界。《游叙弗伦篇》的目的是为神圣下定义。在寻求定义的过程中,苏格拉底提出了神圣的形式:(1)作为客观真实的实体而存在;(2)普遍,在所有神圣事物中都是相同的:(3)是一切神圣事物的本体或原因:(4)是判断一事物是否神圣的标准。关于神圣的这些观念对于其他形式而言,是客观实体、一般概念、本质和标准。
在柏拉图看来,形式是客观实体和定义的对象,因而也就是事物的本质。形式具有普遍性,不能用具体事例下定义。既然形式是判断的标准,那么,正确的道德评价以及幸福本身,最终就取决于关于形式的知识。
古希腊人把形式视为本体,形式是内在的本质,是事物的原因和根据,即形式因。古希腊语“形式” (eidos)一词源自动词“见”或“看” (idein),柏拉图用eidos表示事物的内在结构或可理解的形式(人所认识的是万物的形式)。对定义和形式的关注表明,希腊哲学自始就重视清理言路和思路,关注本质和普遍性。这对我们思考价值问题来说仍具有参考意 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