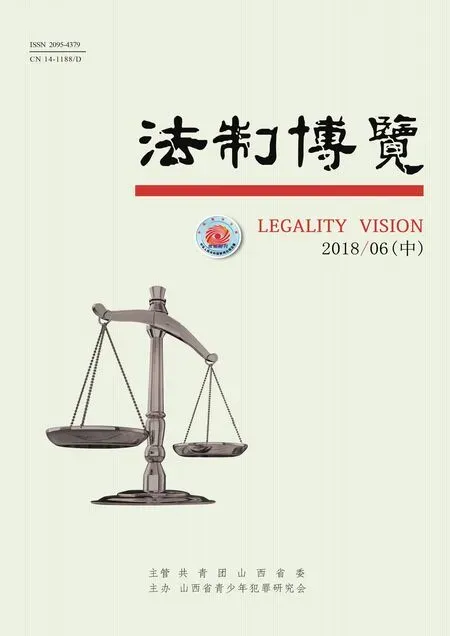试论我国就业歧视的立法规制
佘宇晗
四川农业大学法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
近年来,我国的就业歧视案件时常见诸报端,从身高到基因的各种就业歧视原因层出不穷,就业歧视问题日渐严峻,逐渐演变成了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但现有的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在规制这类行为时也存在着许多先天性不足,制定一部完善的反就业歧视法仍然任重道远,如何有效地消除就业歧视现象成为我国亟待研究的课题之一。
一、就业歧视概述
(一)就业歧视的界定及例外
就业歧视的内涵是指,在求职阶段和就职阶段非基于人的能力和贡献而采取有损公民平等就业权利的任何差别对待。通常来看,差别对待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总是不正当的,在判断何种差别对待是正当或者合理的这个问题上需要法律确定一个标准,这种标准体现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进行差别对待的合理性范畴。[1]一方面,就业歧视侵犯的是劳动者个人的平等就业权,劳动者因此而丧失就业机会和职业待遇;但另一方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系通过契约自治达成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用人单位也具有用工自主权。长期以来,法律难以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以致无法有效地规制用人单位的雇佣歧视行为。当这种合理性范畴被怀疑是对就业者的一种歧视性行为时可以以此为抗辩事由进行正当性证明。抗辩事由具体来看有以下几种:(1)基于职业或业务本身的客观、必要的要求,如果不遵守这样的职业要求,将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正常完成这项工作;(2)基于保护公共利益或实施某种社会政策的需要对劳动者个人权利的限制,比如监狱不招女狱警虽然涉嫌性别歧视,但是相比于个人权利的保障,公共利益无疑具有优先、排他的地位;(3)为了满足促进弱势群体融入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的优先性照顾,例如企业将一定比例的岗位提供给残疾人;(4)因介入了某些临时因素而采取的特别的、暂时的优待措施,例如女性因产期无法工作,只能带薪休假。
(二)我国就业歧视的主要原因
产生就业歧视的原因当然包括了当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产业结构调整、人们的偏见这些因素,除这些因素外,美国法学家波斯纳还曾以“性别歧视”为例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就业歧视的起因,“雇主性别歧视的存在是法律禁止此歧视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首先,不是所有基于性别的就业歧视都是无效率的;所以,防止性别歧视的努力会产生高于这种努力的成本本身的社会成本。”[2]雇主作为一名商业理性人,出于对商业成本收益的精确算度,而可能不会录用那些受法律特别保护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雇主对一些法律的主动规避反而会使劳动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例如用人单位为了规避《劳动法》中关于禁止在女职工的孕期、产期、哺乳期内解除劳动合同的规定而选择不雇佣女性,可以说,现有法律的不完善间接导致了无法有效制约这种歧视性行为。
(三)就业歧视的表现
就业歧视分为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直接歧视以形式平等为理论基础,即相同条件下应当同等对待,直接歧视是指用人单位以带有明显的有违形式平等原则的色彩的行为进行区别、排斥或优惠,比如在招聘环节公然要求只招录男性,这就是直接的性别歧视;而间接歧视指的是在表面上看似中立的入职标准或条件实际上使劳动者获得不利的条件或地位,往往间接歧视手段更加隐秘、无法察觉,但这种变相的歧视行为同样侵犯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
二、我国反就业歧视立法的不足
(一)我国缺少反就业歧视的专门法律
我国目前有关反就业歧视的规定,主要散见于《宪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法规中。这些禁止就业歧视的规定太过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往往停留在权利性的宣告层面,对以下问题的解决在反就业歧视立法上尚付阙如:(1)虽然法律规定了禁止就业歧视,但是对于哪些行为属于就业歧视的界定还十分模糊,导致司法实践部门也难以确定一个具体的标准或原则去判断用人单位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劳动者的就业歧视;(2)“有原则就有例外”,就业歧视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差别对待,但是对于哪些差别对待是具有合理性或正当性在立法中仍然是空白,因此,不仅要规定就业歧视的法定情形,也要规定抗辩事由[3];(3)现行法律也未能准确划定平等就业权和用工自主权之间的界限,并因此兼顾双方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如果根据业务本身的需要而对劳动者进行资格的限定便是在合理的必要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便不应受到苛责;(4)在劳动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法律并没有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这样无疑助长了用人单位无所顾忌的心态;(5)程序上的保障和救济机制的严重缺位造成实务中就业歧视案件“立案难、举证难、胜诉难、赔偿低”。
(二)我国目前确立的就业歧视事由和立法适用范围过窄
我国《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规定了禁止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歧视,以及对残疾人、传染病病原携带者、农村劳动者的歧视,大致做出了对时代发展产生的各种就业歧视现象的回应,但在现实生活中还大量存在着身体歧视、健康歧视、户籍歧视、地域歧视、体貌特征歧视、学历歧视、前科歧视等歧视现象都没有被认定为就业歧视。
另外,反就业歧视在劳动立法上的适用范围同样过于狭窄,《劳动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这个范围内的“劳动者”远小于《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的范围,以至于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等受到就业歧视时无法得到救济。
三、我国反就业歧视制度的完善
(一)明确就业歧视的概念和认定标准
在立法上已经创设了平等就业权,但是还未对就业歧视行为的概念予以明确界定。笔者认为,就业歧视,在求职阶段和就职阶段非基于劳动者本身的能力和贡献而采取有损公民平等就业权利的任何差别对待,这里的劳动者应作广义理解,即具有与其将要或正在从事的职业相符的劳动就业能力的劳动者。因此,当用人单位根据业务本身的客观、必要的要求对劳动者进行区别、判断,基于正当的抗辩事由便构成例外。
(二)合理分配就业歧视中的举证责任
通常实务中就业歧视争议案件遵循的是《民事诉讼法》中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由于劳资双方的地位不同,导致天生具有隶属性且经济实力偏弱的劳动者往往无法获取到能够有效证明用人单位进行就业歧视行为的证据,许多就业歧视争议案件的受害人要么长期忍气吞声,要么由于漫长的等待和高昂的诉讼费用而中止。为了有效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可以适当减轻劳动者的举证责任,从而使双方的举证责任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4],但又不得过于减轻劳动者的义务而增加用人单位的义务,以防止无端滥讼现象的出现。因此我国未来的反歧视立法应当在分配举证责任的规则设计上适度偏向于劳动者,建立特殊的举证责任规则,即劳动者只需证明用人单位存在差别对待的事实,便可推定该用人单位实施了就业歧视行为,用人单位需要提供证据该差别对待的行为是合理且正当的,否则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即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义务和法律责任
明确规定用人单位负有积极的预防不平等待遇的义务,并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劳动者受到歧视行为,例如通过反就业歧视培训、建立内部申诉机制等,在对劳动者的救济上应让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经济和精神赔偿、赔礼道歉,未来还可以对违反禁止就业歧视规定的用人单位施以惩罚性赔偿责任,以提高其实施违法行为的成本,达到对用人单位的不当歧视行为的震慑和遏制作用。
(四)执法层面
“徒法不足以自行”,在规制就业歧视立法上做好了顶层设计,在执法方面更需要得到良好的贯彻和执行。也可以在中央和地方层面的行政体制内设置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机构,该机构主要承担以下职责:第一,加强对公众反就业歧视法律宣传,提高劳动者的反就业歧视意识,并让用人单位也能意识到就业歧视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向社会广泛宣传就业歧视的危害;第二,为那些遭受就业歧视的劳动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服务;第三,受理劳动者对遭受就业歧视的申诉,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服务和调解服务。
(五)司法层面
司法部门需要严格依照法定的原则和程序发挥好反就业歧视的作用,捍卫法律的尊严。劳动法调整的对象是“与劳动关系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因此将求职招聘、职业介绍、工资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劳务派遣、职业培训以及社保福利等劳动者就业的每个环节都纳入到反就业歧视范畴,有利于更好地处理就业歧视案件;并逐步引入就业歧视公益诉讼制度,减少劳动者在诉讼上的费用。
四、结语
我国现行的反就业歧视法律由于缺乏配套的实施和救济机制,往往造成实务中法律被虚置的尴尬状态,在这样的情形下,立足我国的具体国情,借鉴域外反就业歧视实践中的先进经验对于完善我国反就业歧视立法具有重大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李志.反就业歧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视角[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6,18(05):79-86.
[2]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蒋兆康译.法律出版社,2012:497.
[3]娄宇.德国反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制研究[J].德国研究,2014,29(04):36-48+126.
[4]王哲,朱京安.困局与因应:就业歧视立法规制的优化[J].广西社会科学,2017(04):9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