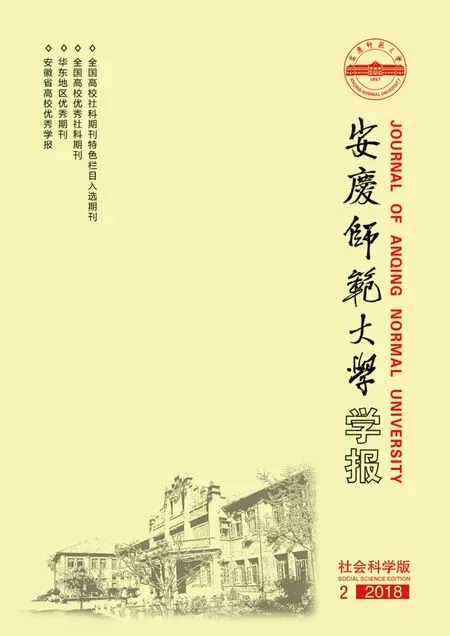士人交结与文本书写:东汉游学士人文化活动考察
杨霞霞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游学是东汉士人重要的文化活动。史书记载其时“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1]2588,顺帝时更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1]2547。近年来学界对这一史实的研究多集中于这三个领域:此期游学的发生、特点与社会影响,某一区域士人的游学活动带来的学术繁荣,游学与文学的关联特别是游学背景下五言诗的兴盛。对东汉士人游学中具体的文化活动则少有提及,对这一时期游学士人文化活动类型也鲜有总结。当是时,游学者日众,京城太学士子们秉持着“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1]2481的新游学理念,彼此交结、互相题拂,逐渐呈现出大规模交结、进而形成群落的态势。士人下行民间、游学成风,又引发了士人间政治、学术、思想层面的多重交流,并进一步促成了文章书写的繁兴,遂有“自东京以降,迄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2]的新局面之形成。士人交结、文本书写正是东汉游学士人的两大文化活动类型,本文拟对这两种文化现象进行具体分析,尝试勾勒出东汉一代士人的活动影像。
一、游学士人的交结
“学宦一体”是东汉的学术政治生态。从小处看,是业师、弟子,同时又是举主、故吏的关系;从大处看,则是学术与政治的彼此渗透。东汉游学者日众,并逐渐呈现出大规模交结、进而形成群落的态势。这与其时“学宦一体”的政治、学术形态密切相关。正是士人学宦一体的天然联系和志士交结的有意为之加速士人的聚合,促进了士人群落的生成。
(一)学宦一体
“汉世,业师门生,恩同君父,关系至重。”[3]无论官学、私学都强调师长的权威和学生的服从。在学术上,学生恪守师法家法。在日常生活中,学生对师长负有各种义务。师长去世,弟子门生无论身处何方、居何职,均有奔丧服丧的义务。乐恢、楼望、郑玄等去世,弟子门生会葬达数百人至数千人。戴封,年十五,诣太学,师东海申君卒,辄送丧至东海。
同时,弟子与业师、故吏与举主,这两组关系又纠缠一起,形成业师亦为举主、门生成为故吏的局面,即“学宦一体”的政治学术生态。
东汉经学大儒往往被朝廷所用,出任职官,如陈留刘昆通晓《施氏易》,“征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1]2550;南阳洼丹,“《易》家宗之,称为大儒”[1]2551,先后为博士、大鸿胪;京兆杨政“善说经书”,“官至左中郎将”[1]2551;颍川张兴,为梁丘家宗,先后为博士、“迁侍中祭酒”、“拜太子少傅”[1]2552;扶风平陵鲁恭、鲁丕兄弟二人“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1]873,后,鲁恭拜博士,迁侍中、拜议郎、官至司徒,鲁丕以明经笃学而屡次被举。此外,东汉帝王为太子时亦需受业于师(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当太子登基,其师多以太傅身份录尚书事,完成由学术名师向朝中重臣的身份转变。
这些以儒学入仕者又大多为学术名师,或在入仕之前就已开馆授徒,如刘昆曾教授于江陵,洼丹有弟子数百人,张兴著录弟子达万人;或居官期间兼以教授,如崔瑗、周防、符融、蔡邕、刘表分别师从时为侍中的贾逵、徐州刺史盖豫、少府李膺、太傅胡广、南阳太守王畅。更有太子少傅张兴、赵相鲁丕、河内太守牟长在任期间,授徒数百至万人者。
既为朝中大员,则拥有举足轻重的荐举权。如鲁恭在公位,“选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数十人。”[1]882鲁丕任东郡太守则“数荐达幽隐名士”[1]884。那么,兼为经师,其弟子无疑有更多机会受到推荐。例如:汝南钟兴少师从少府丁恭,受《严氏春秋》。“恭荐兴学行高明,光武召见,问以经义,应对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迁左中郎将。”[1]2579除钟兴凭借业师入仕之外,太常楼望、侍中承宫、长水校尉樊儵等亦受业于丁恭。桓荣为明帝师,其“都讲生八人补二百石,其余门徒多至公卿”[1]1253。
又有章帝建初八年(83年),“诏诸儒各选高才生……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1]1239至于位高权重者,其门生、故吏不计其数。最典型事例莫过于汝南袁氏,其家族五公三卿,“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1]2375当然,当举主获罪,其门生故吏亦罹其祸。东汉初期,楚王刘英谋反,事泄,朝廷诏捕同党,会稽太守尹兴获罪,其“主簿梁宏、功曹史驷勋及掾史五百余人诣洛阳诏狱就考,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1]2682汉末党锢祸起,朝廷几次下诏“诸附从者锢及五属”,“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1]2189游学者因此牵连甚广。例如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党锢复起,大学者郑玄“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锢”[1]1207。郑玄一生向学,无意仕途,其遭党禁,最有可能是因为与杜密的关联。郑玄曾为乡佐,时为太山太守、北海相的杜密“行春到高密县,见郑玄为乡佐,知其异器,即召署郡职,遂遣就学。”[1]2198杜密于郑玄有赏识、提携之恩,两者即成举主、故吏关系。党锢祸起,杜密下狱死,郑玄作为故吏也遭禁锢。
这种学宦一体现象的形成与东汉社会的学术背景和政治现实有关,究其根源,正是东汉政府大力推行的明经入仕的人才录用机制促成了学术、政治密不可分的结果,即学术政治化的必然产物。
(二)志士结交
在政府诱之以利禄、太学兴盛的背景下,大量士人涌入洛阳。学子们自四海而来,共聚一地,在学业上共同进步,在生活中彼此照顾,渐渐形成深厚的同学情谊。
如东汉初期朱晖与张堪旧事:起初张堪有名于太学,以朱晖为友,并“欲以妻子托朱生”。后张堪去世,朱晖听闻其家人贫困,则前往救济。朱晖少子颉怪而问曰:“大人不与堪为友,平生未曾相闻。”子孙窃怪之。晖曰:“堪尝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1]1453此外又有和帝时期济北戴封为同学石敬平送丧归故里、山阳范式与汝南张劭的“鸡黍之交”的故事,皆显示出学子们重友情、讲信义的道德品质。
中后期的东汉太学,随着游学群体扩张、经书繁杂、仕进艰难,士子之间弥漫着轻学问、重结交的风气。这种结交染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符融与仇览的对话可为一例。“(仇)览入太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1]2481有名望的太学领袖也注重奖掖士人。如,太原郭泰出身微寒,不欲为吏而辞家游学,“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1]2225在洛阳经符融引荐,与其时被奉为“天下楷模”的名士、时为河南尹的李膺友善,于是名震京师,为太学三万诸生之领袖。郭泰“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1]2225。史书记载,乡人贾淑、陈留江原、扶风宋果受其感召而改过自厉;陈留茅容、巨鹿孟敏、颍川庾乘因劝令学,终有所成。
灵帝熹平四年(175年),朝廷“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1]336“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1]1345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官藏图籍的公布活动,促进了士人的流动。士人的这一观视、摹写行为,并不仅是简单的抄录文献,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在交通设施落后、信息传播不发达的东汉社会,士人大量涌入洛阳,又恰逢清议之风的兴起,其背后必然是士人之间的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
(三)士人群落生成
学宦一体的天然联系与志士交结的有意为之最终都促成了士人群落的生成。所谓士人群落,是指聚集一地的士人因共同的生存环境、学术背景和政治理想而自发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形式。这一群体平时联系并不紧密,多是政府监督、指导下的共同体。当然,也包括具有学术传承关系,由经师、弟子组成的师生群体。
1.东汉中央机构士人群落
历史上的洛阳自秦至隋唐,一直都是民众道路可达的核心区域。早在周代,“成王即位,周公之属传相焉,乃营成周都洛,以此为天下中,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钧矣。”[4]而在东汉,洛阳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成为士人们向往的圣地。“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洛阳成为中心点,具有最优的通达性,洛阳成为历史上中心性最稳定的城市,持续了1100多年。”[5]
清代学者赵翼以“两汉时受业者皆赴京师”[6]一语概括汉代游学者的地域流向。的确,作为学术中心和政治中心,此时的都城洛阳具有多重优势,吸引了大批士人朝此间流动。而大批游学者因洛阳的学术向心力而辐辏至此,又加速了洛阳取代长安旧都成为各类学术思想交流新中心的进程。这一时期东汉中央机构主要士人群落依次有:
仁寿闼士人群落。有马严、班固、杜抚。“永平十五年……显宗召见,(马)严进对闲雅,意甚异之,有诏留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1]859
兰台士人群落。光武、明、章时期,聚集洛阳的士人大多集中在兰台,如班固曾与陈宗、尹敏、孟异共成《世祖本纪》,后又撰成“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1]1334。除修史之外,兰台士人还以校书为职。如傅毅、班固、贾逵曾共同校书。其他兰台士人又有班超、孔僖、杨终、李尤等。
东观士人群落。东观是东汉最重要的文化机构,也是洛阳士人荟萃之所。和帝时期东观士人群体,以班昭、马续、马融等十余高才郎为主;安帝时期先后有刘珍、窦章、刘毅、刘騊駼、马融、许慎、蔡伦、李尤、王逸以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等五十余人进入东观;顺帝时期,张衡、伏无忌、黄景、崔寔进入东观;桓帝时期,延笃、朱穆、边韶、伏无忌、黄景、崔寔、马融、延笃、张奂;灵帝时期,蔡邕、卢植、马日磾、杨彪、韩说、单飏。
鸿都士人群落。鸿都门集中了大量“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1]1991-1992,其中可考者有乐松、任芝、贾护、江览、郄俭、梁鹄、师宜官。
2.东汉地方主要士人群落
东汉地方士人群落集中表现在汉末荆州襄阳士人群落与冀州邺城士人群落。这与汉末中央权力式微、地方势力兴起有关。
汉末的荆州“境广地胜,西通巴蜀,南当交趾,年谷独登”[1]2124,同时在荆州牧刘表治理下,“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1]2421大量士民流入荆州,仅关中一地,“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7]610来此避乱的名士有王粲、宋忠、隗禧、祢衡、繁钦、邯郸淳、诸葛亮、傅巽、颍容、赵岐、裴潜、司马芝、孙嵩、和洽、刘廙、杜夔、刘巴等,“皆海内之俊杰也”[7]598。其中,既有依附刘表为其幕僚者,也有仅以荆州为避难之所而不问政治者。
邺城士人群落在喜好诗文的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的倡导下逐渐兴起,并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文人集团。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克邺城,此后直至曹丕定都洛阳,邺城一直是曹魏政权中心。大量士人汇聚于此,形成以三曹七子为主体的邺下士人集团。山阳王粲、北海徐干、广陵陈琳、陈留阮瑀、汝南应玚、东平刘桢、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修、河内荀纬、广平刘劭、陈留苏林、济阴吴质等都是这一群落的代表人物。
3.东汉重要幕府士人群落
大量士人供职于幕府是东汉重要的文化现象。这一时期幕府士人群落主要有:以傅毅、崔骃、班固为主体的窦宪幕府士人群体;以马融、杨震、朱宠、陈禅为主体的邓骘幕府士人群体;以巨览、陈龟、李固、周举、马融为主体的梁商幕府士人群体;以朱穆、周景、崔寔、赵岐、应奉、吴佑、杨赐、马融为主体的梁冀幕府士人群体。
4.东汉著名师生群落
“汉人无无师之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书皆竹简,得之甚难,若不从师,无从写录。”[8]因此,由经师、弟子组成的师生群体也是不可忽略的文化群落。此期著名的师生群落有杜子春与弟子郑众、郑兴、贾逵等;贾逵与弟子许慎、崔瑗、高才生二十余人;马融与弟子郑玄、卢植、延笃等;郑玄与弟子国渊、赵商、王基、郗虑、任嘏、孙炎等;胡广与弟子蔡邕等;蔡邕与弟子阮瑀、路粹、苏林等。在这些师生群落中,弟子从经师处听讲、抄录、答问,经师为弟子传道、授业、解惑,二者奇文共赏、疑义辨析、教学相长,共同推进了学术的薪火相传。
二、游学士人的书写
东汉各地域间大规模的士人流动促成了士人群落的出现,并进一步促成了文章写作群体的生成。这些写作群体的书写,既包括以修史、定经、献赋为主体的官方行为,也有私人性质的个体书写。在共同的书写中,东汉士人们相互启发、彼此竞争,共同促进了东汉文章的发展。
(一)《东观汉记》的踵续而成
“中兴之史,出自东观。”[9]196大批学者陆续进入东观,合作书写、踵续而成《东观汉记》。这一修史活动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明帝永平年间,明帝召见扶风马严,“严进对闲雅,意甚异之,有诏留仁寿闼,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1]859又据文献记载,班固又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后又撰成“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1]1334其他同时期身在兰台,极有可能参与这次著述的士人有:鲁国孔僖,“帝始亦无罪僖等意,及书奏,立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1]2560;蜀郡杨终,“显宗时,征诣兰台,拜校书郎”[1]1597;广汉李尤,“少以文章显……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李尤同郡李胜“亦有文才,为东观郎,著赋、诔、颂、论数十篇。”[1]2616
安帝永宁年间,“邓太后诏(刘)毅及刘騊駼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1]558。除刘毅、刘騊駼、刘珍三人外,此时活动在东观的文人另有马融、李尤、王逸、马融等。李尤,“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等俱撰《汉记》”[1]2616;南郡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拜为校书郎,很有可能参加这次修史活动。此次修史的成果是撰成《建武以来名臣传》,乃“《汉记》之初续也。”[10]
桓帝在位期间,延笃、朱穆、边韶、伏无忌、黄景、崔寔、马融等亦进入东观续修《汉纪》。南阳延笃,“桓帝以博士征,拜议郎,与朱穆、边韶共著作东观”[1]2103;伏无忌、黄景,“元嘉中,桓帝复诏无忌与黄景、崔寔等共撰《汉记》”[1]898;涿郡崔寔,“召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1]1726。此外,延熹二年(159年),马融“复拜议郎,重在东观著述”[1]1972;敦煌张奂因上书献《章句》被诏下东观,因此也有可能参加这次活动。
灵帝熹平年间,朝廷诏令增补《汉记》,“复征拜(卢植)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1]2113此次活动续写“帝纪”和“列传”,增设“志”的部分。至此,《东观汉记》基本成型。
严格意义上,这里所论述的写作群体已不属于前文考察的游学者之列。然而,以上身在兰台、东观修史的士人多有游学经历;并且,兰台、东观士人多为郎官,而“迄乎东汉……三署诸郎多郡吏与经生,贵族豪富之子弟较少”[11],郡吏、经生又是东汉游学主体。这些著作者受察举或辟除而集中于此,这也是广泛意义上的游学活动。因此,这里可视为对东汉游学群体的后续文化活动的研究。
(二)经学文献的师生撰述
东汉游风盛行,士人辗转各地求学问道,多以学习经传为主要目的。在不断的学习中,士人温故知新,常且述且作。翻检文献,可以发现,东汉时期具有学术传承关系的经师和儒生间的经学撰述较为常见。其中,著名的经学师生撰述有:
杜子春与郑众、贾逵师生的撰述。杜子春,曾受《周礼》于刘歆,并为《周礼》作注。史书记载:“《周礼》一书,当永平初年,唯有河南缑氏杜子春能通其句读,颇识其说”,大儒郑众、贾逵“往受业焉”[12]。承师所学,郑众著有《周礼郑司农解诂》,贾逵著有《周礼贾氏解诂》《周礼贾氏注》。
贾逵与许慎师生的撰述。贾逵除师从杜子春之外,还悉传父业(其父贾徽曾师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亦为当时大儒)。此外,贾逵自幼常在太学,见识广阔,兼通五经,世称通儒。除撰注《周礼》之外,贾逵对《易》、《书》《诗》《春秋》亦多有研究,“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1]1240。其弟子众多,而以许慎最为知名。许慎“本从(贾)逵受古学”[13]498,亦精通诸经,有“《五经》无双许叔重”[1]2588的盛誉。其著作有《春秋左传许氏注》《五经通义》《五经异义》。不仅如此,许慎经典之作《说文解字》在问世之前,还“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13]498,可见亦受益于其师贾逵,方成《说文解字》。
马融与郑玄、卢植、延笃师生的撰述。马融、郑玄是东汉经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对师生组合。二者皆博学多闻,兼通五经。卢植、延笃也是马融高足。这一师生群体著作颇丰,且大体相类。如:马融作《易传》,郑玄作《易注》;马融作《礼记马氏注》,郑玄作《周礼》《仪礼》《礼记》《三礼图》《三礼目录》,卢植作《礼记卢氏注》;马融作《春秋三传异同说》,郑玄作《春秋公羊传郑氏义》《春秋左传郑氏义》,延笃著有《春秋左氏传延氏注》;马融作《毛诗马氏传》,郑玄作《毛诗郑笺》《诗谱》;马融有《尚书马氏传》《尚书中候马注》,郑玄作《尚书注》《尚书五行传注》;马融作《周官传》,郑玄作《周官注》;马融作《孝经马氏注》,郑玄作《孝经注》。
上述师生群体是东汉时期最著名、最典型的学术群体。他们基本都有游学各地、转益多师的学习经历,在传道、受业之际,他们苦心著述,体现了士这一群体的传承、传播文化的最基本属性,也大大提升了游学这一文化活动的学术价值。
(三)诗文的文士并作
东汉中后期,随着游学者数量的增多,一些描写游子生活和情感的作品也不断涌现。
“居穷衣单薄,肠中常苦饥”[14]514“凉风率已厉,游子寒无衣”“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14]518“行行随道,经历山陂。马啖柏叶,人啖柏脂”[15]“行行重行行,白日薄西山”[14]442,这是游子的衣食住行;“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同心离居,绝我中肠”[16]180“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16]186“惊雄逝兮孤雌翔,临归风兮思故乡”[13]551“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17],这是思念亲人、思念故乡的游子;“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14]539“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14]540“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1]2631,这是游学中见弃于世人的精神苦痛;“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14]538“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14]541“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14]541,这是游子行走天地间发现的残酷真相。
与家人的书信往来是游学士人的心灵慰藉。在与家人的书信往来中,以夫妻书信往来居多。最为后人称道的东汉时期夫妻两地书是秦嘉与徐淑的往来书信。《两汉全书》记载了秦嘉与妻书有《与妻书》《重报妻书》《赠妇诗》《答妇诗》等;徐淑有《答夫秦嘉书》《又报嘉书》《答秦嘉诗》。秦嘉,陇西人。桓帝时期仕于州郡,举上计掾入洛,除黄门郎。其妻徐淑因病滞留故里。后秦嘉病逝,徐淑“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9]240。两人分在洛阳与陇西,书信往复,道尽思念之情。描写夫妻书信往来的诗句还有很多,例如“客从远方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16]330“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意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16]192这些都是描写妻子收到丈夫书信、礼物心情的诗句,由此也可见东汉游学风气对家书写作的影响。
此外,士子们自各地而来,辐辏一地,在共同的游学生涯中结下深厚友情。当他们分别后,书信便成为彼此交流的最好方式。《全后汉文》中记载了不少朋友间的往来书信。如张奂、延笃曾共同著作东观。张奂作书与延笃,言“唯别三年,无一日之忘”,又言“吾与叔坚剖心相知,岂以流言相猜耶。”[13]651延笃亦感念张奂,谓“离别三年,梦想言念,何日有违?”[13]629孔融交游甚广,朋友众多。他曾致信张纮:“前劳手笔,多篆书。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13]838;写信给韦端,临末不忘赞其二子元将、仲将:“前日元将来,渊才亮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仲将复来,懿性真实,文敏笃诚,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近由老蚌,甚珍贵之。遗书通心。”[13]838
三、结语
士人交结与文本书写是东汉游学士人最重要的文化活动,两者引发了不同领域的喧哗与骚动。士人交结激起了政治的动荡:士人聚集于一地、彼此交结,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促成了士人群落的生成。特别是积聚于洛阳这一各种政治势力纠缠、诸多敏感事件的高发地,士人群落更易转变为政治性(特别是不合作)的集团,并因其在士林、乡里乃至官场的影响力而使得这种政治倾向蔓延全国。东汉后期,“官非其人,政以贿成”[1]3297的政治现实促使太学诸生与朝中清流士大夫走到一起,他们还“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1]2187,彼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遂卷起汉末政坛风云。文本书写则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它是士人游学活动中较为温和、内敛的表达方式,在文章史上却具有重大意义:士人的游学逐渐打破地域之限,士人既可共同受诏作赋、奉命撰史、合作校经,又能私下诗文唱和、书信往来, 引发不同时空的文章书写,并促成个体书写的流行,遂“一世之士,各相慕习”[18],最终带来了东汉文学的繁兴局面。最后,士人交结与文本书写这两类文化活动又不是孤立并行的,士人交结中多有文本的交流,文本书写中又多有士人结交的影像。而关于此二者关系,待另文再论。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章学诚.文史通义[M].上海:上海书店,1988:85.
[3]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C]//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秦汉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1224.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2119.
[5]王成金、王伟、张梦天.中国道路网络的通达性评价与演化机理[J].地理学报,2014(10).
[6]赵翼.陔余丛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295.
[7]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8]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88.
[9]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0]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1361.
[11]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M]//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329.
[12]贾公彦.序周礼废兴[M].北京:中华书局,1980:635-636.
[13]严可均.全后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4]萧统.六臣注文选[M].李善,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
[15]欧阳询.艺文类聚[M].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515.
[16]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896.
[18]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