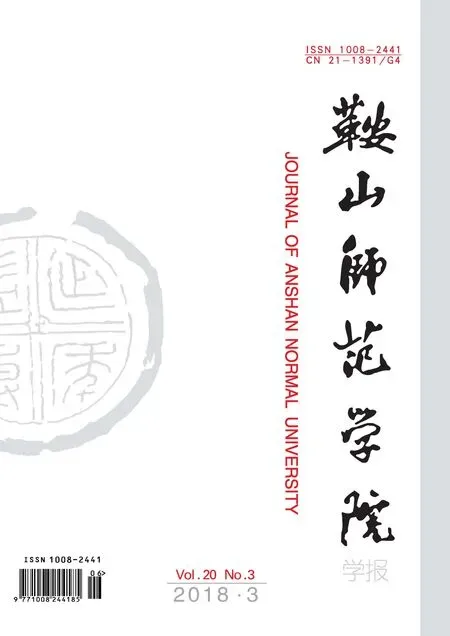废墟上的拼接与凝望
——评《黄雀记》的寓言式写作
张 超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2013年,苏童长篇小说《黄雀记》发表于《收获》第3期。同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黄雀记》单行本。2014年1月,《黄雀记》获选《亚洲周刊》2013年十大华语小说之一,2015年8月16日,苏童《黄雀记》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对于苏童来说,《黄雀记》是他谨慎撤离先锋阵营的标志,原因就在于《黄雀记》这部作品是对中国进入新时期以后、绝对价值崩塌、新的价值理念又尚未健全等问题的反思和揭露,小说以黄雀记的寓言方式叙述这段历史,形成以先锋的方式介入现实的写作特点,成为苏童文学创作转型的重要标志。
一、寓言式的言说
从题目来看,小说的立意取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寓言故事,一方面告诫人们在考虑问题、处理事情时要考虑后果,不可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后患;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一个人在行为的时候,很难预测有怎样的危机在背后潜伏,隐喻着当下现代性不确定性给人们带来的迷惘和困惑。小说中仙女、保润和柳生三主人公分别喻示着蝉、螳螂和黄雀三种角色。在小说开篇部分,三主人公均是青涩少年,保润暗恋着仙女,出于单纯地吸引仙女的目的,他以绳索束缚住仙女,怎料仙女却被作为媒人的柳生所侵犯,由此三人建立联系,青春期的力比多成为小说情节发展的第一道发条;而在小说结尾三主人公均已成年,携带着各自的生命经验,经由井亭病院重回老街,具有戏剧性意味的是,保润与柳生的角色对调,保润成为“黄雀”,误会仙女因柳生背叛自己而杀死柳生。从三人的关系结构来看,仙女依然是“蝉”,但是她已不再是被动受捕的“蝉”,虽然她渴望真挚的感情,但却以麻木放荡的方式在现代性社会中疯癫狂舞,告别了“仙女”时代的青涩懵懂,成为放逐自我的白小姐。三主人公的人生故事充满困境,源于时代的转型给他们的童年所留下缺憾:祖父的“失魂”使保润缺失老街上应有的温情;过早地接触商品市场使柳生缺失应有的道德约束;井亭医院的冷漠与疯癫使仙女缺失对他人和自己基本的信任,由始至终,三主人公被困于黄雀记的寓言当中,好似一道现代性的诅咒,隐喻着“永恒的人生困境”。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本雅明指出,艺术形式应随时代情境、历史要求的变化而变化,并由此提出艺术表现衰微、颓败、充满惶惑与痛苦的20世纪现代社会唯一可能的形式就是寓言。小说以昏黄的底色对保润、柳生和白小姐各自人生经历加以呈现,以衰微倾颓的老街为小说的起点,经过井亭精神病院中病人对生命的践踏,最终新生命“怒婴”接续到老爹手中,完成历史的又一次循环,传达着人们对“线性前行”的现代性社会的惶惑与质疑。这样的故事底色和叙事视角便是作者在这一历史天空下,以寓言的形式对人性应如何存在的思考。从形式上来说,小说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这三个部分分别以三个主人公为叙事核心,以碎片的形式各自独立,却又形成历时性的拼接,以蒙太奇的方式建立小说整体脉络,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苏童此前作品中片段式的先锋写作手法。
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认为波特莱尔以蒙太奇的方式拼接断裂与碎片式的情节,这不仅反映出作者内心的困惑,而且是欧洲衰败的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惊醒迷惘中的民众,在艺术中发现:在市场经济日渐繁荣的同时,资产阶级的丰碑在坍塌之前就已经是废墟一片了[1]。同样,在小说内容上,祖父作为历史的守望者,“魂”即传统的价值准则,已经丢了,祖屋作为空间概念不断被具有现代性意义符号的外贸服装店所征用,而屋子里的人也纷纷离去。祖辈的疯癫,父辈的死亡,母亲的逃离,老街再难担负精神原乡的情感作用。“祖国的面貌真是日新月异啊”,祖父的话便暗指着人与环境间保持整体性关系的生存空间已不复存在,废墟便在老街上升起,颓败便在上空中弥漫。而对井亭医院中病人疯癫的描述则暗含着现代人的虚无与狂欢,使人们趋之若鹜的寺庙则寄寓着狂欢之下价值观缺失给人带来的惶惑。这便是苏童以寓言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社会。
现代人生存在断裂式的空间当中与历史又难以实现对接。对于这种断裂式的书写特点,本雅明曾在《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中指出:为了一个被遗忘和误解的艺术形式的哲学内容而写的,这个艺术形式就是寓言[2]。不仅如此,《黄雀记》中保润家的祖屋,捆绑人的绳结,联系着三个年轻人的小拉,井亭病院里的水塔,这些意象并非是从自身特征出发并以先验的理念注输其中的象征之物,而是以言意分离的方法赋予小说中的物象以新的意义,所显示出的定性也只起一种外加属性的作用,而这正是本雅明相较于象征而对寓言提出的又一特征。可见,《黄雀记》中的诸多意象不仅形式和内容上存在着断裂,小说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也存在着分离。对于这一特征的意义詹姆逊曾指出:寓言精神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了分裂和异质,带有与梦幻一样的多种解释,而不是对符号的单一的表述……它的形式超越了老牌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甚至超过了现实主义本身[3]。断裂与外加,梦境与荒诞,这些特性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去意义。同样,《黄雀记》中以丢魂和找魂这一荒诞的情节联系全文,以各种突兀的意象散落其中,共同书写人物命运的不确定性,通过历史与现代两个向度的张力和冲突表达现代人的迷惘与困惑,以“无意义”方式实现历史叙事的意义,在文体和内容两个维度上使文本、作者和世界三者得到统一,这样的叙事方法正是寓言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可见,《黄雀记》的历史寓言便在香椿树街这片看似存在而实则坍塌的废墟之上被讲述出来。
二、废墟上的香椿树街
小说起初以香椿树街为背景,以保润祖父的失魂为开端,将叙事空间由街区转向井亭医院,故事由一起青少年的强奸案而全面展开。
香椿树街是苏童以童年老家所在的苏州城齐门外大街为原型虚构出来的叙事背景。在《黄雀记》中似乎并没有出现江苏旧式街巷的标志性意象,有的仅仅是鸿雁照相馆、护城河、城墙、老街等宏观意象,或是保润家、邻居家、医院等一般性的空间意象,如果没有以往对苏童作品的阅读经验,仅从这些场域出发,读者是难以判断其明确地域特征的[4]。这与同为江苏籍作家汪曾祺短篇小说的乡土气息和民间质感不同,无论是《大淖记事》中的兴化锡匠、地域时蔬、东台、泰州等地的商贩,还是《受戒》中寺庙的建筑风格、小英子家的农作物种类等等,均具江南水乡和江苏小城的风俗特色,都可以使读者明确地识别出故事发生的地点。此外,明海在寺庙中受戒,锡匠在老街中顶香请愿,这些风景和风俗孕育着人物的性格,也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桥段。然而对于苏童的小说而言,不仅是《黄雀记》,对于《香椿树街的故事》这部直接以香椿树街命名的小说集来说,文本中的环境和场域描写也被模糊或架空。小说中几个重要的转折点,诸如祖父“丢魂”、仙女在井亭水塔失贞、保润出狱后与柳生的相遇等等并没有香椿树街间接或直接的参与,它仅仅作为一个悬置在小说中的地域符号,如果脱离这个预设,情节仍然成立。当然,苏童是先锋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淡化小说中的环境部分符合现代先锋文学的审美特征。但是,以这条街为叙事背景的小说占据苏童创作成果的一半左右,苏童本人在许多创作谈和采访当中也表达了他对香椿树街的坚守:“有很多朋友说,我借《黄雀记》回归了香椿树街。其实,这条街,我从来没离开过。几十年来,我一直孜孜不倦地经营香椿树街小说,香椿树街要写一辈子[5]。”通过自述可以发现,承载苏童童年记忆的香椿树街在小说的虚构和创作当中是难以磨灭的。因此,对于苏童来说,香椿树街的意义远非简单的场域符号这样简单。
既然如此,为什么苏童没有像汪曾祺那样详实地书写童年的家乡?苏童告诉记者:“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生长的街区逐渐消失、倒塌、颓废,所以我想通过创作小说造一条街,这条街是看世界的窗口,我希望它和世界一样辽阔、悠长、宽广,即使时代变迁,也永不消逝[6]。”其实两人都是在回望,汪先生在80年代回望30年代的旧梦,在里下河流域文化史的遗存中挖掘中华民族的坚韧。然而,苏童站在后现代社会回望传统,他看到了一个已经荒芜甚至正在崩塌的香椿树街,这条老街竟然变得如此模糊更难以抵抗现代性的沁染。在苏童笔下,香椿树街已经无法召回游失的灵魂,无法再次承担起安抚和救赎的重任。因而,苏童的小说并没有像汪曾祺那样诗性地书写,而是以黄雀之名在讲述寓言:祖屋在保润母亲的记忆中是失范的长辈、叛道的子女和逝世的丈夫,最终她选择了逃离;药店与服装店的改造与租赁使旧屋变得面目全非,它作为过往和传统的隐喻符码正默默地遭受着时间的侵蚀;柳生和保润从香椿树街出走,经由一个轮回,再次回到老街以后,一个死亡一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而白小姐是因保润和柳生才与香椿树街发生联系,她原本生长在井亭医院的花工房中,香椿树街其实是不属于她的。在小说的结尾,白小姐在租屋当中遭遇街坊四邻的围攻,她狼狈出逃,跳进老宅旁的小河,然而河水也不再清澈,河流里堆满垃圾,一只似乎刚刚被人用过的避孕套在水中急促地尾随着她,喻示着性的放纵,无负重的狂欢所带来的恶果与代价早已侵入香椿树街。冲突与逃亡,破败与污浊,正如波德莱尔《恶之花》中所寓言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下的社会现实。同样,现代性侵染下的老街早已是废墟一片,无法被虚构,也无法被拾起,虽然不再承载一段故事,但是苏童依旧将它放置在寓言之上,仍然是令人惊醒和反思的终极之地。
三、井亭病院里的疯癫与冷漠
相对于老街所代表的传统,医院则是现代文明的空间符号。本雅明认为,站在满目疮痍的欧洲物质与文化的颓败废墟上的波德莱尔,以寓言的形式言说现代人的生存与精神上的危机和困境,抒发出人们的忧郁与呐喊:病态的人群吸噬着工厂的烟埃,呼吸在棉絮当中,汞铅和各种创造杰作所需的毒物渗透在人体组织中。同样,苏童也用寓言的形式通过香椿树街的凋敝和三位主人公命运的纠葛展现出资本神话时代、社会转型之后的信念体系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以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精神世界的不断陷落,而精神病院则是无序与疯癫的最好表征。但是与波特莱尔不同的是,苏童对待废墟的态度并没有义愤填膺的控诉,更多的是以一种疏离冷漠的视角,以精神病院衔接并凝视着小说当中的三个人。
杨国伟在《苏童的归路与迷途》中指出:《黄雀记》依然以主题意蕴的游离状态保持着不悲不喜、不哭不闹、不痛不痒的文本叙事效果。苏勇在《<黄雀记>的叙事策略》中指出:他始终是那么淡定,隔岸观火。苏童没有抗议,甚至连叹息都是那么微弱并且稍纵即逝的。苏童不仅悬置自己的叙事态度,小说中的历史也同样做后置处理。李雪在《变与不变中的苏童》中指出:历史对于苏童不过是布景,是被后置的风景,用以营造氛围和释放想象力,苏童探寻的似乎是超历史的抽象的人。《黄雀记》中的历史虽被后置,但他是一只大手,在场景背后操纵着保润、柳生和白小姐三人的命运。保润是最沉默的底层,只有在精神病院中游刃有余地操纵绳子捆绑祖父时,他的眼中才闪现出逼人的目光,他在绑人中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与其说他迷上了捆人,不如说他迷上了控制与操纵。控制欲源自本我内心深处的原始欲望,有时也是造成历史悲剧的原因之一。在他出狱之后,他选择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他遵循简单的因果报应原则,出于最初对仙女的好感,去找今天的白小姐为自己讨个公道。然而接连的误会,使保润最后酿下悲剧。保润是典型的底层,思维耿直,甘于平庸,当被时代的洪流裹挟时,则因无法融入而造成个人和社会的悲剧。斯皮瓦克曾在《底层人可以说话吗?》这一论著中提出“底层无言”的观点,生存方式形成了他们的思维方式,通过刻板蒙昧的方式证实自身的存在,因而他们自觉无言。
相对于甘愿留在井亭医院照顾祖父的保润,柳生则更为入世。对仙女的强奸,柳生一家选择嫁祸栽赃,与保润多年的相识情谊,在警车之中便瞬间化为乌有,成为陌路,面对个人的利益,情感似乎并不重要。但是柳生身上依旧留有普通人朴素的是非观念和善恶伦常,此后他选择夹着尾巴做人,通过照顾保润的祖父赎过。
至于白小姐,她即是这个时代的狂欢者,又是受害者。仙女自幼就成长在一个疯癫的世界中,隐喻着资本神话时代社会规则的混乱与文明秩序重建前的状态。而她本人是这一问题的直接受害者:保润的捆绑,柳生的强奸,给她的人生留下伤痛的记忆。她无力挣脱命运的安排,在成年之后她成为白小姐,实则就是当下的高级妓女。既然无法抗争那就尽量挥霍,白小姐采取无原则的方式去挣钱,去活下去。在狂欢之中抵抗虚无,而结果却是更加空虚。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指出:一个可以用理性方法解读的世界,不管存在多少问题,它终归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宇宙当中的照明与幻觉一旦全部消失,人会自己感觉自身是一个陌生人,成为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为他关于家乡的记忆被剥夺,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与希望。这种人与自己生活的分离,演员与环境的分离状态才真正地构成荒诞感[7]。白小姐正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她的知识谱系当中“家庭”“希望”这样的概念是陌生的,当自己要成为母亲时才选择回首,即便如此孩子和母亲的天性也没能使她获得最终的安妥,也许逃离、奔波和孤独才是她最适合她的归宿。从这些人物的命运来看,忧郁和昏暗是整篇小说的底色,呈现出类似卡夫卡小说的离奇与荒诞,因为这些人物都存在于一个人与人相互异化达到最大程度的时代,而作者也以同样破碎与分离的方式观照普通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因而,《黄雀记》中的寓言正是苏童在体验香椿树街在不断走向衰败后的结果,以白小姐这个人物更为集中地表现出浓厚的存在主义遗风,通过精神病院这个空间意象反映出现代人在日益异化的社会中理想幻灭、生活绝望的挣扎与无奈。
四、断裂下的拼接
《黄雀记》中“罪恶”的肇始源自柳生少年时性意识的萌动。小说的结尾部分,白小姐回忆当年的水塔上的场景:青春期的柳生有着刀片一样的腹股沟,生殖器官就像紫色的萝卜,力比多便从柳生的本能中释放出来。力比多在稳定有序的社会规则的规范下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如果被无序地释放,则存在于两种情况之中:一种是前现代的蒙昧,另一种就是文明秩序的断裂。弗洛伊德学说的出现实则是现代文明衰败的一种表征。虽然成长是小说的主题之一,但是性却成为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羁绊,因而苏童对于性的书写所寓言的正是这种社会现状。
书写成长的主题与少年性意识的萌动是苏童始终没有放弃的,从《桑园留念》《城北地带》《舒家兄弟》到《黄雀记》,莫不如是。在现代人的观念中,青年一代应该是活泼烂漫的,但苏童却深切地看到了他们孤独的处境,以“性”这一原始的本能为切口,表现现代性社会对青年人的异化。然而,现代性的诸多问题不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对他们父辈和祖辈的异化更是时时加重着这份孤独的重量,呈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与社会之间的断裂,主流与边缘的对抗。在《黄雀记》的情节线索中,小说以三位主人公的季节分别为题,以此形成独立的三个部分,即便三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但是小说以三人断裂的身世背景开始,以三人的断裂结局收场——死亡,收监与逃离。对于这种断裂的阐释,本雅明在《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中指出:从表面上看,情节似乎决定着悲悼剧中突变的进程,但是实际上,无常变化的交替情绪控制着剧情的走向,而此般变化交替的情绪却又是由始终不变的悲悼和忧郁而决定的。
不论以怎样的形式,一部介入现实问题的文学作品是不应停留在对问题的展示这一环节的,提出对该问题的理解和对未来的设想才能真正地反映出一名作家的担当。苏童曾提出:无法摆脱的孤独和心灵的自我救赎是人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这是我们和文学大师都在关注着的现实[8]。小说中,柳生被保润杀害,保润被愤怒焚烧,唯一有机会自救的便是白小姐。她身陷老街坊的围攻当中跳入护城河,然而河水是污浊的,避孕套提醒着白小姐纵欲后的恶果,然而正是这污浊给予白小姐一场洗礼,也让她得到自醒和反思,在她感受到终结与死亡的迫近时,她接受了河水的训诫,急切地用河水清洗腹部,不希望孩子同母亲一起蒙羞。虽然白小姐本不属于香椿树街,但是这条河却像镜子一样照清白小姐身上的肮脏和悲剧,老街反而成为了“他者”的救赎之地。小说的大部分以断裂表现孤独,以终结抵制放纵,在结尾才终于出现情感的反拨。在小说最后,怒婴与祖父贴合到了一起,达成了垂老与新生的接续。祖父作为守望者,阻止了柳生的嫖娼,收养了仙女的孩子,无奈的是象征着传统伦理的“魂”是实实在在地丢了。象征着未来与希望的婴孩则表达着对现代人行迹的怒与耻,而两者接续到一起则形成历史与现代之间的张力。《黄雀记》中的历史不再像《妻妾成群》《罂粟之家》那样在一个怪圈当中循环往复,而是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和光明尾巴,寓言着传统的记忆将在现代人的反思和自救当中被寻回。面对这样的结局,虽然无法明确地发现线性的进步,但确是以接续的观念打破永无休止的循环。
苏童以相对疏离的视角在凝视香椿树街与井亭医院里的人们,他优雅的写作姿态符合中产阶级的偏好,但是他正是以忧郁的目光和以寓言的方式,站在当下回望甚至重建他脑海中的精神原乡。手电筒与骨骸,小拉与绳索,老街与医院,苏童在这些本不相关事物之间建立关联性,在互相替代的过程中使人性的逃离与寻找、价值观念的崩塌与重建、现代生活中的反思与自救等深层的母题得以表达。对于《黄雀记》来说,它就像巴洛克艺术那样,虽然徒劳无益却又任性放肆地试图用谜团和隐蔽的东西取代熟悉且神秘的事物,巴洛克艺术品只想永久地存在,用它的全部感觉恪守永恒[9],目的则在于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