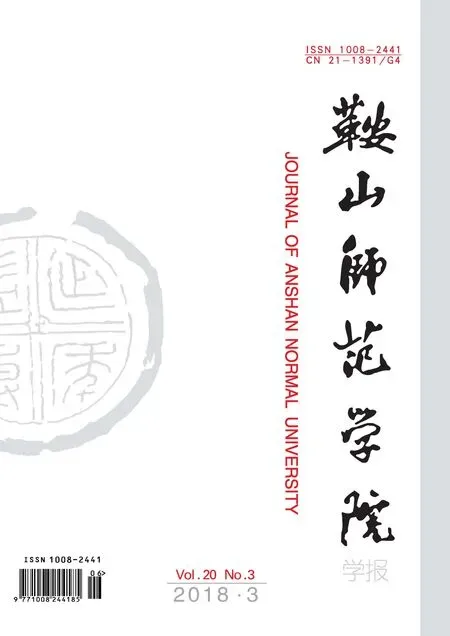羲城与河南淮阳史前聚落遗址
金 宝
(鞍山师范学院 国学研究中心,辽宁 鞍山 114007)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二《渠》记述古陈国今淮阳的古迹时说:“沙水又东南迳陈城北,故陈国也。伏羲、神农并都之。城东北三十许里有羲城,实中[1]。”郦氏所说的“羲城”指上古伏羲时代遗迹伏羲城,郦氏所记载的伏羲城在古陈国(今河南淮阳)境内,约在陈城东北三十里左右。郦氏对伏羲城方位里程的记载言之凿凿,当有所依据。这就为我们寻找人文始祖伏羲在陈地的居处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传说三皇之首的伏羲在古代文献中多被称之为太昊伏羲,为华夏文明的人文始祖。关于伏羲的传说,最早的记载见于出土文献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2],在帛书记述中伏羲已被神化为创世之神,其未被文献记述的传说可能会更早一些。关于伏羲的年世行迹,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神化成分的增加、真实信息的流失,故我们知之甚少。综合早期的文献记载,大致有以下几条可供参考:
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3]。”
汉班固《汉书·律历志》引刘歆《世经》说:“庖犠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帝为太昊[4]。”
晋皇普谧《帝王世纪》说:“太昊帝庖犠氏,风姓也。母曰华胥。遂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犠于成纪[5]。”
宋司马光《稽古录》说:“太昊伏羲氏,风姓,以木德继天而王,都宛丘。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顺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上古民处于草野,未知农桑,但逐捕禽兽,食其肉,衣其皮,禽兽飞走,非人所及,制之甚难,无以御饥寒,故太昊教之为网罟,以罗禽兽,漉水物;又教民豢养六畜,马、牛、羊、豕、犬、鸡,无逐捕之劳,可以充庖,且以为牺牲享神祇,故号伏羲氏,亦号庖犠氏[6]。”
宋郑樵《通志》说:“伏羲者,燧人氏之子,母曰华胥,履大人之迹于雷泽而孕,因风而生,故为风姓。伏羲生于成纪,作都于陈,故陈为太昊之墟[7]。”
宋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引荣氏《遁家开山图》注:“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8]。”
值得说明的是,太昊伏羲时代还没有形成能够记录语言的文字,其相关信息基本来源于传说,传说不同于信史,其中虽然不无历史的信息,但还需要剥离其中的神化色彩与先民主观想象的成分,寻找可靠的文化因素与相关的佐证,然后经过认真考辩,才有可能接近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根据上古史的研究成果,太昊与伏羲不是实有的人物名称,而是两个不同的史前部族的称谓符号与这两个部族融合后所创造的一个史前时代的符号。这两个部族生活的时代要早于传说中的黄帝,所以说太昊伏羲在传说中被排序为三皇之首。上古史研究者普遍认为,太昊是属于东夷的东方部族,活动在今豫东、鲁南、皖北一带,而伏羲则是西北的部族,源起于古成纪今甘肃天水地区。这两个部族之所以在文献记载中成为一个部族的称谓符号,实现了族属的一体化,当然是两个部族融合的结果。传说“伏羲生于成纪”,曾“徙治陈仓”,最后才“作都于陈”。“成纪”是唐代以前的古县名,其地在今甘肃省天水市,处于黄河最大支流渭水的上游;“陈仓”即今陕西省宝鸡市,在天水东方,处于渭水的中段,距离渭水汇入黄河处不远。从成纪(天水)到陈仓(宝鸡),有一条上古沿渭水开辟的通道,从陈仓到宛丘(淮阳),自然可以沿黄河两岸前行,这是伏羲部族东进中原、豫东的必由之路。这个信息便透露了西北伏羲部族向东迁徙的走向和同东夷太昊部族融合的事实。传说太昊伏羲氏为三皇之首,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这是传说中通过部族融合而形成的更大部族或族群并开创华夏文明的重要信息。太昊和伏羲两个部族融合而后,被称之为太昊伏羲,这个称谓仍然是氏族的符号,皇甫谧《帝王世纪》说,“女娲氏……承庖犠制度……及女娲氏没,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混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庖犠之号[9]。”由此透露出,太昊伏羲不仅是上古氏族的符号,而且是这一氏族在上古史中作为某些部族代表开创的历史时代符号。传说中太昊伏羲的事迹当是这个族群在那个时代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所共同创造出来的。战国之际,这个族群符号被人格化甚至神格化,成为了创世之神或人文之祖,这个族群的事迹便被集中在一个创世之神或一个始祖的身上。今天人们探讨太昊伏羲时代遗存的问题,应该摆脱传说中人格化或神格化的传统思维定式,在族群整体发展与其时代历史的前提下进行研究。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太昊伏羲实际上是一个上古族群与她所创造的那段历史的代名词。据文献记载,在太昊伏羲的时代已经有了初始的礼法观念与社会形态,是后世建立国家的族缘基础和文化前提,因此文献记载太昊伏羲时代已有了超越部族酋长的族权中心——都,这无疑符合社会形态进步的发展逻辑。
关于太昊伏羲之都的所在区域,文献有所记载:《左传》(昭公十七年)有“梓慎曰,‘陈,太皞之墟。’[10]”《竹书纪年·太昊伏羲》有,“都宛丘。”其资料来源应当是口传的历史。而《水经注》有“故陈国,伏羲、神农并都之。城东北三十许里有羲城,实中。”这不仅仅是依据传说,而且有了上古遗存文化的佐证,发展成贴近信史化的记述。于是后世的史书、地志皆遵而从之。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九《河南道·宛丘县》说“包犠氏、神农氏并都于此”。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河南道·陈州》承引《元和郡县志》之说。宋司马光《稽古录》亦说“都宛丘”。宋苏辙《古史》说“居于宛丘”。宋郑樵《通志》说“作都于陈”。宋罗泌《路史》说“都于宛丘”。明李贤等《明一统志》说陈州“古伏羲所都”。清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说“伏羲氏都于陈”。清马骕《绎史》亦说“都陈”。清李锴《尚史》说“伏羲氏都陈”。至于《大清一统志》承《左传》与《水经注》之说并转而录之。看来太昊伏羲“作都于陈”“都于宛丘”是古人的共识。请注意,以上史书、地志所说的“宛丘”“陈”都是就地域范围而言。“宛丘”虽然是一个具体土丘的名称,但是在上述记述中是指以宛丘得名的先秦地名,类似于后世的一个县级行政区。“陈”则是先秦古国名,所指范围比宛丘还要大些。只有《水经注》以及引述其说者指出了“羲城”的具体方位与里程。不过对于太昊伏羲所都也偶有异说,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天皇庖羲都陈留”;荣氏《遁甲开山图》注,以为“伏羲徙治陈仓”。“陈留”乃古陈国属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注,“孟康云:留,郑邑也。后为陈所并,故曰陈留。”据有关伏羲“都陈”的记述推测,此“留”字当是衍文;也可能是伏羲部族迁徙到今豫东的曾经居处之地。至于“陈仓”,前已提及,是伏羲部族东迁之际所经之地,伏羲部族可能把陈仓作为迁徙过程中的中转地,在那里逗留过较长的一段时间,故曰“徙治”,而不言“作都”。
这里顺便谈一下民国《淮阳县志》的相关记载。《淮阳县志》卷二《舆地·古迹》说,“羲神实:未详其处[11]。”其记述有三处错误:一是《县志》所用《水经注》版本实非善本,将“羲城实中”妄改为“羲神实中”。日本《京都大学藏钞本水经注注疏》辩证说,“朱城讹作‘神’,笺曰:谢兆中云当作‘羲’,赵云‘按全氏云非也,神即祠也,戴改城’。守敬按:《名胜志》引此作‘城’。考郦书屡言某城‘实中’,若‘祠’不可以言‘实中’也。全不察耳[12]。”二是《县志》对“实”的理解有误,以为“实者对虚之名,言神农所在,人民常实也”,殊不知“实中”乃城中有建筑、居民之谓,以“实”字上属“羲城”,文字不顺,语义不通。三是《县志》舍《水经注》此则全文,引用不完整,不符合学术规范。所以本文不从《淮阳县志》“羲神实”之误讨论“羲城”的问题。
关于太昊伏羲之都的具体所在,《水经注》的记载仅仅是一个线索,要想说得确切,只能在考古发现中去寻找。在淮阳地区发现的上古民居聚落遗址有两处:一是20世纪70年代末发现的被称之为平粮台古城遗址。遗址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城东南4公里的大朱庄西南侧,古城属于龙山文化中期偏晚,在古城的夯土城墙之下叠压有大汶口文化的晚期遗存,出土的陶片以棕陶居多,青灰陶次之,主要器种有鼎、罐、圈足碗、圈足碟、壶等。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文物普查时发现的朱丘寺遗址。遗址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城东北17公里的四通镇王蔡园村东南,遗址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出土有扁平型鼎足、深腹罐、敛口豆、圈足盘、平底盆、澄滤器及陶纺轮、陶网坠、石斧、石锛、石箭镞、蚌镰、骨锥等,同时发现有多处红烧土房屋基址。两处民居聚落,在《淮阳县志》中已有记载,《县志》卷二《舆地·古迹》记述:“贮粮台:在县南五里。”注曰“俗呼平粮冢,高二丈,大一顷,有四门,林木郁然,未详何代所筑[13]。”又同卷《陵墓》记述,“平粮冢:在城东南八里[14]。”《县志》卷二《舆地·陵墓》记述:“朱丘寺冢:在城东北三十五里[15]。”同卷《寺观》记述“朱丘寺:在城东北四十五里[16]。”《县志》的记述说明,两处民居聚落在淮阳民间早有流传,只是不详其考古时代。现代考古解开了其时代面纱,证实了它们都是上古民居聚落,平粮台上古聚落是大汶口文化的遗存,朱丘寺上古聚落是龙山文化的遗存。然而据考古学家认定,大汶口文化为距今4 000~6 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的文化遗存,龙山文化为距今4 000~4 600年的文化遗存,虽仍属于父系氏族文化,但晚于大汶口文化。两处上古聚落遗址都距离传说中的伏羲时代有非常大的时间差距,参照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大地湾遗址的考古时代,其上限可追溯到距今8 000年左右,都无法证明哪一处是太昊伏羲之故都。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城东北三十许里有羲城”。郦道元所说的“城”即其上文明确指出的“陈城”,亦即古陈国都城与楚襄王迁陈后的楚都城。这座陈楚故城在1980年的考古试掘中已经得到证实即是地处淮阳县城域内的古城,遗址尚存。这就是说,郦道元作为坐标的陈城已经明确,以此为参照,羲城在陈楚故城东北三十里许,其方位和里程与考古发现的朱丘寺遗址比较接近。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宛丘在县南三里,高二丈。”“按今县城西移,故宛丘在县东南[17]。”《民国淮阳县志》卷二《舆地·古迹》记述,“贮粮台:在县南五里。”又同卷《陵墓》记述,“平粮冢:在城东南八里。”以淮阳陈楚故城为参照,方位相同,里程虽有出入,是因为文献记载不一所致,若按“平粮冢:在城东南八里”计算则同遗址与县城的距离相吻合。尽管如此,按学理也不能轻易地作出两处遗存是太昊伏羲时代遗址的判断。
认真分析《水经注》对“羲城”的强调,郦道元极有可能认为“羲城”是太昊伏羲的都城所在,但是郦氏没有交代他的根据,假如其依据的是传说,从“羲城实中”的记述看,在郦道元生活的时代“羲城”尚有人居住,“羲城”的得名是民间对传说的认同,而且颇有些渊源,当是历代口耳相传所致。尽管如此,仍然不能下“羲城”是太昊伏羲之都的结论,只能说“羲城”是郦道元时代传说中的太昊伏羲时代的曾经的故都。
按照考古时代,平粮台遗址第一期遗存还要早于朱丘寺遗址,有些淮阳的地方学者认为平粮台是“太昊之墟”,这个提法只能算作一种大胆地假设。这种假设是以假设平粮台遗址可以上推至太昊伏羲时代为前提的,按照这种假设推理的思路,朱丘寺遗址也可以上推至太昊伏羲时代,那么平粮台遗址与朱丘寺遗址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假设二者共时存在,那么应该从太昊部族与伏羲部族融合之初的磨合期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果平粮台古城是“太昊之墟”,是太昊部族的族权中心,那么伏羲部族从西北初到豫东地区不可能在短期内融入太昊部族,甚至取代太昊部族并成为两个族群融合后的主体。传说中记载太昊伏羲族群事迹多是伏羲部族的事迹,很可能太昊部族被文化相对发达的伏羲部族所融入。如此初来乍到的伏羲部族无疑需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这个落脚点可能就是羲城。也就是说,在两个部族完全融合之前,宛丘当是太昊部族的族权中心,羲城当是伏羲部族的族权中心。在两个部族融合后,二者都有可能成为太昊伏羲的都城。假设二者历时存在,一前一后,那么在太昊伏羲族群漫长的发展时代中,就可能发生了都城的迁徙,是从平粮台遗址迁至朱丘寺遗址,还是从朱丘寺遗址迁至平粮台遗址,则无法推测。其实,上述的两种假设目前还缺乏假设前提,即大汶口文化之前的考古发现。
总而言之,以考古发现说话,是客观、理性、科学的;以传说说话,其根据不够坚实,仍然是一种未得到证实的传说;以假设推理说话,虽本于逻辑思维,有着一定的推理前提,但推理在没有得到证实之前只能是一种假说。以上是笔者的思考,望各位专家学者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