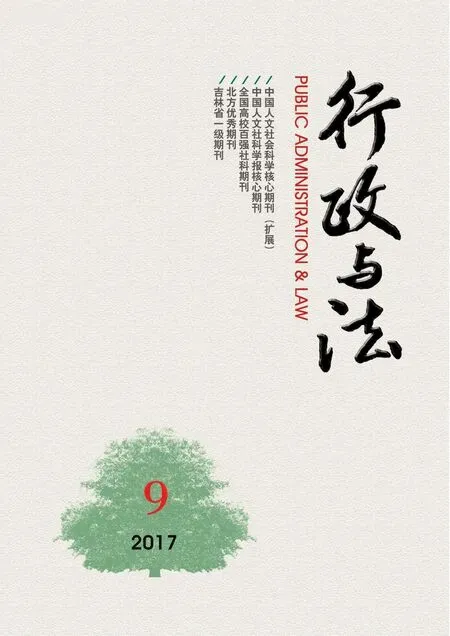我国网络舆论安全面临的困境及改善思路
□ 汪景涛,毛欣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我国网络舆论安全面临的困境及改善思路
□ 汪景涛,毛欣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一个安全的网络舆论状态是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的重要构成要件,在制约公权力滥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功能。当前,国内网络舆论安全面临诸多困境:一方面,地方政府受传统维稳思路的影响,或对其压制或引导不力;另一方面,公民网络舆论漠视和网络暴力等行为亟待理性回归,而境外别有用心者企图通过网络舆论扰乱民心,也使网络舆论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强化网络舆论安全治理,要在推进立法、政府公信力重塑及公民舆论理性培育等方面入手,并且要将境外势力与我国社会内部矛盾区分开来。
网络舆论安全;政权合法性;宪法权利;公信力;舆论理性
网络舆论安全问题的提出,大致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新媒体革命的时代背景。新世纪以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言论表达提供了新的场域,网络舆论作为言论自由的合理延伸为学界所重视和讨论。由于新媒体为每一个拥有客户终端的普通公民都提供了更有效的社会舆论参与途径,因而其本身就蕴含着挑战传统媒体话语权和要求平等互动的人文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革命也是一场表达参与社会治理诉求、思想理性自我塑造的革命。二是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不同于以军事和政治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不断凸显出来的,从传统的安全领域扩展至经济、科技、意识形态等领域,其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网络舆论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领域,也随着互联网络的兴起而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它与文化安全、信息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领域相交织而又未能被其所完全内嵌,因而具有独立的研究价值。三是社会转型期矛盾高发的特征。当前,我国社会已步入改革的关键期和深水期,社会结构更加多样、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导致公共事件频发、网络舆情复杂。而境外一些主流媒体一直未放弃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攻击,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公共事件往往会被其拿来在网络上炒作,严重影响和威胁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与网络舆论安全相关的问题
互联网尤其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为公民提供了参与社会治理和讨论公共事件更为便捷、高效的途径,但在转型期,网络传播的优势却使社会治理和信息导向控制面临困境,给政府应对舆论分歧、整合社会共识带来了严峻挑战。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发布的《蓝皮书(2016)》指出,网络舆论影响着政府决策和中国政治进程。
(一)网络舆论传播的特点
网络舆论影响力不断深入,已成为深度影响转型阶段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这是与其传播特点分不开的。网络舆论传播有以下三个特点:
⒈去中心化。互联网尤其是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使每一个用户都具有发布和分享信息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每个人都是记者、都是媒体平台。传统的以某些权威媒体平台为中心的信息传播模式被逐渐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无数个小型信息中心(这里的“小”指的是物理空间而非传播速度和影响力)。新媒体对权威媒体的影响力与公信力逐渐形成挑战,并将每个普通公民传播信息的能力最大化,让任何一个微弱的发声都具有难以预估的潜在舆论影响力。
⒉分众化。无论QQ、微信还是微博都具有分组与建群功能,具有相同爱好或者以某种特殊关系如亲情、友情所维系的用户会选择组建一个相对封闭的虚拟空间,用以交流感情和探讨话题,新媒体的这一功能便是分众化。分众化的结果是:它使某些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私人化。一方面,提高了信息传播和接收对象的准确性,使信息传播的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在这些相对封闭的群体内容易产生“意见领袖”,从而更加弱化传统信息获取渠道的权威性。
⒊可信度低。这里的可信度低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并非新媒体本身传播信息绝对意义上的可信度低。在信息保真方面,由于传统媒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了制度化的信息审查机制,实现了信息真实性的最大化,而新媒体信息传播的一个特点就是信息的接收者在分享信息的同时可以对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处理,如附上个人评论和情绪,因而导致信息在海量的传播过程中存在偏离本真含义的可能性,甚至与原本意旨相背离。
(二)舆论安全与网络舆论安全
⒈舆论安全。就内涵和外延来看,当前学界对于舆论安全的定义尚难归一。有学者从舆论对于国家利益维护及国家形象塑造的功能价值角度出发,认为可将国家舆论安全界定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家舆论传播、引导及其国家舆论自我更新能力等不被入侵或威胁,国家舆论能够处于正常发挥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形象等功能的一种状态。[1]这是一种广义上的定义。也有学者将舆论安全定义为:维护主权国家根本利益与安全的正向舆论免受威胁损害的客观状态。[2]这一解释将舆论安全限定于“正向舆论”,而将负面舆论从舆论安全的受侵害范围内加以排除。笔者认为,舆论安全的含义应该从两个层次和两个角度来理解:
两个层次:舆论安全应该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的有机统一。一是国际舆论安全,即国家作为一个主权整体在国际社会具有相当程度的话语权,其引导国际话语体系(或者至少是表达权)不受他国或组织的威胁和侵犯以及对威胁和侵犯具有压制和反击的能力。二是国内舆论安全,即国家公权力不对国内合法的网络舆论表达权进行压制,国家公权力所主导的舆论方向能够得到公民的信任而具有权威性,以及网络舆论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两个角度:一是如果将现实存在的舆论本身当作一个客体,那么其本身也存在安全问题,如公权力的压制以及网络暴力的侵害,从这个意义上讲,舆论本身便天然蕴含着表达和言论自由的内在精神,而这个角度的舆论安全便是言论自由安全和不受侵犯;二是舆论并非总具有正向功能,很多情况下舆论为网络暴力和网络谣言所“绑架”,这个角度的舆论安全便是舆论不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威胁和侵害。
⒉网络舆论安全。结合学者们关于舆论安全的相关论述,笔者将网络舆论安全狭义地解释为:国家公权力不对合法的网络舆论表达自由进行压制以及网络舆论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他人合法权益造成威胁和侵害。
(三)网络舆论安全的宪法地位
言论自由是自由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我国《宪法》分别在第35条、第41条对公民的一般言论自由和针对公权力的言论自由作出了明确规定。而网络舆论是言论在互联网时代的延伸,因而保护网络舆论安全,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保护公民言论自由具有相同的宪法价值和宪法地位。
二、保护网络舆论安全的价值
网络舆论是公民言论在互联网时代的延伸和扩展,保护网络舆论安全,既符合保护言论自由安全的内在精神,又具有以网络时代为背景的独特价值取向。具体分析如下:
(一)巩固国家政权合法性
天赋人权论者认为,对于人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人权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和基础,国家权力是由公民的自然权利转让或放弃而来的,是由所有公民授权集合而成的,离开了公民的自然权利和授权,也就没有国家权力。[3]换言之,国家政权合法性来自于公民对国家政权的授予、认同和信任,即社会公意所归。因此,作为公民权利一部分的网络舆论安全权利得到承认和保护不仅是增强政权合法性的途径,也是考验政权合法性的手段。社会和谐并非只有一种声音,而应该是各种因素的相互包容并在此过程中维持动态平衡。网络可以为各种观点的表达提供超越空间距离的域场,使不同的观点能够对话和交流并在此过程中达成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执政党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保护网络舆论安全,让有益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表达,让有益于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的各种智慧和源流充分涌现,从而真实地反映社会声音和民意诉求,才能促使政府有效、高效作为。这不仅不会有损于国家利益和政府形象,反而会树立党和政府倾听公众心声、关注公众诉求的形象,巩固国家政权更为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二)制约公权力滥用
政府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也存在自利的倾向,并且产生权力膨胀的惯性。[4]为使公权力的行使不对私权利构成侵害,必须将其限制在合法范畴之内,而保护网络舆论安全便有制约公权力滥用的重大价值。在欧美等西方国家,舆论自由具有重要的宪法地位,且常常被称为“第四权力”,是公民权利制约公权力的基本手段。网络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微媒体、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为公民针对政府行为和公共事件发表看法和评论拓宽了渠道。在监督和制约力度与维度上,网络舆论相对于传统媒体具有更多的优势,公众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及公众号等形式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例如:将警察执法视频上传到互联网,对司法不公进行批评等,以保证和促进公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对党和人民负责。这些彰显民意与公意的网络舆论是遏制公权力滥用的“笼子”,能够将公权力限制在合法范畴之内、暴露于阳光之下。
当前,我国已进入社会转型期,依法治国、治理腐败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加强和完善对网络舆论安全的保护,充分发挥网络舆论对政府行为制约和监督的价值功能,对于政府廉政建设亦具有重要价值。
(三)推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互联网的发展已使网络舆论深深嵌进社会各项事业的运行机制中,透过近几年网络舆论对于社会公共事件的讨论所产生的效果可以管窥网络舆论对于国家法治建设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因被不当收容致死的新闻刊发后,经平面媒体和网络舆论接续报道和转发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使得实施了21年之久的《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2012年,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案、上访妈妈唐慧案等都在网络舆论中掀起了废除劳教制度的讨论,2013年,实施了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宣布废止;而湖北佘祥林案、河北聂树斌案等一批冤假错案的曝光以及网络舆论锲而不舍地对正义的追求,更是有力地推动了死刑案件审判程序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美国废奴运动领袖菲力普斯对于舆论之于法律的重要价值充分认可:“若法律失去公众舆论的拥护,则法律毫无力量”,即强调了公共舆论对于法治建设的作用。
(四)维护社会稳定
保护网络舆论安全,有利于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观点和看法,及时将社会公意、底层声音反馈给相关部门,使社会热点事件、民生难题能够及时得到回应和解决,进而维护社会稳定。从政府角度来说,公众以图片、视频等直观形式将社会突发事件的舆论热点发布到网络上,便于政府及相关部门及时掌握舆论动态,掌握更多的治理主动权,从而迅速合理地调动人力、物力加以应对。相反,如果政府不重视保护公众的网络舆论安全,在遇有突发事件时一味采取封锁、删帖等侵害公众知情权和表达权的极端应对方式,不但不能及时、迅速地化解危机,反而会给公众造成更大的困惑及对政府产生更多的不信任,进而使事态恶化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三、当前我国网络舆论安全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境外因素导致的困境
境外因素对我国网络舆论安全造成的困境主要有两个方面:
⒈话语权挑战。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必将给世界现有政治经济格局的形成带来一定的影响,如部分西方国家和主流媒体敌视中国,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将本属于中国内部的社会矛盾扩大化、国际化,美联社、《华尔街日报》等西方主流媒体更是将危害香港社会稳定的“占中”事件美化成所谓的“雨伞革命”“香港民主觉醒”。[5]由于西方在网络技术方面占有领先地位,因而其网络舆论的掌控能力及影响力不可低估,网络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和媒体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及和平演变、扰乱民心的前沿战场。他们以新闻自由为借口,通过互联网对我国转型期一些社会公共事件进行带有明显倾向性的扭曲评论,肆意放大我国社会内部矛盾,刻意引起国际舆论关注。这些负面舆论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对我国网络舆论安全形成了冲击,对政府应对网络舆论话语权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⒉网络舆论背后的势力值得警惕。与网络舆论面临的话语权挑战相比,更为值得警惕的是网络舆论背后的势力通过利益交换暗中扶植和资助其在我国的代理人散布、组织威胁国家安全和民心稳定的煽动性言论和行动。2016年,在互联网披露的美国前国防部顾问白邦瑞于2014年10月“占中”期间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访问的短片中,他承认美国当年介入“占中”的事实,又指美国政府透过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提供过数以百万计的资金,协助香港推动“民主”。[6]虽然全面看待“占中”事件尚有许多细节值得反思,但让部分青年学生通过网络和媒体进行舆论造势,继而制造政治对立、威胁国内安定的国外势力及其代理人,才是更需要警惕的幕后推手。
(二)国内因素导致的困境
⒈法治困境。虽然我国《宪法》分别在第35条和第41条对公民的言论自由作出了规定,并且就保护程度而言第41条对公民针对公权力言论的保护程度明显高于第35条,即在宪法原则层面上承认和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但考虑到网络舆论属于言论的合理延伸,因此将网络舆论安全内含于宪法,是对言论自由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宪法只能对其所要保护的权利作出原则性规定,而现实生活中一旦出现有违宪法精神和规定的具体行为还应该依靠具有可操作性的下位法进行惩处。目前,我国涉及网络舆论安全的文件还停留在行政法规层面,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虽然其中或多或少有关于网络舆论安全的一些规定,但法律层级低,缺少足够的强制性,而且这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系出多门,难以适应当下我国网络舆论安全的迫切需要。
⒉政府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维方式僵化。客观地说,政府应要求公众在发布信息之前做谨慎求证,以确保网络信息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最小限度地产生误导后果。但考虑到网络舆论具有及时性的特征,若将此要求作为硬性规定强加于网络舆论则是不现实的。观察近年来多起网络舆论事件不难发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公众的网络舆论安全权利多有侵害,对所谓有损政府形象的揭发、举报和批评动辄删帖封号,甚至对质疑政府行为的公众采取强制措施,这与我国依法治国战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一味以所谓“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官方说辞,固执于删帖封号、封锁消息、打压舆论的手段,都凸显了一些地方政府在应对网络舆论安全问题上的僵化思维方式。二是公信危机即“塔西佗陷阱”。古罗马政论家塔西佗曾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后来这一见地被表述为: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危机,无论其发表何样言论、颁布何样政策,公众都会以负面评价对待之,即“塔西佗陷阱”。虽然目前学界关于“塔西佗陷阱”尚存在诸多争议,但其本身所赋予的理念已基本取得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考察时也指出:政府要正视“塔西佗陷阱”,以警示忽视民意的错误观念。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不会给予另一个喜欢遮遮掩掩、闪烁其词的人太多的信任感,同理,公众也不会对躲在暗处的权力运行过程及运行结果产生信任感。如刚刚平息的四川某地中学生坠亡案,为何公众对当地政府不信任而各种并无实际根据的网络舆论传言却得以大量滋生,这是很值得反思的。在这起事件中,公众看到的是当地政府对舆情的漠视,对真相的搪塞:尚未尸检便公布“排除他杀”的鉴定结论,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也受到了阻挠。笔者认为,近年来不断被网络曝光的政府“强征血拆”、司法冤假错案便是这些不信任的源头,其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公众长期积聚的对于权力运行和公共事件处理未能在阳光下进行的不满情绪。透过这些社会热点事件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对司法机关的判断产生质疑,对警方的解释产生怀疑,对权威专家的论证不再相信,这些盲目化的争辩给网络空间蒙上了一层不信任的面纱。[7]
⒊公民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公民不关心社会公共事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制。某些地方政府出于对网络舆论的偏见和惧怕,往往对批评和指责自身弊病的网络舆论予以压制。另一个原因是网络舆论漠视。网络舆论漠视可以理解为公众对看似与己无关的政府行为和社会公共事件以不关心、不重视的态度来对待。部分公众奉行网络舆论漠视,表现为对政府违宪违法行为不介意、对社会公共事件处理过程和结果不关心,这种行为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政府滥用权力或工作人员贪腐得不到监督、公共事件处理是否公平无人理会,其本质则是对公权力的放纵、对宪法权利的放弃。二是网络暴力。网络暴力表现为通过互联网发布伤害性、煽动性以及侮辱性的言论如文字、图片、视频等,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他人权益造成威胁和伤害的行为。可以说,网络暴力是公众网络舆论非理性的主要表现形式。首先,在技术设计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对于在其平台发布的虚拟信息容量大小进行限制,因而导致信息传播的碎片化,而碎片化的信息和文字使发布者难以对信息的逻辑进行缜密的分析和论证,因而信息接收者也很难全面了解事件全部真相,容易导致认识上的偏激化和极端化。其次,相较于碎片化特征,当前我国网络暴力背后凸显出来的部分公民法律意识和理性素养偏低才是根本原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引用关于微博舆论的一句评价值得深思:“在微博上,理性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少,谁的话语更出格,谁能裹挟更大批的粉丝,谁就能取胜,而这批粉丝往往会用唾沫星子把一个很冷静的专业问题淹没”。[8]非理性的网络舆论参与,不仅会导致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人肉搜索”、网络围攻等情况大量出现,甚至可能产生曝光青少年犯罪主体信息等背离法治精神的严重后果。
四、改善我国网络舆论安全困境的思路
(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分境外因素与我国社会内部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世界范围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更多地参与全球贫困治理、积极对外援助,中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逐渐让位于经济领域的共同合作。而随着交流增进带来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使 “中国模式”逐渐被西方各国广泛地接受和认可,西方媒体开始更多地关注我国社会和民生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甚至开始对资本主义发展弊端进行自我反思。但是,在肯定主流向好的前提下,仍然要对潜在的暗流保持足够警惕,这有赖于政府的外交斗争、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境外舆情监测体系的完善等宏观层面的努力。
笔者认为,在处理与网络舆论相关事件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何为境外因素影响,何为我国社会内部矛盾,要区别对待。当前,我国某些地方政府存在的现实问题是不能正视网络舆论针对政府行为、权力运作、司法不公及公共事件处理欠妥发表的批评言论。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对网络舆论批评的内容是否属于自身工作不到位、是否是事件处理有失偏颇、是否有违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进行客观理性的审视和自省,不能动辄以不明真相、被境外势力所蛊惑为由,对网络批评进行打压,而应正视政府自身存在的不足,积极回应公众诉求,这才是赢得民心、巩固政府权威的关键。
(二)国内层面的改善思路
⒈推进网络舆论安全立法。言论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可能会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他人权益构成威胁和伤害。同时,无论是公权力对网络舆论的压制还是网络舆论肆无忌惮地伤害他人权益都是对网络舆论安全的威胁和破坏。因此,为确保合法的网络舆论之自由权利不被侵犯,亦或超出必要限度的网络言论具有可循之法予以惩处,在宪法的原则性规定之下制定具有保护网络舆论安全的可操作性之下位法都有现实性和紧迫性。首先,应考虑将我国现有的涉及网络舆论安全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进行整合,以此为基础制定《网络舆论安全法》,对网络舆论安全保护原则、权利义务界限、公权力和他人侵犯的追诉作出明确规定。其次,考虑在新出台的《网络安全法》总则第12条中增加政府等公权力部门不得侵害公民网络舆论安全权益的相关论述。
⒉通过宪法解释明确网络舆论安全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在立法工作繁重、立法落后于现实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言论自由的宪法解释,明确网络舆论安全主体的权利义务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首先,明确公权力的义务和权力。一是公权力的保护和引导义务。网络舆论是公民通过网络表达自我观点的一种方式,因而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是一种宪法权利,也是公民表达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而一个安全的网络舆论状态也能够保证公民监督政府,及时指出政府的不足,推进公共事件解决和政府有效作为,这也是公民以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心为前提而作出的符合公民精神的负责任之举,于党于国于民皆有利,因而公权力具有保护公民合法行使自己网络舆论表达权不被侵犯的义务。此外,在承认公权力必须保护公民网络舆论安全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并非任何言论都于国家、社会和他人有利,且事实上由于网络信息传播具有变异性的特点,很多时候这些借舆论自由外衣而传播的信息都可能对他人自由与权利造成侵害。尤其是社会转型期和阵痛期矛盾多发的现实国情以及境外别有用心的因素强化了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渗透的外因,因此,政府有责任对网络舆论形态进行甄别和扬弃,有义务对威胁我国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有害舆论予以剔除。即通过构建良好的网络舆论安全生态引导社会共识,优化整合有利于政府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网络舆论。同时也要认识到,政府强化履行对于超过必要限度网络舆论的整顿和清理义务,正是为保障更多人的网络舆论安全权利不被侵害而做的努力。二是公权力的追究权力。当任何一种言论打着自由的旗号而行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他人利益之实的时候,其本身便失去了合法性。被称为西方新闻出版自由思想先驱的弥尔顿竭力赞颂出版自由,认为它可达到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但他也承认这种自由是有条件的自由,如果出版行为不遵守法令规定,就要受到惩处。[9]现代文明国家大都通过法律对超过必要限度的不当言论予以禁止和惩处,如我国刑法中的侮辱罪、诽谤罪。即便针对公权力的言论限度宽于私言论,但只要网络舆论主体实施了突破法律底线的网络言论行为,危害到网络舆论安全,政府就有权力和义务对当事人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消除对网络舆论安全的威胁,从而使其恢复到安全状态。
其次,明确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是公民的网络舆论权利。笔者认为,公民的网络舆论权利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公民有在合法范畴内通过网络舆论表达自我的权利。网络舆论权利是自由表达权在互联网时代的延伸,是公民与生俱来的一项天然宪法性权利。公民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合法范畴内对政府不当行为进行批评、对热点事件进行点评,而政府不得以网络舆论影响政府形象等借口随意侵害其权利。政府对于公民的网络言行只有在确定其超出合法范畴而确有必要予以纠正和惩处时,才可依法处置,除此以外的任何不当限制皆有违宪法精神。另一方面,公民有对随意剥夺其网络舆论权利的行为进行控告以及对侵害自身合法权益的网络言行进行追究的权利。作为一项宪法性权利,对国家机关或个人于己网络舆论权利造成的侵害,可依据相关下位法进行追究和起诉。这也凸显了当前对网络舆论安全保护之专门性法律的迫切呼唤。二是公民的网络舆论义务。笔者认为,公民的网络舆论义务同样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公民有监督公权力的义务。这个角度的公民网络舆论义务可以监督政府以使公权力不被滥用和防止司法不公,如网络舆论对于“聂树斌案”锲而不舍的正义追索,最终促使其沉冤昭雪,便是公民网络舆论义务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公民有网络舆论表达不得僭越法律的义务。洛克认为 “自由不是人人都可为所欲为”,卢梭将自由亦有边界经典地表述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英国历史上著名法官布拉克斯东曾言,在承认每个公民具有自我意志自由的前提下,也要对滥用这种自由以伤害他人的行为予以惩罚。换言之,保证自己的网络言行不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及他人权益造成威胁和伤害,将网络舆论表达自觉地规制于合法范畴,亦是公民行使网络舆论安全权利时必尽的义务。
⒊倡导政府舆论宽容。所谓舆论宽容,可以理解为公权力对网络舆论中未超过必要限度的言论具有容忍的义务和能力。公共领域中应当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言论自由情境,以保障公民充分表达其观点,哪怕这种观点是苛刻的、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10]考虑到网络舆论声音繁杂,要求它如传统媒体那样以一套细致、严谨的审查体制进行规制未免太过理想化。由于网络舆论主体个人经历、学识学历等参差不齐,且由于普通公民获取信息渠道的有限性、看待信息角度的局限性,要想使每一个网络用户的每一条转发、每一条评论都能做到公正、理性和客观是不现实的。如2009年熊某某于互联网发帖质疑某交通肇事案受审嫌犯被顶替,引起大规模网络讨论后被行政拘留。熊某某承认其质疑的依据仅仅是网络上几张与受审嫌犯长相相近的另一人的照片,未免质疑乏力。但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熊某某既没有鉴定照片是否为真正肇事者的权利也囿于资源所限而缺少求证的能力,但无论其身份地位和能力如何,以公民身份针对政府行为是否违法和滥用权力提出质疑依然是宪法赋予他的基本权利,而非公安机关所言“无业人员”违反治安管理,捏造、散布“谣言”。哈耶克有言:“我们所必须学会理解的是,人类文明有其自身生命,我们所有欲图完善社会的努力都必须在一个我们并不可能完全控制的自行运作的征途中展开,而且对于其间各种力量的运作,我们只能希望在理解它们的前提下去促进和协助它们”。[11]因此,政府要对网络舆论持宽容态度,尤其是要对其中直指公权力机构以及工作人员自身弊病的批评持宽容态度。
⒋政府公信力重塑。与主张政府在面临公共危机时强调应对技巧的讨论不同,笔者认为,从根本上看,政府公信力危机显然不能归咎于政府缺乏应对技巧。对于政府行为是解决问题的实质性行动还是汲汲于欲盖弥彰的拖延应对,公众是具有判断力的。近几年,作为网络热点的“郭美美”“四川中学生坠亡”等事件之所以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了损害,与事件发生后政府的拖延推诿、不公开、不透明有很大关系。西方法谚:“正义不仅要予以实现,而且要以人民看得见的方式予以实现”,即凸显了公众对于权力公开的价值追求。网络舆论危机的应对技巧固然重要,但既然“塔西佗陷阱”的根源是公众对权力的运行缺少信任,因而若要避免“塔西佗陷阱”,就必须构建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在政府和公众之间达成共识。换言之,通过构建和推进制度层面的政府信息公开,规范权力运作,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将政府公权力行使和公共事件处理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推行政务公开,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⒌认可公众明辨真伪的能力。在18世纪法国政府与天主教会醉心于控制社会言论的背景下,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却主张开放言论,相信公民将在真理与谎言的讨论和交锋中获得理性的胜利。杰斐逊也表示:“人民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应该让他们听到一切真实和虚伪的东西,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很能说明问题:在评价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得失问题上,四川巴中“全裸”乡政府在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等指标上位列蓝色区域,成绩斐然。考察近几年我国发生的网络舆情事件,即使有些地方政府未作亏心事,也因怕事件发酵影响当地政府形象而遮遮掩掩,继而导致大规模的网络舆论声讨,但迫于压力公布内情之后,舆论则反转为理性地反思和支持政府。由此可见,公众对是非善恶、真理谎言具有理性看待和客观处理的能力。因此,政府应该对公众的这种能力有信心,政府要充分保证权力的行使和公共事件的处理在阳光下进行。
⒍培育公民网络舆论理性。网络舆论安全生态的构建既有赖于法律法规的出台,也有赖于舆情监测机制的完善,但真正能够改善网络舆论安全生态的根本因素则是公民网络舆论理性的培育和强化。通过开展舆论理性宣传及提高公民自觉抵制网络暴力、网络情绪化等网络舆论非理性行为的能力和素养,对于改善网络舆论安全生态具有质的影响。另外,要加强对“网络舆论领袖”的引导和监督。据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发布的 《2010中国微博年度报告》显示,在当年具有较大网络影响力的公共舆论热点事件中,将近一半存在较为明显的“意见领袖”。因此,通过相关途径对这些“意见领袖”和网络名人的言论进行监督和引导,对于引导公众舆论也具有较大的价值功能。
[1]李忠伟.当代中国国家舆论安全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2]纪忠慧.美国舆论管理[M].新华出版社,2016.
[3]闫斌.网络言论自由权宪政价值初探[J].理论月刊,2013,(04):108-112.
[4]夏玉成.和谐社会与公共舆论自由独立精神之辩[J].云南社会科学,2006,(01):06-09.
[5]香港“占中”十问[EB/OL].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 /2014-10-03 /6649570.shtml.2014-10-03.
[6]美前高官承认美介入“占中”,巨资“助推民主”[EB/OL].环球网,http: //mil.huanqiu.com/observation /2016-10 /9598456.html.2016-10-25.
[7]王晨.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网络舆论与社会稳定[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1):45-48.
[8]陈力丹,安微.微博的作用和我们的责任[N].学习时报,2012-01-02(006).
[9]丁俊杰.简论弥尔顿的出版自由思想[J].现代传播,2002,(05):09-13.
[10]胡杰.论官员的容忍义务[J].法学,2015,(08):146-152.
[11](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
(责任编辑:高 静)
Abstract:The narrow sens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security should include the freedom of public opinion on the Internet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 itself and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s not a threa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social stability and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others.A state of public opinion on the Internet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state power,and has special value function in restricting the abuse of public power and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The current domestic network public security is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On the one hand,the local governm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stubborn stability of suppressing or poor guidance,on the other hand,the public network opinion and network public opinion disregard other acts of violence to return to the rational,and overseas through the network of public opinion have an ulterior motive to mess my people also highlights the contradictions.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ecurity of public opinion on the network, to promote the legislation,the cred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opinion of the rational return of public opinion and other ways to do,in addition to pay attention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external force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Key words:security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legitimacy;constitutional rights;credibility;public opinion reason
The Dilemma and Improvement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Security Protection in China
Wang Jingtao,Mao Xinjuan
D035
A
1007-8207(2017)09-0001-10
2017-06-02
汪景涛 (1990—),男,河南商丘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安学、国内安全保卫学;毛欣娟 (1964—),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