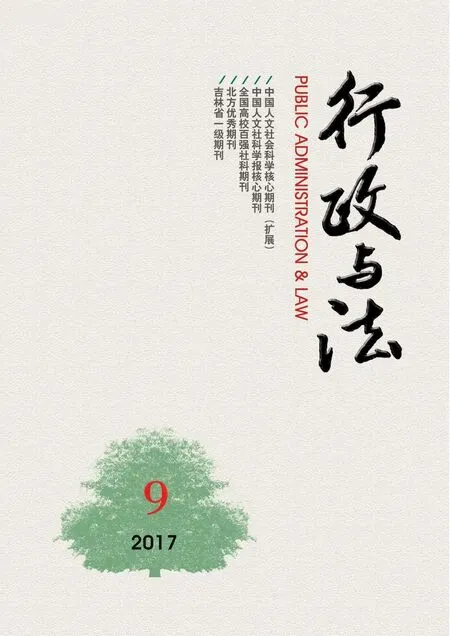“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法保障
□ 于忠龙
(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广东 韶关 512026)
“互联网+”发展的经济法保障
□ 于忠龙
(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广东 韶关 512026)
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多元协同社会化生产方式的推动下,传统的集中化、被组织化的社会样态将逐步被分布化、 “互组织化”的社会样态所替代。与此相适应,法的运行模式也必将发生相应改变,即以传统公私法为核心的 “平面型”部门法结构体系逐渐向以传统公私法为基础,以经济法、社会法为主导的 “立体型”部门法结构体系演进。经济法作为 “促进发展之法”,是保障 “互联网+”发展的主导法,其作用机理将由传统的市场和政府二元调节机制演化为三元论下的协同互动机制,即逐步形成 “市场决定、政府引导、社会自治”相互弥补、协同互动的保障机制。
互联网+;经济法;互组织化;增量利益关系;三元协同
一、“互联网+”推动社会“互组织化”
当前,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以互联网技术领衔的信息革命与先进制造业技术相结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和迅猛发展,信息化、网络化已成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1]以《国务院关于“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等文件出台为标志,“互联网+”必将深度融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催生出各类经济新业态,产生经济发展新动能,助力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同时,“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时代的核心生产力,必将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水平,并在全球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冲击传统时空观和交往思维方式,变革政府治理模式和法治运行方式。笔者认为,社会“互组织化”必将成为以“互联网+”为生产力核心的信息时代最重要的变革之一。
人类社会系统的自发有序运行是互动作用的结果,这种互动作用的过程可称之为互组织化。[2]社会“互组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演进的结果。农耕时代适合封闭、分散化的个体小生产方式,工业时代适合以机器大工业为核心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信息时代则适合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多元协同的社会化生产方式。工业时代社会的结构样态为宝塔型结构,它与强调以分级、集中、控制为特征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社会化生产方式相适应。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多元协同的社会化生产方式要求社会结构向无级交换、分布控制、扁平结构演进。传统上的集中化、被组织化的社会样态将逐步被分布化、互组织化的社会样态所替代。近年来,随着社会“互组织化”的内生动力——互联网技术、产业、应用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跨界融合等方面的积极拓展,我国已具备加快推动“互联网+”发展的坚实基础以及社会“互组织化”的基本条件。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50.3%,网民规模已达6.88亿;无线网络覆盖明显提升,Wi-Fi使用率达到91.8%,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比重提升至90.1%。信息时代社会“互组织化”的到来使得在工业时代“驾轻就熟”的传统发展理论愈发显得滞后,且正在被“互联网+”所引发的新一轮理论创新超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哲学基础上的超越。作为促发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的二元论哲学,愈发显得与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格格不入。如反映在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之争——自由还是干预、分散还是集中、市场还是政府、竞争还是合作等两种思想体系的长期拉锯状态,已经无法适应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多元协同的社会化生产方式。在社会“互组织化”条件下,市场、政府、社会将形成协调共生、三维互动的新型结构,与之相适应的哲学基础也将由传统上的二元论哲学转换为“三元论”或“多元论”哲学。二是价值本位上的超越。工业革命以来发生在经济、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各类危机充分证明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局限性。经济自由主义曾给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带来了深刻影响,但其信奉的价值观核心——经济个人主义已经无法与信息时代接轨。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亚当·斯密所论证的 “人的利己天性是社会财富的根源”已经不适用于信息时代的财富创造,而由“互联网+”引发的新经济浪潮证明,经济个人主义的天然缺陷根本形成不了网络生产力,经济个人主义必然被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超越。三是追求目标的超越。“企业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观点一直是传统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利润最大化原则只在短期内对企业有利,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市场开拓,即使在短期内对企业有利,也可能因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毁掉其收益能力并导致企业走向失败。信息时代,在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的引领下,企业信息将越来越透明化,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如利用信息不对称攫取超额利润)将会使操作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企业的目标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盈利将不再是企业行为的动因而是结果,动因是“互联网+”模式下的创新、营销、顾客效用和质量等体现企业价值(市值)的最大化,其会被企业放置在计算利润之前。也就是说,传统上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目标将被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目标所超越。
二、社会“互组织化”过程中的法律体系演进
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在属于生产力范畴的“互联网+”与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社会“互组织化”的共同作用下,法的运行模式必将发生相应改变甚至变革。以传统公私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为核心的“平面型”部门法体系结构将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向以传统公私法为基础,以经济法、社会法为主导的“立体型”部门法体系结构演进。笔者认为,在我国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和国家大数据战略背景下,经济法、社会法等新兴法律部门是保障“互联网+”发展的主导法,而民商法、行政法、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主要起基础保障作用,属于基础法。其法理论证如下:
根据马克思主义法学对法所作的科学揭示,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受生产方式演进这一客观规律支配的。若从生产方式演进的角度考察,法的产生、发展大体经历了建立在个体小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传统公私法和建立在社会化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新兴部门法或现代法两个阶段。由于二者是对不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法律回应,因此,在价值、功能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一系列显著差异。
(一)生成基础上的差异
传统公私法起源于个体小生产方式,个体小生产方式在促成原始群体化生产方式瓦解的同时,亦萌发出新的社会关系,如财产的归属、流转、继承关系等,传统私法的生成即是对平等主体之间新生社会关系的部门法的回应;传统公法是 “为了不使社会和相互对立的阶级在残酷的斗争中同归于尽,……由此产生了由特殊公共权力强制确立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的必要。”[3]即传统公法是缓和社会权利矛盾冲突的产物。经济法等现代法则是为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需求而产生的新兴部门法。无论是从经济扶植法开始的德日经济法,还是从市场秩序法开始的美国经济法,亦或是从经济管理法开始的前苏联和我国经济法,无不是建立在社会化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社会化生产方式催生出新的社会关系,即剩余(增量)的共同创造、实现和分享关系(增量利益关系),经济法就是调整这一新的社会关系的部门法——经济法是调整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增量(剩余)利益关系的法。[4]
(二)保护法益上的差异
传统公私法缘于对生存利益或存量利益的维护。个体小生产的不发达决定了法对人们生存利益保护的优先性,所以,传统私法一开始就把人们对物的先占权加以确认,并作为所有权的发生根据。而政府为实现其政治统治职能,需要通过税收等方式强制向社会征收必要的费用,即从社会主体那里取走一部分既有利益(存量利益)。传统公法就是防范社会主体的既有利益被非法剥夺的法律形式。经济法等现代法缘于对增量利益或发展利益的维护。增量利益的物化形态表现为剩余产品,即由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产品,其价值形态表现为利润、红利等各种形式的剩余价值。当生产进入社会化以后,市场经济逐渐取代了自然经济,协作生产条件下必然会发生对剩余产品的分享问题,加之商品生产的目的已经变成以营利为目的,生产经营的逐利性又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竞争,以至于产品过剩的危机频频显现。商品卖不出去,其价值就实现不了,人们就要求保护自己生产的剩余产品的利益,即增量利益。另外,由于生产与消费需借助市场竞争完成价值循环,而商品价值实现环节的开放性又使得不正当竞争、限制竞争、垄断等争夺增量利益的非理性竞争行为成为商品价值实现的障碍。上述对增量利益的争夺沿着企业内部、企业间、地区间、国家间这一发展脉络不断拓展且层层凸显。在此种情况下,传统公私法只能在剩余产品的归属、流转等市场交易关系上发挥基础性作用。而解决剩余产品的分享与实现问题,只能在传统公私法调整的基础上,由发挥主导作用的经济法等现代法通过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宏观调控关系的方式解决。
(三)法权诉求上的差异
法权即法律规定的权利,在法治条件下,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必然要通过“法权”这一形式显现出来。而在不同生产方式及不同利益诉求下,社会主体的法权诉求亦不相同。传统公私法来自于保障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法权诉求。一方面,所有权是最基本的财产权利,对物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是人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传统私法法权之核心;另一方面,“权力是从原始权利对立中产生,并且在表现上凌驾于一切权利之上的力量,其根本使命是缓解权利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而且,权力的存在以权利冲突的不可调和为前提。”[5]因此,传统公权力亦源自社会个体(阶级)间不可调和的所有权冲突。经济法则源自保障剩余权为核心的法权诉求。剩余权是指“在社会化生产中对剩余应享有的权利”,[6]包括剩余分享权与剩余实现权。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个体的逐利性和生产的群体性之间的矛盾产生了剩余分享和实现问题,社会主体为了缓和在这一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产生了确立旨在维护其增量利益的剩余权诉求。其在实体法上主要表现为最初的资本主义工厂法以及后来的企业法、公司法、劳动法等现代法,而反映在法权上则表现为股权、剩余索取权或剩余分享权、劳动权等权利形式。上述法权及相应法律制度(如法国劳动法中的“雇员分享制”、丹麦公司法中的雇员配股规定、美国的“职工持股计划”等)克服了传统私法的局限,体现出现代法对传统私法“所有权绝对原则”的扬弃。同时,剩余权冲突也在企业外部(包括企业间、地区间和国家间)阻碍剩余价值实现的垄断、不正当竞争、贸易保护等非理性竞争中体现出来,这就要求政府既要从国内法上行使市场竞争规制权和宏观调控权,又要从国际法上主张发展权来保障社会主体的剩余实现权。
三、“互组织化”条件下经济法的三元协同互动保障机制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多元协同社会化生产方式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巨大动能。经济法作为“促进发展之法”,维护发展利益,推动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是其宗旨和重要使命。在“互联网+”推动社会“互组织化”快速发展的条件下,经济法的保障机制也将随之不断调整,其作用机理亦将由市场和政府的二元调节机制逐渐演化为三元论下的协同互动机制,即逐步形成“市场决定、政府引导、社会自治”的相互弥补、协同互动保障机制。经济法的三元协同互动保障机制天然具有与“互联网+”、社会“互组织化”相契合的作用机理,其主要表现为如下三元协同的“互组织化”架构。
(一)促进市场竞争,发挥市场决定作用
在法律意义上,发挥市场决定作用的基础环节在于市场竞争主体间竞争关系的法律调整,为市场竞争机制和社会自治调整 (软法规制)功能的发挥提供特定环境。市场竞争关系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竞争法的调整对象。竞争法是市场竞争领域的经济法,其宗旨是通过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维护市场正常秩序,解决商品进入流通领域的价值实现问题,即保障在生产领域创造出的增量利益通过市场竞争完成价值循环。在“互联网+”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对互联网产业发展和企业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企业间的竞争性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竞争法对市场竞争关系的调整首先要立足于我国当前“互联网+”的市场竞争生态,研究拟订有关竞争政策。笔者建议,对于当前互联网+”的市场竞争生态,可划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对于前者,根据相关经济学研究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互联网产业总体尚处于快速发展期,还未进入成熟期;二是互联网产业内企业间竞争性呈下降趋势,以2009年安卓系统和苹果手机进入我国市场所引发的智能手机普及为标志,相关企业间的竞争性出现逐年下降趋势;[7]三是现阶段寡头垄断竞争对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利大于弊。“综合我国互联网产业的结构、绩效、行为分析发现,互联网业中很多行业都属于寡头性垄断竞争,但其并未妨碍中国市场创新和提升用户满意度,相反,对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能力。”[8]“互联网+”市场的宏观竞争生态决定了竞争法的调整应继续维护宽松的市场竞争环境,充分发挥“促进型经济法”的功能,“促进型经济法是经济法规范的一种重要类型,它通过积极的和消极的、直接的和间接的、个别的和普遍的等多种类型的促进,来实现其促进发展的调整目标。”[9]对于后者,针对大量互联网领域的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频繁出现且纷繁多样的情况,应在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立法经验的同时,加快修订并完善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或者通过制定高位阶的专门性法律法规,明确互联网市场运行的基本架构,解决现有立法效力层级低、法律规定模糊、无力等问题。
(二)规范政府调制行为,发挥政府引导作用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的关键在于准确定位国家(政府)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的角色。根据前述对经济法生成、法权诉求的分析,社会化生产条件下产生的剩余权冲突已在企业内部、企业间、地区间、国家间层层凸显,这使得国家参与到增量利益的创造、实现和分享活动中具备了合法性。在“互联网+”条件下,国家通过依法行使市场规制权和宏观调控权,引导社会主体共同创造、有效实现、合理分享增量利益,缓解剩余权冲突,并以主权国家身份在国际法上主张发展权来保障社会主体的剩余权。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规范国家调制行为的法律部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调整企业内部增量利益的协作创造关系。社会化生产条件下企业内部形成了劳动者类型和利益分配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其中,劳动者尤其是技能型劳动者在与投资者、管理者博弈中处于相对弱势,经济法可以通过企业法或公司法等法律,创立新型权利形式,即通过劳动力产权的法权化维护劳动者对增量利益的分享权。[10]二是调整企业间增量利益的实现关系。主要表现为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关系需要通过国家行使市场规制权加以调整。通过促进型经济法规范加大扶持中小企业力度,以及保障弱势和低收入群体接触和使用互联网。三是调整区域间发展利益的分享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发展的实质公平不会自发形成,开放、平等、协作、分享互联网精神亦不会直接促成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不会自动消除区域竞争中剩余权或发展权冲突。政府只能依法行使宏观调控权,综合运用经济法上的财政支付转移、税收金融优惠等制度安排来弥补区域竞争的制度缺陷,或通过赋予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区域发展的法定权利(如区域发展权),为缓和区域间剩余权冲突提供实体权利支持。四是培育和推动有实力的企业、区域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由于我国“互联网+”总体上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互联网+”产业的国际市场份额还比较小,这就要求国家通过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等法律形式扶持和激励中国“互联网+”产业国际化。
(三)推动行业自律,发挥社会自治作用
以行业自律规范为代表的软法规制是发挥社会自治作用的重要方式。“软法是一个概括性词语,被用于指称许多法现象,这些法现象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作为一种事实上存在的有效约束人们实际行动的行为规则,它们的实施未必依赖于国家强制力的保障。”[11]软法是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多元协同的社会化生产推动下,社会结构逐渐由宝塔型的层级结构向扁平化的网状结构演变背景下出现的社会规范形式,是互联网思维和法治思维相互结合在社会治理上的重要表现。一般认为,在经济领域,法律规制模式应形成以硬法与软法相结合,实现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的混合法机制,已成为调整当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必由之路。[12]在软法规范的来源或载体上,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通过平等协商机制形成的行业自律规范已成为软法规则的主要表现形式。2002年以来,中国互联网协会相继颁布的 《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互联网终端安全服务自律公约》等一批行业自律性公约,对促进“互联网+”的快速、规范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通过行业自律的软法机制发挥社会自治作用,具有规制效率高、民主性和灵活性强、与互联网商业模式高度契合等优点,符合社会扁平化网状结构下多元治理理念要求。
[1]李慎明.“互联网+”的发展必将引发西方国家生产关系的大变革[J].红旗文稿,2016,(02):4-9.
[2]杨培芳.信息社会的哲学基础是互组织化[J].中国信息界,2011,(11):17-18.
[3]张文显.法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36.
[4][6]陈乃新.经济法理性论纲——以剩余价值法权化为中心[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85—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167-170.
[7]王燕,张奇,卫婧婧.组织密度对中国互联网产业演化的影响———基于组织生态学视角[J].现代管理科学,2016,(06):6-8.
[8]刘茂红.中国互联网产业组织实证研究[D].武汉大学,2011.1-2.
[9]张守文.论促进型经济法[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97-100.
[10]于忠龙.劳动力产权的法学探析[J].唯实,2009,(01):67-70.
[11]罗豪才.软法与公共治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
[12]吕中国,强昌文.经济领域的软法研究述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128-136.
(责任编辑:徐 虹)
Abstract:social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in multiple “Internet plus” as the core of the promotion,the traditional centralized and organized social state will gradually be distributed, “organized” social state replacement.Correspondingly,the method of operation mode will occur corresponding changes,namely traditional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like the core of “flat” department law structure system will gradually change to the traditional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which is based on economic law and social law for lead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department law structure system evolution.E-conomic law as “promoting development” security is the leading method of protecting “Internet+” development,the mechanism will be adjust by traditional market and government regulation mechanism and be evolution of synergistic interaction mechanism,and gradually form a safeguard mechanism of “market decision,government guidance,social autonomy” complement each other,cooper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Internet plus;economic law;organization;incremental benefits;three-element cooperation
On the Economic Law prot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Yu Zhonglong
D922.294
A
1007-8207(2017)09-0124-06
2017-06-05
于忠龙 (1977—),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共韶关市委党校政治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