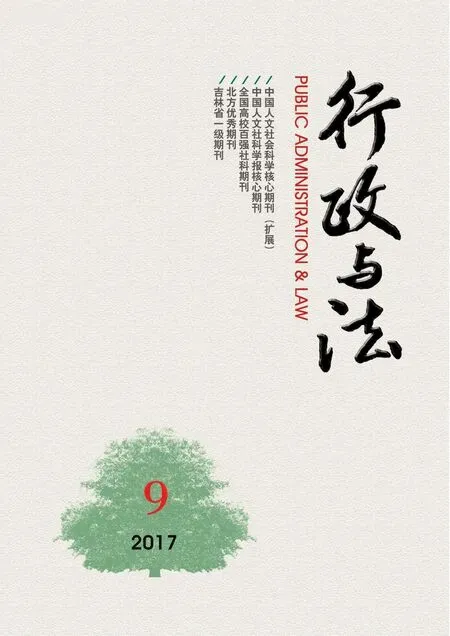共犯理论的中国命运
——从概念到工具
□ 陈文昊
(清华大学,北京 100062)
共犯理论的中国命运
——从概念到工具
□ 陈文昊
(清华大学,北京 100062)
共同犯罪理论在传统理论中是以概念为核心展开的,缺乏实益性的探讨。必要的共同犯罪等概念的设置,对于参与人的定罪量刑没有影响,更重要的是传统理论中的共同犯罪体系本身就是从界定“共同犯罪”概念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和展开的。从工具论的角度出发考察共同犯罪,共犯体系是一套规范的体系,强调 “眼见未必为实”,将结果归属于全部的参与者。在 “共同正犯模式”中,从犯罪共同说到行为共同说, “共同犯罪”的概念被弱化,因果力被强调;在 “正犯——共犯”模式中,从极端从属性说到最小从属性说, “共同犯罪”的概念框架被逐层突破,只要共犯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力,就可以将结果归属给行为人。
共犯理论;共犯体系;共同犯罪
可以说,共犯理论是刑法理论中的一座“绝望之山”。自德日刑法理论引入我国以来,与传统共犯理论相互博弈与对撞,使得共同犯罪理论愈加显得庞杂和繁琐。对比我国传统理论语境下的共犯理论和德日刑法理论中的共犯理论不难发现,两者的定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我国传统理论是在概念框架之下构建的共同犯罪理论,而德日刑法理论是将共同犯罪理论视为一套工具加以使用,两套理论系统在定位上的殊途决定了二者在制度构建上的发展脉络必定走向不同。本文考察了共犯理论从概念到工具的变迁与发展,并对该理论发展的未来趋势提出一管之见。
一、传统理论中的共犯理论构建
传统意义上的共同犯罪理论是以概念作为城墙构筑的天国。简单来说,在传统理论的框架之下,共犯的认定迟于各行为人性质的确立,这就使得共犯的认定不仅滞后,而且缺乏实益,沦为无用的概念。这样的例子在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中并不罕见,下面举例加以说明:
第一,任意的共同犯罪和必要的共同犯罪的划分。我国传统理论中区分了任意的共同犯罪和必要的共同犯罪,其中必要共同犯罪分为对向性共同犯罪、聚合性共同犯罪以及集团性共同犯罪。[1]正如有学者认为:“必要的共同犯罪,定罪与量刑都是由刑法分则明确规定的”。[2]这一点说明,即使不认定为共同犯罪,也不会对各行为人的定罪与量刑产生任何影响。如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根据这一规定,就可以明确地对参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活动的首要分子以及积极参加者追究责任,共同犯罪的认定对于定罪以及量刑而言毫无意义可言。同样的道理,在所谓的“对向性共同犯罪”当中,将 “两人以上的对向性参与行为为要件的必要共犯形态”界定为“对向性共同犯罪”,仅仅是一个概念层面上的问题,[3]也不存在实益可言。例如:甲向乙行贿,乙接受贿赂为甲谋取利益,即使没有共犯理论的存在,也可以当然地认定甲成立行贿罪,乙成立受贿罪,在对二人定性之后再确认二人构成必要的共同犯罪不具有必要性。难怪瑟曼·W·阿诺德教授会发出这样的质问:这些艰深的法学一般性概念到底是有用的法律工具,还是创造了混乱与细枝末节?
第二,传统理论区分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与事中通谋的共同犯罪,并且认为,对于事中通谋的共同犯罪,由于共同犯罪人是在着手实行犯罪后临时形成的,社会危害性相比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较小。[4]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司法实践中,事中通谋的共同犯罪不仅不可以作为法定从宽事由,而且不能作为酌定从宽事由。相反,在一些案件中,事中通谋恰恰能够表现出行为人暴躁、冲动的反社会人格。例如:在左建东等三人故意伤害中,饶某、左建东发生争执,二人厮打,与左建东同车的胡金鹏、李海英从轿车后备箱取出木棍,三人与饶某继续厮打,后饶某逃跑,胡金鹏所持木棍打断后从轿车后备箱拿出斧头,左建东持刀、李海英持木棍追打饶某至马路对面继续厮打,后饶某逃离现场,三被告人追赶未果返回现场。左建东用脚踹饶某的车门、胡金鹏持斧砸烂车灯,后三被告人驾车逃离现场。饶某被巡逻民警发现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法院认为,胡金鹏与左建东、李海英的意思联络表现为犯罪行为之间的相互配合,属事中通谋,构成共同犯罪,判处被告人左建东无期徒刑,判处被告人胡金鹏有期徒刑12年,判处被告人李海英有期徒刑10年。[5]本案恰恰表明,事中通谋的共同犯罪在很多情况下更多地征表了行为人消极的人格,并不能推导出社会危害性更小的结论。从这一点来说,区分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与事中通谋的共同犯罪只是概念层面的探讨,也不具有实际意义。
第三,传统理论中的共同犯罪体系本身就是从界定“共同犯罪”概念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和展开的。传统理论从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当中拆分出共同犯罪的三个要件:首先,主体上需要二人以上;其次,主观上具有共同故意;最后,客观上存在共同行为。[6]不难发现,传统理论对于共同犯罪要件的拆解完全是根据《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展开的,其出发点是对概念以及文义的解读,这样的处理就导致了传统理论框架中,过失行为不可以构成共同犯罪。但是,从语词表面“理解”而非“解释”文义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案件难以处理。例如:2009年2月9日晚,沙某与刘某、李某某在央视新台址工地燃放烟花,造成严重大火,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6亿元。[7]可以看到,在本案中,多个行为人的共同行为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并且无法查明最终结果由谁造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否认过失共同犯罪,就无法将损害结果归属于全部的行为人。显然,这样的处理结论并不妥当。因此,我国对于过失共同犯罪讨论的背后本质上是对于概念与实益孰为表里、孰为体用的问题。具体而言,传统理论是从《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表面含义出发,构造出共同犯罪成立的三个要件。但是,正如有学者认为的:“与文学作品的解读一样,对作为文本的法律规范的理解总存在着多种可能”,[8]如果没有解释方向与目的,就不可能对构成要件作解释。[9]因此,对于法条文义的理解恰恰不能单纯从文义出发,而是要考虑解释结果的实益与影响。事实上,如果从“肯定过失可能成立共同犯罪”这一先验的结论出发,完全可以对《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进行符合目的性的解释。例如将文本中的“故意”理解为行为的“有意”,就可以认为在共犯的成立条件中仅仅是将不具有行为特性的梦游动作或条件反射排除在共同犯罪的认定范围之外,如此就可以肯定过失共同犯罪的成立。[10]
由此可见,传统共同犯罪的理论框架重视概念的划分,忽视概念背后的实益;强调本文中的语词“理解”,缺乏基于目的性的“解释”意识;着眼于概念的铺陈,淡化实际问题的解决与运用。这就导致了我国传统共同犯罪理论成为了一套臃肿、庞杂的体系,犹如一座由概念而堆砌成的固化城堡,这也就造成教义理论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 “李斯特鸿沟”。因此笔者认为,应从机能的、理性的、工具论的角度对共同犯罪的本质进行解读,让刑法教义走下概念的神龛,以真正运用于实践。
二、共犯体系的客观存在
(一)共犯体系是一套规范的体系
刑法理性是贯穿于刑事立法、适用和执行整个过程并保障刑法合理性的根本原则。[11]英国法学家阿蒂亚曾明确地指出:“法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制定和实施法律的人可以通过它实现在其他方面确定的政策和目标”。[12]可以说,刑法体系中的每一套制度的构建都具有一定的目的理性作为支撑,体现某种程度上的工具价值,并且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而不应当仅仅是僵化的概念而已。那么,共同犯罪体系在整个刑法教义系统中应当如何进行定位呢?在德日刑法理论中存在“修正犯罪构成”的表述。具体而言是指刑法总则就未遂犯、共犯对基本构成要件进行修正而形成的构成要件。[13]在笔者看来,虽然“修正犯罪构成”这一概念是否具有引入我国刑法教义体系的必要性有待商榷,但该理论揭示了共犯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将原本犯罪构成要件上不齐备的情形承认为犯罪。换言之,共同犯罪理论在刑法教义体系中是一套不折不扣的“规范体系”。
刑法上的“规范”是一个与“存在”或者“事实”相对应的概念。对此,周光权教授认为,在客观主义内部如何处理事实和价值规范的关系,成了在何种程度上承认 “眼见未必为实”的问题。[14]雅各布斯教授也认为:“刑法的机能主要不是预防犯罪,而是证明实在法规范整体的有效性。”[15]由此可见,法律抽象世界中的现象与现实世界并非完全一致的弥合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法律为了发挥治理作用,赋予现实世界中的现象以新的法律意义,而此时的教义学制度就起到了工具的作用。在规范的视阈之下,最为典型的就是共同犯罪制度。例如Ⅰ:被关押的罪犯甲与乙共谋逃脱,并一起挖掘管道。后乙成功脱逃,甲尚未脱逃就被抓获。根据共同犯罪中“一人既遂,全部既遂”的原则,甲也成立脱逃罪的既遂。毫无疑问,如果仅从事实层面来看,甲并没有脱离控制,应当成立脱逃罪的未遂,但是正如有学者认为的,贯彻“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原则,确实与日常生活的概念有所出入,共同犯罪并非生活化的概念,而是特定的刑法概念。[16]因此,从规范意义上来看,可以将乙脱逃的结果归属于甲,甲成立脱逃罪的既遂。例如Ⅱ:甲与乙共同闯入被害人的家中实施抢劫,甲取得数额2万元的财物,乙取得数额10万元的财物。从事实角度来看,甲、乙分别抢劫了数额2万、10万元的财物,应当对各自的数额负责。问题在于,共同犯罪是一套规范的体系,一旦认定为共同犯罪,所有的行为人需要对全部数额12万元的财物承担责任。也就是说,甲在现实中取得了2万元的财物,但在法律的视野中被评价为取得了12万元的财物,这便是“眼见未必为实”。例如Ⅲ:共犯体系建立的基础正是在于将结果归属于原本没有实行行为的人。举例说明,一个为他人抢劫行为望风的人成立抢劫罪的帮助犯和一个为他人强奸行为望风的人成立强奸罪的帮助犯。从事实意义上来看,望风的行为本身并不存在任何差异,唯一不同的仅仅是正犯实施的行为以及构成的罪名而已。因此,将正犯成立的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归属于帮助犯,本身就是运用刑法教义进行规范评价的结果。
(二)共犯体系的目的在于结果归属
共犯体系是一套工具,它的目的在于结果归属,也就是让所有的参与者对结果承担责任。显然,这一工具论上的视阈转换具有重要意义。亦如上文所述,在概念引导下建立的共同犯罪体系先对各个行为人进行定性,而后再认定是否成立“共同犯罪”,但是,这样的进路显然在逻辑上是本末倒置的。因为既然已经对行为人作出了定性,共同犯罪的认定本身就不具有任何实益可言了。与之相反,以工具论为处罚点的共同犯罪体系是将共同犯罪的认定作为对参与人定罪量刑的跳板,通过共同犯罪的认定进行结果归属,这一点正是共同犯罪这一教义工具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这一性质的转变在犯罪共同说向行为共同说的过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部分犯罪共同说认为,如果可以认定犯罪之间存在交叉、重合关系,实施不同构成要件行为的行为人在轻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17]例如二人分别以杀人故意、伤害故意施加暴力,二人在故意伤害罪的范围之内成立共同犯罪;二人分别以强奸故意、强制猥亵故意实施暴力,二人在强制猥亵的范围之内成立共同犯罪。[18]因此,部分犯罪共同说强调的问题是在哪个罪名以内成立共同犯罪,但是,这一问题的讨论在本质上是不具有实益的,因为在哪个罪名以内成立共同犯罪这一问题并不影响各行为人的性质划定。与之不同,行为共同说的提倡者主张 “在各行为人为了自己的意图共同实施犯罪的场合,也可以成立共犯”。[19]张明楷教授也认为:“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应当淡化‘共同犯罪’的概念,判断哪些参与人的行为与正犯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只要具有因果关系,就可以肯定其为不法层面的共犯,对其进行归责”。[20]如甲、乙、丙三人分别以伤害故意、抢劫故意、强奸故意对被害人施以暴力,导致被害人死亡。对于这种情况,行为共同说认为,甲、乙、丙三人具有共同的行为,成立共同犯罪,一同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承担责任,结合三人的故意考虑,甲成立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乙成立强奸致人死亡,丙成立抢劫致人死亡。至于甲、乙、丙三人在哪一罪名之内成立共同犯罪,行为共同说并不关注。因此可以说,行为共同说注重解决结果的归属以及行为人的定性问题,而不是认定共同犯罪的概念问题。
由此可见,从犯罪共同说到行为共同说的理论转向,表明了以概念为核心的共同犯罪理论开始强调工具价值。在行为共同说的理论框架中,行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立共同犯罪不再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认定共同犯罪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将全部结果归属于所有的行为人。这一点也恰好体现了共同犯罪理论体系的发展趋势。
三、共犯体系的构建
以工具主义作为共同犯罪理论得以展开的基础,就是将结果归属作为共同犯罪体系的核心问题。在笔者看来,教义规则的讨论应当服务于实践问题的解决,因此,对共同犯罪问题的探讨也应当从实践经验的角度出发。正如劳东燕教授所言:“目的构成教义学体系是向外部开放的管道,经由这一管道,来自体系之外的政策需求方面的信息得以反馈至体系内部,并使得体系本身按目的指向调整自身的结构和功能”。[21]其实,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共同犯罪类型无非两类:一是二人以上构成共同正犯罪的情形,以下称为“共同正犯模式”;二是多人分别构成正犯、共犯的情形,以下称为 “正犯——共犯模式”。笔者将以工具论的视角对两种模式下的归责原理分别进行分析。
(一)共同正犯模式
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的情况,[22]在这种模式中最为显著的特征为所有的参与人都实施了相关行为。例如:2012年4月至6月间,被告人高军军伙同被告人高利珍、金艳、顾某、张某、蒋某,先后雇佣高强、孟某、张小龙、高某等人在北京市丰台区、朝阳区等地的宾馆发招嫖卡片,后在被害人嫖娼后进入其房间强行索要小费,并参与分赃。法院认为,被告人高军军、高利珍、金艳、顾某、张某均积极参与犯罪行为,系共同正犯。[23]再如:2012年12月17日凌晨,被告人李某明、杨某燕获悉被害人袁某芬夫妻伙同被告人欧某锋、蔡某兰等人将袁某芬、周某雄带至中山市公安局东区分局、小榄分局协商还款事宜未果。当日下午6时许,被告人李某明、杨某燕、欧某锋、蔡某兰将被害人袁某芬、周某雄带至欧某锋经营的德馨电子厂内协商,后又转移至李某明经营的恩泽灯饰厂内,以不准离开相要挟,催促、逼迫袁、周二人一次性解决欠款问题。法院认为,杨某燕、李某明、欧某锋在非法拘禁共同犯罪中各有分工,互相配合,所起作用相当,属共同正犯。[24]
正如上文所述,在“共同正犯”模式当中,各行为人的罪名确定并不需要依靠共同犯罪的认定加以解决。这是因为,即使单独考察案例中被告人的行为性质,行为人的行为也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各自成立抢劫罪;行为人的行为满足了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各自成立非法拘禁罪。既然不影响罪名的认定,那么共同犯罪的认定在“共同正犯”模式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笔者认为,最终还是要回到结果归责的意义上予以考量。因为当共同正犯中的一个参与人导致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或者当“被害人的死亡结果由谁导致”这一事实无法查明时,将死亡结果归属于全部的行为人,正是共同犯罪理论的工具论意义所在。从共同正犯理论的学说发展史来看,共同犯罪概念的弱化也是趋势所在。传统理论采用的是犯罪共同说,其中,完全犯罪共同说要求各行为人实施符合同一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而部分犯罪共同说要求各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构成要件同质。[25]对此,有学者认为,犯罪共同说是建立在“犯罪”这一概念基础之上的。[26]在我国,完全犯罪共同说是基于《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展开的,但在理解上不仅流于表面,而且僵化生硬。随着共同犯罪理论的工具化定位逐步深化,日本刑法理论中也逐渐出现了从客观主义立场出发论证行为共同说的主张。[27]在我国,行为共同说得到了张明楷教授的支持。与部分犯罪共同说不同的是,行为共同说并不强调共同犯罪的概念与要件本身,而是普遍承认只要存在共同的行为。正如上文所述,在行为共同说的框架之下,不需要回答“在什么犯罪之内成立共犯”,而是直接将全部的结果归属于全部的行为人,这是一种典型的工具思维。换言之,到行为共同说为止,概念的框架体系基本已经被打破,代之以共同行为的考察,即只要对结果发生具有因果力的行为人,都需要对结果承担责任。
(二)正犯——共犯模式
正犯——共犯模式在传统理论中被称为“复杂的共同犯罪”,即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一定分工的共同犯罪模式。[28]这类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如2012年5月,被告人高佩在西京大学商业街经营化妆品店期间,为了能够续租房东张某乙的门面房,向其谎称能买来所经营化妆品公司的“低价返利车”,康卫锋系高佩之男友,与高佩共同经营化妆品店,明知其化妆品店不存在返利车低价出售一事,仍在高佩的指使下冒充化妆品公司的负责人“胡总”与客户对接,以有低价车销售为名骗取中间介绍人朱某某、袁某收取的购车人购车款。法院认为,被告人康卫锋构成高佩诈骗犯罪的帮助犯。[29]2013年6月,被告人陈建全向被告人张桃华、吴瑞祥传授抢劫搭客摩托车司机的方法,并向张桃华提供辣椒喷雾剂一支。同年6月26日21时许,张桃华、吴瑞祥在与陈建全商议后,张桃华、吴瑞祥搭乘被害人谭某驾驶的搭客摩托车至本市牛奶厂附近,张桃华向被害人谭某脸部喷辣椒水,并和吴瑞祥一起对被害人谭某拳打脚踢,抢得一辆五羊牌两轮男装125CC摩托车 (价值人民币4244元),后由陈建全销赃,得人民币650元。法院认为,陈建全属于教唆犯,对本宗抢劫负相应的罪责。[30]
在正犯——共犯模式中,正犯对其造成的全部结果承担责任,关键是对于并没有实施行为的共犯如何处理。对此,存在不同观点:极端从属性说是最早的共犯从属性说的形态。该说认为,共犯得以成立的前提在于,正犯行为必须符合整套的犯罪构成。[31]根据极端从属性说,行为人唆使精神病人实施犯罪的,不成立教唆犯。但是,考虑到这种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极端从属性说的主张者提出了 “间接正犯”这一概念,对以上出现的处罚漏洞进行补充。不难发现,在极端从属性说的框架之下,教义学体系将原本无法通过“教唆犯”进行处罚的情形擢升为“间接正犯”的处理方式,无疑是跳脱了共犯的体系框架,另起炉灶,通过正犯理论进行打击。在这之后,极端从属性说开始向限制从属性说转向。该学说主张,共犯的成立以正犯符合不法性为前提,而不以正犯成立犯罪为前提。[32]限制从属性说将 “不法”这一概念与构成犯罪相区分,在不法层面肯定行为人的合致性,却分别探讨行为人的责任。对此,日本学者西田典之举了这样的例子:“A、B基于共谋侵入X家中盗得100万日元并分赃,A的动机是吃喝玩乐需要钱,而B则是因为母亲住院急需花钱,因此A的责任非难程度要高于B”。[33]不难发现,从极端从属性说到限制从属性说,“共同犯罪”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被缩减到了不法层面。再进一步,由于限制从属性说在参与自杀等问题上存在疑问,因而最小从属性说逐渐登上了刑法的历史舞台。该学说主张,共犯的成立需要正犯满足特定犯罪的构成要件。[34]如甲教唆乙去盗窃丙的手机,而恰好丙是打算将手机赠送给乙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最小从属性说,只要实行者乙符合了构成要件,教唆犯甲仍然可能成立犯罪。最小从属性说在当今的刑法理论中逐步成为有力学说,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在最小从属性说的框架之下,“共同犯罪”的内涵已经被压缩至构成要件层面。
从“极端从属性说”到“限制从属性说”,再到“最小从属性说”,正犯始终是共犯与结果归责之间的一道屏障,共犯的成立条件中必须要考虑正犯的因素,也就是“共同犯罪”这一概念的讨论是区分共犯体系中不得逾越的藩篱。但不难发现,从发展趋势来说,“共同犯罪”这一概念对于归责的影响却是逐渐减弱的。在“极端从属性说”当中,正犯必须要同时符合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在“限制从属性说”中,共犯的构成以正犯符合该当性与违法性为前提;而到了“最小从属性说”,只要正犯符合该当性,共犯就存在成立的空间。毫无疑问,在整个过程中,被弱化的是“共同犯罪”的概念与框架,被放大的是共犯与结果之间直接的因果链条。正如有学者所言:“一旦采用最小从属性说,就很难想象共犯何时不成立,因而共犯从属性可谓名存实亡,根本即丧失从属之意义。这样一来,将使得共犯摇身一变成为正犯”。[35]这导致在大部分案件中,无论是采用最小从属性说还是单一正犯体系,处理结论并不存在过大差异,甚至有学者直接主张将单一正犯体系引入我国刑法理论当中。[36]这一理论转向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在“正犯——共犯模式”中,对于“共同犯罪”这一概念的框定逐渐弱化,工具化的理念与解决问题的意识逐渐凸显出来。根据最小从属性说或者单一正犯体系,只要共犯对结果发生施加了因果力,就可以将结果归责于共犯,这样的处理方式更加立足于司法实践中问题的处理。
总之,在现行刑法理论中,对概念的执着固化是导致刑法治理难以维系的重要原因之一。[37]正如有学者认为,有人将三角诈骗排除于诈骗之外的原因就在于,当人们熟悉了二者间的诈骗时,便习惯于认为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只包含了二者间的诈骗。为什么人们认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不应包含公开盗窃的情形?因为,当人们熟悉了秘密盗窃之后,便习惯于将盗窃等同于秘密盗窃。[38]因此,从概念的角度解读刑法文本对于司法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并无益处。笔者提倡将刑法教义体系视为一套社会治理工具,发挥其问题处理的机能。正如在共同犯罪的问题上,应当将其定位为规范的归责体系,而不是不具实益概念的堆砌,这一点在我国近年来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转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只有如此,才能填补教义学与司法实践之间出现的“李斯特鸿沟”,也才能距离正义更进一步。
[1][4][28]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六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67,168,169.
[2]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第四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4.
[3]钱叶六.对向犯若干问题研究[J].法商研究,2011,(06):124.
[5](2016)宁刑终76号.
[6]刘宪权.刑法学名师讲演录 (总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70-272.
[7]李翔.刑事疑难案件探究 (第二版)[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35.
[8](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缔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M].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92.
[9]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J].中国法学,2010,(04):49.
[10][20][22] 张明楷.刑法学 (第五版)[M].法律出版社,2016.400,386,395.
[11]张智辉.论刑法理性[J].中国法学,2005,(01):172.
[12]P.S.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M].范悦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25-127.
[13]马荣春,朱凤翔.解读修正的犯罪构成[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91):77.
[14]周光权.价值判断与中国刑法学知识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04):126.
[15](德)京特·雅各布斯.刑法保护什么:法益还是规范适用?[J].王世洲译.比较法研究[M].2004,(01):97.
[16]闫利国,徐光华.犯罪既遂与亲手犯的共同正犯研究[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2):46.
[17]周光权.刑法总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09.
[18]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41.
[19][34]前田雅英.刑法総鍝講義(第四版)[M].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412,424.
[21]劳东燕.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J].中外法学,2014,(01):91.
[23](2014)二中刑终字第257号.
[24](2013)中中法刑一终字第235号.
[25]瀧川幸辰.犯罪鍝序説(改銌版)[M].有斐閣,1947.226.
[26]団藤重光.刑法綱要総鍝(第3版)[M].创文社,1990.389.
[27]野村稔.刑法总论[M].全理其,何力译.法律出版社,2001.388.
[29](2016)陕刑终263号.
[30](2014)珠中法刑一终字第26号.
[31]斉藤金作.刑法総鍝(改銌版)[M].有斐閣,1955.244;瀧川幸辰.犯罪鍝序説(改銌版)[M].有斐閣,1947.205.
[32]刑法綱要総鍝(第3版)[M].创文社,1990.384;植松正.刑法概鍝 再銌1(総鍝)[M].勁草書房,1974.375.
[33](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M].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366.
[35]柯耀程.刑法总论释义[M].元照出版公司,2006.595.
[36]江溯.关于单一正犯体系的若干辩驳[J].当代法学,2011,(05):81.
[37]陈文昊.工具化的刑法诠释[A].刑事法评论(第38卷)[C].4.
[38]姚建龙.刑法思潮与理论进展[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90.
(责任编辑:王秀艳)
Abstract:Classical theory of complicity is centered with concept,which lacks the discuss of real benefits.The concept of necessary complicity has no influence to the conviction and penalty to the participant.Moreover,Classical theory of complicity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omplicity.To consider the system of complicity from the angle of tool,complicity is a system of norm,which expresses 'seeing is not believing',and belongs the result to all participants.In the mode of 'coprinciple',from the theory of criminal commonness to the theory of act commonness,the concept of complicity is avian zed and the causation is expressed.In the mode of 'principle and complicity',from the theory of extreme attribute to the theory of minimum attribute,the frame of complicity is avianized.As long as there is causation to the result,the resul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participant.
Key words:accomplice theory;accomplice system;joint crime
The Fate of Theory of Complicity in China:From Concept to Tool
Chen Wenhao
D924.1
A
1007-8207(2017)09-0102-07
2017-03-22
陈文昊 (1992—),男,江苏镇江人,清华大学法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法学院2015级刑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