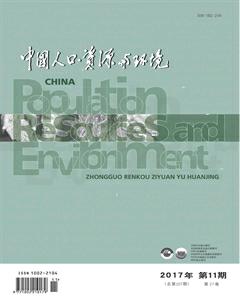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
徐鸿翔 张文彬
摘要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以《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为指导,空间上划分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范围并对其进行旨在生态补偿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现阶段对转移支付的生态保护效应研究大多集中于政策解读和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相对不足,该制度2009年实施以来已有七八年时间,具备了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文章以陕西省33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研究样本,在按各县级政府财政收入高低进行分组之后,实证分析了整体样本、高财政收入样本和低财政收入样本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促进效应。整体回归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影响系数显著为正,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的生态环境质量自2009年以来,呈现“基本稳定,逐渐好转”的趋势,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激励作用密不可分,同时,财政收入水平对生态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且财政收入水平越高,转移支付对生态效益产出的促进作用越大。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财政收入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影响系数要大于低财政收入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影响系数,这表明将转移支付拨付给高财政收入组更有效率。因此从效率角度看,现阶段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标准即县级政府财政收支缺口符合公平原则,但相对缺乏效率,以财政收支缺口为补偿标准的方式不利于转移支付效率提升,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最后文章基于兼顾效率与公平视角提出了充分发挥转移支付生态保护激励效应,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生态保护;陕西省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11-0141-08 DOI:10.12062/cpre.20170618
20世纪后半叶,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环境经济学、生态伦理学、资源承载力、自然权利论等思想深入人心。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国学者开始对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问题进行全面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巴西、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大量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补偿活动,而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也成为世界各国为保护生态环境达成的共识。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将生态补偿方式分为政府和市场两种。其中,政府补偿包括转移支付、政策优惠等;市场补偿包括:环境服务投资基金、流域付费机制、私人交易、生态标志等。在市场机制相对健全的发达国家,倾向于通过市场机制进行生态补偿,国外生态补偿关注的热点是地主与农户私人之间的生态补偿(PES)问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选择政府补偿的方式,尤其是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进行生态补偿。Mathevet等[1]和Folke等[2]认为生态转移支付是一种有效管理保护区的保护与发展的财政再分配方式,它可以提供直接的激励效应。但是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异,国外关于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巴西、德国和葡萄牙等国的生态补偿政策、法规的分析以及效果的实证检验方面。
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同样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我国政府开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受我国国情约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以《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为指导,空间上划分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范围并对其进行旨在生态补偿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现阶段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生态保护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解读[3-5]、转移支付方式改进[6-7]和激励机制效应理论分析[8-9]方面。研究一般着重于个案研究,属于实践经验总结与归纳时期,缺乏实证研究,李国平等[10-12]对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进行了初步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前者对后者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效应有待进一步提高。从2009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确定以来已有六、七年的时间,已具备开展转移支付生态保护效应实证研究的基本条件,这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经典的案例。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
1 模型设定和数据分析
1.1 假說的提出和模型设定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确定标准以财政收支缺口,其具有保护生态环境和改善民生双重目标,并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主。作者所在课题组对柞水、镇安等县进行调研时,政府人员提供的转移支付使用情况表明,改善民生的转移支付主要用于生态保护工作人员的工资、设备购买等方面,转移支付在直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也通过改善民生间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因此本文认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重要因素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提高具有促进效应,获得的转移支付越高,县级政府越愿意保护生态环境,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越高。
Olson[13]通过两人博弈认为,高收入者比低收入者更愿意提供公共物品,Derissen和Quaas[14]同样认为随着生态环境产品稀缺性和消费者收入水平的增加,居民对生态环境产品的风险属性可能由风险中性变为风险规避,增加对生态环境产品的需求并自觉保护生态环境,本文认为这同样适用于不同财政收入水平的县级政府,可以按照各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分类分析生态转移支付的生态环境保护效应,并提出另一个命题:
命题2:财政收入水平是影响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重要因素,高财政收入水平的县级政府更愿意保护生态环境,生态环境质量指数高于低财政收入县级政府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在实际测算中,每年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实际是前一年的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因此,在模型设定中当期的生态环境质量和滞后一期的影响因素相对应。根据假说1和假设2,本文的回归模型为:endprint
lnEIit=C+θ1lnTRit-1+
θ2lnGRit-1+
θ3lnEIit-1
+ωZit-1+εit
式中,EIit表示t年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i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其测度方法详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的规定。TRit-1表示t-1年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i获得的转移支付,GRit-1表示i县t-1年的财政收入水平;财政收入高的县级政府与财政收入低的县级政府相比,对生态环境产品的偏好越强,越愿意提供生态环境保护努力,获得更多的生态环境效益;EIit-1表示i县t-1年的生态环境质量,用于测算生态资源质量对生态效益产出的影响,生态环境质量是由前一期的生态环境保护努力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状态决定的,这也间接表明前期的生态环境保护努力水平对后期的生态环境质量也产生影响,因此为保证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县级政府必须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期性。Zit-1表示i县t-1年其他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控制变量;C为常数项;εit为误差项。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和转移支付数据TR来源于作者所在课题组“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12&ZD072)”对陕西省环保厅、财政厅的调研数据,财政收入数据来源于历年的《陕西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各地区人均GDP(lnperGDPit-1)及人均GDP的二次方(
(lnperGDPit-1)2),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特别是前者影响后者的结论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证实,一般情况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经济增长会以污染环境为代价,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增加,经济增长反过来还会促进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因此本文认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的生态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产业结构(lnISit-1),采用各县域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示,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意味着带来了更多的工业污染和废弃物的排放,不利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中降低环境污染的目标;城乡收入差距(lnINCit-1),采用各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表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村居民不平等的心理加剧,导致其可能会利用自身的便利,通过破坏和污染当地的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获得收入,这会间接带来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居民消费水平(lnCONSit-1),采用各县级政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消费水平的提高一般情况下会带来更多的生产和生活垃圾,同样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并增加环境污染排放;县域耕地面积(lnCULit-1),采用各县年末常用耕地面积表示,土地是生态环境的载体,耕地增加会导致更多的森林草地被破坏,不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
与互变量设置相同,控制变量也采用滞后一期的形式表示,同时,
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和收敛,各样本数据均采用自然对数形式表示。控制变量相关数据来源于《陕西统计年鉴》(2009—2015)《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09—2015)《中国区域统计年鉴》(2009—2015)。
1.2 数据统计性描述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于2008年实施,并于2009年测算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实证研究数据的时间跨度定为2008—2015年,EI指数选取2009—2015年数据,而其他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选取滞后一期也即2008—2014年的数据。根据本文的研究设计,将陕西省完整获得转移支付的33个县按照财政收入水平进行分组,借鉴陈诗一[15]按照能源消费量、碳排放量等要素分为高低两类的思路和方法,本文依据各县级政府2008—2014年人均财政收入的均值进行分类,前16个县级政府为高财政收入县级政府,而后17个县级政府为低财政收入县级政府,分组状况如表1所示。
陕西省33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级政府财政收入水平整体及分组(高财政收入组和低财政收入组)相关数据的统计性描述如表2所示。
2 实证结果分析
2.1 整体数据分析
对陕西省33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整体样本数据进行GMM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可以看到,转移支付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检验,尽管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该系数逐渐变小,但系数仍在0.1以上,这表明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质
量的改善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呈现“基本稳定,逐渐好转”的趋势,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激励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命题1得证。滞后一期的生态环境质量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一方面表明设定的动态回归方程是符合现实的,能够更好的拟合现实状况,另一方面也表明基期的生态环境质量对后期的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确定还应考虑长期性,将前期的生态环境质量也纳入考核范围,实施动态激励机制。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增加也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因素,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收入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县级政府财政收入水平的增加,县级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主体”必然会增加对“自身”的环境质量的重视,通过增加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支出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来说,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人均GDP的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其二次方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人均GDP的增长会阻碍生态环 境质量的提高,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级政府还未达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拐点。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样抑制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但城乡收入差距对生态环境质量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小。居民对零售商品消费量的增加对生态环境质量提高也产生了抑制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将更多的钱用于购买消费产品,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是因为消费品增加,产生的生产消耗、生产垃圾以及生活垃圾也相应增加,影响了生态环境质量。最后,耕地面积同样也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显著因素,耕地面积的增加会造成草地和山地的减少和动植物的破坏,因此,退耕还林还草仍然是改善生态环境的一项重要措施。endprint
2.2 分组回归分析
同样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分组数据进行回归检验,表4和表5给出了高财政收入组和低财政收入组样本的回归结果。
通过对比表4和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县级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主体”,其行为选择与个人相似,高财政收入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影响系数要大于低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中的数值为t统计值;限于篇幅,表中未汇报出截距项回归结果。
财政收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影响系数,即将转移支付拨付给高财政收入组更有效率,命题2得证。因此从效率角度看,现阶段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标准即县级政府财政收支缺口符合公平原则,但相对缺乏效率,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作用有待进一步挖掘。
对于控制变量来说,高财政收入组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人均GDP增长对生态环境质量具有促进效应,但人均GDP的二次方回归系数为负,这表明促进作用在到达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改变,变为阻碍,这与整体回归结果的经济增长水平与生态环境质量负相关的结论不同,实证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在于财政收入的差异。财政收入和经济水平高的县级政府更愿意、也有能力投入更多的环保资金,因此初期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呈现正相关关系,由于环保投入边际效应的递减而最终呈现倒U形关系。整体数据实证结果为负相关关系是因为整体数据的经济水平较低,为发展而牺牲了生态环境。这从不同分组的经济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均值可以看出。因此二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只是不同前提条件下的回归结果。低财政收入组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会阻碍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并且二者不存在“U”或者倒“U”形关系,本文认为这一区别同样是由财政收入水平决定的,财政收入水平高的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更加关注对生态环境的变化和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呈现“双赢”状态,而只有在对生态环境保护利用过度和开发强度不断增加时,才会促使二者的关系发生变化;而对于低财政收入组来说,其更加关注经济增长,希望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本地区的财政状况,但这一行为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有可能造成生态环境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降低了生态环境质量。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其影响方向和整体回归结果相似,同时这也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这里不再进行详细的阐述。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考察了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保护效应,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基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同样对当期的生态环境质量提高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成为必然选择。第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同样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显著因素,财政收入水平越高,县级政府越愿意保护生态环境,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越好,因此,应提高各个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生态保护的禁限政策使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级政府难以通过大规模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增加财政收入,而其他地区特别是优先开发和重点开发地区一直在无偿享受这些区域提供的生态环境产品,其理应为此支付补偿。第三,分组回归结果显示,高财政收入组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系数要大于低财政收入组,这表明将转移支付更多的倾向于高财政收入组会更好地发挥转移支付对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激励效应。但现阶段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对转移支付的拨付标准是县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这一标准符合公平原则,但不符合效率原则。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中央政府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和受益地区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建立区内与区外共同保护生态环境质量的格局。实证结果表明,转移支付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显著促进要素,因此应扩大对当地政府的转移支付。中央政府在拨付生态补偿纵向转移支付的同时,也有必要要求其他受益地区拨付横向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来提升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16]。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的资源禀赋现状和地理位置因素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的落后,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目标又进一步限制了经济增长,使其面临生态环境保护成本增加和机会成本损失的双重压力,中央政府和其他受益地区理应对此进行补偿,提供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也是应有之义。
第二,在不断提高转移支付的同时,也要对转移支付标准进行完善和修正。在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条件下,适度完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根据县级政府财政收支缺口确定转移支付的办法并不利于充分发挥其生态环境改善的激励效应。在转移支付标准方面,根据本文的实证结论,在现有依据财政收支缺口确定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的标准下,可以从以下四方面进行调整:一是充分考虑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财政收入水平越高,县级政府生态环境保护意愿越强,生态环境质量越好,因此在确定支付标准时应将财政收入水平纳入确定标准参考内容;二是将前期的生态环境质量纳入转移支付标准核算中,由实证结论可知前期的生态环境质量同样对当期的生态环境质量产生促进效应,因此在确定转移支付标准时,应将前期生态环境质量纳入考核范围,前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越高,转移支付应越高,以体现长效激励原则。三是可以考虑分批下拨转移支付资金,前期资金的使用效果同样是下一期资金拨付的参考,促使县级政府要获得相应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既要关注当期的生态环境效益,也要关注后期的生态环境效益,保证县级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的持久性,促进生态环境的永续发展。四是考虑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重要程度和影响范围,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测度中包含有特征指标,即根据不同功能区类型确定相应的指标,因此,转移支付的确立也应充分考虑功能区的特殊性和影响程度,如水源涵养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多数位于水源区和大江大河的源头,其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非常大,因此中央政府应对此提供更多的转移支付,而所有水源区的中下游也都應对此进行横向转移支付。endprint
第三,当地县级政府也可以从调整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方面入手,改善生态环境质量。首先要调整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与作为禁限开发区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建设目标存在冲突,本文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工业化的发展不利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因此,这些地区要对存在高污染的企业实施异地开发或者直接关停,转而充分发挥本地区丰富的生态资源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的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业,农村居民还可以依据地理位置的优势开办农家乐等副业[17]。其次,要增加农村居民收入,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增加了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心理,导致其为了提高收入,会基于自身的地理位置便利破坏生态资源和环境以增加收入,这造成了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因此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变其行为选择也是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一个重要举措。再次要继续推进和巩固退耕还林工程,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实施退耕还林的地区存在返耕现象,这在造成成本浪费的同时也不利于生态效益产出,2014年8月,国家多部委联合出台了《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总体方案》,正式下达退耕还林任务483万亩,标志着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正式启动,这要求地方政府做好退耕还林的宣传和指导工作,保证退耕还林工程的可持续性。
(编辑:王爱萍)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MATHEVET R, THOMPSON J, DELANO O, et al. La solidarité écologique: un nouveau concept pour une gestion intégrée des parcs nationaux et des territoires [J]. Natures sciences sociétés, 2010, 18(4):424-433.
[2]FOLKE C, SA J, ROCKSTROM J, et al. Reconnecting to the biosphere [J]. Ambio, 2011, 40(7): 719-738.
[3]李國平,李潇,汪海洲.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生态补偿效果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13, 35(5): 58-64. [LI Guoping, LI Xiao, WANG Haizhou.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effect of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transfer payment policy[J]. Modern economic science, 2013, 35(5): 58-64.]
[4]李国平,汪海洲,刘倩.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双重目标与绩效评价[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44(1):151-155. [LI Guoping, WANG Haizhou, LIU Qian. The dual objectives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ransfer payment in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J].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 44(1):151-155.]
[5]李国平, 张文彬. 最小安全标准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在我国的应用[J]. 管理学刊, 2016, 29(4):15-22. [LI Guoping, ZHANG Wenb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the minimum safety standard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6, 29(4):15-22.]
[6]何立环,刘海江,李宝林,等.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与应用实践[J]. 环境保护, 2014(12): 42-45. [HE Lihuan, LIU Haijiang, LI Baolin, et al.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countyleve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valuation index of the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protection areas[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4(12): 42-45.]
[7]伏润民,缪小林. 中国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重构——基于拓展的能值模型衡量的生态外溢价值[J]. 经济研究, 2015(3):47-61. [FU Runming, MIAO Xiaolin. A new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in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s in China: based on the spillover ecological value measured by the expansion energy analysi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5(3):47-61.]
[8]李国平, 张文彬, 李潇.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契约设计与分析[J]. 经济管理, 2014(8):31-41. [LI Guoping, ZHANG Wenbin, LI Xiao. Design and analysi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contract to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J]. Econom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4(8):31-41.]endprint
[9]张文彬, 李国平. 生态补偿契约设计及地方政府生态保护战略[J]. 经济管理, 2015(3):140-149. [ZHANG Wenbin, LI Guop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s contract design and local government ecological protection strategy[J]. Econom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5(3):140-149.]
[10]李国平, 刘倩, 张文彬.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与县域生态环境质量——基于陕西省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34(2):27-31. [LI Guoping, LIU Qian, ZHANG Wenbin. Transfer payment system in the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quality: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countryside data of Shaanxi Province[J].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14, 34(2):27-31.]
[11]张文彬, 李国平. 生态保护能力异质性、信号发送与生态补偿激励——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例[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5(3):19-27. [ZHANG Wenbin, LI Guop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capability heterogeneity, signal transmission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centive[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 15(3):19-27.]
[12]李國平, 杨雷, 刘生胜.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空间溢出效应研究[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10-19. [LI Guoping, YANG Lei, LIU Shengsheng. Study on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regional eco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the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area in China[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6(1):10-19.]
[13]OLSON M.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M]. New Haven, Connecticut: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DERISSEN S, QUAAS M F. Combining Performancebased and Actionbased payments to provide environmental goods under uncertainty[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3, 85: 77-84.
[15]陈诗一. 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研究, 2009(4): 41-55. [CHEN Shiyi. Energy consumption,CO2 emiss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ese industr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9 (4): 41-55.]
[16]刘炯. 生态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激励效应——基于东部六省46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J]. 财经研究, 2015, 41(2): 54-65.[LIU Jiong. On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ecological transfer payments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of local governments:evidence from 46 eastern prefecturelevel cities[J].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5, 41(2): 54-65.]
[17]庞庆明, 程恩富.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制度的特征与体系[J]. 管理学刊, 2016, 29(2):1-6. [PANG Qingming, CHENG Enfu. On the features and system of the ecological institu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6, 29(2):1-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