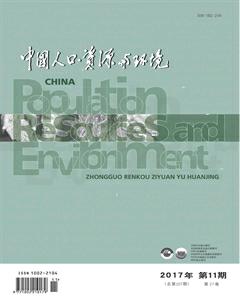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路径优化
张毓峰 胡雯
摘要
顺利推进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不仅事关林农脱贫致富,更关乎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及江河上游生态屏障构建。受独特的自然地理及人文历史条件制约,这些区域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面临两难困境,整体进程滞后。本文基于对四川省“三州”民族区域高山河谷集体林区制度改革实践的考察,尝试性构建了一个博弈视角的制度分析框架,从制度演进的内外约束两方面,对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改革的制度实施及不良激励因素予以理论阐释,并从中发现改善激励、提高制度运行效率的重点和路径。这一制度分析框架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强调“共时性关联”,即作为整体性制度系统中的不同制度安排,不可能孤立地被设计或改变,而是存在耦合关系,只有当关联制度互补共生、相互支持时,整体性制度安排才具有耐久性和生命力;二是强调“历时性关联”,即新制度须与既存制度产生耦合,成为博弈参与人的共同信念,才能最终演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三是强调“社会资本嵌入”,即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对于外部植入的正式制度变迁具有嵌入性影响。通过分析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改革三大目标取向的冲突与权衡、集体林权制度“植入”与民族社群习俗规范相互“解构”、利益驱动下的林农权益与社会排斥,认为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改革既不能简单进行制度移植,更不能搞“一刀切”,而是须充分尊重和善加保护利用少数民族社群长期存续并具效率的山林治理规范,支持社群传统“社会资本”适应性改造,均衡相关主体利益并实施一系列深化配套改革。
关键词 集体林权;制度分析;策略互动;共有信念;西部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 F06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11-0169-07DOI:10.12062/cpre.20170623
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之后,2008年国家林业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绝大多数地区已全部完成确权颁证的主体改革,并全面进入深化配套制度改革阶段。相较之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面临诸多特殊约束条件和困扰,林权制度改革整体较全国其他地区起步晚且改革进程整体滞后。“自上而下”的集体林权分权改革在西部民族地区特定的自然、人文条件下,制度执行是否朝向设计方向、达到預期效果并富有生命力、可持久?本文尝试性地建立了一个博弈视角的制度分析框架,从制度演进的内外约束两方面对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改革的制度实施及其不良激励因素予以理论阐释,并从中发现改善激励、提高制度运行效率的重点和路径。需要说明的是,西部民族地区涉及疆域极为广阔且林区自然地理条件千差万别,林权制度设计也会极不相同。本研究主要基于四川省阿坝州、凉山州和甘孜州“三州”民族区域高山河谷集体林区制度改革实践的理论思考。
1 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演进逻辑、理论回溯与分析框架
1.1 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演进
我国集体林的产权安排历经“分—合—分”的演进,有学者用公有化程度的“倒U型”变动来描述这一过程[1]。历次改革均有典型“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强制变迁意味,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对提高林业管理绩效及林农福利起到一定作用,但始终缺乏林农参与、很少或者没有考虑到农民意愿的满足[2]。部分区域采取惯有的行政主导“运动式”路径,改革目标的设计与实现出现较大偏差,制度绩效并不理想,甚而一度造成森林资源过度砍伐和退化。同时,因政策变动频繁导致林农不良预期和缺乏激励、林权权属不清导致利益侵犯也时有发生,严重制约林业经营效率和林业发展。
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仍是“被设计”的变革。虽有浙江省在2000年左右就基本完成了明晰产权的林权制度改革,但直到2008年中央才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3]。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分异巨大,“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极易陷入两难困境:其一,要顾及区域分异和因地制宜,制度设计就更趋向于框架化和原则化,基层政府的实施细则必然带有明显地方性目标偏向或折中,具体执行千差万别,从而导致中央——地方的政策目标偏离;其二,要顾及政策标准的可识别性和具体操作性,制度设计就须更加细化,但又可能导致改革“一刀切”遭遇地方适应性难题甚而因阻力过大难以推行。当前,改革中的问题已逐渐呈现,如市场导向下经济驱利所致的林木物种单一化及生态退化隐忧,分权到户导致的林地细碎化,“社会排斥”及林权集中于大户,制度“植入”对村庄传统生态文化的解构,制度“真空”或上、下位法规不一致所致的农民利益损失等。纯粹“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很难取得成功,必须要得到“自下而上”的回应,并通过有效的反馈机制对制度安排不断予以调适,使改革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接受度,改革才可能达成效率。
1.2 制度演进逻辑的理论回溯
集体林权改革是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涉及不同的“行动团体”或决策单位,这些不同“团体”根据各自目标偏好和利益最大化采取不同策略行动、互动博弈,以博弈参与人的身份参与到制度演进中[4-7]。最终,制度的选择及其变迁方向取决于各行动团体的成本——收益权衡,以及这些团体的相对市场与非市场权力影响[6-7]。制度具有双重性质:内生性即参与人博弈及信念均衡的内生演化和制度的形成;客观性即外生制度符号的存在如成文法、社会结构或组织等等。但参与人如果没有对外在的制度表现形式和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设计达成信念认同,它就不构成制度[5-8]。
具有典型“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能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并得以强化实 施、达到预期目标?这将取决于相关博弈参与人是否对这一外生制度予以认同并形成共有信念。因此,我们须阐释由博弈参与人共同参与、冲突、协同并最终形成和修正共有信念的过程,以理解制度演进和变迁的逻辑、动力,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怎样使“被设计”的产权制度成为参与人感知和认同的共有信念。
青木昌彦把作为参与人的各类团体或机构及其组织惯例作为制度安排不可分割的内生部分,并试图用精巧的博弈模型推演打开基于参与人互动博弈的制度演进“黑箱”[5]。他定义了六种基本类型的“域”:共用资源、交易(经济交换)、组织、社会交换、政体和一般性组织领域,每一个参与人都可能同时归于多个“域”,根据各“域”行动规则采取策略行动,从而可能引发制度的跨域演化。在此假定下,关联博弈得以强调,这里的关联博弈包含两层意义[5]:一是“共时性关联”,即作为整体性制度系统中的不同制度安排不可能孤立地被设计或改变,而是相互间存在“耦合”关系,只有当关联制度互补共生、相互支持时,整体性制度安排才具有耐久性和生命力;二是“历时性关联”,即新制度须与既存制度产生“耦合”,成为博弈参与人的共同信念,才能最终演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endprint
1.3 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演进逻辑
在上述博弈视角制度演进逻辑的理论框架下,尝试性地构建了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制度分析框架(如图1)。
首先,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以集体林地和林木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涵盖与林权制度关联的系列配套制度改革。这些制度安排间存在“共时性关联”,任何单一制度变革都须得到关联制度变革的支撑和补充,最终在新的均衡点形成一系列相关制度互补共生的集体林权治理整体性制度安排。但在西部民族地区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森林资源分布、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制度环境参数的既有林权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等外部条件制约,以及村落社群特征、资源权属传统、既有社区规范、森林生态文化等内部条件约束下,不同区域在集体林权治理领域业已形成差异性“共有信念”即“社会资本”,并必然“嵌入”集体林权改革进程,影响和制约博弈参与人的行为策略,进而影响制度演进方向和绩效。因此,集体林权改革又具有“历时性关联”,或多或少地打上“历史烙印”,“被设计”的制度变革不可能完全抛开既有制度而实施,反而须充分考虑新制度的社会接受度和地方适应性,否则,很可能偏离设计者的初衷。
其次,内生于这一制度体系的博弈参与人至少包含四种力量,即市场、政府、第三方组织,以及三方力量的多种形式协作团体。在中国特定的城乡二元结构与乡村治理现状下,村级党委及村委会也被视为基层政府在乡村的职能延伸部门和非正式代理人。第三方力量包括为林农、林业或森林生态资源提供援助的国际援助组织,以及其他相关第三方非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机构。
其三,不同层级的博弈参与人分属不同的博弈行动“域”,基于不同目标取向采取策略行动并互动博弈。一方面,既有林权制度安排在参与人的互动博弈中持续演化并自我强化实施,对“自上而下”的新集体林权制度产生社会资本“嵌入”影响;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及其林业职能部门是集体林权制度创新的发起人,“自上而下”的制度植入意味着对既定博弈规则的改变,相当于在既有博弈结构中新增一个拥有独特行动决策集合与偏好序的参与者[5],从而改变相关参与人的博弈参数和策略行为,可能动摇既定共有信念,解构或重构既有社会资本。
最终,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能否形成可持续的治理结构,并使改革的总体收益大于或至少等于改革总成本,成为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实践中的制度绩效主要体现于能否实现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生态优化目标,能否对相关利益主体产生正向激励,能否具有良好的社会接受度和地方适应性。效率、公平与生态任何一项目标的偏离都将成为决策者修正和调适制度设计的信息参考;多层级的集体林权改革相关博弈参与人分属不同“域”并受各域行为规范约束,改革需要多样性、多层次性的制度供给以适应不同环境、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主体的制度需求,以有效遏制不良激励、形成正向激励;能否具有地方适应性和社会接受度则关乎制度改革成败和可持续性。“地方性知识”和“使利益相关者参与改革其中”因此尤为重要,越具有地方适应性的制度越具有正向激励性,其社会接受度也会越高,两者相互强化,并对实现效率、公平与生态目标影响至深。
2 西部民族地区集體林权制度改革实践剖析
2.1 经济效率、社会公平与生态优化三种目标取向的叠加
集体林权改革目标多元,至少涵盖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生态优化,实践中不可避免地相互冲突、相互消减,常常面临多目标权衡或取舍难题。
一是效率与公平矛盾。集体林权分权以“均权”为基本原则,以实现“耕者有其林”。现行城乡二元结构下,集体林权改革最广泛的直接受益的农民在社会分层中整体弱势,尤其西部少数民族林区,远离市场和现代文明,部分民族聚居区仍保留刀耕火种的传统农业生活状态,与外界交流匮乏甚而语言不通,市场配置资源不太可能流向这类群体,大量资源实质为“僵化资产”难以进入市场实现增值。虽然有分散的农民携产出品进入市场交易,但市场弱势必然使其在市场增值收益分配链条中居于末端。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使改革带来的市场红利更多地被其他市场主体获取。
二是效率与生态矛盾。考虑到森林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整体性特征,集体林权不能无限分割,应维持一定规模效应,且林权主体关于林木种类、营林周期安排等决策行为将受到森林生态约束。但分散决策下驱利的短视行为或规模流转受让主体的成本——收益权衡,均瞄准商品林和兼用林尤其是速生丰产林,既弱化了森林资源生态多样性及其生态防护功能,更存在林地地力破坏和资源退化的隐忧;反过来,资源水平下降和生态环境退化最终必将导致市场主体收益回报的长期匮乏。地处于长江上游核心流域范围的四川,集体林近58%为公益林,约为商品林的1.4倍,尤其甘孜、阿坝、凉山少数民族聚居的“三州”地区,更覆盖大面积天保林和重点生态公益林。这些区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林木成材及森林涵养期限动辄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林木采伐和公益林流转方式严格受限,林农很难从以林木为原料的生产中获得收益,也难以参与到林权市场交易中获得资产增值收益。生态优化与集体林权市场效率实现的目标悖离和政策冲突下,“三州”虽已基本完成确权颁证工作,但林农运用林权获得财产增收的目标却未有明显体现。
三是公平与生态矛盾。理论上“谁受益谁付费”的“税负公平”原则,在实践中面临受益群体边界及其受益程度确定的难题。生态屏障功能定位决定西部民族地区不可能走常规工业化和城镇化路径,集体林确权分类划界时,大量集体林被划定为公益林。由此产生的生态效应被江河下游乃至整体生态环境共享,但林农却在运用林权获取收益上受到严格限制,且要求其为林区生态大量投入管护努力。林农所受经济利益损失,目前主要来自国家和省、市三级纵向生态补偿,如国家对重点公益林每亩每年补偿15元,四川省参照这一标准补偿省级集体公益林,部分市(州)制定了地方补偿政策。但国家和省级补偿标准较低,在林改后商品林价值持续升值的对比下,既不能有效激励落实管护责任,也无法满足林农致富脱贫需求;局部地方更存在把集体天然林划定为商品林从而出现政策“真空”,既无补偿又严禁采伐。同时,地方性补偿与地方经济实力正相关,却往往与生态责任负相关,如全国百强县成都双流,地方性公益林补偿标准达到300—400元/亩,而甘孜、阿坝州级财政则无力补偿。此外,由于我国尚无区域间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江河下游区域无偿享用了大量来自源头区域的生态产出。endprint
2.2 正式制度变革与社群治理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集体林权改革的强制性制度植入可能面临两种境况:
其一,制度外部植入下社群传统文化习俗的解构与调适。西部少数民族在长期与自然环境的生存斗争及适应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自然生态伦理文化及其自然资源配置与社群治理规则。其对大自然的敬畏感恩之心,以及以自然保护的伦理义务与社区共有产权为典型特征、由血缘、亲缘及地缘关系网络相互交织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模式,具有某种共通性,在保护自然森林资源、维系社群和谐关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实践中,越是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的林区,森林资源保护的完好性及物种多样性相对越好;而地方习俗的传统性和文化个性越突出,自成体系的社群治理结构相对封闭性和权威性越强。集体林权改革的强制性制度植入将外部世界具有趋同性的市场规则引入社区,可能导致社群传统习俗及治理结构“解构”的出现。“解构”本身是民族地区社群文化习俗因应外部环境和内部累积因素变化而作出的适应性调适与变迁,但当传统规则弱化、异化甚而退出,新的适应性社会资本尚未建立,社群成员便被迫处于适应性变迁的痛苦新生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失去有效规范约束,旧的利益均衡被打破并陷入某种混沌、彷徨状态,甚至引发资源掠夺、利益抢占等负面行为激励。“分权”改革强调私权的申张与保护,社群成员过去根深蒂固的资源共有共管等协作生产观念动摇甚而消解,市场空间范围的扩张及由此而来的森林资源相关产品市场价值提升则对此进一步强化,激励各种最大化林木、林下产品收益的行为发生。国家强制规则成为权利主体对抗社群传统的“利器”,传统生态伦理观遭受冲击,人们摒弃对森林的敬畏和禁忌,甚至开始在神山神林种植经济作物。差序格局下“共有共管”社群产权结构及其资源强制保护、有序使用和社区和谐,以及相邻社区间资源共用共管秩序面临挑战,因资源争夺而生的林权纠纷尤其相邻权冲突被激发和外显。与此同时,民族传统文化也可能流失或趋同,遭遇传承危机。正如有洞见的学者所述——建立“强硬”的政府可能会降低其他机构建设社会资本的能力[9]。
其二,“社会资本”嵌入下外部植入制度的解构与执行。集体林权改革介入基层社群并实际运行的进程中,既有社群规则及社会网络关系结构将“嵌入”其中,产生新的策略组合及合作性规范,使其在实践中被“解构”执行或产生偏差:一是“分地”到“均利”的政策变通。集体林权改革以家庭承包经营、集体成员平等享有为初始产权分配的主体方式,林地勘界基础上“分山到户”理应成为主体改革方式。事实上,四川“三州”林区主要采取“均股均利”为主、“均山到户”为辅的确权颁证主体改革,勘界和“四至”针对村组集体单元,致力于解决过去指山为界的边界模糊、相邻权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而集体内部则按成员人数“分股、分利”到户。二是“核、换、补”的修补实践。部分村寨仅对业已形成的社群林业管理体制予以局部调整和完善,并在此基础上核发林权证。“林业三定”时期的林权边界划分及自留山、责任山成为确权到户的重要依据之一,社群传统的神山、神林或其他社区公益林则权利到村民小组,“共有、共用、共管”,资源治理的村规民约仍然要求集体成员遵从。三是法律标签的“公开话本”与社群标签的“隐蔽话本”共存[10]。尤其在交通条件差并远离市场的林区,林地附著的经济价值不显著,许多林农对林权证的认知更多停留于“打官司时候有用”的本子而已,反而对权利边界是否清晰并不十分关注。令人担忧的是,当“自上而下”的改革演化为目标时间节点下的“运动式”改革,改革效果便大打折扣,“证—地”不符、“换本本”的改革大量存在,一旦集体林权需要大量入市,改革成果将难以经受实践考验。
2.3 利益驱动下林农权益与社会排斥
一是“林农理性”语境下的市场“觉醒”与矛盾激化。“70年不变”的制度安排在林地经济效益明显、林农对林地依赖性强的区域显现出“恒产恒心”效应,搅动了林地市场的活跃度,各种社会资本开始密切关注林地市场契机,伺机进入,政策性让利措施更刺激了经济林林权升值。受经济利益驱动,过去认为山林不值钱的林农开始表现出对山林的高度关注,传统的模糊边界下资源共用转向对有限林地资源的争夺和利益的“斤斤计较”,相邻产权等林权纠纷数量大增,过去的潜隐矛盾也逐渐显化。
二是“消极改革”语境下的“等、靠、要”与矛盾激化。林农为林权实现而努力的程度,取决于所能感知的市场机会和获利大小。两种情况下林农对分权改革的关注和参与热情不高:一是对林地的依赖程度低,二是认为林地并不值钱或林地经济价值确实不高。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越是偏远、生态敏感度越高的地方,越是远离市场,又受到保护性限伐或禁伐政策管制,林地的生态公益价值远大于经济价值。集体林分权改革在这些区域往往“下面不忙上面忙”,林农更多关心自家的林地属于哪种类型的生态公益林或天然保护林,以及应获得多少生态补偿,而对自己该如何参与林权改革以及林改后如何创新性经营利用林地以实现兴林致富缺乏积极性,甚至产生对国家政策性补贴、补偿“等、靠、要”的思想。而某些区域由于村民建房、薪材等木材所需得不到满足,“超伐”、“盗伐”或开采国有林资源等屡禁不止,地方政府则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或在权力范围内调剂指标、放松管制。
三是“势力不对等”语境下的“社会排斥”与矛盾激化。其一,主体改革制度设计中的“政策排斥”。改革隐含的“历史尊重”原则,意味着对早期林地流转和营林造林权利的认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四荒”拍卖热潮及开荒造林“谁造谁有”,大量集体外经济团体或个人以承包、租赁、拍卖、转让、股份制、反租倒包等多种形式参与到林业生产经营活动当中,掌握资本或权力的个人或经济主体、尤其外来非农资本介入及村级干部内部人控制的“干部林”等现象突出,“历史尊重”的改革将形成上一轮林地投资决定新一轮产权形成的内生逻辑关系,难以避免富人比穷人林地多的事实[11];此外,一旦林地大幅升值,如何维护早期流转土地的林农合法收益、平衡业主与林农间利益将颇为棘手。其二,有限市场交易中的“不对等市场势力排斥”。林农弱势集中表现为资本、信息及知识不对等。地方政府出于好心强势介入所致的林农“被流转”潜隐风险。山林招投标偏好大面积规模流转,并往往采取捆绑式集中流转,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元的投标抵押金及流转金,把绝大多数普通分散林农排斥在外,非农强势资本、林企“产业基地”大面积长时间占用集体林地或林业经营大户成为林地集中最主要的方式,流转受让方往往成为国家相关政策性让利的最大获利者,甚至出现流转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及权力寻租,进一步损害林农利益。endprint
3 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路径优化
任何改革均是相关主体的利益重构,各利益相关主体的策略性反应及其行动,必将映射到制度变革中并影响改革进程和方向。改革需要根据利益相关主体的策略性反应不断调适以实现相对利益均衡,以使不同主体汇集到一个大方向上共同推进改革。
3.1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路径优化的核心原则
进一步优化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改革应该遵循以下四个核心原则:
一是“被设计”的制度需要地方适应。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如何关照到少数民族社群长期存续并具效率的山林治理规范,尤其是尊重和善加保护利用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生态伦理基础上的共有产权治理规则,从而避免“一刀切”式地分权与市场化。这需要“被设计”的制度不仅允许产权方式的多种表达,更要允许产权实现的多种方式。
二是既存社會资本需要适应性改造。集体林权改革除了构想未来林权的表达方式及市场实现路径之外,还须关照到新的市场条件下少数民族林区社群文化与治理结构的适应性转型,并不得不支付社群“社会资本”的改造成本。这种支付并不意味着林权作为“私权”亦或“公权”孰优孰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使整体文化禀赋、市场意识、市场谈判力偏低的林农与其他市场主体一起平等入市、对等竞价、公平获利,既包括技术支持与投入,更包括制度性投入。而制度性投入的关键在于林改后使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基于专业分工,以市场契约为纽带、以互惠互利为目标达成“社会化协作生产”,从而在政府、林农与市场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网络合作关系。
三是各方主体利益需要适度均衡。集体林权改革实践中两种情况极易出现:一种是基于林农利益保障和社会稳定的“退让”,尤其突出表现于集体林与国有林或林农与林业经营业主间争议时,政府“兜底”担保下的“林农偏向”;另一种是林农市场弱势和效率优先的“挤占”,突出表现于前文述及的林权集中。两种情况都极易损害某方利益,产生负向激励阻挠改革。西部少数民族林区林农更加弱势及民族和谐诉求使问题更加复杂。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达成各方利益的某种均衡,既保障弱势群体的林农权益,又保护作为精英阶层的企业家精神,还要激发作为中间介质层的村民自组织机构的活力与动力,其核心是找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边界,既要避免简单地将弱质林农直接抛向市场的唯效率论,也要避免基于关照弱势而直接干预市场的唯公平论。政府的核心职责在于构建统一、公平的非歧视性制度体系,尊重合法产权与契约并提供强制性保护,有关林业资源配置的领域则应让位于市场,而林农深入参与市场资源配置博弈的前提是真正成长为具有对等市场势力的主体。因而,政府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引导、资助和协助林农主体成长,对生态目标限制的利益损失予以足额补偿;另一方面在一整套公平竞争法则的规范基础上赋予市场足够的自由空间,实现林业资源优化配置,既不失公允,又激活效率。
四是产权制度改革需要综合配套。迫切需要从三方面切入深化配套改革:其一,政策法律“真空区”,如产权评估、交易规则、交易平台和利益分享机制的建立,产权融资规则及金融产品的创新,林业经营体系创新,以及产权档案联机管理机制创新等方面。其二,政策法律“叠加区”,即同一领域“碎片化”的政策法律或政策前后变化导致的林农利益受损,需要协调标准、消除冲突,如反映最为突出的天保林、生态公益林及集体商品林的交叠区政策盲区,以及四川“三州”木材禁运为代表的地方性政策与中央政策“错位”,均极大限制了林农产权实现。其三,政策法律“特别区”,即基于西部少数民族林区自然生态环境、社群传统习俗、民族宗教文化等特殊制约因素,回应制度适应性需求而建立的针对性政策法律,如大量立地条件差、活立木成材周期长、生态功能突出的林区,如何发展林下经济及关联产业增收致富,如何确立寺庙周边林权及寺庙用材保障机制,如何保存具有效率的社群治理结构并引导其遵循市场法则作出适应性演变。
3.2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路径优化的政策体系
西部民族地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政策体系优化应建立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现代产权制度基础之上,既要完善林权实现和林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要提升林区、林业和林农的内生持续动力。同时,还应协调和平衡相关利益主体关系,从以下四个方向进行政策优化:
一是巩固完善集体林权主体改革成果,切实构建起“边界明晰、权责分明、权能顺畅、保护强制”的现代林权产权制度,赋予农民合法且完整的财产权能。完善机制、查漏补缺,实现集体林权“应确尽确”;探索包括集体林权在内的农村集体产权“多权同确”,奠定农村产权统一管理的基础;探索集体林地“三权分置”,突破集体林权与社会资本相融合的体制障碍;完善集体林权登记管理制度,搭建跨区域的集体林权信息服务平台。
二是完善集体林权成果运用及权利主体权益实现的外部环境,切实增强支林政策和资金的效能。创新财政激励机制,提高财政支林力度和政策普惠度;加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奠定林区发展基础;拓展林业融资渠道,完善林业金融体系;完善森林保险制度,构建多元主体的林业经营风险分担机制。
三是构建新型林业经营体系,提升集体林业发展的内生持续动力。引导集体林权规范流转,促进适度规模经营;积极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构建“全林业产业链条”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对林下经济的扶持力度,促进林业生产向林业分类基础上的多功能经营模式转变;探索参与式森林经营管护模式,重构乡村森林生态治理共同体。
四是探索生态资源经营和生态补偿多元模式,不断完善集体林业的权责利均衡机制。提高公益林生态补偿标准,激励农户管林护林的积极性;探索公益林生态赎买机制,尽可能缩小森林生态价值的市场扭曲;积极运用碳汇林业等创新手段,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
(编辑:刘照胜)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郑风田,阮荣平,孔祥智.南方集体林区林权制度改革回顾与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1):25-32.[ZHENG Fengtian, RUAN Rongping, KONG Xiangzhi. A review and analysis on southern collective forest reform[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9,19(1): 25-32.]endprint
[2]朱冬亮,贺东航.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农民利益表达——福建将乐县调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6.[ZHU Dongliang, HE Donghang. The new reform of collectiveowned forest property rights and expressions of peasants benefit: a case study of Jiangle County, Fujian Province [M].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56.]
[3]国家林业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林业局农村林业改革发展司.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践百例[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1.[The Collective Forest Reform Leading Group Office of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partment of Rural Forest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actice cases of collective forest reform in China[M].Beijing: China Forestry Press, 2009: 1.]
[4]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拉里·施罗德,苏珊·温.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8. [OSTROM E, SCHROEDER L, WYNNE S.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policies in perspective [M].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TD.,2000: 8.]
[5]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AOKI Masahiko. Towards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M].Shanghai: Shanghai Fareast Publishers,2004.]
[6]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C]//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70-276.[DAVIS L E, NORTH D C.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oncept and reason [C]//COASE R H, et 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property rights school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chool.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TD.,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270-276.]
[7]林毅夫.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C]//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61-264. [LIN Yifu.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by government [C]// SHENG Hong. The modern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croller volume Ⅰ).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261-264.]
[8]L·E·戴维斯,D·C·诺斯.制度创新的理论:描述、类推与说明[C]//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97-310.[DAVIS L E, NORTH D C.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description, analogy and instructions [C]//COASE R H, et al. Property righ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property rights school and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chool. Shanghai: Shanghai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TD.,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297-310.]
[9]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资本投资、制度与激励[C]//克里斯托夫.克拉克,主编.制度与经济发展——欠发达和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与治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96.[OSTROM E. Capital investment, institution and incentives [C]//CLAGUE C.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growth and governance in less developed and postsocialist countries. Beijing: Law Press. 2006: 196.]
[10]朱曉阳.林权与地志:云南新村个案[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60-72.[ZHU Xiaoyang. The forestry tenure and the topography: a case study of a Yunnan village[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9(1): 60-72.]
[11]郑风田,阮荣平.新一轮集体林权改革评价:林地分配平等性视角——基于福建调查的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10):52-59.[ZHENG Fengtian, RUAN Rongping. Evaluation on the equality of new wave collective forest reform: a study of Fujian collective forest reform[J]. Economic theor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2009(10): 52-5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