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爨碑的审美价值
聂欢欢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魏碑的书法艺术是我国传统艺术中的一大宝藏,它总的体势和风貌是一致的,但又有南北之别,到每一块石刻又都有各自的特点。其中,南碑首推《爨宝子》最为古朴强拙,此碑纯用方笔,隶意甚浓,似脱于汉《张迁碑》(北碑)。而与其同时的《爨龙颜》与之并驾齐名,世称“滇南二爨”。康有为较早地为《爨宝子碑》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说其“朴厚古貌,奇姿百出。”“端朴若佛之容”。在一些有关书法的论著如《碑帖叙录》中称其“古拙中见凝重”。王晓斌《爨宝子碑书法中的美学意蕴》中将爨体书法结合书法史上“魏晋之风”的风格特点分析,认为爨体书法是一种介于豪放美与婉约美之间的一种中和之美。综合来看,“二爨碑”在魏碑中的独特性即其特异的书风成为南碑的精华,也是爨碑的审美价值所在。
一、魏碑的书法艺术特色
自清代以来,人们开始关注碑学,魏碑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从学者研究的角度来看,大家较多关注的还是魏碑用笔和雕刻的技法以及魏碑的笔法结体与传统楷书之间的差异,整体上还处于技法层面,涉及技法之外的研究还较少。忽略了魏碑内在本质所带给我们的实际意义和审美价值。对魏碑的研究不乏顶级学者的高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已有总结,魏碑体现在“备众美,通古今,极正变,是为书家极则”。意思是说魏碑兼具各种书体的优长,有超越书法史的存在感,有突破书法模式的自由感。魏碑的存在和被关注给中国书法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它打破了传统书法过于讲究笔法技巧、结构过于雕琢的现象,表现出率真、不拘一格的气度,使书体富有超出字体本身的精神层面的表现力,这种精神注入我们今天书法中,可以一扫作美之态,触发勃勃生机。
(一)魏碑书风的成因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字石刻的通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史上政局动乱的时代,随着社会的动荡也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各民族文化相互交织;在精神文明史上极其自由,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最具有艺术精神的时代,是古代中国文明的成熟与繁荣时期。在我看来,这就是促成魏碑无拘无束、自然天成书风的主要时代因素。
北朝延续了汉代石刻树碑之风,尤其是厚葬之风的盛行,促进了石刻树碑之风的繁荣。为逝者立碑颂德,是先人对古代营丧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北朝大量的优秀的书法作品,大多都是厚葬带来的墓志镌刻风行的结果。墓志的兴盛,促进了人们对书法的重视;墓志书法的不断发展变化,对魏碑书风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北朝石刻树碑之风促进了碑刻与书法的发展,促成了刚健质朴、粗犷豪放的艺术风尚。但不可否认的是,北朝文化中儒学传统注重礼仪规范、经世致用的现实精神,仍然对魏碑厚重端严书风的形成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被称为“滇南二爨”的爨碑就是魏碑的一个特异的存在——孤悬西南一隅,独立所谓蛮夷之地,书风略有楷意但隶意犹存,天真浪漫。
(二)魏碑书风
魏碑书法自成面目,独树一帜,而且流传甚广,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北魏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体,它对隋、唐楷书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北魏的书法艺术,前人有过极高的评价。清人包世臣著的《艺舟双楫》及康有为著的《广艺舟双楫》中皆对北魏书法推崇备至。包世臣说:“北朝人落笔峻险,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又说,“出入收放偃仰向背避就朝楫之法具备。”康有为在评魏碑书法时云:“魏碑书法,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紧密非常。”又云,“凡魏碑,虽取一家,皆足成体,尽会诸家,则为具美。”康有为还称赞北魏书法有十美,因与本文关系不大,在此就不一一抄录了。
北魏书法用笔多为大起大落,不重点画的均衡,行笔迅起急收,转折处更多以侧锋取势。形成外方内圆、钩趯力送、撇捺垂顿的特点。魏碑笔法给人以“丰而不满,虚而不空,雄奇角出”的印象。总的来看,使人感到劲健泼辣,雄浑厚实,韵味深长。
魏碑书法的结合体在符合重心位置要求的基础上任意布置,疏密自然,纵横倚斜,错落有致,总体显得朴素俊美。总之,北魏书法的特点就用笔来说,有方有圆,或方圆兼备;就结体来说,有横有纵,或纵横相间,高低错落;就北魏书风来说,初期魏碑雄强矫健,悍劲粗犷,后期魏碑受南朝书风的影响,渐趋浑厚、圆润遒美。
南北朝时期楷书虽然已经成形,但未最后定型,尤以爨碑最为典型。爨碑用笔和结体相对来说不受什么约束,比较自由,故千姿百态,看似各体兼具。
二、爨碑在魏碑中的特殊地位
形成于魏晋南北朝的爨体书法在中国众多的书法字体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是中国汉字发展史上的一种过渡性字体,其实是对隶书的一种创新。“爨体”的得名,主要来源于现存云南曲靖的“二爨碑”,它不仅是中国文字的“活化石”,而且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
(一)爨碑的由来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有三个方面,一是书法艺术完全达到了自觉化,形成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东晋新书风;二是书法书体演变渐趋完善,书法技法体系基本完善;三是碑刻书法兴盛,成就极高,以北魏碑刻尤为突出,史称“北碑”或“魏碑”。北碑有碑碣、墓志、摩崖、造像记几类形质,作品丰富,风格多样,以《石门铭》 《郑文公碑》《瘗鹤铭》为代表。南碑则较少,爨碑是其杰出代表。爨碑以其独特的史料文化及艺术价值等,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被誉为“南碑瑰宝”。
爨碑又称“二爨碑”,即《爨宝子碑》与《爨龙颜碑》。《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出现在中国魏晋时期,被认为是中国汉字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性字体。由于当时实行“禁碑令”,立碑有一定危险,所以碑和碑文少见,但是对于僻处西南边地的世家大族而言,这种影响可能并不大,所以爨碑得以诞生并完整保存至今。此碑清乾隆年间在云南曲靖出土,现今保存于曲靖市第一中学,主要叙述爨宝子的生平、家世及其政绩。《爨龙颜碑》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现存于云南曲靖陆良县贞元堡,碑文为爨道庆所作,追溯了爨氏家族的历史及爨龙颜的生平事迹。此碑与《爨宝子碑》相比,碑石较大,字数较多,故称“大爨”,《爨宝子碑》为“小爨”,“二爨碑”成为现今仅存的爨体字碑刻和爨体字来源。
(二)“南碑瑰宝”
爨体的出现与魏晋风度具有相同的社会历史背景,魏晋风度特有的景观,反映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欣赏与之同时代出现的爨体,仍然可以看出魏晋风度的某种辽远的认同。美学家李泽厚概括说:“魏晋时期的书法表现出来的仍然是那种飘峻飞扬逸伦超群的魏晋风度。”某种程度来说,爨碑与空间距离遥远的北碑在“飘峻飞扬”与“逸伦超群”的“风度”上达成了一定的审美同感。
《爨宝子碑》无论用笔、结体,均已开始由隶书向楷书过渡,处于一种似隶非隶、近楷非楷的中介状态。它横画左右翘起,收尾皆呈锐角,是熔隶楷于一炉;竖末常左带慢弯,更像隶书中竖画的写法,而无楷书中的“悬针”“垂露”笔意;撇捺飞扬呈尖状,略存隶意。它是介于楷隶之间的崭新书体,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书法家的一件杰作。
《爨龙颜碑》基本上舍弃了《爨宝子碑》中似隶非隶、欲楷不楷的怪异状态,大胆地走出了隶书的氛围。钩趯含蓄饱满;横竖中截坚如实铁;撇捺在末端将力量藏住,出锋后又急收,峻利爽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南朝宋代碑刻有《爨龙颜碑》,“下画如昆刀刻玉,深沉精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为隶楷极则”。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后的第二个思想大解放时代。这一时期,主张清静无为,老庄哲学兴盛,形成了玄学。魏晋时期第一次把人格放到了最为重要的地位,体现出一种重追求个性、自由的人生价值,以及重审美的、唯美的人生追求。
就书法来说,魏晋时期是我国书法艺术取得高度成就和不断突破的时代,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等一大批书法家,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这一时期的书法提升到了一种对于人生态度的理解以及力求解放思想文化的境界。在书体方面,从单一追求字形到转向对风骨、神、意、气韵的重视,在审美方面也逐渐转向对于自然清新的追求。从《爨宝子碑》字体书风来看正是魏晋时期“风骨”美学思想的体现,碑中字体或头重脚轻或东倒西歪,顺其自然而取势,饱含了一种“大巧若拙”的“愚”韵以及一种放浪形骸、不拘泥的超凡脱俗;形态率真朴实没有太多拘谨的同时却多了一份流畅自然的豪迈之气。作为与北碑并驾齐驱的“南碑瑰宝”,名副其实。
三、爨碑书法独特的美学意蕴
美的法则并不仅仅是对称与和谐,温文与尔雅。爨体笔法与结体结构的多样性、自由、不规则性是引发强烈审美冲动和情感的因素,也是构成其美的基础条件。爨碑书体虽然处于楷隶之间,但并不具备楷书的规整和隶书的秀逸,它是一种变体,是西南边地书家的自由创作,是融合了中原文化、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与西南山水灵气的率性之作。通观其所处时代的书法,爨体形成了拙中有巧的艺术风格,这也正是其艺术价值和审美意蕴的深层体现。
(一)“二爨碑”笔法个性特征
1.《爨宝子碑》笔法特征
《爨宝子碑》是云南边陲少数民族首领受汉文化的熏陶,仿效汉制而树碑立传之作。此碑刻于东晋义熙元年(405),书体是带有明显隶意的楷书体。碑中一部分笔画仍保留了隶书的波挑,但结体却方整而近于楷书。用笔以方笔为主,端重古朴、拙中有巧,看似呆笨,却常现飞动之势。康有为在《广义舟双楫》中评此碑为“端朴若古佛之容”是恰当的。
《爨宝子碑》结构凝重丰满,随字异形,聚散有致,变化多端。其用笔雄奇角出,笔试舒展。基于此,下面就此碑结构与用笔两个方面具体剖析。
(1)随意的布局
①因字异形,纵横各别
《爨宝子碑》中的字以方形为主,字字呈四角饱满的“块形”。碑中文字很少有像后来楷书成熟时的中宫紧措、恣肆纵横的体态。这种“块形”的造型显得端正凝重。一般来说,上下组合的字构成长方形;左右组合的字构成正方形。如碑中的“穹”“亨”“黄”等字为长方形,碑中的“放”“物”“保”等字为正方形。

②随体畸变,以险取胜
这类字在碑文中虽然不多,但潇洒纵横、不拘一格。如碑文中的“墓”“忾”等字。“墓”字横竖笔画倚侧歪斜,撇捺张扬酣畅,“土”部竖画左倾,和“日”部右倾相互摇曳,动感十足;捺画下加一点,如秤砣般制衡了整个字的重心。“忾”字右半部占空间大,左半部竖心旁两点收缩,竖画下笔和收笔顿挫张扬、骨力气象十足;右半部横折竖画端方平正,点画和撇捺排列整齐又不失错落,显出古拙天趣。

③大小错落,一如繁星
隶书的结体,一般来说整篇字大小匀称,楷书更趋统一。《爨宝子碑》的结构大小错落,极其大胆,造就了参差错落、主次分明的视觉效果。解晋《春雨杂述》说:“一篇之中,虽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峰造极,如鱼鸟之有麟凤,以为之主。”如碑文中的“遵”字就写得特别大,四周字较之甚小。这样以小映大,如群星之拱月,使“遵”字的特殊地位(从立碑者、写碑者甚至刻碑者的角度)和优雅之势更为突出。碑中如“爨”“晋”“宁”三字写得大,但处理得天真活泼,与整块碑的其他字没有违和感且相得益彰(“爨”为碑主姓,“晋”“宁”都有美好的意味)。

(2)独特的用笔
①点
《爨宝子碑》碑中的点状如倒三角,形状繁多,大小不一,向背各殊。俯点:需横切入笔,略顿向下方侧锋行笔,收笔时提笔回锋,略有向下俯的弧度。仰点:向右下顿切,侧锋向右上行笔,收笔时提笔回锋,形状如倒三角,略有向上仰的弧度,较为夸张的有提笔上挑的形态。侧点:形态与楷书有些相近,但更为方正。横切入笔后,略有顿向右下行笔,略有调转笔锋向下顿笔再调锋回到起笔处,笔锋转折时有顿挫、形成棱角。撇点、挑点:撇势点起笔向下方切顿后向上左侧行笔,提笔回锋,有些短撇的笔意和形态。挑点则是向右下切顿侧锋向右上行笔,提笔回锋,有短挑的笔意形态。呼应点:左右点和上下点常常笔势相连,笔意呼应,可以是俯、仰点呼应。如“将”“瀐”字,也可以是左右点的呼应,如“道”字。有些字的撇、捺也作点处理。各种点的变化虽多,但不能统一到三角形,凝重峻力。如碑文中的“秋”“将”“德”等字。

②《爨宝子碑》中的横画,横如水中舟,似隶书遗韵,但没有隶书中横画的俯、仰多变;有的横画不像隶书中的“蚕头燕尾”状。《爨宝子碑》中平行的横画均挑出。其中,长横形态如两头弯翘的小舟,落笔露锋,提笔调转笔锋,向右行笔,中间略细,笔势硬挺,收笔调转笔锋,向右上出锋,犹有隶书波挑的意味,如“晋”字中横。短横写法同长横一样,形态显得短小精悍,两头弯翘的部分更精炼,甚至只留笔意,横笔要求平坦硬挺,如“静”字。

③竖
《爨宝子碑》中竖画末端常带慢弯,此碑中凡楷书取悬针笔势的皆带慢弯,如碑中的“年”“令”等字。个别字把点也做了慢弯处理,如“令”字。这种笔法应该取自隶书中的竖钩,兼具沉稳与飘逸姿态,又与横画、撇捺画的挑、翘遥相呼应,兴味盎然。

④撇捺
《爨宝子碑》中的撇捺笔画多做上翘,个别捺像楷书成熟后的笔势。撇捺笔画的上翘取势与横画起收角出,竖画做慢弯的处理,给我们的感觉是其碑文通篇的统一。凝整中寓飞扬活泼,静中求动。如碑文中“发”“人”“太”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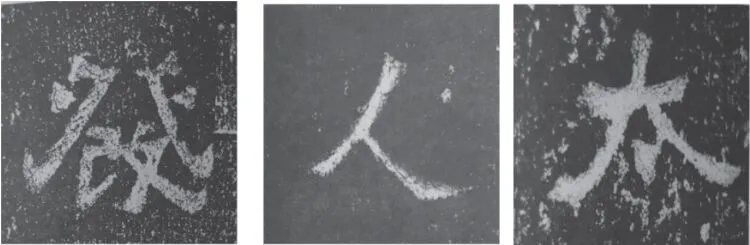
⑤转折
《爨宝子碑》中凡横折处,皆平起直落,凡做“口”字,也根据结体的需要或正方或长方或斜方这种处理乃四角周密。四边做垂直的处理与楷书写“口”字时呈上宽下窄不一样,如“保”“石”“枯”等字。上下等宽,更类似于隶书安排。

2.《爨龙颜碑》笔法特征
《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比《爨宝子碑》晚53年。就几千年书法史而言,可以说,这两块碑是同时代的作品;但是从细节看,它们之间似乎又留下了漫长岁月的雕琢痕迹。《爨龙颜碑》的结体以方整为主,但转折处已使用圆转笔法,而不像《爨宝子碑》那样如矩形的折角,更具有楷书的特征。更奇特的是,可以从《爨宝子碑》笔画的圆润刚强,窥见其运笔实源于篆法,起笔虽有刚圆之分,但笔画均极为厚重。《爨龙颜碑》在手法上俯仰相让、疏密相间,在结构上姿态奇异、收敛自如。康有为评说“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
《爨龙颜碑》的用笔,意态雄强峻厚,雍容舒长,富有飘逸、飞动的节奏。点法丰富,方圆兼施。三角形点居多,兼有尖、圆点。点如高峰坠石,意态险峻,收笔方向变化多端。如碑中的“秋”“深”。

钩趯含蓄丰满。如“薄”“亨”“宁”等字。

竖画及横画中截坚实如铁,起笔、收笔多方、亦时有圆笔。如“河”“军”“季”三字。

撇捺在末端忍蓄出锋后又急收,饱满有力,多含隶意,有横扫千军之势。如“郡”“金”“衣”等。

横折变化多姿。既有横画到头暗转的笔法,圆浑有力,实含篆意;也有转折处换锋另起,顿笔方折,峻险雄强;也有从横画顺延向左回而突兀地转折。如“倾”“丙”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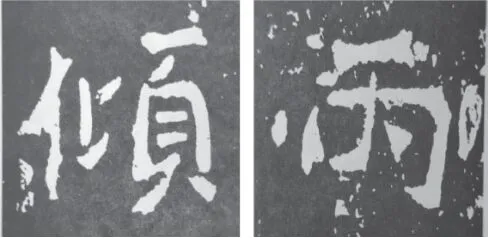
《爨龙颜碑》之所以被称为“正书第一”,是与其整幅章法分不开的。碑文给人以灿烂、庄严、清肃的印象。清代书法家邓石如云:“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此碑整体布局得当,字距、行距之间疏密相间,洞达跌宕。虽笔画粗壮,有茂密之感,然字之间的相互关系,顾盼有致,虽舒朗、透气,但行气连贯,整幅作品并不因大的空白而产生散乱之感。
(二)作为文字的天真之美
“二爨碑”碑文原本是适应于当时主流语言或官方语言的文字,已经具有一般文字的规范性和较为清晰的表意范畴,符合一般碑文的基本规范要求。但是,作为表意符号存在的“二爨碑”文字,因为地方性因素的介入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使得它天然具有了地方山水的特质和特殊人群的灵性,因而也就具有了作为艺术存在的爨体书法的天真之美。
1.笔画之美
线条是书法艺术中最基本的元素,不同风格的线条构成了不同风格的字体。可以通过线条的美来感受线条中所蕴含的情感、精神、气质等。爨体书法将这一点做到了极致。爨体书法用毛笔书写(爨碑被发掘时其文字是刻于石碑之上,但在字体以石碑的形式呈现于世之前是用毛笔书写的),其运动轨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线条的走向,二是线条粗细的变化。碑帖中丰富的线条的变化,形成了爨体书法艺术独特的美感,同时也成为爨体书法区别于其他书法的主要审美特征。
爨体书法具有变幻莫测的线条运动及由此生发出的丰富的内在节奏。根据线条的走向,可将爨体书法的线条特征略作归纳。如线条大概有水平线、斜线、折线,延伸,方、圆,粗糙、上翘等。线条形态给人以不同感受,如两端向上挑起的直线具有严肃、伸展的平稳感;夸张的撇捺和弯钩的曲线具有飞扬的动感;笔直圆润的竖画线条具有内敛含蓄感;曲圆的线条可爱充满稚气,方线坚硬拘谨,粗线钝厚凝重,细线锐利硬朗。这种丰富的线条内部变化所产生的丰富的美感,正是爨体书法笔画本真个性的流露。
爨体书法一切都在于其巧妙的对线条造型特征的拿捏,其笔画线条的美感是有着极强的包容性和巧妙的融合性,它不同于一般隶书的书写方式,隶书线条沉着稳健,但爨体书法又没有一般隶书规整,特别是横画的流动;但是,还是能从其字体笔画中找到隶书的波挑之势,楷书线条规矩严谨,用笔灵活多变,讲究藏露悬垂。爨体书法中又含有楷书的一些笔画特征,比如尖撇、方捺、竖钩之类的笔画,笔画大都“方厚平直”有楷书的飞动之势。
2.结体之美
(1)多姿多变
书法以线条美为上的理论,大致源于元代书法家赵孟頫在《兰亭十三跋》中所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赵孟頫明显把书法的用笔放在了书法学习与审美活动的首要地位。
书法艺术是点画与线条有机统一的艺术表现,是点画与线条的有机调和。抽象地说,书法的结体之美,正是通过点画和线条在一定的时空中按照某种一定的节奏所构成的造型。
书法点画之间的断连关系往往是按照一定的结构规律在进行,线条之间的衔接关系实际上就是气脉相连的线条流动过程。就爨宝子碑书法文字的结体来看,初看会觉得歪斜丑,并不追求平稳与匀称,部分字形甚至给人一种头重脚轻的视觉感受,在隶书与楷书之间求同存异,但它打破了汉字横平竖直、方方正正的常规结体。形态丰富多姿、妙趣横生,取势也较为自由、活泼。
爨宝子碑中的字体的结构大都随意、自然,同样的字在碑中都呈现出不一样的姿态,然而都在变化中又求和谐。
但当我们仔细品味时便发现,一些字体其中一部分发生了倾斜的势态,对应的另外一部分也需要在相对应的方向上倾斜,维持平衡,这种线条穿插所形成的巧妙的节奏美感,将书法结体所表现出的大小、刚柔、动静、斜正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空间美感推向了极致,加之爨宝子碑上文字所特有的刀味、石味,构成了爨体书法结体恣肆放纵、稚拙古朴、拙中带巧、古气盎然、参差错落的独特气质。而这种自然的流露,恰恰反映的就是爨文化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书法字体的本真之美所在。
(2)可爱萌动
《爨宝子碑》的结体初看觉得不遵循汉字结构常理,但正是这种剑走偏锋的处理将爨体字的“拙”与“巧”巧妙地融合到了一起,使两者相互对比、相互呼应,同时又给人一种可爱俏皮的感受。《爨宝子碑》中的字还时常东倒西歪,任意地增减笔画,在“拙”与“巧”的呼应中显得萌动可爱,任其舒展却不刻意张扬,能收敛而不显拘谨,因此给人自然大方而又淳朴可爱之感。
(三)作为艺术的“拙朴”之美
爨体是中国书法史上除篆、隶、楷、行、草之外稀有的一种字体,被认为是中国汉字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字体。《爨宝子碑》因受到民族文化交流的影响而很有特色,开创了书法艺术中的天真稚拙一派;《爨龙颜碑》也是由于民族文化交流的影响而为汉字书法带来新面貌,它和一般南碑北碑的书法形象迥异。其书法艺术成就在此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书法形态。《爨宝子碑》“朴实古茂,奇姿百出”,“端朴若古佛之容”,“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如神女”,表现出《爨宝子碑》的自然之趣,粗犷之势,质朴之神;《爨龙颜碑》则尽显灵变之趣、端庄之神。此二碑,《爨宝子碑》方笔为主,古拙、拘谨;《爨龙颜碑》则方圆兼备,且舒展、端庄。
二是书体演变。爨碑所处时代为中国书法快速发展的时期,二爨碑虽只隔53年,但笔法字形特征却颇为不同,《爨宝子碑》结体在楷隶之间,隶意甚浓;《爨龙颜碑》却已基本脱开隶书笔意,虽隶意略存,但楷意已多。
三是书法审美。中国书法在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形成了以“中和”思想为主导,神形兼备、朴素和谐统一的审美意识体系。这一思想在以王羲之所在的魏晋时期达到高峰,而于王羲之逝后数十年出现的爨碑则树立起另一种书法审美典型,但是其“刚柔相济”的书法艺术特征有中国书法发展的基本规律贯穿其中。
1.古拙与清新之美
云南地区环境优美、气候宜人,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当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审美观。尽管云南少数民族所表现出的审美心理还仅限于潜意识层面,创造出的美往往也具有偶然性,其审美趣味也还单纯地出于对自然和形式的美的欣赏,但他们在质朴的日常生活中所呈现出的真实自然的美,其实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爨宝子碑》书法之美表现出来的朴实而古拙,便不单是似隶似楷的拙,地理位置上相对封闭的云南缺少了城市的约束反而使其更多地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原美,是一种洗尽铅华见真诚的审美取向。它表现出来的有可能是艺术技能不成熟的产物,是一种潜意识的涂抹。但恰恰是这种美构成了一种苍茫之天然的本真、一种原美,它排斥一切刻意的人为雕琢气息,追求一种浑然一体的淳朴感和苍茫感,它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种天然的气质。
爨体书法形神皆古朴而悠远,一方面有着深厚的文化沉淀,传承着历史文化长河中特殊的使命,另一方面它却又毫无修饰,散发着浑厚淳朴之美,这一点正好同拙在本质上构成内在联系,而从碑刻这一书法载体的质感方面来看,“拙”又具有“厚”的意蕴,是一种具有苍茫的存在感的“厚”,一种朴实的厚。
爨体书法以拙为美,以朴为华,既增添了爨体书法的艺术感染力,又使其艺术风格得到自然的显现。这种古拙可以说是一种没有形式的形式,没有修饰的修饰,没有痕迹的痕迹。
仔细品味爨体书法,我们能在字里行间看到一种精神的解放,看到一种灵气,这种灵气是一种源于人们精神灵动的美,这种拙味看似笨拙,却又不失清丽脱俗,故而我们从爨体书法的拙味中不难感悟到一种充满灵性的清新。《爨宝子碑》中的字还时常东倒西歪,初看觉得有些不合书法普遍意义上的常理,但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些拙与巧的呼应中感受到许多的多姿多情、趣味盎然。
《爨宝子碑》结体舒展而又不刻意张扬,看似收放自如却又不显矫揉造作,因此给人古朴大方而又灵动清新感受。这样朴拙的书风与生活在风光秀美而又奇特的地域环境里的人们的性格以及审美意识无疑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2.舒放与典雅之美
在东晋之前,具有豪放特点的作品已有多数,与内地相比,云南是“南蛮”之地,由于受内地文化熏陶较少,所以《爨宝子碑》更多的是随意与任性而书,多少有些舒放的南蛮之气。其碑文结体欹侧取势,苍健有力,不以平整为法,而以重心为正,左倾右倒,气脉一贯,每一个字似乎均有一种膨胀力,体势宽博,有一种奔放豪逸的性格。
典雅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审美美学范畴或艺术风格,也表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那种对人生修养的肯定,它强调的是一种文人的审美取向。《爨宝子碑》作为已故将军墓之碑文,文辞典雅,很讲究对仗和措辞,比如:“山岳吐精”“弱冠称仁”等,体现的是爨文化中受到中原文化影响渗透所反映出的一种典雅之美。
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不断变化,书法文字作为一种有着明确表意功能的符号,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文字符号给予人们的冲击力。反而是新奇的文字形象可以变得更加能引人注目和思考,文字的图形化已然成为一种文字新的表现手段之一。
爨宝子碑出现于中国东晋时期,早在其之前,中国汉字就已经历了从具象到抽象的演变,成为了一种纯粹的表义符号。作为一种书法文字,爨体字形态的多样性和艺术性使得其完全可以独立于语言意义之外而得到欣赏。通过对其形态、笔划、结构等进行合理的设计,将其独特的气质面貌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全新的方式展现出来,以更清晰、更深刻、更形象的表现方式传达这些古老文字所蕴含的意义,这是当代语境下对爨体书法的认知以及爨文化传播发展的必经之路。
《爨宝子碑》记录云南爨文化的历史,它以特有的书法汉字符号,承载着云南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特有的情感。用传统的审美视角,对其书法艺术及文字符号的借用与转换,将之重新解构、改造和发展,这种“古为今用”的观念对探索和领会爨体书法艺术的精神内涵起到了深远的指导意义。
爨体字书法结体严整规素,笔画结构和谐互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爨文化历史时期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滇民丰富的精神信仰。我们知道,汉字的形成凝结了先哲们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和思索,它不仅仅只是对客观事物的简单临摹,而是在日积月累的观察和探索过程中进行的反复的取象和重塑,它完美地体现了先哲们注重整体性和情感表达的思维方式,并最终从感性的认知深化到了理性的抽象。爨体字书法也是如此,它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或表述,其中更是凝结着爨人乃至云南民族对美好事物的审美评价和判断,其中就包括了民族、宗教、文化、伦理等各方面的美学价值。爨体字汉字取象于自然之道的节奏美、秩序美,这不仅是汉字象形背后的精神体现,更是道法自然的道的律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