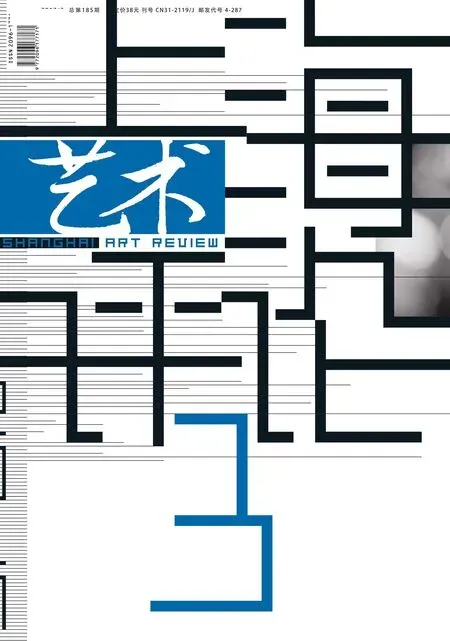工具的理性与观念的解构
——从缪哈伊的《高压电》反思高科技与音乐的互动逻辑
杨珽珽
工具的理性与观念的解构——从缪哈伊的《高压电》反思高科技与音乐的互动逻辑
杨珽珽
布列兹认为“未来音乐需要将想象性和理智性结合起来,进行系统化的发展,简而言之,即艺术需要与科学更进一步结合起来”。从人类音乐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精确的记谱法、乐谱的印刷术和工业化乐器制造技术的进步等,对音乐创作及其观念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到了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后工业文明的高科技迭代式发展,使得音乐观念的构成已不再是单维的了。
法国当代乐者缪哈伊及其频谱音乐的沪上风暴
如果熟悉上海汾阳路20号,一定知道在桂花飘香的金秋季节,总会有一群来自海内外前卫且顶级的音乐家汇聚在那里,在那群古旧又经典的欧式小洋楼周围掀动起一阵阵音乐旋风。这,就是上海当代音乐周。从品质上评判,上海当代音乐周不仅为圈内音乐人集体狂欢营造了一方公共空间,同时也是圈外音乐朝圣者在此洗脑的神圣乐坛。其中最让我们刻骨铭心的就是驻节法国作曲家特里斯坦·缪哈伊与他的作品,并以大师班、讲座和开幕式作品的全套法餐程序,再次将频谱音乐(la musique spectrale)的理念席卷沪上。
虽然,缪哈伊此次带来的《映射之二:高压电》(Re fl ection/Re fl ects II :High Voltage/ Haute tension, pour l’orchestre, 2013)已不再是当年先锋的电子音乐作品,但仍是一部于2013年晚近创作的纯管弦乐队作品,其所呈现的频谱音乐思维依然一耳可辨。借用互联网时代一个耳熟能详的套路话语,缪哈伊的频谱音乐思维,就是要“站在科技的风口,让音乐飞起来”!毫不夸张,“频谱”完全就是一个科技的风口:作曲家们通过计算机辅助获得的视角,将音乐的定义拉伸至更为微观的频谱层面——音乐是一种由各类频率构成的声音。当然,在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景观下,从技术的层面去理解和运用频谱音乐,这并不是一件难事,而难的是“迎着风口飞”。以缪哈伊为代表的一族法国作曲家,他们正是得益于后数码时代的高科技手段,伫立于后工业文明崇尚工具理性的风口浪尖上,以此创立了20世纪最后三十年席卷全球的频谱乐派。乍听上去,频谱音乐似乎颠覆了印象中不食人间烟火的传统作曲家形象,然而请别忘了,频谱作曲家背后则是经历了“戴高乐时期”的法国——这正是法国近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戴高乐主义”时期。
确实,法兰西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1958年,由作曲家皮埃尔·沙埃弗尔(Pierre Schaeffer,1910-1995)领导的原“具体音乐研究小组”(Le Groupe de recherche de musique concrète)以法国公共广播电台(La Radio Publique Française)为中心,摇身转型为“音乐研究小组GRM”(Le Groupe de Recherches Musicales),以一种社会性机构的地位,集中各类媒体的宣传,对新音乐创作活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支持,同时,这个小组又兼具研究性和实验性。在之后四十年的发展中,各地都纷纷效仿这样的模式成立了具有综合性功能的实验机构,而如此“整合资源、集体作战”的方式让法国当代音乐创作很快步入了更新及更宽阔的空间,尤其以1977年成立的“IRCAM”——“声学、音乐联合研究中心”(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Coordination Acoustique/ Musique)成为其中一个标志性的研究机构。著名美国音乐史学教授塔鲁斯金(Richard Taruskin,1945-)曾指出:“IRCAM就是法国政府以总统项目为名(蓬皮杜总统钦点项目),实为‘引诱’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Poulez, 1925-2016)从美国回法国而建立的一个声学电子研究中心。”塔鲁斯金的话语固然充满了酸涩的滋味,然而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揣摩。
法国频谱乐派的前身,是由梅西安的两位高徒缪哈伊和杰哈尔·格里塞(Gérard Grisey,1946-1998)独立创立的L’itinéraire“旅程”小组,而后米伽埃勒·勒维纳斯(Michaël Levinas, 1949-),罗杰·泰斯埃(Roger Tessier, 1939-)和于格·杜付赫(Hugues Dufourt, 1943-)三位作曲家也加盟其中。频谱乐派作曲家强烈反对序列主义所带来的严格控制和束缚,并通过全新的创作理念,同时借助日益强大的科技手段,来打造音色音响的音乐世界。
20世纪科学技术对现代音乐创作的本质性介入
但是,要提到频谱音乐早期的发展态势,并不是法兰西一枝独秀。在同期较有声势的还有德国“Feedback”反馈小组的各类音乐实践活动,以及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广播小组”和罗马尼亚的一些作曲家。但是布列兹的回归,的确产生了蝴蝶效应,让法国作曲家们一下子成为了黑马“杀出重围”。
首先,布列兹认为“未来音乐需要将想象性和理智性结合起来,进行系统化地发展,简而言之,即艺术需要与科学更进一步结合起来”。布列兹的音乐观念与“旅程”小组作曲家们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契合。其次,1980年,“旅程”小组在以集体入驻的形式来到“IRCAM”,并伴随着“当代室内乐团”(Ensemble Intercontemporain)不断上演着自己创作的新作品,同时,“IRCAM”也推动了这些作曲家来到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宣讲自己的创作和理念。于是,法国频谱乐派就从达姆施塔特开始一路高歌猛进,甚至走向了美国,影响了全世界。“IRCAM”逐渐成为一个被全世界瞩目的音乐创作前沿阵地、教育机构和传播中心,并且“IRCAM”以多学科交叉为基础的风格,不断地吸引来自于国际各种文化语境下的乐者前去朝拜。当然,“IRCAM”的技术人员也乐此不疲地奔波于世界各地,传播着科技思维的同时,也推销着各类最新软件和电子音乐产品。
然而,科技思维这一潮流在音乐中的介入并不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出现的,可以说,整个20世纪西方当代音乐的进程,都无法离开科技迭代式发展的推动。首先,19世纪末录音技术和电话技术这两项重大的发明,给音乐的媒介和传播带来了全新的变化,由此也带来了声音产生的新技术视角。这一切对20世纪乃至之后的音乐创作观念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到了20世纪初,美国发明家萨迪厄斯·卡希尔(ThaddeusCahill, 1867-1934)发明的电传簧风琴(Telharmonium,1906),将声音转化为电流,并通过电话线进行长距离的输送,再转化并进行播放。这一技术在当时颇为轰动和时髦。虽然这一“新乐器”重达几百吨,但是一些饭店、宾馆和俱乐部都竞相购买,使得当时的作曲家和音乐家们都为之一振。如此新式电声乐器的发明,昭示了20世纪电技术时代(l’âge électrotechnique)的到来。
与此同时,1906年产生的三极管“作为一块基石标志了电子时代(l’âge électronique)的开端”,振荡器和扬声器成为这个电子时代的代表性技术。在“二战”前,利用这一技术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1920年泰勒敏琴(Theremin)和1928年马特诺琴(OndesMartenot)两大电子乐器的发明。虽然两种电子乐器各有自身的特点,然而其基本原理都是用装有三极管的振荡器来产生或者改变电流的频率,再经过放大和扬声器变成声波而发声。
而后还有约翰·凯奇1939年创作的《想象的风景一号》(Imaginary Landscape No 1),瓦列兹创作的《赤道仪》(Ecuatorial,1934),梅西安创作的《美丽温泉的节日》(Fête des Belles Eaux,1937)和著名的《图兰加利拉交响曲》(Turangalîla-Symphonie,1946-1948)等。由于当时技术和条件的诸种限制,此类作品也只是作曲家为了进行个别实验所完成的,其并没有形成一种思潮性趋势,也不代表着此类作曲家的集体式探索。然而无论如何,这些作曲家的实验性音乐为“二战”后频谱音乐的高潮性发展给予了不可或缺的铺垫。
“二战”结束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音乐工作室如雨后春笋一样林立起来。可以说,正是音乐工作室对音乐作品创作和无线电广播的介入,极大地推动了音乐与科技在共谋中走向深度的合作。如有皮埃尔·舍菲尔领导创建的“具体音乐”,以及1950年左右以德国科隆音乐工作室为标志的“电子音乐”的声音。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融合“具体”和“电子”双重音乐特征的作品问世了,它们既使用了“具体”的声学材料,又有“电子”的后期制作,但在技术层面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直到1957年,美国电子工程师马克斯·V·马修斯在贝尔实验室成功研制出第一台计算机控制的声音合成器,标志着音乐与科技的结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一个以编码和电脑为代表性技术的音乐时代的到来:数字/计算机时代(L’âge numérique/informatique)。正是由于强大的计算和数字处理功能,作曲家们可以借助计算机对声音进行重新塑造和音乐的创作,并且从各自不同的目标和切入视角对这一时期的新技术进行多样而全新的探索。
无论是具有编译器(compilateur)功能的处理器,或是“声音处理”(traitement des sons)利用计算机的声音参数数字化转化和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在科技之风的层叠推进下,将合成器和声音处理两种方式在数字化的技术层面上进行扬长补短地互相融合,这是频谱音乐得以在70年代成为“风口”的大时代背景。
工具理性对作曲家传统审美想象的解构
从人类音乐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精确的记谱法、乐谱的印刷术和工业化乐器制造技术的进步等,对音乐创作及其观念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0世纪初,为了彻底突破调性的壁垒,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以来的序列思维对音乐各要素内部及相互之间的传统关系进行了重新洗牌,并且以其先锋的姿态,在现代主义思潮下撕开了20世纪音乐与传统的决裂之口。当然,对各要素的重新结构和去中心化,确实取消了几百年来西方传统音乐中的阶级性,把十二个音解放为“自由”的个体,这一切给那个时代的作曲家带来了全新的创作与想象的空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把当代音乐的创作推向了另一个极端,即音乐元素之严格的序列性和高度的控制性,实质上,这也是再一次铸就了对作曲家之表达与想象的束缚。确实,这是操用另外一种更为严苛的体系来打破之前的“束缚”,一切似乎陷入到一种不可遏制的悖论中。
于是,20世纪下半叶,在后现代主义思维的统领下,一波又一波作曲家再次前赴后继,带领严肃音乐经历了偶然音乐(aleatory music)、简约音乐(minimal music)、具体音乐(la musique concrète)和计算机音乐(computer music)等不同风格,同时也被爵士、摇滚与电子舞曲等流行音乐所冲击且裹挟。然而,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形成一个在较长的时段中独当一面的流派。而频谱音乐,作为20世纪后半叶极少出现的一种群体性风格,其本身走过了近40年的发展历程,也经历了从初始崛起到成熟再到转变的过程。时至今日,其仍然在变化和发展着。因此,笔者认为国人对它的理解和判断,如果只停留于早期外在创作技法的解析上,或是仅停留在以其对计算机的借助而产生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的盲目崇拜上,那是对频谱音乐创作研究的异化,更是对西方当代音乐发展的认知偏离。
虽然“频谱”这一词语,作为音乐种类的一个术语,第一次出现在西方音乐中,但其在音乐创作中所使用的技术并不是全新的。如频谱的加法合成技术(synthèse additive)或环形调制技术(modulation en anneau)等,早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施托克豪森在其所创作的作品中就已经多次使用和试验过了。本文无意在此对频谱音乐的创作技术及使用做过多的阐述和溯源,只是希望指明,缪哈伊所代表的频谱音乐创作理念,并不是板滞地追寻上文所提到的数字化合成(抑或是“具体音乐”)之思路发展下去,而是借助崭新的科技手段,在频谱的层面对声音进行解构,全然颠覆了传统音乐创作理念中以“组合”(combinatoire)或“叠置”(superposition)为核心方式的结构主义理念。也就是说,缪哈伊反对“序列”思维所带来的束缚和高度的控制,力图找寻新音色表达的更多可能性与更多丰富的空间,最终是为作曲家的想象力插上更为自由的翅膀,而绝不是对技术性操控的复杂性给予盲目的崇尚。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缪哈伊本人的相关论述:“……因此,一定程度的复杂化、对所有形态进行模型化设计和一些处理,会导致我们违背初衷,尤其是在(声音的)感知方面。换句话说,这种方法就像内里隐藏着一个自我毁灭的装置一样。但是,这(内在的毁灭性)对任何一个体系来说都是存在的。而我希望(我们的)这个方法能足够开放,能允许自我内部革新。只是我不想给它在实际层面上的发展做预判,因为我不想把自己置于立法者的位置上……它也不应该替无用的复杂化提供借口。”
确实,音乐是直接通过声音对人类审美智慧的艺术性表达,而后现代工业文明的高科技作为工具理性,在音乐创作的方法论层面上只能是对音乐审美感性表达的技术性提升,如果工具理性全面压倒了人类音乐本然的审美感性,其无疑会成为对作曲家审美想象力进行异化的颠覆性元素。而审美想象力的异化与否,依然需要通过最终的声响给予呈现,如此才能对作曲家们的胆识和智慧进行深度性的印证,否则与哗众不取宠的皇帝新装又有何异呢?无论怎样,人类音乐史行走至工具理性操控的后现代文化时期,脉动于频谱音乐中的高科技元素及后数码时代的技术逻辑思维,对源出于人性本然的音乐感性体验及其审美自由,究竟是异化了,还是合法化了?这是值得音乐学界展开讨论的话题。
作者 上海音乐学院博士后,南通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1. Richard Taruskin,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Music, volume 5,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478.
2. Anne Veitl, Politiques de la musique contemporaine, le compositeur, la ☒recherche musicale☒ et l’☒tat en France de 1958 à 1991, 1997, Editions l’Harmattan, p.63.
3. 这种发展路径不是断代的,而是以互相交织甚至互相融合的方式存在,但随着技术发展和进步,以往的交织混合会逐渐分流清晰。
4. Jean-Claude Risset, Composer le son : Repères d’une exploration du monde sonore numérique, Hermann ☒dition, 2014, p. 84.
5. 例如,频谱音乐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于格・杜付赫(Hugues Dufourt),他是法国的著名作曲家、音乐学家与哲学家。2014年,于格・杜付赫推出了自己的重要论著《频谱音乐:一种认识论的革命》(La musique spectrale : une révolution épistémologique)。这部著作是作者历经了探索、实践和总结之后,就频谱音乐对当代音乐创作理念产生的影响所进行的重新思考。
6. 其中的环形调制技术是施托克豪森较为喜爱的技术,尤其是他60年代的作品,如Kontakete, 和Hymnen等。
7. 本人在博士论文《特里斯坦・缪哈伊频谱音乐创作风格嬗变研究》中,通过对缪哈伊使用的频谱技术及其创作理念进行梳理和研究,认为其借助的计算机辅助系统创作只是为了获得更多声音探索的可能性,从而达到探索乐器的新音色表达。而其创作理念随着作曲家不断地写作、积累和再思考,也仍然会呈现出一些变化。例如,在为2006年创作的《城市的传奇》说明中,作曲家就曾提到要对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伟大配器”致以敬意。
8. Tristan Murail, Modèleset Artific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Strasbourg, 2004, 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