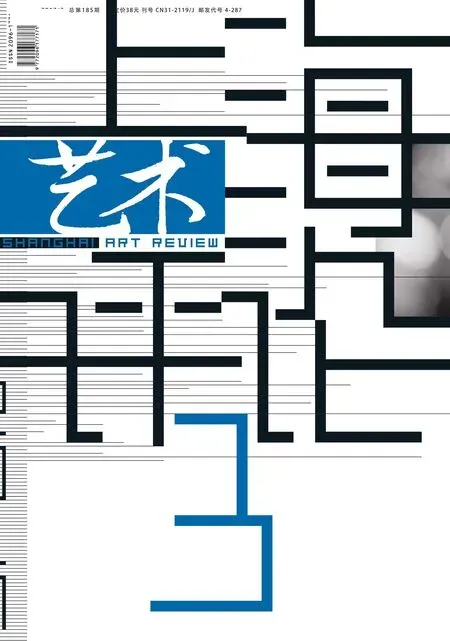“上海当代音乐周”九年回眸
李鹏程
“上海当代音乐周”九年回眸
李鹏程
中国当代音乐的艰辛发展历程本身就见证了自己的收获与荣耀,从当年个别作曲家离开本土走向西方,到现在北京、上海与武汉三个音乐节把最优秀的当代音乐资源引进来,其间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相信在上海当代音乐周这样的稳固平台上,会推出更多中国作曲家的优秀作品,而这项活动自身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国际化。在功能上,不仅仅是展现与储存当代声音的博物馆,更是孕育中国新一代作曲家及作品的重要基地。
惊雷:于无声处崛起的中国当代音乐
“于无声处”四个字出自鲁迅1934年写下的《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然而往事并不如烟,这四个字典出自鲁迅之手,却成为“文革”结束后中国文艺界唤醒民众的第一声呐喊。
1978年10月,上海工人作家宗福先创作了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并在《文汇报》以连载的形式刊出,随即这部话剧被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彩排,正式公演。也正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转捩点,《于无声处》所表达的思想全然冲破了长久以来政治高压的禁忌,把沉默的愤怒在积蓄的压抑中释放为一股爆发的力量,从而在思想界与文艺界产生了“惊雷”般的轰动效应;11月14日,《于无声处》剧组被请进北京再度公演,令人振奋的是,也就在同一天,北京市委通过了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12月18日至2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此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也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僵滞的思维中封闭已久的中国音乐人开始以惊奇的眼光看待与接受西方艺术思潮。无疑,那是一个第二次启蒙的年代:一批年轻的中国作曲家陆续远赴欧美学习西方现代音乐技术。
1995年,著名的荷兰电影导演菲利普斯(Eline Flipse)拍摄了一部弥足珍贵的纪录片《惊雷》(De oogst van de stilte,1995),以视觉记忆的影像摄录下初出茅庐的莫五平、陈其钢、谭盾与瞿小松,把他们在西方的习得音乐及完成他们作品创作的生活转码为影像记忆的历史。从《于无声处》到《惊雷》,鲁迅诗句的意涵通贯于这两部作品,宣告一个让人瞩目的中国当代艺术思潮的到来。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惊雷”是一个具有双重隐喻内涵的修辞,其不仅概述了中国作曲家初识西方现代音乐所获取的心灵震撼,同时,也指涉了西方音乐人对中国第五代作曲家崛起的惊叹。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国际乐坛呈现了多种形式的现代音乐节,毋庸讳言,这些现代音乐节对国际新音乐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二战”后,德国的达姆施塔特现代音乐暑期班曾将序列音乐推向了至尊的地位,而“华沙之秋现代国际音乐节”(Warsaw Autumn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更是催生了享誉国际乐坛之“波兰乐派”(Polish school)的崛起。欧美所成功举办的一系列现代音乐节,也启蒙且激发了中国作曲家迫切建立自己的现代音乐之“根据地”的渴望,时值2004年,中央音乐学院率先发起与举办了“北京现代音乐节” (Beijing Modern Festival),2007年,武汉音乐学院随后举办了“武汉国际新音乐节” (Wuhan International New Music Festival),而上海本然就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上海亟需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现代音乐节。
2008年,也正是《于无声处》呈献于舞台三十年之后,依然是在金秋十月,上海音乐学院隆重地举办了第一届上海当代音乐周,并且提出了“没有当代,就没有未来”(No Today, No Future)的口号,上海当代音乐周在第一次崛起时即为国际乐坛所瞩目,而首届上海当代音乐周(New Music Week)的倡导者与推动者是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杨立青教授。
杨立青是在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走出国门并将西方现代音乐介绍到国内的作曲家。2007年3月,在杨立青的召唤下,旅居海外多年的作曲家温德青来到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温德青回国后即把自己的全部热情与精力投入于现代音乐的教学与创作,2007年,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开设了“现代音乐演唱演奏课”,在这个课堂上,经由古典音乐体系训练出来的青年乐者,学会了五花八门的现代演奏法,他们通过一系列汇报音乐会“现学现卖”,促使多部中外当代作品在中国大陆首演,可以说,那就是当代音乐周的雏形。
值得提及的是,温德青此时为孕育中的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设立了自觉的理论目标:“音乐周的目的在于宣传与保护当代具有前沿性和实验性的新作品,展示新音乐的新成果。让国际上最新的音乐、最新的著名的大师级的作品与上海的听众直接见面,让我们共享人类创造的新文明,也让本院作曲家的新作品直接面对听众。”可以说,当代音乐是在学院派体制的教学与创作中所接受及前行的。
第一届上海当代音乐周是精彩且成功的,其推出了7场音乐会、7场讲座、4场大师班、1场研讨会与1个视频装置。可以见出,当代音乐周在建立伊始便形成了“三位一体”建制:以音乐会、讲座、大师班为基础,以驻节作曲家为中心。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第一届上海当代音乐周,唯一获取尊荣的驻节作曲家是第五代作曲家代表之一:瞿小松,他也是中央音乐学院77级作曲家群体中的年长者。
在第一届上海当代音乐周成功举办之后,第二届音乐周在音乐观念的细微修辞表达上调整了自己的口号:“有了当代,就有未来。”第二届音乐周及其口号不仅在自觉的音乐观念上透露出更为蓬勃的学院派气象,同时,还表达了音乐周不仅仅限于把自己营造为一个当代艺术博物馆,而是力图把自己筑构为一方培育当代音乐新生力量的创意性平台。可以说,无论是职业音乐人,还是大众爱乐者,他们对当代音乐周的创办与持续性前行,投诸了渴望已久的期待与信任。除了上海音乐学院各系部及其师生以极为炽热的专业激情给予行动上的支持,“胡景敏当代音乐基金”也开始资助音乐周的活动,一如温德青所陈述的那样,若不是这些援手及时相助,“‘当代音乐周’只能改名为‘当代乌托邦周’。”
转型:从学院派当代音乐走向民间音乐传统
中国作曲家在20世纪断断续续学习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之后,他们逐渐认识到传统和当代多元文化对于自我音乐语言塑造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来反思一下第三届上海当代音乐周的口号。在音乐发展史的观念上,不同于第一、二届上海当代音乐周,第三届上海当代音乐周毫不犹豫地把曾投向未来的目光链接到传统的历程上去,从而在音乐发展史的完整逻辑上提出:“传统带来当代,当代揭示未来”。
在第三届上海当代音乐周,其开幕音乐会以“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之命题深度诠释了这一口号承载的主旨。我们注意到,六部作品两两一对分为三组:浙江昆曲十番《闹花台》和徐孟东据此创作的《相生·弦管之乐》;湖北锣鼓《茅草开花扯不齐》《五句子》和叶国辉的《徒歌II》;蒙古呼麦《四季》和许舒亚的《草原晨曦》。这一自觉的创意理念在另外两场音乐会中也给予了准确的出场。
“贾达群昆曲风新歌剧——音乐会版《梦蝶》”是一部具争议性的实验性作品,其在融合中西音乐体裁的汇通性观念上给出了深度的尝试,作者通过中西混合的乐器编制、动机贯穿、音色音乐与支声复调混合、多种和声体系,从而打造了“强烈昆曲风格的、具有一定独立意义的室内化音乐戏剧”“上音作曲家民乐新作首演专场音乐会”汇集了上海音乐学院八位作曲家的新作品,其中七部是音乐周的委约作品。
尤为值得提及的是朱世瑞的《水想II》,这部作品是为古筝和二胡两件乐器而作。作者把自己在这部作品中所呈现的乐思探源于道家哲学的形上意境,让乐思的灵感在心斋玄览的审美体验中叙述着老子“上善若水”的思想,作品的在场风格于看似单纯的表现形式中流动出极为丰富的变化。
让人振奋的是,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为国际当代乐者所提供的舞台绝然不是一个在音乐观念上求取守成的空间,我们注意到,主办方始终在理性地调整每一届音乐周的口号。
第四届上海当代音乐周的口号是“当代汇集多元,多元丰富当代”。这个口号的提出,我们可以看到主办方在应时调整自己的美学立场,把音乐周的空间向当代大众文化景观延展,以更为敞开的姿态接受那些既非先锋亦非传统的乐者及其作品加盟。显而易见,上海当代音乐周的审美定位在观念上发生着悄然的转型,从第四届开始,学院派创作之外的多元艺术形式也逐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众所周知,世界音乐以其丰富的民族性与地域性文化特征对当代音乐创作产生了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上海当代音乐周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文化现象,于2011年9月26日,尼泊尔唱咏者琼英·卓玛(Ani Choying Drolma)的“心与灵——梵呗与古琴音乐会”受到邀请加盟了音乐周。琼英·卓玛的这场音乐会以古涩且神秘的音响风格营造了一种原始宗教的音乐氛围,作者以音乐的沉静律动去探求生命在原始生态中创生的洪荒感,古琴、萧、鼓轻柔地应和着,一脉天籁般的声音已然超越当代的疆域达向了史前的自然。
第四届上海当代音乐周的闭幕式是“肢体与表现——金星现代舞作品专场”,当然其所涉的音乐既有当下温德青的《一石二鸟》之首演,又有古老的琴歌《归去来辞》,音乐语言与舞蹈的肢体语言在自由的碰撞相互对话,其表达了音乐与舞蹈在跨界的交集中所尽显多元融合的无限可能性。
其后几届上海当代音乐周所呈现的音乐会更以其特色性风格持续抓取着爱乐者的眼球。2012年,图瓦的另类歌者珊寇(Sainkho Namtchylak)即兴喉音演唱,吴巍的笙和马头琴、李劲松的电子调音台,三个在时空上原本相距遥远的声音奇妙地并置为一体。
2013年,周云蓬的民谣专场音乐会出现在当代音乐周是出人意料的,毕竟中国的学院派音乐对民谣歌手一向是充耳不闻,然而这位拥有众多歌迷的盲人歌手的确属于中国当代音乐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他甚至一度成为了中国当代民谣和诗歌的新生代代表人物。
同届还有一位由主办方邀来的颇具争议的跨界人物,他就是画家陈丹青。陈丹青以画家的身份跻进音乐舞台,然而他的讲演并未局限在“我画画时为什么要听音乐”这个讲题上,而是以上海人特有的嘲讽口吻,将青歌赛、超女、艺术市场及连带前一天听到的学院派音乐挨个儿调侃了一番。我不愿意评论上海音乐周是否应该接纳陈丹青出场,只是他那些不懂音乐的外行调侃,着实让音乐周因为局外人的出场多了一点开放的气氛。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当代音乐周在其所摄取的乐者与作品中,除了那些显而易见可以在准确的学院派“当代音乐”定义下呈现的作家作品,主办方还大胆地跨出了学院派所囿于成见的音乐观念,在极为接地气的选择上走向了民间。我们注意到,2014年,当代音乐周接纳了台湾布农族的“八部合音”;2016年,又引入了陕北盲人说唱艺人张成祥的专场音乐会等。当代音乐周秉有一种接纳多元音乐现象的敞开审美心态,其无不真切地呈现了在世界各族群与不同区域延续至当代的传统声音及其审美文化的存在方式。上海音乐周所持有音乐美学立场,在本质上彰显为一种开放的实验性姿态:探索未来的声音,必然要打破学院与民间、严肃与流行、创作与即兴、传统与当代之间的壁垒。无疑,上海当代音乐周已然做到了这一点。当然,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及其后殖民批评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所抨击的“杂混”(hybridity)现象,其也成为当代音乐周所不可抹却的另类标致。
成熟:推动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及批评的发展
除了上述多元艺术现象的杂混与交集,在过去九年的跋涉历程中,上海当代音乐周凭藉敞开且多面相的音乐美学观念,实现了自己的初衷,即“宣传和保护当代新作品”。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这种敞开且多面相的音乐美学观念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定义“当代音乐”的本质。这无疑是存在于当代音乐与当代音乐周之间的一个不可调和的悖论。无论怎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每年一周的国际性音乐活动,在文艺思潮的扩展性效应上,务实地推动了上海乃至中国的当代音乐的创作与表演,同时,也涉及了中国当代音乐如何推向市场的商业机制问题,最终,中国当代音乐评论之水平低下的问题也因当代音乐在北京、上海与武汉三地的繁荣而反差了出来。因此,呼唤着更为专业且被大众爱乐者所能够接受的中国当代音乐评论,其也成为当下乐界所热切关注的问题。
还一个现象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每届驻节作曲家中的华人面孔是最大的看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新潮音乐”的代表群体是让我们无法忘却的,他们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77级的瞿小松、郭文景、谭盾、叶小纲、陈其钢、陈怡与周龙。上述“新潮音乐”的代表人物曾被上海当代音乐周依次邀请,他们都以音乐会与专场讲座的方式给予了热情的参与,纪录片《惊雷》中的四位在世作曲家悉数到场,令人遗憾的是若非莫五平英年早逝,想必他也会被邀请加盟其中。
当两代中国作曲家在同一音乐周各自以自己的专场形式呈现时,其不同的音乐观念及风格给听者带来的历史感显得尤为鲜明。例如2009年,杨立青和郭文景作为中国第四代和第五代作曲家的代表,在连续上演的音乐会中凸显出各自的代际美学特征。
杨立青的专场音乐会上演了其跨度近50年的作品:从《九首山西民歌主题钢琴曲牧羊歌》(1961)到《唐诗四首》(1982),再到《三重奏》(2009),随着作曲家身处时代和地域的变化,其音乐作品表现观念及其风格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其可谓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一个缩影。
郭文景的专场音乐会上演作品的跨度也有20余年:从学生时代的习作《巴》(大提琴与钢琴,1982)到《戏》(为三对铙钹而作,1996)、《狂人日记组曲》(1997)以及三重奏《炫》(为六面京锣而作,2003),这些作品在表现风格上无论是戏谑抑或疯癫,无论其音乐技法是如何嬗变,郭文景生为巴蜀汉子身上的血性已恒久地驻留在这些作品中。
再如2013年,历届驻节作曲家中年龄最大的罗忠镕和年龄最小的秦文琛登上同一舞台,前者以“五声性十二音集合”引领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中国化,后者则以极富想象力的“长线条宽旋律”享誉世界乐坛。两人皆是在上海习得现代音乐技法、在北京形成独具个性的创作语言,尽管两者作品音响风格相距甚远,但他们的创作都根植于山水情怀与诗情画意。
此外,音乐周每年委约项目也催生了诸多新作,当然,其中能够真正流传为经典的不多,然而每届哪怕只有一部,也是其重要价值所在。值得注意的是,被青年乐者戏称为上音作曲系“四大金刚”的叶国辉、温德青、陆培与陈牧声多次集体创作,他们推出了《辛亥交响》(2011)、《交响牡丹亭——天地人和》(2013)、《交响上海》(2015)等紧贴时代主旋律的交响乐,在此不论及作品本身的优劣,近年来,这种集体创作的形式在上音作曲家群体中屡见不鲜,难免令人想起上个世纪红色艺术经典的诞生历程,对于重在追求个性的当代艺术创作来说,当代音乐批评界究竟应该给出怎样的评价?
上海当代音乐周的另一大功绩是上演了一系列广受赞誉的西方现代作曲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即便不作为标杆,我们至少现场感受了同时代最具创意的音乐杰作。最难以让人忘却的是2010年上海当代音乐周,法国频谱音乐(La musique spectrale)代表人物缪哈伊(Tristan Murail)向中国乐界介绍了频谱作曲的基本方法和最新软件,其专场音乐会完美地诠释了法式音色在当代是如何过滤与升华的。
在2011年上海当代音乐周,英国新复杂主义(new complexity)作曲家芬尼豪(Brian Ferneyhough)的专场音乐会展现了如魔法般繁复至极的缠绕音响,其赢得了在场听众的争论和赞叹。在2012年上海当代音乐周,古拜杜丽娜(So fi a Gubaidulina)在琴弦上展现的神圣与世俗的挣扎,克拉姆(George Crumb)让全场听众深陷神秘的幻境;当然我们也难以忘却2014年和2016年的音乐周,两次利盖蒂(GyorgyLigeti)的专场音乐会引导爱乐的受众踏上充满惊险的新音乐探索之旅……
毫无疑问,呈献这些杰作的是蜚声当代国际乐坛的一流新音乐演奏家,并且这些投身于现代音乐的新音乐团也以他们的精彩演出,一次次引发全场的喝彩。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11年9月29日,荷兰新音乐团(Nieuw Ensemble)特意将莫五平的 《凡II》(1992)作为音乐会的压轴作品,演出结束后,乐团负责人歇尔·邦斯(Joel Bons)起身回忆了乐团与那批海外中国作曲家之间的友谊,当天他还佩戴着莫五平送给他的领带,歇尔·邦斯深情款款的回忆让在场人无不唏嘘感怀。在当晚的节目册上还刊印着1991年莫五平、谭盾、何训田、瞿小松和郭文景五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骑着自行车的照片,而拍摄者正是歇尔·邦斯,这场跨国界与跨世纪的音乐情谊在此被深深地纪念。
更重要的是,历经耳濡目染,中国演奏家对于现代音乐的热情也被激发出来。意义非凡的是2013年,在此届音乐周上亮相的“上海小交响乐团”填补了国内缺乏小交响乐团的空白,这种在20世纪初应运而生的乐队编制对于现代音乐会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遗憾的是“上海小交响乐团”仅仅是昙花一现的亮相,如今的舞台上竟再难觅到他的身影。毋庸置疑,在九届上海当代音乐周的舞台上,我们不仅见证了王之炅、谢亚双子、唐瑾与张倩渊等优秀青年演奏家的成长,也看到上海爱乐乐团与上海交响乐团等学院外的专业乐团受到吸引,开始加盟其中;无疑,这些独立乐团的参与推动了上海这个具有百年交响乐历史的国际大都市不断地更新音乐会的曲目库,从而培育出更多的本土音乐作品。
除主题音乐会之外,上海当代音乐周自2009年设立了两个看似不起眼而实则影响深远的板块。
一个板块是“国际学生作品音乐会”,主要是接纳来自不同国家学习作曲专业学生的创作作品,同时,主办方也邀请驻节作曲家给予现场评点。可以说,这种现场评点成为了音乐周一个极为闪光的亮点。一方面,青年作曲家们可以从中获取丰富的经验和启示;另一方面,因不同文化背景的作曲家持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从而折射出当代音乐创作与批评的多元审美风格及特征。
另一个板块是“中国当代音乐作品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在次年发展且成熟为“中国当代音乐评论比赛”。令人振奋的是,这个板块近年来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青年乐评者踊跃投稿参加,主办方专门为入围参加决赛的作者提供当场宣讲与辩论的平台。然而,客观地讲,参与这个板块的乐评质量并不尽如人意,因此持续举办了七届的评论比赛在2016年不得不中止,更名为“乐评高峰论坛”,为此主办方请来了杨燕迪、周海宏、韩锺恩三位音乐学教授坐而论道,希望能够提升这个板块的学术品质。该板块的一系列尝试性活动与转型,或许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内当代音乐评论的孱弱和荒凉景象,当至少促使了一批音乐学者对同时代新音乐投去关注的目光。
中国当代音乐的艰辛发展历程本身就见证了自己的收获与荣耀,从当年中国个别作曲家离开本土走向西方,到现在北京、上海与武汉的三个音乐节把最为优秀的当代音乐资源引进来,其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相信在上海当代音乐周这样的稳固平台上,会推出更多中国作曲家更优秀的新作品,而这项活动自身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国际化,在功能上,其不仅仅是展现与储存当代声音的博物馆,也更是孕育中国新一代作曲家及作品的重要基地。
对于我们当代音乐人来说,上海当代音乐周的意义何在?虽然其历史不像西方各大现代音乐节那样悠久,却扎实地印刻下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音乐的走向及其一个个不可磨灭的足迹;虽然上海当代音乐周的规模不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Shanghai Spring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那般庞大,却依然持续性地吸引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爱乐者集结于这方空间,他们每年一度在这里,以领受当代音乐的洗礼。虽然上海当代音乐周的历届主办者凭借着作曲家的情怀和理想,以自己的实验性行动召唤着越来越多的爱乐者。也正是在遭遇、聆听、体验与见证上海当代音乐周的每一个场景中,我们的音乐观念及其美学属灵在当代音乐的介入性体验中升华为我们这一代音乐人的哲学思考。
作者 上海音乐学院博士
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