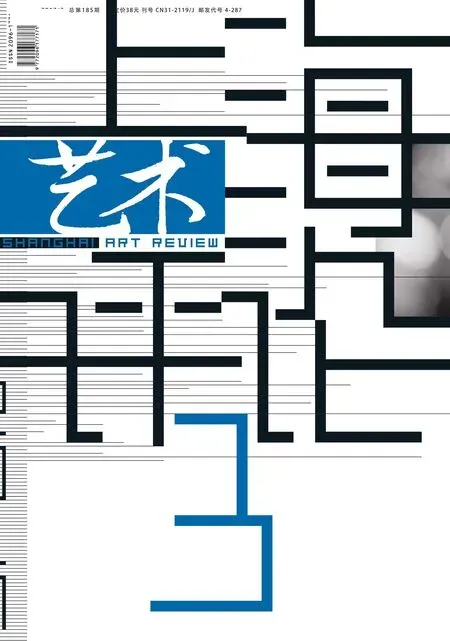新音乐崛起的繁盛与当代音乐评论的贫困
杨乃乔
新音乐崛起的繁盛与当代音乐评论的贫困
杨乃乔
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一次偶然的跨界思考中,对新音乐的书写却成为专业音乐学研究者的必读之书,新音乐哲学家也成为被尊重的首席身份。而我想表达的是,新音乐在中国当代乐坛崛起得如此繁盛,当代中国的专业音乐学研究者又有什么理由容忍当代音乐评论依然处在不对等的贫困状态?当然,音乐评论需要哲学的深度性思考,这也对当下的专业音乐评论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概念的系谱诠释:现代音乐、新音乐与当代音乐
从21世纪元年至2016年,以学院体制为代表的中国新音乐在观念与思潮的先锋性求取上崛起得相当前卫,且迅速取得了空前未有的发展。这种前卫的新音乐姿态以三个国际性音乐活动的连续性盛大举办为标志,让当代中国学院派音乐人投以无尽的瞩目和热情的参与:2004年,中央音乐学院率先发起了北京现代音乐节(Beijing Modern Festival);2007年,武汉音乐学院随后配合举办了武汉国际新音 乐 节(Wuhan International New Music Festival);2008年,上海音乐学院再度跟进推出了上海当代音乐周(Shanghai New Music Week)。在接近12年短暂的时间线性逻辑上,这三个盛大的国际性音乐活动在北京、武汉与上海隆重推出,特别是中央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以每年一届的节奏连续性举办,再加之国内与国际一流的新音乐人及其作品在此三方平台上的密集性出场(presence),如此繁盛的气象宣告了当代中国新音乐时代的彻底到来。
在准确的学理上,我们从一个概念的操用即可以透视出其外延与内涵所涵盖的形上逻辑与形下现象。我们注意到,中央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各自操用了三个不同的概念,先后命名自己所举办的国际性音乐活动:现代音乐(节)、新音乐(节)与当代音乐(周)。这三个操用不同汉字书写的概念,无疑,是应该引起音乐批评与音乐理论界给予思考的。其实,我们只要聚焦与反思上述三个国际性音乐活动的音乐美学本质,对其在12年内所邀约的音乐家及其曲目做一个归总性的分析,不难发现,上述三个不同的汉字译入语概念所指称的是在同一种音乐观念下所出场的音乐现象,从理论上界定,其在共通的音乐观念本质上所指称的就是“新音乐”——“New Music”。在艺术评论的场域中,我们必须要注意对书写为不同文字符号的概念进行同义替换,以便在复杂的书写概念(concept)中求取一个统一的学理逻辑,否则,会让自己淹没在复杂的术语(term)表述中不知所措。
需要提及的,这三个国际性音乐活动是在学院体制下发起与创办的,绝然不是源起于民间大众的商业性通俗音乐活动,所以它们都有着自己的理论宣言。在此,我不再就其理论宣言给予一一的概述,然而,圈子内的音乐家、音乐批评家与音乐理论家,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对这三个国际性音乐活动有组织、有纲领秉持的新音乐观念在美学的本质上应该获有不可置疑的共识。
但是在这里,我还是要给出一个必要与简要的概念系谱诠释。乐界皆知,新维也纳乐派的三位主将是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韦勃恩(Anton von Webern,1883-1945) 与 贝 尔 格(Alban Berg,1885-1935),他们主要生活在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推进时期。我注意到,在《新音乐哲学》(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一 书 中, 阿 多 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是启用新音乐这个概念以指称上述三位反传统的无调性音乐家之身份,因此,在阿多诺那里,现代音乐指涉的就是新音乐,这也是中央音乐学院为什么把其举办的国际性音乐活动冠名为“北京现代音乐节”的学理缘由。
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上海音乐学院把汉语书写的“当代音乐周”翻译为英语书写的“New Music Week”,在学理上,其已经表达了主办方举办的当代音乐周在音乐观念的本质上隶属“New Music”的立场。客观地评判,这个翻译是非常专业且智慧的,其既宣示了上海音乐学院举办这一国际性新音乐活动所持有的音乐观念之美学立场,同时,也在汉字概念的修辞表达上回避了与武汉国际新音乐节的撞车。当然,我不知道最初在创办上海当代音乐周时,杨立青及其同仁在策划上启用“当代音乐周”与“New Music Week”的择取中,在思考的先后逻辑上,哪一个是源语概念,哪一个是译入语概念?这一点很重要!因此,我们一再强调,在此三方特定的国际性音乐活动语境下,我们操用“现代音乐”与“当代音乐”这两个概念时,其外延与内涵所指涉的就是“新音乐”。
在这12年特定的新音乐时代景观下,这里的现代音乐与当代音乐已经不再是指称音乐史教科书上所厘定的那种断代音乐史的概念,而是言指曾经历过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与后现代主义工业文明洗礼,所发生与延展的先锋性音乐观念——新音乐。当然,这种先锋性的音乐观念必然是通过具体的乐者所呈现的一部部作品,如果我们究其音乐美学的本质特征,那就是多元性(multiplicity)、实验性(experimentality)、前卫性(avant-garde)及其不确定性(nondeterminacy)。所以这里的“现代音乐”与“当代音乐”作为特定的合法性能指(signi fi er),其所指(signi fi ed)就是“新音乐”这个概念所负载的全部音乐美学意义。因此,我特别提醒读者注意这三个概念在此次笔谈中的交集性使用。
其实,关于新音乐及其观念先锋性的创作技术与表现风格,我们从这三个国际性音乐活动繁盛的曲目及反传统音乐的音响效果中瞬间就可以捕捉完毕。在音乐观念的美学本质上厘定这三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是在音乐批评与音乐理论上为这三个盛大的国际性音乐活动进行定位,其目的是为了整一性地讨论与界定它们所属的新音乐美学本质。
北京现代音乐节、武汉新音乐节与上海当代音乐周三足鼎立,在深度上推动了国际新音乐及其美学观念在中国汉语本土的发展,一批优秀的汉语乐者先后受邀,以极大的热情成功地参与其中,我们来看视以下的参与者强大阵容:罗忠镕、谭盾、杨立青、叶小纲、陈其钢、赵季平、关峡、郭文景、秦文琛、瞿小松、周文中、陈怡、周龙、温德青、许舒亚、何训田、贾达群与叶国辉等;除此之外,我不再一一列举受邀而来的那些优秀的国外当代音乐家。的确,由于在中国举办以及中外当代音乐家的推动性参与,这项活动已经成为被全球当代音乐家所瞩目的国际性新音乐事件了。当然,这与当下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大国崛起的世界性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较之于新音乐及其观念在中国当代音乐界崛起的显赫气象,中国本土的新音乐评论却尴尬地处在极为贫困的态势下,呈现出与新音乐活动繁盛气象的严重脱节。
在这里,让我操用“当代音乐”这个概念给出一个替换的表达,中国当代音乐批评与当代音乐理论是极为贫困的,基本上还处在学术真空的状态。需要提醒学界的是,我在这里言指的是学院派当代音乐创作、当代音乐批评与当代音乐理论。最近,我翻阅了多篇关于“描述”汉语本土当代音乐活动的文章,其作者都是生存在学院体制下的音乐学研究者,的确,较之于当代音乐活动的繁盛气象,这些文章在学理上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苍白的,匮乏批评的敏锐性与研究的理论深度,令人失望。这些为数不多的文章完全是滞留在表象上,对驻节音乐家及其作品给出平面性的“描述”,书写者全然无法据守音乐哲学、音乐美学与音乐理论等高度,对出场于汉语本土的新音乐活动及其作家作品进行深度且前沿的学理性分析与研究。准确地讲,这种平面性“描述”的文章在任何名义上都不应该被认定为是有效的当代音乐研究,因为学界无法从中提取多少启示性的理论元素,所以这些当代音乐批评的文章也无法对更加贫困的当代音乐理论体系构建给予补缺。
毋庸置疑,当代音乐——新音乐以其敞开的国际性姿态在当代中国乐坛的崛起是繁盛且显赫的,递进一步陈述,我之所以给出这样一个价值判断,也更是把崛起的新音乐——当代音乐投射在当代中国整体的艺术门类创作景观下给予首肯的。我在这里言指的整体艺术门类,其包括音乐、美术、舞蹈、戏剧与电影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在这里,我们不妨引入另外一种艺术门类作为参照系——中国当代美术,就中国当代音乐与中国当代美术给出一个比较研究。其目的是在空前崛起的中国当代美术创作及其批评、理论的参照背景下,我们可以清晰看视到新音乐——当代音乐处在一个怎样前卫的当代中国艺术地图的位置上。
我在这里之所以引入中国当代美术作为评价中国当代音乐的参照系,在宏观意识上,从事艺术批评与艺术理论的学者皆知,中国当代美术在创作观念与评论思潮的先锋性上是走在国际美术界最前沿的。在这里,还是让我首先从清理概念的逻辑谱系以展开以下的比较性思考。
当代艺术与当代音乐对学院体制的差异性态度
需要申明的是,我在这里所言指的中国当代美术,一定不是美术史教科书上的断代史概念,而是言指当下在国际美术界普遍称谓的“当代艺术”——“contemporary art”。我有必要在此强调这一点。
在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以来的传统艺术观念进行抵抗与解构的激进上,新音乐与当代艺术这两个术语,是在激进的艺术观念上对传统艺术观念进行反动的共谋概念(concept of collusion)。注意:在这里,我绝然不是就一组术语或概念的逻辑推导在玩弄能指游戏(game of signi fi er),因为如果不为这些术语或概念在理论系谱上做一个明晰的逻辑清理,一定会导致缺憾理论功底的艺术现象描述者跌入无尽的困惑中,且无以自解。
也就是说,在音乐与美术两种姊妹艺术的交集场域中,新音乐与当代艺术是一对在激进的艺术观念上共谋的先锋性概念,或我们也可以如此对应地组合这两个概念:当代音乐与当代艺术。我再三强调,这里的“当代艺术”是一个专用术语,作为一个能指,其所指是当代国际美术界在观念上对传统架上绘画(easel painting)进行激进反动的诸种视觉艺术现象,如行为艺术、装置艺术、新媒体艺术等。
当下是一个后现代高科技工业文明与后数码高科技编程打造的融媒体(convergence media)时代,所有的信息都网络化与全球化了。在这个时代,任何学者已经没有理由仅仅把自己的知识结构囿于一个孤独且狭隘的单一学科向度上,相关学科之间的多元知识性汇通已成为当代学者在全球化时代学界行走的通行证。
倘若,一位乐者与音乐研究者了解同期国际美术界正在行动的前卫知识信息,一位画者与美术研究者也了解同期国际音乐界正在行动的先锋知识信息,我们告诉他们:在当代崛起的激进艺术美学观念中,新音乐相当于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就相当于当代音乐;那么,无论是音乐研究者还是美术研究者,他们可以澄明且通透地看视一个时代在共通的哲学思潮或美学思潮影响下同频共振的那些艺术行动。的确,当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崛起后,在其崛起与后续发展的历史踪迹中,音乐、美术、舞蹈、戏剧与电影等诸种门类艺术表现形式均受其影响,在现代派哲学思潮的浸润下,他们以各自不同的审美形式本体呈现为多元的现代派艺术的先锋现象,不要说文学了。
我们认定:当代音乐界的新音乐就相当于当代美术界的当代艺术。在艺术观念的共谋性本质及其学理上,我们已经把话说到底了。然而关于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我在这里还是要谈一些的,因为,我的目的是为了澄明新音乐——当代音乐的新贵族品质。
毋庸讳言,当代艺术现下正在当代中国美术界持续性地发酵,并且波及了国际美术界,已经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先锋性潮流。然而,其中鱼龙混杂,当代艺术在品质上所积累的负面影响也是众所周知的,在某种评价的程度上,当代艺术以其极具争议性的商业性与伦理性而名声扫地。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在乱象杂生的当代艺术中,也存在着于艺术观念上极具突破性、创意性且不可复制的优秀作品。而当代音乐全然不是如此,其同样持有激进的反传统艺术观念,而新音乐却表现出自身的新贵族品质。
以下让我从几个维度来简约地透析当代音乐与当代艺术两者之间的共谋性与差异性。
如上述我所提及的,面对传统艺术观念的守成,当代音乐与当代艺术在骨子里均释放出一种激进主义(radicalism)的反叛情绪。
就西方美术史而言,如一揽子统摄在现代主义思潮下的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野兽画派(fauvism)与立体主义(cubism)等等,无论他们是怎样地对古典主义画派进行反动,其还是在架上绘画的较量;而崛起的当代艺术在对传统美术观念的颠覆上,则端起一种极为嚣张的激进姿态,他们甚至把现代派的架上绘画也打入了地狱。
在此,我不再涉及当代艺术在欧美崛起之际所释放的那些偏激观念的表达,仅在北京的798艺术区、宋庄画家村、环铁艺术区等,我与那些汉语本土一线的当代艺术家交谈时,他们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就是:“这个年头谁还画画!”其实,究其学历与学缘,他们本科几乎都毕业于美术学院油画系、国画系、版画系与雕塑系等,而当下他们都背叛了架上绘画,玩的都是行为、装置与新媒体艺术什么的。当然,其中他们也有画画的,我操用另外一个相关的术语来指称他们作品,即类似美国当代艺术策展人玛西娅·塔克(Marcia Tucker)所指称的“坏”画——“Bad”Painting。他们显然没有人愿意模仿与重复逝去的徐悲鸿等与当下的靳尚宜等老一辈画家的传统绘画观念,他们不愿意瑟缩在传统美术观念的巨大阴影下苟活。
因此,当代艺术与现下美术学院的教学体制及其所守护的传统美术观念充满了不可协调的冲突,以激进的反潮流姿态抵抗学院体制及其守成的艺术观念是当代艺术行动者为自身张贴的时代标签。所以只要提及当代艺术,靳尚宜、邵大箴等老一辈画家与美术史论家就忧心忡忡,且充满了无尽的焦虑与莫名的紧张。需要提及的是,我这里无意详述当代中国美术界的那些人与那些事,我仅仅是把当代艺术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系和透镜,跨界地透视当代音乐的美学品质。
非常值得学界深思的是,当代音乐——新音乐恰恰是生发在学院体制下的一脉激进主义的艺术思潮。2017年1月4日,我在汉堡拜访了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的故居,在故居的二楼,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弹奏了勃拉姆斯的那架古旧的三角钢琴,那位守护故居的音乐老人告诉我,勃拉姆斯的浪漫主义音乐在结构上承继与发展了贝多芬,因此才有了勃拉姆斯。当代音乐对巴赫、海顿、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古典主义及其之后的浪漫主义、印象主义与表现主义音乐观念进行反动,在反传统艺术观念的激进上,当代音乐与当代艺术如出一辙,而在一定的程度上,新音乐人在音乐的观念、结构与音色等元素方面,他们不希望对任何前辈音乐大师有什么承继,只求另类与全新的自我发展,否则永远没有他们自己。因此,我反复提及在颠覆传统艺术观念的激进上,当代音乐与当代艺术是一对共谋的概念。
但是我特别注意到,北京现代音乐节,武汉新音乐节与上海音乐周是在三所音乐学院的体制支持下举办的,并且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北京现代音乐节,还得到了教育部与文化部的支持。那么,为什么学院体制对当代音乐与当代艺术表现出两种截然差异性的接受与拒绝的态度?提出与回答这个问题都是令人深思的。
有一点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不少介入当代艺术的行为者不屑一顾地扬言“这个年头谁还画画!”的确,在相当任性的程度上,他们以激进的艺术观念以抛弃架上绘画为己任,因此,行为艺术、装置艺术与新媒体艺术等必然成为当代艺术人的主打表现形式;而非常有意思的是,新音乐人玩的还是音乐,当代音乐人以激进的艺术观念在反传统中追求另类的音响出场形式时,他们并没有把音乐彻底抛弃。我们只需归总三所音乐学院举办的新音乐活动之全部曲目,且对其做一个总体性的分析,在现场听一下,或者网络上看一下现场录像,即可以显而易见地视听到这一点。遗憾的是,由于字数的限制,我在这里无法对近二十年来在当代音乐与当代艺术之名义下创作的诸类作品,进行全面的概述与比较性分析,以此展开地讨论这两类现象。当代音乐与当代艺术是在一种不期而遇的共谋中张扬激进的艺术观念,那么,为什么当代音乐可以获得音乐学院的体制性支持,而当代艺术却遭遇了美术学院的体制性拒绝?其隐匿在背后的学术政治及其审美意识形态又是怎样的呢?这是值得学界讨论的。
音乐的本质主义立场与对绘画本质的颠覆
我个人认为,作为后来者的艺术家永远是不幸的,尤其是对音乐与美术而言。因为,在人类业已逝去的历史上,那些最为辉煌且完美的艺术表现形式,已经被过去的历代艺术大师发现完毕与占用完毕,使后来的从艺者全然遮蔽在前辈大师的阴影下而黯然失色。前辈艺术大师的辉煌必然是遮蔽后来从艺者的高大阴影,几乎全部后来的从艺者在创作风格与美学观念上的唯一选择,只能是模仿与重复前者。艺术不同于科学,先行艺术大师行走且留下的足迹永远是后来从艺者阅读的墓志铭,这种残酷导源于人类艺术最为本质的一个特性:艺术家其作品的尊严即在于——他个人的美学风格及其不可模仿且不可重复的内容与形式。的确,艺术的模仿与重复标志着从艺者的彻底失败。
艺术是唯一性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当代音乐与当代艺术为什么持有一种激进的另类艺术观念,且不可遏制地彰显出企图颠覆与解构传统艺术观念的野心。他们从不甘心情愿地遮蔽在传统艺术观念的辉煌阴影下,无尽且无能地模仿与重复前人,他们向死而生,伺机奋起,在压抑与绝望中为自己寻找崭新的艺术观念之出场的内容与形式,以追寻自己另类的表现风格,力图让自己出类拔萃于庸常艺术家生存的境遇。说高了,这是他们的一种生存方式;说低了,这也是他们无法逾越经典而另辟蹊径的不得已而为之。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非常功利性的。因此,无论是当代音乐还是当代艺术,为了达向这样一种功利性目的,其作品人为“做”的痕迹是非常严重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其艺术本然的自然审美全然消失了。当然,这是另一个可以接续讨论下去的话题。
问题在于,同样嚣张于反传统艺术观念的激进中,当代音乐在形式本体论上不是反音乐本质的,这一点是我肯定的。约翰·米尔顿·凯奇(John Milton Cage Jr)于1952年推出了他的偶然音乐(aleatoricmusic)作品《4分33秒》(4′33″),即便如此,他也是在追求一种蓄意的声音缺席——“the absence of deliberate sound”,也是在静默中让现场观众依凭自己的审美诠释,以获取自身内心与内视的音乐想象。中国学界习惯操用东方道家哲学家的美学范畴“大音希声”去理解与解释《4分33秒》,从这部作品创意观念的美学本质上来看,无论怎样“希声”,还是在静默的审美心态中求取一个内在想象的“大音”,因此音乐没有被消解,而是拓展出一方由参与者多元想象音乐出场的自由空间。其实,我们把《4分33秒》定义为行为艺术也未尝不可。
韦伯恩(Anton von Webern)是新维也纳乐派的代表人物,在颠覆传统音乐的结构与音色等趋向上,他的点描主义(pointillism)音乐把短暂休止的无声视为音响,但是此处的无声也必须组合在音乐整体构成中。另外,无论是约翰·米尔顿·凯奇在钢琴的弦之间夹上诸种异物以求取另类的音色,还是噪音音乐及击打日常生活中的诸种器用,这些激进的音乐人没有彻底放弃音乐本身。并且此类作品在当代音乐中也是极少数的,绝然没有像当代艺术大规模地抵抗架上绘画那样,在当代美术界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诸如凯奇在1962年推出的另外一个作品《0分00秒》(0′00″),其完全可以被定义为行为艺术作品,与音乐全无逻辑关系。中国学界都忽视了这样一个关键点,凯奇最初是对绘画及当代艺术充满了兴趣,当然还有诗歌,而是在1933年,他才从绘画转向音乐的。可以说,没有凯奇早期的当代艺术家身份,也就没有他转型后两部冠名为偶然音乐的行为艺术作品。
因此我认为,新音乐依然持有音乐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立场,而在相当的程度上,当代艺术则是反绘画本质的,在形式本体论上是持守绘画的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立场,他们求取的不是“大象无形”,而是“大象无画”。他们就是要消解架上绘画的本质,因此,当代艺术最终无法不沦陷于怎么玩都可以的泥沼中,甚至其中的低俗者依凭自己的无知无畏违背了人文道德伦理。关于音乐与美术的这两种现象,学界是大可以展开讨论的。于润洋非常欣赏罗曼·英伽顿(Roman Ingarden)的美学思想,罗曼·英伽顿恰恰是把绘画与音乐整合在一起给予讨论的。
客观地讲,在曲式、对位、和声与配器等技术性结构方面,加之十二音序列音乐(twelve-tone series music)、微分音乐(microtonal music)与频谱音乐(spectral music)等出现,音乐创作在复杂性与技术难度上远远超越了绘画,并且乐器演奏的技术性难度也是如此。我们不说写实主义的古典绘画没有技术难度,而当代艺术恰恰是在绘画的技术难度上做减法,甚至是在形式本体的观念上完全颠覆绘画;新音乐人在对传统音乐观念进行颠覆时,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在调性音乐之外使他们的另类音乐观念之表现方法更加繁复化与工具理性化,新音乐的构成(composition)在表现技术上则是做加法。贝尔格的歌剧《沃采克》(Woyzeck)是一部无调性的表现主义作品,其在音响表现的技术手法上就极为复杂。更多的新音乐作品甚至加入了现代工业文明与后现代工业文明的高科技元素,如频谱音乐及其构成(composition)在繁复性上被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所操控(manipulate)等。注意:这里在指称音乐创作的表述中,我把“composition”这个源语概念翻译为汉语译入语概念出场时,使用的是“构成”,而不再使用“创作”指称新音乐的完型,因为一部分新音乐的作曲观念及其技法的操用已经远离了艺术的审美“创作”,仅仅是技术的“构成”而已。从一个术语的翻译与使用,就可以见出一种美学价值评判的立场。
我想指出的是,同样是对传统艺术观念的颠覆与解构,进入当代音乐的门槛相当高,而进入当代艺术的门槛非常低。在当代艺术圈子内,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全无美术专业的技术性,一些当代艺术行为者可以不择手段,仅仅是玩弄一个毫无深度却看似隐喻的观念,浅陋地表达行为者对社会、文化与历史什么的暧昧且无聊的评价。从国内这三个新音乐活动的全部参与乐者来评判,我们注意到,其参与者都是当下国内与国际学院派的优秀音乐家,且无一例水平低下与媚俗的乐者可以介入其中,从目前来看,即便是玩流行音乐的通俗音乐人也应该没有资质跻身于这个圈子。
在当代中国音乐的宏观背景下,还有一个不可调和的差异性现象是必须要指出的:即新音乐与大众音乐是绝对不可兼容的;在音乐观念与审美的价值取向上,新音乐与大众音乐既是势不两立的,也是誓不两立的。因此,新音乐是少数的学院派当代音乐人玩赏于体制下的小众化音乐(music of antipopularization)。请注意我在这里所使用的英语源语概念是“anti-popularization”,而不是“minority”。我认为较之于当代艺术的媚俗性与低俗性,新音乐的小众审美风格恰恰秉持着这个时代严肃音乐的高贵品质。
孤岛和大众:当代音乐的高贵与通俗音乐的媚俗
让我们暂且退出当代中国艺术空间,来检视在当代中国音乐宏观空间中所存立的两种不调和的审美差异性。也就是说,我们在观念上必须把新音乐——当代音乐与大众流行音乐界分开来。注意:在这里,大众音乐、流行音乐与通俗音乐是三个共通且可以同义替换的概念。较之于把传统的严肃经典音乐尊称为贵族音乐,我愿意把新音乐人称为当代音乐圈子里的新贵族,他们制作的音乐盛宴仅仅是生存于学院体制圈子里少数专业爱乐者的菜,而大众绝对不吃这口菜。充其量,在新音乐持有的小众受众者中,也仅仅存有极少数的业余附庸风雅者,事实上,他们并不能够真正地理解新音乐。
2014年,北京音乐节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开幕,艺术总监叶小纲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伦兵的采访时说:“音乐就是理想,我们音乐家的理想不能离大众太远。”“音乐就是理想”,这句表达是不错的,作为口号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的音乐家,而显然叶小纲在这里所陈述的第二句无疑是官方音乐节的体制性表达,并且他所言称的“音乐家”无疑是指学院派的当代音乐家。凭心而论,叶小纲在后面的表达才直白且专业地透露出一位真正的当代音乐家内心的隐密:“我的音乐是孤岛,我只讲一种语言,就是自己的语言,别人很难模仿。”不错,我们把叶小纲的作品一路地听下来,叶小纲就是纯粹的叶小纲,在更多的意义上,他的作品是写给自己听的,或也是写给学院派圈子里小众同行把玩的。在当代音乐创作的纲领性表达上,叶小纲是非常清醒的:“从历史上看,那些过于挑战自身以及观众的艺术品,一般欣赏者不多。如果不是艺术史需要,那些作品也没有生存空间。北京现代音乐节的曲目挑选不是唯学术论,而是考虑在思想、观念甚至表现形式上是否有所启示和价值,这就是北京现代音乐节的特色。”这是一种纲领式的宣言,叶小纲已经宣示了现代音乐——新音乐——当代音乐是小众音乐,其仅仅是学院体制下当代音乐家个人诗意栖居的孤岛。所以记者伦兵也把叶小纲称为“中国音乐界的异数”。在音乐表现观念的风格上,几乎每一位新音乐家都渴望成功地打造自身的“异数”形象,以让自己突围于传统音乐观念的庸常而出类拔萃。
当代音乐总不能只是小众新音乐家之间相互抚摸的诗意表达,然而不幸的是,于创作之始,他们就在音乐观念的追求上告别了大众,成为在一意孤行中无视大众的孤芳自赏者。当然在批评价值的反向表达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他们成为被大众抛弃的孤芳自赏者。这种现象的确是值得学界深思与讨论的。在表现的观念与风格上,甚至某些新音乐作品另类到就连圈子里的小众同行也无法接受。
我认为,新音乐是高贵的,有着自身不可多得的新贵族品质,雅俗共赏不一定是新音乐追寻的审美价值取向。新音乐就是小众音乐,这又为何不可?在音响构成的审美观念本质上,新音乐从来就是小众的,叶小纲声称音乐家的理想不能离大众太远,这也是新音乐家的一种无奈的策略性表达。在这里,让我借用康德的一个概念来完成以下的判断性表达:当下是一个多元的全球化时代,新音乐与大众音乐是一个既相互对立又各有自己存在合法性的二律背反(antinomy)。
我认同现代音乐——新音乐——当代音乐秉有一种不可多得的新贵族品质。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隐喻性评价,也是一个值得音乐评论界深度讨论的现象。让我们再度返回当代美术界,来考察一下当代艺术及商业炒作的恶性介入,以给予参照式的比较反思。还是让我们从艺术的形式本体论来展开思考。
美术作品的存在本体就是其审美的造型与表现形式,用形式主义美学与存在论美学的理论给予概述:形式即本体。我还是长话短说,一言以蔽之,美术作品,其诉诸视觉的形式本体具有形下的物理性,其作为一种负载时代及作者个人审美意象的物理形式存在(existence),具有商业收藏的可能性,因此美术作品的本体形式决定了美术作品的收藏价值。音乐作品的在场形式本体是形上的音响,是音响在一定限度的时空中展开且诉诸听觉的抽象审美表达式,音乐这种抽象且非物理性存在(being)的审美表达式,激发了受众内视的审美想象。在《音乐作品及其身份问题》(The Work of Music and The Problem of Its Identity)一书中,波兰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伽顿专门撰写了《音乐作品是怎样存在的?》(“How Docs a Musical Work Exist? ”)一章,在这里,罗曼·英伽顿讨论了音乐作品的身份问题(a problem of the identity of a musical work),他认为音乐作品就是一个抽象的意向性客体:“一部音乐作品不是一个现实(a real)而是一个纯粹意向性的客体( purely intentional object),严格地讲,是一个高层次的意向性客体。”音乐从创作、演奏到以抽象的形式本体出场,及对受众内视审美想象的激发,其抽象的动态展开过程要比具象的静态美术复杂得多,并且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所在,就是出场展开的形上音乐不具备商业收藏的可能性,因此,音乐作品的本体形式决定音乐作品没有收藏价值。
援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当下的富商或土豪无法像他们收藏美术作品给予商业性增值的炒卖那样,去收藏一部出场展开的抽象性音乐作品,以给予囤积后的商业性增值炒卖。无疑,这是音乐与美术的形式本体之差异性所导致的本质分野。这也是当代新音乐家比当代艺术家在物质的生存上要贫困得多的根本原因。非常有意思,原来音乐与美术在形式本体上本然的差异性,铸就了音乐家与美术家各自的经济身份与商业地位。
当代音乐家充其量是靠私下教学生挣钱,而不是靠卖作品挣钱。的确,较之于一幅美术作品开价到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元,音乐作品怎样拍卖?一部没有出场展开且静止在书桌上的交响乐总谱是音乐吗?什么是音乐?在《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Zur 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 Th.Adornos)一文中,德国学者斯茨勃尔斯基(L.Sziborsky)也触及到这个问题:“音乐放弃了它的存在,即作为暗号它只是潜在的音乐,它在演奏中发出音响并同时被感知时,才真正地存在。”总谱只是潜在的音乐,是音乐密码化的文本,而不是音乐本体的存在。其实,我们应该重新讨论音乐本体论的哲学问题。
让我们的思考回到流行音乐那里去。
需要强调的是,我在这里所讨论的是指艺术作品的商业性收藏与增值。大众音乐有买卖交易纸本乐谱的那些事,这种纸本乐谱的商业交易最终还是要在现场演出变现为商业效应,而不能被解释为演出商是投资收藏在现场展开的音乐本体形式。这个问题也还有待于音乐批评界与音乐理论界给予展开性的讨论。我想声称的是,不同于当代艺术,也不同于大众音乐——通俗音乐——流行音乐,在相当的程度上,现代音乐——新音乐——当代音乐没有被当下经济大潮的功利性所全面裹挟,没有像当代艺术那样被商业污染到那种不堪入目的地步。
这,是当代音乐的新贵族品质。
我在这里所言指的新贵族不是以物质上的占有与富有为衡量的,而是指涉精神上的占有与富有。也就是说,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新音乐人是纯然的精神贵族。这也是当代新音乐人在品质上的高贵!我们必须指出,新音乐人秉有自身的高贵,然而在学院体制营造的当代音乐圈子里,小众新音乐人之间的拼才华、争高低与背地里的相互攻击也是存在着的。毕竟,他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新音乐人。
其实,关于当代音乐不向商业妥协的社会伦理问题是值得展开讨论的,温德青及有良知的当代音乐家自律地拒绝当代音乐的商业化,这是一种高贵的品质,而当代美术与大众音乐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沦落于商业资本获取的功利性中,跌向了媚俗化与低俗化了。在资本全球化的商业性策动下,媚俗文化和低俗文化是随之而来的必然附庸性产物。同样是创作观念上的激进与前卫,然而,新音乐既不商业化,也不媚俗化,更不低俗化!我们只在现场或网上视听当代音乐——新音乐的展开,则一目了然。
音乐形式本体具有非收藏性,这让流行音乐在商演的大众现场频频展开,且出尽了风头。在商业资本的运作与获取上,流行音乐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新音乐,大众娱乐至死的疯狂及其在场的呐喊,成为支持通俗音乐人瞬间走红且获取巨额利润的商业杠杆。我们不妨设问:叶小纲与周杰伦,在当下中国的宏观音乐平台上,究竟谁拥有的受众多?谁的商业价值高?谁拥有社会话语权?或许我们本身就不应该把这两类音乐人置于同一平台,给予比较性的设问。但不幸的是,他们毕竟生存于同一蓝天下。
放大了评判,叶小纲们完全可以指责在商演平台玩通俗音乐的周杰伦们:你们不懂音乐!而周杰伦们也可以嘲讽在学院体制下玩新音乐的叶小纲们:你们的音乐没人听,真正懂音乐的人是大众,面对着大众的审美需求,叶小纲们不懂音乐!我想,或许这句表达也可以这样书写:你们的音乐没人需求,真正需求音乐的人是大众!在这个年头,“需求”是一个逼使人们脑洞大开且求取商业机遇的字眼,所以还有一种心酸的情愫是让人无法释怀的:周杰伦们几场商演的收入,可以让叶小纲们辛劳半辈子;何止如此,当代艺术家几幅“坏”画作品商业拍卖的收入,可以让高贵的当代音乐家低头操劳一辈子。这无疑是一个令人烧脑的问题!其实,当下已经到了在法律与伦理上限制漫天要价的商业性艺人的时候了。
此刻,我突然想起了纽约大学的那位教授——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也想起了他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书写的那部读本:《娱乐至死》(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我真的不希望娱乐文化成为把商业资本隐指为上帝,而形成一种亚宗教形态,其中聚众着太多的只懂拜金主义的文化贱民。我们不妨操用尼尔·波兹曼的话语设问当代音乐与通俗音乐:谁操控着“演艺时代的公共话语”?新音乐人是学院体制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或许拥有本科、硕士与博士学位,甚至还有博士后,然而,在娱乐至死的商业文化时代,他们的确没有向社会大众释放音乐的公共话语权。
那么,究竟谁懂音乐呢?究竟谁又需求音乐呢?历史在此设问!的确,不少新音乐作品在一次实验性演出之后,也就束之高阁了。在相当的程度上,不少作曲家也就是拿着国家的课题经费,完成一个科研课题而已,音乐创作的社会性本质也被改变了。我们还可以递进一步设问:这个时代怎么了?艺术究竟为何?
话又不得不说回来,残酷的是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商业资本的运作与支持是推动艺术行为持久性发展的内在动力。谈到这里,一种焦虑不可遏制地蒸发出来,较之于在大众群体中商业性流行的通俗音乐,现代音乐——新音乐——当代音乐的未来真是命运多舛!上海音乐学院在第一届当代音乐周提出了“没有当代,就没有未来”的口号,在第二届当代音乐周又调整了自己的口号:“有了当代,就有未来”。从形式逻辑学上判断,这两个口号在语义上仅是同义反复的不同修辞性表达而已。流行音乐恰恰更属于当代,看着通俗音乐在大众消费文化层面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流行及获取巨额商业利润的发展态势,这两个口号究竟是指向新音乐还是送给了大众音乐?小众的喝彩与大众的掌声,究竟哪一种在未来的生存境遇中能够持续得更为久远?谁的掌声又为谁喝彩?这还要走着瞧!
如上述我们所指出的,当代艺术的进入门槛低,也正是如此,在商业资本的诱惑下,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事与什么样的作品都可能生发在当代艺术空间,所以在审美意识形态与艺术批评领域,当代艺术的争议性特别大。再加上当代艺术作品的可收藏性及其商业性炒作,来自于批评的反正两个方面合力推动了当代艺术评论的异常繁盛,当然,这里的繁盛也浮泛着泡沫与假象,我们必须承认,除去一批有水分的文章之外,其中不乏优秀且持有真知灼见的当代艺术评论文章。
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家身份与中国当代音乐评论的贫困
较之于当代音乐的进入门槛高及其难能可贵的新贵族品质,当代音乐批评与当代音乐理论却处在极为贫困的状态。“中国当代音乐评论比赛”或“乐评高峰论坛”曾是伴随七届上海当代音乐周开创的一个乐评板块,旨在推动当代音乐评论的发展,然而因参与者所提交的音乐评论文章质量较低,或还存有一味“唱赞歌”的现象,最后,不得不被中止。这无疑是让人警惕的!2016年上海当代音乐周邀请杨燕迪、周海宏、韩锺恩三位音乐学教授,以坐而论道的方式取代这个乐评板块,这只能是进一步证明了当代音乐评论人才的匮乏。
我认为,邀请音乐学专家出场以补缺当代音乐评论的贫困与人才的匮乏,这显然是无奈之举。我们希望,杨燕迪、周海宏、韩锺恩、洛秦、肖梅与宋瑾等一批优秀的音乐学教授身体力行,站在一线,写出扎实且具有良知的当代音乐评论来,以切实地带动更多的青年音乐评论者积极加入,从而推动中国当代音乐批评与当代音乐理论的繁盛和发展。
客观地讲,在汉语中国本土崛起的现代音乐——新音乐——当代音乐是非常繁盛的,其中可引起乐评界思考的问题也是非常丰富多元的,这个时代新音乐气象在呼唤着当代音乐评论的崛起与发展。以下我再简约地列举三点。
第一,在概念的使用上,“北京现代音乐节”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读与争议。从西方艺术史教科书划段的一般概念上来理解,上个世纪早期发生的现代派艺术或现代派音乐已经把“现代”这个时间概念占有完毕,如果中央音乐学院坚持使用“现代音乐”指称在中国当代乐坛正在发生的新音乐,而拒绝使用“当代音乐”或“新音乐”给予指称,这样可能会导致对“现代音乐”产生理解与解释的误读意义。并且无论是作为历史时间意义上的“现代”,还是作为哲学思潮意义上的“现代”,两者均已有定性的诠释,并且当下已经进入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文化时代。“北京现代音乐节”这个术语在逻辑上有破缺,其争议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需要重新界定,或者中央音乐学院可以给出一个更为恰如其分的解释。
第二,总体地评析,从三个国际当代音乐活动所邀请的乐者及曲目来看,其所集纳的音乐观念、作曲技法、表现风格、审美原则与演奏形式等相当“杂混”(hybridity)。我坚持认为“杂混”不等于“多元”。主办方所邀请参加的音乐家及曲目,不应该是无原则敞开的什么都行,从而不恰当地把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拼贴观念作为繁荣新音乐舞台的简单方法论。现代音乐——当代音乐——新音乐的边界越是开放,主办方越是要持有自觉的音乐观念与美学立场给予限定;严格地讲,这三个国际性当代音乐活动对任何一位乐者及其曲目的邀请,均标志着主办方对现代音乐——新音乐——当代音乐之本质的理解与回答。所以邀请任何一位音者及其曲目的参加,主办方必须投以谨慎的选择姿态,并一定要把庸俗的人际关系排除在外。否则,这三个国际性当代音乐活动,必然因其什么都行的“杂混”式拼贴,让现代音乐——新音乐——当代音乐失去了本质,最终成为什么都是而什么也不是的“杂混”平台。
第三,人在原始自然生态中的审美需求本质化出音乐、绘画与舞蹈等感性的原初表现形式,因此音乐、绘画与舞蹈是人的本质自然审美的对象化,而现代与后现代工业文明的高科技元素对音乐构成的渗透,让音乐源起于自然的审美表现形态最终疏离于人的本质。频谱音乐是新音乐发展的风向标之一,当代音乐评论界对其正面介绍的多,而批评的少。让我担心的是,音乐构成中的科技崇拜及过多后现代工业技术元素的带入,使得审美的音乐在创作——构成的目的论上直接对象化为工具理性的异化物,从而逼使音乐疏离了生命——人在本质上对音乐无目的而合目的之感性需求,音乐在构成的目的上被工具理性异化了,从而音乐的美学本质在此也被改写了。法兰克富学派在上个世纪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应该引起当代乐评者的关注,毕竟人是音乐的本质。
写到这里,有一个场景是难以让我忘却的:创建于1923年的法兰克福学派及所属的多位哲学家对国际学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在法兰克福大学新校园的中心草坪,校方专门为纪念阿多诺而设置了一方公共广场,把阿多诺生前使用的几件物品置放在一个全封闭的玻璃空间中,以向周遭的公众展开,从而表达对阿多诺的敬重:阿多诺曾经使用过的一张硕大的褐紫红办公桌,还有一把同样颜色的带扶手的靠背椅,桌子中间镶嵌着墨绿色的台面,台面上摆放着一盏老旧的乳白玻璃罩台灯与阿多诺的一部代表著,我怀揣着崇敬的心绪靠近,特别想细看一下,究竟阿多诺的哪一部读本可以作为代表著陈列在这里,我注视着这部代表著白灰交织的封面,其赫然书写着“Philosophie der neuen Musik”——《新音乐哲学》,并且还有几页阿多诺撰写《新音乐哲学》的德文手稿散落在旁边,更有一座体量较大且老旧的栗色节拍器,以其一角斜压在《新音乐哲学》的书侧上。无疑,这是德国学界对阿多诺作为哲学家之另一种身份的敬重:一位杰出的新音乐哲学家。
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一次偶然的跨界思考中,对新音乐的书写却成为专业音乐学研究者的必读之书,新音乐哲学家也成为他被尊重的首席身份。而我想表达的是,新音乐在中国当代乐坛崛起得如此繁盛,当代中国的专业音乐学研究者又有什么理由容忍当代音乐评论依然处在不对等的贫困状态?当然,音乐评论需要哲学的深度性思考,这也对当下的专业音乐评论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者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1. 按:除了武汉国际新音乐节的举办有间断性之外,北京现代音乐节与上海当代音乐周是以每年一届的节奏连续举办的。
2. 按:在这一句表达中,我们使用的是“另类音乐观念”这一术语,而没有仅仅使用“无调性音乐观念”这一术语,因为当下的新音乐在反动调性音乐的尝试行为中,其实验性技术已经超越了“无调性音乐观念”所限定的边界,在另类的音乐观念上趋向了更为多元的可能性及未确定性。
3. 按:这里的“贵族”仅是一个隐喻性的修辞,而不是实指传统历史上具有世袭爵位的那类人物。
4. 伦兵撰:《叶小纲:给观众更缤纷的音乐世界》,见于《北京青年报》,2014年5月16日,第B11版。
5. 伦兵撰:《叶小纲:给观众更缤纷的音乐世界》,见于《北京青年报》,2014年5月16日,第B11版。
6. 伦兵撰:《叶小纲:给观众更缤纷的音乐世界》,见于《北京青年报》,2014年5月16日,第B11版。
7. 伦兵撰:《叶小纲:给观众更缤纷的音乐世界》,见于《北京青年报》,2014年5月16日,第B11版。
8. Roman Ingarden, The Work of Music and The Problem of Its Identity,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Polish by Adam Czerniawski, THE MACMILAN PRESS LTP, 1986, p.119.
9. 斯茨勃尔斯基著,王才勇译:《阿多诺的新音乐哲学》,见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9年,第三期,第15页。
——评《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