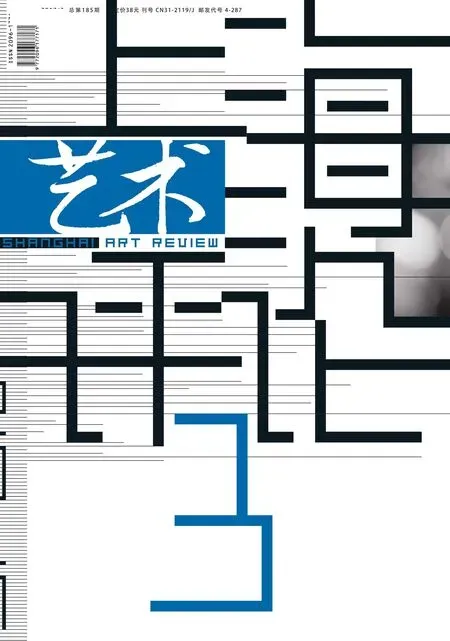营造更为敞开的文化空间
李 昂
营造更为敞开的文化空间
李 昂
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当代音乐迅速从严肃音乐的创作中突围并崛起,以其更为显著的多元化及现代人文深度挑战着调性音乐数百年的统治话语。然而,若从当下的学院派创作理念以及当代音乐周活动的整体美学价值取向来看,似乎对于调性音乐的拒斥已经达到了非常绝对化的地步,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另一种话语霸权呢?这是否也与当代音乐的初心相违背呢?
当代音乐周的魅力与困惑
第一次接触真正意义上的当代音乐是在2008年,当时恰逢北京现代音乐节(Beijing Modern Festival)在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也正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厅,我遭遇了作曲家温德青的两部作品:一首是向约翰·凯奇(John Cage)致敬的琵琶版《4分33秒》(4′33″,1952),另一首是《悲歌——为京剧韵白与三个打击乐而作》。特别是后者,由温德青亲自上阵和另外两位打击乐家合力完成,他们所敲击的“乐器”都是大众日常生活中的盆盆罐罐,整部作品在呈现时再铺垫上富有张力的京剧念白,当时那种令我感到非常新奇的现场听觉体验至今难以忘却。
2010年来到上海音乐学院,此时温德青担任总监的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New Music Week)也已经接续举办到第三届了。我依旧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一场“上音作曲家民乐新作首演专场音乐会”,这是我听赏的第一场完整的当代音乐作品的音乐会。音乐会中作曲家徐坚强的民乐九重奏《ZHI》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作品渲染着一股都市感十足的俏皮劲儿,色彩斑斓且富动感的音色织体呈现得相当精彩。当然,无尽的困惑也同时驻留在我的思考中,如温德青的唢呐重奏《唢呐爵士风》,唢呐是一件非常难以控制精确音准的中国民族乐器,为什么这部作品一定要把唢呐与风格属性要求准确表现的爵士乐来个“拉郎配”?而我想设问的又是缪哈伊 (Tristan Murail)的音乐会,在这位频谱音乐(La musique spectrale)大腕的作品中,如此艰深的写作和演奏技术又是如何完成的?这种类型作品的创作目的又是什么?
这届当代音乐周无疑成为了我关注当代音乐现象的启蒙事件。从此以后,我尽可能出席每届上海当代音乐周的所有场次。当然对于当代音乐,我更是在学理上做足了功课,尽可能多地积累现场的听觉经验,以迎接每一届上海当代音乐周的到来。可以说,每一场当代音乐会及其配套讲座的举办,均让我们很兴奋,音乐会与讲座结束之后,我们常常难掩激动之情,相聚在永康路的酒吧继续我们的讨论,我们会交流音乐周的惊喜与遗憾,也会猜测下一届的驻节作曲家是哪一位大师,同时盼望着当代音乐忠实受众心目中的偶像来到上海。也正是历届上海当代音乐周,我得以近距离接触到古拜杜丽娜(So fi aGubaidulina)、缪哈伊、威德曼(JörgWidmann)、曼托瓦尼(Bruno Mantovani)、谭盾、陈怡、周龙、陈其钢及秦文琛等国内外一线当代音乐作曲家。
如今,上海音乐周已成上海音乐学院乃至上海文化的显赫标签,每当我回想起历届当代音乐周的点滴,总是情不自禁地激发出一些细碎的思考。
学院派作曲家与大众乐迷之间的鸿沟
无疑,每届当代音乐周的主体部分是活动期间场次众多的音乐会。第一届上海当代音乐周创办于2008年,我们注意到,前三届有许多场次的音乐会是免票入场的。随着成功经验的积累和音乐周品牌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当代音乐周开始以相对较低的票价进行成本的回收,甚至是赢利,也出现了部分场次一票难求的现象。如2011年第四届上海当代音乐周,其中由琼英·卓玛(Ani Choying Drolma)和成公亮担纲演出的开幕式音乐会、由荷兰新音乐团呈现的驻节作曲家谭盾作品音乐会,其门票都是在短期内售罄。2014年第七届上海当代音乐周,法国钢琴家艾马尔(Pierre-Laurent Aimard)演奏的利盖蒂(GyorgyLigeti)钢琴作品音乐会等场次,热情的爱乐者将原本就不大的贺绿汀音乐厅塞得爆满。当然,也会出现另一种极端的情况,如2016年的第九届当代音乐周,驻节作曲家的几场合唱作品音乐会则遭遇了爱乐者的冷淡,其中多次出现中场之后观众离场的现象。
同为当代音乐的呈现,为何会出现审美价值判断截然相反的现象?若论演出的质量,平心而论,第九届当代音乐周的几场合唱作品音乐会是具有相当高的水准的。我想,除去合唱作品因语言问题所导致的沟通疏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依然在于大众和学院之间存在的那条泾渭分明的鸿沟。由于上海当代音乐周是由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因此保持音乐周所接受作品的学术高度及专业观念是主办方优先考虑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作为在音乐学院教书育人的音乐周总监温德青教授,将音乐专业学子们的收获放在首位是理所应当的。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学院派的专业标尺,历届当代音乐周所邀请的国外作曲家大多是来自于欧洲的专业音乐家,且其中有多位是当下领导欧洲当代音乐流派及其思潮的代表性艺术家。他们的音乐和讲座所呈现的不仅是极富个性的音乐观念,相当一部分甚至是激进的他们会把艺术思想渲染到极致,所有的这一切让拥围在上海当代音乐周的年轻学子们迷狂地沉浸于头脑风暴式的启迪中。如约尔克·威德曼(Jörg Widmann)在当代音乐周的讲座中发出了“调性音乐已经死亡”的言论,令人哗然。
我们也注意到,在当代音乐周,对一部作品的接受往往会出现巨大的审美价值评判的反差。就2013年当代音乐周驻节作曲家威德曼的创作而论,温德青给出了“德奥全才音乐家莫扎特、贝多芬的返祖现象代表人物”这样的定位;很显然,威德曼及其作品在音乐学院受到了部分专业乐者的热情追捧。然而对大众乐迷而言,甚至也包括一些专业人士,对威德曼并不买账。对比之下,一部分乐迷更乐于接受同样在德国学习的中国作曲家秦文琛的唢呐协奏曲《唤凤》。具体地讲,对于威德曼的管弦乐作品《魔鬼爱神》(Teufel Amor,2009, revised 2011),有的乐迷在听完音乐会之后将其形容为“炸弹炸过的马勒第十交响曲”,而音乐史学家伍维曦的批评则更为直白,他认为这部作品“味同嚼蜡”。
就我看来,当代音乐在学院与大众之间,之所以存在着审美判断的巨大差异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作曲家在创作中所追求的目的不同所致。
在音乐学院,学院派作曲家们享有一系列体制上的支持,他们可以大胆地进行实验,力图使自己的音乐观念及其美学原则行走在时代的最前端。正如第一届上海当代音乐周的开幕辞所宣称的那句著名的口号:“没有当代,就没有未来” (No Today, No Future),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口号成为学院派的体制作曲家在当代音乐创作中紧跟时代所坚守的主旨。
作为学习音乐技能的学生,他们必须对于作曲技法进行尽可能多的接触。在当代音乐周,随处可见作曲专业的青年学子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双眼,然而时时在我的思绪中不可遏制地溢出这样一种疑问,如果这些年轻人毕业之后走出校园,该如何以他们的创作获得回报甚至生存?也许在执著于当代音乐的艺术家们看来,我的疑问是与当代音乐之精神所对立的一种焦虑,这种焦虑是在冒犯当代音乐所探求的纯粹性及其美学原则。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虽然我非常喜欢当代音乐周上一系列充满了先锋性和冒险精神的音乐作品,但是这些作品若是被大众所拒绝,对于完全以学术性考量为重的当代音乐周来说,显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尤其对于那些将从音乐学院学成走向社会的青年学子来说,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了。
当代音乐对传统的承继绝然不是一种炫技
这一讨论看似老套,但较之于上海当代音乐周的品质而言,这的确是一个必须引起我们深思的当下性问题,同样,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应该引起当代音乐创作者的关注。
我们注意到,每届当代音乐周都会刻意地纳入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诸种表现元素,如邀请评弹、川剧、陕西盲艺人说唱等等纯粹民间表演形式加盟,同时,主办方还会邀请如舞蹈家金星、画家陈丹青等其他艺术领域的知名人士跨界参与,以良苦用心显示出上海当代音乐周秉有不乏多元受众口味的美学原则。
纵观西方当代音乐创作,时至今日,经历了持续性的反叛传统和抵抗权威的创作方式。勋伯格(Arnold Schönberg)以序列主义(serialism)摧毁了调性音乐(tonal music)的大一统局面,而当他逝去之后,27岁的布列兹(Pierre Boulez)则以一篇《勋伯格死了》(Schoenberg is Dead)的檄文,再度宣告属于战后当代音乐家时代的开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以自身的天才艺术创造力把自己铸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然而无论如何,他们对于自身传统的挑战也好,反叛也罢,在这些“任性”十足的前卫行为背后,欧洲音乐的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与浪漫主义(romanticism)传统依旧岿然屹立。并且我们注意到,现下新浪漫主义(neo-romanticism)等当代音乐流派已然显示出回归传统的诉求。值得关注的是,科里利亚诺(John Corigliano)、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等美国作曲家的大量作品不仅开始回归浪漫主义的审美情致,并且已然被大众所接受与所喜爱。作为当代音乐的健将,他们的音乐充分反映出属于当下时代的典型气质,并且,在创作上同样具有非常令人赞叹的巧思,这也是他们的音乐创作有别于自身文化传统音乐所表达的显现。
另一方面,在欧洲当代音乐家群体中,仍有如缪哈伊、芬尼豪(Brian Ferneyhough)这样坚守自身创作个性的作曲家,他们仍然以充满想象力的声音不断回馈关注他们创作的人们。特别是在第九届当代音乐周,缪哈伊带来了他的管弦乐作品《高压电》(High Voltage/Haute tension,2013),这部作品以其极富冲击力的乐队音效刺激着观众的听觉神经。对于如缪哈伊这样的作曲家来说,以声音本身的力量充实他们对于客观世界的陈述,这本身就是他们的个性所在;而对于听者而言,至少是对于我,完全没必要费尽心思去揣摩其声音本体,以苛求是否蕴含着更为深刻的隐喻。所以,无论是反叛还是回归,西方的当代作曲家们都以传统为基准,表现出他们独具个性的创作才华。
反观中国作曲家,他们所面对的传统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朱践耳是中国当代交响曲的先驱,他们那一辈人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走出国门求学的作曲家,所面对的所谓“传统”与西方作曲家是一样的;同时,他们接受了彼时彼地西方当代的音乐思潮的熏陶,正是在“文革”后,他们发出了中国当代音乐的强音。然而,更多的当代中国作曲家进入专业创作领域后,他们所接受的是承袭西方音乐学院教育体系下的培养,特别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中生代作曲家,如谭盾、叶小纲、陈其钢乃至秦文琛等。这一代作曲家痴迷于从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汲取养分,同时,在创作中以西方的当代技法抑或观念来呈现他们富有个性的解读。所以在我们看来,与西方作曲家对于传统的反叛不同,中国作曲家一直在努力与自身的传统对话,这成为中国当代音乐作品中屡见不鲜的陈述方式。
然而我以为,恰恰是这种中国当代作曲家已然个性十足的表述方式,却是需要我们这一代年轻音乐人给予正确认识的。
第一,一般来讲,对于技法的热衷是作曲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品质,好的严肃音乐作品在技法的运用上必然有着可取之处,诸多优秀的中国作曲家及其作品均是如此。
第二,对于传统音乐艺术的表达与对话,作曲家若仅仅流于形式与表面,甚至断章取义,这必然沦陷至一种不可取的窠臼。技法永远是为表现内容服务的,如果音乐创作总是刻意从具体的技法出发,沦为炫技的奴隶,这是很难创作出精彩的音乐作品的。
对于传统的认知,恰恰是音乐学院学生最难把握的一种姿态。譬如,上海当代音乐周自第一届以来,就回顾和呈现了许多经典和新创作的不同编制的民乐作品;但是,在今年的当代音乐周,从缪哈伊大师班学生所创作的中国民乐作品来看,其质量很难令人满意。就几位中国学生所创作的作品来说,他们对于乐器自身特性的了解显然不够,尤其他们对于乐器音色的把握显得非常生涩。这种在表象上以纯粹炫耀或卖弄为目的而展现自我的“个性”,多少显得有些轻浮了。当然,关于如何推动我们培养的当代作曲家更好地承继传统,以使得他们的创作更加具有深度和厚度,这是一个值得持续讨论的问题。关于这样一个问题的讨论,我们更希望在上海当代音乐周的舞台上,以实际作品的推出使得答案愈发清晰起来。
当代音乐的本质在于拒绝审美唯一性的话语霸权
记得在2014年第七届当代音乐周,驻节作曲家陈其钢举办了一场题为“机会主义(Opportunism)是作曲之大忌”的讲座,陈其钢就创作的目的及行为的问题与聆听讲座的学子们展开讨论。他认为,创作行为和做人是一样的,一定要诚实,必须要遵循自己的内心,作曲家创作只能代表个人,而没有人需要作曲家来代表,所以作曲家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陈其钢是一位成功的作曲家,这也是他给年轻学子的忠告。
我认为他的忠告是很有意义的,指出了当代音乐个人表达和个性彰显的诉求;但是如果年轻作曲家将这样的观点奉为不二信条,其也难免走入另一种极端。我一直持有这样一个立场,当代音乐绝对不能沦为标榜自身孤傲的工具,作为一位从事创作的艺术家,首先要明确自己创作行为的目的何在。对于作曲家来说,要清楚自己的音乐是创作给谁听的,如果音乐作品没有了受众,那么它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属性又如何体现呢?
绝大多数彪炳史册的作曲家,都必然有其杰出的作品,即所谓的“活儿”。诚然,创作的纯粹性的确是需要作曲家去坚守的,但反过来说,带着目的去创作,并不一定影响作品在艺术上的纯粹性,即便是为了一个比赛的奖项、一个委约、一个演奏家去创作,如果能够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也一样可以呈现出好的作品。由此介入当代音乐创作精神的讨论,其必然引发我的思考,究竟什么是当代音乐?难道当代音乐仅仅指涉西方或囿于欧洲的那一小股勇敢者的创作吗?
还记得在2015年当代音乐周的中国当代音乐评论比赛上,针对一篇以中央民族乐团“印象国乐”演出为评论对象的乐评,温德青直言不讳地说:这样的音乐是商业音乐,并不能算作当代音乐的范畴。而我恰恰认为,当代音乐周最为重要的是传达当代音乐的精神,且不论“印象国乐”是否属于当代音乐,如果能以当代音乐的视角来关注所有当下的音乐现象的话,也未尝不可。
当下有关文化的讨论中,“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常常难以避免的热词。我们若将当代音乐周放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中予以关照,也许可以从宏观层面对上述问题产生较为清晰的理解。
在现代主义(modernism)横扫全球的历史时段,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表征方式,也在作为严肃音乐大本营的德奥以外,产生了大量在形式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的“民族乐派”(Musical nationalism)。20世纪初以来,严肃音乐创作面临着调性音乐的冲击,特别是在“二战”之后,又产生了大量“音响化”甚至“噪音化”的作品,如潘德列茨基(Krzysztof Penderecki)的《广岛受难者的挽歌》(Threnody to the Victims of Hiroshima,1960)这部作品,其中非常规演奏技法营造出野蛮粗壮的弦乐织体,其透露出作者对于战争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当然,不得不令人注意的是,这部作品后来加上的标题也是其人文性得以彰显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从“音乐”向“音声”转型的逻辑上,音乐创作中关于“差异逻辑”所主导的“后现代”思潮则更为强烈地撕扯着“现代主义”的审美秩序,《4分33秒》这一极端个案凸显了这一现象。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强烈地扩张下,“频谱乐派”(spectra music group)“简约主义”(minimalism)与“整体序列主义”(total serialism)等作曲家们在创作中不断地寻找着自身得以栖居的流派,似乎将音乐视为理性控制的艺术或音响的宣泄已成为当代音乐不可拒绝的不二法则。
从上述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当代音乐迅速从严肃音乐的创作中崛起,以其更为显著的多元化及现代人文深度挑战着调性音乐数百年的统治话语。然而,若从当下的学院派创作理念以及当代音乐周活动的整体美学价值取向来看,似乎对于调性音乐的拒斥已经达到了非常绝对化的地步,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另一种话语霸权呢?这是否也与当代音乐的初心相违背呢?
众所周知,美国有一大批杰出的当代音乐家同时从事大量的电影音乐创作,当代作曲家郭文景也曾在访谈中对于美国当下的电影工业中高质量的音乐创作赞不绝口。近期如《荒野猎人》(The Revenant,2015)中约翰·亚当斯(John Coolidge Adams)那充满简约主义风格的杰出配乐,为影片增色不少。至少在我看来,这样的音乐已经很难区分到底是商业音乐还是当代音乐了。毕竟,在其中我们听到了目的明确的艺术表现和技术上同样先锋的雕琢抑或是“回归”。
正如阿尔君·阿帕杜莱(AljunAppadurai)所提出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所倡导的那样,对于文化的关照应当聚焦于社会最微小单元的日常之中。真正的人文性在于对文化差异个体予以充分的尊重和理解。在此,对于当代音乐周是否能真正地扛起“后现代”人文观的大旗,我是抱有极大的期许的。
我认为当代音乐周应当以更加宽容的姿态来接纳当代音乐的走向。在我看来,无论是在学院的专业音乐教育平台上,还是在社会效应的层面上,上海当代音乐周若能把更为多元面向的音乐作品纳入其活动的空间中,也许会使其生命力更加灿烂。无论如何,当代音乐的本质是在多维度的表现性中趋向拒绝审美唯一性的话语霸权。我还记得在第七届上海当代音乐周,索伦森(Bent Sørensen)的电影音乐专场曾引起众多作曲专业学生的关注,他的作品《在后院》(Behind a Backyard)当晚与阿伯吉斯(George Aperghis)室内乐作品同台出场,那种忧愁与甜蜜混搭的精致音效,至今依然令我回味。所以,如果当代音乐周在引导听众于听觉积累的层面上再耐心一点,这或许有益于营造更加大气的当代音乐文化生态。
上海当代音乐周以每年一届的节奏走过了九个年头,所经历的一切使上海乐迷得以近距离地接触到国际上最为先锋的音乐创作。在不断的讨论中,我们惊喜地发现,有关于彰显独立个性的当代精神,不断地为从事音乐创作和音乐研究的人们所接纳与理解。从学理上来评判,上海当代音乐周的本质就在于“当代”,并且这是一种引领未来的“当代”。我想这也是为何当代音乐周语境之中“当代音乐”的表述为“New Music”而非“Contemporary Music”的原因吧。其本身就已标识了此活动在学术视角上的指向性。但如今上海当代音乐周已然不是只属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节,已成为来自于国际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爱乐者所狂欢的空间。所以,我殷切地希望上海当代音乐周能够依托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开放门户,以接纳多元的“敞开”姿态与世界对话,从而发出更具魅力且更具生命力的中国当代音乐之声!
作者 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1. 李明月:《通透、酣畅、纯真——“当代音乐周”驻节作曲家约尔克・威德曼速写》,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2. 关于音乐“差异逻辑”的论述,请参见宋瑾著:《后现代差异观与音乐主体文化身份》,载《音乐艺术》,2010年第1期。
3. Globalization,Aljun Appadurai,Ed,Duke University Press,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