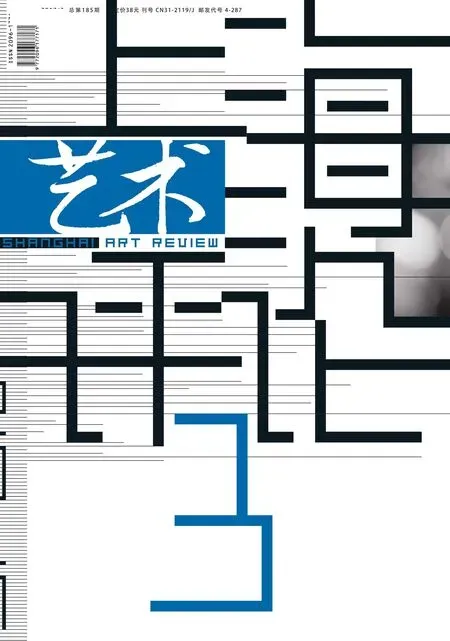一次民族精神的招魂
——《中华士兵》的艺术创造
吴 戈
一次民族精神的招魂——《中华士兵》的艺术创造
吴 戈
尊重历史,崇拜英雄,也许是我们这个历经苦难的民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强调的价值观念。《中华士兵》是一次感人的正史招魂,是和平年代久已沉睡的民族血性的一次动情重温与一声激越唤醒,是一片戏说历史的抗日神剧与一堆嘲弄崇高的庸俗笑剧环境里一次庄严的英雄祭奠。
中国国家话剧院排演的壮丽史诗式的《中华士兵》,表现的是中条山战役中,兵源不足的中国军队招收的一群未及弱冠的男娃,在父辈军人的带领下冲杀向战场、最后弹尽粮绝投身黄河、慷慨赴死的事迹。整个演出让人热血脉偾张,荡气回肠。在“抗日神剧”饱受诟病的背景下,这部以玉碎精神为表现内容的中华士兵慷慨赴死的壮美悲剧,显得格外醒目。远离战争年代的人可能在这种复仇快感或者娱乐倾向的作品中被遮蔽了战争残酷、被模糊了淋漓鲜血而淡忘了英勇壮士、民族英雄。而话剧《中华士兵》却还原了伟大的民族抗日战争那些被遮蔽、被模糊、被淡忘的内容,为民族缅怀先烈、感恩英雄搭建了一个激发壮心的公祭台。
剧情发生在当时的国军部队里,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艺术家从“中华民族”的大视野出发,去书写民族精神的大格局、大情怀。《中华士兵》引导观众走出娱乐、走出“神剧”去正视这种力量极度悬殊的对抗,更重要的是引导观众去正视这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能够超然于现实困境之上困兽犹斗、向死求生的大勇精神。
在正义与邪恶的生死搏杀变成资料与数据的历史钩沉时,《中华士兵》这部剧目鄙弃消遣性、娱乐型的复仇快感,避免考据癖、数据执的复原诉求,而是活色生香、生动感人的事件重现、场面重温、精神复活,最重要的是精神复活。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敢于自焚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
导演查明哲1997年和2003年之间推出的“战争三部曲”《死无葬身之地》《纪念碑》《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接二连三获得舞台轰动效应。后来,“走出战争硝烟”,“贴近底层民生”,就从外国剧目的排演创作转身关注国内剧作家的创作,由此展示了深厚的导演艺术功底,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艺术影响力。排演《中华士兵》并不是泛泛的应景之作,在查明哲导演一贯苦心孤诣的艺术创作追求中,《中华士兵》也体现了他的过人创造,这从思想深度和艺术创新两方面表现出来。
剧目选择了一个特殊题材来表现抗日战争,表现的是“玉碎”的失败英雄。这样的题材稍稍有失分寸,可能就会变成令人丧气的惨剧,因为剧情的指向是抗日军队的以弱抗强、宁死不屈。那是玉碎人格的壮美,绝对精神的追求,所以,失败战役的现实成为捐躯壮士、国殇勇士虽败犹荣过程表现,壮美画卷,一页页,一幕幕;这种从容地赴死,冷静地舍生,只有越过了生物的可怜本能,具有巨大勇气的族群能够做到。
这种赴死的选择,对于整个民族的生存发展策略来讲也是富于选择理性和生存智慧的。这首先是一个生死辩证的问题,《中华士兵》引导观众展开的,正是一个族群“向死求生”的深邃思考。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在反侵略力量悬殊到了一望而知、令人沮丧甚至绝望的时候,在筑起血肉长城拼死节节抵抗敌寇的时候,一群又一群勇士血拼在火线前沿,以不屈不挠的英勇粉碎敌寇气势上摧垮中国的幻想,用慷慨赴死的精神激励同胞坚持战斗,以死亡换取时间,以死亡来激励同胞、粉碎敌人幻想。用个体的死换来族群的生,用小群的死换来大群的生,用民族部分的死换来民族整体的生。这部话剧,正面、细致、热烈地歌颂这种体现民族生存智慧同时也充满了生命体验痛苦的壮烈,剧作家、导演和全体演职人员选择了一个特别的题材、讲述了一个特殊的故事,铺陈了中华民族最近一次危机中生死选择的特殊仪式——一种牺牲的仪式,让观众在仪式中体验自己生命中未曾经历过的圣洁与壮美。
在今天可见的不少抗战时期的照片上,抗战娃娃兵也是常常令人潸然泪下的形象。在《中华士兵》中,“冷娃”就是“娃娃兵”的形象代表。冷娃热血,是投河壮士群像塑造当中十分感人的内容。中华民族在阻抗强敌的时候,男女老少齐上阵,大敌当前,已经没有什么是可以珍惜和留恋的了。更重要的是,剧情表现了送郎投军、送子抗日、一个英雄母亲的四个儿子全部在抗战中为国捐躯。这些情节固然表现的是英雄的大地、英雄的人民,但是更主要的,剧情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军威与民族之间的天然联系。
《中华士兵》的故事结构,是“碎片闪回”式的“事件组接”,序幕和尾声交代背景和表现结局,中间四幕的剧情,展示了一支中国杂牌军在黄河边集结、赴死、敢死、弹尽粮绝时扑向黄河的过程。
双重叙述是《中华士兵》舞台叙述的特点。为了交代戏剧故事并推进发展,尤其是引导观众的思考焦点与价值判断,剧作设计了中、日军队双方军官的想象对话和意志较量。这样就形成了戏剧情节的双重叙述的特征:军官对话之于剧情表现来说,是宏大叙事,外在叙事;而中间的集结、离别、轮生、赴死、包括尾声的扑入黄河,都是剧情——戏剧行动的内在表现。这样的叙述结构还带来特殊的效果,那就是在剧情的关键节点上,在生死抉择的当口,在中华士兵义无反顾地走向黄河的时分……日本军官和中国军官的隔空对话,也在引导着观众的思考点和观看点,剧目创演者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牢牢控制着剧场氛围,把握着戏剧行动的节奏。
套层表现是《中华士兵》很重要的表现方式。象征方面,奔腾咆哮的黄河与黄河文明的子孙们在剧情表现中互为表里,写黄河的奔腾蹈海的气势,也是在写中华民族的性格;写民族发展史上的英雄辈出、前赴后继,又用黄河的源远流长、浪花千叠相比照。这样,民族与黄河,成为比体与喻体之间意义、形象的套层表达。
套层表现还有文化滋养上的与精神层面传递性的对英雄主义的表现。显然,对于曾经的农业人口大国来说,中国戏剧是上演着的社会百科全书。中国人的家国观念、人伦理想、社会道德、价值取向等等,很大程度上是从戏剧舞台上看来的。《中华士兵》抓住了中国文化传播和民族精神生活的这种特征,在剧情中用了不少的场面表现乡亲们送郎参军、抗日杀敌的壮行活动——唱戏。唱的是杨家将、穆桂英挂帅、佘老太君百岁挂帅片段,将男女老少齐上阵的现实事件与文化生活里、精神层面上的民族生活无缝连接了。
赌钱的旅长宋恩九,残废后送子参军、自己投河的英雄团长田文杞,曾为土匪的黑大个……皆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尤其南京陷落后从俘虏屠场死里逃生的陈淮靖,怀着羞愧与仇恨再次投军,从实际效果的“偷生”走向“赴死”,其心理空间展示得格外充分。因为他认识到:“留得青山在”的观念,在日本侵略者那里会变成焦土;因为他体验到,放弃抵抗,只能任人宰割,成为日寇取乐、训练、逞凶的“杀材”;因为他身为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的副连长,曾经阻止士兵在遭受奇耻大辱、生命危险临近时奋起反抗,让大家心存幻想地“苟活保命”,结果是受尽凌辱、丢尽尊严、生不如死。在剧情连缀的作用上,他连接了戏外的南京保卫战和戏内的中条山保卫战、把战役局部变成了战争整体,他粉碎了面对凶残敌寇时民间自然会有的幻想,捡拾惨痛的碎片给人们看,他用军人的屈辱和生命的尊严论证了战争中的生与死,让“向死求生”成为理性选择,他背负着南京军队屈死的兄弟们的冤魂洗刷了自己,作为军人、作为人也重新顶天立地,是一个摔倒后站起来的英雄。要说人性的深度,宋恩九的“匿子”、乡绅家的“留种”、死过一回的军人的“雪耻”等,都是有相当深度的人性解剖和表现。
查明哲导演对艺术的执着,犹如虔诚信徒之于宗教;他对真相的探究、对人性探查的执拗,常常会被人认为喜欢“残酷”,不怕残酷情境下的人性追问与良心拷打而引起心智脆弱的观众的不适、不快,不怕因此而失去观众,恰恰因为他是一个有社会良心、人类良知的导演,他周围有一个情感热点相近、思想共振相同的艺术家群体,不断推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剧目。他们不用软性心理按摩廉价娱乐地取悦观众,不放下艺术家肩上的责任,不抹去艺术家心头的忧伤,不无视艺术家眼前的缺陷,不标榜零度写作和拒绝崇高,不向“小时代”的小情怀、小情调、小格局屈就。
幸而有这样一群坚持社会责任、体现社会良知人类良心的艺术家,将社会理想和生命追求化为感人的艺术形象,我们的当代舞台才有了那么多的可圈可点,我们的精神世界才不会只存留下娱乐至死后的空虚和渺茫。
作者 云南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