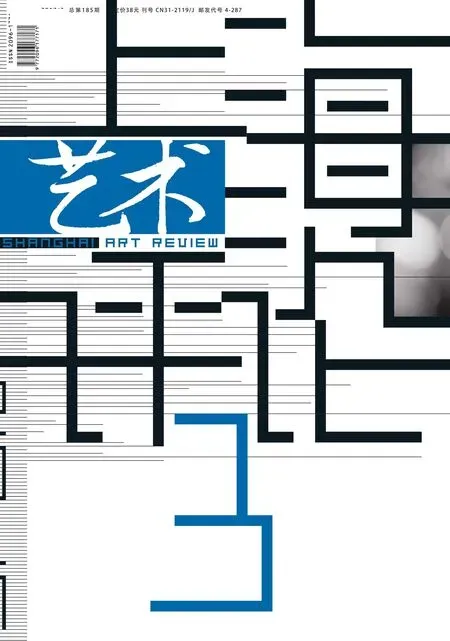中国电影“走出去”
陈犀禾 田 星
中国电影“走出去”
陈犀禾 田 星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本文梳理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电影对外发展和交流的基本思路,讨论了不同历史时期政策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电影对外传播的实践、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希望借此描绘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和产业经济链条之间的动态关系,对电影政策的重要性和产业的可能性从历史的向度进行深入思考,从而为今天中国电影的对外发展政策和产业可能性提供借鉴。
在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带动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文化和电影的发展也力图在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做出新的贡献。
纵观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下,中国电影有序地展开了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但由于国际关系和历史环境的局限,建国初期三十年,我国电影“走出去”的区域范围大多局限于和我们有着良好外交关系的亚非拉国家。“第三世界”战略不仅仅建立了一个政治同盟,互相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共享也是加强彼此情感连带的重要手段,电影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被赋予了“铁盒大使”政治使命和荣耀。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家发展路线,这成为一个转折。此后,电影发展的“内循环”和“外辐射”两个方面彼此交织、互动,共同推动着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明年,“改革开放”即将迎来四十周年,回顾中国电影“外事”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能够看到,因为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对电影对外发展的指导政策和理念也不尽相同,这就使得不同的阶段,电影的对外传播在深广度、侧重点、战略方法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展现出清晰的历史分野和时代特色,对国家电影“外事”发展战略进行梳理和回顾,思考国家政策和电影产业发展之间的彼此影响和互动关系,将为我们清醒地看待电影“走出去”提供一个参照。
第一阶段:1978—1988年
新时期伊始,电影在复苏的同时,“对外开放”也被重新提上了日程。在是否应该鼓励、倡导电影对外交流,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以怎样的立场、姿态去面对体制、意识形态都和我们有着巨大差别的西方社会,在文化的交流中,该怎样去构造一个新的民族形象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其时的文化领导阶层有着清晰、明确的思考。
80年代初,电影的复苏起自于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求真”“求实”成为对文艺评判的首要标准。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到了1983年底,电影的对外传播相较建国三十年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979年到1984年,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故事片有17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看,电影对外贸易的逆差不容忽视:“从1979年到1982年,我们平均每年收入外汇为69.6万美元和7.3万协议美元,共折合人民币为141万元,平均年支出为人民币466万元。收支相减,每年亏损人民币325万元。”
1985年之后,新时期开放的文化政策所累积的影响慢慢体现出来,一方面是国家电影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浪潮和时代氛围培育了新一代影人,使他们能够携带风格浓烈的作品踏入西方文化视野中心。1985年《黄土地》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以第五代为首的中国艺术电影开始步入了辉煌时期。1985年到1994年,共有63部中国艺术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比第一阶段(1979—1984年)获奖影片多出了49部,几乎囊括了所有A类电影节奖项,在戛纳、柏林和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更是频繁地出现中国影人的身姿。从此时期艺术电影获奖电影节的级别、奖项数量以及所造成的世界影响来看,国际电影节获奖无疑已经成为中国电影海外传播的主要模式。这和当时国家的鼓励不无关系。1987年12月7日,电影局为近两年国际获奖的影片举办的庆功会上,陈昊苏(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谈到:“在今天对外开放的时代,我们要逐步适应和参与世界文化领域里的竞争,并要自己组织国际性的电影电视等文化方面的评奖、交流活动。……既不能‘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也不要载誉归来却成众矢之的。……中国电影主要还是拍给中国观众看的,因此要多研究中国观众,要把赢得观众看得比在国际上获奖更重要,或至少同样重要”陈昊苏的这段讲话,在两个层面上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于电影海外传播观念的规训:其一是,针对舆论指责国际获奖影片对中国落后面的展示,陈强调要肯定这些影片的成绩(官方对获奖影片的支持和肯定,为这些影片的存在提供了确切的合法性,在政治层面上助推了艺术电影的海外传播),但同时也要防止“崇洋媚外”心理的泛滥;其二是,强调电影海外传播的本土本位,以及电影创新和群众接受之间的关系。
第二阶段:1989—1991年
1987-1988年艺术电影海外获奖带给中国电影的振奋之情,在此后急剧变化的政治风潮中很快消散。配合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变化,电影对外文化交流政策在这一时期开始有所调整,强调文艺创作的意识形态性,强调要保证社会主义方向,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精神的表现。“今后不论是对外合拍协拍的影片,还是向外推荐影片参加国际电影节的竞赛和展映,都要清醒地考虑到当前国际上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酷斗争形势,明确树立起以我为主的自主意识,有所为也要有所不为,不能为了某些眼前的暂时利益而牺牲我们的原则。总之,我们对外的一切工作,都要着眼于在世界面前宣传中国形象,扩大我国民族文化的影响,巩固我们对外宣传的阵地。”“政治稳定”和“文化民族主义”成为文化对外交流政策的主题,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对外发展。一方面,国内文化部门对于外出参展影片加强了政治审核。而国际上,因为学潮带来的舆论反弹,也造成有一些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的排斥;另一方面,80年代北美学界兴起的“第三世界文化批评”,90年代初被国内学界转喻为文化民族主义的批评武器,围绕第五代影人展开了颇为严厉的批评,这种颇为严厉和狭隘的文化态度,无形当中也给电影创作者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原本是为国争光的英雄,一时之间,成为众所谴责的对象。
第三阶段:1992—2000年
1992年年初,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作为90年代初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扭转了此前因为经济的停滞和思想的分化所导致的沉闷、压抑的社会氛围。这一事件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推动了国家体制改革全面走向深入。国家政治发展路线的稳定,“改革开放”合法性的重申,为中国电影(艺术电影)的海外传播提供了政治保证。将电影的对外传播放在国家和民族形象建设、文化外交的框架中来考量,是官方一以贯之的立场,艺术电影如同体育竞技,其海外传播的政治价值在官方的意识形态考察中已经成为“显性存在”,它实实在地为90年代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营造了合法性的政治氛围。这一阶段,以第五代影人为主的中国艺术电影在跨文化交流中获得了更多的荣耀:1993年,《香魂女》和《霸王别姬》分别在柏林和戛纳国际电影节揽殊荣,至此“中国电影已拿遍全部重大国际电影节的大奖(戛纳、威尼斯、柏林、蒙特利尔、卡罗维伐利、东京)”。这些奖项将中国艺术电影的国际声誉推向了一个新的顶点,也使得这一年成为国际上公认的“中国电影年”。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90年代电影对外政策中民族意识的增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府管理部门加强了对电影海外传播的审查和监控。这主要凸显在三个方面:一是颁布法令,加强对于境外合拍片、协拍片的管理;二是以颇为严厉的处罚来应对“地下电影”未经批准参加国际电影节的文化事件;三是对不符合国家意识形态范畴的国际获奖影片继续采取禁映的方式进行惩戒。原本在电影投资的紧缩、体制改革相对于市场化进程的滞后等多种因素挤压下,艰难生存的新一代影人,因为官方对于“地下电影”所采取的颇为严厉的监控和惩戒,被推入到了一种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之中,这不仅激促了第六代影人对国家政策的“反弹”,也不利于国际市场上中国电影人才的更新换代,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跨文化语境中中国电影的多元化发展。
90年代中后期,国家电影对外发展战略开始强调中国电影海外商业市场的开拓。产业经济改革的发展现实影响了国家电影观念的变迁:1999年,全国电影制片厂厂长、公司经理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应该“确立自己电影产业的地位、性质、产业发展方向与产业发展政策”。国家从产业角度对电影身份的重新阐释,有力地促动了中国电影海外商业市场的开发。中国电影海外传播商业诉求的兴起,国际化路径的多元开拓,使得电影文化的对外传播形式更为多样,这在某种程度上就缓解了中国艺术电影在跨国流动过程中所承担的压力。
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加入WTO。彼时围绕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国内几近沸腾。2002年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徐光春(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针对新的历史形势下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做了明朗而又详细的阐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央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加快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应当看到,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传媒的国际化趋势逐渐显露,传媒的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一种国际性的竞争,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传媒都不可能关起门来自己发展。电影也是如此。”可见,从长远来看,加入WTO将在外资吸引、影院改造、丰富市场、满足需求等方面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开辟一个新的局面,可以帮助和刺激本土电影产业的生长和强盛。当然,政府管理部门也并没有忽略或者否认“入世”后民族电影产业将要面临的挤压和种种困境。针对这一点,徐指出:“在这次谈判中,我们争取通过了一系列保护我国电影发展的政策措施,只做了相当有限的承诺,避免了我国电影同国外电影在现有水平上的完全竞争,为电影的改革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机遇。”
如果说“入世”对中国电影发展来说,更多意味着“请进来”,那么作为国际化的另一面,“走出去”工程也几乎同时被启动。2001年12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细则(试行)》(广发办字[2001]1494号)颁布,标志着电影“走出去”工程正式启动。该实施细则对新世纪十年广播影视文化的国际传播图景进行了具体的规划。
整体来看,国家电影对外发展的政策,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非常明确地将欧美受众作为传播重点对象,并提出了利用十年时间,分两步走,最终达到与西方抗衡的目标。难能可贵的是,这一目标实现的过程,不再单纯地依靠对外影展和艺术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的单打独斗,而是产业化和国家化并行,互相促进。
这一时期,艺术电影参加国际电影的种类比上一阶段更繁杂、更多样化,获奖数量也有所增加。第五代影人开创的“乡土中国”文化想象模式尽管在这一时期走向衰落,但其美学经验被化入到新的跨国范式之中,第六代影人在世界影坛崛起,他们逐渐培育出自己的风格,形成了新的关于中国当代都市城镇的叙事范式。从1995年到2010年,我国故事片国际获奖共81部。姜文、娄烨、王小帅、贾樟柯等人在欧洲电影节上频繁入围和获奖,2006年,《三峡好人》获得了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显示了第六代导演在艺术创作和国际声誉上开始走向巅峰。
伴随着电影体制改革市场化和产业化的不断深入,民营资本进入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领域,利润最大化的价值目标,使得这些民营资本更加重视电影海外市场的开拓和收益。当然,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国内市场产值的迅速扩大,也使得人们对海外市场的重视相对降低。
总之,纵观近四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电影政策和电影产业的密切互动,以及电影政策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思路。今年5月,中国又在北京召开了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这也把中国电影“走出去”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必将为中国电影对外传播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相关的电影政策如何具体落实和推动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相关电影产业如何利用这一机遇在做大产业的同时,做强中国的电影文化,是我们当下相关管理部门和电影人所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陈犀禾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田星 复旦大学博士后,南阳师范学院讲师
1. 科教片、动画片、纪录片不包含在内。
2. 胡健,《体制改革与对外宣传》[J],《电影通讯》,1983年09期,第24页。
3. 《电影局为一批在国际电影节获奖的影片庆功》[J],《电影通讯》,1989年01期,第41页。
4. 滕进贤,《继续端正方向努力提高质量为迎接电影创作的更大繁荣而奋斗》[J],《电影通讯》,1991年Z1期,第28页。
5. 张兴援,《在困境中奋进——一九九三年电影对外交流合作综述》[J],《电影通讯》,1994年04期,第8页。
6. 1994年7月5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布第14号令:《关于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的管理规定》以加强对于中外合作制片的管理。(参见《关于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的管理规定》,《中国电影年鉴(1995)》,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7. 1996年9月19日,电影局发出《关于加强影片参加境外电影节、展等交流活动管理的通知》,其中第4条规定电影出口单位如出售、转让所产影片的海外发行权(或版权),必须在合同中注明,所出售、转让的权利中不包括选送影片参加各类电影节、展等活动。1998年,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布了《举办、参加中外电影节、展活动管理规定》(广发影字[1998]94号),规定:“未经批准,选送电影片参加国际电影节、展的,广播电影电视部可以对电影制片单位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同时追究电影制片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给予行政处分。” (参见《关于印发〈举办、参加中外电影节、展活动管理规定〉的通知》[J],《电影通讯》,1998年04期,第5页。)
8. 礼士,《完成向共和国献礼的历史使命——全国电影制片厂厂长、公司经理工作会议综述》[J],《电影通讯》,1999年01期,第29页。
9. 徐光春,《多出精品依法管理加快改革促进繁荣——在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电影年鉴(2002)》,第22页。
10. 徐光春,《多出精品依法管理加快改革促进繁荣——在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电影年鉴(2002)》,第22页。
11. 相关具体数据统计,请参看田星,《艺术电影的跨国流动:历史、文本和思潮(1979——2009)》,上海:上海大学,2015年。
12. 《鬼子来了》获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苏州河》获第29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虎奖;《十七岁的单车》获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站台》获第5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促进联盟奖(同时获金狮奖提名)、2000年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热气球奖、最佳导演奖,贾樟柯于2004年获颁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任逍遥》获第55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提名。
13.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2003年《电影艺术》刊发的关于民营电影企业的采访。其中,张伟平在谈到《英雄》的投资回收时,颇为气愤地抱怨国内分账比例的不合理,影院瞒报票房,税率过高,盗版等问题带来的压力,所以只能期待海外市场的利润。(张伟平,《新画面投资影片在于求精》[J],《电影艺术》,2003年03期,第15页。)此外,北大华亿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总裁董平和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中军访谈中都谈到了对海外市场的开拓问题。(具体请参阅董平,《2003年是中国电影产业的春天》[J],《电影艺术》,2003年03期;王中军,《中国电影业需要更专业化》[J],《电影艺术》,2003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