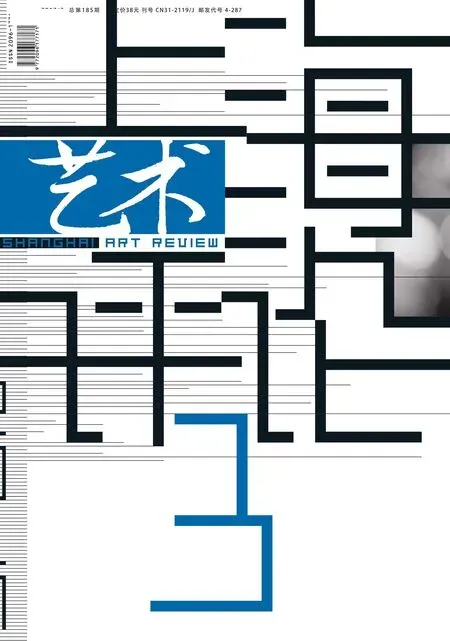对谈:两岸小剧场三十年
许仁豪 林克欢 王墨林
对谈:两岸小剧场三十年
许仁豪 林克欢 王墨林
2017年5月8日,两岸两位颇具代表性的戏剧人——林克欢与王墨林在将近三十年之后,再度公开对谈。两人结识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当时中国大陆以林克欢为首开始了解大陆以外的华人戏剧创作。1988年在北京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他们首度公开对谈两岸戏剧状况。三十年来,世界局势大变,在新一波世变之际,二人再度聚首,于台湾中山大学剧场艺术学系展开对谈,以“冷战与两岸戏剧”和“华语剧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为题,回顾三十年来两岸剧场变化及其历史意义。以下内容经过编辑删减以达话题聚焦之目的,除了纪录以作文献之用,更有助于两岸青年了解时代变迁的轮廓,也供后来的研究者参考与思索。
林克欢: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王墨林:台湾资深小剧场工作者,剧评家,编导
许仁豪:台湾中山大学剧场艺术学系助理教授
许仁豪: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两位剧场实践和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前辈来进行对话。林克欢老师是中国大陆非常资深的一位剧场评论家,同时也曾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见证了整个中国大陆从改革开放之前到当下的变迁。除了大陆之外,整个海外华文剧场的文化变迁他都熟悉。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一线导演,如孟京辉或牟森等,几乎都是他带出来的青年导演,他几乎是话剧界的一个活化石。王墨林先生的著作《都市剧场与身体》出版于90年代初的台湾,集结了他在80年代不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是台湾戏剧整个时代的记载,非常犀利地批判阐述了80年代台湾小剧场运动诸多现象。今天两位对谈其实是一个历史场景的重现与延续,《都市剧场与身体》一书记载他们1988年第一次在北京青艺公开对谈两岸小剧场状况。今天,两位戏剧界前辈重聚,回顾过去三十年两岸剧场的变化,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我们此时此刻回溯这段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对于未来的想象是什么?
林克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陆的文化人、剧场人,纷纷从干校、从农场回到城里。在停顿十年之后,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人们探头探脑、东张西望,想了解西方、东方的戏剧同行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怎么做?我们先后派出各种代表团到世界各地看戏,引进许多现代 /后现代的艺术理论和技法,囫囵吞枣地企图在短时间内走完西方现代主义近百年的历程。我当时想,大家都抢着去西欧、美国、日本访问,为什么不看看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华语剧场的戏剧人在做什么呢?当时大陆刚开放不久,一般人看不到台湾的报刊,只有在国家图书馆(当时称为北京图书馆)的报库才能看到一些。我们还托广东的朋友,在香港工作的台湾朋友,替我们搜集台湾的剧本。在阅读这些剧本的过程中,我感到非常好奇:许多作品看来看去都似曾相识,其结构、情节、人物,几乎与我们所写的揭露匪谍罪恶的剧作一模一样,只要将人物身份一改,这些作品完全可以拿到大陆演出。差别只在于,一方认为是“英雄”的,另一方认为是“狗熊”。一方认为是“狗熊”的,另一方认为是“英雄”。我感到十分诧异,尽管当年两岸的政治、意识形态极端对立,但两岸那么多作家,那么多作品,其思维模式、思维定势,几乎毫无二致。人物黑白分明,情节胡编乱造,既无真情,亦无真相。于是,我将目光转向另外一些剧作家。当剧院的艺术委员会要我推荐台湾戏剧时,我就推荐了姚一苇先生的作品。当年剧院的艺委会由一些老艺术家组成。他们看中了姚先生的《来自凤凰镇的人》。而导演陈颙和我都觉得作品虽好,却和曹禺的《日出》太像。我大力推荐《红鼻子》,因为作家对人的异化的思索与其中所蕴含的自我献身的宗教况味,已超出我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戏剧的艺术视野。《红鼻子》1982年2月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首演,连演六十多场。除了大量的报道外,仅北京一地就发表了四十多篇评论文章。中国香港、台湾和加拿大的主要媒体都作了大量报导。一次民间自发的戏剧活动,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应和政治解读,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也说明了戏剧交流在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我将此次演出的有关资料结集出版了一本专书《〈红鼻子〉的舞台艺术》,并托人辗转送到姚一苇先生的手里。1985年底,我编辑、出版了一本《台湾剧作选》,收录了李曼瑰、姚一苇、张晓风、王祯和、白先勇、金士杰、黄美序、马森、陈玲玲、纪蔚然等人的作品。当年两岸均未参加国际版权公约,也无法与剧作者联系。有人开玩笑说,这是盗版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没错,只是当年没有稿费,凭的仅是一股热情而已。此后我先后接待了来访的马森、王墨林,以及优剧场、河左岸、环墟、台湾渥克、临界点剧象录、莎妹、金枝演社的黎焕雄、田启元、杨长燕、刘静敏、魏瑛娟、王荣裕等年轻朋友。人来人往,接连不断。90年代时陈映真先生开玩笑说,我的家简直就是台湾小剧场驻京办事处。
王墨林:林老师回顾当时的历史背景,其实提醒了我们进行戏剧交流时要考虑的文化议题。语言形式的背后是文化建构,透露了更多现实政治体制的差异,华语剧场在美学上的表现,以及演员的表演方式和质地,其实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都有关,可以进行比较。当时台湾的姚一苇在大陆非常红,红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来自台湾,在当时他的戏剧在大陆算是展现了新颖的形式。虽然那个时期台湾处在戒严年代,社会和对岸同样封闭且思想没有流动。基本上,自由思想的艺术家是创造的重要动力,对比之下,现在看似真的很开放,可是这种开放里面仍然有很多自我造成的封闭。我觉得在考虑戏剧与社会的关系下,不是选择要看好戏或坏戏,而是选择剧场形式和现实社会关系、和时代的关系。我们在那样一个封闭的年代,对很多事情充满了想象,这种想象是我们的创作动力。剧场能够启发我们的动力来源不是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或是像现阶段整个资本主义商业的流动、货币的流动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的年轻人完全在一个货币流动空间里面,对于他们自己本身拥有的自由进行想象。参照现在,或许我们那时候欲望不自由、被压抑,却在思想上必须自己去找出口,于是爆发出了那么多的另类剧场形式。那个时候兰陵剧坊的形成不只是为了追求新剧场的美学、或是寻找身体,这些议题都是后设的,而是几个年轻人透过剧场的形式要去改变社会的冲动。当时年轻人不只和剧场、小说和电影全方位接触,而是与所有文化形式紧紧连动,从而改变社会。
我理解到戏剧到某个阶段产生某个流派,是有历史脉络的,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戏剧的发展跟文明的发展一样,所以西方欧洲剧场的发展和他们的文明史必须放在一起认识。比方说,他们拿弗洛伊德或者是荣格的精神分析来谈亚陶的残忍,背后说明的是欧洲现代性的危机。但是戏剧美学的出现,在台湾往往没有这种相关性。 台湾文化去脉络化庸俗化的原因,我想是文化冷战的结果。后来锺明德写《台湾小剧场运动史》,论述兰陵剧坊为台湾小剧场运动的开始,这样的历史观点,可以说是文化冷战的结果。对历史如果不了解,如何明白80年代小剧场的涌现?现在学生读莎士比亚、希腊悲剧,更重要的是在戏剧史脉络里面的经典,怎么去诠释与处理文化背后的历史变迁问题? 不管是《雷雨》还是《茶馆》,这些文本的重要不在于它是谁写的,重要在于美学,以及美学的历史脉络。我们必须思考美学与历史的问题,才能明白做剧场的目标,以及如何往下发展,没有思考,就没有目的跟拓展的可能。冷战历史结构下的剧场,不管是大陆或台湾,要回到历史去追溯,不能倒戈于后现代去历史化、去脉络化、去中心化的倾向。
许仁豪:大墨的谈话要摇醒大家的灵魂,他讲了一个重点也是我想牵引出来的,我一直强调,所有的剧本生成、美学风格的形成,和后面的历史变迁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不可能被抽空来看。大墨其实在提醒我们这一点,我们今天好像活在一个很自由的世界,所有的东西都好像我给钱就可以买到,但是如果我们细细思考,可以用消费的方式取得所有的东西,其实也是历史环境造成的,而这个历史环境是什么?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情境里?大墨那本书指称80年代末的台湾为“资本主义的烂熟期”,把这本书跟锺明德的书摆在一起读, 我们可以读出大墨对锺明德叙述小剧场运动去历史化的批判,而这样的去历史化,跟锺明德接受的美国后现代思潮有关,把冷战的全球历史忽略了。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美国在冷战时期自诩为自由世界的领袖,的确,美国在台新闻处、CIA(美国中央情报局)、亚洲文化协会后面有政治运作的逻辑,而在此之下,透过文化机构所要散播出来的文化氛围是什么?在那个时代的台湾,直接去拥抱美国那样高度资本主义媒体工业、文化工业生产的一种后现代美学,是不是令人堪虑?台湾在80年代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剧场美学形式来呼应当时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大墨的批评是左翼戏剧的传统,左翼戏剧强调的是文化形式(不管是文学、小说、电影、音乐、戏剧)都应反映这个社会里的人在当下历史状况的生存矛盾,美学处理现实矛盾,要提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以兰陵剧坊的意义不在于其后现代的美学实验,而是和当时大墨领导的一批年轻人一样,比如《拾月》或是《驱逐岛屿的恶灵》,都是透过剧场形式,年轻人试图理解当时社会高速现代化化之下资源分配不均,城乡落差,有机生存意义断裂等等生活里重要的矛盾议题。
林克欢:时间过得真快。从我与王墨林先生第一次对谈至今,近三十年过去了,王墨林还是那样的愤青。但也有变化,在他刚才的论述里,我听出某些新保守主义的味道。他始终将社会的不公,转化为一股不可遏止的愤怒,而某些保守的言论也未尝不是成熟的表现。
在台湾的剧作家中,我最尊敬的两个人:一是姚一苇,一是李国修。姚一苇先生学养深厚,为人正直。上一世纪60年代、70年代,在国民党严酷统治的氛围下,姚一苇先生始终坚持对西方现代主义精神和中国戏剧传统的研究,其成就远在他人之上。有人说他是一位旧式知识分子,这不公正。离开特定的时代背景,离开特定的语境,无法公正地评论作家、作品。不错,在《孙飞虎抢亲》《一口箱子》等剧中,都存在难以调和的双重语码,这是任何历史转变时刻探索戏剧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李国修身兼演员、导演、编剧于一身,多才多艺。他的《京戏启示录》《女儿红》等剧,讲述生活在台湾的外省人身份认同的焦虑,表现的是政治偏见、心理纠结、人事关系……种种生命难以承受之重。今天再看看他的学生辈的作品,舞台色彩纷繁,金光闪烁,目迷五色,犹如青少年的电玩游戏,极尽视听之娱,好看是好看,却像时尚消费一般,轻飘飘,总给人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感觉。
在中国大陆,80年代是一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再启蒙时期。1979年北京有两台重要演出:一台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第三度复排的《茶馆》,这是一台人才济济、制作精良的力作,呈现了现实主义戏剧所能达到的高度;一台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伽利略传》。作品生动地塑造了一个既动摇神权统治又屈服于教会淫威、既推动科学发展又阻碍社会进步的复杂的人物形象,第一次向中国观众展现了布莱希特叙述体戏剧和间离(疏离)效果的魅力。叙述体戏剧的观念与技法,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与接受,促使一大批段落体、多场景、组合戏剧……作品的涌现,也引发了导演技法、舞台观念的一系列变革,为以《绝对信号》为标志的小剧场探索作好了准备。
王墨林:林老师认为姚一苇和李国修在台湾的剧场文史或剧场美学有重要的位置。我到了现阶段,才转变对他们的看法,中间有个辩证的过程。年轻的时候很多观点没有辩证,可是我现在了解姚一苇的重要性,那就是,他在做台湾所缺乏的戏剧理论研究时,提出一个剧场现代性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反而没有人在探讨,很可惜。提到姚一苇和剧场现代性,必须了解同时期的张晓风的重要,她的重要不是因为其戏剧美学价值高,而是因为她的剧作反应出在那个时代的问题:当时的人在发展现代、当代剧场的时候,如何进行现代性的探索。我们今天才知道兰陵剧坊心理剧场的那一套发展到后来为什么变成了波瓦的被压迫者剧场,而被压迫者的剧场为何变成身心灵剧场。台湾为何也走了同样的路径?台湾在剧场发展的过程中有太多类似的议题,我们都没有进行历史梳理。我们引进不同形式的剧场美学,要如何教育?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和我们自己的历史状况有何呼应?好像都没有好好思索,一味地拼命模仿人家。
而中国大陆在林老师讲的《绝对信号》之后,先锋戏剧的发展是不是出现了类似的历史路径? 有没有人提出批判和重估?该如何批判?当到了我这个年纪回头再看姚一苇还有李国修,反而看见作为一个外省人,他不只是将自己外省移民的历史甚至是将自己的生命史表现出来,更艰巨的是展现生命史和现实、政治如何联结。剧场是人活动的地方,也是创造人的活动、分享人的活动的地方,美学当然重要,可是当我们没有思考剧场的作用、功能性与存在,就会变成单纯的创作竞赛罢了。我重新看当年很多作品,深深感觉到他们背后的历史暴力对他们的影响折射到剧场,然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台湾是比世俗化更惨的平庸化,就是被统独二元论宰制的社会体制、被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人权概念异化,被资本主义异化:货币作为一种人跟人、人跟思想的交换,还有人跟艺术交换的异化。那种异化反映到年轻人的戏里,而在对岸,我们也看见资本的力量无所不在,穿透了年轻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个时候我们重新去探究台湾或大陆前辈戏剧家如何在历史局限下,探索现代性的挣扎和过程对我们会有价值性启发。我们好像太快直接去拥抱去历史化的后现代,面对新一波全球资本主义的控制,后现代的去历史、去深度太快太容易,我们要找回自己历史的轨迹,所以该是我们重新审视这些前辈的生命史和创作史的时候了。
许仁豪:我们从1988年这场对谈开始回溯,其实试图要建立一个历史,了解冷战对我们的意味为何?80年代起,很多的历史书写认为冷战已经终结,但冷战真的终结了吗?现在回头看三十年,我们和冷战到底有多远,而现在的台湾到底是什么状态?很自由,百花齐放,电视台都有九十几个台,艺术也变成像美食街一样能够被消费,节奏变化非常快速,就像今天的网络视听一样,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到另一个异次元空间,而这一切看起来很自由很多元的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在对岸,我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后工业文化现象。我想两位前辈一直在讲的历史,大墨刚刚讲的回顾前辈的生命感悟都会是帮助我们思考当下状况的契机。大墨这本书当时有一个在野的姿态,也就是刻意处在体制外的位置。但时代演变到今天,所谓的体制内外的界线何在?包括消费行为,我觉得我们在学校里面对抗的是更大的体制,就是整个资本主义养成的那套控制人注意力的机制。今天学校的课堂已无法去对抗手机,我觉得这套资本养成的视听系统才是体制,这个体制是看不见的,它已经不存在于任何具体的建筑里面,它散布在整个科技消费社会的网络里,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历史的重要性? 因为后工业消费社会创造的景观娱乐社会,太容易让我们以为乌托邦已经降临,而把历史发展的生存矛盾一笔消解。我觉得重新批判性认识历史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所对抗的情形是如何被资本的力量塑造的。而这又关乎今天哲学性生存的议题: 或许回到哲学可以提问的传统,或许剧场提问的功能和剧场在人类社会起源的本质是有关的。
林克欢:我赞赏布莱希特的说法:今天的戏剧是分裂观众的:实验戏剧、商业戏剧、主流戏剧、宗教剧、起治疗作用的戏剧活动……不同的戏剧为不同的观众服务。你不可能制作一出戏,既要高台教化,又要老少通吃,这是不可能的。
不少人都在谈论“戏剧要回到它的源头、本体,主张舞台表现的仪式化”,但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1979年,希腊国家悲剧院访问北京,在座谈会上,希腊国家悲剧院院长阿·米诺蒂斯告诉我们:我们非常羡慕东方戏剧,因为你们的舞台形态、戏剧传统四五百年来始终没有中断。而你们所了解的希腊戏剧,尤其是悲剧中的歌队,已没有人知道当年的具体形态怎样。出现在今天舞台上的希腊悲剧的歌队,完全是导演根据文献资料的重新创造。所谓希腊悲剧的源头、传统,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当代人根据理解进行的一种重新建构。
在今天这个后工业时代,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政治、经济、文化、家庭、舞台……都走向断裂与碎片化。但旧传统、旧体制、旧思维方式,仍盘根错节地残留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旧的未去,新的未生,戏剧在全面世俗化、平庸化的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实验空间。
王墨林: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对生命的感触让我学习到很多,他拍的最后一部电影《永远的一天》常常让我想到自己的状态。我们现在看到的剧场里面少了这种能量、动能,只用嘴巴讲话然后起个制式的舞蹈动作,所传达的精神世界是没有能量的。你没有看到社会对导演、演员、剧组的压迫,没有看到这个社会体制对他们的排挤,永远看到自己心里面非常个人的感情、私有化的欲望。在70年代台湾的《剧场》杂志,刊载的文章几乎都是翻译文章。艺术家翻拍的影片,基本上也都是西方的那种无厘头、前卫电影,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历史中为什么那么重要?是因为我们看到的艺术作品反映了时代。有些问题到了三十年以后并没有被解决,那时候我们充满了左翼运动的想法,反对资本主义、希望革命和反抗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追求颠覆性,“颠覆”这两个字是在80年代小剧场运动时开创出来的,那时候有的人还觉得颠覆太强了,可是颠覆就是反其道而行,给我们带来的是身体的动能,当身体这个概念在剧场出现以后,不管是对思考文化现象,还是技巧记忆的磨练,艺术家通过身体来探索主体的存在状态。我们历经四十年的戒严,到1987才解严,说实话到现在也适应不了解严状态,只不过现在戒严从外部世界转到心理层面。那时候我们内心有一种长期被戒严压抑的声音,在小剧场里面,我们觉得应该创造一个乌托邦,在戒严时代,大家在历史氛围与脉络中在寻找什么?想要反抗突破什么?这个才是重要的,而乌托邦的追求在今天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回头看才会知道未来要怎么走。
许仁豪:我想两位前辈都给了我们重新评估当下剧场状况的一些方法,而这种剧场创作远离人精神本体,变成私人化欲望满足与消费的状况,我想在两岸同时都在发生。80年代或许是今天这个全球境况的起始点,重新回访那个历史节点,希望研究当代的剧场学家或是当下的青年人可以更历史地去看待那个节点的转变,在两岸小剧场的涌现都有呼应其自身社会变革的需求,这和各自的社会具体状况、现代性的追求有何关联? 而放在更大的全球冷战历史结构来看,两岸的交流其实是历史动能下的必然结果。要如何重新去回望这一段历史并且做出前瞻? 我想两位都给了我们同样的答案。理解两岸前辈的心路历程和他们在艺术追求上与现代性的挣扎,在娱乐至死后的真实此刻,对两岸的年轻人都是重要的。
(高雅芳 文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