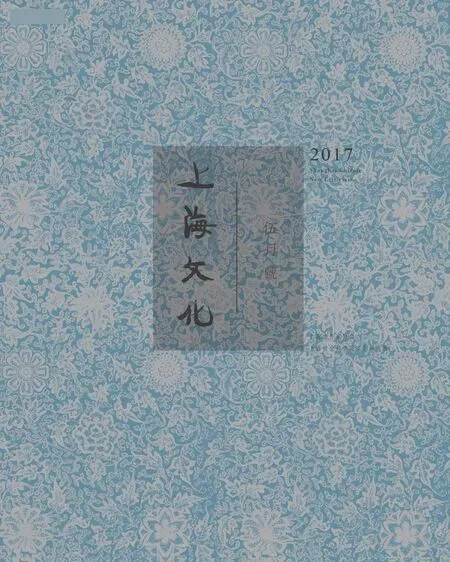1952年后张爱玲的文学立足
姚玳玫
1952年后张爱玲的文学立足
姚玳玫
1952年离开大陆,对于张爱玲来说是既有一切的连根拔起。在海外,立志以写作为生,她除了要确保素材资源的取之不竭和文学才情的充沛鲜活外,还得建立自己的读者圈,形成自己的图书市场,她必须与书商、读者达成一种良性关系,就像当年她在上海一样。从她跨过深圳罗湖桥那一刻起,她得为在新环境中立足而拚搏。
以香港美新处为靠山:冷战格局中的市场铺排
1952年8月张爱玲到香港大学复学。其时的香港,鱼龙混杂,如何安妥自己,她尚无头绪。事后,她致夏志清的信述及:
港大有个老教授帮我弄入境证从大陆出来,这件事原经手人是我母亲的朋友,夫妇俩都在港大教书,异常怕事,硬要我至少暂时重进港大,反正原来的奖学金仍在。读了不到一学期,因为炎樱在日本,我有机会到日本去,以为是赴美捷径,匆匆写信给Registrars Office 辞掉奖学金。不知道这份奖学金还在开会讨论,老教授替我力争,然后发现人已不在,大怒之下,我三个月后回港道歉也没用。学校叫我补付学费,付满了以为了事,但是后来一次应征一个译员的广告,没想到是替个英国什么东南亚局长做事,录取后一调查,查到港大,竟有人说我有间谍嫌疑……
到港大复学,是她入境的理由。但张爱玲并非真的想去复学,是那位怕事老教授硬要她“至少暂时重进港大,反正原来的奖学金仍在”。这才会入学不久她就擅自去日本且辞掉奖学金之事。之后,应征译员广告,录取后对方来调查,竟说她“有间谍嫌疑”!这件事透出“二战”结束后香港作为政治角力地带的复杂情形,配合冷战而来的间谍机构遍地皆是。那个英国东南亚局应属于这类机构。在这里,即便卖文为生,也得背靠这类政治机构。
张爱玲以译员受聘香港美新处,情况应与应征英国东南亚局相似。但进入后不久,她提出要写小说。她显然有备而来,以她的文字才华和生活体验,两作均非其时应命之作所能相比的。麦卡锡说:“初读《秧歌》头两章,我大为惊异佩服。我自己写不出那么好的英文。我既羡慕也忌妒她的文采。”恰好美国名作家、普利策小说奖获得者马宽德(John P. Marquand,1893-1960)访港,读了《秧歌》头两章后说,“我肯定这是一流作品”。在香港美新处和马宽德等推荐下,1955年英文版《秧歌》在美国顺利出版。《纽约时报》及其书评专栏、《星期六文学评论》、Herald Tribune、《时代》周报发表书评予以推介。这是张爱玲出国后首次在美国出版小说。此举似乎让她一下子站到国际舞台上,其欣喜程度不亚于当年《传奇》的出版:“本来我以为这本书The Rice-Spond Song(《秧歌》)的出版,不会像当初第一次出书时那样使我快乐得可以飞上天,可是现在照样快乐!”她明白“当日出书容易,现在难”,她称:“闻得新书发行,面色之感动震恐状如初度闻示爱时。”夏志清也说:“想来因为《秧歌》已出了英文版,她才决定来美国。”她留意林语堂、韩素音、赛珍珠一类华裔作家在英语小说市场上成功的经验,自信自己的能力较之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实际上,《秧歌》的出版,与其说是一次市场成功,不如说是冷战政治格局给予她的一次机会。《纽约时报》等书评,欣赏的是《秧歌》暴露了民生艰困的内幕,关注点显然在其政治指向上。更值得注意的是,《秧歌》“先写英文,然后自译为中文”,而中文版比英文版更早在香港见刊。1954年中文版《秧歌》在香港美新处的机关刊物《今日世界》连载,同年7月由天风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由资金雄厚的美新处一手操办,发行量不得知。接着,她又推出《赤地之恋》(以下简称《赤地》)。《赤地》1954年10月由天风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比《秧歌》出版迟两个月,也是美新处推动的结果。政治宣传运作不同于市场运作的另一证明是,《赤地》在运作过程中的卡掐。相比于《秧歌》,美新处对《赤地》的介入明显加强。从张爱玲事后对美新处干预创作的抱怨、从该作先以中文版在港、台、东南亚及全球华人圈中发行看来,《赤地》应该是美新处部署的文艺宣传的重头戏。有意思的是,该作在出版单行本之前并没有先由《今日世界》连载,而且“印得一塌糊涂,幸亏现在我正为了《秧歌》在美国出版事而很开心,否则火气更大……”这种草草了事的做法,不符合财大气粗的美新处推出“重头戏”的作风,显然别有原因。英文版《赤地》1956年由美新处旗下的香港友联出版社(Union Press)出版,几乎没什么影响。1957年移居美国的张爱玲又就《赤地》在美国出版一事作了多方努力,都没有结果。
美国出版商不愿意出版《赤地》,可能与市场有关。但香港美新处没有让它在《今日世界》连载,则是人为的安排。二十年后平鑫涛说及《赤地》在台湾出版被卡时称:“小说中描写共产党员辱骂国民党政府,甚至对先总统蒋公也颇有讥讽,在当时的书刊检查制度之下,难获通过,若大幅删改那些敏感的部分又伤害了原著的精神,以出版社的立场而言,委实两难。”关于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政治生态书写,自然会涉及诸多重要人物,如“蒋介石”、“杜鲁门”、“毛泽东”、“陈毅”之类。《赤地》有这样一段文字:“刘荃和机关里的一个通讯员一同推着一辆囚车,囚车里面是孔同志扮的杜鲁门。另一辆囚车里面是张励扮的蒋介石。乐队的调子一变,杜鲁门与蒋介石从槛车里冲了出来,戴着巨大的彩色面具跳跳踪踪,像西藏的‘跳神’仪式。”不管这段文字的真正指向是什么,它已隐含对蒋公的不敬。对于美新处来说,反共它可以不遗余力,得罪蒋政府,则是它不愿意干的。正是诸如此类的细节,堵住了该作的出路。
政治是把多刃剑,在上面游走,随时会有意想不到的触犯。在敌我两分法格局中,非我即敌,其对政治正确性和忠诚性的要求,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初次尝试政治小说书写,穿行于市场与政治之间,张爱玲有一种“心理的错综”。《秧歌》出版的成功让她有点忘乎所以,刺激她旋即列出后半生的创作计划,所谓七部小说计划。但《赤地》出版的勉强,也让她明白政治的不可通融。以美新处为靠山,她开始其去国后重建读者市场的尝试。她的确出版了两部小说。实际上,这是一个虚幻的市场,她的成功和挫伤,都是冷战巨掌拿捏出来的幻术。短短三年,她在香港并没有建立自己的读者市场,其起步是靠冷战机构资助而获得的。到美国之后遭遇的冷落和举步维艰的现实,证明香港三年她并没有打下什么基础。倒是在香港结下的人脉关系——有电影人兼文学经纪人的宋淇及其夫人邝文美,有热爱文学、乐意将手中的冷战宣传经费用于扶持文学创作的麦卡锡及其美国朋友马宽德等,为张爱玲在美国的生存和立足提供长期的帮助和支持。这些朋友均有香港美新处圈子背景,他们的立场取向,影响了张爱玲,为她日后的路子铺定了色泽。
无论如何,香港三年,张爱玲已经完成其心理转换和人缘朋友圈铺垫,有如过河的卒子,她只有往前走了。
游走于三角地:美国的冷、香港的实和台湾的热
张爱玲决心移居美国,可能有其更实际的考虑。“二战”结束后,美国是唯一没有受到战火焚伤且经济富庶的国家。1950年代美国黄金的储存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万能的美元统治着整个地球的经济市场”,移居一个与自己没有直接的血缘亲情联系且经济富庶的国家,张爱玲对未来的生活还是怀有信心的。
这是一个虚幻的市场,她的成功和挫伤,都是冷战巨掌拿捏出来的幻术
依据美国政府1953年颁布的难民法令(Refugee Act)提出申请,由美国公民的香港美新处处长麦卡锡作担保,1955年张爱玲移居美国。没有学历背景的难民起点,她其实沾不到美国的光。初到美国,她住纽约87街救世军办的性质几近难民营的职业女子宿舍,翌年2月在生活无着情况下向位于新罕布夏州彼得堡的麦道伟文艺营提出住营申请,由原《秧歌》推荐者马宽德(Marquand)和出版人、司克利卜纳(Scribbner)公司的主编哈利·布莱格(Harry Brague)作担保人,她获得这项申请。《粉泪》(Pink Tears)在文艺营动笔,这是她美国写作生涯的开始。3月份正值彼得堡零下二十度,在完全陌生的冰窟里,关起门来写过去的故事,那种怪诞感,从此伴随着她。几年后她给夏志清的信,讲述这段经历:“(Pink Tears)英文本是在纽英伦乡间写的,与从前的环境距离太远,影响很坏,不像在大城市里蹲在家里,住在哪里都没多大分别。”她对美国冰寒住营之事的抱怨,与及后Pink Tears的出版受挫有关。作为她到美国后的第一个成果,Pink Tears 1957年初完稿后即联系出版,谁知四处碰壁,原出版《秧歌》的Scribbner公司“不准备选用她的第二小说,即《粉泪》”,上述Knopf那位编辑称它“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美国出版界对她的写作风格并不欣赏。初到美国,从居住环境的冰寒到出版商的冷漠,让她领略真味。
正是这种处境,她迅速走向第二次婚姻。1956年8月19日致邝文美的信,她平静地描述了她的新婚姻:
十四日我和Ferdinand Reyher 结婚——Ferd是我在MacDowell 遇上的一个writer……他以前在欧洲做过foreign correspondent,后来在好莱坞混了许多年doctoring scripts,但近年来穷途潦倒,和我一样 penniless,而年纪比我大得多,似乎比我更没有前途。除了他在哈佛得过Doctor & master degree这一点想必approved by吴太太之流,此外实在是nothing to write home about。Fatima(炎樱)刚回来的时候我在电话上告诉她,说:“This is not a sensible marriage, but it’s not without passion。”详细情形以后再告诉你,总之我很快乐和满意。
该信末还附有赖雅的问候——诚恳,友好,慈爱。关于张爱玲与赖雅这段“乏善可陈”的婚姻,各有各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对左派的反感并没有妨碍张爱玲选择赖雅。她在《忆胡适之》中说,她对左派有本能的反感,中国左派的影响不像西方,“只限1930年代”,话里有话。赖雅洋溢左派激情的作品的确多作于1930年代,他后来对《秧歌》的欣赏,对《粉泪》结构的提建议,显示了他们的志趣相投。1956-1958年,他们在不断地申请新的住营、拮据地搬家、英文版小说《粉泪》、《赤地》出版受挫、赖雅再度中风及恢复的动荡中渡过。至少在张爱玲赴港台谋求生路之前的一段,他们生活居无定所。1961年10月张爱玲赴台北时,同时决定搬离旧金山。赖雅再次向亨亭屯·哈特福申请住营,并将他的东西寄放在华盛顿的女儿家。那天他送张爱玲到机场,“再返回到他们的公寓时,家具已经变卖,房中空荡荡的一片,人去楼空,心也碎了”。那是一种连根拔起的感觉。
初到美国那五六年间,除了住营外,张爱玲谋生机会主要靠香港朋友提供——“来自香港宋淇所提供的写作任务,还有麦卡锡所给的翻译工作。”1956年宋淇加入香港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任制片总监,排名第二”。1955年11月至1963年10月,张爱玲在宋淇介绍下为电懋公司写过八部已拍摄的电影剧本,几个电影故事大纲和两部未拍摄电影剧本《红楼梦》、《魂归离恨天》。这成了她在美国头几年的主要收入。每个剧本稿费估计约七八百美元,1962年1月张从香港致赖雅信提及:“他(指宋淇)建议我多留一个月左右,再写个剧本。我当然同意,多赚几乎八百美元,照我们在旧金山生活标准,约四个月开销,帮助解决如何度过六二年的难题。”宋淇在张爱玲1963年1月24日信上注:“2月22日寄去支票美金$788.88”,2月27张爱玲回信:“剧本费收到了”。一个剧本八百美元左右的稿费,足够她与赖雅四个月开销。这笔收入是多么重要!
麦卡锡方面给她提供的帮助是翻译小说;将《秧歌》改编为广播剧,供哥伦比亚广播电台上播;为“美国之音”编写广播剧。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麦卡锡给她的一份美差:
他奉美国务院使命找张爱玲翻译陈纪滢反共小说《荻村传》(Fool in the Reeds)。一九五九年由香港虹霓出版社(Rainbow Press)出版,这个出版社背后支持者就是美新处。这本书印了七版,每版三千册,共二万一千本,美新处把这些书分送东南亚各国及世界各国,作为反共宣传。当时美新处付给张爱玲的翻译费高达一万多美金,凸显出当年“反共”为重要任务阶段。
相比之下,为电懋写剧本可能不如为麦卡锡翻译小说收入多。由政府投资的冷战运作总比受市场规律牵制的商业运作要财大气粗得多。写剧本背靠市场,受制于商业运营规则,辛苦且有不被录用的风险。1962年初张爱玲在香港那段日子,为赶写剧本熬得眼睛出血,腿胀脚肿,“阴郁寂寞的生活使我格外苍老”。如果不符合邀约方的要求,可能还会劳而无功。“通常她会先写个大纲给电影公司,若公司有兴趣才会动笔写成剧本。有些大纲会被公司拒绝,如她跟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合作的《香港妻子》就无人问津。”何况还有呕心沥血劳作半天而后石沉大海的呢!为电懋写剧本,她夹在人情友谊、谋生需求和工作舒心程度三者之间,可谓一言难尽。在香港期间,她同时为麦卡锡翻译小说。她致赖雅信说:“这几天有空,为麦卡锡翻译短篇小说。想到我们的家,就觉得安慰。”翻译一部《荻村传》,可获一万多美元的翻译费,相当于写十来部剧本。还有些副产品,如1959年她翻译《荻村传》的同时,又将之改写为剧本。1964年她到“美国之音”工作的第一项任务是将《荻村传》“改编为若干半小时的广播剧”。冷战时期的美方宣传,东南亚是重要的一块。这些参与,也让张爱玲走近东南亚。她在《忆胡适之》中提及《赤地》“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自己很不满意”。赴台时她提及了解东南亚是其原因之一:“有两支想写的故事背景在东南亚,没见过没法写,在香港住个一年光景,希望能有机会去看看。”这两个故事中是否包含《少帅》,不得而知。但这些考虑应与美新处建立东南亚宣传阵线的方向有关。
1961年10月的台、港之行,是张爱玲将美、台、港三角地相联系的开始。其时,麦卡锡已是台北美新处的处长。喜欢文学的他,利用其职权,支持《现代文学》,培养一批台湾年轻作家。“《现代文学》出版时,他就订了七百本。他选了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我的小说(指王祯和)各一篇翻译成英文,书名为New Voices……”经济上的资助——订购杂志和文化上的推介——组织人员翻译台湾作家作品,既将当时一批台湾年轻作家推上国际舞台,也将这类创作纳入美国在东南亚实施冷战宣传的范围中,所谓New Voices有其双关含义。他称,这是官方与个人的“快乐”合作:
为电懋写剧本,她夹在人情友谊、谋生需求和工作舒心程度三者之间,可谓一言难尽
美新处乃政府机构,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然而香港美新处同仁比较关切出版我们认为是文学类的出色作品。几种不同的个人与官方的兴趣快快乐乐会合起来。在台北美新处任内,为了出版台湾年轻作家毫无政治色彩的作品,我必须向上级陈情。我辩称这些作品与北京外语出版社那些英语作品迥然不同。他们听从了我们的建言。但是我个人真正的兴趣,当然在于让那群正要改变索然无味台北文坛的惊人的年轻作家,在台湾之外引起注意。个人与官方的兴趣再度朝同一方向奔驰。
从大陆自我放逐之后,美国的冷,香港的实,都让张爱玲碰壁,唯有台湾例外
麦卡锡将张爱玲与台湾拉近。1961年10月他以东道主身份邀张爱玲逗留台北,同时安排她与殷张兰熙、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王祯和等一群年轻文学作者会面座谈,共进晚餐。这是继1957年台湾《文学杂志》正月号刊载她的小说《五四遗事》、同年第四期刊载夏志清著、夏志安译《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之后,张爱玲真正的走进台湾。
到美国第一个十年,张爱玲不可谓不努力。英文小说由《粉泪》而《北地胭脂》、《少帅》、《易经》两卷,近百万字的书稿完成于这个期间。而美国出版界给她的,始终是一副拒之门外的冷面孔。甚至可以推测,《秧歌》如果不是迎合冷战题旨,也会落得同样的命运。其中一层无法逾越的隔阂是,美国人对东方的固态想象,不喜欢张爱玲那种揭丑笔法。她说:“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面对这层隔阂,即便她与美方站在冷战的同一阵线上也无法被接纳。她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秧歌》成功出版的幻象,让她低估了在美国入行的艰难。没有学位,除了写作不想以其他方式生存,她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奔突,依靠香港朋友提供谋生渠道,游走于香港电影娱乐市场与国际冷战政治文学邀约之间,以为他人作嫁衣裳消磨着自己的文学才华。离开大陆已经多年,她的想象力和素材来源依然停留在1952年之前那个中国的生活层面上,她用揭丑、捅娄子方式不断重写中国老家庭的故事,与战后美国读者的东方想象出入颇大。即便像Keene那样的东方通,也觉得“许多地方‘不是那么回事’”。她深知“语言障碍之外的障碍”有多么严重。
1950-60年代海外的中国叙事和文学市场直接间接地受控于全球性冷战大背景,作为政府行为的各类文宣机构的介入文学,引导着市场走向。从大陆自我放逐之后,美国的冷,香港的实,都让张爱玲碰壁,唯有台湾例外。无论文化根性或是冷战格局中的政治取向,她与台湾之间,更具有和谐性。台湾作为张爱玲原乡的替代物、“中文”世界的延伸,有更为特殊的牵系。自1957年台湾《文学杂志》上夏志清兄弟联手将她推出,至1967年她与台湾皇冠公司签署出版全集合同,以“台湾”为中介,她步步走向中国现代文学舞台的中心。
冷战思维结构中的学术机缘和社会推动
张爱玲的进入评论界视野中,始于1944年。迅雨的《论张爱玲小说》和胡兰成的几篇评论文章,构成早期一个小小的热潮。连同张爱玲本人也卷入其中,以迅雨的文学纪念碑论与胡兰成、张爱玲的反纪念碑论,构成一次冲突。那是文学事关社会还是事关个人的观念冲突。但总体而言,那时张爱玲并没有进入主流学术界的视野中。抗战胜利后她的地位更加尴尬,有女汉奸之嫌的负面形象,1952年的离开大陆,令她很难为建国初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所认同。
踏出国门之后,张爱玲开始寻求她在海外的文学/学术支持。1954年秋《秧歌》出版时,她即将此作寄给正蛰居美国的胡适,期待得到这位“五四”新文化领袖、其时也是国共双方对垒中的敏感人物的关注。两个多月后她收到胡适的回信。胡适称他仔细地将《秧歌》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胡适将小说归结为“写的是‘饥饿’”,却没说出饥饿的缘由。他不谈小说的“政治”题旨,只谈小说的“艺术”特色。他引文摘句,盛赞其平淡自然的细致工夫。将《秧歌》寄给胡适,张爱玲对胡适的政治文化影响有所期待。这位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在国共分立时选择跟随蒋介石。之后受蒋委托,到美国充当“不是大使的大使”,以一介书生,游说于美国政界,争取美政府对蒋的支持。1949年8月《中美关系白皮书》公布,美国对蒋政府有撒手不管之意,令胡适陷入尴尬境地。之后他蛰居纽约,那七八年间没有固定职业,状如流亡,境况狼狈,“惶惶如丧家之犬”。加上,1950年代大陆两次大规模批胡,蒋氏父子对他也有戒心,他真有些“左右挨打,站在夹击的中间了”。在这种背景下,他读了张爱玲的《秧歌》,并于1955年底,接受了初到美国的张爱玲的两次拜访。他对《秧歌》的喜欢,不可能只是对其“艺术”感兴趣,更可能从中获得一种政治声援——与他在冷战境遇中的认知有吻合之处。居美期间,他热心于做中共研究。1950年夏他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长文《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表达他对自西安事变以后苏、美、国、共策略局势的总体分析和带倾向性的褒贬。1957年他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中国大陆的反共抗暴运动》演讲,将1956年匈牙利事件与中国的反右扩大化相比拟,称当时,“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已被剥夺净尽”。后文与他从《秧歌》中获得某些感性信息相吻合。《秧歌》证实了他对中共治下现实的认知。
可作旁证的是,胡适对台湾作家姜贵的反共小说《旋风》也予“热烈棒场”。收到姜氏寄书,胡适即予回信,不仅夸奖其白话文的流利痛快,更对其内容大加赞赏。1960年秋,胡适还发动学人,推荐《旋风》为当年度台湾文艺奖金的候选作品。当有学者认为该作“太残忍”,“使人感到可怕、可厌、气闷、失望”,胡适仍为之辩护。胡对《秧歌》、《旋风》感兴趣背后有一种政治热情。夏志清也将两者相联系,他借高阳《关于〈旋风〉的研究》的话,称姜作“是一部能够发人深省的研究共产主义的专书,与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占着同样重要的地位”。有意思的是,其时这类反共小说,寻找学术支持的路径几乎一样。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初版本)附录也有论姜贵《旋风》一节。张爱玲、姜贵文学的学术支持者,是政治倾向相同的胡适、夏志清一类学者。
1950年代,美国华人学者多为亲台派一脉。1951年初完成博士论文的耶鲁大学英文系学生夏志清,遇上“以反共著名的中国之友”、耶鲁大学政治系教授饶大卫(David N.Rowe)。饶刚得到政府一笔资金,编写一部《中国手册》(China: An Area Manual),供朝战“美国军官参阅”。夏称:“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二人一谈即合拍。”参与《中国手册》项目,撰写《文学》、《思想》、《中共大众传播》及《中共人物》等章节。把原本研究西洋文学的夏志清带进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文学》这一章重点却放在现代文学上,占全章篇幅三分之二……把耶鲁图书馆所藏的茅盾、老舍、巴金等作品都略加翻看。此外还有一批尚未编目的中共文艺资料……”这段经历促成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撰写,用王德威话说,《中国现代小说史》的顺利出版及其在美国学界产生的影响,得助于“冷战期间特有的中国信息真空期”,“那是一本让他在西方扬名的著作。一个学科也因此建立起来了”。
现在看来,冷战时期特定的思维方式干扰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史”的客观论述,书的章节安排和论述口径都明显受政治思路的影响。性情中人的夏志清一直不讳言他的立场,《中国手册》最终“未被正式纳用”,原因是美国军政方高级官员审阅时,“发现全书反共立场太强硬”,这可能与重要章节撰稿人夏志清等立场“强硬”有关。摆在这种格局中来看1957年先后发表于台湾《文学杂志》、后来收入《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评〈秧歌〉》,其学术的客观性和公允性就值得怀疑。
1957年台湾《文学杂志》元月号刊载张爱玲的《五四遗事》,夏济安给友人的信中称:“……真不能相信原文是用英文写的。张女士固熟读旧小说,充分利用它们的好处;她又深通中国世故人情,她的灵魂的根是插在中国泥土深处里,她是真正的中国小说家。”4月号刊载夏志清著、夏济安译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6月号又刊载《评〈秧歌〉》,二文及后均收入《中国现代小说史》中。
夏志清早在1944年夏天“一个沪江同学的集会上”就见过张爱玲。但当时张的作品没有引起他的兴趣。“我在上海期间,即把钱钟书《围城》读了,当时张爱玲的作品更为流行,却一直没有好奇心去读它。”如果不是放在1950年代那种特殊的背景下,夏志清对张爱玲也许不会如此激赏。写小说史,“耶鲁那时中文部门书籍极少”,跑哥大图书馆又相对麻烦,所以“香港好友宋淇、程靖宇二兄邮寄赠”资料正好解决了眉睫之急。其中,“香港盗印张爱玲的两部作品,《传奇》与《流言》,也是宋淇赠我的,使我及早注意到这位卓越的作家”。此时伊始,他才真正注意到张爱玲。
夏对张的关注,自《秧歌》进入。《张爱玲的短篇小说》从《秧歌》谈起:
《秧歌》作风严肃,销路当然比不上同样以中国为背景可是带有商业性的伤感气味的最近几本小说:韩素音的《生死恋》(Love is a Many-Splendored Thing),以及赛珍珠的《慈禧太后》(Imperial Woman)。
美国报界每季都要挑出十几本新出的小说,乱捧一阵。因此,报界的棒场,也不足以使大众注意到这本书的价值。除了报界的好评以外,美国文坛对这本书似乎不加注意。《秧歌》真正的价值,迄今无人讨论;作者的生平和她的文学生涯,美国也无人研究。但是对于一个研究近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殊菲儿(Katherine Mansfield)、安泡特(Katherine Anne Portor)、韦尔蒂(Eudora Welty)、麦克勒斯(Carson McCullers)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夏志清予《秧歌》以高度评价。之后,他又单独撰文《评〈秧歌〉》。从这里进入张爱玲的世界,他更能找到自己的感觉:以专制政治为参照和驱动,体察在政治高压下人性、人情受扭曲之情形,其学术演绎和才情发挥更为酣畅从容。从《秧歌》谈到《传奇》,用“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不朽之作”、比英美若干现代女文豪“还要高明一筹”、“《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之类“独断”语气,论定张爱玲作品的旷世价值。《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十五章《张爱玲》的篇幅比第二章的《鲁迅》几乎长一半。在“史”的价值考量上,他大大加重张爱玲的筹码。
其时,夏志清对大陆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有逆反心理。他推重市民作家张爱玲,建构日常生活叙事,逆抗“五四”尤其是1930年代以左翼文化为坐标而建立起来的宏大叙事及其评价规则。在这种背景中,张、夏相遇,张爱玲研究在海外得以起步,进入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中,成为文学史中去政治化叙述的一个范例。王德威说,夏让“上海的通俗女作家首度与鲁迅、茅盾等大师平起平坐……为日后的‘张学’研究,奠定下基石”。“夏先生对张爱玲有‘知遇之恩’,没有夏的登高一呼,张爱玲神话不会有如此精彩的开始。”刘绍铭也说:“《小说史》问世前,张氏作品鲜为‘学院派’文评家齿及。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她极其量不过是一名新派鸳鸯蝴蝶说书人而已……夏先生的品题,使我们对张爱玲作品的看法,耳目一新。也奠定了她日后在中国文坛的地位。”
更有意思的是,及后三四十年间,张爱玲与夏志清及其师生群建立了私人友谊。从文学知音到私人朋友,友情帮助跨越学术的界线,达成一种更为默契的互动关系。从相关书信看,1962年张爱玲从香港回美国不久,张、夏开始有通信联系。之后,张爱玲在美国几所大学获得短期项目,都是夏氏及其师生朋友作为推荐人。这些任职,促成了国语本《海上花列传》和《红楼梦魇》的问世。1966年,作为张爱玲的“全权代办”,夏志清在台湾与平鑫涛商谈“有关《怨女》的‘连载与出单行本事’”,并向平建议出版张爱玲文集,从而开启了皇冠出版公司与张爱玲几十年的合作。夏志清以其在美国、台湾两地的学术影响,介入张爱玲作品从学术鉴定到出版发行的一系列活动,成为张爱玲文学传播最强有力的推手。
作为文学知音,夏、张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建立于冷战政治文化想象相一致的基础之上。矫枉过正的政治激情和独到的文学眼光,使夏氏激赏张爱玲。事过境迁之后,夏也觉得当年说了过头话。2000年10月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的“附录”收入夏志清当年那两篇文章《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评〈秧歌〉》,文尾有几行附言;“本文原为介绍张爱玲给美国读者而写,因此讨论的时候态度也许显得过分‘热心’。假如这篇文章能够使国人也注意到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重要性,她将能得到更公允的批判。”张爱玲去世时,夏的悼文也对原来那种过分热情的评价有所修正,他说:“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表示敬佩,同时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为此,我们公认她是名列前四、五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张爱玲下阶段文学传播的另一位推手是宋淇。作为张爱玲受聘香港美新处期间的同事兼好友,1957年宋淇将张爱玲小说介绍给夏志清,使《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张爱玲留下位置。1965年宋淇向台湾皇冠老板平鑫涛推荐张爱玲,为张、平合作铺路,疏通张爱玲中文作品在港台出版的渠道。宋淇与其说是一位评论家,不如说是一位文化经纪人。1956年他转向电影界,加入香港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成为刚刚起步的香港电影界的台柱人物。与夏的学院派作风不同,作为宋春舫的后人,宋淇不仅有话剧、电影经验,更有出色的经纪人头脑,懂得抓住商机,懂得投合市场又规避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张爱玲居美初期,为电懋写剧本成为她主要收入。以致1962年已入美国籍的她重返香港,有开拓谋生渠道之意。
1976年,宋淇以林以亮为署名的《私语张爱玲》在《明报月刊》3月号发表,同时连载于《联合报》1976年3月1-2日,这篇出自张爱玲挚友手笔、以“私语”口吻写的、追求good taste的文章,带来一个新的张爱玲热潮。作为在野的兼及经济运营的文化人,宋淇有另一种敏感,他对大局的判断相对中立,有其务实而善于谋划一面。《私语张爱玲》就充满这种“谋划”:“处处在为你宣传而要不露痕迹,傅雷、胡适、Marquand [马昆德]、李丽华、夏氏昆仲、陈世骧都用来推高你的身份,其余刊物、机构都是同一个目的,好像我们在讲一个第三者,非常客观似的。”1977、78年,台湾左右两派正就“乡土文学”展开激烈论争,是一段敏感时期。1977年,围绕着《色·戒》,张、宋有频密通信。宋对女主人公王佳芝的身份非常担忧,他认为一个抗日女间谍事到临头出卖自己人,一般读者不会接受,尤其是对于其时台湾国民党政府来说,他们的特务绝对不会变节。台湾是张爱玲最大的市场,如果审查没通过,损失就大了。宋建议,一定要把女主角写成“一个普通人受特务安排,而去执行一项特别的任务,甚至可以说连外围都不是”。宋淇竭力阻拦的另一部作品是《同学少年都不贱》:“《同学少年都不贱》一篇请不要发表。现在台湾心中向往大陆的知识分子很多,虽不敢明目张胆公开表态,但……攻击无所不用其极,想尽办法打击。你……自然成为对象,好在你有其他出色的作品,为你撑腰的有夏志清等学院派和很多作家,其中最出力的是朱西宁。”宋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中国日报·人间》编辑桑品载一段记述可为佐证:
……终于在朱西宁处获得她在美国的地址。正要与她联络时,忽然间接获得警告,表示张爱玲的政治立场有问题(那时爱用“思想有问题”)。主要理由是因为她曾是胡兰成的妻子,而胡兰成做过汪精卫的秘书,是汉奸。由此而引申出她离开大陆后在香港所写在美国新闻处出版的《今日世界》上所连载的长篇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的问题。在那个年代,文字检查党政军都有专职单位,副刊编辑被怀疑思想有问题而勒令去职,至于被捕入狱者大有人在(如林海音、柏杨、童尚经;童尚经更遭枪决),至于遭警总约谈更是司空见惯(我便是警总的常客,亦被调查局约谈过),副刊编辑的政治警觉乃为报社用人的重要考量。张爱玲既然“有问题”,我还要跟她通信吗?
其时台湾文学界左右两派之争,与政府高度的政治警觉构成一种怪圈式的环境,动辄得咎。《同学少年都不贱》信马由缰地写早年女校几位同学的海外交往,涉及同性恋、左右派抵牾、反共牢骚之类:“中共有原子弹,有自卑感的人最得意”;“这两年因为越战与反战,年青人无论什么态度也都不足为奇了。她又是东方人,也许越共之外的东方人他们都恨”;“选修中文,往往由于对中共抱着幻想,因此都知道《东方红》这支歌。”这类文字从不同角度可以作不同解读。宋淇的顾忌不无道理。1978年8月8日张爱玲回宋信:“《同学少年都不贱》本来已经搁开,没预备发表。台湾现在的左派势力我很能想象,时尚的趋炎附势的影响力实在大。”8月20日她给夏志清信也说:“《同学少年都不贱》这篇小说除了外界的阻力,我一寄出也就发现它本身毛病很大,已经搁开了。”置于冷战背景中,宋淇更关注细节,懂得规避政治风险,一切让位于商机。他建议用胡适的信作为作品集的序;出谋划策对付唐文标的“盗版”;促成“发掘出土”或“漏网之鱼”的张作(《余韵》、《续集》)结集出版,并“毛遂自荐代为执笔”写序。这类操作不仅意在抢救张的遗落作品,更想让张爱玲不时地出现在读者眼界中,“表示你仍在继续写作”,“目前正在《余韵》出书时,大家又revive(恢复)了对你的兴趣……”可见其制造张爱玲影响力的整体规划性。他的所作所为,更着意于为“张爱玲”品牌铺路。宋淇这些指引,对张爱玲后期创作有很大影响。
张爱玲海外的关注者和推动者中,还有“张迷”一群,唐文标、水晶、司马新、朱西宁等。这群人身份各异,共同点是对张作有近乎痴迷的热爱。作为“张迷”,他们不仅关注张的作品,更关注她的生活起居、为人风格等。与学院派的夏志清、冷战时期美方政治文化宣传官员的麦卡锡、港派文艺经纪人的宋淇一起,共构“张爱玲”的多维形象。作为自发性的民间文人、报刊编辑记者,他们从感性层面靠近张爱玲。唐文标的《一级一级走向没光的所在》、水晶的《蝉——夜访张爱玲》、司马新的《张爱玲与赖雅》、朱西宁的《一朝风月二十八年——记启蒙我与提升我的张爱玲先生》等是其代表。王德威后来称张爱玲是“落地的麦子不死”,影响了新一代作家——上述这群“张迷”于其中起着桥梁作用。
张爱玲1952年去国至1995年逝世的四十余年间,恰好是全球性左、右两大阵营分裂、冷战的时期。她带着国、共两党分权留给她的刻骨铭心的经验,开始其海外三十多年的文学书写,这是一个新的起点。1950年代初赴港后,她在海外的市场铺排随之起步。靠冷战机构的推动,《秧歌》的出版由香港而美国。轻而易举的成功背后,其实是政治机构的支撑。及至她以难民身份赴美,她面临的却是无名之辈无助的陷落。英文小说由《粉泪》而《北地胭脂》,以及《易经》、《雷峰塔》两卷,均无人问津。在异国他乡,她只有长、宽、厚的体积,却缺乏“点”的位置。最后仍是通过私人关系,靠麦卡锡提供的小说翻译和宋淇提供的电懋公司剧本写作糊口。这个过程既激发她冷战参与的热情,也诱导她介入海外的以台湾为中心的中文文学市场。而真正为她提供学术支持且最终让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确立位置的,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对张爱玲的激赏既有其美学的学术的赏识及甄定,也有冷战的政治的共鸣和引导,二者的交汇,奠定他研究的基础。更值得注意的是,与1949年之后大陆将现代文学史构建当作为新政党、新政权修史的思路对着干,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构建旨在拆解这一思路,以美学的人性的个人的平凡诸价值彰显,抵制政治的革命的集体的文学史叙事。实际上,二者皆是冷战思维结构的产物,体现这种结构的两个面。而张爱玲恰好为夏志清的文学史叙事提供重要的案例。
① 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9-30页。
② 香港美新处是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的简称,该时期正肩负“反中共宣传”的“中国报告计划”,有其雄厚的资金经费执行此计划。
③ 高全之《张爱玲与香港美新处——访问麦卡锡先生》,《张爱玲学》漓江出版社2015年,第166页。
④ 《秧歌》英文版才写完两章即被马宽德(John P. Marquand,1893-1960)看好,推荐给美国的出版公司,1955年由美国司克利卜纳(Charles Scribner’s Sons)公司出版。马宽德(John P. Marquand,1893-1960)美国颇负盛名作家,普利策小说奖获得者。
⑤ 邝文美编《张爱玲语录》,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49、48页。
⑥ 夏志清《张爱玲与赖雅·序》,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台湾·大地出版社1996年5月,第12页。
⑦ 宋淇《私语张爱玲》,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33页。
⑧ 邝文美辑《张爱玲语录》,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47页。
⑨ 香港友联出版社(Union Press)为1950年代香港美新处的出版机构。
⑩ 参见彭树君《瑰美的传奇·永恒的停格——访平鑫涛谈张爱玲著作出版》,《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转引高全之《张爱玲学》第142页。
(11) 张爱玲《赤地之恋》,台北: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122页。
(12)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中,说她向大人询问祖父的事,总碰壁,“我几下子一碰壁,大概养成了个心理错综”。张爱玲《忆胡适之》,《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11页。
(13) 张爱玲曾向邝文美提及她要写七部小说的计划。参见邝文美辑《张爱玲语录》,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51-52页。
(14) 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台北:大地出版社1996年,第75页。
(15) 该法命“允许少数学有所长的人士到美国来,成为美国永久居民”,参见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第74页。
(16) 1963年9月25日张爱玲致夏志清信,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3页。
(17) 1957年2月2日致宋淇夫妇信说:“Pink Tears正写到高潮的一章,又夹着生些小病,直挨到今天总算完工,正开始打。”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152页。
(18) 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第115页。
(19) 1964年10月16日张爱玲致夏志清信,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0页。
(20) 从申请书可知,张爱玲在麦道伟文艺营住营的时间是1956年3月13日开始。而司马新的《张爱玲与赖雅》写道:“三月十三日,张爱玲第一次遇见赖雅。到了第二天,方有机会作几分钟的小谈,赖雅觉得她既庄重大方,又和蔼可亲……那次邂逅两天后,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风雪袭击了这一地区……大家挤缩在大厅中。张爱玲和赖雅则在回廊上、营地成员互访时间、以及晚餐桌彼此谈得逐渐深入。到了将近三月底,他们开始互相到对方的工作室作客。”张爱玲几乎是到达文艺营当天就与赖雅相识,参见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第97-98页。
(21) nothing to write home about:“乏善可陈”。
(22) This is not a sensible marriage, but it’s not without passion:“这婚姻说不上明智,但充满热情”。
(23) 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147-148页。
(24) 张爱玲1960年成为美国公民。赖雅的前妻“似乎认为张爱玲是靠结婚入了美国籍”。庄信正《张爱玲致庄信正(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注释》,庄信正编注《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25) 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第98页。
(26) 有人认为,“赖雅是美国左翼作家,却与许多走回头路的‘同路人’不同,至死无悔”。“在政治上张爱玲一生属于保守派,这对夫妇一左一右,突出地显示了文学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其实也可见张爱玲的左派与右派认识带有模糊的感性特征。庄信正编注《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第24、25页。
(27)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第145页。
(28) 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第142页。
(29) 宋以朗《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第66页。
(30) 参见宋以朗《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第199页。
(31) 符中立《张爱玲的电懋时代》中说:“稳定的剧本收入,成为张爱玲往后八年的经济支柱。”林幸谦主编《张爱玲:传奇·性别·系谱》第498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32) 1962年1月18日张爱玲致赖雅信,引自高全之《张爱玲学》第261页。
(33) 宋以朗《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第204页。
(34) 苏伟贞《孤岛张爱玲——追踪张爱玲香港时期(1952-1955)小说》第82页,台北:三民书局2002年。
(35) 1962年1月18日张爱玲致赖雅信,引自高全之《张爱玲学》第261页。
(36) 宋以朗《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广州: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199页。
(37) 如电影剧本《红楼梦》的石沉大海,参见宋以朗《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第202-203页。
(38) 张爱玲1962年1月18日致赖雅信,引自高全之《张爱玲学》第261页。
(39) 1959年8月9日她给邝文美的信提及“我在赶写《荻村》剧本,中文版昨晚刚写完,Dick McCarthy十五日过埠,大概来不及译好打好给他看。”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165页。
(40) 高克毅《请张爱玲写广播剧》,季季、关鸿编《永远的张爱玲——弟弟、丈夫、亲友笔下的传奇》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372页。
(41) 张爱玲《忆胡适之》,《张爱玲散文全编》第307页。
(42) 1961年9月12日张爱玲致邝文美信,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171-172页。
(43) 王祯和、丘彦明《在台湾的日子》,季季、关鸿编《永远的张爱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245页。
(44) 高全之《张爱玲与香港美新处——访问麦卡锡先生》,《张爱玲学》第167-168页。
(45) 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3页。
(46)1965年2月2日张爱玲致夏志清信,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15页。
(47) 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23页。
(48) 张爱玲《忆胡适之》,《张爱玲散文全编》第304页。
(49) 参见杨金荣《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48页。
(50) 除了有两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有个整理古籍的职位外,只有一些短期的讲学。
(51) 唐德刚《胡适杂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页。
(52) 1959年胡适有一段分析吴虞的话:“在五四运动前后,他被指为左派,后来便变为中间偏左,而逐渐的中间偏右,现在则成了右派,左右挨打,站在夹击的中间了。”这段话用来说他自己,倒也合适。司马桑敦《胡适东京一席谈》,台湾《联合报》1959年7月13日,转引自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第2954-295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九年校订版。
(53)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第2604页。
(54)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557页。《旋风》(原名《今梼杌传》)脱稿于1952年,至1957年才以单行本面世。小说以20世纪20-40年代山东T城为背景,写几十年间共产党在T城的组织活动、一群党性强弱各异的共产党人的命运及其“祸国殃民”的历史,是一部反共小说。
(55)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第3383页。
(56)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第3382页。
(57)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556-557页。
(58)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原作者序》,《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2页。
(59)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原作者序》,《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页。
(60) 《对话王德威:夏志清让西方认识中国文学》(引自网络文章,出处待查)
(61) 《对话王德威:夏志清让西方认识中国文学》,同上
(62)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原作者序》,《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页。
(63) 转引林以亮《从张爱玲的〈五四遗事〉说起》,陈子善编《私语张爱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64) 夏志清说:“只看过《西风》上那篇《天才梦》,她的小说一篇也没有看过,不便同她谈话。”转引宋以朗《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187页。
(6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原作者序》,《中国现代小说史》第6页。
(66)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原作者序》,《中国现代小说史》第5-6页。
(67)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原作者序》,《中国现代小说史》第6页。
(68)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十五章 张爱玲》,《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97-398页。
(69) 王德威说:“夏先生在1960年代以一种独断的一种语气,非常精到的眼光,肯定了张爱玲的成就,这是石破惊天的举动,之后我们这类所有的批评文字,也不过是重复夏先生的一些看法而已。”《“祖师奶奶”的功绩》,刘绍铭、梁秉均、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
(70)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力与“张派”作家的超越之路》,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第367页。
(71) 王德威《“信“的伦理学》,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351页。
(72) 刘绍铭《落难才女张爱玲》,金宏达编《回望张爱玲·昨夜月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2003年,第300页。
(73) 刘绍铭、梁秉均、许子东《再读张爱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29页。
(74) 夏志清《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75) 宋淇致张爱玲信,1976年3月21日,转引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17页。
(76) 宋以朗《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第253页。
(77) 1978年7月19日宋淇致张爱玲信,引自宋以朗《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第290页。
(78) 桑品载《与张爱玲周旋——拾掇她与〈人间〉的一段因缘》,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六十年》第211页,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
(79) 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42,43,46页。
(80) 1978年8月8日张爱玲致宋淇信,转引宋以朗《〈同学少年都不贱〉解密》,《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第291页。
(81)夏志清编注《张爱玲给我的信件》第241页。
(82)1987年1月22日宋淇致张爱玲信,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250页。
(83)1987年3月22日宋淇致张爱玲信,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252页。
(84)841987年1月22日宋淇致张爱玲信,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250页。
(85)1987年5月24日宋淇致张爱玲信,宋以朗编《张爱玲私语录》第254页。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