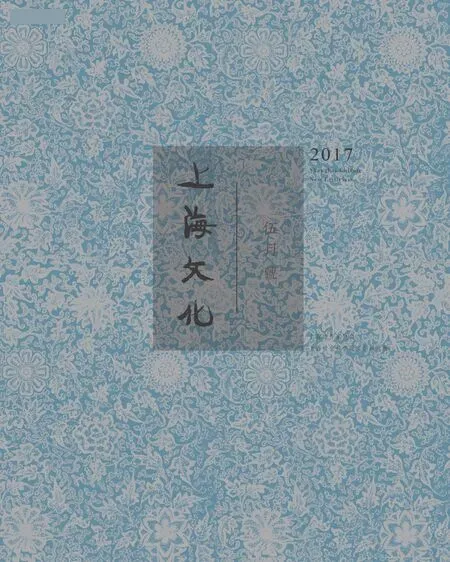虚浮的民国葛亮《北鸢》
岳 雯
虚浮的民国葛亮《北鸢》
岳 雯
葛亮的《北鸢》,笼罩在一片昏黄的光晕中。你可以将这片光晕称之为民国的魅力,或者别的什么。葛亮曾经如此描述过写作的场景,“多年来,《据几曾看》摆在案头。写作前后,我时不时会翻一翻。不为别的,只是视之为习惯,作沉淀心智之道”。可以想见,葛亮祖父葛康俞的遗著《据几曾看》充当了时间的信物。葛亮凭借此,得以从喧嚣的此世脱离出来,顺利地抵达祖父的时代,优游地写下他家族的故事,以及想象的民国。
这般想象,自然有其根源。据葛亮自述,写作《北鸢》的动因,是编辑寄了一本陈寅恪女儿所著之书给他,希望他从家人的角度,写一本书,关于祖父的过往与时代。然而,对于已有多年小说创作经验的他而言,竟是相当为难。葛亮供述原因说,“但我其实十分清楚,真正的原因,来自我面前的一帧小像。年轻时的祖父,瘦高的身形将长衫穿出了一派萧条。背景是北海,周遭的风物也是日常的。然而,他的眉宇间,有一种我所无法读懂的神情,清冷而自足,犹如内心的壁垒”。假如这番自述为真,则可以证明葛亮严格确实遵守了小说家的准则,即从自己完全熟悉,有充分把握的人物开始,构建小说情境。因此,他将焦点对准了他的外公,沉下心来,一笔一画地勾勒他的来路与去处,以及他身披的时代烟霞。对于小说家而言,想象一个时代,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而想象一种生活方式,须从想象一个人开始。好吧,关于 《北鸢》的故事,且从“这个人”开始。
1
世家子弟卢文笙出场之时还是个婴儿,却已然不同凡响。
干净的孩子,脸色白得鲜亮。还是很瘦,却不是“三根筋挑个头”的穷肚饿嗦相,而有些落难公子的样貌。她便看出来,是因这孩子的眉宇间十分平和。阔额头,宽人中,圆润的下巴。这眉目是不与人争的,可好东西都会等着他。
想象一个时代,就是想象一种生活方式。而想象一种生活方式,须从想象一个人开始
这描写有几分《红楼梦》中宝玉出场的味道。有意思的是,此时的相貌描写,已不再像19世纪欧洲小说那样,为的是让读者对小说主人公有一个清晰的形象。不,直到小说结束,读者恐怕也很难在心中描摹出文笙的样子。所谓的描写,不过是为了暗示其性格,进而以预言式的口吻暗示其命运。
这是极具症候性的时刻——葛亮的踌躇两难从一开始就清楚地呈现在文本中:他确定小说以写人为第一要务,如果没有人,小说就犹如沙中筑塔,溃散是早晚的事。但是,他又不甘心让小说成为“小”说,他有强烈的野心,要去摹写一个时代,一个被众多知识人目之为黄金时代的好时代,一个他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时代。要写出一个时代,一个或两个人显然是不能够的,只有让他们更多地去看,让更多的人进入视野之中,一个“大”时代才有可能从纸面上缓缓显形。
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我以为,这是葛亮的根本困境。理想的情境,或者说,葛亮追求的境界是“人”“群”皆在:一个人历历在目,一群人声形毕肖。这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葛亮熟读的《红楼梦》就是如此。但是,《红楼梦》是有严格的时空限制的。虽然总体时间跨度达十五年之久,但小说主体笔墨集中在大观园内的五六年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是可以包容“大”,或者说生出“大”的。葛亮显然认为,只有假以充裕的时日,让文笙和仁桢从一个婴儿成长为一个青年,经历更多的人与事,才得以见出时代之风声。可是,切口过大,原本对人物的那份熟悉反而遁去,令作者失去了整体把握人物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去看《北鸢》,我们会发现,文笙在小说中的露面次数实在不算多,且每一次露面都遵循了同一原则,即作者以神谕的口吻宣布其出众的德性与以其德性相匹配的更好的命运。比如,葛亮是如此描绘刚刚一岁的文笙的:“他的脾性温和,能够体会人们的善意并有回应。回应的方式,就是微笑。一个婴儿的微笑,是很动人的。这微笑的原因与成人的不同,必是出自由衷。然而又无一般婴童的乖张与放纵……然而,人们又发现,他的微笑另含有种意味,那就是一视同仁。”有时候,这种神谕式的宣布是借助其他有威望有德性人之口说出来。比如,在文笙抓周那一天,葛亮叙述他什么都不抓,“仍然是稳稳地坐着。脸上的笑容更为事不关己,左右顾盼,好像是个旁观的人”。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人就此再次以肯定其命运。小说选择了为世所重却淡泊名利,与俗世瓜葛无多的吴清舫说出了这样一番掷地有声的话语,“公子是无欲则刚,目无俗物,日后定有乾坤定夺之量”。这样的叙事策略一用再用。再举一个例子。小说写文笙一直不会说话。突然有一天,孩子开口说话,家人引为大喜之事。小说用庄重的语调记下了这一幕——
这小小的男孩,站在落满了梧桐叶子的院落里。四周还都灰黯着,却有一些曙光聚在他身上。他就成了一个金灿灿的儿童。她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却已经有些惊奇。因为笙哥儿扬起了头,在他的脸庞上,她看到了一种端穆的神情。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小童,甚至与她和家睦都无关。那是一种空洞的、略带忧伤的眼神,通常是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无所挂碍之后才会有的。这一瞬间,她觉出了这孩子的陌生,心里有一丝隐隐的怕。
她慢慢走向他。这时候笙哥儿蹲下来,捡起一片枯黄的叶子。她停下了脚步。这孩子用清晰的童音说,一叶知秋。
“一叶知秋”是整部小说的定音。葛亮自己常常说的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其实是一个意思,意味着大历史往往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折射出来。让小文笙字正腔圆地说出这个词,显然是葛亮对小说整体基调的定位,也暗含着将文笙这一人物形象圣化和神秘化的打算。
当然,赋予小说人物以神秘感从而提高人物的魅性,不是不可以。给读者以某种命运的暗示之后,让文笙去感受去经历,并以自身的经历详解或者违逆命运,也是极好的写法。但是,葛亮被众多的人物迷惑了目光,他似乎很难从文笙周围的人物身上回过神来,专心致志地让他“端穆”的神情之下长出血肉,迸出心跳。或者,另外一种可能是,其实同读者一样,葛亮知晓的只是他沉默的表面,无法深入他的内心,去了解他的行事逻辑,进而也无法理解他的性格,感怀他的命运。
如何想象文笙呢?按照葛亮的叙述,文笙应该是一个受过传统儒家教育,以经商为业的世家子弟。倘若葛亮能以小说人物的职业身份为突破,掀起民国时期五金业乃至整个商业的变迁史的一角,由此更进一步,以经济见证时代,想来就令人兴奋。然而,涉及文笙职业身份的,不过是他遵循母命,投奔舅家,一边读书,一边学做生意。怎么个学做生意法,葛亮并无详细描述。不过是带了一句,因为日本人占据了华北和海南的铁矿命脉,并课以重税,导致生意萧条。此后,也不过是文笙跟着永安,奔赴上海去“商场上一展拳脚”。文笙并未像《子夜》中的吴荪甫一样,向我们展现出他如何在商场叱咤风云或者困难重重的一面,当然,说到底,到小说结尾,他也不过是个青年,似乎并未到大展宏图的时刻。但是。我以为,最根本的问题是,葛亮对于文笙究竟该如何定位,想得也并不透彻。或许是因为孟家重文轻商的传统,葛亮仿佛也耻于言商事,或者说,他根本就不认为文笙实际上是一个年轻的资本家,而是更倾向于将他定位为知识分子。好吧,假如将文笙指认为知识分子,但他又尚未表现出“智性”的才华。在这一点上,作者对主人公文笙的刻画倒不如仅仅寥寥几笔的克俞,至少,克俞还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才子的印象。对于文笙,我们的印象反而是模糊的,不得要领的。尽管作者用了许多褒奖的词语赞赏他,但究竟不如“察其言观其行”来得真切。
在小说中,文笙不仅讷于言,似乎也并不敏于行。如果说,在文笙的生命中有浓墨重彩的一刻,应该是他在同学凌佐的带领下无意中加入了工人夜校,并在韩喆的带领下参军。这是新文学中经常描写的一刻:出身世家的少年从大家庭中挣脱出来,投身于大义。对于葛亮,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假如他能让我们进入文笙可信的内心世界,进而认同于他,他或许还能“活”过来,可惜的是,葛亮过于克制,也过于“淡笔写深情”了;墨迹淡了,人物的风采也随之黯淡了。一个核心主人公无法叫人建立起情感认同,对于一部小说来说,真真是一件极危险的事。失去了一个可信的主人公无异于松动了小说的核心构件,小说对于时代的反映必然也会失真。
于是,在大部分时候,文笙真的成了葛亮所说的“旁观的人”。在小说中,他由主人公下降为一个功能,就像一只风筝,线头在葛亮手里,飘飘荡荡,于是,我们只能通过他的目光,看到了更多的人,以及葛亮所认为的更重要的时刻。
这涉及了葛亮的第二个困境。因为要写更多的人,不可能工笔细描,只能选择一二,画出其神彩。写日常生活是一种,比如,“勇晴雯病补雀金裘”,是晴雯大放异彩的一刻,但说到底,也是极家常极生活化的一刻。《红楼梦》还是在日常生活的底子里让人物“活”起来。另外一种路数是,写生活里奇迹发生的时刻。这是葛亮的选择。比如,小说写到了石玉璞府里的一个小妾小湘琴,与徐汉臣相恋。事情暴露之后,小湘琴被石玉璞打死在房间里。这大概是葛亮所认为的不同凡响又特别能象征民国的一刻:鲜血与情欲混合着,在空气里,蒸腾出传奇的味道。我们是如此盼望奇迹,因为,只有奇迹才能将我们从乏味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同样的,我们往往将对当下生活的不满意投射到另外一个时代,比如民国,认为那个时代充满了种种变数,种种不可能,种种 “神启时刻”。《北鸢》满足了我们对另外一种生活的想象——这也是葛亮的写作策略,在写作一群人的时候,着力写令人难忘的一刻,写人冲破自身的牢笼化为神的那一片刻。不妨试举一例。
石玉璞的死亡彻底击溃了昭德。在死亡线上挣扎之后,她苏醒过来,精神却已失常。对于精神失常这件事,葛亮并无太多解释。何以一个刚强的女子,在军阀时代看惯了生死,却精神一溃至此。不管有怎样的疑惑,作为读者,我们须得遵守与作者的契约,相信他所述为真。我们只得相信,昭德返回到了她的童年,困在各种创伤之间。然而,这些却只是伏笔。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日军攻占襄城之后,卢家人举家逃难途中。当土匪将卢家人围住,暴行在肆无忌惮地发生,眼看所有人都陷入危险境地之时,奇迹发生了。一个老妇人,瞬间从疯癫变成装疯以谋划大事的状态,其心智水平确实相差甚巨。她不仅有谋,还有勇,居然胁迫土匪头子不得动弹,还从土匪身上摘了一只手雷。结果是,她成功地解救了卢家人,自己与众土匪同归于尽。一个羸弱的老妇人,不仅瞬间恢复心智,还做成了有武功的汉子所做不到的事情。只能解释为“如有天助”。此时的昭德,已经不再是疯癫的昭德,甚至也不是昔日的昭德,成了一位“神”。
不管有怎样的疑惑,作为读者,我们须得遵守与作者的契约,相信他所述为真
神迹遍地,固然能让人兴奋,能让人拚命抑制惊呼的愿望,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已经发生和尚未发生的一切。然而,神的降临意味着人的退场,属于人的欲望、脆弱、过错等等都消失不见。这不免让人疑惑,这真的是出现在我们历史上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一个时代吗,还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至此,葛亮的“黄金民国”,在人情和事理上,已然有些摇晃不稳了。
2
或许是因为要写的人物太多,除了主人公文笙和仁桢,其他人不免都是一鳞半爪,描绘的都是他们生命中最为华美的片刻。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青衣言秋凰。她的故事,包括她的来路和去处,被全须全尾地记述下来,成为包裹在《北鸢》之中的“戏中戏”。葛亮本人也十分珍视这个故事。在自序里,他特地说,“我便写了一个真正唱大戏的人,与这家族中的牵连。繁花盛景,姹紫嫣红,赏心乐事谁家院。倏忽间,她便唱完了,虽只唱了个囫囵。谢幕之时,也正是这时代落幕之日”。可见,他是把言秋凰当作那个时代的象征来写的。那么,言秋凰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倘若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这就是一个名伶与日本人的故事。最初,言秋凰对日本人,是暗地里不合作的态度。得知日本人和田要来听戏,言秋凰听从仁桢父亲的建议,饮下泡入了雪茄末的茶水,暂时变成哑巴,不能唱戏。这颇有几分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意思。紧接着,事有凑巧,听戏的和田逮捕了冯家二小姐,言秋凰日后得知那正是她的女儿仁珏,仁珏在日军看守所吞针自杀。言秋凰同和田之间,除了国恨,也有家仇。再后来,阿凤代表的地下党组织表示“我们的确需要一个懂戏的人”。他们密谋了一个计划,言秋凰正是这个计划的核心执行人。在这个计划里,需要言秋凰跟和田虚与委蛇,寻找机会除掉和田与一份秘密名单。她们说服言秋凰,凭借的是仁珏的遗物玉麒麟。当然,结局可想而知,言秋凰设了一个局,与和田同归于尽。
名伶抗日,确实是在民国故事中反复被讲述的传奇。这大概是因为,戏曲本身是极具文化性格的传统艺术形式,更遑论在特定历史时期包含了名士、美人、艺术与国族等种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讲述故事的人都试图往故事里添加进自己的理解,形成了具有层层裂痕的故事。比如,在陈凯歌的电影《霸王别姬》中,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痴迷唱戏,同时也是为了救段小楼,去给日本人唱堂会,在他看来,京剧或者艺术是无国界的。甚至,在他心目中,艺术是可以超越国族的。所以,在法庭上,他凄声喊出了,“要是青木活着,京戏就传到日本国去了”。他用生命实践了“不疯魔不成活”的谶语。我猜,葛亮在塑造言秋凰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可能也想到了程蝶衣,所以特意安排言秋凰有这样一番夫子自道(唱戏的时候):“当成自己自然不行,入不了戏。可也不能全当成了戏中的人。唱一出,便是戏里一世人的苦。唱上十出,便要疯魔了。”这仿佛是言秋凰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对程蝶衣的回答,也显出了言秋凰与程蝶衣全然不同的性格与命运。
那么,葛亮是如何想象言秋凰这样一个民国名伶呢?当然,葛亮极力写她在舞台上的光彩照人与日常生活中的世事洞微。她的艺术之高超到什么程度呢?作为京城数一数二的青衣,言秋凰在与师父的擂台赛上竟然“换新天”。这便是烘云托月的写法了。及至和田出现——这应该也是青木式的人物吧,热爱中国文化,尤爱京戏,两人立刻进入紧张的关系之中。但是,在对言秋凰作了这么一番精心的点染之后,葛亮竟然放弃了让艺术参与两人关系中来。也就是说,言秋凰与和田因为“戏”缠绕在一起,“戏”却未对二人的精神世界辐射出能量。言秋凰与其说是作为“名伶”的形象出现,不如说,是作为一个母亲的形象出现的。她的性格与行为逻辑,只有在母亲这一身份中才能得到理解。戏曲,成了装饰言秋凰的一堆亮晶晶的头面。
这是葛亮对于“名伶抗日”这一“故”事的改写。由此可以看出,葛亮更加重视情感结构在叙事中的位置。可以作为佐证的是,言秋凰的女儿仁珏,因为支持革命,被日军逮捕。而仁珏支持革命,却是出于对范逸美的感情。小说中有这么一段话,“到头来,‘国’是男人的事,‘家’是女人的事,没人改变得了。可如今,这一代人却合并成了‘家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葛亮改变了“家”与“国”的位置——不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而是“家”在“国”先。
这样一种拆解,大有深意。众所周知,“家国天下”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意义框架,家、国、天下之间有着不言自明的等级秩序,即,“身”从属于“家”,“家”从属于“国”,“国”从属于“天下”。葛亮向往的民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将“家”从“家国天下”的格局中拆卸出来,认为家族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牢笼,从而将“自我”解放出来,直接服务于建设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莫不如此。葛亮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将“家”、“家族”重新镶嵌回“自我”—“国家”的秩序链条中,认为个人只有重新回到家族关系之中,才能直接应对民族国家之事,这固然重新赋予了政治生活以伦理意味,但某种程度上也改写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如果真的有所谓的“黄金民国”,那么,那个时代最有魅力的地方正在于,在民族国家危亡的时刻,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受到了个人之于国家的责任。他们放弃了个人的一己之私,冲破家族的桎梏,以期建立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此间种种,无论是观念还是行为,都十分动人。一部以大时代下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命运起伏为题材的小说,一部以君子之道为核心价值的小说,支撑小说的,不是知性力量,而是情感结构,不能不令人叹息。葛亮这般处理,或许是因为,在我们的时代,宏大有时候会被视为一种虚伪,他宁可趋小、趋实,从我们所能理解的人情与事理出发,却在描绘一个更为高远的精神世界面前止住了脚步。我们就是这样逐渐失去了我们曾有过的一切。
我们就是这样逐渐失去了我们曾有过的一切
3
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北鸢》是一部有精神追求的小说。它的精神追求又是什么呢?
葛亮在自序中对“北鸢”之由来有一番解释。他说,“小说题为《北鸢》,出自曹霑《废艺斋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一册。曹公之明达,在深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之道。字里行间,坐言起行。虽是残本,散佚有时,终得见天日。管窥之下,是久藏的民间真精神。”葛亮确实偏爱“民间”。在一篇叫做《文学》的随笔中,他说,“一种新的文学应运而生。新文学的创作者同时成为话语的生产者。在这种话语模式中,伴随着一些神话的诞生,英雄主义不再大行其道,历史重荷亦翩若惊鸿。我们看到了来自民间的价值观,渐渐清晰,让我们无以回避。”由此可见,“民间”是葛亮的出发点,也是理解《北鸢》的一把钥匙。作为一个暧昧复杂的概念,葛亮理解的“民间”指的什么呢?
根据《当代文学关键词》的说法,“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作为文化空间的民间。“民间”意味着与国家权力结构相对立,保存了社会生活面貌与下层人民的情绪。二是作为审美风格与创作元素的民间。三是作为一种价值立场的民间。细察葛亮的创作,他的“民间”,刻意与国家权力、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是与知识分子或者说“士”的价值立场和精神追求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卢文笙的母系一族,昭德、昭如是孟夫子的后代。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两姊妹,特别是昭如,即对这一身份的重视。尽管与卢家睦举案齐眉,昭如对于自己嫁作商人妇,心里多多少少有芥蒂。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昭德突然说起租界里有门亲戚叫孟养辉,无意文章,投身商贾,富甲一方,却不为昭德、昭如姊妹所看重。昭德这般说他,“好端端的孟家人,书读不进,官做不成,便去与银钱打交道”。她教育妹妹昭如“卢家睦若不是为了承就家业,如今倒还在享耕读之乐。我们孟家人,可嫁作商人妇,自个儿却得有个诗礼的主心骨”。儒家重诗书、重官仕,而轻商业,由此可见一斑。葛亮将孟子的人格追求作为涵养文笙的精神源头,满怀崇敬之情地描述了昭如在丈夫亡故之后,是如何勉力支撑,甚至替丈夫的女儿办了冥婚,以求了结丈夫的心愿。葛亮慷慨地将美德赋予底层人民。比如,信。与风筝有关的意象在这部小说中总是格外突出。于是,读者记住了卢家睦盘下一个铺子赠送给龙师傅,唯一要求是给儿子文笙在本命前年制上一只虎头风筝。龙师傅为了此约等了九年。此后竟绵延至几代人。此所谓“言而有信”。比如,孝。文笙的朋友凌佐就是个孝子。他在战场中弹受伤,弥留之际还惦记着拜托文笙将老太监的宝贝一起葬了。“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我答应过我娘的,我不能不孝。”凡此种种,不可一一而数。
《北鸢》整部小说,落实在“善好”上,落实在“仁、义、礼、智、信”等古老中国的善行义举上。如果联想起此时烽烟连天的现实,战乱、饥荒无不像猛兽一样追逐着每个人,这番对比更加让人触目惊心。这大概就是葛亮所说的“民间真精神”。在随笔中,葛亮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民国的倾慕之情。“民国是个好时代,好在作文与做人的尺度。及至当世,仍可以之为鉴,躬身自省,反求诸己。世故人情,皆有温度。内有渊源,举重若轻。”“祖父的时代,人大都纯粹,对人对己皆有责任感。这是时世大幸。投射至家庭的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深沉的君子之道。所谓家国,心脉相连。”
现在,我们对葛亮的精神追求看得更清楚了。葛亮显然强烈倾慕于塑造了中国文化之根柢的“旧”,因此,他所想象的民国,浑然是古典精神的涵养与呈现。然而,作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国的意义恰在于它开启了现代性时间。“新”与“旧”剧烈碰撞,纠缠、角力,绵延至今,尚未彻底结束。虽未结束,但是,“旧”已经逐渐消失,成为我们怀想的美好。可是,对于写作者而言,中正端方地书写“旧”,完全将“旧”作为民国的时代精神,却对诞生于同时的“新”选择性视而不见,某种程度上却是对这一时代的遮蔽。在一而再地赞咏中,民国从文字里逃逸了,留下的不过是纸上的镜像,以及写作者本人的文化投射。
当然,人人都有自己格外钟情的时代,艺术家概莫能外。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小说这样一种文体,适合用这样清晰明了的方式致敬一个时代或者文化理想吗?
这是什么样的方式呢?不妨让葛亮自己现身说法。在评论毛姆的作品时,葛亮认为,毛姆的声名得益于对世相的精准描摹,然而不止一次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世相经验些微的背离立场。“其间的真实感,更多来自性格力量的强大,而非复杂的对于社会逻辑的承袭。以由因导果的角度而言,‘尊严’的延伸力量,覆盖了所有线性的细节铺垫。”换句话说,葛亮认为,类似“尊严”这样的美德,足以击破小说的因果逻辑链,成为支撑小说的最强大力量,并充分唤起读者的情感认同。但我认为,人们将越来越不愿意接受如此简单的判断。《北鸢》在充分赞许古老中国的传统美德的同时也在简化一切。好的小说,一定是表现出极大的理解力的小说。它需要读者付出巨大的努力,投入自己的经验、情感、知性与智慧,从混沌一团的作品中炼出一点或几点金子。但现在,《北鸢》并不需要做出理解的努力,它的观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除了赞同或者反对,它没给读者留下太多可供思想驰骋的空间。
或许,葛亮的态度是这一切的根源。他真应该听一听美国文学批评家特里林的说法,“艺术家和他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不同政见者的小团体文化,都是复杂的,甚至具有一定的矛盾性:艺术家必须接受他的文化,同时得到该文化的接受,但同时——事实似乎也是如此——也必须成为该文化的批判者,根据自己的个人洞察力来对这种文化进行纠正,甚至抵制;他的力量似乎生发于这种爱恨矛盾的境况所产生的张力,而我们则必须学会欢迎这种矛盾的情感”。《北鸢》的无力感正在于,它无条件地表达了对民国这一时期的文化的赞许之情,甚至没有丝毫的矛盾和犹豫。我理解葛亮对他所爱的一切美德的忠诚,包括了晚辈对长辈的敬仰之心——《北鸢》当然是一部诚恳之作,但是,作为优秀的小说家,葛亮不能从自己的个人情感中跳脱出来,审慎地反思一切,这不免令人遗憾了。
4
在回答记者为什么将文笙与仁桢的故事定格在1947年时,葛亮的说法是,“这也是一种美感的考虑。因为以我这样一种小说的笔法,我会觉得在我外公和外婆汇集的一刹那,是他们人生中最美的那一刻。到最后他们经历了很多苦痛,中间有那么多的相濡以沫,但是时代不美了。其实我之前有另外一本书叫《七声》,第一篇叫《琴瑟》,写到他们在这个时代一系列的砥砺,这个错乱的时代已经过去之后,他们又进入到一种尘埃落定的晚年的阶段。那个阶段我才觉得他们的美感又回来了,所以我才会写那么一篇小说。前两天一个朋友问我,那段多么精彩啊,你外公他作为当时最年轻的资本家,经历了公私合营等等历史,肯定身上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确实有,但是不美了。我从内心是想把他留在1947年,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在一而再地赞咏中,民国从文字里逃逸了,留下的不过是纸上的镜像,以及写作者本人的文化投射
《北鸢》确实很美。它的美,体现在语言上。葛亮精心雕琢了《北鸢》的语言,似旧实新,力求语言与人物具有一致性。它的美,也体现在人物上。但凡小说着力刻画的正面人物,葛亮都赋予其完美的品性,恰似一翩翩公子,着一白色长衫,丰彩俊逸,不惹尘埃。葛亮对于美的追求,真真到了极致。但是,这也是《北鸢》深层的问题。小说是一种世俗文体,建构它的根基是活泼泼的泥沙俱下的世俗人生。是的,小说家可以带领我们,去体认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是,世间的事,并非只有好与坏,真正考验小说家的,是对于好与坏之间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倘若一味追求洁净,构成小说这一大厦的基石就会摇晃,那么,小说所描绘的一切就难免虚浮了。
美,有时候竟然是一种束缚。
编辑/黄德海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关于葛亮研究的总结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