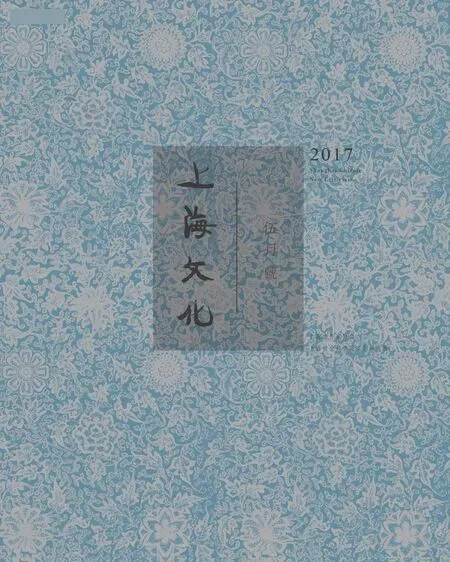圣经二题
张 闳
圣经二题
张 闳
尼哥德慕或知识分子的精神暗夜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犹太人的官长。他夜间来到耶稣那里,对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因为如果没有神同在,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就没有人能行。”
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德慕说:“人老了,怎能重生呢?难道他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不要因为我对你说‘你们必须重生’而感到希奇。风随意而吹,你听见它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
尼哥德慕说:“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教师,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知道的,才讲论;见过的,就作证,然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讲天上的事,怎能相信呢?除了那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把铜蛇举起,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藉着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上,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邪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原因,就在这里。凡作恶的都恨光,不来接近光,免得他的恶行暴露出来。凡行真理的,就来接近光,好显明他所作的都是靠着神而作的。”
约翰福音第3章第1-21节(新译本)
名叫尼哥德慕
尼哥德慕是当时在犹太人当中最具势力的法利赛派系的成员,而且还是法利赛人当中的上层人物,一位官员,可能属于议员一类的高级别官员。同时,他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以色列人的教师。这种教师负责教导人们学习圣经。甚至——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出——他还颇有财富。他在耶稣死后,“带着没药和沉香混合的香料,约有三十二公斤”,前来收殓耶稣的遗体(约19:39)。这等重量的香料,在当时是一笔数额不小的财富。可见,他有政治权力,也有经济实力和文化地位,而且还有宗教身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诸方面,都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属于社会精英阶层。总而言之,尼哥德慕称得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成功人士。
然而,尼哥德慕跟其他的法利赛人不同,他有一种特殊的属灵的眼光。在法利赛人领袖当中,只有他看出了耶稣与神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别的关联。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这将是一个跨世代的伟大发现。此前的四百多年,以色列这个被神所拣选的民族,一直陷于与神隔绝的处境当中,在这漫长的四百年里,以色列的神沉默不语,神的选民看不到神迹,也听不到神的声音。他们,尤其是法利赛人,日日盼望着神能够亲自来向他们说话,显出神迹来救他们于黑暗,于异族统治的苦难深渊。或是派下天国的使者,来向他们传讲天上的消息。现在,真的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拿撒勒人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显神迹并传讲天国的消息。这个拿撒勒木匠的儿子,跟神有什么相干?他所言所行,有何权柄?凭什么相信他?然而有许多普通人信了。但法利赛人领袖,那些祭司长、经学家等人,却坚决不信。相反,他们对耶稣极为忌恨,欲除之而后快。在他们当中,唯有尼哥德慕看出来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尽管他还未能认识到这就是神的儿子,是神差遣来的救世主。
尼哥德慕与众不同之处还不止于此。尼哥德慕虽然有着可以说是万人艳羡的成功,但他仍有不满足。在世的成功不能安慰他的灵里的需求,他有着一种灵里的饥渴。当他看见耶稣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听到耶稣的教导之后,他知道,此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学教师或宗教领袖,乃是真正从神而来的教导者。
这种认识一旦确立,尼哥德慕决定要做一件事。
他夜间来到……
他夜间来到耶稣那里。
他只能夜间来到。因为他是一位成功人士,在白天,他会有“许多要做的事情”。他必有许多的烦忙。趁着夜间,那些白天的烦劳歇息之后,他方得以脱身,抽出空闲,来见耶稣。我们也是如此:把白天的交给世界,把夜间交给神。许多基督徒也常常只有在夜间安歇之际,才得以打开圣经,来倾听神的话语,来向神求告,来过一种基督徒的属灵生活。而在白天——抱歉,实在没空。
尼哥德慕选择夜间来到,还另有原因。耶稣在耶路撒冷已经大大地得罪了当地的当权者,他与法利赛人的矛盾日益激化,法利赛人正在谋划如何捉拿耶稣,定他的罪。许多信了耶稣或同情他的人,都不敢公开承认,甚至都不敢谈论耶稣。尼哥德慕虽然也是权贵阶层,但他显然也不愿公开与法利赛人对立、决裂。他选择夜间来到,显然是要避人耳目。另外,尼哥德慕是犹太人的教师,他显然年事已高,且属于那种德高望重者。而耶稣,虽然有令人讶异的真理教导能力,但他不过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的乡下人,来自拿撒勒这种小地方的一个木匠的儿子,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在他教导真理的时候,犹太人就感到奇怪,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会通晓经书呢?”(约7:15)犹太人是很重视经书教育的,经书教师地位很高,但像尼哥德慕这样既博学又有身份的人,也并不多见。若他要公开来拜访耶稣,向耶稣这样一个人请教的话,无异于一位哲学教授去向小学还没毕业的工人请教他自己的专业问题。这不仅不合常理,还会让自己颜面尽失,周围的人,尤其是那些接受过他的教导的人,也会感到难以接受。夜间来访实属迫不得已。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人,穿过耶路撒冷漫漫暗夜,朝着远处那个微弱但却是唯一的光走去,像个贼一样。他平时习惯了气宇轩昂地走在大街上,路人们都会主动跟他招呼,“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而此时,他却脚步游移,左顾右盼,生怕被别人看见。事实上,人一旦直面真理的时候,是会害羞的。人很难坦然地站立在真理面前。当初,摩西与神面对面的时候,也不禁要“把自己的脸蒙住”。就好比身体突然完全暴露在强光之中,会让人惶惑不安,不知所措。或许他几度要打道回府——实在是犯不着做这样一次造访。可是,当他越走越近时,那光越来越亮,他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敲开了那扇窄小的门。而且,他情不自禁地要对眼前的这位年轻人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因为如果没有神同在,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就没有人能行。”他实在是一个慕神的人。
你们必须重生
作为一位犹太知识分子,经学教师,尼哥德慕当然很关心神迹和天国的事情,这是他们毕生追求的事情,也是他们在世的盼望。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弥赛亚的降临,首先盼望有先知来预告这一消息。可是,自从旧约时代最后一位先知玛拉基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先知的声音,没有任何天国的消息。现在,尼哥德慕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看到了希望。这位慕神的拉比,热切地想从耶稣那里探听好消息。至少,还可以跟这位睿智的年轻人探讨一番神学和天国文化。这种切磋,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然而,耶稣开门见山地直奔主题——“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知道尼哥德慕是何许人,也知道他为何而来。他的这一当头棒喝,令人震惊,也令人不解,连博学的尼哥德慕也大感困惑。“人老了,怎能重生呢?难道他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倘若不是,那“重生”又从何谈起?另一方面,当着一位老人的面,说出如此荒诞不经之论,也甚唐突。倘若一位老人需要重生,那也就意味着他这一生是白过了。因此,这位温和的老人似乎感到有些被冒犯,他的回应多多少少暗含讥诮。
作为知识分子的尼哥德慕,只能用世界的逻辑来理解这个问题。在世界的逻辑里,重生是不可能的。而现在,他面前的这位年轻人却实实在在地告诉说:必须重生。
重生,对于尼哥德慕来说,意味着他一生所积攒的成就、功名和美德,现在要被弃绝,化作尘土。这是从根本上对他在现世的全部成功的否弃。在耶稣看来,一位功成名就的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学识、成就和声誉,反而成为他进入天国的障碍。现在,他必须决绝,与旧我决绝,也与世界决绝。这个他曾经从中获益的世界,现在必须割舍。基督徒在世上被分别出来,不是来得世界的益处的,不是来迎合世界,成为世人眼中的好人和成功者的。相反,他要与这个世界决裂,放下在世上的一切,背弃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曾经有一位行善积德的财主,向耶稣询问过“永生之道”,他有着尼哥德慕同样的困惑和障碍。活在这个世界上,却要与世界决绝,这是一个难题。
怎能有这事呢?
“怎能有这事呢?”——尼哥德慕提出了自己的怀疑。
是的,怎能有这事呢?尼哥德慕问得有理。根据尼哥德慕所能理解的,这事是不可能有的。以他丰富的知识和全部的人生经验,都不能解释此事。现在,尼哥德慕面临着一个“可能性”的问题。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验,考验着他的知识,考验着他的智力,更重要的是,考验着他的信心。他需要理解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处于希腊化时代的文化环境中,犹太的知识分子也深受影响。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希腊哲学,对可能性的论证,乃是其逻辑学核心内容。尼哥德慕的哲学也是如此。在尼哥德慕的知识体系里,这事是难以理解的。不仅是尼哥德慕的知识体系,而且甚至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都缺乏对这种问题的解释,至少是不足以提供解释。或者,它们仅仅是提供一种观念性的解释,而且仅仅停留在观念的层面。然而,在这一夜,尼哥德慕感觉到了知识的无力。不仅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尼哥德慕,全部的人类知识本身也面临挑战。尼哥德慕临到了知识真理的极限,这个极限就是理性逻辑的尽头。现在,他需要去理解那“不可能”的事情,理解在逻辑上无法推论和研判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夜晚。正如尼哥德慕的处境,整个世界进入了午夜时分。
尼哥德慕的暗夜,如同浮士德的暗夜,只不过他是一个反向的“浮士德”。他们同样处于世界的精神暗夜。作为浮士德的古代镜像,尼哥德慕走到了自己的精神旅程的尽头。他现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此前他靠着自己的智慧、能力和美德所赢得的一切,如今都已变得可疑。知识真理被置于终极的维度来打量。知识真理曾经有如光照,映射在作为学习者的人类的脚前。而现在,知识真理的烛光突然变得昏暗,摇曳欲灭。
关于“重生”,尼哥德慕同样需要得到论证。在尼哥德慕的哲学中,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重生”不是一个逻辑论证的问题,也不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实践。“重生”是一个神迹。重生得救,并非依靠自身的努力,亦非依靠逻辑学上的可能性论证,也就是说,福音的重点,不是“因行称义”,亦非“因知称义”,而是“因信称义”。神迹是信的一部分。没有神迹,就没有拯救。神迹,是犹太-基督教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乃至世界其他各种哲学的重大差别。当门徒们看到那位恪守律法和有良善行为的有钱人依旧难以得救时,“就分外希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的回答是:“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却凡事都能”(太19:26)。而人往往根据经验和知性,因为自己的不能,无法相信神的大能。当然,对于以色列这个神所拣选的民族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存在。以色列人一直都活在神迹当中。尼哥德慕来见耶稣,本就是因为讲过那些神迹,而且也承认,“如果没有神同在,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就没有人能行。”尼哥德慕的问题在于,他却未能从圣子身上看出圣父的形象。
然而,与希腊哲学不同的是,犹太教的神圣启示始终指向的神的作为。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在摩西身上,在旷野上的以色列人身上,在以利亚等诸先知身上,已经彰显了这样或那样的神迹,早已成就了诸多“不可能”的事。没有神迹,就没有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全部的犹太教圣经(《旧约》)都在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真理,包括重生的真理作证。尼哥德慕是以色列人的教师,却忘记了这一点。他甚至更像是一位希腊哲学家。于是,耶稣提醒他以色列的神的道:“你是以色列人的教师,还不明白这事吗?”如果信圣父,也必信圣子。尼哥德慕研习圣父的道,却未能在圣子身上看到这道已成肉身。从根本上说,若不能认识圣子,也就无法真正认识圣父。未能领受“道成肉身”的真理,就无法真正走出精神的暗夜。神的儿子行走在地上,信靠和跟从这一位“道成肉身”的拿撒勒人,乃是通向天国的唯一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你们认识我,就必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了他”(约14:6-7)。不然,“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讲天上的事,怎能相信呢?”
光来到世上
经过彻夜长谈,窗外晨光熹微,光线显露在两位谈话者的脸上,他们各自的面貌渐次清晰,面向光的部分和背光的部分尽都凸显,层次分明。就好像穿过漫长的隧道,走向黑暗的尽头,黑暗另一头的光明开始涌现,周边世界的轮廓也慢慢显露出来。
耶稣乃就这光讲论他的真理。“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约8:12)。这就好像起初天父所做的一样——“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1:3)。而在《约翰福音》一开头,施洗约翰就已经为这光做了见证——“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约1:14)。“那光来到世界,是普照世人的真光。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约1:9-10)。人类最初从蒙昧之中走出来的情况,就是如此。理性之光不过是这终极性的光源在人类头脑中照亮和开启的结果。从理性出发,通向真理的路径必然抵达此处。它看上去是理性的尽头,是智慧的限度,是精神午夜最黑暗的时刻,但同时它又是一个伟大的转折时刻。尼哥德慕就处于这样的境况中,见证了由黑暗转向光明的伟大时刻。
穿过慢慢长夜的尼哥德慕终于看到了黎明。黎明时分,需得面向光明,前来就光,方可看见天色越来越明亮,世界越来越清晰。“凡行真理的,就来接近光。”就光,就是面向光源,并与光亲近,将自身生命沐浴在光线之中。背向光,眼中看到的依旧是黑暗。接受、信靠基督耶稣的,就得重生。“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利,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不是从血统生的,不是从肉身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约1:12-13)。重生、永生等人生根本性的精神问题,至此方有了终极性的解答。
马大的日常烦忙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名叫马大的女人,接他到家里。
她有一个妹妹,名叫马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道。
马大被许多要做的事,弄得心烦意乱,就上前来,说:“主啊,我妹妹让我一个人侍候,你不理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主回答她:“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操心忙碌,但是最需要的只有一件,马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分,是不能从她夺去的。”
路加福音第10章第38-42节(新译本)
许多要做的事
是的,有许多要做的事。不仅马大有,我们大家都有。有许多要做的事,多得好像永远都不完。人活着总要做事,不仅要作事,而且还要勤勉。虽然对一些人来说,工作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苦差,但一般而言,它首先是人生的需要。往小处说,是养家糊口的需要;往大处说,可以造福人类;往至高处说,是荣耀神。工作是一种美德。
马大当然有许多要做的事。作为一个普通人家的长女,她要做的事情通常还会比常人要多。何况还是在主耶稣光顾的日子里。耶稣不是一个人来,他还有门徒跟随,一同出入。在本章前面,提到耶稣不仅已经拣选十二门徒,甚至还差遣七十位门徒出去传道。虽然并非这么多门徒都在耶稣身边,但跟随他进入马大兄妹村庄的人数不会太少,至少会有诸如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等经常跟随耶稣左右的那几位。
马大兄妹对于耶稣的到来,自然是十分高兴。马大的兄弟拉撒路,也就是后来耶稣让他从坟墓里复活的那一位,是耶稣的密友。耶稣唯一一次哭泣,就是因为他的死。马大和马利亚姊妹也是耶稣好朋友。耶稣素来是爱他们兄妹的(约11:1-5)。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有“许多要做的事”。马大需要预备饮食,招待这一帮子旅途劳顿、饥肠辘辘的贵客。
弄得心烦意乱
因为耶稣一干人的到来,马大欣喜激动,并开始忙碌起来。马大恪尽地主之谊,依待客之道而行,以世俗的眼光看,她确实是一个贤惠、善良而且热情的好女子。即便以一般宗教的观点看,她的行为也无可指摘。马大服事主,心诚意切,实在是一个忠心而又勤勉的主的仆人。而现在,因为热切好客,又因为客人众多,马大一时间手忙脚乱。她苦于找不到帮手,难免有些焦躁,“心烦意乱”起来,正如主耶稣所说——“你为许多事操心忙碌”。
“操心忙碌”,英文作careful and troubled[KJV],或care and troubled[BBE],德文圣经译作Sorge und Mühe。在现实生存活动中,各种“操心忙碌”总是难免的。马大的处境,从根本上说,揭示了人类现实生存的一般性的和普遍的状况。Sorge(care),“操心”、“劳神”,或“烦”,正是存在论哲学(特别是马丁·海德格尔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
马丁·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试图探讨存在论意义上的“世界”。海德格尔的哲学回到古希腊的哲学源头,以“存在”本身作为基本问题,他假定世界乃是先验地在那里,人的存在的基本结构即是“在世”,“在世”的生存结构,表明人作为存在物与世界是结为一体的。在没有危机和救恩的情况下,世界及“在世”之存在者的存在状况以及所谓“本真地”之可能性,在神不在场的情况下,“存在”任何可能和意义何在。海德格尔的结论是——“‘在世’的存在,就存在而言刻有‘操心’的印记。”脱离了与神的连结,人在世上的活动就失去了超越于属世之操劳的可能性,人的生存活动构成了人之存在的全部依凭和目标。“此在之在绽露为操心”, 如果不能从属世的操心中赢得意义的话,那么,人所能看到的就是“忙碌”。海德格尔写道:“此在的向世之存在本质上就是操劳。”被“操心”所缠绕,被世界上的“许多要作的事”所捆绑,存在即被遮蔽。海德格尔将这种存在状况称之为“非本真状态”。而这一切必然成为其“烦”的根源。海德格尔关于“非本真的生存者”的描述,简直就是针对马大的——“他手忙脚乱地迷失于所操劳之事,同时也就把他的时间丢失于所操劳之事。”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就有了克服在世烦忙的途径和手段,相反,海德格尔的哲学乃是在认可和接受存在者这一本质属性的前提下而展开的,并且,他试图在这属世的烦忙的框架内,为生存寻找意义。从根本上说,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就是“马大的哲学”。
然而,所谓“本真状态”又如何可能?海德格尔以一种晦涩的语言,不无迟疑地表达了某种可能的途径,即对“当下”的肯定。以“决心”接受存在的被抛性,并将这种被抛的偶然状态转化为可“持存”的时间性本身,向着历史和将来敞开,成为对当下的担当和占有。没有危机,也没有从天而来的救恩,在此情况下,人的属世的操劳有何盼望?后期海德格尔则显得更为明确和有信心。他提供了一条自我救赎的路径。他小心翼翼地规避神的道,试图从一条幽暗的林间小径寻找通向澄明、敞开之境的道。在通往生存意义的小径上,当人们不再瞩目于(可能是无可企及的永恒性的)终极价值的时候,而将此在的当下处境、此时此刻的存在,视作一个可能性的“瞬间”之际,生命的意义之风将吹拂你的身体表面,而又有所领受和若有所思的瞬间,意义就如是这般地向着生命敞开,如同诗一般的美妙。这就是存在的意义的全部。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给马大指出的克服烦忙之空虚的道,就是:既然生存之烦忙是无可避免的,既然在世之操劳终将归于虚无,那么,唯一值得信靠的就是让这种无意义的烦忙变得富于诗意,让我们这些无意义的生命得从“诗意地栖居”于这昏暗空虚的大地上,让这种来自“诗-思”的诗意之光,来照亮世界之午夜。海德格尔将这视作摆脱生存之烦的途径和手段,将诗意的沉思,视作通往真理和生存家园的道路。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意的言说就是“真理、道路、生命”。马大必须假想自己是快乐的。阿尔贝·加缪就是这样设想他笔下的西绪福斯的。西绪福斯选择担当荒诞,独自忍受生存的无意义,在不断重复推石上山的徒劳苦役过程中——加缪写道——“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不错,马大完全可能唱着歌儿烧饭、洗碗。当她独自劳作的时候,将恼人的日常事务“诗化”,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然而,这种生存“筹划”却是那么的脆弱不堪。当世界还有“他人”存在时,当她卷入到“在世”的关系当中时,“诗化”的梦想就变得不可靠和不真实了——因为她的妹妹在那里领受另一种意义。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马大对自己操劳的价值产生了怀疑,或者说,在她眼里,妹妹的行为乃是一种闲暇和舒适,是对操心和责任的逃避,并因此而否定了自己操劳的价值。当生存活动的价值来自于世界,遵循世界的标准,这种活动就纯然变成了徒然的操劳,“诗化”这种烦忙,也成为了不可能。脱离了对神的信靠,在世的生活就沦为一种纯粹的“操心”。神学家麦奎利针对这一状况,提出了自己的批判性的意见:“人并不是为了过一种操心的生活,而是为了过一种本真的生存而受造的,同时,只要此种生存能摆脱沉沦,它就能摆脱操心。”
现在问题是,马大并非没有得到领受恩典,摆脱沉沦的机会。此时此刻,救主正造访她家。可是,她只是将耶稣当做一位贵宾来接待,只是依照属世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作为主人与这位贵客之间的关系。她并没有意识到,她自己正在接待神。此刻坐在她家中的,并不只是一位高贵的客人,不只是一位亲密的朋友,甚至不只是一位尊贵的拉比,乃是救主弥赛亚。
耶稣来到这里,也不只是来做客,或者是布道行程中的一次短暂的歇脚。这位神的儿子来到我们这个世上,为的是要传讲天国的消息。这是“道成肉身”的真正目的。他不是客人,他是主人。对于一个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和家庭来说,他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马大虽然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但她仍未能从属灵的层面上认识到这位主就是神,并且,也未能正确地处理与神的关系。
但遗憾的是,主耶稣的到来,马大并未因此而感到生活样式的变化和生命的更新,相反,她更深地陷入到属世的日常事务的操劳当中。毫无疑问,她是在“服事”,从一般生存的意义上和天国的事务方面而言之,这都是有必要的。问题在于她与主耶稣之间的关系状况。她将自己与主之间的关系照着世界性的伦理关系——待客之道——来处理,将“人-神”关系处理为人际关系。她的世界结构被自身有限的伦理结构所规定,是一种简单陈旧的平面结构。马大所领会到的,乃是属世的必要性,并被这种世界的必然性的关系所制约和奴役。被世界的必然性所奴役,成为事务的仆人,而与真正的主人——神——相隔绝。
坐在主的脚前听道
妹妹马利亚则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与主耶稣打交道——“坐在主的脚前听道”。
马利亚有着特别的属灵的敏感,她总是能够在正确的时间里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另一次,她曾经用一整瓶极贵的真哪哒香膏倾倒在耶稣身上,并用自己的头发为主耶稣膏抹,在无人知晓耶稣即将受难的情况下,她凭着自己的属灵的感动,在耶稣身上预先做了安葬前的荣耀的涂油礼。所有在场的人都大为不解,只有耶稣肯定了她的行为——“我实在告诉你们,福音无论传到世界上甚么地方,都要传讲这女人所作的来记念她”(可14:9)。这一次也是如此,她在姐姐马大为日常属世的事务操劳的时候,她却选择了与主耶稣在一起。因为与主同在的机会是——如耶稣本人说的——“却不常有”。
马利亚凭着信,紧紧地抓住与主耶稣同在的机会。而信道并非凭空而来的决心。“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所听的道是藉着基督的话来的”(罗10:17)。一个人在信靠主之后,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乃是属灵。神将信徒的生命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归为神圣,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但他仍生存在世界当中,时时可能按照世界的惯性来生活。圣徒需要靠着神的道来使自己的灵里的生命长大。信,依靠的不是人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决心,而是靠着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即便是耶稣本人,也时时靠着神的话语来喂养自己。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世上的光,是圣徒每日的灵粮。每日领受生命的粮,灵里方得饱足,属灵的生命才得以长大。然后我们才有能力和勇气,面对世上的工作,并能够在工作上得着宁静、平安和恩慈。只有通过听道,才能够领会日常事务的意义,并能够真正赋予这些事务以价值,真理才得以光照日常生活。被事务所塞满的世界,方可摆脱其物质的昏昧性,而被真理照亮。
而马大服侍肉体,忙于准备物质的粮。马大代表了世人普遍的想法,也就是认为,可以因为种种理由,而不去听道。如果因为要煮饭、烧水而暂时地放弃听道,那么,人们还可以因为其他理由,工作、学习、会友等任何一种事务,而放弃听道,如此一来,也就可以永远放弃听道。只要在世上活着,总会有事情,成为放弃听道的理由,正如马大那样——有“许多要作的事情”。或者说,可以将听道放在次要地位,而服侍肉体、顺从肉体,被摆在了首要位置。
耶稣基督的教诲是:首要的是坐在祂脚前聆听祂的教导、领受祂的旨意。耶稣反复强调说:“有耳的,就应当听。”并吩咐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太6:31)?信道,必要信神主宰一切,预备一切。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上面临断粮断水的困境时,神从天上降下吗哪,满足他们每日的物质需求。而现在,耶稣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吗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使人吃了就不死。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食物,人若吃了这食物,就必活到永远”(约6:49-51)。这份灵粮,就是耶稣的所说的真理的话语。
上好的分,是不能夺去的
耶稣说,马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分”。与主同在,在主的脚前,聆听真理的话语,这就是得了“上好的分”。
许多释经家将马大解释为律法主义和完美主义的典型,是企图靠着好行为称义,但在我看来,这一解释并未切题。马大并未自我称义,也没有追求行为上的至善,她只不过是在践行日常的义务,做属世的工。马大的错误乃是在于,她将日常服事为优先,甚至因此而贬低“听道”这一属灵行为的至高价值。人活着,不是为了生存而烦忙。固然有许多事情要做,此时,人们面临了一个选择:日常事务的操持或倾听真理话语。圣经教导并不否认日常事工的必要性,却规定了行动价值的优先性。与神同在,生存的操劳就被赋予了意义,它不再是徒劳的烦忙,而是成为荣耀神的途径,也是在世的生存者最大的蒙福。可是,当人们选择了“上好的分”的时候,是不能因着世间事务的烦忙和日常的需求,不可以因任何理由而被夺去。
马大当然也是在侍奉神。能够在日常事务上侍奉神,这本是神的恩典,本当感恩。可是,马大的问题在于,她并未真正意识到,这也是一种福分,并未在服事当中体会到神恩,并未因此而欢欣快乐,相反,服事成为她的负担。她被这个世界的日常事务所缠绕,裹挟,以致难以自拔。她被事务所拖累,事务的规则支配了她的行为,构成了她的“烦”。她只能感到身体的疲惫和灵里的烦乱。于是,她就开始了抱怨。在一个与主面对面的机会到来之际,她却转身投向了现实世界。当她再一次回到主面前时,则带着一肚子委屈和抱怨,从自己的属世的操心忙碌中产生出来的负面情绪。
马大是在服侍人。她并没有意识到,造访她家里的那一位,乃是至高神的儿子。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服侍神。当她转眼看妹妹马利亚的时候,也未能发现妹妹所选择的行为的真正价值所在,只是看到了妹妹脱离了烦忙的事务。在她看来,这是一种懒惰的表现。她所想的,是要将妹妹也拖入到自己的烦忙当中。她试图通过主耶稣的介入,而取消乃至夺去马利亚的已经得到的“上好的分”,好让她妹妹也来分担她的日常烦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她所承受的事务的压力。她甚至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请求神,让神来满足她的意愿。这也是人最容易犯下的错,哪怕是信神的人也难以避免。人在自己需求帮助的时候,往往首先想到的不是顺着神的旨意,而是请求神来成就自己的意愿。好像不是人应当以神的仆人的身份来事奉神,反倒是人要支配神做这做那。如是,乃是颠倒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马利亚因着灵里的渴慕,专心在主的脚前聆听真理的话语。正如彼得在领悟到耶稣基督的真理时所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约6:68)?正是这个马利亚,当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蒙福的人的时候,她将自己的事奉推向了完美的至高境地——在主耶稣即将完成他在地上的使命的前夕,她打碎玉瓶,将极贵的香膏完全倾倒在耶稣的身上,于是,世界顿时充满了芬芳。在这个污浊的世界,荣耀主的香膏的芬芳,才是真正的生命价值所在。耶稣论到这件事,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福音无论传到世界上甚么地方,都要传讲这女人所作的来记念她”(可14:9)。
马利亚——这个有罪的而且卑微的女人,因着她的忠心,因着她的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奉献,为我们在世的人的事奉,提供了辉煌的典范。
①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229页,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②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21页。
③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67页。
④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63页。
⑤ 阿尔贝·加缪:《局外人 西绪福斯神话》,见《加缪文集I》,郭宏安译,第19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⑥ 麦奎利:《存在主义神学》,第132页,成穷译,(香港)道风书社,2007年。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