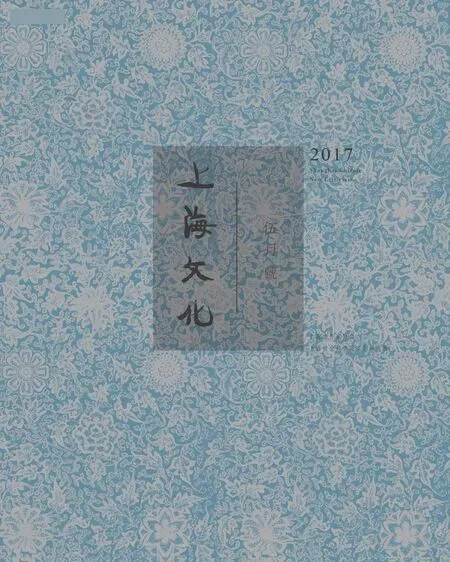文本世界的青年往何处去石一枫小说里的斗争与无望①
吕永林
文本世界的青年往何处去石一枫小说里的斗争与无望
吕永林
一
近几年来,我心头常常会萦绕一则略显抽象的故事:起初,每个人都是自己想象中的国王或英雄,后来多数人失落了,沦为被流放、被关押、被挟持、被异化的对象,大家一同忘却了自己想要“解释世界”、“改变世界”、“与世界执手相欢”的原初热望和极乐未来,也忘却了自己并非天生就孤苦一人的创世神话和英雄史诗。因此,当我看到在《b小调旧时光》的作者简介中,石一枫说,“五岁的某一天上午,我是这副模样:艳阳之下,肥白的小胖子,将一只电视机纸箱子套在身上,把自己想象成了一辆坦克,嘴里砰砰有声,在大院的林荫道上开动。已经过二十多年了,我不时幻觉自己仍然是那模样。一颗稚嫩的、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心,比任何东西都有资格成为人所追求的理想”。我直观地认定,这是一个青年作家对自身完整历史的某种呼唤和重构行动,而当他将自己童年时代的那一“模样”和“游戏”命名为“个人英雄主义”之时,也必埋伏着他对现在的自己、他人和整个世界的某种新的想象和命名。
这么多带“小”字的主人公接二连三地出现在石一枫的文本世界里,应非偶然
当然,小说家总免不了命名,其中之一种,便是给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取名号。石一枫的作品中,许多主人公的名号都带个“小”字——赵小提、李小青、陈小米、安小男、颜小莉、小李……给自己创造出来的主人公取什么样的命字或称呼,无疑是一个作家面对世界、解释世界的重要方式,这么多带“小”字的主人公接二连三地出现在石一枫的文本世界里,应非偶然。而在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语境中,“小”既可能意味着还原和真实,也可能意味着无能或丧失——比如一个人在全社会中(而非小说中)的“主人公”地位或精神的丧失,比如一个人的生活疆界、思想疆界和行动疆界的不断坍缩与板结。对此,最具文学性的传递之一,就是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尽管刘震云本人在事后时不时地会为“一地鸡毛”和生活在其中的有姓无名的“小林”正名,说那“一地鸡毛”同时也是“一地阳光”。让我感兴趣的是,石一枫小说中的这些“小字号”人物会跟那个最终在“一地鸡毛”间死心塌地的“小林”有所不同么?还是不外乎某种换了套新装束的文字重演?
在论及史诗、悲剧和小说的区别时,青年卢卡奇曾说,“史诗的主人公”一定是“国王”,因为“严格地说,史诗中的英雄并不是一个个人”,“史诗的一个本质标志就是它的主题并不是一个个人的命运而是一个群体的命运这一事实……在其内部,每一部分都无法在其自身中与自己的内心相分离,成为一种充分地自我封闭、自我依赖的个性存在”。我们知道,卢卡奇彼时所指的国王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国王,直到1917年之后,他才找到了无产阶级联合体这一新的历史主体和史诗主人公。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听到来自梭罗的声音:“不,做一个发现你内心的新大陆和新世界的哥伦布吧,开辟新的海峡,不是贸易的海峡,而是思想的海峡。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王国的君主,和这个王国相比,沙皇的尘世帝国只不过是个区区小邦,冰原上留下的小圆丘。”读了《瓦尔登湖》的人们应该清楚,梭罗此处所邀约的,并非某个充满等级制的政治共同体的君主,而是那些古往今来既彼此独立又互相对话的思想国的君主,是那些地位平等的思想界的同道中人,这样的同道中人,无形中也构成了一个可视或不可视的生命共同体,一个特殊的民族,并一直在创造、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史诗。然而,无论是在卢卡奇话语意义上,还是在梭罗话语意义上,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显然都不能被归入史诗的行列——即使有人祭起“平民史诗”的概念,也仍是如此。小林的命运虽然具有一种普遍化的悲剧色彩,但他对灰色现实的忠心归顺使其同各种心怀不满且坚持抗争和历险的群体彻底脱落开来,并最终隶属于一个数目广大却支离破碎、孤独分化的人类物种。借此,我实际想要追问的是,石一枫小说中这些“小字号”人物会成为当代社会中的另类“英雄”或“国王”么?或者说,石一枫这些以“小字号”人物为主人公的作品会成为某种另类的“史诗”么?再换而言之,石一枫这些作品的主题有没有可能被我们理解为:它们指向的并不是一个个人的命运,而是一个潜在的或无形的群体的命运?
二
在石一枫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一个叫赵小提的人物,比如《恋恋北京》、《合奏》和《世间已无陈金芳》,而这个人物之所以名叫“小提”,大概跟他少年时代曾经苦练过小提琴的经历有关。这便涉及一个人的精神前史,以上三篇小说给三个赵小提安排了一个共同的命运:告别小提琴。个中原因不尽相同,《恋恋北京》里是因为一次可悲的“开窍”事件,使刚拿到一个全国性比赛金奖的赵小提猛然意识到自己在拉小提琴这件事情上的天赋限制,同时也触发了他对自己这一“平庸”或“无能”的分外恐惧,因此决意自伤左手中指,以断绝小提琴之梦;到了《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是音乐学院的主考教授在“艺考”环节直接给赵小提判了“死刑”;在《合奏》中,则是一场因于自身的情感暴力给赵小提留下了意想不到的精神创伤,从而导致他“再也无法用小提琴拉出一个音符了”。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事件”,照我理解,赵小提的这段精神前史,同时也构成了我们许多人的精神前史。在各自的童年或少年时代,我们都曾梦想过以某种自己欢喜的方式抵达生活的中心或峰顶,“长大后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当医生”,“我要当画家”,“我要当作家”……每一种愿望背后,其实都矗立着一个英雄或国王般的自我理想“镜像”。因此,无论现实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屏障挡住了他,对于成年后的赵小提而言,跟小提琴告别,本质上是跟那个自己曾经无限制地投入其中并对之满怀期待的“世界”告别,是跟自己想象中的无限欢乐和“淡紫色的远方”告别。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共情”性地理会到,为什么赵小提高考时凭着“几十分的特长生加分”,最终拿到了一所综合性大学“烫金的录取通知书”后,“心情仍然颓丧极了,整个儿人沉浸在漫无边际的失败主义情绪之中”,有时甚至还会“恶狠狠地诅咒自己:让车撞死才好呢”。
更具灾难性的后果在于:跟小提琴“分手”之后,赵小提在长时间内既找不到新的支撑性的爱欲对象,找不到他可以为之“献身”或值得他勇猛“捍卫”的事物,找不到实实在在的生活的“热情”;也找不到他进入社会并与之顺畅欢合的“合法”路径,成年人必须要摆放稳妥的道德和伦理难题,在赵小提这里以一种精神焦虑的形式出现了。赵小提既做不了b哥(大名龚绍烽)式轻松穿越“底线”的黑暗投机者,也没有勇气成为时代的叛逆,他于是将自己“半吊”在中间,如同他跟陈金芳所说的那样:“比起那些狠捞人间造业钱的主儿,我宁可把自个儿的欲望尽量降得低一点儿,当个无伤大雅的寄生虫,这也是一个混子、一个犬儒主义者最起码的道德标准了……”对此,陈福民的评论可谓体现出一个批评家应有的了然于情和体贴之心,他说:“石一枫小说中的人物,多是一些无所事事之徒,他们顽固持守着一些不明所以、不可理喻的信念,貌似在一塌糊涂的泥浆里打着滚而又努力抬头仰望着什么。”“石一枫通过自己的写作见证并呈现了致命的时代病——一个多元混乱的社会表象背后,赫然矗立的无坚不摧冷酷无情的商业逻辑以及由此形成的单向度一体化的价值系统对人的赤裸裸的压迫。在这个时代的对面,在几乎所有人的对面,石一枫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敢以真理自居,但却勇猛无畏地无所事事。也许可以把这一点理解为石一枫文学写作的脆弱的先锋性和批判性所在。”“在小说中,石一枫始终被一种力量纠缠着,换言之,一种让他无法彻底放下的东西支撑着他的写作。我姑且把它叫做‘青春后遗症’吧。作为一位标准的‘青春后遗症’患者,石一枫通过自己的写作,生动刻画出这个时代中各个患者的艰难挣扎及其负隅顽抗。他以自己的小说写作捍卫了少数人的青春后遗症的权利与合法性。”
严格地说,即使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无所事事”的青年人形象也并不罕见,譬如在朱文和韩东笔下,就有不少这样的人物。但是相比较而言,赵小提这个人物的独特性在于,“无所事事”并非其固有的生命情态,当他回望自己的少年时代,就曾发出过如此这般的自白:“我是多么热爱小提琴啊。如果不热爱,我怎么可能忍受十几年严酷、枯燥的琴童生涯呢”(《恋恋北京》)?因此所谓“献身艺术”的说法,也全非事后的自我调侃之语。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自从艺术和科学在人类生活整体中被专门化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将它们抬举为离真、善、美最近的事物之一二,从而使其拥有近乎天然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甚至使其拥有在道德质询和伦理审判层面的优先豁免权。因此,对于少年赵小提来说,对小提琴的投入和热爱不仅为其提供了一条可能通达人生胜境的幽曲小道,同时也在无形中为其提供了一处道德和伦理上的临时庇护所,使其在有意无意之间,以为自己会在世界总体化的利益交换链条中享有某种自然而然的洁净和清白,尽管在一些具体而微的事情上,他们也可能“从来没在道德品质方面过高地信任过自己”,但这并不会妨碍其在想象和抽象的层面,培养出一种根深蒂固的自我道德期许。我认为,成年赵小提之所以反复念叨他作为“一个混子、一个犬儒主义者”还操守着的“最起码的道德标准”,还操守着他自设自认的伦理“底线”,此乃一个极其重要的精神来源。而在《我妹》中,面对好友李无耻及其所代表的现实世道,杨麦最后之所以会激烈地“呕吐”起来,以及在《我不是陈金芳》中,庄博益最终在心里选择了对中国贪官二代兼美国商人李牧光的倒戈,也都与这样的“底线”伦理及其精神起源相关。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拥有一个类似赵小提般的“小提琴少年”心灵史,但的确又有许多成年人仍拥有着自己的“底线”情结和道德冲动,无论其各自的精神起源与维护机制如何,赵小提这个可谓折射出了当代许许多多人共同的道德和伦理心象。说实话,我个人倒是非常希望,石一枫在之前创作中所行的这些对赵小提的“零敲碎打”,乃是在做有意识的演练和准备,而非真地出于某种写作上的“推卸责任”和“自我逃避”。我更希望有一天,石一枫会“创造”出一部属于赵小提其人的另类“史诗”,以扫荡或摆脱那种“一地鸡毛”式的旷日持久的宿命。
并不是人人都拥有一个类似赵小提般的“小提琴少年”心灵史,但的确又有许多成年人仍拥有着自己的“底线”情结和道德冲动
三
与成年赵小提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来,陈金芳这个人物的可爱之处在于,她轻易不会死心。这是一个来自当代社会底层和精神荒原的“孤魂野鬼”,却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与命相抗的生命力,在遭遇小说中“最后”的失败之前,陈金芳一直怀有对世界和未来的某种热望。陈金芳在少年时代就是一个对生活有着“非分之想”的人,在这一点上,她倒还真有点“女版盖茨比”(《十月》杂志责编季亚娅语)的味道。巨大且现代的北京,无疑是在无限黯淡且令人绝望的故乡对面,为少年陈金芳扮演了一个神奇召唤者和“美丽新大陆”的角色。但是,“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是被封死的,陈金芳自己也未奢望过多,由于种种原因,她上课常常睡觉,课程从来就没有跟上过,然而音乐,具体说是赵小提在夜晚拉的小提琴,却给陈金芳带来一种奇异的启蒙。初中时代,陈金芳常常把自己藏在夜色深处听赵小提拉琴,琴声,音乐,或者说所谓艺术,定然在这个少年心中划破了黑暗,划亮了一道勾引梦幻的光,使她不由自主地向着模糊的未来眺望着什么,就像盖茨比朝着“通向树顶上空一个秘密的地方”眺望一样。包括后来辍学跟了豁子,陈金芳在二人的服装生意“赔了个底儿掉”之后,“还一个劲儿地逛商场、吃西餐,每逢北京有小剧场话剧、音乐会之类的演出,都会死磨硬泡地让豁子给她买票”。而最让豁子想不通的是,就这样陈金芳还“不知足”,“后来居然偷偷把店里所有的钱都拿出去,说是想买钢琴”,就跟“疯了”似的,豁子说,“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人脑子里想的到底是什么……”到此为止,我相信,石一枫笔下的陈金芳和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一样,都会让那些神经尚未完全钝化的读者打开一间人类所共有的心灵秘室。
不过,石一枫并没有真的将陈金芳塑造成一位“女版盖茨比”,虽然他在后面也让陈金芳接近了“财富”,踏入了当代城市中产和上流社会,从而在一些表面的设计上与《了不起的盖茨比》有相似之处。但是小说结尾处,在作者的“指使”下,陈金芳亲口供认了自己孜孜以求的梦想不过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一下子,一棵枝叶自在的文本之树被砍得只剩下光秃秃的主干,或者说,小说主人公之一陈金芳的故事顿时被落实为一个与“失败”相关时代的寻常故事,陈金芳这个人物也因此失掉了她对许多人心灵幽秘处的隐喻或象征功能。至于豁子所说的陈金芳的“不知足”,及其对陈金芳“脑子里想的到底是什么”的巨大悬疑,也最终就成了不了了之之物。当然,拉低陈金芳这个人物形象的,不仅仅在小说的结尾,小说中间也有。例如陈金芳对意志消沉且玩世的赵小提的体己式劝慰,乍一看似乎颇有些深刻之处,可实际上并未高出现时流行的心灵导师们多少,更与盖茨比的心灵深度距离甚远。而同样是言笑晏晏之态,成功实现了其“变态发育”的陈金芳给赵小提带来的心灵击打至多是“花媚玉堂人”般的美好,而盖茨比给尼克造成的感觉却是:“这是极为罕见的笑容,其中含有永久的善意的表情,这是你一辈子也不过遇见四五次的。它面对——或者似乎面对——整个永恒的世界一刹那,然后就凝住在你身上,对你表现出不可抗拒的偏爱。”由此可见,走出少年时代的陈金芳,似乎已经不再拥有朝着树顶上空的某个神秘地方眺望的能力,无论是其心灵的疆界还是性格的深度,都比之前窄了许多,也浅了许多。因此,如果说小说的名字“世间已无陈金芳”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个陈金芳,应当首先指向少年陈金芳,而非成年陈金芳。成年陈金芳是在这个时代是无穷尽的,这一个倒下去,更多的站起来。如此看来,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除了成年陈金芳的失败这一显在的悲剧,还有一个潜在的悲剧未被写出,或者说未被十分真切地写出,那便是成年陈金芳对少年陈金芳的“失去”。
四
《地球之眼》中的安小男是一个将其少年情志保存完好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叛逆。不过与赵小提或陈金芳不同的是,自从其父亲跳楼自杀后,安小男最核心的少年情志就不再是对世界和未来的某种热望,而是试图解答父亲临死前留下的那句关于道德的“天问”。也正是由于这一隐秘的心结,安小男拒绝同“敌人”苟合言欢,而是决意通过自己的技术专长对李牧光及其贪官父亲进行惩罚。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安小男的斗争精神和他所实施的“个人化”惩恶行动可能并不会对当前社会的总体疾病形成多少有效的治疗,但从文学的角度看,安小男这个人物形象却具有一种正当其时的感召与唤醒功能。小说最后刹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带的一个叫作挂甲屯的地方,无疑也传递出一种复杂的意味:微观英雄安小男带着双眼近乎失明的母亲在此隐遁,而“我”(庄博益)却经由安小男这个人,“对于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的观念,似乎也发生震撼性的改变”。
这并非石一枫第一次写到“斗争精神”,当然更不是最后一次。之前在长篇小说《我妹》中,石一枫就已经书写过几位“战士”——陈小米、肖潇和老岑,老岑甚至被作
走出少年时代的陈金芳,似乎已经不再拥有朝着树顶上空的某个神秘地方眺望的能力者塑造成一位“圣徒”,尽管在“我”(杨麦)眼里,老岑有一种被迫成为的“中国式的圣徒”意味,可是在许多时候,老岑却实实在在地担当了陈小米、肖潇和“我”的精神父亲的角色。小米是“我”同母异父的妹妹,比“我”小很多,这是一个连老岑都会另眼相待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孩子,中学时热爱新闻专业,却因患有色盲症而无法报考,并放弃了南京大学的会计专业。在小米身上,一直升腾着一种近乎天然的对真相、正义和爱的固执要求。后来,她自愿加入老岑和肖潇的队列,和他们一道,用他们能够守得住的方式果决地生活和行动着。并且,这老、青、少三代人的会师,也给早年离开老岑、退出“战场”的“我”带来一种新的激荡和召唤,让“我”在某个瞬间忽然觉得,“多年前的那个自己也被找回来了”,而在之前的许多年里,“我”却长期不愿直面鲁迅所说的那个“皮袍下面藏着的‘小’”,这也恰恰是“我”一直“害怕见老岑的真正原因”。至于比《我妹》、《地球之眼》更加晚出的《营救麦克黄》中,小说主人公颜小莉则因无以解除的良心自责而走到了退无可退的精神悬崖边上,好在,她也终于选择奋起相抗,跟货车司机于刚联手,用计对黄蔚妮实施了一次必要的“惩罚”,以此尝试纾解自己心中的焦苦难安。及至再后面的《特别能战斗》,石一枫则干脆“创造”了中老年妇女苗秀华这一嫉恶如仇且永不缺席的“斗士”和“勇者”形象,上班时期她跟单位头目斗,跟深得单位头目欢心的女办公室主任斗,退休后跟违约的房产开发商斗,跟无良物业斗……不过在这篇作品中,石一枫也写出了他对苗秀华这样的斗争者的疑虑和担心。
书写“斗争精神”的同时,石一枫也触碰到众人感同身受的巨大愤懑与悲怆,比如在《地球之眼》中,这种愤懑和悲怆是连“我”(庄博益)这种精神上的“丢盔弃甲者”也轻易拆除不掉的:
按照我惯有的那种嘲讽性的、自以为世事洞明的思路,安小男的生活可以被定义为一场怪诞的黑色喜剧,而我也可以一如既往地从几声苦涩的冷笑中重新获得轻松。
但我没能做到。夜已经深了,窗外的天空静谧、幽深,连风的声音都没有。孩子吃饱了奶,和保姆睡在隔壁,小张正靠着枕头看书,脸色在台灯下分外光洁。在这安详得暄软的氛围里,我却感到了浩大无比的悲怆,仿佛肉体以外的东西都被震成了粉末。
一个人的胸口如果还能生出悲怆与愤懑,就可能意味着他还揣着一颗未死之心。不过这悲怆和愤懑亟待人们去实施更进一步的动作,否则就会让人产生极大的焦虑和极深的抑郁,而这正是一个时代患有集体焦虑或抑郁症的根源之一。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疗治方式,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最终混迹文化圈的赵小提选择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乃是通过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式的“放纵生活”,才“成功地克服了那如影随形、让人几乎想要自杀的抑郁”。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样的治疗恐怕未必有效,哪怕只是换一个赵小提,或者给赵小提换个不一样的人生处境,情形就可能会大不相同。于是我们看到在石一枫所创造的文本世界中,不断有人开始从脆弱、无能的精神泥泞中站起身来,从各种卑贱、苟且之中爬了起来,走向斗争和叛逆,比如《地球之眼》中的安小男和《营救麦克黄》中的颜小莉。至于《我妹》中的陈小米,则似乎从一出场就比别人“多了一分从凡俗生活里挣脱出去的力量”,当然在更加真切的意义上,小米那种果决、坚定的生活态度,恰恰是她很早就开始面对和治疗自己所遭受的特殊创伤(色盲和丧父)的结果。
我想,上述这些,已经构成石一枫写作中的一个多少有些“与众不同”的起点。我甚至猜想,在石一枫今后的写作中,将会有更多的少年、青年、中年乃至老年人出来重拾他们的“英雄”或“王者”镜像以及“原始自恋”,去直面自己的失落与创伤,以个人或集体行动的方式去操持必要的良善之心,践行应有的正义之道,从而实现对其个人创伤乃至时代疾病更加长久、深远的疗治。当然,这样的“英雄”或“王者”——文本世界的“主人公”——最好能懂得在所有的斗争中,一个人“反对自己的狭隘和隋性”的斗争才是“最耗精力、而又几乎无望的造反”行动。如此,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人们将有机会阅读由石一枫“创造”出来的别样的“史诗”系列。
①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晚近二十年中国文学中的小微化青年形象谱系研究”(项目号: 2015BWY006)的阶段性成果。
② 石一枫:《b小调旧时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
③ 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2-43页。
④ 梭罗:《瓦尔登湖》,王家湘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324页。
⑤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8页。
⑥ 陈福民:《石一枫小说创作:一塌糊涂里的光芒》,《文艺报》2011年11月7日。
⑦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第17页。
⑧ 同上,第233页。
⑨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巫宁坤译,中国宇航出版社,2013年,第124页。
⑩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第37-38页。
(11)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第53页。
(12) 石一枫:《我妹》,外文出版社,2013年。
(13) 同上,第262页。
(14) 同上,第281页。
(15) 同上,第259页。
(16)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第209-210页。
(17) 同上,第42页。
(18) 石一枫:《我妹》,第281页。
(19) 此处引用的虽然是拉康在讨论人的“镜像阶段”所提及的一个概念(见《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第95页),但我并不完全同意拉康对人的“童年大梦”的那一判决。
(20) 雅诺施记录:《卡夫卡口述》,赵登荣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56页。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