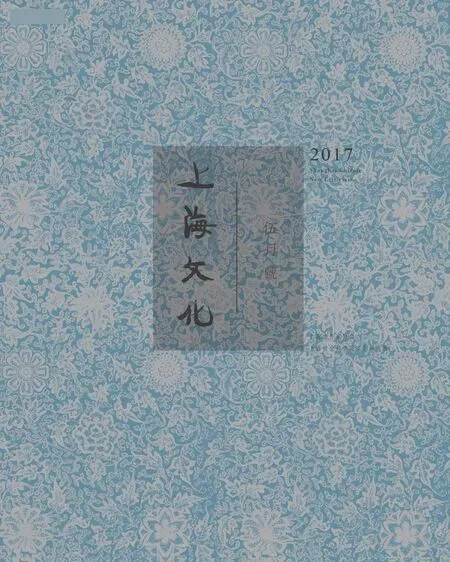金嘴
霍拉斯·恩格道尔万 之 译
金嘴
霍拉斯·恩格道尔万 之 译
我哀伤的是我的嘴不是无限的。
——贡纳尔·布约灵
一个人的声音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考虑的只是某种生理学或物理学现象,比如呼气、声带、口形和声波等等,那么这个问题看起来琐碎细小。不过,一种自然科学的解释,对于正在说话的声音,等于什么都没说。
那么我们就进一步进入语言科学吧,但依然会感到困惑失望。语言学家研究的不过是声音的发声读音,但这个声音本身是在这个领域之外。这样被排除在外,很可能是方法上的,隔行如隔山。就算更换别的声带,也不会影响到语言声音的形式,不会触动所说句子的词汇上语法上的特性。在某个特别声调或者强调重音也构成表述之一部分的范围内,那么这种表述的调整必须能用一种所有语言表述者使用的同种方式来执行,这样才能在该语言系统里做这种调整。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了,我们对于某种表述的理解会发生变化,这取决于这种表述是由男人说还是由女人说,或者说话的听起来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是完整的还是断断续续的。罗兰·巴特写道:“对声音的倾听建立了和其他声音的关系:通过这个声音我们认识了其他的声音(就如一个信封上手写的文字),这种声音为我们显示出它们存在的方式,它们的快乐或者痛苦,它们的场所;这个声音会带着一个其身体的图像而且不仅如此,还带着完整的心理状态(比如我们会谈到热情的声音或一种没有色彩的声音等等)”。古代的修辞学者已经知道,听众对于某一叙说的判断首先是基于说话者的性格特征,即希腊语“ethos”。我们对于谁在说话的评估(有多少力量?有多少诚实?有多少经验?有什么样的感情状态?),决定了某一措辞是否达到了或者失去了其说话的作用。听众得到的性格图像是取决于说话者的声誉,但是也受到他出场讲话情况的影响。一个人的声音就是这个人的浓缩形式的性格特征,一个发出声音来的信号描述。
修辞的经验显示出,声音能起到语言的标志作用,标志单独个别的起源。这意味着这个声音既是语言性的,同时又不是语言性的。它本身是言说之物的载体,也是可言说之物的界限。在个人那里,声音代表了不可象征化的事物,不过它的前提同时也是语言的象征化,因为从一个人嘴里冒出来的不清楚的发声还不能算是声音。一个人的声音并不等于在所谓“用嘴巴发出的声音”之意义上的“口说”。它和言说是不可以分离的。听一个声音,就是听某人说话(或者说唱或者唱歌)。这是一个有身体意义的充满了形式的发声。德里达称之为“干燥的声响”。那么哼哼的有节奏但没有词语的音响是什么呢?显然当有人用元音来唱歌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声音了。这同时也是被排除在外的第三者——没有语言的语言——也是说话的开端。儿童在学会词语之前,在理解言说的参考功能之前,就能模仿词语的旋律了。有节奏的造句,语法的胚胎形成,是在词汇之前。
嘴巴是一个混合声气的容器,一个变换的洞穴。我吞下了其他人的词语,又把它们当作自己的词语吐出来,并混合了我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是无法冲洗干净的,而是让我的表述改变了特点(有了另外一种性格特征)。当我抓起笔来书写的时候,这种关系也并不取消其有效性。在书写中会让人想起的那个主体虽然没有什么声音上的特别种类,不过还是会在意识中作为声音出现:一个声调、节奏和音响的单元,会告诉我们那些说出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理解一个文本,其实就是把一段话的口语经验转到无声的字母世界。这段话在一种无形的套子中被包裹成了句子,并在一种收集动作中呈现给读者。在包容了一个声音形式的同样范围内这些文字就成了可读的。这就是康德所说的“阅读的超越条件”。不过也有其他人,比如保罗·德·曼把这点看作审美的幻觉,严格的文学批评家应该与之保持距离。
嘴巴是一个混合声气的容器,一个变换的洞穴。我吞下了其他人的词语,又把它们当作自己的词语吐出来,并混合了我自己的声音
那么文本也应该有嘴巴吗?
对这样的分析推理必须提出一个警告。写出来的文本掩藏了结构,这种结构在它们转变为口语化的时候才呈现,这并不意味着文本在本质上是抄写下来的话,或者只有在和活生生的词汇的关系中的一种服务功能。谁要相信这一点,谁就会成为德里达已经很成功地诊断出来的“声音中心主义”病症的牺牲品。文字的特殊之处就是文本中发出的读者听不到的声音很可能是作家从来不会说出的东西。
1818年,瑞典批评家阿特布姆在从意大利回国的路上经过维也纳,到皇家宫廷剧院看戏,剧目是格里尔帕尔泽的《萨福》,主演是著名的女演员施罗德夫人。格里尔帕尔泽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生从来没有听到如此高声朗诵诗歌;完全是诗歌的音乐,有最美妙的音色变化,抑扬顿挫,让人如醉如痴;当诗人心里涌现出这些诗句的时候,他的耳中就是这样的声音,尽管通常他只是用笔写下来,而不是用他舌头来表达,但是在这里和一种非凡的美结合在一起,宏亮饱满,都是每个灵魂琴弦的动人的声音。”阿特布姆坐在剧院包厢里喜极而泣。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他的思路。在高声朗诵中实现的美,其起源并非是诗人的舌头,也不是由他的笔来诠释的,而是在他的笔本身。通过它和诗人耳朵的联系。也就是说,诗人写下的文字倒比他的说话更具有口语性,甚至到了只有施罗德夫人的杰出嗓音才能表演再现的那种程度。
阿特布姆理解了,在这样的声音承载的美里有某种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时刻,这个声音是诗本身的声音,而不是诗人的声音。在最个人化的事物之中,隐藏着一种非个人性诗学的胚芽。
在这个时刻,这个声音是诗本身的声音,而不是诗人的声音
马拉美
似是而非的是象征主义文学的某种期望,即期望一种作家本人从中消失的诗歌,它让马拉美反思“文本中的声音”这样的奇妙现象。他是从他的诗的概念出发,在他看来诗不是相对散文而言的文体,而是有意识地对风格进行尝试的每一种语言表达的名称。“除了广告和报纸的文化版之外,诗到处可见,只要有节奏的语言就有诗。”
对于马拉美来说,简而言之,诗就是个人性的发声,发音。“……每个个人都有自己的说话韵律,新的韵律,和这个人的呼吸息息相关的韵律……”但要注意:在诗中显露出来的是诗的主体——不是那种资产阶级的个人,甚至也不是作家本人。马拉美谈到“除掉那个还留在写作中的绅士”。输送词汇的是那个通过写作而成为输送者的主体。诗歌的嘴则是另外一张嘴。
其实还是一回事情。马拉美的诗歌句法显然有对话的特点。句子开始的时候他的想法还没有完成,这种想法还在活动中,还在继续扩展,在强化,在变得更准确,在和其他想法隔离开。各个词组都获得一种手势动作的特点。他的短语要求制动,要求声调的转换,要求有重点有韵律节奏——也许还必须高声朗读才能理解。马拉美现在被看作是法国文学最不容易理解的散文作家之一,但是听过他朗读的人都不认为他是法国作家中难以理解的一位。亨利·列吉涅尔就提出这样的证词:“通过美妙的遣词造句,马拉美文本的晦涩就消散了,不用去掉其神秘性也能呈现其内容。在朗读的时候,那些书写的句子都降落在听众可及的范围……”
尽管如此,马拉美在其理论思考文字“诗之危机”中预见了一种诗歌,口语的措辞会从这种诗歌中消除。他写道:“纯粹的文学作品是以说话的诗人消失为前提的,这是通过词汇被激发的不同性的冲突,把主动权交给词汇;它们用互相反射来彼此照亮,这种反射有如宝石上闪现的一道真实光线,代替了那种古老抒情灵感中或者句子里热情的个人意向中的可感觉到的呼吸。”
同时,马拉美诗歌的韵律节奏又可以构想成一种意念的散射,化为一种有空间感的形式。他谈到了诗歌中的音乐成分,就好像这是有关一种内部建筑的问题。当他把诗歌看作无声的音乐,他的意思并非悦耳的声音,而是一种有韵律节奏的观念关系的分配,这“比在公开的或者交响乐里的表达还要有神性”。这是一种思想的音乐:“这些诗句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古老的比率,一种规则性等,都依然会保存不变,因为这种诗性的活动能持续下来就在于能突然看到某种观念在一系列同样价值的动机中分解开来并把它们进行组合;它们能押韵……”
马拉美把印刷文字的书页的白色纸面和沉默联系在一起,意思是说在这里放置了诗歌的思想骨架(“智慧的框架”)。就连空格也创造出一种有空间性的节奏。
这种看法与书写图像的常规功能是抵触的。一张印刷文字的书页的力学通常不在于能看到不同字体痕迹上的韵律节奏运动,而是一种其起源在于句子的措辞造句中的运动。如果不是沉默的话,这也是说话说出来的。而在马拉美作品中,那些空行的精心计算过的用法扰乱了这种关系。而在他的活字排版印刷的长诗《骰子一掷》(Un Coup de dés)中也非常明显,朗读的韵律节奏并不能再现通过文字图像的编排而产生的韵律节奏。这个声音失去了对于这首诗的形式的控制。
乔伊斯的双重游戏
一种这样的变化会让那种古典文学阐释学面对一个困难。当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说理解会包含一种内在发言的时候,他是在概括说明现象学派诠释学的中心教义。我们是用听力在阅读。这毫无疑问是最古老的而且依然是最规范化的学习掌握文字作品的方式。韵脚、声音形象、多音词游戏,或许还包括韵律节奏等,很显然是在字母被作为声音来考虑的时候才存在的。不过,即使是句法,在很多情况下也会要求一种特定言说才能显示出来。某句子的力学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其逻辑的理解,这是现代主义已经善加利用而毫无犹豫的。比如贡纳尔·布约灵这样的瑞典诗人在很大程度上让韵律节奏代替了那些语法的关联,这也是明白无误的。总体来看,句法和词法上脱离常规的差异会加强一个文本的声音特点。我们被迫去品尝这些词汇,以便试验其各种关联的可能性。对一个文本内容产生怀疑,其实就是对于如何朗读这个文本产生怀疑。
作为内在发言的阅读,其前提就是在涉及到韵律节奏和声调的时候要做一系列的决定。反之,这个发言——不论是可以听到的发言还是沉默的发言——没有条件再现的正是在涉及某段话如何说出来的时候文本里的不可决定性。当听力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继续阅读呢?比如在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这部著作里,当我们看到“And we war”这个短语的时候,我们如何阅读呢?其中的第三词,如果我们读成[va:r],那么这三个词在内容上是对上帝之名耶和华的一种暗示,即“如是者”。如果我们读成[wɔ:],那么它们就是指上帝对巴别塔建塔者的战争。也就是说乔伊斯利用了“war”这个词应该读成英语还是德语的不确定性,这是在发言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一种飘忽不定。一个朗读者就不得不做出选择,因此也破坏了这种双重性。我们可以这么说,在这里有多个发音在同一个地方发出了声响:这个文本在自己的嘴里发言说话。
那么我们要不要放弃让文本发出声音呢?不,这同样是有破坏性的,因为在《芬尼根的守灵夜》里多重多样而不同的意义关联就建立在同音意义词和声音的回声效果的基础上,也建立在词源学的暗示以及来自一种或多种语言的词汇的融合的基础上。就算是这种多声特性无法在发言中表达出来:它还是完全要以声音世界为前提。把《芬尼根的守灵夜》在发言中说出来,就等于是消灭它,同时它也不需要发言说出来才成为《芬尼根的守灵夜》。正如德里达在评论“And he war”这段话时提出来的,乔伊斯的文本仅仅存在与其制版形式和其声音形式的分隔线上,而没有在其中任何一个单独维度上。它是被一张更大的嘴在言说出来,这张嘴与符号学的法则背道而驶,允许多个元素,没错,也是允许多个系统占据同一个地方。这样一种写作方式的想法其实乔伊斯是从马拉美那里得来的。这是文学史家大卫·海耶曼通过深入彻底的调查得出的结论。
《骰子一掷》
大众嘴里的语言,混杂了生活的垃圾,在诗人的嘴里就被清洁了,得以和一种陌生的措词造句方法一起震动
一个相应的问题出现在一首马拉美《骰子一掷》这样的诗中,尽管这里不是声音和拼写之间的边缘的问题,而是发言和排版图像之间的边缘的问题。高声朗读这首诗(本来这是应该发生的事情,要有多个当时的人的声音,大约就和一次未来派歌舞表演会上的情景)就可能提供对于这样一种想法内容的理解,但同时这也会使得其形式瓦解。除了字母会融合成线条,在空白处描绘出苍白图像,这些词汇的排版和在纸页上的位置安排会建立起发言中无法兑现的关联和种种差异。读者的任务是注意到文字的编纂,其多少就和倾听发言一样。
马拉美在其诗作如《烤面包葬礼》和《纯正指甲》中使用的句法可谓声名狼藉,其句子成分不是以那种自然顺序来通告的,而是用另外一种顺序,所以经常会有多种可能性来进行组合其语法路线,这就预告了一种革命性的改变。读者不是跟随一种声音的流动,而是得用词组来做碎片拼图一样的游戏。
马拉美给他的《骰子一掷》写的前言中,关键概念是“间距”(espacement)。这篇文字用其空间分配的方式对发言的与时间的简单关系提出了质疑,也是对其在活生生的当下中占据什么位置表示疑问。那些要用口语说出的内容在被说出的时刻就很快蒸发掉了,其全部内容是集中在倾听动作的现在时间里,是在持续不断地更新的累计中。与之相反,文本是处在这个时刻之外的。文本在综合一批同时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时间上不确定的意义,这些意义都可以提供给概览或组合的不同形式。要说文本和什么相似,那么也不是发言,而是记忆。不过这也可能是海市蜃楼一般的幻觉。在马拉美那里,书写出的文字是被作为一种固执不变的组合而揭示出来的,这是声音和空间的组合,是消失的和永恒的事物的组合,也是发言的持续性和书写的不持续性的组合。一种两者都分发词语又保留词语的方式;一种没有尽头的开始。
金 子
对于马拉美来说,对于从马拉美出发的全部写作方向来说,文学写作就是一个把日常生活语言转变为一种更纯粹和更真实的语言的问题。大众嘴里的语言,混杂了生活的垃圾,在诗人的嘴里就被清洁了,得以和一种陌生的措词造句方法一起震动。这种言说出特定词汇的新方式,最终就使得这些词汇从其他残剩语言中解脱了出来,因为尽管句子和音量经过调配,残剩语言依然会夹带在这些词汇上。马拉美向读者承诺,他会给他们带来“惊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平常的发言,同时对那些所提到事物的记忆沐浴在一种新的氛围里”。
当玛格丽特·杜拉斯梦见一个剧场,在这个剧场里我们真的可以听到词语的那种“在平常生活中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那么她就是马拉美的弟子。
马拉美在讨论诗歌的时候,使用了两个模式,一个音乐模式和一个星座模式,这已经被文学史家视为一个问题。阿尔伯特·提巴德在其已成经典的研究著作里就尝试过分析评价这个问题,对此有部分的异议。具体地说就是提巴德认为马拉美的文学创作是在爱伦·坡的影响之下从一个声响和语音构成的层面开始,不过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书写的诗人。提巴德把《骰子一掷》看作马拉美明确告别音响美学的作品。事实是我们时常发现,这两种思维方式可以在同一个段落里出现,那么这样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看来也是不可取的。
马拉美的原创性在于他把看起来不可能结合的东西结合了起来,把嘴巴的法则和文字的法则结合了起来。他谈到了“在文本下面的歌曲”(法语“l’air ou chant sours le texte”)。空格或间距的形式还是远远不够的。乐器必须发出声音,就算是不能听到的,因为要使得韵律节奏(形式)成为现实的存在。语言的声响关系会创造出比任何思想所能包含的关联还要巨大的关联,而这是诗歌构建的前提。在每一可能场合放置在文本嘴里的这个词,会在其他不在场的词中形成分支扩展开来。这是新的倾听的方式,是诗歌创作引发出来的方式,更是一个对这些关联加以关注的问题,而不是加重词汇意义的问题。这是通过其他词汇在某个词中如镜像反射出来,而使得这个词被改变。
我们可以采用马拉美散文中一个不言说出的关联中出现的几个术语,用于构建一个简单的例证:
Son(or)al
“Sonore”、“or”和“oral”这几个法文词意思分别是“发出声音的”、“金子”和“嘴巴的(口的)”;这些词一般并不常一起出现,但是在一个文本的空间里可以谨慎小心地互相回应,但并不包容在其发言说出时的现在时里。这就好像这个声音可以同时向两个方向说话,一个是语言的流动方向,而另一个是这个文本的回流的方向。做一种释义时的错误不在于这个声音阐明了词义,而是它变换的器官,把文本的声音放入一个过于狭小的嘴里。我们称之为理解的事情,其实常常是一种归还,还给通常的文本的“一次就一件事”的释义。魅力被取消了,被“说出什么”的需要给接替了。这种解释就和医生对催眠睡着的病人用手指打出响声一样:其潜藏地下的声音消失了。我们不是应该在睡眠中也阅读吗?也许金子只会对那些梦游中的关注才会显示出来?
书写的诗学的起源也只有在口语性中找到。上述例子中把字母“or”(词义为金子)括起来的括号,可以想象为这个文本的嘴,这个词就在里面发出声音,不过只是为了呼唤出一个并不在场的词。有没有可能想出一种发言,它虽然在震动,而且有丰富的关联,还是赢得了现在时,赢得了理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嘴的内含就是诗歌的金子。
语言的声响关系会创造出比任何思想所能包含的关联还要巨大的关联,而这是诗歌构建的前提
A 作者简介:霍拉斯·恩格道尔(Horace Engdahl,1947-)是瑞典著名文学批评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机构瑞典学院院士及该奖评委会评委。此文选译自其文学批评论文集《风格与幸福》(Stilen och lyckan,1992)。全书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
② 贡纳尔·布约灵(Gonnar Björling,1887-1960)是出生于芬兰的瑞典语诗人,芬兰的瑞典语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人物。
③ 参见罗兰·巴特论文集《显义和晦义》(L’obvie et l’obtus)巴黎1982版第225页。
④ 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比利时出生而长居美国的文学家。
⑤ 阿特布姆(Per Daniel Amadeus Atterbom ,1790 -1855)是瑞典浪漫派作家、批评家。其代表作有《至乐之岛》(Lycksalighetens ö,1824-27)。此处引文见其散文集《来自德国意大利的记忆》(Minnen från Tyskland och Italien)1859年版第553页。弗朗兹·格里尔帕尔泽(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是奥地利剧作家,《萨福》(Sappho,1818)为其代表作之一。施罗德夫人(Wilhelmine Schröder,1804-1860)是著名德国歌剧女高音演员。
⑥ 参见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1842-1898)《全集》(Oeuvres complètes)巴黎1951年版第867页。
⑦ 同上参见马拉美《全集》第364页。
⑧ 同上参见马拉美《全集》第657页。
⑨ 最早提出这一点的是法国文学批评家舍尔勒(Jean-Jacques Scherrer,1855-1916),可参看其论著《论马拉美作品的文学表达》(L'expression littéraire dans l'oeuvre de mallarmé)巴黎1947年版第192-196页。
⑩ 引自舍尔勒的著作《马拉美的语法》(Grammaire de Mallarmé)巴黎1977年版第68页。亨利·列吉涅尔(Henri Regnier,1864-1936)是法国诗人、作家,马拉美的学生。
(11) 同上参见马拉美《全集》第366页。本文作者认为,马拉美所谓“说话的诗人消失”也就是指纯粹的文学作品要告别修辞。
(12) 引自马拉美1893年1月10日致顾瑟(A.E. Gosse)信件,收录于《通信录》(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第6卷第MCDIII号。
(13) 同上参见马拉美《全集》第364页。
(14) 引自马拉美1892年10月27日致莫里斯(A.C. Morice)信件,收录于《通信录》(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第5卷第MCCCLV号。
(15) 参看德里达《尤利西斯留声机》(Ulysse gramaphone)巴黎1987年版第46页。
(16) 参看大卫·海耶曼(David Hayman)《乔伊斯与马拉美》(Joyce et Mallamé),巴黎1956年版。
(17) 有关这种相似性的更详细分析说明,可参看作者发表于文学批评期刊《危机》(Kris)1983年第25/26期合刊的文章《更进一步》(Vidare),第88-91页。
(18) 同上参见马拉美《全集》第368页。
(19) 同上参见马拉美《全集》第368页。
(20) 此处引文出自瑞典文版《日常事物》(Vardagens ting),译者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Katarina Frostenson),斯德哥尔摩1989年版第14页。
(21) 阿尔伯特 · 提巴德(Albert Thibaudet,1874-1936)是法国现代文学史家,此处提到的经典著作是《论马拉美的诗歌》(La Poésie de Stéphane Mallarmé)巴黎1912年版。有关《骰子一掷》的段落见1926年第4版第419页。
(22) 同上参见马拉美《全集》第387页。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