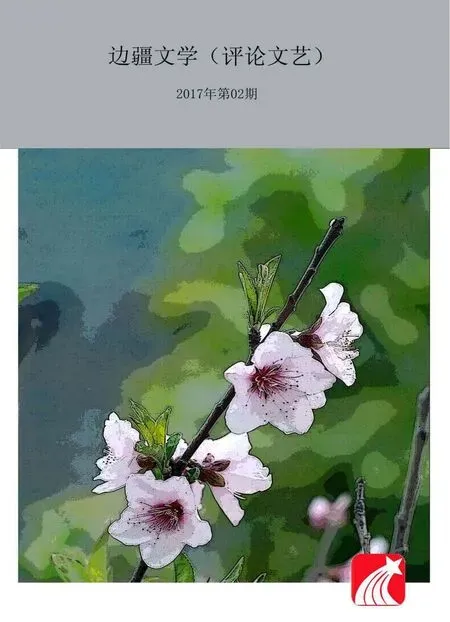论诗歌形式的表层结构
李 骞
理论前沿
论诗歌形式的表层结构
李 骞
·主持人语·
多年来诗歌创作都是云南文学创作中最富特色和最具优势的领域,但是,对于诗歌创作的研究和评论却不多,李骞的这篇“论诗歌形式的表层结构”一文,深刻阐述了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表层结构。作者认为:诗歌的表层结构是通过作品的审美意象来完成的,意象作为诗歌的表层结构,是诗人的情感与客体物象相结合的一种有序化的物我形态的艺术式样,也是诗歌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象在诗歌文本中主要是通过外在的审美形式来完成,特别是通过语言来直抵诗歌内蕴的核心;诗歌的意象结构不是单个意象的随便拼凑,而是完整的诗意的审美组合。李骞关于诗歌的这些认知和观点对我们创作、阅读或欣赏诗歌有很大的启迪。(蔡雯)
诗歌的表层结构是通过作品的审美意象来完成的,尤其是诗歌文本中的复杂意象是诗人在作品中进行叙述的主要视点,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意象是构成诗歌表层结构的主要艺术形式。那么什么是意象呢?意象是诗人直接进行思考和感悟现实社会的一种方式,是诗人表情达意的一种特殊的手段,是一种具体化了的诗性感觉。一个优秀诗人对物象的表达,最重要的一点要深入到所表达事物的核心,把握事物的特性和事物的实质,将自己的感情与思想寄托于所反映的客观物体,达到明示或暗示作者思想感情的审美境界。意象是美感氛围的创造,是诗歌表层结构的特殊审美艺术形式。
一
意象在诗歌文本中的结构原则,主要是通过外在的审美形式来完成,特别是通过语言来直抵诗歌内蕴的核心。德国学者胡戈·弗里德里希认为:“诗歌创作的开端是构造一种‘音调’,它先于赋有意义的语言,而且贯注始终,是一种无形体的氛围。为了赋予其形体,作者要寻找语言中那些最接近这音调的声音材料。”这里所说的“音调的声音材料”和“无形体的氛围”就是一种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象征功能,而诗人要在诗歌中营造这样的审美形体,就必然要挖掘表达这种审美形体的语言材料,并通过意象的表达来强调诗歌的内在含义。意象所指向的方向,表面上看是生活中的现实物,但实际上是经过诗人情感过滤、提升后的审美图像,不仅会改变现实秩序,让现实生活中本已存在的物体变形,甚至于摧毁原有的物象意义,让物象在诗歌的词语中成为纯粹的美学理念,而诗歌所表达的精神本质在变形的意象的驱驶下,完整地得到表达。这种情形下,诗歌叙述的视点呈现出多样性的格局,诗人从生活观察者的位置进入审美的场域,作品的立场在诗人能动的审美观照下得到全方位的彰显。当然,在这种情形下,正如俄国学者鲍·安·乌斯宾斯基所说:“叙述者的位置在被研究的情况中是相对现实的,因为在此作者仿佛潜在地参与行动,他仿佛直接从行动地进行报导——因此,他的方位每次可以以不同程度的准确性在空间和时间的坐标上被固定下来。”诗人对原始生活物象的改造虽然是“潜在地参与”,甚至诗人的这种再创造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诗人有目的参与,使不同的意象在文本中交潜运用,这正是诗歌审美结构必不可少的审美过程。
意象不是诗歌表达对象的复制品,更不是客体的影子,而是通过诗人的主观理念对外部世界的再认识。现实生活的客体物象是复杂多变的,带给受众的信息多种多样,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原始物象时,内心世界的感触也是千变万变。因此,当诗人以物像作为参照系进诗歌创作时,必然要借助意象的结构功能对瞬息万变的生活进行认真的疏理,将生活中具有表达意义的材料进行创造性的归并整合,使原始的客体符号的意义发生质的变化,并通过语言的审美功能,让诗歌文本中的意象与生活中的实物产生距离,从而达到以意象带动情感的审美意义。当然,诗歌对原始物像的消解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要通过“物”的变形实现“意”的升华。但是诗人在剔除和消解原始物象的意义时,肯定要通过语言的作用力,把自己的主观体验赋予表达对象以新的理念和意义,让诗歌中的意象实现超现实的飞跃。活跃于19世纪法国诗坛的明星波德莱尔,以一种奇特的艺术手法,通过理性思维的审视,运用变形的审美技巧,使原始意象在词语的通变中发生本质的变化,而变异了原材料在语言的表达中重新组成有审美质感的艺术形式,诗歌隐喻的力度得以自由发。比如他的《情侣之死》:
我们有充满清香的床,
像坟墓一样的长沙发,
板架上的奇花异卉
在美丽的天空下怒放。
两颗心发出最后的余光,
变成两个最大的火炬,
两个灵魂汇成一对明镜,
镜中反射出双重的光彩。
神秘的玫瑰、蓝色之夜,
我们感应着唯一的电光,
像充满离愁的长长抽泣;
而后,一个天使开门入房,
忠实而愉快地将熄灭的火
和灰暗的镜子重新复活
“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潜在互换,是波德莱尔诗歌艺术的显著特色。诗人为了展示人性和现实的丑陋,用一些非常有趣的物象来反证以丑审美的必然性。《情侣之死》中的图像都是很美的,但是这些美的图像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之相应的“丑”和谐共鸣,作品中的美与丑不再是对立的两种价值,而是现实生活的同异变体。诗歌中的物象“床”充满清香,沙发则用“坟墓”比喻;而自我与“情侣”的“两颗心发出最后的余光”竟然“变成两个最大的火炬”,最后“汇成一对明镜”,并从“镜中反射出双重的光彩”,而“唯一的电光”变幻成了“离愁的长长抽泣”。这些意象的组合,就是证明“情侣”的肉体虽然死了,但是她的灵魂却依然存在,并形成了一种非现实的物体,如天使般地复活。波德莱尔的诗歌总是用变异的意象群来表达诗人对社会的解构,而组成意象群的每一个单个意象都具有可感性和陌生化的美学效果。“两个灵魂汇成一对明镜”、“灰暗的镜子重新复活”,这一切都是来自感性的非现实元素,是诗人对超现实的一种个体幻想。波德莱尔的诗歌所表达是这样的现实:现实只存于诗歌幻想的语言之中。
波德莱尔的诗歌意象具有繁杂的完形意义,尽管他的诗歌有许多变异的梦幻性色彩,但是都是来自现实世界的感性元素,只不过诗人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并置、移位、变形、省略等艺术手法进行重新组合,将这些元素罗列成诗歌中的意象群,如此一来,生活中的物象得到审美强化的同时,也超越了现实生活的意义。单个意象是诗歌最小的独立单位,而每一个意象按一定的逻辑顺序被串联成一个整体时,诗歌结构的表层艺术形式就得到完整的体现。这就是波德莱尔诗歌结构的审美指向,也是现代诗歌表层结构的一般规律。
在诗歌作品中,单个的意象只有文字的原始意义,但是当它被纳入一个组织系统的审美结构中时,其原来的意义也许会丧失。从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看,意象结构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当诗歌中的意象群体出现时,各个独立的意象的原始意义已经丧失,其审美意义必须服从整体结构的控制,其功能价值必为整体结构的指向所左右,这种“完形”的诗才具有审美意义。事实上,在诗歌创作中,不仅意象之间互相牵制,即便是意象群,也难摆脱诗人情感结构的控制。诗人潜伏在诗中的隐性情感,使散乱的意象和有序的意象群,都服从一个审美的结构形态。这样,诗就能够以“完整的艺术体”与世界对话。诗歌的写作方式多种多样,但在意象的结构上却始终以意象的完整性来解释生活。
韦勒克·沃伦认为:“像格律一样,意象是诗歌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我们的观点,它是句法结构或者文体层面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意象是关于过去生活的感受记忆,它既是一种对生活的图像再现,更是一种理智与感情的综合体验。这就是说,诗歌作品中每一个零碎的意象是在诗人审美情感的作用下,才可以转化为诗歌文体层面的审美形态,因为诗歌是诗人感情升华的结果。在诗歌创作中,由于形象思维的作用,意境的创造必须达到情与境、意与象的高度统一,这样诗歌才会具有浓烈的韵味和深厚的艺术感染力。从诗歌艺术的表层结构看,意象通常是评判诗歌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一首诗,如果意象太苍白,太单调,就没有诗意。即便是诗中具有正确的思想、进步的世界观、高尚的人生观、有立体感的语言、有鲜明的节奏,但只要缺乏高境界的审美意象,就不可能有深厚的艺术力量。没有意象形态的诗,读者就很难深入其境,在感情上当然不会产生共鸣,读来味同嚼蜡。意象是诗人的真感情与外在的真景物组合而成的统一体,诗人通过构思,把外在的景物形象与内在的深刻感受合二为一,创造出一个新的艺术世界来。中国古人创作诗歌时,讲究虚实结合,即所谓“实以形见,虚以思进。”用在诗歌的意象创造上,“实”就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景物;“虚”则是指诗人的主观审美感情。外在景物靠诗人的感情获得生命,诗的审美感情靠景物得以表现,二者互为表里。正如王夫之所云:“情景各为二,而实不可分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情中景,景中情。”也就是说,诗人在“选境”时,务必使“情”与“景”二者达到高度辩证统一,才会达到“情中景,景中情”的审美效果。
二
意象作为诗歌的表层结构,是诗人的情感与客体物象相结合的一种有序化的物我形态的艺术式样,是诗歌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写诗很讲究物象与情感的内在联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这里的“神”是指诗人创作时的一种美学理想精神,这样的“神”是要靠物象来贯通,而客观物象用它的外形面貌来打动诗人,诗人产生的审美情感又反过来顺应物象的变化。由此可见,意象在诗歌创作中是独特的艺术风格的表现,而意象的产生则是遵循“神用象通”的结果。明代文论家胡震亨甚至在《唐音癸签》中非常肯定地说道:“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意思是说,古人诗歌之所以写得出色,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对意象的精益求精。如此说来,意象是诗歌妙笔生花的关键,是诗歌有没有艺术生命力的原因所在。外国诗人也主张要用语言文字把诗歌中的意象和盘托出,庞德是英美意象派诗人的鼻祖,他认为诗歌创作不能用无助于表现内容的词语,而是要用“纯意象和全意象”才能完整地表达诗歌的审美内涵。只有在诗歌中使用“纯意象”和“全意象”,诗歌作品才会产生审美结构的艺术张力。意象对诗歌创作如此重要,但仅仅强调纯意象还不够,纯意象在诗歌中作为具有审美欣赏价值的最基本单位,只有当它们组合在一起,成为“全意象”、成为一个完整的意象群或意象复合体时,才会产生整体的美感效应。一个单个的纯意象,单独看来可能是美的,但是如不纳入一个有机统一的意象结构中,就谈不上审美价值。意象群的整体效果,表面上看有许多互不关联的纯意象存在于句法之中,但诗歌的完形结构中却潜伏着一条情绪线,并由它把所有的意象串联起来,形成浑然一体的意象复合体。意象的审美结构对诗歌的美学意义是很重要的,作为诗歌美学的一个基本技巧,古今中外的诗人都自觉地穷尽才华而为之奋斗,为之笔耕不止。尽管对“意象”常常有“智者见智”的不同诠释,但“意象”是表达思想、情感升华的结构艺术方式,则是所有诗人创作时所遵循的艺术准则。
从创作实践看,一个审美风格成熟的诗人,在意象的运用上不仅纯熟,而且他的诗歌会体现出与众不同而又别开生面的艺术审美形态。其诗歌的文本意象看似深沉繁复,其实是用平淡的语言去追求一种深远的艺术效果,诗人的情感与所反映的客观物象共同支撑起一片美丽的诗歌时空。这样的诗,不迷恋于意象的绮丽神秘和隐晦生涩,而是用一种明朗的诗歌语体,运用视觉与听觉的通感,完成深层次的意象群,使诗的外表气象显得通达恢宏。比如舒婷的《岛的梦》:
我在我的纬度上
却做着候鸟的梦
梦见白雪
梦见结冰的路面
朱红的宫墙后
一口沉闷的大钟
撕裂着纹丝不动的黄昏
呵,我梦见
雨后的樱桃沟
张开圆圆的舞裙
我梦见
小松树聚集来发言
风沙里有泉水一样的歌声
于是。在霜扑扑睫毛下
闪射着动人的热带阳光
于是,在冻僵的手心
血,传递着最可靠的春风而路灯所祝福的
每一个路口
那吻别的嘴唇上
所一再默许的
已不仅是爱情
我在海潮与绿荫之间
做着与风雪搏斗的梦
这首诗带有浓重的情感色彩,诗中既有诗人的独特体验,又有对生活的重新发现,意象的推移往往随着所反映的物象的不断变化而变化。无论是“梦见白雪”、“梦见结冰的路面”、“梦见雨后的樱桃沟”,还是“梦见小松树聚集来发言”,这些客体的意象都在“我”的“梦”中发生,作品中的意象本身超越了比喻和象征,实现了自我与客体物象的融合,表现出诗人对于“岛的梦想”这一总体意象的感悟和再认识。《岛的梦》的意象不仅语言新鲜,而且是诗人深沉思考的审美结晶。就诗歌的审美结构而言,现代诗的意象提供给读者的不是常识,也不完全是画面、形象,更多的是诗人自己的思考,诗人美学观念的探索,诗人洞彻生活的直觉。平庸的意象,只会使诗的艺术生命丧失。诗人只有打开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大门,并与客观物体发生深层次的感应,诗的意象才会有密度,诗的艺术生命才会长久。只有来自于诗人的情感思考,诗歌中的意象才可能是纯粹的意象。《岛的梦》所写的“岛”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实物,只是诗人梦中的想象。“梦”作为一种意识,则是诗人歌颂在艰苦环境中与风雪搏斗的韧性精神。这首诗是借“岛的梦”对平凡人的赞美,诗中没有哲学的说教,也没有训人的口号,而是通过“我”对梦中物象的挖掘合并,形成诗歌审美外形的完美结构。《岛的梦》不但读来感人肺腑,动人心魂,而且“岛”的原型已经物化为诗人的思想情感,并成为诗歌圆满的外观艺术形式。
现实生活中的物象转换为诗歌艺术的审美结构需要一个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状物移情,即诗人将原有的主观感情,有意识的移植到外景之上,使客观物体染上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当然,状物的关键是触景,也就是古人说的“感于物”,正如陆机在《文赋》中所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这是指构造意象时的触景生情,诗人有感于四季的变幻,万物盛衰而引发灵感。于是,看到秋天的落叶就悲伤,看到春天的柳条便高兴。触景生情是创造意境的一种特殊方法,在生活中,当诗人遇到特殊的景物和场面时,因受到感染而激起爱憎,并把这种爱憎提炼、升华,溶入眼前之景物,熔铸成诗的“意境”。这种从境入手,状物写景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感情融洽进客体对象之中,在意象的描绘过程中,面对凋零的景物,诗人的心情有“悲落叶于劲秋”的感受,而面对春天的繁花似锦,则有“喜柔条于芳春”的情怀。这说明意象的产生就是文以情生,情因物感的结果。当诗人面对某一客体物象,内心深处必然会有一种情感流露,于是便产生创作的欲望,再通过诗歌的想象来表达内在的情感,于是,诗歌中或隐或显的审美结构便得完整表达。如拜伦的《在马耳他,题纪念册》:
正如一块冰冷的墓石
死者的名字使过客惊心,
当你翻到这一页,我名字
会吸引你沉思的眼睛。
也许有一天,披览这名册
你会把我的名字默读;
请怀念我吧,像怀念死者,
相信我的心就葬在此处。
这是一个由内而外的感情推移过程,也就是通常说的“移情于境”,当诗人面对“纪念册”时,立刻感觉如“一块冰冷的墓石”,那些被纪念的死者使“过客惊心”,于是诗人联想到自己如果有一天离开人世,后人来“披览这名册”时,会不会把自己的“名字默读”?“请怀念我吧,像怀念死者,/相信我的心就葬在此处。”这是由景而生的对人的生命存在价值的拷问,诗人非常明白,人的生存不仅是活在当下,更应该转化为永恒。“我的心就葬在此处”是这首诗的情感焦点,所表达的是死而复生,死而再生,从而进入永恒的人的生存内蕴,而这一切都是缘自“墓石”、“名字”“眼睛”“名册”这些物象启发的结果。
在诗歌写作中,要做到移情于景,必须有目的地选择最能表达主观感情的形象注入诗人自己的感情,求其似我。文思不是凭空想象而来,而是要通过现实生活中物象的触景生情,才能由想象构成意象。如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于风云而并驱矣。”一旦诗人的情与外在的“山”“海”等自然外物相联结,诗人的才情就与风云驰骋,一发而不可收。由于诗人是有意识的在生活中寻找一定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意象所达到的境地,往往是情胜于境,重点是表情达意,而不是对外在景物的描绘。很显然,《在马耳他,题纪念册》是作者生活中亲身经历的人生过程,也是诗人由景生情的证明。其意象与诗人的情感既虚又实,虚实相生,极富立体感,给人以鲜明的深刻印象。
三
诗歌的意象结构不是单个意象的随便拼凑,而是完整的诗意的审美组合。瑞士学者皮亚杰认为,结构有三个要素,即“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任何艺术作品都有其本身的内在规律,诗歌的意象结构也一样,总是有自己独立的组合规律和法则。诗歌的意象结构不仅有“整体性”的美感图形,而且相互间的意义还可以转换,这都是源于意象结构固有的自身调整性。前面说过,意象结构就是诗人情感结构有序化的物化形态,其组合方式复杂多样,但意象本身并不是自我封闭的客观物体,它虽然是诗歌形式的最小单元,却具有释放诗歌艺术能量的功能。因此,作为意象结构的完整形态,当然有其独特的审美组合方式。根据前人的论述,结合个人的阅读视野,我把意象结构的组合方式总括为:平行的意象组合结构、两相对照的组合法则、放射式的意象组合结构三种。当然,意象审美结构的形态如五彩云霞一样多姿多彩,这三种方式也不过是它的一般性构成规律而已。
意象的平行组合结构是诗歌艺术中最常见的一种组合方式。
所谓“平行意象组合结构”是指诗歌的意象采用平行的并立推进,这种结构方式的优点是叙述性强,对诗人的情感宣泄能起到强化的作用。莱辛在《拉奥孔》中就画与诗的艺术区别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绘画用空间中的形体和颜色而诗却用在时间中发出的声音。”在莱辛看来,画是“空间艺术”,诗是“时间艺术”,这就说明诗歌必须按照时间的顺序展示诗人的情感,表现诗人的精神本质。作为表现诗人内心情绪的诗歌,其时空观十分重要,尽管有时诗人的情感是跳跃式的,但是作为一种平行的意象的叙述,则是诗歌艺术的基本特性。意象平行组合的优点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象在诗歌创作中互为补充,其意义交替释放,可以起到强化诗歌艺术力量的作用。比如顾城的《有时》:
有时祖国只是一个
巨大的鸟巢
松疏的北方枝条
把我环绕
使我看见太阳
把爱装满我的篮子使我喜爱阳光的羽毛
我们在掌心睡着
像小鸟那样
相互做梦
四下是蓝空气
秋天
黄叶飘飘
这是一首用心灵感悟祖国的诗,诗人的心灵顺着几组意象的平行推进,完成了对主要意象“祖国”多意义性的注释。第一段中的“鸟巢”“枝条”“太阳”、“篮子”“阳光的羽毛”都是对主题意象“祖国”的一种外形描述。因为诗人预设了“有时祖国只是一个/巨大的鸟巢”的信息,所以这几组平行的意象组织成一个有序的结构,交替性地推出诗人内心深处的“祖国”景色。诗歌意境的审美意义清楚明白,韵味极浓。作品的第二段通过意象结构来表诉诗人的情感,“掌心”“小鸟”“蓝空气”“秋天”“黄叶”这些容易辨认的物象,都是围绕“鸟巢”的形状展开叙写。诗人把每一个单个的人比喻为“小鸟”,而祖国如同“鸟巢”,每一个人都在“鸟巢”这个空间中“相互做梦”,空间外则是蓝色的空气和秋天的黄叶。《有时》这首诗歌中的物象虽在时间上没有承续关系,但是可以看出来,几组平行交替推进的意象,都是沿着诗人自我情绪的内在逻辑来立意造像的。而且外在物像在“鸟巢”的空间上下左右联系,凭借诗人的情绪流动来构筑完美的意象,这样的描写,使整首诗的意象结构更具有立体感。
意象审美结构的两相对照组合法则。
“两相对照”就是把两个意义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意象组合在一起,运用矛盾的物象而形成新的意象组合,并构成一种审美反差的艺术效果。当然,这种对比意象的组合,不仅仅是两个矛盾物的组合,更不是诗人深层情感的对立,而是两种互相对立的物象相互撞击之后产生新的意象。表面上看,诗歌中意象的对立是尖锐的、无法统一的,但在诗人审美情感的控制下,矛盾的双方又构成一个诗歌结构的有机统一体。对比的强度越明显,越能够唤起读者的情绪,诗歌的艺术形式更具有强烈的审美效果。
自然界中的原始物象之所以有矛盾对立的现象出现,是因为大自然时刻处于千变万化的缘故。这种变化造就了客观事物的变幻莫测,甚至会改变意象的原初意义。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认为:“宇宙中事事物物常在变动生展中,无绝对相同的情趣,亦无绝对相同的景象。”事物因为没有相同,就会有对立,有对立,才会有统一,意象审美结构的两相对照,就是从矛盾的统一中完成了诗歌审美结构的建构。事实上,无论是外部万物,还是人情世态,都存在着一种统一对立的关系,一方面是尖锐的冲突,另一方面又是和谐的统一。就诗歌审美精神层面而言,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互为因果、互为补充的。其对立的两个物体总是有一定的合理秩序,这个秩序就是形成诗歌意象对比的依据。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只要努力找到事物对立的内在依据,就能按照意象的内在逻辑地将若干对立的意象有意识地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里尔克早年创作的诗歌《黄昏》就是用对立的意象来表达诗歌内蕴的一个经典案例:
冲着最后房屋的背影
红太阳寂寞地入睡,
白昼的寻欢作乐已经消退
于严肃的结尾第八音。
散漫的灯火互捉迷藏
于屋顶边缘已经很迟,
这时黑夜早把钻石
播向了蓝色的远方。
这首诗用了几组意义殊异的意象组合方式,不但把“黄昏”的完整图像完美地凸显给读者,而且准确地传递了诗人的情感理念。第一段中寂寞的“红太阳”与寻欢作乐的“白昼”,虽然表示的是同一种物象,但颜色却是相反的。第二段中的“灯火”“黑夜”“蓝色”等诸多内含不同的意象,在同一个生活现场出现,从而造成了很强的美学反差效果。特别是最后一句“这时黑夜早把钻石/播向了蓝色的远方”,既是诗人审美理想的高度凝聚,也是诗人在黑暗中呼唤“蓝色远方”的情感表达。《黄昏》中的意象是相反的,但这些意象的审美结构都有着自己合理的、有序的规律法则。
放射式的意象组合结构是一种审美意象的综合体。
随着后工业文明的到来,当代人的意识越趋变幻多样。现代诗歌是表现当代人复杂意识的特殊情感的艺术形式,必然要对当代人的内心世界,当代人的生活现实作全方位的把握。现代诗歌作为情感的载体,它所传达出的信息必然是高密度的,网络式的,否则就无法完成当代人的情感传播。就诗的意象结构而言,放射式的意象组合,更能够体现当代人的复杂情感。
所谓放射式,是指在诗歌的意象结构中,由一个“母体意象”裂变出若干“子意象”,最后构成一个庞大的“母子意象结构”。诗歌的表面意象是“网络”式的,但传播出来的审美信息密度较大,给人以“天地有大美”的感觉。而且,这种网络式的意象中,“母意象”常常是诗人的主体情感传播的载体。诗人在诗歌里往往与外部事物达成精神上的交流,到达“神与物游”的奇特境界。诗人用主观情感去涵盖客观世界,诗人不仅仅在描写客观物象,客观物象也在“描写”诗人。“放射式”的意象构造,意象都是“生”出来的,换言之,就是诗人从语言出发,找到了一个包容性很大的“母”意象。在用语言描述这个意象的过程中,诗人的感悟发生突变,于是一连串相同、相近、相似的“子意象”刹那间从诗人的体验中接踵而至。郑敏的《世纪的等待》就是以一种意象结构的“放射”式描写,向读者表达一种世纪末的等待情绪。诗人这样写道:
冬天的等待
冬天的灰云翻滚
等待着雪
稀疏的柳条枯脆
寂寞挂在枝梢的摆动里
等待使弱小者生存
等待使专横者颤抖
翻滚中灰云终于洒下
鹅毛白雪扬扬洒洒
转眼间无声的白野
将一切浮躁变成遗忘
暂时的遗忘是一只飞鸟
传送着世纪临终的等待
“冬天”是这首诗的“母体”意象。由“冬天”又裂变出一系列的意象:“灰云”“稀疏的柳条”“枝梢”“弱小者”“专横者”“鹅毛白雪”“白野”“一只飞鸟”……每一个“子意象”虽然有相似性,但并没有紧密的联系意义,然而在主导意象“冬天”的控制之下构成一个整体,而且诸多意象在互相矛盾和互相冲撞中,推出一个新的情感:“世纪临终的等待”。就诗歌意象的审美结构而言,《世纪的等待》的意象结构是母体意象“冬天”与诸多子意象互相包容、互相渗透的结果,因而,这首诗体现了一种深奥的“世纪等待”的人生哲学意蕴。
诗歌艺术的意象结构应该“是一种在瞬息间形成的感情与理智的综合体。”在诗歌的“放射式”意象结构中,“母体意象”就是诗人的理智对外在物象综合的结果,而“子”意象则是诗人情感的流露。当代社会,人们的感情已经由单纯走向复杂,作为情感结构物化的意象结构,应该尽量摆脱平面式和静态式,追求多线索、立体式和放射式。在多种意象结构艺术中,“放射式”的意象结构艺术,不失为一种具有广阔前景的审美方式。
著名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认为:“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能成立。”这就是说,诗歌虽然是以主观抒情为主,但是离开意象情趣就不能充分表达出来,只有情趣与意象相互补充,实现情与景的融会贯通,诗歌的表层结构才呈现出完整的审美效果。
【注释】
[1] [德]胡戈·弗里德里希著,李双志译,《现代诗歌的结构》第37页,译林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2] [俄]鲍·安·乌斯宾斯基著,《结构诗学》第84页,彭甄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
[3] [法]波德莱尔著,《波德莱尔诗选》第319-320页,苏凤哲译,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
[4]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文学理论》第246页,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5] 王夫之著,《薑斋诗话》,见《清诗话本》第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6] 周振甫著,《〈文心雕龙〉今译》第253页、第250页,中华书局1986年12月出版。
[7] 胡震亨著,《唐音癸签》第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
[8] [美]庞德,《回顾》,转引自《诗探索》1981年第4期。
[9] 舒婷著,《舒婷的诗》第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1月出版。
[10] 郭绍虞主编,《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1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11] [英]拜伦著,《拜伦诗选》第20页,杨德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12] [瑞士]皮亚杰著,《结构主义》第2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9月出版。
[13] [德]莱辛著,《拉奥孔》第84页,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8月出版。
[14] 顾城著,《顾城的诗》第1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15] 朱光潜著,《诗论》第56页,生活·读书·三联书店1484年9月出版。
[16] 郑敏著,《郑敏诗集》第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17] 郑敏著,《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第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
[18] 转引自朱光潜《诗论》第56页,生活·读书·三联书店。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程 健
——“意象”阐释的几组重要范畴的语义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