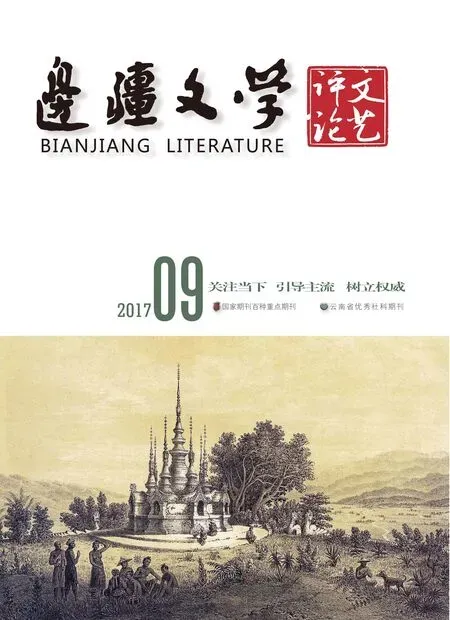另类的批评文本
——评冉隆中的《底层文学真相报告》
黄桂元
另类的批评文本——评冉隆中的《底层文学真相报告》
黄桂元
《底层文学真相报告》是标示冉隆中作为国内文风迥异、个性鲜明的批评家的奠基之作。与本书相关的诸多因素中,我首先想到的是:性格。有些逸出常轨的事,若一般人去做,可能会引来“惊世骇俗”,对于冉隆中却稀松平常,天经地义,似乎没有不做的道理。他做起来,也未必顺风顺水,未必功德圆满,更未必皆大欢喜,但是一旦他去做,就会风雨兼程,义无返顾,即使自讨苦吃,无人喝彩,也要一条道走到黑。这时候的他,已无丝毫“精明”可言,完全不像一个有过丰富生意场经验的前商人,而是会浑然忘记诸如成本核算、投入产出比之类的商场法则,顾自我行我素,如入无人之境。
冉隆中注定不是一位肯于消停、规行矩步的批评家。久居文坛,人们很容易对一些表面堆积的现象习焉不察,熟视无睹,认为存在的自然就是合理的,无须大惊小怪。冉隆中却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偏要扒开那些表面堆积,执拗地打探其前因后果,分析其来龙去脉,然后亮相发声,奔走呼号,以期引起关注。对此的解释,也许只能借助一句被人们用得滥俗了的哲语:性格即命运。无论幸或不幸,此类人物的命运,都可能带来风险,招致争议。
《底层文学真相报告》,见证了冉隆中充满质疑精神与挑战意识的一次批评实践。有关“底层文学”中的“底层”概念如何界定,是着眼于某一弱势群体低微无助的社会地位(比如农民工),还是就某一类人群生存境遇的最低贫困度而言(比如下岗无业),抑或特指过往政治灾难中受害者群体的苦难命运(比如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中那些流放右派、饥荒遗孤等的惨烈遭遇),至今众说纷纭。而“真相调查”中的“底层”对象,不是“底层文学”作品,却是指属于文学创作主体或作家的“文学生态”范畴,此类内容尚无人问津,这决定了接通本书主脉的是田野地气,而不是书斋玄思。也正因为如此,作者为之付出更多的是奔波和汗水,然后才是思考和书写。我想象,他的批评选择最初带有某种随机性,不经意性,或许还有一些走马观花、投石问路的意思,只是随着“真相调查”的不断深入,他的批评目光才开始聚焦,由愕然、迷惘,而变得凝重、深邃起来。这时候的他,很像一个无意闯入文学森林的机警猎人,不断嗅其异常,察其怪相,辨其真伪,然后才张网一步步实施自己的“捕猎”计划。这个捕猎过程困难重重,他也曾自我质疑,“调查写作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被调查者距离的远近以及配合的程度,自费调查所必须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更大的困难还是来自调查写作设计本身——文学批评的写作可以借助田野调查手段来实现吗?调查意味着批评者与被调查者的近距离接触,而被调查者又身处底层,那么,这样的调查写作还能够保持必要的理性和高度吗?其实我自己知道,无论是调查者还是被调查者,都不可以依凭任何道德制高点在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竞技场上取胜。相反,由于底层写作者的艰难、弱势,他们天然地会比较容易唤起同情、感动和赞美,而让人忽略了对其所处幽暗位置的烛照,以及对其文学坚持的真实动机、作用、意义感的深入探询”。(《底层文学的幽暗与遮蔽》)很显然,他并非在为个人利益而患得患失,着眼点还是关乎文学批评本身,因为他从事的毕竟不是扶贫工作,更不是一般的慈善事业,而是另类的批评文本。
既然如此清醒,他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要从他的批评理念说起。某种意义说,他是一位有着自觉意识的“在场”主义者。“在场”,原本是用来定义一种哲学范畴的存在方式,移植过来,意在形容他特有的写作状态。对于批评家,所谓“在场”,并不意味着他们只能走“田野”这条路,而是希望他们视点下沉,身段放低,亲临文学现场,不要仅凭道听途说就来指点迷津,不要躲在圈圈里坐而论道自娱自乐。“在场”,尽可能地拥有现场经验,问题意识,这样去做,并不会限制他们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反而有助于其拓展视野,激活感受。
稍微知情者都会清楚,如今做一位所谓的批评家完全可以不必那么辛苦。以常见的新书研讨活动为例,一些大牌名家穿梭于天上地下,山南海北,赶场赴会,行色匆匆,既然分身乏术,便只有蜻蜓点水。好在若干研讨活动,也多为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自然便有捷径可寻。久而久之,批评家们练就绝技,应对自如,临阵磨枪,上场即灵,更有甚者,仅仅利用赴会途中和落座之后的时间争分夺秒,翻一翻书中的内容提要、作者介绍、作品序言、他人评语,以及开头、结尾,就可以口若悬河,举一反三。其不竭的工作激情与言说动力,很难归结于某种敬业精神,更与诸如批评家的良知、道义与责任毫无干系,实在是市场经济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冉隆中自然也是一些研讨活动场面的常客,却不愿丧失批评家的职业自律和人格操守。令人惊讶的是,为了走入纳西族“文学奇人”王丕震的浩瀚世界,他居然花费长达三个多月时间,细读了作者一百多部小说中的十几部,还翻看了其中的数十部,“我看着书房里单本堆积高约两米的《王丕震全集》,在百余天里被我无数次翻了个七零八落,又无数次将它重新整理堆砌成山,我觉得自己更像是在做一个庄严的游戏。”(《一个奇人的写作史》)这种“庄严的游戏”,不光得不偿失,似乎还有些可笑,已经没有批评家愿意玩了,冉隆中却“乐此不疲”,只能算是特例。
而他对底层文学“真相调查”之身体力行,之情有独钟,更是令一些同行匪夷所思。事实上,他没有义务搭上人力物力财力,离开都市,顶风冒雨,远赴数百里之外的偏远小镇,穷乡僻壤,实地考察那些近乎于“苟延残喘”的文学生态,且不遗余力地为之奔走呼号,奋笔疾书。君不见,当今中国文学与市场经济接轨之后,一些批评家的日子随之水涨船高,他们忙着四处秀场,图得是名利双收。置身文学现场,关注边缘幽暗,孜孜研读作家文本的活法,显然已经落伍。聪明如冉隆中者,又何尝不清楚何为“事半功倍”,何为“四两拨千斤”?他其实并没有逆时代而动的企图,而不过是不肯在批评队伍里滥竽充数,“在某些评论家放弃文本细读,忙于飞行集会的当下,能够坚持真实阅读之后的发言和写作,就成为了这个时代评论家堪称可贵的品质。我对诚实的批评家心生敬意的同时,却主动选择了另外的批评路径——坚持文学调查,获取一手资料,再做阅读分析,然后开始写作。这样的方式显然是不合时宜并且困难重重的:慢而且笨,成本高而收效微。有时候,为了跟一个被调查者现场对话,我要数度往返于几百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有跟被调查者同在不通公路也没有信息的山里,一待就是数天的经历。我坚持自主选择调查对象,而且被调查者大多是文坛底层、民间、基本不出名的写作者。这就意味着我必须为自己的调查买单。这样做的好处也显而易见——我可以保持自己调查写作相对的独立性,而不必顾及包括被调查者在内的任何需求。这样的独立写作,有时候就会特别的吃力不讨好——不仅是意识形态组织部门,而且也包括一些被调查的作家或组织”。(《底层文学的幽暗与遮蔽》)这样的出发点,赋予了他的“真相调查”以一般的批评言说所难以企及的洞察性与穿透力,他的批评实践便不能不与“田野”情结渊源深远,在这条路上“一意孤行”,也几乎成了他的一种宿命。
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成了本书每篇文章的第一位读者。作者先是在2008年第一期《文学自由谈》发表了《底层作家,你们还好吗》,接着从第四期开始,每个双月的下旬,我的邮箱都能准时收到他的文稿,那里透露了他的调查踪迹、活动半径、思考重心和写作状态。阅读这些结晶着他的汗水、心血与忧思的文字,我时有恍惚之感:这还是那位相处了整整两个月的鲁院同窗吗?
结识冉隆中,缘于2005年鲁迅文学院那一届“中青年文学理论评论家高研班”,从事业角度说,这无论对于我,还是他,都算得上一个收获——我所供职的《文学自由谈》增添了一位实力型作者,而他则站在了一个可以发挥其批评才情与个性的平台。两个月的同窗生涯,为我们这些外省学员提供了朝夕相处的机会,大家一起食宿,听课,讨论,参观,散步,聊天,购书,喝酒,唱歌,打乒乓球,活动之频繁,内容之多彩,剧情之跌宕,完全称得上是大学校园生活的青春压缩版,就连争执与吵架都那么书生意气,令人难忘。我和冉隆中的交往,比别人还多了刚刚被划为“智运会”项目的围棋对决,课余时间,我们俩常常躲进宿舍,公牛抵角般埋首黑白世界,直杀得暗无天日。他从遥远的昆明来到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其言谈举止竟透着一股子无视天子、鸟瞰天下的心高气盛,无论是球台争锋还是棋盘搏弈,他都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获胜欲望。这之前他曾在商海扑腾十年,收益不得而知,回头是岸,重操旧业,想必还是他的文人本色起了决定作用。他谈风甚健(有时不免出语尖刻),常发奇谈怪论(有时也仅仅属于牢骚之类),不习惯附众(有时略显孤立),不按常规出牌(有时会表现为一相情愿的天真)。什么事情,他认定去干,主观上并不一定就想出人头地,结果却往往如此。“高研班”接近尾声,他拿来了一篇“鲁院听课记”给我看,洋洋洒洒近两万言,完全一副自信满满的质检员口吻,好象唯有他才是带着脑子来听课的。文章发表后的事情就不说了,反正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这家伙便以一位异类批评家的姿态,开始引起界内关注了。
记得曾有一度,他的写作似乎有些沉寂。不久便得知,他正在“扮演”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常从事的“田野”工作者那类角色,而出没的地方,当然不会是星级宾馆,不是度假村,不是旅游名胜,而是与都市的繁华盛景形成鲜明反差的偏远荒凉地区。他的风尘仆仆与云南特定的文学生态有关,只是我从未听说过文学批评与“田野考察”有何搭界。云南是少数民族分布最多也最分散的省份,他的“真相调查”也是有针对性的。作者熟悉包括普飞在内的峨山几代本土彝族作家现状,了解他们一路走来的种种不为人知的千辛万苦。关于莫凯·奥依蒙(汉族名字李士学),他写道:“在峨山第二代本土彝族作家中,他至今仍是一个真正的农民写作者。在他的作家头衔之外,更重要的身份是:峨山县岔河乡进宝村的村民小组长。这个身份带给他每月50元的补贴和无尽的烦琐事务。真正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是他10来亩承包田和200多亩核桃林。在他打理完这些事务之后,才有一点点属于他的写作时间。他是目前我看到的最艰难的底层写作者之一。但是他也是真正有自己的文学理想的一个写作者。他的作品,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农民身份和写作条件的艰难而受到重视、同情或者获得好评——事实上,他确实写出了让人值得注意的许多小说。”(《他们该怎样走下去?》)于是我们了解到,在当代中国,不同地域、不同作家的“文学生态”,居然可以有天壤之隔,云泥之别。我们还知道,如果我们不是居高临下地俯视文学版图,不把作家的级别分成三六九等,还可以发现,那些远离庙堂的文学弱势族群,对写作的追求毫无功利性可言,文学在他们心目中的那种圣洁与崇高,是无与伦比、无可替代的。
感谢作者让我们知道还有这样一份文学期刊,“这份名叫《红地角》的刊物,它有时是报,对开四版;有时是刊,厚厚一册。细细一看,这份由云南红河州蒙自县红地角文学社主办的文学内刊,居然已经出版近百期。而编辑这份文学内刊的红地角文学社,则连续不间断地开展活动并存在了24年。”记得那天读到这里,我忽然鬼使神差地想,那些真正的底层作家对于批评家冉隆中的远道而来,有没有久旱逢甘霖那般激动,有没有像迎来救世主那样兴奋?激动和兴奋过后,却并没有得到所期盼的雪中送炭,会不会陷入巨大的失望深渊?我们无法断言,由于热爱文学并投身写作,而加剧了他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每况日下,但文学写作为他们清贫日子带来任何改善,却是事实。什么东西鼓舞他们,至今仍在支撑着他们在文学写作道路上匍匐前行,世俗的眼光难以理解。他们是一些不计功利的朝圣者,文学有如荒漠甘泉,点点滴滴滋润着他们的心灵沃土,也赐予他们的生命绿意。对于他们而言,世间没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滋润更值得珍爱与感恩了。
种种身临其境的目睹和交往,引起了冉隆中越来越深切的忧虑和关怀。他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是“真相”的披露者,描述者,还为他们的代言,责无旁贷地传达他们的诉求。他从哈尼族诗人哥布的身上,发现了“比天分更难能可贵的,却是他在母族文化选择上的自觉”。哥布已经具备了写作汉语诗的能力,但是强大的汉语诗写作队伍中,并不缺少一个哈尼族青年,哥布的选择是,“他要退出原本好不容易进入了的汉诗写作竞技场,要改变自己符号化的族群身份,进而实现全面和真正意义的母族回归——从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开始,回到真正的起点之上,去发声,表达,对话”(《梯田上的写作者》)。这意味着,哥布的写作正谋求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从成功汉语回到寂寞的母语。冉隆中担忧的是,回到母语写作的哥布,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一系列难题:不要说文学市场了,他的哈尼族母语诗歌,在哪里发表?读者又在哪里?作为读者,我在为哈尼族诗人哥布的文化抱负而感慨的同时,也被批评家冉隆中的担忧所打动,当今文坛,还有哪一位批评家会操这种没用的心呢?
至此可以理解了,冉隆中的行走身影,何以一直固执地晃动在曲曲弯弯的偏远路途,并且沿着纵深的角落不断延伸。他厌倦枯坐书斋,凌空蹈虚。他瞩望山河,悲天悯人。那种与复杂的文学生态仅仅保持隔空喊话、纸上谈兵的关系,从来就不是他的批评选择。他对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有着本能的敏感与执守,他的观照视野,没有放过庙堂与主流文学之外的一切边缘地带。举凡体制外写作,退休者写作(许多作家担任作协要职之时声名显赫,呼风唤雨,一旦退休即沦为“弱势”一族,也算是中国文坛的小小奇观),小地方写作者,非汉语写作者,少数民族写作者,网络写作者,以及民间奇人写作者,危险写作者,“殉身”写作者等等,他的目光穿透了那些被遮蔽的真相,那里的幽暗与苍凉使人震惊,也令人唏嘘,通过文字表现出的,却是一种付诸行动的爆发力与相伴文学的持久力。遍观当下文坛,具有如此平民心态、忧患意识、言说勇气、职业精神的批评家,不能说寥若晨星,比例极小却是有目共睹。
倘若以正统“批评文本”的标准衡量,这些文稿似乎不够“纯粹”,不要说缺少新概念的堆砌、洋术语的轰炸,就连“学院派”们极为看重的引经据典都很少见,这表明本书要与那种大而化之、大而话之的宏大话语体系保持距离,与各类哗众取宠、生搬硬套的“后”学鼓噪敬而远之,与无性繁殖、无关痛痒的“八股”模式划清界限。据说,出版社就曾一度为书的归类颇费斟酌,认为不好归类,恰恰反证了其难能可贵的独创性。从写作技术操作层面看,尽管有些篇章略嫌粗疏,带有“急就”痕迹,但整体看来,这部“文稿”筋骨坚实,血肉饱满,融田野考察、数据资料、批评言说、散文句式、诗意描述、作品评价、艺术赏析等诸多元素于一炉,集思辨性、研讨性、写实性、传记性、史料性之大成,这一切浑然交织,互为印证,凸显了全书的综合价值,也赋予其独特与厚重。不消说,本书呈现的是一种“冉氏”文体,究竟其成色如何,还是要靠读者自行鉴别。
责任编辑:臧子逸
(作者系天津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