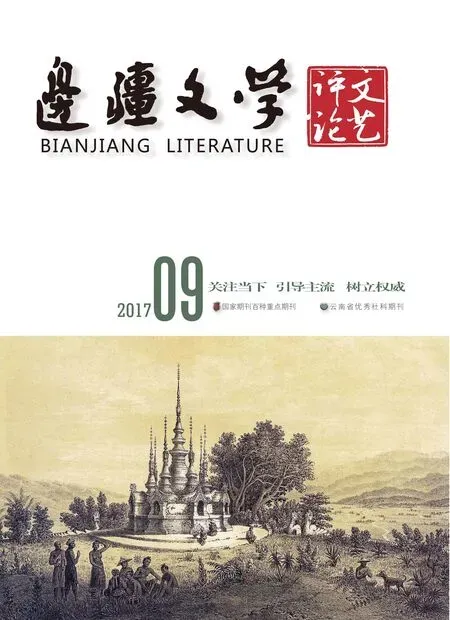大雅之梦透亮中西文化美感
——柯军中英版《邯郸梦》赏析
邓宝君
艺苑评谭
大雅之梦透亮中西文化美感——柯军中英版《邯郸梦》赏析
邓宝君
“认识”柯军,是通过著名作家莲子的新书《传奇》。莲子笔下“动静相生、铁骨柔情”的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令我有两点格外心生感动:一是视戏比天大的柯军,靠吃药、打封闭针上场演出,让人触悟到他舞境之外的猎猎奔程;二是作为中国最大领军式演艺集团之一——江苏省演艺集团总经理兼艺术总监的柯军,当看到学生的作品竟第一时间站出来喝彩,还亲自在新媒体上为学生做宣传,让人沐浴到他薪火相续的名师光辉。
再关注柯军,是他凭借筑梦七年的“汤莎会”走进中央电视台《大国外交》节目之际,我作为作家莲子于品牌期刊《家庭》刊发的名篇《素颜的魅力》一文责任编辑,再次与万千读者一同透过文学亲近柯军的昆曲表演艺术,两位名家碰撞出的无上火花,让我试着仰望这位在“最传统”与“最先锋”间葳蕤绚烂的昆曲传承人。渐渐发现,柯军昆曲世界的开阔和深邃,来源于他对传承与发展昆曲理解的开阔和深邃,来自于他作为“昆曲之子”潜扎在大地中的深情根须。由此,也便有了他策划并担纲主演的中英版《邯郸梦》,使得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两位中西方戏剧巨擘在400年后“相会”——此次“相会”,是世界戏剧舞台首创“汤莎会”,体贴着绵厚耐久的现代戏剧人自然敬仰之心,更透亮着中西方相敬相融的文化美感。
一个深有意味的戏剧样式
坦率地说,阅读柯军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难度在于习惯妥协和随顺的我们与一颗炽热的、高远的心灵对话的难度。试想有多少人,如果在自己的事业领域已经取得他人无法企及的成就后,还会打破辉煌光亮的藩篱,揉碎自己投入这份事业再创造行程?柯军的“最先锋”昆曲,曾遭遇种种不解,他因创作上的前瞻意识让他的作品逾越出现时段包括文艺批评界的某些理解和逻辑框架,好在我们前进中的民族与时代有着太多的东西可以入戏入史,柯军用圆合的坚韧与润朗的年华从容唱啸舞袖,为中国昆曲史留下必为后世铭记的一笔。
中英版《邯郸梦》,不同于柯军的实验《夜奔》以“素颜”魅力倾心于世人,而是用“最传统”的昆曲挽起莎剧,以前所未有的承载量,让经典的中西方戏剧共舞生辉,自然也让昆曲创作带上了不易觉察的神圣性。这“最传统”的相携一舞何尝不是“最先锋”的心志和形貌?昆曲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完整独特表演美学体系的艺术形态,柯军在符合法度的创造中完成了由蛹化蝶,化人为己,化古为今。从他接受各种媒体的访谈,不难感受到,传统已如沉静的处子,一直生机无限且蓬勃强劲地生活在其艺术生命的现场,让他随时清醒地接续上昆曲创作的使命担当。“《邯郸梦》是汤显祖‘临川四梦’的最后一梦。学界通常认为,‘四梦’之中,《邯郸梦》因其深刻的批判性、现实性最为伟大。可以说,该剧对现实的批判、对生命的思考,与莎剧气质最为接近。”柯军表示。
果真,中英版《邯郸梦》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仅从创意来看,是以昆曲《邯郸梦》为主干,将莎翁作品中的著名片段与汤显祖原本进行拼贴、演绎。比如第一折中,卢生入梦时,莎翁作品《麦克白》中的女巫上场歌唱;第二折中,卢生成为大将军征战边关,莎翁作品《亨利五世》中的战争场面适时切入……这样丝毫不影响一出戏曲故事的完整逻辑,特别是两剧表演的原汁原味使得中英版《邯郸梦》呈现出交错的听觉,烘托出似有重影的艺术效果。
其实,内容与形式的有机融合,一直是文艺创作最具体也最艰难的创新原点。在中英版《邯郸梦》的最高潮部分,莎翁作品中的李尔王与八旬卢生挤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对比着子女、身家、人生。雷鸣声中,仿佛梦碎的背景声,卢生在冰冷中醒来,回到现实。这时,西方女巫吟唱人生各个阶段,东方众仙跟着唱和……最后,全剧在莎翁作品《第十二夜》的人生咏叹声中落幕。剧中对现实人生的关切和表述形态,将叙述和生活的本然活性、横生妙趣相匹配,让观众不禁感慨,两位戏剧巨擘作品中的人物没在时间的暗河里寂寂无声,如此“相会”,让跨越时空的新故事明亮开锣——这样的文本创新高妙自然,观过之后又熟悉又新鲜,又能感知到以往常规观戏中未曾体验又实际存在的别样的叙事元素。
就这样,昆曲和莎剧与时代同频共振,鲜活着现代生活,使得中西方优秀文化在新的全球交往时代得以激活和赓续,让中西方观众从静水深流的戏曲故事的表达中,品出了比人情世态和人生况味更真诚的“中国式”情感。我以为,这是柯军作品中卓尔不群的诸多特质中的一部分,如同他领衔创作的以汶川大地震为题材的振奋人心的现代昆曲《1428》。
可以说,中英版《邯郸梦》是世界戏剧创作中重大题材的新收获。这新时代的“剧中上品”,是安于昆曲传统又心系其发展的柯军,对这门艺术迷恋的电光石火。这份迷恋,让他宁愿含笑燃烧于极境。
按照创意,中英版《邯郸梦》的演出是从柯军饰演的卢生从台口一端上台点蜡烛开始,可新烛芯埋得深,火柴又短,柯军用手指和火柴拨起烛芯,发现手上的蜡油也被点燃,而火柴就要熄灭,他就那样任手上的蜡油继续燃着,终于将蜡烛点亮……唏嘘间,不难明白,难道他不是以自己文艺的筋骨与品质,卫护着昆曲高尚的名字吗?“昆曲应该是大众的,应该是全社会的,昆曲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这是柯军微博上的一段话,也许这种近似誓言的文字,换个人写来我会觉得有虚假嫌疑,于柯军却是那么真诚可信,因其朝圣般行走的背影——这背影是他走过40年昆曲旷野投下的大悲喜,以及他由此发现昆曲绿洲的大彻悟。
“将人生的富贵荣华、生死轮回浓缩到入梦回梦的过程中,在不知何为梦何为醒的找寻中探求‘本真’的意义。”柯军说这是《邯郸梦》触动人心之所在。这也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真切地感知中英版《邯郸梦》用探求“本真”奋斗构筑的“人类的梦”,而这,恰是“中国梦”踏实而又活跃的青春质地,体现出柯军向着人类精神世界最深处不断探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属于中国文艺智慧的愿望和努力。
当下,世界戏剧究竟应该怎样融合尚在表演艺术家们的摸索完善之中,毫无疑问,柯军的中英版《邯郸梦》创作提供了一个深有意味的戏剧样式。
一个辽阔的现代昆曲传统
柯军的新媒体表情,是他那张年轻时的俊朗容颜,略锁的眉头,加之目光里所映射出的情感、信念,都是惊涛拍岸的磅礴力量;而他的新媒体标签,不是荣誉与官位,只是“昆曲演员”这浅浅四字,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过去的认同和对未来的承担。
柯军说,“汤莎会”选取《邯郸梦》,还源于他一个小小的“私心”,他是昆曲生行演员,对生行最熟悉,也最擅长,而《邯郸梦》恰恰可以全面呈现生行表演艺术。这小小的“私心”,在我看来,正是一个昆曲人的脊梁硬度,是一个泱泱大国文化自信的雄浑充沛与浩然之气的至大至刚。欲与世界戏剧交融,理应是先锋与先锋的交融,精神与精神的撞击,这样才能达成文艺的“美”的创造和提升审美效能。它与沽名钓誉无关,不论在任何时候,只要有这样的“最熟悉”与“最擅长”的融合与撞击,那么创作出的作品必定会进入胜境和臻于完型。
著名作家莲子在《昆曲名家的铁骨柔情》一文中,曾这样描述柯军为了演出中英版《邯郸梦》提前几个月加强体能,以确保在氍毹上超水准发挥:“在那段日子里,不再年轻的柯军,经常在练功场上敛起思想的羽翅,生生地把自己折腾得精疲力竭。高强度的练功之后,有时会发张自拍照给我看看。镜头中的他,静笃中眼神坚定,满头满脸大汗淋漓。心力和体能耗尽之后,悲情化育出的整个人冷峻得令人惊异,眉宇间有一股颇难描述的奇气,也显得格外粗粝、纯粹而本真。这汗津津的,坚韧沉默如铁的风容,直逼人心,让人感受到一种生命的重量以及人品戏品的升华……”
这段可以浸入灵魂的文字,成为陋室循环播放的有关“汤莎会”各种资料的生动注解,倏忽间,我竟有种海阔天高、富甲天下之感,脑海中已有身着彩裤水衣的柯军舒展自如而来,那气势有着他书法篆刻时的汪洋恣肆和无所不包的昆曲容量。如果说刻苦是柯军肉体的磨砺,那么超常的领悟思考则是决定和成就他优秀艺术思维方式的“心明火”。曾与柯军有过交流,在谈到“汤莎会”时,从其坚毅明达的话语中,可以捕捉到属于他自己的意蕴空间,那就是昆曲和莎剧的真正交流,应是艺术家与作品、古人与今人的深度交流,回归纯粹的创作本体,通过艺术作品观照当下。这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是柯军不变的戏剧信仰。这种追求,柯军以单纯热望的、一往直前的方式,创造着远比想象更丰富的昆曲画卷。这些年来,他携《余韵》《浮士德》《奔》《藏·奔》《1428》《录鬼簿》《夜奔》等多出新概念昆曲剧目到世界各地巡演。“古人早已在演‘现代戏’了,如明代的《鸣凤记》《万民安》,清代的《清忠谱》《桃花扇》不就是古代的‘现代戏’吗?”柯军不客气地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昆曲“实验观”,宣誓了自己“最先锋”昆曲的态度和立场。
柯军明白,当代昆曲观众是一个复杂而现实的欣赏群体,特别是青年观众,生活在日新月异的当下,对昆曲审美标准已有了尊古而不泥古、求精而不弃新的成熟感。这也让他的创作渐渐有了另一个传统,那就是贯穿于传统作品中的循史而著的现代文艺追求。所以,他所有新概念作品都无一例外地更沉入属于现代心灵探索的层次,以己困顿修身找到昆曲修戏的精神封地。
在《怕——柯军多元艺术探索》一书中,编发了柯军写的《印度日记》。读着,不知何时泪水打湿了书页,这是鲜见的日记式悼词。原来在印度讲学演出之际,柯军的母亲突然离世,瞬间声泪俱下后,他马上停止哭泣,连吃7颗安眠药,强迫自己休息,要将最好的声音和表演在数小时后带给观众……“为了昆曲的传播,我不能放声痛哭。”这份挤压着的思亲光芒,就那么冷峻地打在失衡与巨痛的个体情感上,却在年光过处,留给读到此处的每一个人是千疮百孔状的耗损。我在开篇写下的“昆曲之子”一词,便是在此时泪水崩塌时瞬间敲击而出的——柯军为观众呈现昆曲现代之美中,显见人心山河与地久天长,也便有了他修戏里如此修身的澎湃与优雅、永恒与热切,人间隐忍的长情大爱,化为他方寸舞台纵横虚空古今的那份初心与尊贵。
正是这份心中不灭的爱与美,建构起柯军作品人性光辉的庇护所,让他终其所学奋斗、实践着这个内核,以保证昆曲的思想光芒永存。至此,豁然开朗,中英版《邯郸梦》就是用中西方相敬相融的文化,共同拆解一根人性链条上的纷繁世界——在想象力一路盛放与目标落成并无限延展的剧情之旅中,关乎生死、欲望、功名、子女等人类共通的话题,那些不可破碎的生命形态、不可轻慢的意识抵达、不可丢弃的尘世心灵,都在剧中给予中西方观众酣畅淋漓的现实回应。
随着演出,观众一同入梦,然后归于沉默,人性便在紧凑密集的故事中收缩与扩张。诚如剧中卢生有时分不清现实与梦境,我们也分不清是我们解构剧中人,还是剧中人重构着我们。应该说中英版《邯郸梦》,是一个自我重构的过程。在梦与入梦中,相信不论是剧中人还是我们,这种“梦化”之感来自一种信念:生命境遇、时空如何不同,根,必然会在氤氲馥郁着人性的土层中相会,就如汤公与莎翁400年后这异曲同工的大雅之梦一“会”,初见却已深谙共荣共生的世界,舞动续展起浩浩荡荡的丝路文明。
演出是在英国圣保罗教堂古老的建筑和浓郁的艺术氛围中进行的,这近乎完美的表演环境,让柯军如“触电”般瞬间点燃创作欲望,他说:“回到没有现代声光电的演剧样式中,在柔和的烛光中,两位大师的作品直指人心,在今天的剧场仍然散发着人性的光芒。我们就是要做一个远离技术的艺术行动,正如昆曲‘一桌二椅’的传统简约美学。”
这样,柯军的创作和他的人格,也就构成了一个辽阔的现代昆曲传统,并且以蓬勃沉静的姿态继续鼓舞着更新一代的昆曲人的创造。艺者之乐,在于探寻之途。的确,这是一个文化友好的时代,但与此同时,还是一个可以定义自身伟大的时代。柯军便是站在时代文艺山巅丰瞻而俊逸的修持者。
当柯军想将关于透亮着中西文化美感的“汤莎会”之种种录入《汤莎会》后,邀我写篇短文,我着实惶恐。他,梨园大家;我,戏剧外行,区区平素写文的感悟企能配得上他沉甸甸的作品?柯军笃信作答:“就需要你这样的外行看昆曲。”好一个“看昆曲”,透露出柯军心中昆曲之重之深;这“外行”,无关身份与交情,只在文化之共鸣与认同。如是,我便放肆地送上此文。
责任编辑:杨 林
(作者系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会员、家庭期刊集团副编审、《家庭》杂志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