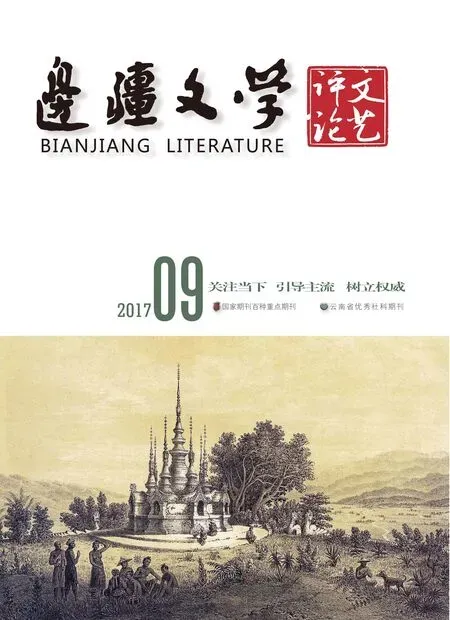浅析《萨拉辛》叙事中隐含的逻格斯权威
孙佳丽
浅析《萨拉辛》叙事中隐含的逻格斯权威
孙佳丽
“逻格斯”(Logos)来源于希腊文,它有两层含义,既指词语,更为常用的是表示本原性的或终极的真理,类似于我们所说的“道”。而“逻格斯中心主义”则是雅克·德里达为适应其解构主义思想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德里达认为,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是一种逻格斯中心主义传统,即总是把真理的本原归结于逻格斯,或是口说的话,或是理性的声音,或是上帝的话。“在一个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中,唯见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而绝无两个对立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踞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这个二元对立,便是在一特定时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因此,可以认为,逻各斯中心传统总是试图追求一个永恒的中心或一种绝对的权威,而这种中心或权威是通过一系列等级分明的二元对立表现出来的,在二元对立中,总会有一方处于中心地位,而另一方被弃之边缘。总之,就现代的学术观点,“逻格斯”代表的就是一种权威性的、上帝般的存在,而这种权威在《萨拉辛》中如何体现呢?在此,先简单介绍一下文本《萨拉辛》,《萨拉辛》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作品,在《人间喜剧》中处于“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部分,它大体上讲述了如下内容:在巴黎上流社会的舞会上,一个年轻人“我”为了讨好一位少妇,就用一个故事来吸引她,从而达到满足自己情欲的目的,而这个故事就是萨拉辛和赞比内拉的“爱情”故事:年轻雕塑家萨拉辛带着对艺术的狂热爱恋来到罗马,并在这里爱上了歌唱家赞比内拉,通过种种努力,他和赞比内拉有了亲近的机遇,然而在“爱情”就要达到顶峰时,他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原来赞比内拉是个被阉割的男人,在他恼羞成怒,打算杀了赞比内拉时,却被赞比内拉的保护人——红衣教主所杀。下面笔者将从非线性叙事时间结构、“潜变化”叙述者、身体伦理叙事三个角度来论述文本的叙述策略中内蕴的“逻格斯式”的话语权威。
一、非线性叙事时间
作为现世的存在,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脱于时间,具有一定长度的文本也必须是有一定时间度量的读物,而时间维度也是作为叙述彼此之间区分的依据。叙事学对叙述时间的硏究主要是指对叙事文本的时间的关注。叙事文本时间又可以划分为:写作时间、事件时间和叙述时间。事件时间是指事件真实发生的自然时间,叙述时间则是指文本中故事呈现的时间方式,事件时间与叙述时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家关注的重点。就《萨拉辛》来说,按照事件时间应该是先叙述萨拉辛的故事(过去时)——“我”与少妇的故事(现在时),然而实际上文本呈现的时间是现在时(“我”与少妇的故事)——过去时(追忆“萨拉辛”故事)——现在时(“我”的故事)。这两种时间顺序是有出入的,前者可以说是“线性的”叙事时间,中间不存在回溯的时间结点,而后一种叙述则是“非线性的”。这种时间呈现方式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错时”。关于“错时”(anachronie)又译“逆时序”、“时序倒错”,又称“时间畸变”。克里斯丁·麦茨说,由于叙事中包含有叙事和故事两个时间序列,“这种双重性不仅使一切时间畸变成为可能,挑出叙事中的这些畸变是不足为奇的,更为根本的是,它要求我们确认叙事的功能之一是把一种时间兑现成另一种时间。”托多罗夫认为:“叙述时间(话语时间)的顺序永远不可能与被叙述时间(事件时间)的顺序完全平行;其中必然存在前与后的相互倒置。这种相互倒置的现象应该归咎于两种时间性质的不同:话语时间是线性的,而故事时间则是多维的。两者之间既不可能平行,则必然导致错时。”而这种“错时”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故事的断层。叙述者本身处于一层故事层,成为“故事外层”,而他所追忆的故事属于故事中的故事,成为“故事内层”。由逆时序的时间叙事所形成的两个故事层面相互之间也有些微妙的关系。下面结合文本《萨拉辛》来具体分析。
《萨拉辛》的非线性叙事时间表现为“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模式,“我”和少妇的故事是属于外故事层面,而萨拉辛的故事则属于内故事层面,从而把整个故事分裂成两层叙事。这两个故事内部的叙事时间都是严格按照传统的线性叙事来完成的,将两者并置,在结构上是平行相对、相互独立的。一层是发生在18世纪,讲述了萨拉辛小时候童年上学经历,跟着老师布夏东学习绘画与雕塑的过程,以及到意大利罗马进一步深造,直到遇上女歌手赞比内拉,然后一步步坠入情网,最终认识到真相,故事终结于萨拉辛的死亡,关于萨拉辛这个人一生的故事就结束了。而另一层故事发生在19世纪,也可以简单概括为这样的一条叙述线:“我”在舞会与一个美丽的少妇相遇、交谈,为了吸引她的注意从而满足自己情欲的目的,就给她讲了一个“萨拉辛”的故事,最终少妇拒绝了“我”。这两个故事都遵循着“开端、中间、结局”的时间叙事模式。这是表面上的分离与独立,实际上两者之间关系并非如此“泾渭分明”,而是相互纠缠与粘连的,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表层结构来看,两个故事的叙述是相互穿插的,这种穿插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套入。“我”给少妇讲关于萨拉辛的故事,在此,这个故事已变得不纯粹,它变成一种类似工具的存在,而少妇对此很感兴趣,从这里可以证明内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推进外故事前进的手段,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外故事的“催生”使得内故事的价值得以实现,更有甚至,内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外故事的故事走向:少妇听了萨拉辛的故事,对现实很失望,从而拒绝了“我”的请求。另外,“我”在进入内故事叙述层面中也是随时被受述者不断拉回现在时间,这里面包含的技巧将在下一部分分析。
实际上,两者之间更为深层的关系反映在各自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中。巴特对两层故事关系的分析是这样的,他认为导致萨拉辛爱情悲剧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对阉割的恐惧,在整个萨拉辛的故事中时时笼罩着阉割的氛围,而且这种阉割具有传染性,而少妇最终拒绝“我”也是因为受到阉割的传染,而“阉割”象征着“去中心化”、“无根”等。从内故事表现的内涵来看,实际上表现的是对“阉割”的厌恶和痛恨:萨拉辛作为一个情欲旺盛而又痴情执着的男人,遇到一个心仪的女性本来可以促成一段佳话,诚然,因为赞比内拉的“阉割”成为悲剧的导火索,这点与巴特的论述是相符合的,但巴特止步的地方并不是文本最根本的要义所在。“阉割”实际上是掌权者实施权利的一种暴力手段,被阉割者是受害者,进而再变成间接施暴者,欺骗、玩弄、伤害无知者,在整个内故事层面,到处充盈着红衣教主的压迫势力。在外故事层面,“我”给伯爵夫人讲这个故事本来是为了取悦她进而满足自己的欲望,然而伯爵夫人却因为听到这个故事对激情、爱欲产生了厌恶,直致“我”的企图落空。伯爵夫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萨拉辛的故事引起了她对“阉割”的恐惧和反感,更深层地说,引起了她对巴黎,甚至是整个现实社会中那种毫无底线的欲望化的反感和憎恶,正如她所说,“您的故事使我对生活、对种种激情感到厌恶,而且这种态度短时间内不会改变。除了没有心肝的人,所有人类感情不都是以痛苦的失望而告终吗?友情!世上有友情吗?今后,如果在生活的狂风暴雨中我不能像岩石那样岿然不动,我就进修道院。虽然基督徒的未来也是个幻象,可是这个幻象至少到死后才破灭。”这段文字既可以说是她的“听后感”,更可以理解成她对现实的指控。
二、“潜变化”的叙述者
叙述者(narrator)是叙事文分析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叙事学,“叙述者”被定义为“陈述行为主体”(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文本中的声音或讲话者。“叙述者代表判断事物的准则:他或者隐藏或者揭示人物的思想,从而使我们接受他的‘心理学’观点;他选择对人物话语的直述或转述以及叙述时间的正常顺序或有意颠倒。”)叙述者具有五种功能:叙述功能、管理功能、交际功能、见证功能和思想功能。“这个只能说明叙述者在多大程度上以该身份介入他讲的故事,他和故事有什么关系。自然这是情感关系,但也是精神或智力关系。当叙述者指出他获得信息的来源,他本人回忆的准确程度,或某个插曲在他心中唤起的情感时,该关系可表现为单纯的见证,似可称为证明或证实职能。但是叙述者对故事的直接或间接的介入也可采取对情节作权威性解释的、更富说教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职能可称作叙述者的思想职能。”就像热奈特自己所说,这几种功能并不是相互独立、单独起作用,“我们知道巴尔扎克大大发展了这种解释和辩解性话语的形式,它在巴尔扎克和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中传递出现实主义的动机。”而所谓的“潜变化”叙述者,这是笔者根据《萨拉辛》的叙述者特点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也可以称为“局限视点转换”,主要是指在故事叙述层面,叙述行为表面上是由同一叙述者发出,实质上已在潜层改变了叙述者的身份,从而达到通过话语控制叙事距离的效果。局限视点(limitedpointofview)这一视点包括两种主要形式: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和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华莱士·马丁指出:“这种‘局限视点’常常既含有心理上的也含有视觉上的限制:叙述者表现的仅仅是这个人物所看到的,好像他是通过这个人物的眼睛看的,或者是作为‘不可见的目击者’站在他身边。”局限视点因而也成为“戏剧式呈现”或“客观展示”的主要方法。而巴尔扎克正是通过这两种局限视点的转换技巧使其文本表现出一种既显得“客观”、“不干预”的叙事风格,却又在思想上牢牢控制着受众的道德伦理走向。
《萨拉辛》整篇故事的叙述行为是由“我”一个人承担的,“我”讲述舞会的繁华场景,讲述“我”内心深处的感受,讲述萨拉辛的故事,毫无疑问,“我”承担了所有的叙述行为,但实际上在双层故事叙述中,通过细致的分析,可以发现视点已经改变了,由“我”潜变成萨拉辛,最后又变成“我”,实现了叙述者的“潜变化”。首先,在外故事层面,文本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first-personnarrative),文本在开篇提到“我”处在上流社会的舞会上,这时“我”眼中的景象是这样的:“大厅里不时突然爆发出赌客们的大声吼叫。钱币的撞击声、舞乐声和宾客的低语混成了一片。此外,弥漫在空气里的各种各样的香气和普遍的狂热情绪也刺激着人们兴奋的想象力,使那些被上流社会所有这些迷人之处所陶醉的人完全神魂颠倒了。”这是一种直接感受,隐含了对现实的一种态度,叙述者对这种情况的评价是“活人的狂舞纵饮行乐图”,这里叙述者和作者的态度都不明了。随着情节的发展,“我”的思考行为被打断,从而也融入现实的一派繁荣之中并且看到了老年的赞比内拉,“我”眼中看到的老年赞比内拉是“这张脸焦黑,瘦骨嶙峋,布满纵横交错的皱纹,下颌和太阳穴全凹进去,眼珠消失在黄色的眼眶里。因为出奇的瘦,上下颚骨非常突出,双颊成了两个大陷窝。”这里都是以“我”的第一叙述视角来观察周围的行为和人物,从而使读者获得了一种以受限制的全知方式来接近文本。“我”给少妇将萨拉辛的故事,包含了对少妇美丽肉体的觊觎,这都是第一叙述给予的方便之处。正如福勒认为:“以第一人称视点叙述故事有种种显而易见的长处,例如它可以使作者十分自然地进入主人公的内心深处,并用意识流或其他方式将他最隐秘的思想公之于众。”但同时他也提到“然而这种叙述方式也有其短处:如果说随意深入小说主人公的内心的权利是破格特许,那么基于同样的理由,小说中其他人物的思想感情就成了一个谜。”正是因为由“我”的第一人称叙述视点会导致在进入萨拉辛的故事有心理上的阻碍,所有巴尔扎克很聪明地使用了“潜变”叙述者的技巧。整个内故事层的叙述是以第三人称的局限视角来完成的,所以虽然在内故事叙述中,实际上“我”的叙述是被移置在主人公萨拉辛的身上,从而以萨拉辛的视点来展开叙述的,因此整个内故事虽然都是用第三人称叙述,但这并不妨碍读者近距离地来体会萨拉辛的心理变化历程。
在内故事层面,实际上是萨拉辛在叙述,只有这样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其内在的感情,从而达到一种震撼的效果。首先,“得到她的爱,否则就去死,这就是他给自己的命运做出的选择。532”这是萨拉辛初见赞比内拉时所许下的诺言,正因为读者也被这种限制型视角的牵引,所以总会陷入对美好爱情的幻想之中。然而最终的结局是萨拉辛发现赞比内拉是个“阉人”,这种结果对萨拉辛所起的效果是致命的,对读者同样起到震撼的效果,原因是我们和主人公一样一直被蒙在鼓里。这种效果在作品中的受述者(少妇)身上得到验证。在内故事中,萨拉辛疯狂地爱着赞比内拉,千方百计地向其求爱,最终因为“阉割”而使一切打破,在这层关系中,受阉割的赞比内拉作为一个被追求者,是掌控着萨拉辛的喜怒哀乐与最终结局的。然而,赞比内拉也是受害者,他作为歌唱家,受制于当时罗马教皇的规定,而成为一个“受阉割者”,最终沦为人们眼中的“怪物”,这说明了他的一生也是被控的,真正背后操纵的是红衣主教,即他的保护人和包养者西科尼亚拉——传统威权的代言人和执法者。因此可以说,内故事整体是处于一种黑暗权势操纵下生命与金钱被吞噬的恐怖氛围之中。由于“潜变化”叙事的转移,这种恐惧直接外涉到外故事层面,在现实的巴黎,以最卑劣的方式换来的金钱得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德·朗蒂先生和他的夫人从不谈他们的出身,他们过去的生活,以及在世界各地的社会关系,这种谨慎本来不会长久使巴黎人感到惊奇。因为巴黎也许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理解韦斯巴芗的那句至理名言。在这儿,金钱哪怕沾有泥污和血迹,也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而是能代表一切。一旦上层社会得知你的家产数目,它就把你归入拥有同等家产的那类人之中,从此,谁也不会问你是否真有贵族头衔,因为大家知道,这些头衔是多么不值钱。”巴尔扎克就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通过拉近萨拉辛与受众的距离,进而使之产生同情,再文本结束处让文思会聚在一起,以达到一种震撼人心与批判现实的写作目的。
三、身体叙事
身体,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从物理学上来讲,身体即肉体,它是独立的、个体的。同时,身体承载了诸多社会性的内涵,这时它可以说是非自由的、符号化的。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个体与社会的集合体。身体叙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性别叙事与权力叙事。首先,性别叙事在文本中主要体现在萨拉辛对赞比内拉性别的“误读”和“中间性”身体的存在。造成萨拉辛悲剧的直接原因是他对罗马文化的无知,而这种无知是由他外来者的身份所决定的,所以当他见到赞比内拉时,他仅仅通过视觉印象来确定赞比内拉的性别,在他作为艺术家的眼睛里,“他看到一张表情丰富的嘴,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白得耀眼的皮肤。胳臂与上身连结得那么优美,颈子那么浑圆,双眉、鼻子的线条那么和谐,还有那毫无瑕疵的椭圆形脸庞,轮廓明晰而纯净,浓密而翘曲的睫毛,宽宽的、令人销魂的眼睑,他欣赏着这一切,真是百看不厌。”这说明他认为的女人就是具有这种气质的身体。继而,“他向赞比内拉做了一个会心的表示,赞比内拉羞怯地垂下了她那令人销魂的眼睑,好象因为自己的心意被情人理解而感到幸福的样子。”萨拉辛对此也解读成女人的娇羞。特别是当赞比内拉告诉他自己是个男人的时候,可由于他害怕蛇,从而再次使萨拉辛相信她是女人,“‘嘿!现在您还敢说您不是女人吗?’艺术家微笑着问。他看到这个柔弱无力的女人有着卖弄风情、脆弱而且娇滴滴的性格。她那突如其来的惊吓,莫名其妙的任性举动,内在的心烦意乱,难以理解的冒险行为以及细腻入微的感情变化,都是典型的女人的表现。”这些实际上都是对赞比内拉行为的“误读”,而造成这种“误读”的根源则来源于萨拉辛意识中对女人的定位:害羞、任性、胆小、柔弱。这种对女性的传统定位是西方在一直以来评价女人的标准,但这种标准在《萨拉辛》中却失去了其准确性,也从侧面说明传统权威文化的失效与无力。在文本《萨拉辛》中,有很多存在于“中间分界”的身体,比如,在文章开头,“在我的右方是一幅沉寂阴森的死亡图景,在我的左方是活人的狂舞纵饮行乐图;一边是冷冰冰的、阴沉沉、披着丧服的大自然,另一边是寻欢作乐的人类。而我则置身于这两幅画的交界处,我本身也是一个既令人好笑又令人悲伤的精神大杂烩:左脚打着舞曲的节拍,右脚却似乎已经跨进了棺材。原因是舞厅里常有一股穿堂风,能把你的半边身子吹得彻骨冰凉,而另外半边身子仍感受着大厅里腾腾的热气。”“我”在这里实际上是一个清醒的沉沦者,是一个中间者。赞比内拉受阉割的身体,导致其非男非女,成为一个中间者,巴特认为这是一种中间叙事,最终走向得是一种增补的平衡。实际上,无论是“我”还是赞比内拉的身体,都二元对立的结果。而二元对立中的两项从来都不是平等的,“我”最终会有给少妇讲故事这样一种行为,其实是“我”的中间状态被打破,从而跌入现实舞会纸醉金迷的结果,从这一效果可以看出“金钱”的权威与诱惑力紧紧控制着人的心智;赞比内拉受阉割的身体则是教会权威和财富欲望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之,中间状态被打破与被塑造的背后都是有一个巨大的操纵力量。
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身体总是会和政治、文化等相联结,正如尼采所说,“肉体乃是统治的产物。”赞比内拉“非男非女”的身体正是强权文化,抑或是强权政治施暴于肉体的结果。然而除了一种暴力的方式外,文化政治更多地是通过一种潜移默化的“冷暴力”方式来控制人的思想、限制人的行为。萨拉辛从一开始便受到这种“冷暴力”的钳制。出身于一个传统保守的小镇,萨拉辛却从小就表现出一种旺盛的激情,“他带着一种不寻常的热情,古怪的性格,他不好好学习希腊文的基础知识,却在那儿给可敬的神甫画速写,他还画数学教师、省长、听差的、阅卷的,他把所有的墙壁都涂满了一幅幅难以辨认的草图。在教堂望弥撒时,他不唱赞美诗,却在长凳上画画刻刻,或者要是弄到一块木头的话,便在木头上雕刻某个圣女的形象。不管是临摹用来装饰祭坛的画幅上的人物,还是即席创作,他总要在自己的位置上留下粗野的图画,内容淫荡,连最年轻的神甫也看不下去,而老年的神甫呢,据有些说话刻薄者称,他们看了暗暗微笑。他被赶出学习,因为有一个星期天,他在忏悔室等待忏悔时,把一块大劈柴雕成了耶稣像。这个雕像太亵渎神圣了,不能不给作者招来惩罚。他不是还曾经胆敢在圣体柜上方了一个形象猥琐的雕像吗!”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出萨拉辛的“不安分”是其反抗传统文化与宗教文化压抑人性的一种反抗,最终成功了(被教会学校开除,才华得到认可)。然而这种成功只是短暂的,在布夏东那里其本性再次受到压抑,“他尽量把萨拉辛那非同一般的狂热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看到他陷入某种构思不能自拔时,就不让他工作,叫他去消遣消遣;当他想要纵情放荡时,则交给他一些工程浩大的任务。”而当萨拉辛独自一个人来到罗马时,虽然对这里文化显得格格不入,但至少他可以自由地投身于艺术创作、释放天性,而这种释放在碰到赞比内拉时达到顶峰,“雕塑家先是感到全身一阵寒冷,继而又感到身体的最深处,就是我们缺乏其它词称之为心的地方,有一妒火在噼啪燃烧!萨拉辛想冲上舞台,抢走这个女人。他精神上感到一种压抑,这一现象很难解释,因为发生在人所观察不到的区域,可是他的体力却因精神上的压抑而百倍增强,这力量快要以令人痛苦的冲击力迸发出来了。”最终的结局是萨拉辛的反抗最终断送了他的性命,他喊道“你们欺骗了我”是对心中艺术理想破灭的呼喊,更是对传统文化虚伪、丑恶、残暴一面的控诉,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他只能无力地嘲讽道:“你们做了件好事,称得上是基督徒的善行。”
四、隐含的“逻格斯”权威
罗兰·巴特对《萨拉辛》的解读可谓独树一帜,他颠覆了文本的整体意义和中心意义,将小说分解成561个意义单元,由此证明小说表面看来连贯的意义系统实际只是一大堆能指碎片的集合。然后,巴特进一步指出,这些能指碎片并不直接与所指相关,而是受制于其在文本中辨认出来的五种不同的符码代码,这五种不同的符码分别是阐释性符码、能指符码、象征符码、行动性符码、文化性符码,它们集合起来完成了一个开放的文本“构成”过程。这些都让我们看到,文本是没有整体意义和向心结构,甚至没有稳定的意义,而是一种“无中心”的存在。实际上,从巴特对文化符码的阐述就可以看出他规避了文化意义在文本中的效应。罗兰·巴特说:“文化代码是对一种科学或知识的指称,当目光转向它们的时候,我们只是指出这知识的类型,如物理的、生理的、医学的、心理的、文学的、历史的等等,而不更进一步去建构或重构它们表现的那一文化。”但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文本的意识形态》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文本中文化内蕴的巨大影响力,“文化代码有点像格言式的智慧或对普遍的行为、事件和生活的常识的仓房,当需要某个具体细节的时候,它就会被说出来。因此这种代码也几近意识形态的孳生地。所有现存的意识形态本应是那样的,而总是趋向于看到某种旧意识形态断片的仓房。当叙述的策略需要选择另一条道路或需要为自身的发展辩护的时候,就可以向它去求助。”在文本中,每个人都受着其所处文化的牵制,在萨拉辛故事的,“逻格斯”的具象化身就是教会及传统文化,而在巴黎则是金钱,这二者的权威使人们敬畏、尊崇。这是在这样的文化控制下,萨拉辛那纯真的爱情变成了一种被人取乐的噱头,而最终扭曲的传统现实则扼杀了这种纯洁爱情的所有苗头,在这里也隐含了萨拉辛对赞比内拉的爱,对雕塑的狂热其本质是来源于对一种纯粹美的追求,最终这种美被所谓的权威摧毁了,这也证明了,在强大的“逻格斯”权威面前,任何的反抗都是无力的。
在巴尔扎克时代,资产阶级日益成长,贵族阶层日趋没落,财产和贵族封号一起成为涌向权利巅峰的两个必要条件。人们毫不讳言对金钱的贪欲,人成为金钱的奴隶,整个时代的风气就是追逐金钱和权势。而一直把创作小说看作是书写历史的巴尔扎克立志如实书写法国的这种充满污秽的现实,为了规避检查机制,同时也为了吸引读者阅读兴趣赢得赖以生存的生活费,选择了这样一种“客观化”的写作策略,事实证明获得了成功。他借萨拉辛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逻格斯”权威的巨大杀伤力,特别是在开头时众人对丑陋的赞比内拉的追捧与结尾处对其钱财来源的解释,让人们对巴黎所谓的上流“贵族”们产生了厌恶,最后由受述者少妇来发出内心的呐喊,“巴黎真是个好客的地方;”她说,“它对一切都来者不拒。不光彩的家产也罢,沾满鲜血的家产也罢,它一概欢迎。罪恶和污秽全能在这里得到庇护和同情,只有道德廉耻不受崇敬。是啊,纯洁灵魂的乐土在天上!”550作者这种借人物之口成功把自己隐藏起来,而又以最残酷地方式惊醒依然沉睡在迷梦中的人们,引起受众心灵最深处的反思。
结 语
作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有着一个文人的自觉性——拿起笔杆,反映现实。他的“非线性”叙事时间巧妙地讲故事分层,既有对传统叙事时间表达的继承,又带有现代性“错时性”的先锋性;而“潜变化”叙述者则进一步将分层的故事展现得既脉络清晰,又增加一种神秘性,通过“局限视点”的相互转换,在结尾处会聚,从而使整个文本达到高潮,借人物之口传达写作的动机,取得震撼人心的警示效果;而身体叙事也是巴尔扎克对身处在巴黎这个大染缸中人的身体该如何归置的一种思考,并且表达了在这样一种正常欲望被扭曲,天才式的欲望被悬置和扼杀的一种深深的焦虑与担忧。总之,文本从三个角度阐明在“逻格斯”——金钱、权利的统治之下,巴黎乃至整个法国道德人性底线无限沦丧的现实的批判与反思,可以说,《萨拉辛》整个文本无不笼罩着一种强大“逻格斯”权威的压抑与残酷的高压氛围,但同时也展现了小人物的不同流合污与无力挣扎的动人魅力。
[1] W·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 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 巴尔扎克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4]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 张隆溪.道与逻格斯[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6] 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 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M].朱金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8] 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9] 罗兰·巴特.S/Z[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0] 黄晓华.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11] 黄晋凯.巴尔扎克文学思想探析[J].外国文学评论,2000(3)
[12] 罗智文.巴尔扎克短篇小说叙事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5
(注:此篇论文为“2016年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杨 林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雨花校区文学与传媒学院15级文艺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