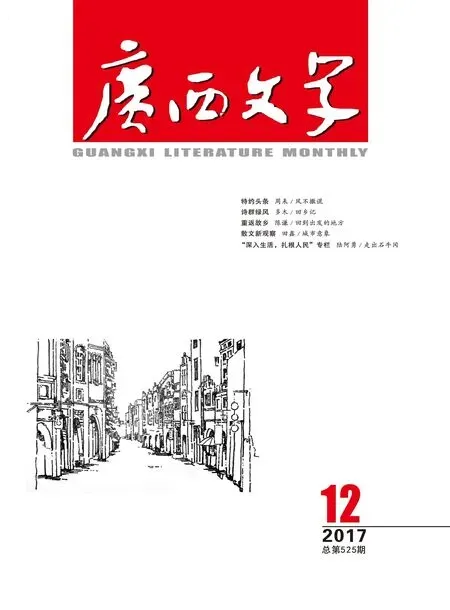稻米女人
曾丽艳/著
生活,痛并快乐着,这种体会不分朝代和贫富贵贱。人们常常习惯将苦涩藏在心里,而把幸福变成四季餐桌上的食物。男人,在餐桌前肆意宣泄;女人,则将喜怒哀乐融进美食里。于是,一个民族千年的饮食习俗,得以经久不衰。
——题记
曾经,一个考古专业的小伙子问我:你真是壮族的吗?太好了,那你应当是住在岭南啦?你们是骆越古国的后裔吧?你家乡的文化如何?……
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似乎他才是正宗的壮族人,而我不是。说起来惭愧,我说不出岭南的具体方位,也并不十分了解骆越古国。我所知道的,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壮族人,我的家乡在广西南宁著名的大明山脚下。据说,这里是古骆越王国的中心,骆越古国的文化发源于此。
至于骆越文化如何,小伙子,抱歉,我真的是不知道。我更不知道你所说的龙舟文化、航运文化、太阳文化……真要我说一个?稻米,女人,算吗?
那时,考古专业的小伙子盯着我,眨眨眼,眼里透着一丝失望,但还有些许的执着:算吧,但应当没什么新意!
或许吧。女人,稻米,与高雅的文化比起来,的确俗气。
俗就俗罢,谁让这样的认知早已深入我的骨髓?
一
农历二月,当春雷响起,女人们就从谷缸里取出一捧又一捧稻子,轻轻抚摸,像抚摸即将出嫁的女儿,嘴里不停地唠叨着。浸泡,播种,稻子从女人指缝间撒落,开始沐浴风、阳光和布谷鸟的鸣叫。慢慢地,稻子探出可爱的脑袋,伸起细长嫩绿的懒腰,世界醒了。
男人们在女人们的督促下,卸下厚实的棉衣,把厚脚板伸进刺骨的稻田,犁,耙,撒肥,封埂,田野里,片片明镜般地晃眼,冷静得刺骨。
后来,女人们来了,田野也便活了。
女人们挑着满满的担子,三三两两,说说笑笑,或唱着调味的山歌,和着“吱吱呀呀”的挑担声,袅袅婷婷走向田野。来到田坎上,轻轻放下那一蔸又一蔸聚拢在一起的禾苗,卷起裤腿,露出捂了一节冬藕白的小腿,相互打趣一番,让笑声咯咯咯地响彻田野上空。男人们见了,“唿——”地打着清脆的哨音,吆喝声变得高远而生动。
女人们身子弯弓着,似成熟的稻穗,随风上下左右轻轻摇晃。她们握住一把禾苗,左手掰,右手拆,再快速插入泥水里,拇指和中指似在弹奏着曲曲弦乐,配合得如此默契。女人们心里还有一面鼓,那手指夹着禾苗落地的瞬间,就是清脆的鼓点,一下一下,急促而明快,干脆又利落,一曲未终,女人们的身后已是绿意荡漾。一株株禾苗在女人们的手指间,踏上了新的征程。
家乡的天,还没有体会到春的温顺,热辣的夏季已早早到来。阳光,雨露,禾苗幸福地享受着,疯狂地吐芽拔节,似乎一夜间,已郁郁葱葱绿成一片。女人们有事没事总会来到田边,或锄草,或施肥,或杀虫。更多的时候,她们站在田塍上,摸一摸,嗅一嗅,脸上满是宠溺。
水稻抽穗的时刻激动人心。一棵棵腆着肚子的水稻像怀胎十月的年轻母亲焦急地等待着。终于,黄澄澄的太阳暖融融地停在空中。风止了。水稻在女人们热切的注目下慢慢分娩。没有挣扎,没有血迹,没有痛苦的呻吟,一切都在神秘的静谧中。一个又一个满怀母爱的稻子诞生了,它们舒展着蜷曲的发丝,欣欣然,接受太阳的洗礼。几天后,水稻抽穗差不多齐了,一束束淡黄的谷舌像一双双高举的手。女人们看着心醉了。
七月流火,把田野镀上金色,可以开镰了!女人们的热情如同这炎热的天。抓禾,挥镰,堆放,捆绑,再一担担地挑向空地,一把把地伸向脱粒机,一圈圈地扬起筛子,一袋袋地搬上牛车。夕阳西下时,健壮的水牛拉起牛车,埋头前行,鼻子里喷着重重的粗气。女人们坐在高高垒起稻谷的牛车上,劳累了一天,她们的腰背已经不再挺直,眼睛微微眯着,脸上,如天边的酡红一片,那么美丽。
浸泡,播种,育苗,插秧,拔节,抽穗,壮籽,开镰,扬秕,入仓,这就是水稻生命的全过程。女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
二
女人催生了稻米,稻米在女人们灵巧的双手里,幻化出千姿百态的形与闻而生津的味。
记忆里,家乡的女人勤劳而忙碌。我的母亲亦是。
小时,要想在白天里见到母亲,那是一种奢侈。晨起,当第一声鸡鸣声响起,母亲默默作别还在沉睡的孩子们,以及那打着饱嗝的鸡鸭鹅猪,前往田地里耕作;晚上,当喧腾了一天的万物安静下来,我在迷糊的双眼中,看到了母亲似有似无的疲累的身影。
只有节日里,才可以真切地在白日见到母亲。我们称之为“母亲的假日”。
好在家乡节日很多,每月都会有。二月初二,三月初三,四月初四,五月初五,六月初六,七月十四,八月十五,九月初九,十月初十,十一月冬至,十二月一月是春节。每一个节日,是可以围着母亲转的日子,更是各种风味小吃汇聚的节庆。
家乡的女人们不仅勤劳,而且手巧。五色糯米饭、粽子、馍馍、榨粉、米花糖、米饼……每一种味道迥异的小吃,都是由一粒粒饱满滚圆的稻米变化而来。
家乡的小吃,或以糯米为主,或以籼米、粳米为主。因此,女人们每年都会有选择地种上几种稻米,分批分类收藏着。待到用时,适量取出,去皮筛糠,或整粒浸泡蒸煮,或碾成粉状捏成圆的扁的方的。每一种小吃,每一道工序,烦琐而富有技巧,男人们缺乏耐性视而不见,孩子们虽然帮忙打着下手却常常偷懒,唯有女人,忙起来就是一种忘我的境界。
我的母亲在每个节日必做的小吃是生榨米粉。哪天鱼肉糍粑吃多了,黏黏腻腻的,这个时候,呼噜呼噜灌下一碗酸酸馊馊软滑细长的现榨米粉,真是大快人心。母亲做的生榨米粉是村里的一绝,粉条就是要比别人的细长,味道不会酸得过分,拌菜不咸不淡清鲜可人。曾经出于好奇,我参与到前来讨教的队伍里。母亲说,粳米有很多种,籼贵矮这个品种做出来的粉更清香、有韧性。节前的几天,母亲便拿出去糠的大米,浸泡一夜,次日滤掉水后,倒入已铺好芭蕉叶的竹篓,随后在上面盖一张芭蕉叶,一层干稻草,封严实,等着发酵。一两天后,揭开,一股醇香浓郁的发酵味会扑鼻而来,母亲把散发着热气的泡米倒进大瓦盆,以双掌把鼓囊囊的泡米搓烂,最后用石磨磨成稀米浆。
不要以为到这里工序就结束了,那只是开始。米浆磨好后,母亲在大竹匾上盛满草木灰,铺上白布,再把稀米浆倒进去。母亲说这个程序目的是让草木灰吸干水分,等米浆变稠后搓碎,再揉弄成粉球团,埋进大箩筐里的草木灰,让它在草木灰里再次发酵。
节日当天,天未放亮,母亲早已起身烧开一锅水,然后从草灰堆里扒开粉球团清洗、晾干,下锅煮熟,最后以石碓把粉团舂成粉浆。等我们醒来的时候,米粉独特的香味已经轻悠悠地沁人心脾了,不由得让人咽了下口水。看到我们都醒来,母亲便开始榨粉条。她娴熟地拿起榨粉机,往槽里加一勺白色的粉浆,慢慢用力,白色的粉条扭动着身躯落进滚烫的水锅里,翻腾着。两三分钟后,母亲用粉兜打捞起粉条。一旁的父亲也忙开了,他将精选的五花肉剁碎,与切剁成末的头菜一起炒香,装进已装有榨粉的大盘,撒上葱花、香菜、胡椒粉、五香粉,再浇几勺上乘的土花生油,一勺大锅里的粉水,这样一大盘洁白、细嫩、软滑、爽口的榨粉便正式问世。
所有小吃里,我个人最中意的是米花糖。单是看一看黄灿灿的、挨挨挤挤凑到一块的爆米花颗粒,已经满口生津,更不用说咬上一口了。“咔——”的一声脆响,咀嚼它,只听见“洽洽洽洽”的轻响,甜丝丝、脆生生、香喷喷的味道充斥全身。准确地说,要吃上米花糖,要花上五六天的时间。每年的小年廿三,家乡的女人都会翻出上等的大糯,去糠去沙土,浸泡,清蒸,熟透后趁热撒上细腻的木薯粉,不停地搅动揉搓,直至木薯粉贴满糯米而一粒粒独自分开。待糯米凉透,每次抓几抓放到石臼里,来回舂,直至糯米粒被压得扁实。女人们常常是一边擦着汗水,一边筛掉木薯粉,仔细地掰掉粘在一起的米粒,然后很慎重地拿到室外晾晒,等着干透了在年三十晚加工成正品。因为我爱吃,早晚晾晒的任务就自揽了。若是晴天还轻松,若碰上阴天,那可是悬着一颗心,一整天都不敢出门。终于盼到年三十了,一大早,母亲在我们的吵嚷声里,把压扁晒干的糯米放入小盘,浇上花生油与白酒,说是浸泡几个小时后才能制作米花糖。年夜饭后,是女人们最忙的时候。爆炒,煎糖,搅拌,出锅。可别看着简单,都是技术活。爆炒米粒不能太多,一次只能一小抓。糖是当年村里自榨的红糖,煎糖时火候、时间、黏性凭的都是经验,因此女人们做出来的成品里,有硬的,也有软的;有结成块的,也有散成沙样的;有金黄色的,也有黑糊状的。
大凡所有的参与者都会叹道:真不容易啊!而我们这些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学会了思考:每月的节日真的是母亲的假日吗?
三
是的,家乡小吃的生成,没有哪一种是简单容易的。
去年春节,第一次回老家与母亲包粽子。在我的印象里,包粽,不外乎就是把米和馅儿放到粽叶上,合起来,绑上绳子,放到锅里煮几个小时就可以,不难。其实不然,单是包粽前的准备工作就很烦琐:粽叶,一张一张地洗刷;粽叶焯水不能太生,也不能太过;米要一勺一勺地淘;绿豆要一次次地去皮;五花肉要切得大小厚薄合适。等到做完这些事情,时间已过大半天。包粽时,母亲熟练了,粽子包得丰腴匀称;而我,不是两头大小不等,就是漏米跑馅儿,严重时啪地掉在地上,散成一朵花。那天等到包完粽子,已是傍晚,母亲支起锅,开始熬煮。当晚,因为白天忙个不停的缘故,我终究没能与母亲一起守到夜里两点,提早睡去了。
次日,看着已经出锅的一列长长的粽子,疲累感挑不起我的食欲。
“妈,以后别自己做了,街上买几个就行。”我不禁发着牢骚。
母亲此时正在清洗油腻腻的大铁锅,瘦小年老的她,渐渐地已搬不动这古老沉重的铁锅。那熬夜的双眼,浑浊而布满血丝。我的心揪了一下。
“街上卖得贵,又没有自己做的好吃。何况大过年的不包粽,老祖宗会怪罪下来的。”母亲吃力地直起身,喘口气对我应着。
我赶紧上前,从母亲手中接过那口铁锅。尖底平口的铁锅,笨重无比,平地上都无法放置。于是我建议换成铝锅。
母亲说,铁锅煮出来的粽子才是正宗的,老祖宗吃了会高兴,高兴了才会保佑我们平平安安的。
我不吱声,但心里还是暗暗想,都什么年代了,还那么迷信。
忽然间,我想起了已过世的奶奶。奶奶在世时,逢年过节的小吃做得极是认真,因而做得好看又好吃,估计母亲就是得到了她的真传。奶奶很固执,她每一次都会说:“第一口必须给老祖宗先吃,然后才到我们吃!”为此,每次粽子出锅了,榨粉开榨了,五色糯米饭揭盖了,糍粑出灶了,无论是哪一样,她都会小心地盛上两碗,再倒半碗白酒,烧上一炷香举过头顶,跪地三拜。这样的仪式,雷打不动。偶尔,我们兄弟姐妹等不及了,偷偷地将黑乎乎的小手伸向诱人的小吃,奶奶总像是长了第三只眼一样,一巴掌便把我们的手打回。
“连先人都不敬重的人,能干成什么大事?”奶奶虽没读过书,但说话似乎都很在理。这句责骂的话语,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如今在母亲身上,有着奶奶的影子。后来,几天后的大年初一,我看到更多人身上有着母亲和奶奶的影子。
大年初一那天,我破天荒地跟随母亲去村里的祠堂祭祀。我们到时,天色尚早,但祠堂里外已挤满了村里的老老少少,轰鸣不绝的鞭炮声,说不出是喜庆还是沉重。因为人多,一次同时祭祀的只能有三户人家,我和母亲在祠堂外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待我们走进去,祠堂里烟雾缭绕,鼎炉上已插满香火、红烛,跳跃着红光。母亲打开篮子,一一摆上祭品。闲着无事,我仔细清点正在祭祀的五婶和二伯母所带来的祭品,肉类冥币水果糖饼酒水自不必说,还有粽子、米花糖、糍粑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没有说笑声,室内一屋子的人,人人虔诚地上香,或跪地或俯首三拜。
“那天你一定跟着三拜了,是吧!”考古专业的小伙子突然打断了我的回忆。
我愕然——竟让他给猜中了。
小伙子兴奋地说:“你说的就是你们骆越民族的稻作文化呀。知道‘骆越’两个字怎么解释吗?”
我摇头。小伙子也摇头:“亏你还是骆越人。”
“考古学上说,‘骆’的表层意义是‘鸟’,但其深层意义却是‘水稻’的代码,即最早的栽培稻‘糯’,‘越’的本字为‘戉’,是挖土的工具,‘骆越’就是用‘戉’种植水稻的民族。稻作是骆越民族的根,与稻作相关的祭祀也叫‘糯祭’,是骆越人最重要的祭祀。”小伙子滔滔不绝。
我听得迷糊了,或者说我根本没有用心听。我在想,这稻子跟女人怎么就联系在一起,成为文化了呢?
小伙子的高兴劲儿没有因为我的迷糊而减弱:“给你看个记载,或许就会明白了。”
一本厚厚的资料上,果真看到了几行小字:二月二播种祭土地神,三月三插秧祭始祖神“浦神”(龙母神),四月八农事结束洗犁耙祭牛魂,五月五求洪水止息祭龙神,六月六招稻魂祭稻神,七月十四丰收祭“娅王”。
“简单说,你们民族早些年赖以生存的是稻米,所以你们的祭祀是围绕着稻作进行,祭品当然是稻米了,而女人是祭品的制作者与传承人。”小伙子有些得意地说。
“稻米,女人,祭品的制作者与传承人。”我喃喃自语。那一刻,我想起了我的母亲、奶奶,还有家乡的女人们,她们在田间劳作的快乐,她们不厌其烦地在自己的“假日”里创造了一道道工序烦琐的小吃,她们为了美好的生活虔诚地祭拜着……
是的,女人就是稻米,彰显着无私中的伟大!
“总有一天,你一样也会学做各种稻米小吃!”小伙子眨巴着眼睛说。
我没有否定。
有一种滋味,或许出身低微却可以自成一家,在演变中不因各方冲击而消失,反倒越来越强大。我想,这或许是做一个稻米女人的意义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