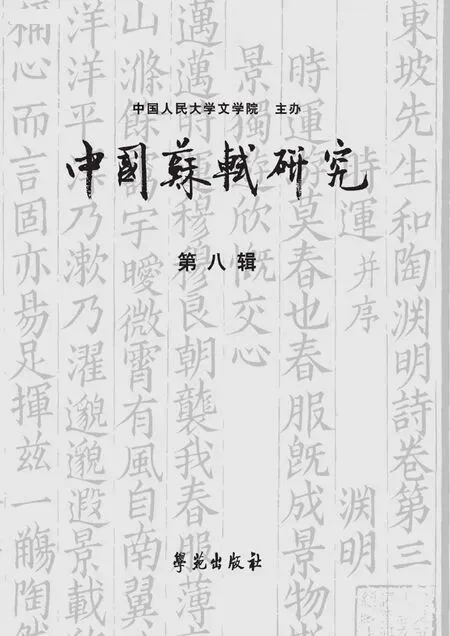苏轼隐逸词的情理结构
◇吴宇轩
仕与隐的关系一直是我国古代士大夫普遍思考的问题,也是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主题。中国的隐逸文化传统按其发展顺序大致可分为道隐、心隐、朝隐、林泉之隐、中隐、酒隐、壶天之隐七个阶段,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孔子。苏轼作为士大夫人格的典范,一生仕途坎坷,三次被贬,宦游十余年,对仕隐关系有独到的思考与理解,这种探索与思考于其词中随处可见,而且大多流露出隐逸情怀,可以称之为“隐逸词”。本文拟以苏轼的隐逸词为研究对象,以苏轼对仕隐关系的思考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其中的情理结构,探究苏轼对仕隐关系的处理方式及从中体现的人格境界,以期探究苏轼对仕隐关系的理解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独特性。
一、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隐逸与情理结构
干仕与隐逸一直是我国古代社会极为重要的两个概念,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语·泰伯》有云:“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是孔子对隐逸的看法,孔子也因为这类话而成为隐逸文化的理论先导。孔子是依据“正义原则”而提出“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这实际上是规定了一个客观标准。这一理论的提出富于现实实践性,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究其实质,孔门仁学依然是教人积极入世的,孔子提出的隐逸“并非要人避世,而是要人避开无道的政治,以保持人格的完善”。“道”的存在与否是人是否隐逸的决定性标准。中国隐逸文化还有另一种类型,这就是以庄子为理论先导而创立起来的依据“自由原则”的隐逸模式。庄子的隐逸理论主要是教人保持精神的独立与人格的自由,对人的“异化”进行反拨,其实质在于远离世事以保持心灵的不受侵扰。
仕隐关系是困扰古代士大夫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他们一方面无法否弃官场生活带来的功业和名利,另一方面深感仕宦生活对精神的束缚,因而常处在仕与隐的矛盾冲突中。汉唐时代的政治本体赋予士人极高的政治自信,他们充分相信政治本体,并对此有着深情的希望和强烈的乐感,渴望建功立业并且把外在的功业视作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盛唐时期诗歌积极向上、昂扬奋发的基调就是这种时代精神的充分体现。这在李白的诗中尤为典型,即便是面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的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坎坷现实,李白也依旧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对仕隐关系有独到的思考与理解。苏轼的许多词中都表现出他对官场生活和身外之物等外在价值评判系统的否定及对本真生活的向往,流露出隐逸情怀。而仔细分析这些词的情理结构不难发现,其词中的“理”往往能够被充分情感化,因而成为建构价值的方式。
情与理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一对基本概念,二者并非对立的关系。“情”是以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为基础而产生的最为原初意义上的情感,而“理”则是经过相当长一段历史实践后建立起来的富于合理性的价值观念。既然是富于合理性的价值观念,必然会经过绝大多数人的情感认同;一个被绝大多数人反对,且不能对人类总体存在与发展带来正面价值的观念则不能被称为“理”。在中国主流文化中,“理”本身即蕴含着情感的因素,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人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化应然之理为生命情感”。也只有在理性选择和情感体认两个维度上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才更为开放、有活力,而不会走向僵化。儒家文化提供的提高道德修养和人格境界的方式不是生硬地告诉人们几条具有正面价值的“理”,而是通过“化理为情”的方式让人对“理”进行充分的情感认同,从而内化为内在于人的生命情感。也只有这样,人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基于自己内心真实的情感,而并非是不得不做出的理性选择。《论语》中即有这样的例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篇》)人会因《诗》而兴起美好的情感,这是一种原初的情感;《礼》则是对人性心理的规范,是一种理性选择;如果人对其进行充分的情感体认并按照这种价值观念行事,就会达至审美人格,“成于乐”就是这种审美化的人格境界。与孔子思想一脉相承的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究其实质也是“化理为情”。“知”是一种理性选择,而“行”则是通过对“知”的充分体认后将心理行动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王氏‘知行合一’说的实质是要求提高人格境界,将人的理性与情感合为一体,把心理活动的行与社会实践的行合为一体”。
古典诗词中的很多作品都体现了情理结构,已经成为审美类型之一。情理结构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情”未能对“理”进行充分体认而表现出的情与理之间的张力,如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对人情的珍惜与热爱是为人所充分认同的“理”,而建功立业、保家卫国则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充分情感化的“理”,此诗在情与理之间的张力中表现出独有的艺术魅力。二是“情”对“理”进行了充分的体认并将其情感化,化为内在于人的情感状态,并据此建构价值。苏轼的绝大多数词都具有这个特点。
二、苏轼隐逸词情理结构的类型
苏轼对仕隐关系的思考贯穿生命始终,于隐逸词中多有体现。苏轼隐逸词的情理结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类型:“乌台诗案”前,主要体现为自由人格的彰显;而被贬黄州期间及后期,对仕隐关系的思考更加深入,体现为归于心理本体并建构起精神家园。其隐逸情怀是经过对仕隐关系的理性思考后,本真心灵和生命情感对隐逸之理充分体认和情感化的产物。
(一)“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自由人格的彰显
“乌台诗案”前,苏轼基本上还是“奋厉有当世志”的传统儒家士大夫的性格。然而,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外放杭州后,苏轼逐渐在词作中表露出自己对于仕隐关系的思考,试看: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虚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行香子·过七里滩》)
此词作于熙宁六年杭州任上。上片和过片通过细腻的笔触写出七里滩的美丽景色,虽是目之所及的真实情景,却能见出苏轼有一颗“民胞物与”、对自然深情体认的美好心灵,否则不会如此细腻地刻画七里滩的细节,因此这既是景,也是苏轼对自然、对生命的深情。之后笔锋一转,写道“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虚名”。这是经过对个体生命意义的理性思考后对功名利禄的否定。汉光武帝与严子陵抵足而眠的故事足以见出君臣之间的深情,然而即使是这样可贵的人情,最终也只落得“君臣一梦,今古虚名”,这就产生了浓厚的历史悲剧意识和价值悲剧意识。君臣关系、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这些外在于人的东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词的最后又回归到景的描写,但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景。经过这样一番对人生的理性思考后,这种理性逐渐向人的情感积淀,情感不断对这一“理”进行充分体认,因此才能达到“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的境界,这既是景,也是情,同时更是一种人格境界。
又如:
四大从来都遍满,此间风水何疑。故应为我发新诗。幽花香涧谷,寒藻舞沦漪。
借与玉川生两腋,天仙未必相思。还凭流水送人归。层巅余落日,草露已沾衣。(《临江仙·风水洞作》)
此词为苏轼杭州任上游风水洞有感而作,看似全词描写风水洞的美好风光,仔细读来却发现其中也暗含着思考仕隐的“情—理—情”内在理路。上片写景,让人读来仿佛置身仙境一般,美好的景色让苏轼流连忘返,因此面对“还凭流水送人归”的不得不离去的时刻,按照正常的思路应该会心生不舍之情。然而,苏轼之所以成其为苏轼,就是他总能以超旷洒脱的态度对待世事,而这种情感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是不断在理性思考人生意义的过程中理性向感情积淀,因而产生的一种更富于历史合理性的情感。因而苏轼面对不得不离去的美景,并未作伤心之态,而是说“层巅余落日,草露已沾衣”,与其说这是离开风水洞后看到了斜晖落日,感受到了草露沾衣,不如理解为更希望流水能够将他送到这样一个宁静平和、使人心旷神怡的情境中去。此时的情境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苏轼的心境。“层巅余落日,草露已沾衣”这两句化用自杜甫“层巅余落日,草蔓已多露”(《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所营造的情境却更容易让我们想到陶渊明诗中的很多场景,如“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这是陶渊明对自己隐逸生活的描写,苏轼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心灵诉求,正是因为其情感已经对隐逸之理进行了充分的情感体认,因此才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这种心境,苏轼笔下的情境正是他心境的最好反映。
最能体现苏轼对仕隐关系思考的是下面这首著名的词,其中“情—理—情”的内在理路也经历了两个完整的流程,具有典型性: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上片从“孤馆灯青”一直到“朝露漙漙”都是描写在前往密州的清晨所见之景,“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则转入对人生的思考:人生在世,起落、悲欢、离合数不胜数,而如果将有限的个体生命执着于这些外物,像今日这样奔波在仕途,那么人生就充满了不如意,因此苏轼否定了外在的事功。随后追忆往昔,开启了新一轮的情感生发与理性思考的流程。自己和弟弟苏辙初入仕途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而当时的自己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十分强烈,并且充满自信,认为“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经过之前理性思考的苏轼已不再把外在事功当作人生的目标,而是提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全新的价值建构方式,这就与“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格境界。“致君尧舜”实际上是对历史合理性的直接体认,这种思想依旧是承接汉唐时代对政治本体的巨大乐感和自信而来,是将人生的价值建立在外在事功上。而“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则是自由人格的彰显,它建立在心灵的自然而然、人格的自由上。这不同于孔子提出的“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亦非庄子提出的“逍遥游”。孔子的选择是基于社会现实的有道与否,而庄子的选择是以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游”作为最终目标。但苏轼的选择则是不给人生设定客观、具体的目标,是归于心理本体的自然而然。仕与隐都不再是根据客观现实而决定,正如苏轼在《灵璧张氏园亭记》中所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仕或隐,何时该仕,何时该隐,都是以自己的本真心灵作为评判标准。这样一来,这种全新的价值建构方式就不再是将人生价值建立在外在事物上,也不再是取决于客观现实,而是回归了内心,通过“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的最符合本真心灵、最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建立了价值。而于“闲处”过“优游卒岁,且斗尊前”的生活也绝非“酒宴歌席莫辞频”(晏殊《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的带有及时行乐思想的生活。在苏轼的世界里,生活的具体内容已不重要,他所真正热爱的是生活自身。而此词中的“情—理—情”经历了两次完整的流动过程,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苏轼的人格境界也就在情对理的不断体认中得以提高。
(二)归于心理本体,建构精神家园
苏轼黄州时期的词作不仅在数量上达到了巅峰,而且对人生诸多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思考,其中对仕隐关系的思考不在少数。如: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依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临江仙·夜归临皋》)
上片通过描写夜饮醉后,因家童睡下而无法归家的情景,开启了价值追询的过程。夜阑人静,苏轼一个人面对滔滔江水发出“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人生感慨。老子曾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老子》第十三章),而苏轼则感慨“此身非我有”。人处在各种束缚之中,身不由己,何时才能忘却纷扰的世事,过最本真、最自然而然的生活呢?经过这样一番思考后,苏轼看到的情景就是“夜阑风静縠纹平”,这不仅可以理解为真实的场景,更为重要的还是苏轼的内心世界,正是对外在价值评判体系的否弃让苏轼找到了失落的主体。“休把闲心随物态”(苏轼《定风波·咏红梅》),如果外物给心灵套上枷锁,那么人就会因为对外物的执着而丧失本真的心灵和自由的人格,苏轼否定了这种负面的生活。剥除外物的束缚,一颗本真的心灵便袒露出来,以这样一颗了无挂碍、自然而然的本真心灵面对这个世界,自然就会体会到“夜阑风静縠纹平”的情景。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则是这种本真生活方式的最好注脚。苏轼并非要乘一叶扁舟远离世事,而是要破除心灵栅栏,按照积淀了最多历史合理性的本真状态生活。苏轼自己曾在《雪堂记》中明确表示“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他并非要远离世事,而是要远离羁绊“本心”的“机心”,不为世间的沉浮荣辱、世俗机务所累。这不仅是否定外在价值评判体系,甚至是否定生活的具体内容,一切以内心的适足快意作为唯一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是从生活的自然而然达到了心灵的自然而然。只要“心闲”,那么“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雪堂记》)、“美恶在我,何与于物”(《答毕仲举二首》)。在苏轼看来,形式上归隐与否已经不再重要,只要拥有一颗纯粹本真的心灵,哪里都可以成为精神家园。因此,当郡守徐君猷听闻苏轼作此词,恐“州失罪人”而特意到苏轼家中查看时,看到的必然会是“子瞻鼻鼾如雷,犹未醒也”(叶梦得《避暑录话》)的场景。
苏轼虽然在词中多次表达归隐之愿,如“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浣溪沙·感旧》)、“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不如归去”(《减字木兰花·送东武令赵晦之》)、“读尽床头几卷书。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南乡子·自述》)、“独棹小舟归去,任烟波飘兀”(《好事近·湖上》),等等,然而“终老未践”,这是因为苏轼并非归于山林与世隔绝,而是归于心理,在本真的生活方式中找到归宿。苏轼词中经常提到“闲”字,如《行香子·述怀》:“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开头几句先描写夜朗风清、月下独酌的情景,进而展开对人生意义的理性思考,通过对功名利禄的否弃,提出本真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又如《蝶恋花·述怀》:“云水萦回溪上路。叠叠青山,环绕溪东注。月白沙汀翘宿鹭。更无一点尘来处。 溪叟相看私自语。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尊酒不空田百亩。归来分得闲中趣。”上片描写荆溪的美景,青山环绕、溪水东流,月照鹭洲、上下一白,这样的景色让置身其中的苏轼怡然自得,而在一派不染纤尘、宛如仙境的情景中,对自然山水的细腻感知与亲切体认便导向了理性思考与价值追询,“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就是对追求世俗功名的不合理生活状态的否定。苏轼真正向往的是归隐田园、有酒盈樽、闲中有趣的本真生活。此词亦呈现出“情—理—情”的内在理路。又如《满庭芳》(归去来兮)下片:“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翦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既然“人生底事,来往如梭”,荣辱穷达、起落沉浮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烟消云散,那么又何苦汲汲营营呢?不如用一颗闲适之心按照心灵和生命的应然状态行事。正如苏轼自己所说“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南歌子》),苏轼的“闲”绝非无所事事,也并非刻意远离世事的“身闲”,而是“心闲”,也即否弃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等世俗的评判标准和价值观念,冲破外物对人心灵与精神的束缚,用一颗本真的心灵行自然而然之事,达至人生的审美境界。
情理结构只是诗词创作的一种内在理路,并非一定要遵循“情—理—情”的固定的写作模式,如: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馀龄。(《江城子》)
此词不能准确区分出哪部分是情,哪部分是理,而是情感对应然之理充分体认之后浑融一体。正是有了对田园生活的充分认同和对归隐之理的充分体认,苏轼在谪居黄州期间才能做到怡然自适。词中虽然没有出现价值建构的理性话语,但苏轼渔樵耕读的本真生活以及此词中对田园生活的内心适意都是建立在对人生意义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外在的功名利禄、事业功勋对自我价值的建构毫无用处,甚至反而成为一种牵绊和阻碍。苏轼否定官场蝇营狗苟、争名夺利的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充分认同并且一直追询不为外物所累的本真生活方式。词中的情景描写与情感流动都有理性思考蕴含其中,是涵容了价值建构的情感表达。这种表达方式在苏轼词中很常见,如黄州时期所作的一组《渔父词》:
渔父饮,谁家去。鱼蟹一时分付。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
渔父醉,蓑衣舞。醉里却寻归路。轻舟短棹任斜横,醒后不知何处。
渔父醒,春江午。梦断落花飞絮。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
渔父笑,轻鸥举。漠漠一江风雨。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
苏轼通过对渔父饮、醉、醒、笑四种有代表性的生活方式的描写,勾勒了一幅渔父生活的图景。渔父之饮,不计多少,以醉为期,交付给酒家的鱼蟹和酒家提供的酒都不计较钱数的多少,哪里像官场之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都要斤斤计较。渔父之醉,醉卧小舟,任其飘荡,万事不挂碍于心。渔父之醒,不仅是酒醒,更是对人事的清醒,世俗之人被名缰利锁束缚,执迷不醒,何其可笑。渔父之笑,笑江边骑马的官场中人,为功名利禄疲劳奔波,为声名富贵丧失自由,不如我乘一叶扁舟无求于人,悠然自得。渔父以心灵的自适与纯粹作为行事的唯一依据,不被外物牵累,也无求于人,永远都过着逍遥自适的生活。苏轼对渔父生活状态的描写并非单纯的情景描写,其中蕴含着对渔父纯然无机的心灵和潇洒快意的生活方式的充分情感体认。这不仅仅是苏轼眼见之景,更是苏轼内心中真正向往的生活。没有理性话语表达,纯任情感意绪流动,沉浸在当下情景中,情感体验化为审美化的生命感受,具有了本体性意味,情与理在这一过程中融为一体,密不可分。
三、苏轼隐逸词的情理结构与精神家园
情理结构不仅是价值建构的方式,深刻、典型的情理结构更能为人提供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中国人在没有外在超越的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境界来实现内向超越,而这终将归向人性心理,因此情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结构。
苏轼于嘉祐四年出川,之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家乡,其词中多有体现。如:“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醉落魄·离京口作》)“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醉落魄·席上呈元素》)“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临江仙·送王缄》)这不仅是漂泊无定的感慨,更是心灵找不到归宿的哀伤。然而这种基于生命原初情感的悲剧感在对人生的理性思考和价值追索中实现了审美超越,最终实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的以心理本体作为精神家园的审美化境界,而不再执着于外在形式上的家乡。如《临江仙》上片:“我劝髯张归去好,从来自己忘情。尘心消尽道心平。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当世俗之心消尽,悟道之心不为外物扰乱之时,便会觉得“江南与塞北,何处不堪行”。正是因为专注于内心,家乡就成了外在形式。
苏轼对仕隐关系的思考同样可以纳入对精神家园的追索中来,正是因为“心隐”“心闲”,因此不必拘牵于外在形式。苏轼一生并未真正归隐,但由于对隐逸之理和本真生活的充分情感化,已经将其化为内在的生命情感,因此在朝为官也好、宦游各地也罢,都能用审美的态度观照生活。归于心理本体,生活也就成为纯粹的审美体验和情感状态。
在找寻精神家园方面,孟浩然的诗十分典型。然而孟浩然与苏轼不同,他一生都处在仕与隐的矛盾冲突中,有些诗表达强烈的用世之心,如“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临洞庭湖赠张丞相》),“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自浔阳泛舟经明海》);有的诗又于明山丽水、清风明月中找寻心灵归宿与精神家园,典型的如“之子期宿来,孤琴候萝径”(《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暝还归骑下,萝月映深溪”(《登望楚山最高顶》)都是以具体的地点或处所象征心灵的归宿。但每每读孟浩然的山水诗,总感觉到背后还站着一位将人生意义寄托于外在功业的诗人,因此诗中的山水景物虽美,其情感却总让人感觉“隔了一层”,正是因为他未能完全摆脱外在评判体系的束缚。汉唐时期是政治本体时期,士人对仕途充满自信,认为外在事功是评判自己是否成功的标准。盛唐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给了孟浩然过高的期许,所以他始终执着于建功立业。苏轼则不同。首先宋代已全然不同于盛唐,政治本体自中晚唐逐渐瓦解后,外在功业就不再是士人的精神归宿;文化本体逐渐建立,士人把目光从现实政治转向世事人生,越来越注重个体的感性生活,追询个体生命全新的意义。而且苏轼是一位洞悉世事人生的智者,他选择了本真的生活,不但超越了功名利禄等外在标准对心灵与精神的束缚,更是不为生活设定目标,对生活进行审美化体验,达到了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的生命审美化的最高境界。
苏轼词中的情理结构往往表现为“情”对“理”充分体认后的浑融一体,而孟浩然诗中的情理结构则表现为“情”未能对“理”充分情感化而产生二者间的张力。孟浩然虽然试图投身于自然山水中以寻求精神家园和心理归宿,却是一直在追询,而并未真正找到归宿。山水之于苏轼和孟浩然的意义也是全然不同的。苏轼是用一种“民胞物与”的态度观照自然,人与自然是平等的关系,他在自然中关注的是审美主体内心的适足快意,人生的意义都在当下的生命活动和情感体验中,无须再追求身外之物,更不必为人生设立目标。但自然对孟浩然来说更像是暂时消解悲剧意识的场所,当他因仕途不得意而产生悲剧意识时,会选择投身自然,但自然并不能帮助他超越悲剧意识,因此诗句背后站着那个内心仍然执着功业的诗人。
怀着对政治本体的强烈自信和乐感,盛唐诗人几乎很难真正做到像苏轼一样以当下最鲜活的生命状态和情感体验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准绳,就连李白这样终身不愿参加科举考试的浪漫洒脱的性格其实仍然是以用世之心为底色。因此,他们虽然在诗中以自然、酒、仙境等方式暂时消解了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而产生的悲剧意识,却终究未能真正对其进行超越。盛唐给予他们巨大的乐感和自信,同时更决定了他们一生都会将生命的意义建立在功名利禄等外在评判标准上而无法真正获得心灵解放与精神自由。而生活在文化本体时代的苏轼对仕隐关系的思考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一环,他通过生命实践将心灵视为评判与衡量事物的标准,对事物不作功利性考量,而进行审美化观照。这样一来,仕与隐都成为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选择。正如他在《书李简夫诗集后》所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不必为功名利禄而仕进,也不必为孤高自标而隐退,该做官则做官,该归田即归田,一切都是以内心作为标准,归于心理本体,生活就完全成了纯粹的审美活动。苏轼彻底解决了困扰士大夫的仕隐矛盾,达到了审美人生这一最高境界,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典范意义。
注
释
[1] 参见冷成金《隐士与解脱》,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2]参见刘方《宋型文化与宋代美学精神》,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八章《隐逸的两种类型》。
[3]冷成金《论语的精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4]引自冷成金先生课堂讲义。
[5]王宗堂、邹同庆《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
[6]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7]参看爱课程网—冷成金《唐诗宋词的审美类型》—第四讲《情理结构与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