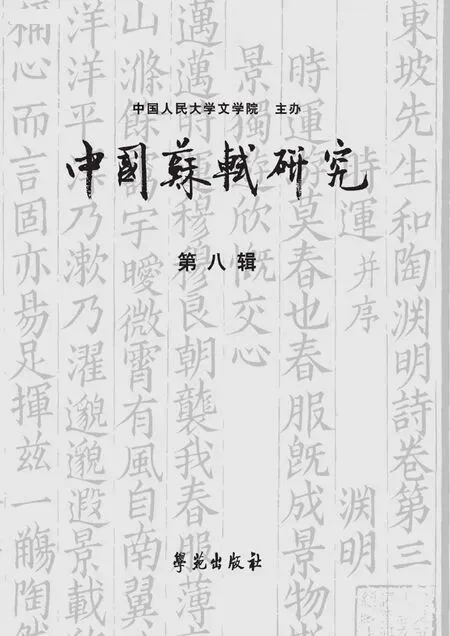苏轼诗歌悲剧意识的消解和超越方式
——兼及苏轼诗歌豪放风格成因分析
◇张永宽
苏轼是中国“豪放派”文学中首屈一指的大家,其豪放超脱、旷达不羁由来有因,是在经历悲惨的人生命运、面对人生困境之时,对内心兴起的悲剧意识进行消解和超越而形成的。苏轼诗中流露着老病缠身、人生苦短的生命悲剧意识,德位不匹、历史虚无的历史悲剧意识,飘零无定、亲友乖隔的宦游悲剧意识,政敌迫害、壮志不酬的政治悲剧意识,人生如梦、世界泡影的价值悲剧意识,暴露了人生和世界的悲剧真相。但他并未因此颓废沉沦,而是积极突围,对悲剧意识进行消解和超越,用旷达和豪迈反抗人生悲剧,成为中国文学中一颗耀眼的明星。本文对苏轼诗中悲剧意识的几种超越方式展开详细论述。
一、向世间感性生活沉入
儒家文化鲜明体现了悲剧意识不注重外在超越的一面,即不依赖上帝、天国和居于现象界之上的先验理念世界,而注重现实、世俗的人世间及其日常的感性生活,在“此世间”寻找价值和超越。常见的就是渗透于文学中的追求现世生活甚至及时行乐的思想。物质生活有时能给人带来肉体快乐与精神愉悦的双重效果,暂时消除心理痛感和不良情绪,从而缓解意志与现实之间紧张的压力。疾病缠身,时感生命短暂、世事无常的苏轼也不例外。
(一)饮酒
饮酒是包括苏轼在内很多文人的重要行乐方式。“顾惭桑榆迫,岂厌诗酒娱。”(《和陶赠羊长史》)“在时光飘忽、人生苦短的死之悲的背景下,在对人生之乐的追求里,酒的位置一下子就重要起来。”久而久之,酒便获得了某种文化品格,饮酒成了摆脱政治现实、消解悲剧意识的一种物质手段,体现了文人的独立人格,不少诗文名篇正是乘着酒兴得以完成,或是直接为赞美酒的“品德”而作。
苏轼的日常生活离不开酒,“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和陶饮酒二十首》),他不仅爱喝酒,会酿酒,还写过不少诗文来阐述酒的文化内涵和现实功用。《酒隐赋》、《浊醪有妙理赋》两文将酒奉为与天工相并的自然神物,系统论述了酒的功用:酒不仅可以远害全身,躲避政治追杀,具有了隐逸的文化品格,“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醉”;还与大道相通,“杳冥似道”,是知心体道的媒介,借酒得以“识心之正”;更重要的是借助酒可以“内全其天,外寓于酒”,暂托酒以排意,“酣羲皇之真味,反太初之至乐”,使胸中洞然无悲。这与“谁言大道远,正赖三杯通”(《和陶饮酒二十首》)表达的是同一观点。
酒的这种功用,足以用来排遣现世的苦痛。苏轼常常借酒消愁:“白酒无声滑泻油,醉行堤上散吾愁。”(《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逝将江湖去,浮我五石樽。”(《复次前韵谢赵景贶……》)“使我有名全是酒,从他作病且忘忧。”(《次韵王定国得晋卿酒相留夜饮》)喝酒解除心灵痛苦所带来的愉悦远远大于喝酒的弊端,一向重视养生的苏轼甚至连生命健康也不顾了。
在这里,酒是作为对生命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而出现的。酒可以使人忘记时间的流逝,消解时光飞逝带给人的生命焦虑,甚至将焦虑转化成欢乐:“簿书常苦百忧集,杯酒今应一笑开。”(《送钱穆父出守越州二首》)酒是可以抵抗衰老的妙药:“强镊霜须簪彩胜,苍颜得酒尚能韶。”(《叶公秉王仲至见和次韵答之》)《蜜酒歌》《薄薄酒二首》《新酿桂酒》则通篇写酒之美,酒之真,表达饮酒之趣、饮酒之乐。特别是《薄薄酒二首(其一)》似乎已将饮酒上升为生命的本体性的真实存在了:
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襦玉柙万人相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都两忘。
此诗体现了历史悲剧意识、价值悲剧意识及其超越和消解。“五更待漏”是指帝王将相的政治生活,“珠襦玉柙”是指荣华富贵,这些虚华的事物在苏轼看来都是无价值的,即使死后足以流芳后世的作为“经国之大业”的文章也同样是无价值的,二者都比不上北窗高卧、悬鹑负日。“夷齐盗跖俱亡羊”化用《庄子》中典故,将圣贤伯夷、叔齐代表的正面价值和恶人盗跖代表的负面价值全部否定,将所有的意义全都聚焦于眼前一杯美酒,人世的一切是非荣辱都比不上把盏一醉。
酒消解悲剧意识的心理机制是“醉忘”,当人们进入醉境时,其精神常混沌一片,立足于思虑之上的人生一切束缚和失意全都自动解体,生命衰老、历史虚无、人生空漠、漂泊羁旅等悲剧意识以及贤愚是非之辨,全都被消解了。“醉时万虑一扫空”(《孔毅父以诗戒饮酒……》)所描写的就正是无思无虑这种“醉忘”的精神体验,而“笑谈万事真何有,一时付与东岩酒”(《送张嘉州》)则肯定了酒在虚幻人的世间的实体性存在及其意义。
醉酒消解悲剧意识的另一心理机制是“颓然醉里得全浑”(《惠守詹君见和复次韵》)。在“全浑”状态中,一切束缚被挣开,一切痛苦的根源被消灭;精神彻底得到解放,复归原始自然的体验,获得了与世界本体融合的最高的欢乐,在极度的自由与开放中尽情展示生命的活力,用苏轼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醉白堂记》)。“醉里未知谁得丧”(《与潘三失解后饮酒》),对人世间得失荣辱不作感知,更不作区别。这既是“醉忘”也是“全浑”,都是对悲剧意识的消解。
在这种“全浑”的自由中,个体身心全方位解放,言行举止皆不受世俗礼法约束,也没有得失利害的考量,纯然是自由而行、自由而止的“醉而狂”。因此,醉酒与中国狷狂文化往往联系在一起,狷狂者也大多是爱酒者,“醉后粗狂胆满躯”(《刁景纯席上和谢生二首》)正是狂者形象的最佳写照。苏轼也时常借酒“聊发少年狂”,大醉之后亦是狂人,“坐睡落巾帻”,“蓬发不暇帻”(《岐亭五首》);醉后言语、作诗文也不顾后果,“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二)涵泳日常生活
苏轼认为,“一物有一物之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超然台记》)。只要以审美的眼光审视世界,生活中一切皆有可乐,“行住坐卧,饮食语默,具足众妙”(《观妙堂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宝绘堂记》)。苏轼对待日常生活总不乏审美的态度,凡事以审美的态度欣赏,平凡的日常生活就获得了超越它自身的价值。
人一诞生就置身于他的生存境域中,一开始就循环于他的生存方式中,生活由于见惯而对于他变得“平常”甚至乏味,不能勾起他的好奇心和“惊异感”,他已经不能从日常生活中“瞥见”“大道”,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世界已经向他关闭。审美的生活则不同,它是一种诗意的生活。审美的生存者处于醒悟和澄明状态中,世界对他敞开,大道向他显现,因此他始终保持着对生活世界的新鲜感,生活中的点滴小事都是通达“至乐”境界的途径。以审美的态度欣赏生活,尺幅小景亦包含着大千世界,门前覆砌茂草也能观大化流行之生生不息,盆池数尾小鱼亦能知万物自得之意。比如睡眠,本是人类例行的日常行为,苏轼却从其中悟出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在《游惠山》一诗中写道:“吾生眠食耳,一饱万想灭。”睡眠和饮食似乎成了人生的得意追求,成了灭绝妄念、消解悲剧意识的重要媒介。他还特意写诗描述身心两忘、烦恼消尽的睡眠体验,如《谪居三适三首·午窗坐睡》:
蒲团盘两膝,竹几阁双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身心两不见,息息安且久。睡蛇本亦无,何用钩与手。神凝疑夜禅,体适剧卯酒。我生有定数,禄尽空余寿。枯杨下飞花,膏泽回衰朽。谓我此为觉,物至了不受。谓我今方梦,此心初不垢。非梦亦非觉,请问希夷叟。
苏轼的睡美之乐一方面与他多病经常闭门不出有关,但更有文化上的渊源,他的睡美之乐受陶渊明影响。《晋书·陶潜传》:“尝言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放朝三日君恩重,睡美不知身在何。”(《次韵杨褒早春》)睡眠是感觉器官的暂时关闭,是自我意识的暂时丧失,时间和空间消失了,因而整个现象界也消失了,只剩下了杂乱无章、随机拼凑的梦境,“身心两不见,息息安且久”描述的就是这种退出现象界的睡眠体验。因此,与现象界相关的人世的一切不如意,以及人间的是非善恶之辨等,社会强加给人的一切东西,无论好的坏的,全都消失了。此时的意识主体彻底达到无意识界,完全不受外物的干扰,“物至了不受”“此心初不垢”。苏轼自己对睡眠的功用也有系统的总结,在《睡乡记》中明白阐述了对睡眠的看法:“昏然不生七情,茫然不交万事,荡然不知天地日月”;睡乡之民“其人安恬舒适,无疾痛札疠”,不知得失利害。
美食也是苏轼常常借来消遣苦闷的方式。他在贬谪期间生活上常常陷入困窘,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何谈其他活动。延君寿《老生常谈》中谈到苏轼的饥馑之状与落魄中的孤傲:“人生太穷,至于饮食不继,虽说该去忍饥读书,然枵腹高吟,肚里如何支架得住。偶忆东坡诗绝句云:‘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只鸡斗酒定膰吾。’夫以东坡之豪贤,饿到十来天,也想人家馈东西吃,而真率之气,妙能纵笔写出。”每当暂得美食,苏轼便乐不可支,品尝之余还要写在诗文中,表现美食带给人的愉悦感。如:
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尝滟玉蛆。暂借垂莲十分盏,一浇空腹五车书。青浮卵碗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淘》)
梦回闻雨声,喜我菜甲长。平明江路湿,并岸飞两桨。天公真富有,膏乳泻黄壤。霜根一蕃滋,风叶渐俯仰。未任筐筥载,已作杯案想。艰难生理窄,一味敢专飨。小摘饭山僧,清安寄真赏。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白菘类羔豚,冒土出蹯掌。谁能视火候,小灶当自养。(《雨后行菜圃》)
此二诗典型地体现了宋诗的日常化特征。苏轼极其懂得以审美的眼光品味日常生活的艺术生存方式,在其笔下,无事不可入诗,无物不可为诗材,平凡的饮食、喝茶等琐屑之事都具有非同寻常的蕴味。对平凡日常生活细节的反复吟咏恰好证明了宋代个体意识的高涨,以及日常生活的发现。汉唐朝代宏大的政治本体将人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遮蔽了,人们大多关注着外在的政治功利而很少注视与自身切近的日常生活,多注重参与政治化的集体活动而忽略了日常生活的本真意义。魏晋以来人的个体意识觉醒,到了中晩唐尤其宋代,切近的日常生活也被发现,进入了文学的书写范围,这是宋代文化了不起的进步,苏轼诗是这方面的代表。第一首诗的构成要素除了酒,还有槐芽饼、藿叶鱼等“俗不可耐”的事物,全诗都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第二首诗亦是由菜圃小菜等微不足道的事物构成。这些在汉唐时代很难“载道”和入诗,因为当时所谓“道”是高高在上的与政治相关的宏大事物;只有在宋代,在苏轼那里,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事物才因日常生活的被发现而进入价值领域,“小摘饭山僧,清安寄真赏”,“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又把闲暇时光之饮酒吃饭及其“醉”“饱”等生理体验上升为“真事业”。
日常生活的发现及其进入价值领域具有重大的意义。日常生活的审美欣赏对悲剧意识具有重大的消解和超越作用。日常生活之乐是纯粹的生命乐趣,是对生命本身的观摩和体验,抒情主体一旦进入敞开着的纯粹的生活世界,那么政治上的失意、生命流逝之悲、流离颠沛之劳累、人生世界的空漠之感,将全被涤荡净尽。
二、自然山水与天地境界
向自然山水中融入,借山水化其郁结,也是悲剧意识的重要消解方式。在对自然山水的俯察仰观中体味天地大道,消融自我意识,即庄子所说“忘我”“丧我”“忘身”,从而进入忘掉生死、“不知老之将至”、物我合一、与天地同化的心灵状态,达至“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天地境界(又作审美境界)“表现为一己身心与自然、宇宙相沟通、交流、融解、认同、合一的神秘经验”,“它是泯灭了主客体之分的审美本体”,是人与自然的合一。
(一)人的自然化
人的自然化一层意思是“把自然景物作为欣赏、欢娱的对象,栽花养草、游山玩水、乐于景观、投身于大自然中,似乎与它合为一体”。自然不仅包括罕无人迹、幽僻清冷的荒野,也包括经人类改造过、富有人文气息的苑囿田园等。
落魄文人和仕宦失意者常常以自然山水、荒野田园为寄托和排遣,宦途显达者也不例外。究其根源,人类诞生于自然,在漫长的原始时期,自然一直是人类的家园。人类虽然从自然荒野中走出,建构了人群聚集的城市,但与自然山水比起来,城市是人类的异乡,自然仍是人类的故乡,人类有一种回归故乡的原始冲动。自然是作为城市的对立面存在的,它所代表的心灵原始自由状态也与城市世俗文明强加于人的诸种悲苦压抑的心灵状态相对。后者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对人类的心灵产生某种程度的异化作用,这是人类文明自身发展的必然内在缺陷。只有回归自然,才能解脱心灵苦痛。自然山水是抵消文明异化作用的解毒剂,人的自然化对人类的健康发展而言是应当和必要的,这也是自然山水能够化解悲剧意识的关键所在。
苏轼在悲苦之际,常常将自己投入山水之间,融解在自然山水里,借天地自然之大美排遣苦闷抑郁。试看被贬海南时的《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
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诗中有鲜明的自我形象,这个“我”行居宇宙之内,在天地之间流连徜徉,仰观俯察。“四州环一岛……但见积水空”这几句构造了异常辽阔的物理空间,这个空间浩渺无垠,使诗人感到自身微弱渺小,顿生途穷末路之悲,这是由于诗人“执着生计,梗塞未通”,“尚拘泥于现实,未求得解脱”。但这个空间同时又磅礴壮美、充塞天地,这种壮美使诗人悲极生乐,在极度的迷茫困惑中获得解脱和超越:“眇观大瀛……永啸来天风。”苏轼在此以宇宙视角俯观个体人生,将自然历史、个人遭际“放到一个更大甚至无穷的参照系中去考察,随着参照系的无限扩大,具体事物的价值和意义就缩小,以致可以忽略不计”,泯灭了万事万物相互对待的区分与差别,成与败、荣与辱、雌与雄都在心灵的“力场”中浑然齐一,最终“幽怀破散”,完成了超越。诗的最后几句表现了获得解脱后心灵的陶醉和乐状态,此刻诗人已完全融化在宇宙自然中:千山仿佛跃动的鳞甲,天地间处处充溢着生命的活力,万谷散发着风雨悦耳的奏鸣,仿佛九天仙乐播扬人世;诗人沉浸于自然呈现的美的外观中,陶醉于对自然事物形式化的审美中,身心节律与自然节律齐鸣协奏、呼应合一,刹那间原本可怕的自然力量获得生动的诗意,世界完全揭开了遮掩的面纱,美彻底向诗人显现了。
人的自然化最终导致以自然为本体和归宿,即情感心理指向自然,将所有的情感收束在自然中,把自然当作实在的价值归依。这是人向自然融入后的必然结果。当政治权位、功名利禄、官场倾轧等一切浮华事物失去意义后,当人面临价值缺失、无所归依的精神状态时,宇宙自然为人提供了可供憩息的归宿地和价值场,人生在了然无味之际突然重新发现了乐趣,在同宇宙自然的浑同冥合中体天地大道,这就是《庄子·天道》篇所说的“天乐”。人的自然化既有人向宇宙自然的亲近、靠拢和融入,也指情感心理上向宇宙自然的归依,否则无法融入宇宙自然,觉悟和显现天地之美。这种将所有心理情感归于自然的写法,似乎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在苏诗中很常见。再如《九日次定国韵》,开头与中间全是写历史虚无、世界泡影、人生空漠、政治浮华等种种悲剧意识,诗尾归于宇宙自然、丘壑田园:“北山有云根,寸田自可耰。会当无何乡,同作逍遥游。”
自然山水能够使人忘掉死亡的忧虑感、价值的空漠感等悲剧意识,内在机制在于它能够使人暂时忘掉自我。在对自然的直观审美中,在那种主客体不分的状态下,审美主体摆脱了意志的束缚,上升为纯粹的不带意志的,“栖息于、沉浸于眼前对象的亲切观审中,超然于该对象和任何其他对象的关系之外”,“自失于对象之中了,忘记了他的个体,忘记了他的意志”。在观审中主客体都消失、融合了,认识不但处于时间、空间之外,而且既不用感性,也不用理性。“他已是认识的主体,纯粹的、无意志的、无痛苦的、无时间的主体……当它完全浸沉于被直观的对象时,也就成为这对象的自身了。”在自失之中,那“永远寻求而又永远不可得的安宁就会在转眼之间自动的光临,而我们也就得到十足的怡悦”。所以,大自然才可以净化人的心灵,洗去一切苦闷,消解悲剧意识。
(二)以象观道,乐天知命
人具有理性能力,在对宇宙自然的形式化审美过程中,往往能够突破事物美的表象,捕捉其背后的本质,这美的表象的本质即造物者;这种造物者并非实存,而是生生不息、无形无象的虚灵大道。万事万物都是大道一体运作过程中的产物,都是大道的“遗迹”,有形事物都是短暂、有限的,念念迁变,刹那即逝;只有大道是稳定、永恒、无限的。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将目光投注在大道,总能看到繁华消歇背后的永恒本体,不会因有限而短暂的事物而悲伤。正如《庄子·田子方》所说:“天下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肢百体将为污垢而死生终始将如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自同于大道,就能进入天地境界,不怨不怒,不悲不喜,不忧不惧,体道顺化,乐天知命。
苏轼常常通过反思导致人生痛苦的现实人生社会现象,了悟世间万事多变、短暂的表象本质,直达导致这些表象的“道”或“理”,消解人生痛苦。苏轼的“道”或“理”并非超验的形而上学概念,而是亲近日常生活和指导现实人生的。如《安国寺浴》写自己为消除衰病苦恼,“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静息跌坐,临竹参禅。这是在向自然融入,在自然中体“道”、悟“理”,最终获得解悟和解脱,以与大化冥合为一,“忘净秽”“洗荣辱”,挣开一切人世烦恼因缘,完成心灵的内在超越。再看他晚年谪居儋州的《和陶游斜川正月五日与儿子过出游作》:
谪居澹无事,何异老且休。虽过靖节年,未失斜川游。春江绿未波,人卧船自流。我本无所适,泛泛随鸣鸥。中流遇洑洄,舍舟步层丘。有口可与饮,何必逢我俦。过子诗似翁,我唱儿辄酬。未知陶彭泽,颇有此乐不。问点尔何如,不与圣同忧。问翁何所笑,不为由与求。
这首诗更是遇物顺化、体道明理、乐天知命的体现。自我意识把外在世界客体化,人的意志与自然的意志就割开、分裂了,就会发生冲突,如死亡意识。因为有自我意识存在,生死才成为问题,死亡才令人恐惧忧虑。如果看透了个体化原理,穿过万物的表象,直达万物的本质,即生生不息而又毁生不止的生命意志,就与天地大道统一了。无论生与死,在他看来都是大道运作的过程,生的必然结局是死,死又意味着另一物的新生,生死只是事物之间的相互转化。他“以道眼观物”,从大道而非自我意识的角度看待生死,知生灭之无常、生死都是顺化,不因一物死生而悲喜,“无所谓怕死不怕死”,对自己的死不会悲伤,对生死已无所芥蒂,因而不受死的威胁。晚年的苏轼已尝遍人生百味,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天地境界,不受生命衰老、死亡和时间流逝之悲的困扰,因此虽垂暮流放蛮荒,仍不失山水悠游之乐。对待生死和一切事务均不再有“我执”,那种以物从我、顺我的固执的“我心”已消泯,取而代之的是与物曲折、无所适而无所不适的泛泛大道之“心”,真正做到“无意,无必,无固,无我”。“我本无所适,泛泛随鸣鸥”是对这种境界的自况,因此中流遇洄便舍舟步行,不必效穷途之哭;饮酒无伴便把盏自酌,“何必逢我俦”。结尾借孔子风乎舞雩再次肯定这种向自然融入、无所不适的天地境界。其心灵和意志已自同于大道造化、天地万物,不再受现象界困扰,遇物无伤,逍遥无待,不与穷达俱存亡,达到了绝待的自由意志。
《老子》第十三章云:“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即吾无身,吾何以有患?”“有身”便为生老病死、贪嗔痴怨提供了受体,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烦”和“畏”的人生基本现实情态。初生赤子,虽有形体,却无“我心”,虽生不知其生,有死而不忧其死,不知名位权禄之厚、声色犬马之乐、穷通贫贱之别,无知无欲,浑然与宇宙同体。清净如水的人之本心随着现象界经验的浸染,在获得文化知识和生存经验的同时,也被人世的贪嗔痴怨、爱恶取予、聚散离别所苦。观道察理,回归本心,浑然与物同体,追求天地境界,其实与饮酒、睡眠一样,都是为了暂时清空从赤子到成年这漫长过程中积压在人心中的负面经验,甚至一切经验,达到无欲界甚至无意识界。这不是与木石禽兽一般的无知无识无欲,而是有意识的主动修为。处于天地境界的苏轼,对现象界的无常已能做到动静不惊,对人世的得失荣辱无所挂心,陶醉于知天之乐中。他已对生活的终极目的无所驻心,“思我无所思”(《和陶移居二首》),“往来付造物,未用相招麾”(《和陶还旧居》),只是以不喜亦不惧的心态悠游世间,纵浪大化。
三、“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
苏轼时常对历史、人生、人世和世界整体都进行怀疑和否定,历史虚无,人生无价值、无意义,世界假有而不实,彻底将人生和世界的悲剧性暴露在人的面前,但这并非结束。苏轼在价值虚无、人生空漠之际,并未彻底向人生的悲剧投降,而是在绝无价值之处建立起价值,完成对悲剧意识的超越,这就是“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向空而有”建立在人的自足性基础之上,与人的自足性是统一的,同时人的自足性也是悲剧意识的超越方式之一。
(一)人的自足性
人具有自证能力,通过自证建构价值。“自证是不依靠宇宙自然和外在社会条件或是对之否定而确立价值,‘空而有’是在空的基础上通过对自然或人事的体认而建立价值,其本质仍是自我寻找式自证。”这种自证能力决定了人具有无待的自足性,二者是二而一的。“人的‘自足性’是指人自身的价值完全依靠自己建立,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困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价值既不是遥不可及,也不依赖他人或外在的上帝天国,纯由自我一己建立;即使在一无依傍的情况下,依然能依靠自我内在的自足性,建构起本真的价值。苏轼晚年在《迁居》一诗中有“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之语,正是对个体无待的自足性的体现。再如《和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当欢有余乐,在戚亦颓然。渊明得此理,安处故有年。嗟我与先生,所赋良奇偏。人间少宜适,惟有归耘田。我昔堕轩冕,毫厘真市廛。困来卧重裀,忧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宁当出怨句,惨惨如孤烟。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
诗题点明是以抒发内心哀怨为主题,“嗟我与先生,所赋良奇偏”亦是说自己与官场不合,“我昔堕轩冕……忧愧自不眠”表达对出仕的自悔愧疚之意,接着写被贬的贫困,突出政治失意之悲与人生的窘态。但结尾又对此完成了超越,肯定了陶渊明和他所代表的隐逸的价值。苏轼赞美隐逸并表达隐逸之思的诗很多。与其说隐逸是对政治和社会的逃避,不如说是对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的无待。隐者最大的特点在于个体的价值不需要官场、社会承认,而建立于内心,即使遁迹山林园野,仍能逍遥自任,即使寂寂无名,仍能在个人化的自由生活中悠然自得。清冷孤寂的山野生活在世人看来是难以忍受的,在隐者眼中却是充满活泼生气的;没世而名不称于世在儒者看来是令人忧惧的,在隐者眼中名利却是妨碍心灵自由的重负。隐者抛开了社会性存在,处于对社会的决然无待。“宁当出怨句,惨惨如孤烟。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是对官场政治的否定,是对荣华富贵的拒斥;朝廷是错误的,新党是不贤的,唯有陶渊明那种隐居以求志、“但使愿无违”是正确的,唯有自身“隐居亦何乐,素志庶可求”是正确的。诗人的政见对否、贤愚与否、有罪与否完全不依赖朝廷和官场的裁决,而是取决于内心对仁的追求、对道的固守;苏轼推崇渊明之贤,亦是在自表心志。此诗充分体现了诗人主体精神的自证能力和对政治无待的自足性。
苏轼始终都怀有用世济民的理想,但理想的实现与否已经无关朝廷是否重用他,无关皇帝是否圣明。于海南贬所,《借前韵贺子由生第四孙斗老》写“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高抬人伦之乐,贬低功名利禄,告诫子孙“不须富文章”,“但令强筋骨,可以耕衍沃”便足矣。政治已然成为人生重负,“功名正自妨行乐”(《和孙莘老次韵》),唯有脱离官场,才能获得身心的轻逸自由。
(二)向空而有
苏轼的哲学思想融合了儒释道三家,其思想虽然在消极处时时体现出佛家的空幻思想和道家的厌世情绪,但对人生价值的怀疑、对世界真实性的否定并不是苏轼思想的全部,在怀疑此在人生和否定世界之后,他总又要回到此在人生中和此在依寓其中的世界之内。如《九日次定国韵》:
朝菌无晦朔,蟪蛄疑春秋。南柯已一世,我眠未转头。仙人视吾曹,何异蜂蚁稠。不知蛮触氏,自有两国忧。我观去来今,未始一念留。奔驰竟何得,而起无穷羞。王郎误涉世,屡献久不酬。黄金散行乐,清诗出穷愁。俯仰四十年,始知此生浮。轩裳陈道路,往往儿童收。封侯起大第,或是君家驺。似闻负贩人,中有第一流。炯然径寸珠,藏此百结裘。意行无车马,倏忽略九州。邂逅独见之,天与非人谋。笑我方醉梦,衣冠戏沐猴。力尽病骐骥,伎穷老伶优。北山有云根,寸田自可耰。会当无何乡,同作逍遥游。归来城郭是,空有累累丘。
这首诗集多种悲剧意识为一体:“南柯已一世,我眠未转头”“俯仰四十年,始知此生浮”写生命短暂、浮若漂萍的人生有限性,既是生命悲剧意识,同时也包含着此在人生的虚幻和无意义;“仙人视吾曹,何异蜂蚁稠”是站在超人间视角俯视人世间的无价值、无意义。“我观去来今,未始一念留”写时间的飞逝,透露着世界的瞬间生灭性,也是对世界真实性的怀疑和否定;“奔驰竟何得,而起无穷羞”写人世的追名逐利到头来也是一场空,“王郎误涉世……或是君家驺”表面上是在说王定国,实际是在具体解释汲汲于世、追名逐利者究竟无所得的悲剧,既是对政治本体的否定,也是在强调“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浮华历史的无意义,体现了历史悲剧意识。这些总体上给人一种对人生、社会、世界整体怀疑、厌倦、无所希冀的空漠虚幻之感。人生虽然空无意义,但人毕竟还要活着,必须在绝无价值之处为自己建立价值。“北山有云根,寸田自可耰。会当无何乡,同作逍遥游”就是价值的建立,即在否定了人生、世界的真实性之后,并未归向超验的理念世界,也没有飞向宗教性的上帝天国,而是仍然回到这个世界,过着逍遥山水、寄情田园的本真的农耕生活,沉浸于对现象界的审美观照。用李泽厚先生的话来讲就是“事件、景物、人生、世界、生活、生命即使虚无空幻却又仍然可以饶有意义和充满兴味”,“虽知实有为空,却仍以空为有,珍惜这个有限个体和短暂人生,在其中而不在他处去努力寻觅奋力地生存和栖居的诗意”。
与人生和空漠感一样,苏轼对历史虚无感的消解同样是“向空而有”地建立起新价值。“对历史‘空而有’的价值建构方式——通过对浮华喧嚣历史的否定和对永恒不变的宇宙自然的肯定积淀起具有本真意义的价值观。”中国诗人常用自然的永恒来突显人事的短暂,在强烈反差中表达历史的虚无感。永恒的自然往往也成了消解历史虚无之悲的重要因素,“空而有”之“有”也常常落实在自然上,如《游灵隐寺得来诗复用前韵》:
君不见,钱塘湖,钱王壮观今已无。屋堆黄金斗量珠,运尽不劳折简呼。四方宦游散其孥,宫阙留与闲人娱。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纡。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乔松百丈苍髯须,扰扰下笑柳与蒲。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氍毹,绝胜絮被缝海图。清风时来惊睡余,遂超羲皇傲几蘧。归时栖鸦正毕逋,孤烟落日不可摹。
从开头至“何用多忧心郁纡”,讽刺和批判钱镠广征徭役赋税,大兴土木,建造奢华宫殿,过着奢靡的生活,揭露其功业和浮华生活终归虚无。钱王的历史是浮华历史的代表,诗的前半部分是对浮华历史的否定,表达历史虚无之悲。在对浮华历史进行了否定之后,接着又肯定了自然,在一否定和一肯定的转折中,历史的“空”转向了自然的“有”,肯定了纯真山林田园生活的永恒价值。
四、以心理本体进行内在超越
心理本包含情感和理智两个要素,前者指以情为本,后者指以理性思索超越人世间悲欢的理性直观。苏轼在陷入人世悲苦和绝境之际往往寻找并回归人间温情,这种人间温情或来自亲旧挚交,或来自美好的自然风物,并因之消解内心苦闷,是即情本体对悲剧意识的消解。当外在世界一无可依傍时,他又能凭借理性看透人世一切的现象性,实现对人世悲欢的超越。
(一)“情本体”与宇宙情怀
所谓“情本体”,是以“情”为人生的最终实在、根本。每个个体“在这个世界中”与他人共在,人与人之间交感而产生“我活着”的悲欢、情爱、苦痛、哀伤,以及恼恨、耻愤、同情、平静等。人际情感即本真本己的最终实在,这是“现象即本体”的思维理路。积极的人际情感,即人际温情,是消解和超越悲剧意识的有效途径,也是精神的归宿。如《东府雨中别子由》“莫忘此时情”就是以兄弟温情消解悲剧意识。再如《过淮》:
朝离新息县,初乱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渡千山赤。麏鼯号古戍,雾雨暗破驿。回头梁楚郊,永与中原隔。黄州在何许,想象云梦泽。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独喜小儿子,少小事安佚。相从艰难中,肝肺如铁石。便应与晤语,何止寄衰疾。
元丰三年正月苏轼将家眷留在子由处,独携苏迈赴黄州贬所作。“麏鼯号古戍,雾雨暗破驿”是苏轼被贬后沉重心情的写照,这里的自然景象是生疏、异己、阴暗、冰冷乃至压迫人的。人与自然并无交会、沟通、融化、合一,自然不再是审美对象和悲剧意识消解因素,不再具有温暖的人的情感,反而成了人的对立面和对峙物,带来巨大的压抑感和逼迫感,加强了政治失意之悲。“回头梁楚郊,永与中原隔”正是在冰冷阴暗的自然力量的压迫之下政治悲剧意识的明确表达,“永与中原隔”表明强烈的贬谪之痛和对朝廷的眷恋。“黄州在何许,想象云梦泽”既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也是对即将处身的黄州之险恶地理环境的忧虑。在自然力量与人世力量的双重打击和压迫下,苏轼内心的不安与焦虑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自然而然生出“吾生如寄耳”的感叹。从“独喜小儿子”到诗尾,这多重交织的悲剧意识都化解在亲子之间的人伦温情中:“便应与晤语,何止寄衰疾”,即使羁旅他乡、自然险恶、前途莫测、人生短暂,似乎人生一无所有、一无依靠了,但仍然有儿子朝夕相从,可以相对晤语,排遣寂寥,聊寄衰疾,人生的种种失意都在这可供栖息依傍的亲子温情中受到了抵抗和瓦解。
情本体也与宇宙情怀相通。“所谓宇宙情怀,是对宇宙自然的情感体认,赋予中性的宇宙以积极温暖的情感。”这是一种有情自然观或有情宇宙观。宇宙天地本是客观中性的,人以自己的温情给予宇宙万物以温暖的情怀,这就是自然的人化。自然事物由恐怖或无关的自在对象,变而为人可以有着亲切关系的主体间性的存在,在杂乱无章、毫无秩序的自然事物中发现令人愉悦的美的感性形式和规律,人从中获得舒适感、安全感和家园感。
苏轼诗中将温暖积极、刚健不息的乐感赋于自然事物的情感多有所见,以此来消解悲剧意识。如作于海南的《儋耳》诗中有“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赋予自然刚健不息的壮大昂扬之情,象征着诗人内心的雄豪超迈之情。再如诗人被贬黄州时曾作《红梅三首》,描摹梅花的冰清玉洁、傲岸独立、玲珑可爱,使梅花具有了人的品格和德性,寄托自己被贬谪后独立不屈的人格。晚年被贬岭南复见梅花,诗人触物生情,复借梅花抒怀,诗中都充满了宇宙情怀: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蜒雨愁黄昏。长条半落荔支浦,卧树独秀桄榔园。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泠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
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天香国艳肯相顾,知我酒熟诗清温。蓬莱宫中花鸟使,绿衣倒挂扶桑暾。抱丛窥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门。麻姑过君急洒扫,鸟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再用前韵》)
两诗不涉议论与说理,对宇宙自然并无理性的思索和寻“道”悟“理”,全是对宇宙自然的情感体认。前一首诗,作者突破物我主客二分的理性思维方式,将梅花视作久别重逢的故友,直接对梅花展开人际对话,“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蜒雨愁黄昏”,面对梅花直接倾诉漂游和贬谪之悲。后韵中同样如此,“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将自我抒情主体置于辽阔的江海荒园中,抒发漂流异乡的孤寂落魄之悲。“天香国艳肯相顾,知我酒熟诗清温”,“抱丛窥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门”,都是人际互动和双向沟通。自然物不再是冰冷死寂的被认识对象,而具有了灵动的生命气息和温暖的人际温情,人恬然嬉戏于花草鸟兽之中,与自然为友,与自然同乐。自然界活了起来,成了人类孤苦无依时的伴侣:“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窥”和“黏”二字更是将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的感情写得活灵活现。在穷途落魄、孤独无助之际,宇宙自然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支撑和归宿。
(二)以理性超越现象界悲欢
有时,酒、仙、梦、自然、女人、亲情等外在媒介全部失效或无法依赖,似乎陷入绝境。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消解悲剧意识,实现超越?苏轼的策略是,直面人生或世界的悲剧性现象,以理智思索追询变易不息的现象背后的本质,抑制过度的意欲等感性活动给心灵造成的创痛,以理性超越现象界悲欢。这就是通过心理本体消解悲剧意识的理性直观。
“世界所包含的一切有限性,一切痛苦,一切烦恼都属于它所欲求的那东西的表现。”人间情感具有两面性,感情需求得到满足时能给人带来欢乐,得不到满足时往往成为痛苦的原因。人不能改变现实遭际,却能改变看待遭际的态度,形成心境的反转,转苦为乐、化悲为喜,在极端困厄的绝境中仍能以泰然达观处之。解脱之道就在于对宇宙和人生的全部现象、一切存在展开理性反思,摆脱现象对认识的遮蔽,普遍地看穿世界的本来面目,看透个体化原理,超脱现象性的存在,获得更高的解悟,从而削弱乃至消除感性欲求,消除由现象界关系而产生的烦恼、忧惧和痛苦。
理性思维的最大特点在于从具体、个别的现象出发,继而摆脱这具体、个别的现象,上升到抽象普遍、无差别化的概念层次。道家对“一”与“多”关系的探讨以及最终归于“一”,佛教对“色”与“空”关系的探讨以及最终归于“空”,其实皆然。苏轼擅于运用佛道二家的思维方式对人间万象进行反思和理性追问,淡化乃至摆脱与现象界各种对象的关系,以理性克制感情,缓解乃至消解悲剧意识。如《和陶王抚军座送客》:
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三年无所愧,十口今同归。汝去莫相怜,我生本无依。相从大块中,几合几分违。莫作往来相,而生爱见悲。悠悠含山日,炯炯留清辉。悬知冬夜长,不恨晨光迟。梦中与汝别,作诗记忘遗。
首句所谓“胸中佳处”指心理本体、自由心灵已经明天地之道、万物之情,与宇宙本体为一;“海瘴不能腓”指有心理本体为支撑,摆脱了一切外在束缚,困苦险厄皆不能摇荡其心志,不再使自己有所病厄损伤。“三年无所愧”是指自足性和自证,无待于外在的一切,无愧于天地、鬼神、君王、朝廷,乃至自己的良知。接下来对人生和世界的现象性关系展开理性反思:“汝去莫相怜,我生本无依”是对人与人之间现象性关系的看破,是对人际情感的超越;“相从大块中,几合几分违”是穿透个体化原理,将生命视作大化之一流程,将聚散离合上升为无常的造化之现象;“莫作往来相,而生爱见悲”,劝诫朋友和自己不要执着于现象性的“往来相”,不要因现象性的人际关系而哀痛伤身。此刻的苏轼已了悟“诸法无我”之真谛,心灵不再受现象界的困扰,海岭毒瘴、眼前离别、官场升降浮沉、人世冷暖悲欢等一切都是大化反复往来之现象,都不能在其心灵中搅起波澜,不再是心灵痛苦的根源。到这里,全诗一直是议论,直接对人生和世界的现象性展开反思和理性总结,直接以理入道,并未凭借自然山水悟道。最后“悠悠含山日,炯炯留清辉。悬知冬夜长,不恨晨光迟”,似乎又回到自然,但这不是借自然证道,而是宗炳所谓“含道映物”,在悟道后对自然的反观。因为理性认知已超脱了现象界的悲欢,所以此句格调明朗轻快,如万里晴空,无一丝阴沉悲苦相。
再如《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
吏民莫扳援,歌管莫凄咽。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而我本无恩,此涕谁为设。纷纷等儿戏,鞭蹬遭割截。道边双石人,几见太守发。有知当解笑,抚掌冠缨绝。
人与人之间的现象性关系及人间情爱是人的价值和归宿所在,但有时也是悲剧意识产生的重要原因,即苏轼所说的“悲恼缘爱结”。意志要求团聚和情爱的实现,而现实是不可避免别离,意志被现实束缚的不自由感,即离别之悲的根源。理性认识可以影响意志,发生意志的自我扬弃,使主体从现象性的关系中解放出来,超脱于情感,获得愉悦和恬静,从尘世得到解脱。“吾生如寄”是苏轼对人生悲剧真相暴露后进行理性思索所得出的结论,尽管这种结论带有悲情色彩,但仍是理性的。“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而我本无恩,此涕谁为设”,苏轼站在理性的角度对人间情感进行反观和超越,他不要求吏民在送别他时夹道扳援,也不要求送别的歌管悲伤凄咽,将人际情感削弱乃至消除。此刻的苏轼已无所求于任何事物和人际情感,他自己的意志也不牵挂在事物上,而保持去留无意的无执态度。甚至在智者看来,人间情感不仅不值得留恋,而且显得幼稚可笑,故而面对离别的亲友反倒说“纷纷等儿戏”“有知当解笑,抚掌冠缨绝”。到此,离别之悲被理性认识消解或超越,意志、情感都按照理性运作,与理性统一,理性不喜、不悲亦不惧,心理本体也同样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陶渊明《形影神赠答诗》)。《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亦是以理性超越离别的悲伤之情,实现情理的圆融无碍;诗中有“去住两无碍”,最后“大千在掌握,宁有离别忧”,都表明了苏轼对现象界的存在和现象性的关系做到了了无挂碍、随缘任运的平静超脱境界。
苏轼诗悲剧意识的诸种超越方式并非界限分明、相互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贯通包含。苏轼常常于一首诗中进行多种方式的超越,诗歌内容丰富蕴藉、气象万千,意境上有一种甩开一切羁束的豪迈旷达、超尘绝俗。苏轼同别人一样经历人生坎坷,乃至甚于他人,正是凭借诸种消解和超越方式,才能在悲剧情境中实现反转和突围,成为中国豪放派文学的代表。其作品为后世失意文人提供了一片精神家园和乐土,其人格和精神也深深沉淀入中华文化内核,成为民族的文化性格之一。
注
释
[1](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校点《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4](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5]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6]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7]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
[8][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9]冯友兰《新原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0]参见冷成金《孔子思想中的“自足性”》,《光明日报》2012年7月16日国学版。
[11]冷成金《唐诗宋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12]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