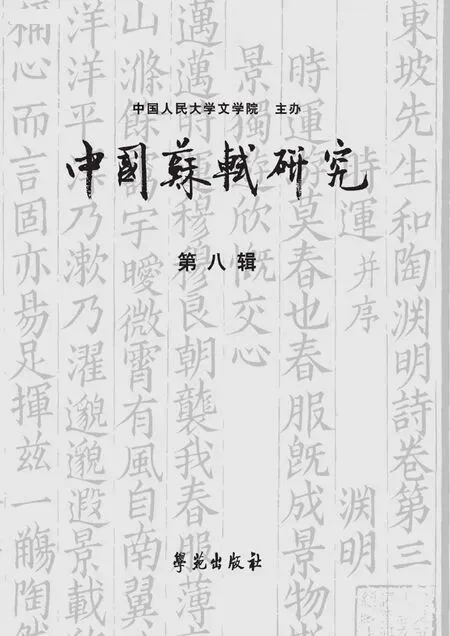秦观词情理结构特点
——兼与苏轼词比较
◇蔡明月
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评论“少游词境最凄婉”,切中肯綮,但秦词意蕴不止于凄婉。秦词现存八十多首,观其全貌,约为情、愁。元祐以后作品数量不及此前,但“个人情绪”之词占比最大,而且其最富盛誉的名篇多花开此苑。这些词中,多有以个体存在之“我”为主的词作,即个人情绪达到了观照个体存在和价值询唤的高度。情理结构是冷成金先生提出的唐诗宋词审美类型理论的重要内容,简言之,“情”“理”分别是从人类总体出发来进行理性追问形成的理和对这种理的体认,理未必能为个人情感所接受,二者往往不统一,但最终是希望完成情对理的认同,情和理形成了张力,而这种张力往往是诗词艺术魅力的来源。笔者将主要以情理结构这一审美类型进入秦词,希图透视其精神世界之景深,并与苏词比较。
一、情理难并山重水
首先是情理结构中情、理未能和解或统一,而在巨大的张力中沉入悲怨、恨愤,典型的是下面两首。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踏莎行》)
起首即将人抛入茫茫迷雾,暗示词人价值无解、归宿无着的心境。得不到解答,只得退回孤馆内,春寒包围的孤馆象征作者孤寂、落寞、闭锁的心理空间。无论“楼台”“津渡”是否实景,“望断”是否实际行为,总之外界中一切原本看似蕴含着希望的美好事物都了无影踪,不能提供精神寄托。而独坐驿馆只听得杜鹃的啼血哀鸣,外界环境的凄衰又将心灵渲染得更加黯淡。王国维《人间词话》评:“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为凄厉矣。”词人想要通过寄梅传书来排遣思乡怀人之苦,反却复堆此恨。词至此处,从外界无望到哀鸣凄厉到书之愈苦,恨已一唱三叠。“砌成此恨无重数”是对上文的极好概括。恨已至此,投射到自然上就是嗔怪郴江,与客观事物和自然规律相抗拒,不愿意也无法走出愁怨的个我世界。这种不顺意、不平气本质上是词人极其执着于现实,而又不愿意体认现实之实然常情而形成的情理矛盾。
这与苏轼《南歌子》(雨暗初疑夜)形成了鲜明对比。该词上阕描绘晨酒未醒,轻快骑行所见的犹如仙境的奇丽景象;经行蓝桥而历此景,自然联想到裴航遇云英的传奇,恍惚如梦。但苏轼明白仙女终是不能遇逢的,仙村也不存在于现实,经过这一番理性的追询与选择,再看自然——“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情感上就更加体认自然与现实的温暖(“淡云斜照著山明,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这是在经历了情—理—情的价值建构之后,人格与心怀的新的提升。同样是看流水,秦少游与之相抗拒,苏轼视为多情伴侣,根本系于二人的情理结构之不同。但是秦词情与理的巨大张力已达到集中化典型化程度,所以能够穿越千年与人心相通,这也是其魅力所在。
高城望断尘如雾。不见联骖处。夕阳村外小湾头。只有柳花无数,送归舟。
琼枝玉树频相见。只恨离人远。欲将幽事寄青楼。争奈无情江水、不西流。(《虞美人》)
这首词较特别,是典型的秦观特色——悲剧意识循环往复,与自己与天地过不去。上片登高恋往而昔时无迹可寻,悲情意识若隐若现,这在柳花伴人归的情景中得到弥合。但随即又上心头,生出分别之恨。想要在欢场快乐中消解悲愁,可是“无情江水、不西流”。上阕结句可以感知自然之温情,作者有融入其中的倾向而弥合了悲情意识;但是这次否定了自然,实际上是一种不得解的绝望——沉湎于昨日不复重现的悲凉心绪之中。结句不同于“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较之苏轼《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中的“门前流水尚能西”,“心境之差距昭然可见”,盖苏轼在价值追询后获得心境的打开和人格的提升,少游却必欲使自然规律顺己意运行,即此情无法认同此理,找不到精神家园。
苏轼总是“此心安处是吾乡”,化故乡为天下,与自然融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浣溪沙》上阕“潇潇暮雨子规啼”,是季春更兼暮雨又闻子规啼晚的伤愁之景,苏轼却能于此般氛围里瞩目于“西流”之罕景,又从这种自然景象出发,生出“谁道人生无再少”“休将白发唱黄鸡”的高亢强音。这不仅“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林语堂《苏东坡传》)这么简单,更显露了永远葆有对青春毫不掩饰的热爱与渴望,这是符合人类总体意识的年轻向上的审美人格,也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苏轼何以能屹立千年,以强大的人格磁场吸引“后之览者”。这种审美化的人格就是情理浑融的结构和境界。
二、深慨长叹归于心
秦观词情理结构的另一种导向是归于心理本体,即目下心境及其外化的情景。心理本体就是归于心理,实质上是归于人格境界;中国人没有西方宗教文化传统对于外在与超验的信奉,而是相信一种人格、一种境界以及追求人格境界的过程,如此诸种全在个我(之心),是谓心理本体。表现于诗词就是归于情、归于心。如:
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樽。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
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满庭芳》)
上下两片文路相同,都是先写离别之景和离别之情,后均以景结情。上阕最后三句闲淡宁静的情景因为上文惜别怀人而成为心理归宿。在秋山衰草的萧瑟中与情人伤别,而这在词人的回忆中又如烟漫漶,更添伤感;离别本是人生之常理,却是人力无奈的,所以作者只有体味这种伤情,“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正是伤别中归向内心,斜阳、寒鸦、流水、孤村营造的秋晚之景衬托了词人幽微深远平淡的心境。下阕最后三句亦是营造情景,因为“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就让人体会到黯然神伤的感觉,同时让心情意绪有了归宿。灯火是家的象征,黄昏是归家的时刻,而作者却不可归,亦无家可归,于是最后这个情景引人沉入其中,不断体会上面营造的情理结构——不愿分别却对这种现实无可奈何,于是“伤情”化作对人生的深情感慨,即“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是“向心理本体淡淡的沉入”。
晓色云开,春随人意,骤雨才过还晴。古台芳榭,飞燕蹴红英。舞困榆钱自落,秋千外、绿水桥平。东风里,朱门映柳,低按小秦筝。
多情。行乐处,珠钿翠盖,玉辔红缨。渐酒空金榼,花困蓬瀛。豆蔻梢头旧恨,十年梦、屈指堪惊。恁阑久,疏烟淡日,寂寞下芜城。(《满庭芳》)
此词和上一首内部结构近似,都是先写景或忆昔,而后以情景作结。往昔春日与恋人寻欢的美好生活一去不返,弹指惊过十年,作者因此产生了淡淡的愁情,“恁阑久,疏烟淡日,寂寞下芜城”正是这种心境的审美表达和向心理本体的沉入。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记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望海潮》)
初春俊游,春色喜人;雅集欢饮,回首已老。追恋美好往事却难以复现,词人的情思在嗟叹中归于“倚楼极目,时见栖鸦”的情景之中,心境亦趋于平和淡定。最后“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就是对人生现实的深情感慨,虽然无奈不愿,但终究面对现实,所以情理结构中蕴含着精神家园。
西城杨柳弄春柔。动离忧。泪难收。犹记多情,曾为系归舟。碧野朱桥当日事,人不见,水空流。
韶华不为少年留。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江城子》)
这首词的思路仍然是写景、追忆而后抒情,且仍然是留恋昔日美好岁月,但更多的是沉湎于昨日,所以最后就沉入深深愁绪之中,“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即归于当下的心境,包含着深刻的凄凉甚至绝望——人事不可见,自然不可托,这是心灵无可依傍的空与伤。这种心灵无可依傍的状态并不会导向空虚,而实质上是以心理为本体,向内寻求、建立价值,可以说是家园在内心、依傍在自我的文化本体渐趋形成的预示,使读者感受到另一种层次的正面向上的艺术力量。
东风吹碧草,年华换、行客老沧洲。见梅吐旧英,柳摇新绿,恼人春色,还上枝头,寸心乱,北随云黯黯,东逐水悠悠。斜日半山,暝烟两岸,数声横笛,一叶扁舟。
青门同携手,前欢记、浑似梦里扬州。谁念断肠南陌,回首西楼。算天长地久,有时有尽,奈何绵绵,此恨难休。拟待倩人说与,生怕人愁。(《风流子》)
上片写春色恼人,是触景生情,后归于斜阳烟静、舟中听笛的情景,最是容易逗出深情沉思,果然进一步引起了往日交游欢会的回忆,且难以忘怀。岁月本该天长地久却如梦难永,人生本该携手长久却客老沧洲,正是这种情感理想与客观现实的冲突,即情与理的张力导致了绵绵难休之恨。最后两句不仅是直抒胸臆,作者看似消愁有心无计,实则是心理本体之下不愿为外人道而宁愿浸淫其中,细细体味这种悲情意识。这既是一种心理归宿,也是一种消解方式,“所积累的丰富的情感终究会成为追询新的价值的动力”。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
秦观这些词大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上下两片先写景或追昔,其次有的词时或兼抚今,而后以情景之句作结(偶尔直抒胸臆,如“怕与人愁”);而这首词同上面《江城子》、《虞美人》、《满庭芳》(山抹微云)结构最接近,这是观之显见的。本词“回忆苏轼及其门人往日相聚的情景,而今日天涯流落,未来也不可测度”。“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无法体认自己所处的现实又难以超越,于是只得浸淫在这种情绪之中,不得自拔之法。
苏轼在文化本体时代进行价值追询,建立起情本体的情理结构,这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证明。“该词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起句,超越了现实的功利的局限,以一颗自由的心灵来询问宇宙和自然。”具体说来,关问明月的诞生和宇宙的年岁,根本上是源于相形于自然之恒久,生命有限的人类对青春永在、生命长久的本能期愿。这种价值问询和“人生有限情无限”的悲剧意识的兴起本身就体现了最原初的情。在经历“乘风归去”和“高处不胜寒”的理性追索后,最终的答案是选择现实的温暖——“起舞弄清影”,以下的“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就是这个具体的温暖的人间,总之这个过程就是对应然之理的选择。最后,虽然“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作者并没有障目于悲欢离合、阴晴圆缺这些人事和月态的具体内容,而是祝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永驻长存的形式。所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既是对现实常态的深刻体认,也是对生命的深情感慨;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既是深情感慨,也是对现实的审美超越(经由现实而超越现实从而建立起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人类总体价值)。这种祝祷是从人的自然感性欲求(即最开始的情),经过理性追询后抽绎出的普遍人情,是典型的情—理—情的价值建构理路,源于情而归于情,一般的心理本体就升华为“情感本体化”的情理结构。但像苏轼这样毕竟是少数,秦观才是“文化本体时代的神伤,是价值追索失败后的绝望”的普遍表现,这也是为什么秦观的很多词虽然充斥悲愁甚至常以绝望收场,却仍然不乏其价值,因为它能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心态。
碧水惊秋,黄云凝暮,败叶零乱空阶。洞房人静,斜月照徘徊。又是重阳近也,几处处,砧杵声催。西窗下,风摇翠竹,疑是故人来。
伤怀。增怅望,新欢易失,往事难猜。问篱边黄菊,知为谁开。谩道愁须殢酒,酒未醒、愁已先回。凭阑久,金波渐转,白露点苍苔。(《满庭芳》)
本词上阕与《踏莎行》(雾失楼台)几近同一结构,仍然是先写凄凉之景,后托出幽独深居的主人公形象,虽然都营造了寂寂封闭的氛围,但两首词中的主人公都在探听外界的动静。砧杵声和风敲竹的响动衬映出作者敏感幽微的内心。过片新欢亦会成为故人,进而成为难猜之往事,只会复添怅惘与怀伤。作者希图通过人世人情来排解悲情意识,却再一次失败;只得投向自然之怀,可是试“问篱边黄菊”,也是无用的;希望借酒消愁,结果是“愁已先回”,“谩道”一词便透露出作者再次失败的怨气。一而再、再而三的消解悲愁的努力受挫后,词人的情绪下行已至谷底,到了绝望境地,却也由此出现了触底反弹的契机。结尾三句呼出的是秋波依旧缓慢旋转,点点白鹭下苍苔的娴静自若的情景,可以说词人在一次次情理的交锋后归于心理本体。按照王国维的意境论,如果“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为“有我之境”,那么“凭阑久,金波渐转,白露点苍苔”可谓“无我之境”。这种“无我”从另一个角度言,反而是不愿面对与体认人生离别和个体孤独的应然实然状态,对那个“此刻”之心境最深细的体味,其实蕴含着对生命真相的深情感慨,而这种感慨之中满含词人的证悟——自然而然地生活,此即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
锦帐重重卷暮霞。屏风曲曲斗红牙。恨人何事苦离家。
枕上梦魂飞不去,觉来红日又西斜。满庭芳草衬残花。(《浣溪沙》)
这首词的具体内容并无定解。清代苏黄《蓼园词选》评价此词“写闺情至深,意致浓深,大雅不俗”,以之为闺怨思妇之语。而杨世明《淮海词笺注》曰:“写客中与宴…自称恨人。”石海光编著《秦观词全集》题解:“由酒宴歌席之会一转而至思乡之愁。”笔者亦以为是即宴事作。华宴之上,歌姬拍红牙歌唱,耳目之乐并没有浇灭词人的离家客愁,可谓乐极生悲。“恨人”可为己称,更可将“恨”理解为动词,“人”不必具指,乃可为所有人而发问。就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不仅是希望自己和弟弟长久安好,而且上升到对全人类的祝愿。此亦然,一人之问,千万人之惑,其实是对人类的整体关切。如此悲剧意识也因为具有普遍意义而更加深沉。离家之恨的悲剧意识在此兴起,欲消而难消,即使梦归亦不可得。离家客居本是人之常情和现实常态,“恨”字却表现出作者执着于常聚长圆的理想状态而不愿意体认这种现实和常情,正是内心之情不肯接受现实之理的剧烈冲突的掷地有声的集中迸溅。最后“满庭芳草衬残花”,满目的草盛花残的生活情景让人兴起新的更加深浓的悲剧感,而作者此刻就归于这种情景之中。
这第二类情形的几首词中,《浣溪沙》(锦帐重重卷暮霞)、《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虞美人》(高城望断尘如雾)、《千秋岁》(水边沙外)几首是最终沉入悲凉和绝望心绪的,这是“试图解决生命的有限性和情感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本质上就是情与理的冲突,最终没有找到答案,因而表现出绝望的价值悲剧意识”。
与第一种情况情理无法和解不同的是,虽然也是对悲凉心境的体味,但仍然指向了心理归宿,哪怕沉溺的是悲凉(但并不会把人引向颓废和毁灭,如上文每一首具体分析所指出的,或蕴含着对生命深情感慨,或积蓄着继续前行和新的价值追询的力量)。但《踏莎行》(雾失楼台)和《虞美人》(高城望断尘如雾)是情始终不愿体认理,内心始终不能与自我和解,投射到外物和自然就是暗暗抗拒,真正的“怨”天“尤”人,这是反复的价值追询失败后的积郁和不平,不甘心不愿意就此体认这样的现实和自然。但这仍然不会导向虚无主义和自我毁灭,因为这些词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比如其所构筑的循环往复之悲剧意识实质就是不断尝试建立价值,而一首词的有尽的时空并不是这种努力的终截;再如当抖落了一切世俗、外在、惯常的价值,也就是彻底悲剧意识净化心灵而结出心理本体新果实的契机,这个果实就是文化本体时代归于心灵的精神家园和价值归宿。
三、理化入情无参商
最后一类是完成了情对理的认同,一般内含情—理—情的结构,大致就是以下几首:
千里潇湘挼蓝浦,兰桡昔日曾经。月高风定露华清。微波澄不动,冷浸一天星。
独倚危樯情悄悄,遥闻妃瑟泠泠。新声含尽古今情。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临江仙》)
作者联想到昔时湘妃、屈原亦经行此处,发思古之幽情,内蕴淡淡的历史悲剧意识,必然唤出价值追询的欲求。而风、露、月、波、星构成幽眇深邃的世界,又构成净化心灵和自证的最佳契机。此刻词人独倚危樯,远远地听见清越的琴声。古今人同此心,声同此情,尽含于新声。作者将一己之生活和情思上升到古今普遍的高度,实质上也是对生命的深情感慨——历史皆然,人生同是!经历这一番洗礼,词人终于达到对悲剧意识的审美超越——“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在情—理—情的结构上则是归于宇宙情怀。
这近于苏轼《行香子》(过七里滩)的“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上阕轻舟过七里濑,水天清湛、鱼鹭自在、霜月溪明,是对自然景物的单纯美好的自然感受;而下阕中“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是经过理性思考,发现功名得失、成败胜负都是一场空,正面、负面的价值都被消解。但随即“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苏轼从自然而然的自然中悟道,这是对宇宙情怀的深情拥抱,在自然中对自然之道进行充分体认而化理为情。所以,与秦观这首词都是情—理—情的情理结构,最终“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钱起的名句在这里被赋予新的意义——营造了渺远空明的境界,成为生命境界打开的诗性化表达。
秦峰苍翠,耶溪潇洒,千岩万壑争流。鸳瓦雉城,谯门画戟,蓬莱燕阁三休。天际识归舟。泛五湖烟月,西子同游。茂草台荒,苎萝村冷起闲愁。
何人览古凝眸。怅朱颜易失,翠被难留。梅市旧书,兰亭古墨,依稀风韵生秋。狂客鉴湖头。有百年台沼,终日夷犹。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洲。(《望海潮》)
上片先绘写会稽一带自然胜景,下片先追述历史风流。但佳山丽水之间,作者“冷起闲愁”,兴起历史悲剧意识,具体表现在下片览古而生幽思,因为与绍兴山水相关的历史人物和风云际会已然消失,徒留后来游人在荒台茂草之间终日流连;可是秦峰依旧苍翠,耶溪依旧潇洒,而千古风流人物及其丰功伟业、历史佳话这一切浮华历史似乎都不值得追求,不如归隐沧洲醉乡。最初对自然的体认之情在经过历史悲剧意识洗礼后,情感与人格进入新的境界,这就是“最好金龟换酒,相与醉沧洲”。最后看似以隐居、酒和自然作为精神寄托,其实是找到价值归所的新的人格境界的打开,所以也是情—理—情的心路。
苏轼词集中常见情—理—情的心理净化机制,但《望江南·超然台上作》或许与本词更加形似。上阕作者于细风烟雨中登台眺望,所见乃“半壕春水一城花”的初春美景,对现实对自然都给予充分体认。古人凭栏登高必怀远感喟,苏轼“酒醒”而“咨嗟”,从后一句“休对故人思故国”可知是因思念故国与故人,但他直接出以“休对”之句,说明悲情意识的产生与持续过程十分短暂,随即直达理性自我,而且在情感上诗意地展现为“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透显出情理情的心理本体已相当稳定,情早就达到了与理的深然合一。唯其如此,苏轼的价值建构理路才成其为“情感本体化”。虽然感性人情的悲情意识的兴起转瞬即逝,但和秦观此词最终都是归于诗酒快意的文人本真生活(而这已理化为情),情理结构是相同的。
红蓼花繁,黄芦叶乱,夜深玉露初零。霁天空阔,云淡梦江清。独棹孤蓬小艇,悠悠过、烟渚沙汀。金钩细,丝纶慢卷,牵动一潭星。
时时,横短笛,清风皓月,相与忘形。任人笑生涯,泛梗飘萍。饮罢不妨醉卧,尘劳事、有耳谁听。江风静,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满庭芳》)
这首词是对情理结构进行整体体认。秋夜却有花叶之红黄绚烂,初上露珠,在天阔云淡的明霁夜色下,词人的一叶孤舟悠然漂泊在清江烟水上,独拥这月如钩和一潭星。上阕把自然描绘得明丽、亲切、可爱,整个清空的世界都向词人敞开;当一个人独自面对透明澄澈的宇宙,是观照自我存在的最佳契机,最容易唤起价值追询的理性思考。此刻孑然孤蓬的词人也疏空了心灵,仿佛下片那清风皓月吹送的短笛乐音隐喻着心灵的洗礼,在吹尽心灵的浮尘之后留下的就是本真心灵,所谓“相与忘形”。上阕是作者对宇宙自然的充分体认和完全融入,返归本真心灵后的“任人笑生涯,泛梗飘萍”则是这种宇宙情怀的结果;“饮罢不妨醉卧,尘劳事、有耳谁听。江风静,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是忘形而归真之后的应然状态的诗性表现,即词人内心此情对此理的高度认同。是以整首词起于宇宙情怀,在宇宙情怀的荡涤下,勘破“尘劳事”的“飘萍”“生涯”,心灵冲刷掉世俗价值,留下的是无所挂怀的洒脱本真的生活状态,是对琐屑浮生的审美超越。最后“日高未起,枕上酒微醒”,营造的率性洒脱的情景简直和苏轼的“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如出一辙。
所以说这首词每一句都在体认宇宙自然和本真生活。与唐人不同的是,没有“何处春江无月明”式的高亢的赞美和兴奋,经过杜牧“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的与自然了无间隔的融合,到宋世的秦观这里已经可以淡定悠闲地观审自然之美好,以享用的姿态安放自己的灵魂。而宇宙自然亦在作者的参与中变得明媚动人、温暖可亲,人和宇宙自然相互促生、相互成就。作者已在内心找到精神家园而变得从容自得,所以才有底气说“任人笑生涯,泛梗飘萍”,有耳不听,有心无惧。小结起来,作者的情理走向是宇宙情怀—否弃世俗价值—对本真生活的情感体认,体现出的心理净化机制是情—理—情的理路。
同样是对情理结构进行整体体认,苏轼的《定风波》与之不同。一上来就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面对“雨具先去”“穿林打叶”的现实,相比“同行皆狼狈”,作者的“莫听”是一种自我提醒和宽慰。苏轼在这种悲剧意识即将兴起之初即开始理性思索,甚至可以说未兴之时理性就已上道,而探索的出路就是“何妨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因此这首词所表现出来的悲剧意识的兴起过程更短于《望江南·超然台上作》,而近于无。但心灵净化与人格升华的进展尚未止步,苏轼在雨过天晴的良机中得到了妙悟——本无晴雨,焉有“何妨”?因为“莫听”实质正是源于对现实的执着和困扰,而“也无”则表明词人已不需要对人生的“晴”“雨”进行理性的选择和过滤了,直接跃升到纯任情感的臻于“思我无所思”的“天地境界”,即“将天地运行的自然而然化为人生的自然而然的境界”。这种情感沛然莫御,就像孟子的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消融了生活的具体的幸难喜哀,直接与自然冥然合一,以自然而然的生活态度处之,生命也就无悲无喜,而达到情感本体化的高度。
过秦淮旷望,迥萧洒、绝纤尘。爱清景风蛩,吟鞭醉帽,时度疏林。秋来政情味淡,更一重烟水一重云。千古行人旧恨,尽应分付今人。
渔村。望断衡门。芦荻浦、雁先闻。对触目凄凉,红凋岸蓼,翠减汀苹。凭高正千嶂黯,便无情到此也销魂。江月知人念远,上楼来照黄昏。(《木兰花慢》)
少游词多述凭高登楼,此词亦是。上阕词人骑马游目,面对疏阔清淡的秦淮秋色,“吟鞭醉帽”,享受着自然的静好,好不潇洒惬意,宇宙情怀透出纸外。结句却翻出“千古行人旧恨,尽应分付今人”,情绪下转——于空旷的空间思接千载,由个人行吏之悲联想到千古行人之共恨,与“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同是对全人类的一种观照。在这种共情的悲剧意识的观照下,下片词人登高望远,所见秋景皆着了凄清之色,又因凄凉之景而更加黯然销魂,悲剧感更加深沉,情绪最终归入“江月知人念远,上楼来照黄昏”的情景;这一轮光照今古的明月并不无情,这是自然与人的亲和。所以在全词最后,词人既归于心理本体,也在自然与人情的统一中找到精神归宿。词人由清秋旷野之潇洒惬意到行客凄伤伤千古的情绪,到在凄凉的自然风景中洗礼而达到人与宇宙的新的亲和,也就是由体认自然之情感到理性思索与选择,而完成新的情感体认的审美超越,亦是情—理—情的理路。
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
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江城子》)
元符三年,徽宗即位,苏轼、秦观等谪臣予以赦还,苏轼自海南北上与秦观相会于雷州,此即为宴别之作。秦观时年五十二岁,可以说此时已阅尽沧桑,遍历人生之升沉起伏,正是勘透人生、臻于平和淡定之际,故言别后之悠悠,不足言道——这正像苏轼的“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只需珍惜此刻之重聚,畅饮痛醉,因为醉后又将各分散,可见词人已体认“人生何处不离群”的现实,而不似不甘不平的积郁之前情,也不再与宇宙自然相抗拒。“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至结尾都是作者勘破生命的深情感慨,如同刘长卿的“明发遥相望,云山不可知”和王维的“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皆系同质之情理结构,孕育着顺其自然而“不喜亦不惧”,活在当下而继续前行的力量。
根据苏轼的《书秦少游挽词后》可知,词中宴别发生在元符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距少游八月十二日卒于滕州光化亭上,日可指数。可以说这首词是秦太虚整个人生这一最大的情理情结构的审美总结,虽然很大程度上是生命过程的磨炼所致,而不似苏轼之能动清明,但晚年词人终于在词中所蕴含的深情感慨中完成了对人生对现实对自然的情理认同,这从晚年其他为数不多的作品如《醉乡春》(唤起一声人悄)等亦可看出。
四、小结
以情理结构的审美类型挖掘秦观词意蕴和词人之心,得窥更加具体深细的景观:除了少数情理冲突十分强烈,情始终不愿意体认理而沉入深度的怨悱不甘(但蕴含着后续的价值崛立和家园感询唤的空间与希望);大多数词作即归于一种情景和心境,向心理本体沉入;少数篇什甚至体现出情—理—情的结构而实现了对悲剧意识和悲情意识的审美超越,实现了人格境界的提升(虽然不如苏轼那么典型和普遍)。总体来说,秦观词情胜于理,在情理结构上多表现为在当下情景中细味此刻的心情,其实这正是因为还没有完成情对理的体认,有家园感的倾向却不充分。
在这一点上,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秦观在心理本体的筑就上更多地拘牵于情理矛盾上,以至于情理结构的链条不够彻底和完善,即在情理交锋后往往要么陷入抑郁不平乃至绝望,要么沉入当下情境和此刻心境,缺少苏轼那样多见的理化之情的审美外化和诗意表达。苏轼在心理成本体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已然臻于情感本体化境界,要么通过情—理—情的心理净化机制或者说价值建构理路,典型的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要么自然感性的悲剧性情感短暂兴起以至于径出以理,又上升到情感上进一步的新的认同,如《望江南·超然台上作》;要么天时良机之下妙悟而迈入“思我无所思”与自然一样的自然而然的“天地境界”。故苏轼很多时候总能在自然中安放自我:“雨具先去”,那就“莫听穿林打叶声”;“尽日行桑野,无人与目成”,那就“且将新句琢琼英”,还不无标榜地自嘲“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延及人事,三更归家,“敲门都不应”,那就“倚杖听江声”,还浪漫地想起小舟江海之志。苏轼是先即融入了自然,也自然能与自然和解,因为这种融入本就意味着天我合一。而秦观在处理自我与自然的关系上,试图以一方狭小的个我天地去涵盖自然,欲使自然按照自我世界的意志运行,与自然相抗,本质上是与自己过不去,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剧烈之时可至于“流不尽,许多愁”和“争奈无情江水、不西流”。所以,从词心与自然的相处这一具体问题上,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二人词作情理结构特点的不同面貌的产生原因。
少游喜登城凭高,词中多所体现,且但凡登高,无不是令人称赏的名篇。或许正是因为“许多愁”“流不尽”又深“如海”,才喜登高,却仍是难以解证(多数情形以当下的情景和心境为心理归宿,以此或通往精神家园)。要之,少游词虽是愁满乾坤,却绝不把人导向颓废、毁灭与虚无,反而是从另一角度助益于正面情感与价值的积淀,有助于心灵的净化与成长。这组词不仅是深刻典型的诗性表达,同时也是一种审美体现。
注
释
[1] 根据爱课程网—冷成金《唐诗宋词的审美类型》—第四讲《情理结构与精神家园》整理。
[2] 石海光《秦观词全集》,崇文书局2015年版。
[3] 冷成金《唐宋诗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宋)秦观著,杨世明笺《淮海词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 冷成金《苏轼词对现实悲剧性的审美超越》,《河北学刊》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