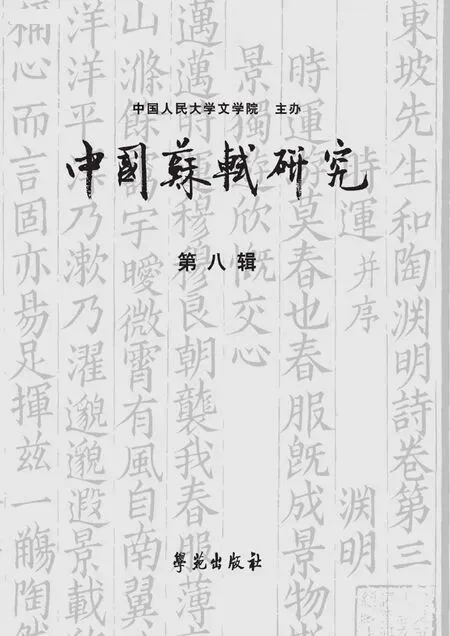人的自证与悲剧意识的兴起
◇冷成金
中国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成熟的悲剧意识,且唐诗宋词是其重要的载体,而其中苏轼诗词文中的悲剧意识又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因此,在研究苏轼的诗词文时,探讨悲剧意识的源起及性质尤为必要。但历来对于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的源起、性质、特点以及作用的研究尚不深入,也不明确。兹从三个方面来简要论述这一问题。
一、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价值建构的起点和原动力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在人和道的关系上,这句话是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性质命题(直言命题),“人能弘道”的思想不仅是孔门仁学的基本观点之一,更对中国哲学以及思想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人是什么?即人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其意是说,相对于“好德”“好仁”,人更容易“好色”“恶仁”,其中的“好德”“好色”、“好仁”“恶仁”是两组对立的概念,又都同时存在于人的身上。
但对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历史上有这样的解释:
谢氏曰:“好好色,恶恶臭,诚也。好德如好色,斯诚好德矣,然民鲜能之。”《史记》:“孔子居卫,灵公与夫人同车,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丑之,故有是言。(朱熹《论语集注》)
本章叹时人簿于德而厚于色。或曰:好色出于诚,人之好德每不如好色之诚。又说:《史记》“孔子居卫,灵公与夫人同车,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故有是言。今按:孔子此章所叹,古固如此,今亦同然,何必专于卫灵公而发。读《论语》,贵从人生事实上体会,不贵多于其他书籍牵说。(钱穆《论语新解》)
钱解甚好。好色之色亦可作宽泛解,不必止于女色,一切过度之华美文饰均是。(李泽厚《论语今读》)
显然,钱穆承袭的是《论语集注》的说法,从“今按”看,李氏是同意《论语集注》的说法的。朱、钱、李的解释一脉相承,但不正确。
朱熹将“好色”的“人欲”看作人之“诚”,是为证明人欲的存在,是出于“灭人欲”的考虑。但《四书集注》对“诚”的使用有很不一致的地方,《中庸集注》在“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下注:“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如果按照这一解释,“好色”便是“天理之本然”。朱熹与钱穆之意,大致是教人“好德如好色”,将“好色”之“诚”移植到 “好德”上来,但既然是“诚”,又如何能移植?况且二者是对立的。
“诚”本是原始巫术活动中的要求和心理感受,随着历史的发展,“诚”逐渐被提升到宇宙和人的本质的高度,所以才有“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所谓“天之道”,就是天然之道,就是最本真、最自然、最无人为的样子,以无人为干预自然而然地运行的“天之道”来标举人类社会,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无战争无剥削无压迫且富裕文明的状态,因为这是人的最本真的希望和追求,是人的本真心理的真诚显现,所以是“诚”;但人类社会并未达到上述的应然状态,那就要使之不断趋近,所以说“诚之者,人之道也”。因此,“诚”本身就是对基本历史合理因素的体认,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这种对“诚”的体认的要求就被确定为人的本质规定性。这样一来,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合理因素来讲,“诚”就成了人的人性心理形式。
如果“好色”是人之诚的话,那些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就没有了“诚”,只有贪生怕死、见利忘义的人才有“诚”。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朱、钱、李所说的“诚”并不是原始儒学意义上的“诚”,更多的是人的动物性的自然物欲心理。
在原始儒家看来,人不是抽象的,人的本质属性是由人的动物性(自然物欲)和人的社会性(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建构理性的结果)两个方面组成的。动物性是人性的基础,其本质特征是生本能,即要活着并延续族类,主要体现为物质欲望;社会性是人性的指向,是对人的动物性的规范、提升和转向,其本质特征是奉献。“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其中的“好色”“恶仁”是人的动物性,“好德”“好仁”是人的社会性。必须看到的是,“好色”“恶仁”是随时随地地自然产生的,而“好德”“好仁”则要克制私欲,通过“克己复礼”(《论语·颜渊》)的艰苦修炼才能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断地克服和转化人的动物性,增加和提升人的社会性。)
所以,“好色”“恶仁”仅仅是人的动物性,是人的自然欲望,而非人之“诚”。而“好德”“好仁”则是人的社会性。在这个问题上,《孟子》以其深刻的思辨性进行了彻底的论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其意是说,人喜欢感官享受,是人的自然天性,但能否得到这些享受,却有偶然性,是外在命运,是人不能把握的,所以君子不把乐于享受看作是人的天性的必然;至于仁义天道能否实现,虽然也属于命运,也有偶然性,但它是人的天性的必然,是人的本质规定性,所以君子不认为能否实现仁义天道属于命运,而应该看作是属于人的天性,因此应该努力去实现仁义天道。在这里,孟子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类总体意识)将“性”与“命”、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置换,确立了人的社会属性为人的应然之“诚”。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孟子的哲学中存在着一些先验的或设定的东西,如:“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在这里,孟子将“四端”等同于“四体”,是混淆概念,将“四端”“浩然之气”这种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人性心理当成人生来就有的东西,这就导向了先验,为后来的随意设定(比如将封建社会某个阶段的道德规范当成永恒的东西)开了方便之门,失去了以人为本的历史实践的源头活水,必然走向僵化。但同时,孟子哲学思想中又有与孔子高度一致的地方,如上段引文中的将仁规定为人的本质属性,就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应然要求出发来思考问题,而不是从某个固定的先验的东西来思考问题,是孔子“人能弘道”思想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要“活着”是人的动物性的永恒的本能冲动,然而,由于人的高智商与高情商,动物性的要活着一旦在人的身上体现出来,就必然体现为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的合一,所以,人的要“活着”与动物的要活着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性的要活着仅仅出于生本能和族类延续的本能,而人的要“活着”基于上述的动物性本能并进行升华,即为了个体的存在与发展必须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就是孔子的“人”(或君子),也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与核心。
那么,人为什么能弘道?人要“活着”是人的内在亲证。所谓内在亲证,即不依赖于任何外在证明的内在的亲切感受,是每个人都不需要理性论证就能亲切感受到的感性状态。当一个人怀疑自己是否想“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证明他想“活着”并且正在“活着”。
当然,人的内在亲证有多种,不只有要“活着”,但在“食色二性”、支配欲、贪欲等诸多的内在亲证中,唯有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是最根本和最有决定意义的。这种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决定了人想更好更长久地“活着”,而人要更好更长久地“活着”就必须建立起有利于人更好更长久地“活着”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这些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就是“道”。
这是人能弘道的根本原因,也是人能进行一切实践活动的根本动因。在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中,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接下来的问题是人根据什么来弘道?“人能弘道”,人是第一位的,在这里,这个“人”是有着要“活着”的内在亲证的人,其弘道的依据必然是有利于“活着”的规范、准则或思想观念。由于人类具有区别于动物的高智商和高情商,纯粹为个体“活着”而发生的各种动物性行为只能使人类退步乃至灭亡。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动物虽与人类同样有着要“活着”的内在亲证,但因动物无人类的高智商和高情商,其利己行为一般不会导致族类的退步和灭亡,即动物没有能力自我灭绝。所以,与动物不同的是,人类必然要依据利他、奉献的思想观念来建构社会规范和价值准则,而这个利他、奉献的终极状态就是为人类总体的更好更长久的存在,这就是人类总体观念。
《论语》的精神实质就是要建立这种人类总体观念,其中的各种推论的依据就是这种人类总体观念。如人生来未必是爱学习的,却是必须要学习的;人生来未必是爱孝的,却是必须孝的;人生来未必是性善的,却是必须性善的;人生来未必是有价值的,却是必须有价值的;人生来未必是愿意走向大同社会的,却是必须也必然要走向大同社会的。这种推论之间的保障不是形式逻辑,而是人类总体观念,其论证方式不是易于导向各种唯心主义的“主观性设定”,而是以历史实践为根本的“客观性推断”。
最后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道能弘人?如果是道能弘人,将道置于首位,那么道就必然僵化,因为无论这个道多么富有合理性,它总是带有历史的局限,总是不能与现实情形完全符合。只有活生生的人才永远处于当下的开放境域中,人因对自己负责而永远不会产生僵化的问题。当然,道具有宣教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道是可以“弘人”的。
二、人的自证:价值建构的形式
人的自证与仁的来源紧密相关。关于仁是什么,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论语集注》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章后注曰:“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为远者;反而求之,则即此而在矣,夫岂远哉?”这实际上赋予了“仁”以某种先验性。在哲学运思方式上,朱熹与孟子相近。
近代也有很大的争论。牟宗三先生认为“良知是呈现”:“三十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十力)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之语底根据是康德。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良知是真实,是呈现,这在当时,是从所未闻的。”后牟宗三先生花三十年的时间来理解、消化“良知是呈现”这一命题,自谓得明启而学术大进。他认为,“良知”是一个创生的实体,该实体既是“理”又是“心”。“儒家之天命不已的道体就是创生万物……乾元就是最高的创造原理。所以儒家看天地之道,是‘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这就是创造,创生万物。”但“理”不具有“活动性”,只有“心”才具有“活动性”,是“心”创生了“良知”,使“良知”具有了“活动性”,故能滋道德、生善行。但这一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理”从哪里来,“心”为什么有创生性,牟宗三先生并未说明。这仍是受康德“倒逼”思路——即从现象推定本源——的影响,与原始儒家历史实践本体论思想相去甚远。
在原始儒家看来,仁不是纯粹的客观或主观性的存在,而是一种主客观融合的审美性的情理结构,是以社会客观性为基础,以人性心理追求为主导,以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为动力源泉的灵动的心理生成。仁具有历史性、实践性、开放性和社会客观性。
从精神实质上讲,王阳明的良知说是对孔子仁学的进一步阐发。著名的阳明“四句教”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人生来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这是“心”的本来样子。为什么“有善有恶意之动”?因为人性当中有动物性和社会性两部分,人的社会性一动便是善,动物性一动便是恶,这就是“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是在一定历史阶段里形成的最合理的应然观念,人的情感认同使这些观念化为生命情感,这种生成在人的心理中的情理交融的情感状态就是良知,以这种情感状态对情事进行观照就能知善知恶。“为善去恶是格物”,是由上面的良知情感状态上升到理性状态,因为对于有些善的东西人们不一定愿意留下,对有些恶的东西人们也不一定愿意去除,所以“为善去恶”必须由理性来控制完成,这就是“格物”。如果能够再将“格物”的理性化为生命的情感状态,那么人格境界就上升了一个层次,这是一个螺旋上升、永无止境的过程。
所以,“仁远乎哉”,道不远人,仁就在人的心中,因为仁是由每个人以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为动力建立起来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因为仁在每个人的心中,所以,只要“欲仁”,仁就一定能来。为了人类的存在与发展,必定是多数人在多数时间里“欲仁”,而不是相反。上述的一切有关仁的生成的心理活动,都不受外在条件的影响和限制,完全是主体的自由、自主的选择,因此是自证。
所以,人的自证即人的自我证明,是指人不依赖于外在价值评判系统的内在价值的自我贞立,是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在价值建构中的表现形式和必由路径;只有通过人的自证,即只有在人的自证的情理交融的状态中,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才能开始价值的建构,向人的理性积淀价值观念(对这种价值观念的情感体认而形成的情理交融的状态则是人的人格境界的又一次提升)。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是人的自证的动力源泉,人类总体意识是人的自证的根据和指向。
人的自证何以可能?这是由中国文化中人的“自足性”决定的。在中国主流文化中,没有外向超越的价值观念,人的一切价值都是由人自己建立的,在这一意义上,人无待而自足。“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闻道”,不在于生死,人通过“闻道”而建立价值,并超越生死。“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也’,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鬼神是否“赦免”人之“罪”对于人的道德的圆满并无意义,人生的全部价值只在于现实道德的完满,而不在于是否信奉鬼神。鬼神既然对人能否实现价值毫无意义,人和鬼神也没有任何关系,鬼神有无的问题就是假问题,这就是对鬼神无待。同样,对他人也无待。“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剪除外在“天”(命运)“人”(机会)的因素,只有通过“下学而上达”的进德方式,才能由现实到超越,最终达到与“天”同在的人格境界。
摒除一切外在因素,剩下的只有个体的自觉,这就是人的自证。“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就是人的自证宣言。
人的自证只对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负责,因此保证了它的纯粹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成为(正面)价值建构的形式,即一旦人的自证出现,便会有(正面)价值向人的情感积淀。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是中国主流文化价值建构过程中的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是由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为动力正向生发出来的,而不是像康德的自由意志那样以“倒逼”的思路逆向推导出来的,在建构理路上没有留下外在设定的罅隙。
三、人的自证与悲剧意识的兴起
一般说来,悲剧意识是指人在对现实悲剧性的把握过程中由于对待现实悲剧性的态度、方法和目的的不同而产生的各种思想和意识;现实悲剧性则是指人的主体意识(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自觉意识)与客观限制之间的矛盾。对于中国主流文化来讲,主体意识与客观限制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即宇宙中性、价值无解和生命有限,而在三个问题中,生命有限处于核心位置。因为生命有限性如果得到了解决,其余两个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思路和可能;反之,无论是希望把宇宙自然当作人的外在归依,还是将人的精神价值当作人的内在归宿,都会留下宗教设定的罅隙而落不到实处。
问题是,在中国主流文化中,这种悲剧意识从何而来?即在面对不可改变的客观限制性时为什么会有与之冲突的主体意识?这是由中国主流文化的价值建构方式决定的。
自证是人的心灵处于最纯净状态时的精神走向,也正是在这种最纯净的心灵状态中,人的动物性必然最彻底地显露出来。在人的高智商的观照下,这种最彻底的动物性不是食色二性,而是希望人永远活着,进而希望填满各种根本无法填满的欲壑。同时,这种高智商又使人明确地知道客观限制性,即人不可能永远活着,也不可能满足自己的各种不合理的欲望,于是,人的主体能力的某些方面(主要是高智商)与客观限制性之间便产生冲突。
在这个意义上,人的高智商是没有价值属性和情感色彩的纯粹的智能,这种智能只能感知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并对此产生恐惧感,这就是现实悲剧性的产生。现实悲剧性不带有情感色彩和价值倾向,因此不是悲剧意识,它只是人的高智能在认知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当然,这是人的高智能能够提出的所有问题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
当悲剧性问题凸显出来时,由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融合而成的人性心理必定对此进行各种形式的把握,由此而产生的思想、观念、情感等就是原初意义上的悲剧意识。
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决定了人有着对现实悲剧性进行把握的永恒冲动,同时也决定了这种把握的指向,即对现实悲剧性的超越,这种对现实悲剧性超越的指向就是中国文化中的悲剧精神。
人的自证虽是纯粹的心理活动,但绝非无所依傍的绝对自由,而是恰恰相反。人在剥除了外在依赖和束缚的时候,人的本真心灵就会呈现,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就会鲜明、充分、彻底地显现出来,人类总体意识就会自然而然地生成,因此,人性心理在对现实悲剧性进行把握时,其依据是人类总体。
人的动物性是人性的基础,人的社会性是人性的主导。在人的自证中,人的高智商观照下的动物性决定了现实悲剧性的产生,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融合而成的人性心理决定了悲剧意识的兴起,人的社会性则决定了对悲剧意识的超越。
当然,自证的过程并不一定都伴随着悲剧意识的兴起(在很多情形中自证直接选择了历史合理性),但却不可避免地有悲剧意识的兴起。因为对人的社会性的检讨是自证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情形(即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追问),一旦启动这种检讨,就必然会触及人的动物性(“人”生本无价值,只求“活着”),一旦触及人的动物性,现实悲剧性就会产生(高智商观照下“人”意识到不能永生的现实悲剧性)。因此,人的自证中存在着对历史合理性的直接体认和追询两个基本维度,以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为永恒的动力,对历史合理性的直接体认便直接积淀价值,而对历史合理性的追询就必然触及生命有限的现实悲剧性,这就是原初意义上的悲剧意识的兴起。这种悲剧意识对于其他所有类型和所有层次上的悲剧意识都具有基础性意义。
必须看到的是,当这种原初意义上的悲剧意识产生之时,给人感受更深刻的往往是生命的悲情,“哀兵必胜”的悲情力量反而更激发了对这种现实悲剧性的超越——一种经过追索后的价值建构的冲动。因此,悲剧意识的兴起不仅不会使人走向空虚和毁灭,反而能够使人更加坚强起来。
悲剧意识的兴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从根本上净化价值,从根本上保证价值建构内容的正确性。在人的自证的第一个维度——即对历史合理性的直接体认——中,人往往无法选择和确认历史合理性,因此,有些价值建构未必是正确的,这些不正确的价值就不能称其为价值;而在悲剧意识兴起时,人只对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负责,即只对人类总体意识负责(因为只有这样人才能因获得价值而永恒),从而摆脱了很多僵固观念的束缚。因此,通过悲剧意识的兴起而建构的价值总是纯净和正确的。当然,这里的价值更多地是指向文化层面的,而非指向社会或政治层面的。
现实悲剧性与人共生共在,是人的重要存在形式,因此它不会被克服,也不会消失,但它可以被超越,“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就是对悲剧意识超越的经典表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是说“闻道”后就可以死,而是说人生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在于“闻道”,不在于生死,即“闻道”可以超越生死。在这里,将“闻道”与生死对举,也说明“闻道”与生死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如果生命可以永恒,人就不必急于“闻道”;既然生命不能永恒,人就应该用“闻道”来超越这种无可逃避的现实悲剧性。这个意思,也可以用西方某些哲学流派的观点讲,即死亡是价值的起点,但价值建构的心理机制和原动力,这些流派并没有讲清楚。
中国主流文化中的悲剧超越不是走向外在,而是走向内在,在人的精神境界的观照下而执著现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在说了“逝者如斯夫”后,没有对人生的有限性采取直接的对策,而是如实地描摹了水流的性状:“不舍昼夜”。流水逝去,人生有限,这是不能改变的悲剧性现实,如果进行理性追询,就必然导向宗教;而承认现实,深情感慨,则导向审美超越。这种深情感慨既来自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同时又向人要永恒地“活着”开出:既然逝水不回,流水不停,那么人生也应该像“不舍昼夜”的流水一样,把握一切可把握的东西,做一切应该做的事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首先激起的是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继之而起的是人绝待于天、人的自证,与自证同时兴起的是生命的悲情——无法超越人生的有限性;在经过这种反复的情—理相融的心灵磨啮之后,最终选择的是“天人合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舍昼夜”。
中国悲剧意识的形态应该在中国哲学与文学的互证中来确定,中国文化虽一脉相传,但其哲学思想丰富,流派众多,哪些哲学思想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需要细致分析。事实上,如果将哲学分为内在亲证和外在设定两种路径,则哲学史上的很多问题可以更明晰地划分和解决。以中国哲学为例,以孔子、王阳明为代表的中国主流哲学走的是内在亲证的路径,而以孟子、朱熹为代表的哲学走的是外在设定的路径。中国文学艺术中蕴含的主要是孔子、王阳明的思想,这些思想已经内化为我们的民族情感,是我们民族文化最深层的心理结构,对我们的价值建构和存在方式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孟子、朱熹的思想更多地指向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对民族文化心理影响较小,有很多时候甚至仅仅停留在“高头讲章”的格位上。
中国文学中的悲剧意识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态:生命悲剧意识、价值悲剧意识和冲突悲剧意识。生命悲剧意识直接指向的是对生命有限现实悲剧性的把握,先秦汉唐时期的文学对此体现得较多。价值悲剧意识指向的主要是价值的建构,宋代文学对此体现得较多。冲突悲剧意识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人想永生与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和各种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而之所以有这些冲突,就是因为找不到价值,正是因为缺乏价值感,人的感情需求才被极度发扬,因此产生了突破生死有限性的一些戏剧和小说(如《牡丹亭》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什),这也是明清浪漫主义思潮兴起的重要文化原因。
这三种悲剧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以生命悲剧意识为基础,以价值悲剧意识为核心,以冲突悲剧意识为最为激烈的表现形式。对于上述三种悲剧意识,各个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情景中表现的侧重点是不尽相同的,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割裂的,在很多情况下是融合在一起的。
悲剧意识是中国文学的基调,通过悲剧意识的兴起进行价值积淀是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唐诗宋词中悲剧意识最为丰富,也最为全面,其对后世的影响和对中国人心灵塑造的作用也最大。
注
释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2]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3]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4]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5]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