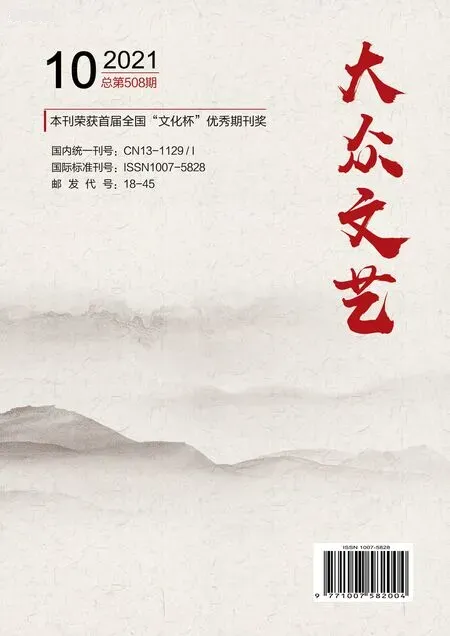象征主义与风景画
章 犇 (江苏省书画院 210019)
象征主义与风景画
章 犇 (江苏省书画院 210019)
在1890年,在欧洲的不同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绘制风景画的样式,显然易见,画家所注重的是伴随着形式的日益抽象来表达特定的心理诉求。风景画,事实上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就成为一种关键的绘画题材,尤其是印象主义的绘画,它加速了“主题绘画”的“死亡”。然而就在它剥去它的描述性功能的题材之际,象征主义有效地将风景画变回了一种主题性的对象。虚幻和现实的空间就如同一个介于与神话和历史有着冲突的场所一样。
风景画;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者的风景画是极度主观的,几乎很少出现有关象征主义对风景画处理手法的质疑,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明确地将风景画转化为本文所说的“主题”。这种变化是对绘画的空间与俗世的世界的简单图像的不满的觉醒。在1890年,在欧洲的不同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绘制风景画的样式,显然易见,画家所注重的是伴随着形式的日益抽象来表达特定的心理诉求。
阿尔伯特·加缪声称:“尼采,在超越露·莎乐美后,走进了一种永恒的孤独。在从事这项他自己建立的浩瀚的工作时所产生的思想是活跃的、粉碎性的。夜晚漫步在群山中俯视热那亚的海湾。点燃叶子和枝条并且观看它们燃烧。”1这幅关于孤单的创造者的在夜色下点燃火苗、从高处往下看的图像,是尼采追寻巅峰的最让人钦佩的召唤之一。查拉图斯特拉离开本国国土去寻求一个之前只存在于他想象中的山的环境,那些被少数先知的蛇和鹰探访过的山峰——是哲学家的头脑可以超越人类精神的地方。2一个可以拥抱世界的有秩序的整体的观点,即将宇宙还原为一个美学的和哲学的概念的观点被塞冈蒂尼采用。他最初在米兰师从于布拉雷,并于1880年搬迁到布里安扎,开始围绕布里安扎进行户外写生。十年之后,他的声誉已经响彻了意大利,他的那些与阿尔卑斯山风景相关的作品在柏林、慕尼黑和利物浦相继展出。1894年开始,他回到海拔6千米的恩加丁高地,在这里,他每天持续工作,引领了一些意大利的知识分子。这时,他已经成为欧洲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但是他的生活是乌云密布的,原因是他没有获得意大利国籍。他出生在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区的奥地利国家,他因为诡辩自己的国籍在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之间而被抓,最后他定居在了这里。
在1897年,塞冈蒂尼写了一封信给维托里奥-皮卡,信中描述了他准备将一幅恩加丁全景图在1900年的世博会上展出的宏大计划;他提到了一件完整的艺术作品应该是对壮丽的自然的再造,“一件有关于阿尔卑斯山作品由声音和颜色共同组成,包含了高山上的各种和声”。3早些年前,他被一首据说是路易吉-埃利斯从梵文里翻译出来的诗激励而重生,从而转变为了塞冈蒂尼的象征主义。在《邪恶的母亲》中,马洛亚地区的山脉被准确的描绘。对纯洁和幽静的赞颂是否达到了最高点成为了辨别一个艺术家和一件风景画身份的证明,对于一种视觉的表现,塞冈蒂尼已经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山脉都属于地球,他们构成了人类能够凝视的广阔无垠的蓝天,代表着一种完全超出了人类生存的愿望、灭绝的欲望--重生。这一时期也见证了塞冈蒂尼对海拔高度的追求,那是一种对巅峰的向往,摆脱了浪漫主义画家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潮流趋向于独特和雄伟,这种类型的意向为泛神论增添了一种新的语调。群山成为一个蕴含着高远沉思的地点,它所遗留下的不仅是朴实的需要征服或防御的土地,也包括这日常生活中的平庸的风景。因而十九世纪晚期的评论,远非仅仅将乔凡尼·塞冈蒂尼视为一位描绘群山的艺术家,而是用他的例子建立一个孤独的艺术家与现实分离的神话(并且与那些选择日常的场景作为他们的领地的印象主义画家形成鲜明对比)。
象征主义风景画彷徨在两个极点之间:宇宙的整体和精神的幻想。爱德华-蒙克的《呐喊》表现了一个接近疯狂的人,艺术家的创伤被印刻在了风景画里。关于焦虑的强烈悸动没有通过转换地形来表达,然而,透视也完全不能够被辨认。克里斯蒂那的峡湾和城区是完全可以辨认的,虽然这个自传体景观因经过彻底的非描述性的处理而导致旁观者的注视方向不同。此外,蒙克按照惯例根据小镇的地形选择制高点来描绘小镇。艺术家站在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其中一个想最后看看这座城市,之前是站在了这条向北的道路的前头。这个熟悉的地点的转换发生在两个不同的阶段,自从1892年1月22号它就被认为是好的,蒙克记在他的日记本上的一件往事间接导致了《呐喊》的出现。“我和两个朋友一起散步,太阳正落山,忽然感到一阵惆怅,突然天空亮了起来泛起了血红色。我停了下来,感到十分疲惫,扶着栏杆,看着云泛起了血色,峡湾和城市上面笼罩着一层黑蓝色,我的朋友走开了,我保持不动,身体因恐惧而瑟瑟发抖,我长时间的惊叫着,无尽的惊叫声能够穿过一切荒凉之地。”4消失的不仅仅是那些风景画中的细节,还有那些传记,故事的解释在分阶段消失,人物在前景中,他开始作为一名扶着栏杆的艺术家,转化到嚎叫的人影,再到人与自然合并的听觉形象。
象征主义是赞同天地合一这个观点的,所以象征主义风景画中的天地和前景背景有时会采用相同的处理手法,这样做是为了用相同的结构去统一不同的表述方式。因为这种概念,自17世纪以来都不允许在风景画的练习中使用夸张的结构,只是因为它挑战了风景画的描述功能。消失对纵深空间的描述,这种对自然的修饰是通过一个经过挑选的孤立的场景和一些令人震撼的逼真感形成的。在克里姆特的作品中,通过大量的笔触,符号和图案在画布表面的覆盖,不同的平面仿佛消失在画的表面上。这种对纵深空间表述的概念有时会体现在一个简单的表象当中,就像画面仅通过一棵孤单的树却给画的意味带来明显的改变。在回顾修拉在制定他绘画中问题的时候 ,古斯塔夫.卡恩于1924年写道:“修拉第一次用的带大条纹的白色框架很快就让他感到厌恶,它就像在画的四周放置了一个屏障。相比孤立这一状态,修拉更为厌恶的是它彻底破坏了一种在背景与角落中与主题相呼应的和弦。他开始尝试通过重复画面的色调,有序的笔触去绘画画框,从而克服这个缺点,5最终,他脱离了画面的局部,进行主观的修改切割。这样做对他来说很痛苦,他基于深层的逻辑和感情,认识到艺术的要求和需要应凌驾于工艺上的现实性(技艺上的写实性)。但绘画终究只是绘画。然而,它仍是自然的一部分,这种绘画的概念引起了修拉的焦虑,同时这种焦虑也影响到马拉美。马拉美面对一本书的结构和它页面的延续性问题时候,他选择反对杂乱脱节的诗歌和华丽辞藻形成的枷锁。在理解这一点的基础上,他发现用绘画的空间来比喻宇宙整体这个概念似乎跟新印象主义对颜色的理念是不可分割的。通过主观的修改,作品的个性化的表达已被削弱到最小。
随之而来的影响就是越来越多带暗示性的风景画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的欧洲,画中的世界相对应更符合一个理念——艺术应当消除一切的记述性。那时象征主义风景画甚至仅仅被定义为一个模糊的,根据抽象的韵律编排的画面。户外写生和印象派的革命其中大部分发生在风景画领域,由此传统审美开始被一种认为“主观感受,画面的主要感觉该让位于知识分子对客观存在的实质理解和表达”(主观感受应让位于客观存在)的审美所超越。在马拉美谈到受到新印象主义这种奇迹般的转变的影响的一份批注中,他问道:“如果非得让纯概念通过客观存在去表达,那么这种通过文字游戏去使自然片段的失去生气的奇妙转换有什么意义呢?”6
注释:
1.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1957年12月14日的会议”.《讽刺诗》(巴黎,1958年),P68-69.
2.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由杰纳维夫·比安基斯编辑(巴黎,1969)P53,P81.
3.1897年11月4日塞冈蒂尼与维托里·奥皮卡通信,《未公开的信件》(奥焦诺 - 莱科,1985),P645.
4.参见展览《蒙克在法国》(巴黎:奥赛博物馆/奥斯陆:蒙克美术馆1991-1992)的展览目录,P361.
5.居斯塔夫·卡恩,《法兰西信使》(巴黎,1924年4月1日),P14.
6.斯蒂芬·马拉美,《德雷娜·格希尔》,伯特兰·马夏尔编辑(巴黎:伽利玛2003),P768.
[1]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1957年12月14日的会议”,《讽刺诗》[M](巴黎,1958年).
[2]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M],由杰纳维夫·比安基斯编辑(巴黎,1969).
[3]1897年11月4日塞冈蒂尼与维托里·奥皮卡通信,《未公开的信件》[M](奥焦诺 - 莱科,1985).
[4]参见展览《蒙克在法国》(巴黎:奥赛博物馆/奥斯陆:蒙克美术馆1991-1992)的展览目录[M].
[5]居斯塔夫·卡恩,《法兰西信使》[M](巴黎,1924年4月1日).
[6]斯蒂芬·马拉美,《德雷娜·格希尔》[M],伯特兰·马夏尔编辑(巴黎:伽利玛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