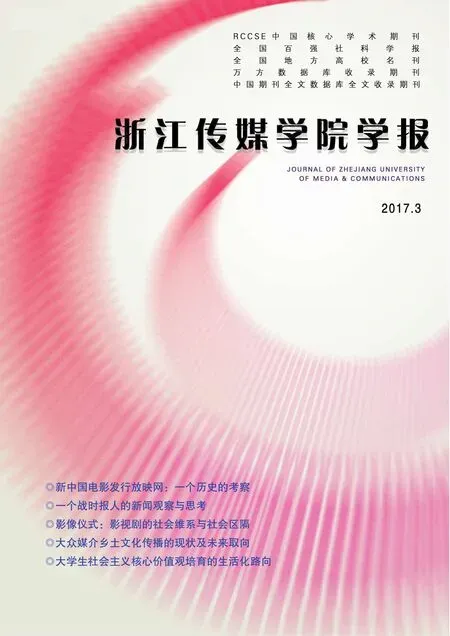原型范畴视角下“绿”语义的认知解读
贾改琴
原型范畴视角下“绿”语义的认知解读
贾改琴
“绿”作为汉语中的基本颜色词之一,从隋唐沿用至今。“绿”的语义由最初的颜色义不断扩展丰富,现在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多义词。以原型范畴理论为研究视角,分析“绿”由“青黄色”的原型义项向“通行、快捷”义、“环保、健康”义、“卑微、卑贱”义等边缘义项扩展过程中的深层认知理据性原因,得知范畴特化和隐喻演变等对“绿”语义扩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词义扩展中范畴结构保持稳定性的主要原因在于词义原型的稳固性。
“绿”的语义;原型范畴;家族相似性;隐喻演变;范畴特化
语言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程度的体现。人类对世界中绚丽色彩的认知体现在了语言的颜色词系统中。语言中颜色词的发展是进化式和有序的:黑/白>红>黄/蓝/绿>粉/橙/灰/紫。基本颜色词的语义范畴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以物代色—以物比色—抽象化或符号化—隐喻化。[1]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颜色词除了表示事物的颜色之外,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还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带有鲜明的民族和文化特色。
本文主要讨论基本颜色词“绿”的词义演变情况。对“绿”语义的研究目前大都集中在“绿”的义位结构分析、词义变化及其所体现的英汉文化的对比分析等方面,如李蓉(2007),[2]王春磊、杨蕾(2009),[3]黄林慧(2009),[4]丁道勇(2011),[5]吴建设(2012),[6]桂永霞(2013)[7]等的研究成果。而从原型范畴的角度来解释“绿”词义演变机制的相关研究还很少看到,“但根据Geeraerts(1992,1997)的说法,如果我们站在认知立场上,用原型范畴来解释词汇意义,那么词义发展过程中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共存就可以得到最好的解释”。[8]
一、原型范畴理论
为了认知万千世界,我们必然要对事物进行分类。范畴就是人类对外界事物进行主观概括和类属划分的认知结果,但范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和固定的外延,它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而不断调整。
那么范畴怎么划定?范畴成员又怎么确定呢?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Wiittenstein)提出了家族相似性理论(Family Resemblance Theory)。该理论认为,范畴成员是以某一特定方式相互联系的,它们不必拥有定义该范畴的所有属性,但各个范畴成立的基础是成员间至少存在一个共同属性,即成员间的属性相似性。正如Rosch和Mervis所述:“每个项目与一个或多个其他项目,有至少一个,也可能是几个共有的成分,但是没有或者很少几个成分是为全部项目所共有的。”[9]
20世纪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Rosch通过关于“图形、颜色、鸟”等范畴的实验提出了“原型”(prototype)概念。[10][11]她认为,属性是范畴结构的主要部分。“认知范畴的原型成员指的是拥有最多的与这一范畴的其他成员的共同属性,而拥有最少的与相邻范畴的成员同现的属性。”[8](35)所以,原型就是“范畴的最好样本”、“范畴成员身份最清晰实例”、“一个类别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或者“中心和典型成员”。[12][13]如“知更鸟”和“麻雀”完全拥有整个属性集束,它们就可以看做是“鸟”范畴的原型,也是最好样本。
20世纪80年代,Lakoff 和Taylor对此作了更深层次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提出可用理想化的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简称ICM)来解释原型范畴,强调了范畴化过程中人的主观认知能力和想象力。他们认为,“原型”和“范畴”都是人类的认知活动,语言中的范畴都有原型范畴。颜色范畴也一样,它不是任意固定的,而是固定在焦点颜色上的。而焦点色具有特殊的感知—认知的显著性,这种显著性可能独立于语言之外,并反映了人类感知机制的生理学上的某些方面。词义范畴也一样,一个多义词有原型义项和边缘义项之分,词义范畴就是围绕着原型义项不断向外扩展而逐步形成的。
二、“绿”的语义
汉语中的颜色词“绿”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但直到隋唐两宋时期,它才作为常用的基本颜色词出现在各种文献当中。[6](13-14)“绿”也是Belin和kay在1969年进行的Munsell色卡实验中收集的近20种语言的基本颜色词之一。[14]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绿”被解释为:“象草和树叶茂盛时的颜色,蓝颜料和黄颜料混合即成为这种颜色。”[15]例如:绿叶、绿地、绿茸茸、……这是一种“借物呈色”的描述方式。如: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选自朱自清《绿》)
根据张旺熹的研究,颜色词一般以一定的客体为依托。[16]而“绿”最多的依托为植物,如橄榄绿、苹果绿、茶绿、苔藓绿、豆绿等;还依托于玉石,如松石绿、石绿、水晶绿、墨石绿等。还有一些非典型的表示层次性的依托,如深绿、灰绿、暗绿、青绿、淡绿、碧绿等。
“绿”的本义与现代汉语中的解释相似。《说文解字》中写道:绿,帛青黄色也,从糸录声。《广韵》解释道:“绿,青黄色。”例如:绿兮衣兮,绿衣黄裹。(《诗经·邶风·绿衣》)“绿”在古代还指乌黑色,古诗词中常用来形容头发。[17]最典型的就是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的:“绿云扰扰,梳晓鬟也。”这里的“绿云”就是指乌黑的头发。此外,还有“绿鬓”,指乌黑而光亮的鬓发,引申为青春年少的容颜;“绿媛”,指黑头发的美女等。但随着语言的发展和词义的调整,“乌黑色”这个义项没有被沿用下来。因此,本文主要关注“绿”最常用的基本义,即“青黄色”这一义项。它也是发展出其它引申义项的原型义项。
结合《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绿”的边缘义项(也称作“引申义项”)主要包括如下几种:(1)指简便、安全、快捷的途径或渠道,如“‘绿’色通道”;(2)生命力,活力,希望,如“绿洲”;(3)符合环保要求,无公害、无污染的,如“绿色食品”;(4)卑微,卑贱,如“绿帽子”。
三、“绿”语义的范畴特化
从原型范畴理论的角度来看,“词义的演变被描写为泛化、特化、比喻用法”。[8](356)语义范畴特化是词汇演变的三种基本类型之一。词语的语义原型是一个范畴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认知能力的变化,这个范畴集中的某个义项或者义素被特定化,从而以此为中心引申出其它的边缘义项,这便是范畴特化。不管是哪种演变类型,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该词的原型范畴结构。
(一)“绿”语义的原型范畴
“绿”的原型义项为“青黄色”。人类认知经过了一个以物代色、以物比色的过程。“绿”原型语义的认知当初也是借助于“草、树、菜”等原色。所以在人类最初的认知模型中,“绿”的原型义项所对应的外延范畴很多,我们称之为“绿”的范畴家族,可用图表示如下:

图1 “绿”的范畴家族图
图1中,粗实线连接的是“绿”的典型样本(好样本),而细实线连接的为“绿”的边缘样本(差样本)。其中,典型样本拥有比较多的范畴属性,而边缘样本则仅拥有比较少的全范畴属性或相似属性,称为家族相似性属性。其范畴属性情况如下:
全范畴属性选 家族相似性属性选
a.青黄色 e.生命
b. 部分或整体 f.生命力最为旺盛时
c. 显著 g.本色,无加工
d.安全色,与“红”色对比最强 h. 非本色,加工
i. 稳定,永久
上述属性集合是对“绿”的原型义项——“青黄色”——的深层次分析。可以说,每条属性就是一个义素,这可以看成是“绿”的语义原型的属性集。它的边缘义项是以这些属性为原型通过某一种方式引申出来的。
(二)“通行、快捷”义的认知解读
“‘绿’色通道”在现代汉语中被广泛使用,解释为“医疗、交通运输等部门设置的手续简便、安全快捷的通道;泛指简便、安全、快捷的途径或渠道。”[15](893)要说清楚这个义项的来历,还要从其原型义项说起。
由“绿的范畴家族图”可知,“青黄色”和“安全色、与‘红色’对比最强”为其全范畴属性,即为其外延成员所共有的一条原型范畴属性。“绿”作为“安全色”的来源还要从人类对“红”的认知谈起。“血”为“红”色,而“血”在中华文化中有多重意蕴,其中有一种含义是危险。因此,“‘红’灯”表示危险降临,禁止通行;“‘红’灯区”则表示不宜去的地方。而“绿”色为草木等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的颜色,代表着生命。同时,人类的认知体系里也被认为“绿”是与“红”对比最强的一种色彩。因此“绿”便作为了一种生命色、安全色和通行色。
“‘绿’灯”长期作为通行信号灯,其“通行”义是很具体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各种需要特殊照顾的情况,为了予其方便,便让其先行“通行”,于是便出现了“‘绿’色通道”、“‘绿’卡”、“开‘绿’灯”等词汇,“快捷、方便、畅通无阻”等义项也就成为了“绿”的常用边缘义项。
因此,“绿”的“通行、便捷”的义项是凸显其“安全色,与‘红色’对比最强烈”的全范畴属性和相似性属性“生命,生命最旺盛时的颜色”而形成的结果,是对其特化的结果。
(三)“生命、环保、健康”义的认知解读
《现代汉语词典》中,“符合环保要求、无公害、无污染的”是“绿”的主要引申义项之一。为了表述的简便,这儿表述为“环保、健康”。此义项在汉语中的使用很广泛,如“‘绿’色蔬菜”、“‘绿’色食品”、“‘绿’色殡葬”、“‘绿色’GDP”、“‘绿’色科技”等。
“环保、健康”义的出现与社会发展有很大关系。二战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先后实现了工农业的现代化。在增大农作物产量、满足食品供应的同时,也使大量化肥和农药流入农田,环境和资源遭到了破坏,人体健康也受到威胁。20世纪70年代以来,源于美国的“有机农业”思潮影响了许多国家。1990年5月,我国农业部正式规定了“绿色食品”的名称、标准及标志。
“‘绿’色食品”(green food)指无公害、无污染的安全营养型食品。[15](893)“无公害、无污染”就是要保持农作物本来的生长规律,不使用添加化肥、农药等促其成长的手段,在制作过程中也不使用添加剂等。总之,就是要保持其本色,顺其自然。而“绿”语义原型的属性集中,有两条,即:“青黄色;本色,无加工”。后来的词义发展中,以此为基础,在特定的环境下,引申出了“无公害、无污染、健康、营养”等义项。
不使用农药、化肥,便不破坏土壤,保持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绿”后来又产生了“节能、环保、可持续”等义项,例如:“‘绿’色出行”、“‘绿’色奥运”、“‘绿’色管理”等。这样“绿”的语义便由简单走向了抽象。因此,“绿”的“环保、健康”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新的环境条件下,由其“青黄色、本色、无加工”这两条基本义项特化而来的,是人类认知由简单走向深入的一个体现。
四、“绿”语义的隐喻演变
大多数隐喻用法都源自把词汇范畴的边缘统一起来的家族相似性,而不是源自范畴的中心。这儿主要讨论“绿”的边缘义项中的隐喻演变用法,即“卑微、卑贱”义的认知解释。
(一)“卑微、卑贱”义的认知分析
谈到这个义项的来源,我们不得不从当时人们的认知模型说起。认知模型表现的是一定时期人们对某一领域所储存知识的总体情况。在一个认知模型中,任何一个认知范畴的成员都包含原型、好样本和差样本等,“颜色”范畴也不例外。
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盛行。当时人们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宇宙万物的五种主要元素,它们充盈在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它们相生相克,共同维系着自然的平衡。五行有着它们各自相应的质地、声音、形状、颜色等。因此,古人曾认为,五行所表征的颜色即青、赤、黄、白、黑为正色(纯正的颜色),而其余的颜色如绀、红、缥、紫、绿等是由正色混合而成的颜色,属于间色。《广韵》中解释“绿”为“青黄色”,孔颖达注疏为“绿,苍黄之间色”。由此可知,“绿”是由青色和黄色调和而成的,属于间色。郑玄首次列举正色、间色各一种,如《诗经·邶风·绿衣》中所写:“绿,间色。”
在中国早期社会人们的认知模式中,正色是事物相生,即相互促进的结果,而间色是事物相克,即互相冲突、排斥的结果。“正色”代表着纯正,突出,高贵。而间色是杂色,不纯的颜色,也就代表着低微,次要,卑贱。因此,古代规定“正色做衣服,间色做下裳”。并且把正色和间色作为名贵贱、辨等级的标志,所以作为间色的“绿”就有了“卑微、卑贱”之义。
(二)“卑微、卑贱”义的隐喻演变
“绿”由原型义项“青黄色”发展为边缘义项“卑微、卑贱”,可以分析为人类认知的一种隐喻演变,是当时人们关于宇宙中物质的认知模型在“颜色”范畴认知域中的类比转移。这个类比转移的过程可以用符号描述为:
S:CONTAIN(物质|五行,其他元素)
T:CONTAIN(颜色|正色,间色)
∴(五行≈正色),(其他元素≈间色)

图2 物质域向颜色域的类比映射
图2中,“物质”域中包含“五行”和“其他元素”,而“颜色”域中包含“正色”和“间色”。“五行”在“物质”域中具有“好样本”(即原型)和“相互促进”两个属性,而“正色”在“颜色”域中也具有对应的属性;“间色”则类似于“其他元素”,是其论域中的“差样本”(即边缘成员),并“相互冲突,排斥”。
这一认知过程可用扩展的谓词逻辑描述为:∃T1∃T2∃T3∃T4[(ACTION(T1,好样本)∧AGENT(T1,颜色)∧PATIENT (T1,正色)) ∧(ACTION(T2,相生) ∧AGENT (T2,正色)) ∧ (ACTION(T3,差样本) ∧AGENT (T3,颜色) ∧ PATIENT (T3,间色)) ∧(ACTION(T4,相克) ∧AGENT (T4,间色))。
(三)“卑微、卑贱”义的体现
人类对“卑微、卑贱”义的认知主要体现在我国古代的服饰制度中。《诗经·邶风·绿衣》中写道:“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宋代的朱熹注解道:“间色贱而以为衣,正色贵而以为里,言皆失其所也!”他认为《诗经·邶风·绿衣》是春秋时期齐国公主庄姜所作,“庄公惑于壁妾,夫人庄姜贤而失位,故作此诗,言绿衣黄里,以比贱妾尊显,正嫡幽微,使我忧之不能自已也”。庄公把贱妾比作绿衣,把正嫡比作黄里,“绿”的“卑微”之义显而易见。
到了隋唐,“绿”有幸成为了官吏的服饰颜色。《隋书·礼仪七》中明确规定: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贾以皂,士卒以黄。即六品以下的官员要着“绿”色官服。唐代很多诗人在诗歌中反映了因穿着青衫绿衣而苦闷怨恨,例如,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写道:“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是一个九品官吏,要着青衫。《忆微之》中的“分手各抛沧海畔,折腰俱老绿衫中”反映了白居易因着青衫绿袍而苦闷郁恨的惆怅。此外,“黄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杜甫),“自堪成白首,何事一青袍”(高适)等也都体现了对绿衣青衫的怨恨。元代时“绿”衣被降为了八品、九品官员之官服。
“卑微、卑贱”义在现代汉语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绿’帽子”。“‘绿’帽子”来源于“‘绿’头巾”。在古代,“‘绿’头巾”是一种“贱”服,有“羞辱、侮辱”之义。唐代封演在《封氏见闻记》中讲到: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投巾以辱之……延陵县令李封对罪犯不实行杖刑,但命令他们头裹碧绿色的头巾以示羞辱。且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决定裹绿头巾的时间。元明时规定娼家男子带“‘绿’头巾”。《元典章》中规定:娼妓穿皂衫,戴角巾儿。娼妓的家人,特别是娼妓的丈夫,要裹着绿头巾出门。朱元璋也规定:“教坊司乐艺着卍字顶巾,系灯线褡膊,乐妓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民妻同。”即娼妓家的男子头上必须佩戴“‘绿’头巾”,腰上系红色褡膊,脚上穿带毛的猪皮鞋。现代汉语中,“‘绿’帽子”取代了“‘绿’头巾”,指“妻子有外遇的男子”,仍然保持了“卑微、卑贱”之义。
五、结 语
经过了长期的发展,“绿”的语义由最初的颜色义扩展到了“生命力、环保、畅通、卑微”等抽象义项。无论其边缘义项多么抽象,都源于其原型义项。要么是对原型义项中某条或某些属性范畴的特化,要么是对某些属性范畴的隐喻转移。原型义项中属性范畴的泛化也是词义引申和扩展的主要方式之一,不过在“绿”的语义扩展中没有涉及到。
总体来看,语义范畴结构跨了多个世纪却仍保持了极大的稳定性,主要原因在于范畴的中心区域,尤其是原型,在很大程度上未受到范畴特化以及隐喻演变的影响。因此,虽然词语的多义性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但整个词汇系统和词义系统都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归根结底还是原型范畴的稳固性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然,当一个范畴的核心属性被替换时,我们称之为原型转移(prototype shift),这通常是语言外部变化的结果。但“绿”的语义变化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1]陈家旭,秦蕾.汉语基本颜色的范畴化及隐喻化认知[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2):75-77.
[2]李蓉.从认知角度看“绿色”和“green”的异同[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7(10):154-155.
[3]王春磊,杨蕾.“绿”的义位结构分析[J].淄博师专学报,2009(1):49-51.
[4]黄林慧.汉英语中“绿”之隐喻对比研究[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12):75-76.
[5]丁道勇.作为一种教育隐喻的“绿色教育”[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5):136-142.
[6]吴建设.汉语基本颜色词的进化阶段与颜色范畴[J].古汉语研究,2012(1):12-14.
[7]桂永霞.语言的模糊性与全球“绿色文化”[J].怀化学院学报,2013(1):88-90.
[8][德]弗里德里希·温革瑞尔,汉斯-尤格·施密特.认知语言学导论[M].彭利贞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357.
[9]Rosch,Eleanor and Caroline B.Mervis.Family reaemblances:studies i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J].CognitivePsychology7,1975:573-605.
[10]Rosch,Eleanor.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erceptual and semantic categories,Timothy E.Moore,ed.[M].CognitiveDevelopmentandtheAcquisitionofLanguage,New York:San Francisco;London:Academic Press,1973:111-144.
[11]Rosch,Eleanor.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J].JournalofExperimentalPsychology:General104,1975:193-233.
[12]Rosch,Eleanor.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Eleanor Rosch and Barbara B.Lloyd,eds[J].CognitiveandCategorization,Hillsdale,NJ;NY:Lawrence Erlbaum,1978:27-48.
[13]Brown,Cecil H.“A survey of category types in natural language”in Tsohatzidis(ed)[J].Meanings and Prototypes:Studies i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1990:17-47.
[14]Berlin,B.& Kay,P.Basic Color Terms: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M].L.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849.
[16]张旺熹.色彩词语联想意义初论[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8(3):112-122.
[17]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8卷本)[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4321.
[责任编辑:高辛凡]
本文系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基于逻辑视域的认知研究”(11&ZD088)和2016年浙江传媒学院青年教师科研提升计划项目“基于语用论辩理论的美国总统竞选辩论之话语分析”(ZC16XJ029)的研究成果。
贾改琴,女,讲师,文学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H13
:A
:1008-6552(2017)03-013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