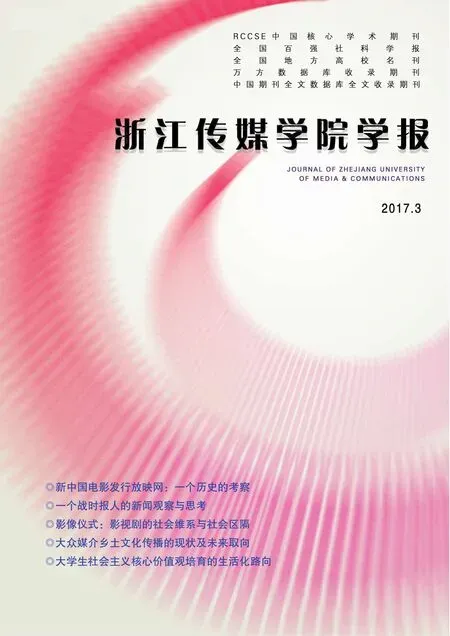个体记忆与学术人生: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口述历史研究初探
陈 娜
个体记忆与学术人生: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口述历史研究初探
陈 娜
以口述历史为主要研究方法,以学者的学术人生发展历程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对当代中国33位新闻传播学者展开的个案研究,提出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在学术边界、学术轨迹、学术路径、学术视野、学术代际、学术情怀、学术争论、学术身份等八个方面的整体特征,并进而对口述历史与个体记忆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可能带来的启示提供参考。
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口述历史;学术人生;个体记忆;新闻传播学者
一
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以来,几代新闻传播学者筚路蓝缕、上下求索的学术人生构成了展现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鲜活窗口,他们的教育背景、治学经历、研究旨趣、学科见解,他们的贡献与遗憾、经验与忧虑、困境与突破,他们对前辈的使命继承及其对后学的导引方向,他们的学术命运与时代、学科的关联等,这一切都无疑是探寻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源头活水,更是把握与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及其理论基础与学术传统的必要前提。
作为影响和推动学科发展的主体,新闻传播学者既受到不同时代下学科发展的影响,又实际参与了学科的建构,在个体命运、群体认同、社会变迁等一系列作用下,不同时代的新闻传播学者在继承与巩固中奠定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命脉,也在反思与突破中影响着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流变。要找到中国新闻传播学赖以依存的价值核心,理解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石的由来,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人生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以当代杰出新闻传播学者的治学路径为研究视角,通过对他们的人生阅历、心路历程、治学经验以及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建树与思考等,具体、生动、实际地展现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轨迹与理论脉络,成了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进程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寻找自身根基与前进方向的重要使命。
有鉴于此,笔者以口述历史为主要研究方法,对33位当代中国杰出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历程展开系统梳理,力求通过对其学术人生的全面呈现与开掘,探索个体记忆之下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时代特征。
具体研究对象如下:

序号姓名性别出生年份工作院校籍贯/出生地主要研究领域1甘惜分男1916年中国人民大学四川邻水新闻理论2方汉奇男1926年中国人民大学广东普宁新闻史3丁淦林男1932年复旦大学江西南昌新闻史4张允若男1935年浙江大学江苏海门外国新闻史5赵玉明男1936年中国传媒大学山西汾阳中国广播电视史6曹 璐女1937年中国传媒大学河北保定广播理论与实务7艾 丰男1938年经济日报河北玉田新闻实务、品牌战略8白润生男1939年中央民族大学河北雄县民族新闻史9邱沛篁男1939年四川大学重庆新闻实务10卓南生男1942年北京大学新加坡新闻史、日本问题研究11刘建明男1942年清华大学辽宁营口舆论学、媒介批评学12赵传蕙男1942年天津师范大学河北抚宁新闻实务、公共关系13吴廷俊男1945年华中科技大学湖北天门中国新闻史、新闻传播教育14郑保卫男1945年中国人民大学山东高青新闻理论、新闻教育、气候传播15李良荣男1946年复旦大学浙江镇海新闻理论16范以锦男1946年暨南大学广东大埔新闻实务、报业经营管理17郭镇之女1951年清华大学江苏镇江外国新闻史、广播电视史18刘家林男1953年暨南大学湖北武昌中国新闻史19孟 建男1954年复旦大学江苏常州新闻传播理论、视觉文化传播20刘卫东男1954年天津师范大学天津新闻理论21熊澄宇男1954年清华大学江西南昌新媒体研究、文化产业22黄 瑚男1955年复旦大学上海中国新闻史、新闻法规与伦理23尹韵公男195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庆新闻传播史24蔡铭泽男1956年暨南大学湖南岳阳中国新闻史25芮必峰男1957年安徽大学安徽马鞍山新闻传播理论26潘忠党男1958年(美)威斯康星大学安徽黄山新闻传播理论27程曼丽女1958年北京大学江苏宿迁世界新闻传播史、国际传播28李 彬男1959年清华大学新疆乌鲁木齐新闻史、传播学29魏 然男1962年(美)南卡罗莱纳大学河南(美籍)新媒体、传播效果30张举玺男1964年郑州大学河南辉县新闻理论与实务、国际新闻传播31赵月枝女1965年(加)西门莎菲大学浙江缙云(加籍)传播学、传播政治经济学

序号姓名性别出生年份工作院校籍贯/出生地主要研究领域32胡正荣男1966年中国传媒大学宁夏银川媒介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33冯雪松男1970年中央电视台内蒙古海拉尔新闻史
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说,“凝聚一个社会(及各次级社会群体)的‘记忆’是一种相当多元的、易变的综合体,在一个社会中,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有同样的‘社会记忆’。所谓‘共同社会记忆’,是在各种社会利益群体的对立与竞争中,强化自身或本群体的记忆,或扭曲、抹杀敌对利益群体的记忆,如此在争辩与妥协中产生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记忆’”[1],区别于文献资料以及文献资料所裹挟的社会记忆。口述历史研究所关注的个体记忆在记忆生产的过程中往往遵循着一套与前者不同的叙事逻辑。以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提出的“意愿记忆关乎体验、非意愿记忆关乎经验”[2]这一对辩证关系为例,个体记忆的叙事规律及其为历史叙事的转向所带来的结构性功能不仅值得深究,更能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提供全新的突破口。
在本研究所面对的33位研究对象中,涉及女性学者4位,男性学者29位;出生于上世纪10年代的学者1位、20年代的学者1位、30年代的学者7位、40年代的学者7位、50年代的学者12位、60年代的学者4位、70年代的学者1位;海外华人/华裔学者4位,大陆学者29位。研究对象的工作院校覆盖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湖北、安徽、四川、河南等多地,其研究领域也涉足新闻传播学多个方向,其学术成果均具有一定代表性。更为重要的是,这33段学术人生中的苦难辉煌实则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勾勒出了一幅真实且丰富的众生图景,其人生轨迹中的共性与个性也足以突显出个体与时代的交相辉映。
二
基于以上,33位受访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人生展现出了一幅历史画卷,其学术经历中所折射出来的学术精神与学科发展之间的勾连,展现出了如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学术边界与政治领域交织紧密
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治学之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大,在本研究中,出生年代越早的学者受到的影响就越深,他们的学术思想、命运轨迹几乎与中国的政治变迁紧密相关。尽管这期间同样存在服从与对抗、跟随与反思的不同面向,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学术命运有着一条相同的逻辑,那便是直接服务于且受制于政治环境,并且这一影响也直接投射在了他们各自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成果之中,更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被永远地保留了下来。当然,政治因素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影响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并非特例,而这种影响尽管在其后年代出生的学者们身上有着相对弱化的表现,但实则依旧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学术轨迹从“半路出家”到“百花齐放”
总体而言,受中国新闻学科建设发展的影响,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治学轨迹大都同样坎坷曲折。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新闻教育的一度中断以及其后的恢复重建,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生的不少新闻传播学者都经历了“半路出家”的辗转,并且很多都是从中文系的专业背景中脱胎而来,而这一点又与早年间新中国新闻学的学科设置和归属地位直接相关。有关于此,与新时期相比,从旧社会走出来的新闻传播学者更为明显,而出生年代越晚,学者们的专业背景就越发呈现出扎实纯粹的科班出身以及学科共融、百花齐放的特点。
时至今日,新闻学的学理基础早已从注重采写的语言文学框架中脱离出来而迈向了更加宏富深刻的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的体系框架,于是从60年代出生的学者开始,除了大多数从新闻专业科班出身之外,中国新闻学界慢慢出现了一大批由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转入新闻学,或是经由新闻学转出到这些学科领域继续深造的学者队伍。在此背景下,中国新闻学在迈入新世纪以来愈发呈现出了多元交融、百花齐放的勃勃生机。
(三)学术路径重思辨轻方法,治学规范相对欠缺
总体而言,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新闻学科自身发展阶段的影响,普遍存在思辨性有余而规范性不足的特点,体现在研究方法系统训练的普遍缺失这一点上尤为明显。而与绝大多数在国内接受学术启蒙的新闻传播学者所不同的是,早在求学阶段即远赴海外并且取得学位的一些学者在研究方法等方面受到了较为严格的训练,并且他们对于国内在治学规范等方面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以及国内学界与国际学界在学术规范方面尚存在的较大差距,大都比较敏感且焦虑。
也正因如此,受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出生于60年代并且求学于80年代的这一批人当中涌现出了一批较为出色的学者,他们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浪潮为契机,较早走出国门,先国人一步与国际学术前沿接壤并且完成了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学术融合,中国新闻学的发展也在他们个体的学术反哺事业中呈现出了新的生机。
(四)学术视野的相对局限及反思
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受制于语言基础、政治环境以及求学经历的客观因素,在学术视野的国际化和开放性上相对局限。并且,在全球化时代下,许多学者往往对这一问题保持着较为清醒的认知,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而这一特点也反映出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极强的集体反思能力和前瞻意识。
有鉴于此,大多数新闻传播学者在着意紧跟前沿、求新求广的同时亦形成了对西方世界知识体系与中国接轨的自觉反思,在学术视野不断开放的同时愈发展现出了理性的辨别能力和审慎的选择能力,这一特点体现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启学术生涯的新闻传播学者们身上尤为明显。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者们正用心用力奔走在一条不断求索的道路上,为新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腾飞和社会建树完成着突破自我和集体超越的蜕变。
(五)学术代际之间的鲜明集体特征
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就是,33位出生于不同年代的新闻传播学者们展现出了相对鲜明的代际特征。其中,出生于旧社会的学者,有着根深蒂固的精神信仰,在特殊年代中历练出来的人生经历锻造了他们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服从大局的精神品质。这一代人有着极强的政治意识和集体观念,自我意识相对较淡,家国情怀强烈,奉献精神较强。
40年代出生的新闻传播学者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展现出了更为多元的精神特质。他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和命运轨迹的重大改变,因此,他们在思想深处往往对历史、社会、政治等方面会产生自觉的质疑与批判。但与此同时,受成长环境的影响,他们的精神深处又无法摆脱传统文化以及制度环境在其启蒙时期对其精神人格塑造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因此这一代学者们身上往往兼具着较为复杂多元的学术性格,在传承与创新中负重前行。
对于50年代出生的新闻传播学者而言,高考改变命运的人生际遇几乎映射在了他们每个人的身上,职业身份的变化与命运轨迹的转折给这一代人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惜时、感恩、事业心、使命感,这些品质成了成就他们的共同标签。
对于60年代出生的新闻传播学者而言,正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精英以中国国门洞开为契机,率先闯出大陆,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开启了与西方学术传统接轨的集体轨迹,尽管出国留学并非60年代出生的新闻传播学者的绝对共性或必由之路,然而时代环境与客观条件的铺垫恰恰让这一代学者在学术资源的享有和学术视野的拓展等方面展现出了与之前的学者有较大不同。
(六)学术情怀的忠诚博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个领域中堪称杰出代表的新闻传播学者们,尽管其出生年代、成长背景、求学经历、学术旨趣等各有不同,但是几乎都兼具一个共同的情怀,那就是对于学术事业的热爱,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
换句话说,一段段具体且生动的个体命运呈现出了这样的规律,即没有深切的爱国情怀与对家国命运的责任意识,也将无法真正成就这些一流的新闻传播学者在学术道路上的建功立业。这也便是赵月枝所说的“学术人格”与“自然人格”合二为一的深层意义。
(七)学术论争由“显”至“隐”
在新中国当代新闻传播学术史上曾出现过几次重要的学术论争,这些学术论争本身也客观反映了新闻传播学自身艰难攀爬的发展历程。有幸的是,在本研究所面对的这33位访谈对象中,许多人都是历次学术论争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然而遗憾的是,这些论争的亲历者中有许多人都已作古,口述历史研究不可避免的怅憾也即在于此。
时至今日,新中国的新闻学科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停滞、沉淀、复兴之后,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而与早年相对浓厚的学术争鸣环境所不同的是,新世纪以来,学者与学者之间就学术问题公开的、直面的、激烈的学术争鸣现象越来越少,新闻传播学在日新月异的媒介社会发展态势之下进入了一个跨学科、多分支的阶段。在学术团体、学术会议、学术交流从主题到形式日益丰富多元的今天,学术场域的人情味愈发浓郁,学者们之间有关学术论争的话语形式和表达方式从显性转向隐形,这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八)学术身份与实践领域的相对脱节
仅以本研究所针对的33位研究对象为例,有过相对丰富和扎实的新闻从业经历的学者并不算多,尽管甘惜分曾担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白润生曾在工人日报社任职一年,邱沛篁与芮必峰都有过长期的校报工作经历,卓南生曾长期主持华文报刊笔政,刘建明在辽宁丹东做过多年的广播电台记者和广播电视局局长,范以锦曾以南方报系掌舵者身份叱咤风云,艾丰与冯雪松均为业界涉足学术研究领域的特例,但此外的绝大多数学者与新闻业界大都缺乏直接、深入的接触,更倾向于从学理层面构建新闻学的学科基石,而这一特点也对中国新闻学的现实图景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纵观33位新闻传播学者学术人生的共性与特性,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学术精神的流变一方面受社会发展变迁中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当代中国新闻学科的发展相辅相成、互为映射。换句话说,从微观层面看,转型社会背景下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分化涵养了新闻传播学者个体学术精神的异彩纷呈;而从宏观层面看,随着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不断繁荣,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对于学科的主体性认知也愈发清晰理性,学术精神恰如学科地位,从曾经的荒芜逐渐走向了自觉、自信。
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赵智敏在其博士毕业论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新闻学之演进(1978-2008)——学术精神的追寻与理论重建》中曾做过如下梳理:“在这30年里,新闻学的学科地位终于得以确立。如果说,共和国前30年的新闻学因为充当政治附庸的属从角色,被驱逐于学术研究的殿堂之外,因而被人戏称为‘无学’的弱学科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里,中国的新闻学则渐渐成长为当前的‘显学’,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学科身份,自立于哲学社会科学之林。30年来,由于学科地位的确立以及相关学术环境的改善,新闻学学术的生产力得到大大解放。”[3]
众所周知,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新闻学受到历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发展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曾一度陷入了“新闻无学”的低谷。尽管造成“新闻无学”这种说法的原因是多重的,例如有人认为所谓做新闻不过就是新闻工作经验的堆积,有“术”而无“学”;还有人认为新闻工作缺乏自身规律,被意识形态裹挟得太久太紧,不过就是对上级宣传精神的领会和遵照,是附属于政治学或文学的子学科而已。然而,造成所谓“新闻无学”之说一度甚嚣尘上的局面,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新闻学迟迟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即便在其中摸爬滚打多年的新闻传播学者对于新闻学的学科边界和理论核心往往语焉不详,相当迷茫,其学术精神的涵养可想而知。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传播学的引入、新闻学术理论体系的不断夯实以及新闻学科建设的日益完善,“新闻无学”的说法时至今日已经逐渐销声匿迹了,至少远远没有了早先的喧沸。几代新闻传播学者的坚实付出正在慢慢打消人们对新闻学曾经的偏见和误解。在中国新闻学逐渐实现重建、复兴并一步步成长为“参天大树”的同时,其研究主体的学术精神也在经历着不断的磨砺和塑造,并且在学术环境的日益变迁之下呈现出了自觉追求、自信坚守的全新气象。遍览33位新中国杰出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人生,他们在兢兢业业参与新中国新闻传播学术殿堂筑造的历史过程中,也不断接受着历史变迁与学科发展在他们身上所留下的烙印。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回忆、他们的历经沧桑、他们的悲欣交集,无一不是中国故事的绝佳例证,也无一不彰显了中国学者的真实心路。
总而言之,穿越时代巨变,兼具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正在形成,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集体格局与个体特质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并且融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之林。
[1]王明珂.谁的历史: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A].定宜庄,汪润.口述史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2.
[2]赵静蓉.作为范式的记忆与被书写的历史[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3]赵智敏.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新闻学之演进(1978-2008)——学术精神的追寻与理论重建[D].复旦大学,2009.
[责任编辑:赵晓兰]
陈娜,女,副教授,博士。(天津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天津,300387)
G219.2
:A
:1008-6552(2017)03-003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