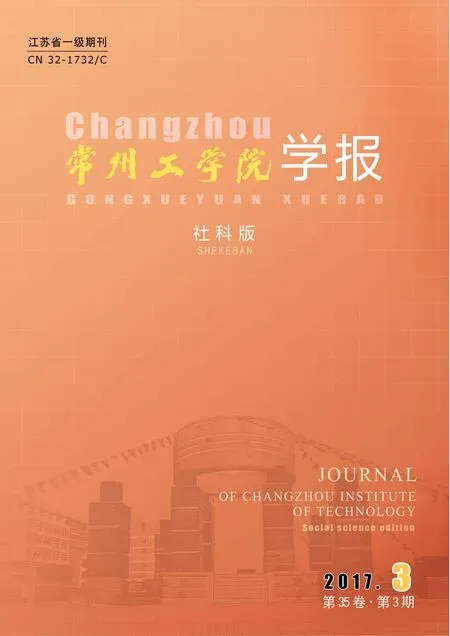启蒙声音的新世纪回响
——从苏童《河岸》中的父与子看开去
李杨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启蒙声音的新世纪回响
——从苏童《河岸》中的父与子看开去
李杨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有关父子关系的创作,自新文学肇始,便常与“启蒙主题”并置。然则,不同历史时期的书写,对“启蒙”的解读也不尽相同。2009年出版的《河岸》,苏童借由“文革”年代的特殊背景,对父子关系进行了深刻阐释。透过亲情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反拨,描绘出扭曲时代下的文化与人性的双重困厄。
父与子;启蒙;规训;反抗;和解
20世纪末,王富仁先生曾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本质内涵是以启蒙主义思想标准作为界定,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近多半个世纪文学的根本标准,并以之作为组织中国变化了的文学的历史构架。”①20多年过去了,启蒙思想仍以它顽强的生命力,活跃在人们的视野中。
不难发现,自新文学初,父子关系便时常与启蒙联系在一起,屡屡被摹写与讨论。苏童的《河岸》,再一次向我们展现了一曲有关父子的悲歌。由此切入,或许能为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发现与思考。
一、父对子的“规训”
一切讨论的开始,得先回到“启蒙”上。由此,不得不提到康德的名篇——《什么是启蒙》。这篇文章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多年后福柯论述“什么是启蒙”时,依旧无法绕开。文中,康德对于“启蒙”的解读是,“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挣脱出来”②。而这“不成熟的状态”,指的是“如果没有别人的指引,他就不能应用他自己的悟性”。显然,在一个人成长的最初阶段,对其进行指引的,是父母。这也是众多抒发“启蒙”声音的作品,将立足点放在父子关系上的因由。毋庸置疑,当父母的声音加诸孩子之上,他的“悟性”势必受到影响。而多数时候,这种指导性的话语背后,是父母对于经验世界的认知。他们接受了外在的规则,再用以规训自己的孩子。
《河岸》里库文轩对其子库东亮的第一次“规训”,源于那本“黑材料”。“文革”年代,失去了烈士邓少香之子的光环,库文轩在被工作组隔离审查三个月后,遭到了妻子乔丽敏的拷问。至此,夫妻关系破裂。离婚后落户向阳船队的库文轩,偶然发现库东亮私下藏起了那本记录着他“生活作风问题”的工作手册。库文轩很愤怒,“追出来踹了我一脚,滚,你这个下流坯,不准你在我的船上,马上给我滚,滚到岸上去,去找乔丽敏吧”③。库文轩明显将库东亮当作了乔丽敏的同伙,或者,换句话说,将库东亮视作将他打倒的“体制”的同伙。在他的愤慨之下,隐藏的,是对“体制”的深深恐惧。而对库东亮的训斥,也是出自对于秘密泄露的担忧。不敢对“体制”本身提出质疑的他,将过失归结于自身的生活作风,并多次让库东亮投递信件给上级领导,以求恢复他烈士之子的荣耀。为免库东亮将来重蹈覆辙,他开始以“父”之名,对库东亮的私生活(包括“性生活”)横加干涉。
这种干涉,强烈地表现在他对于慧仙去留问题的处理上。她“像一个神秘的礼物,落在河上,落在向阳船队,落在我家的七号船上”④。库文轩看穿了库东亮的小心思,但他显然不会让库东亮得逞。明知道慧仙看上了库东亮家的沙发,那个“很久以来一直是船队最奢侈的物品”,他还是赶走了她,连续两次。第一次是假借“组织”的名义,在船民不知道对慧仙作何处理时,将其归到了代表“组织”的队长孙喜明家。至于第二次,则表现得更为露骨。即便库东亮通过抓阄的方式,名正言顺地取得了慧仙的抚养权,仍旧没能挽留住心爱的姑娘。显然,慧仙并没有被扮作老虎的库文轩和他那蹩脚的谎言吓到,但她的聪慧足以让她知晓,这里不欢迎她。她是如此的美丽和高傲,多的是船民想要接纳她。而库文轩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她与自己渐行渐远。
如果说,在这场战役中占据主动权的库文轩,始终保持着一种淡然的面目。那么,当他目睹“我发育蜕变的生殖器官,那顶该死的‘钢盔’”⑤时,他无疑震惊了,甚至禁不住发出“一声惊叫”。“他开始厉声质问我,你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东亮,你夜里究竟在干什么勾搭?”⑥跌倒在作风问题上的他,这时候才发现自己对库东亮的性“压抑”,丝毫没有取得他所期望的结果。是的,他失败了。他制定得了规则,他监视得了库东亮的一举一动,但他阻止不了库东亮的生理发育,他更无法阻止库东亮性意识的膨胀。
事实上,失败的不光是他,也是千百年来所有试图对人们的“性欲”实施压制的权力体制。诚然,你可以将一系列的界域列为禁区,用无数的规则去管理它。但是,与此同时,“人们谈性的界域和人们被迫倾听谈性的界域不但扩大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言语通过产生各种不同效果的复杂组织,通过无法仅用禁令作出适当解释的部署,与性联系了起来”⑦。作者有意将背景设置在了“文革”年代,一切看似扭曲的事情都显得如此“合理”。当体制“规训”无处不在的时候,一方面人们对于“性”的刻画难以得见,另一方面“造人计划”又在不停开展。“规训”本身存在的空隙,为性意识的发展开拓了道路;而规训本身也在对性的“压抑”上,得到了那份无可替代的快感。有关性的讨论,自始至终就没有断绝过,它一直吸引着人们以无限的精力投诸其上。联系文本,监视着库东亮的库文轩,让库东亮在他无法督查的时刻,用属于自己的方式,观察着、向往着慧仙。他能管住库东亮的目光,但他控制不了库东亮的思想,库东亮的梦。
那么,除却“文革”时期,我们又如何理解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作品选教材中,绝少对于性描绘的篇目?此外,又如何看待20世纪末以至新世纪初,性描写呈几何式呈现,甚至可谓泛滥的现象?就前者而言,不难理解,因为教材的编选始终是有权力机制的干预成分在里面。它不可能按照历史本来的面貌加以还原,只是按照它应该呈现的方式被“打扮”。而后者,情况较为复杂。第一,当代史与我们相隔较近,尤其是20世纪末以至新世纪初的文学,几乎与我们共同成长。身处其中,制度还来不及“规训”,便泥沙俱下地冲入视野。第二,伴随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学的人力资源、作家的文学生存、文学生产的‘合法性’观念已经根本改变”⑧。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市场走向全面指引着写作的潮流,人们对窥探“性世界”的极大兴趣被充分利用,使得致力于无限谈性的作品纷纷露面。
由此可见,《河岸》中父对子的“规训”牵扯到的重心,在于“性”。而对于“性”的描写,首先可以看作是对于新文学初期以郁达夫《沉沦》开启的“性启蒙”的回应。“性”需求,属于人的基本欲望。消解旧有体制对人的压迫,势必先得解放人的观念,释放千百年来沉静地诉说“性”的渴望。其次,不厌其烦地诉说它,也是出于对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妥协。作品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得缘于读者的反馈,消费市场的认同度。因而,必须有足够的话题性,满足人们的阅读欲望。再次,将文本背景设置在“文革”年代,或许是作者一次“戴着镣铐”的“舞蹈”,他要满足读者,也不能“亏待”自己,用病态的描写,刻画病态的年代,堪称“恰如其分”。最后,诚如前文所指出的,“性”本身,既是他人的欲望,如何又不是书写者自身的欲望?满足他人“偷窥”欲的同时,也是对于自身书写欲望的满足。
二、子对父的反抗
父对子的压制和惩戒必然要引发子的反抗。反映到库东亮身上,激发他反抗的,无疑与两个女人有关。她们,一位是他的母亲,一位是他的恋人。不,准确地说,应该是他暗恋的人。
摆在库东亮面前的第一个重大选择,是“父亲和船”,与“母亲和岸”。他选择了库文轩,因为他觉得“就像水跟着水流逝,草连着草生长,其实不是选择,是命运”⑨,命运让他选择了库文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母亲乔丽敏。他与库文轩的第一次争吵,恰是因为那本乔丽敏遗留下来的“罪证”。而与赵春美的相遇,也是在他被乔丽敏以三个巴掌招待后。正是这次偶然的相逢,让他得以见证生命中最血腥的一面,库文轩亲手阉割了自己。由始至终,乔丽敏并未在库文轩与库东亮之间直接充当导火线,但她就像在地面上埋下了雷,等着库东亮踩上去。甚至不管她是否出现,库东亮都不可避免地踩个正着。
直接引发库东亮反抗库文轩的,是慧仙,那个让库东亮心动不已的姑娘。从母亲到慧仙,两者间有一次仪式上的转换。当库东亮带着慧仙去找她妈妈,却被七癞子困在厕所的时候,乔丽敏突然出现。她站在外面,喊库东亮出去。面对乔丽敏的指责,库东亮选择了躲避,一直到她离开。去了遥远的西山煤矿的乔丽敏,自此消失在库东亮的生命中。而慧仙却代替她,成了横亘在库东亮与库文轩间的一条“河”。
正如前文所言,在有关慧仙去留的问题上,库文轩曾两次横加干预。第一次库东亮选择了忍耐,品味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寂寞与孤独。可是到了第二次,库东亮再也忍受不了了。他发现自己的内心充满了仇恨,甚至用恶毒言辞羞辱了库文轩。用库文轩一生中最大的耻辱,最不堪的残缺攻击他。这是库东亮对库文轩的一次重大反击,看似胜利的库文轩,却由衷地感觉到愧疚。后来发生的紫药水事件,可以看作这次冲突的进一步发酵。库文轩惊讶于库东亮的生殖器官,他觉得库东亮对他的劝诫无动于衷,他不光厉声质问库东亮,还把治疗用的紫药水扔进了河里。几个回合,库东亮与库文轩互有胜负。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文中库东亮与库文轩最后一次冲突的直接后果,是库文轩喝农药住进了医院。他之所以会如此大动肝火,无疑与库东亮在人民发廊里当众揭露与他行不轨之事却在背后编排他的赵春美和金丽丽有关。这看似与慧仙关系不大,但库东亮几次三番来往人民发廊,甚至最后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全是因为慧仙在这里。此外,库东亮后来的“胡言乱语”,也是因为“我看着慧仙进了锅炉间,她一走,理发店明亮的店堂就暗淡了,萧瑟了,寒意逼人”⑩。慧仙的离开,成了压倒库东亮理智情绪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此而言,《河岸》中子对父的反抗,所牵扯的重心,是话语权的问题。父辈以权威压抑子辈,子辈以反抗形式企图重构话语权体系。但,整个话语权的旁落,又消解了这一争夺的中心。库东亮与库文轩的“你来我往”,为“话语权”争得“头破血流”,但是,事实上他们两个都被“岸”排斥,在“岸”的世界上都没有发言的权利。他们的这场斗争,本身就是一场“闹剧”。偏偏“岸”的世界里,“文革”正在上演。于是乎,在原本就是“闹剧”的时代大背景中,他们的举动又变得可以“理解”了。
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文本的诸多地方可以看作是对“启蒙”的回应,但又不单单是回应。“启蒙”在于理性的宣扬,对于个体理性精神的召唤,但是,“文革”的社会背景,混乱的父子关系,使得《河岸》充斥着太多的非理性色彩。从这方面来看,他在回应“启蒙”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反拨。这种反拨,主要以亲情伦理为切入点,将政治伦理作为突破口,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不过,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让情节继续发展,用信念或者说是信仰支撑着库氏父子走下去。他很明白,当人处于困顿之中,必然会找寻某种寄托。出于对这种寄托的认同,库氏父子的关系得以和解。然而,短暂的温暖后,他们又陷入更深的困厄之中。
三、父与子的和解
由父对子的压迫,再到子对父的反抗,最后两者取得和解。这一切的背后,除了表面上的理由,怕是还有一样东西如影随形地跟着两人。那就是,镌刻着邓少香烈士光荣事迹的花岗岩石碑。或者,准确地说,是石碑后的一幅浮雕。更确切地说,是浮雕上的“那只箩筐”。它不光是“浮雕的一个焦点”,也是全文的一个焦点。

正如前文所言,上船后库东亮跟库文轩的第一次冲突,缘于记载了库文轩作风问题的那本黑材料。这本材料记述的基本都发生过,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些发生过的事情在何时被书写出来。是乔丽敏的一时气愤吗?不是,从根本上说,这本黑材料的诞生,是因为库文轩失去了革命烈属的称号,失去了“光荣的血缘和显赫的门第”。深知事情本质的库文轩,故而才会不厌其烦地让库东亮带着申述书,一遍一遍地投进邮箱,投给那些上级领导。




事实上,不光是在库东亮面前,甚至在全船队中,库文轩启蒙者的形象也若隐若现。那张象征着身份差别的沙发,便是最后的明证。只是他们对于库文轩的认知,仅仅体现在库文轩辉煌的过往。他们或许无法理解,库文轩为一块“石碑”葬送了自己的一生。这里深层蕴含的,是一个启蒙者无法自我启蒙的悖论。库文轩能够用自己的话语干涉库东亮的成长,干预慧仙的去留,但他无法认识到,自己究竟从何而来。他的一辈子,不过是在编织那个由别人造出来的梦,他认同了这个梦,并把它上升到信念乃至信仰的高度。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与“岸”相对的“河”的世界中继续存活下去。

四、结语
自新文学肇始,“父与子”的关系,常被拿来宣扬“启蒙”思想。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到梁斌的《红旗谱》,再到苏童的《河岸》,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血脉得以传承。

注释:
①王富仁:《我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解读》,《灵魂的挣扎》,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页。
②康德:《什么是启蒙》,盛志德译,《哲学译丛》,1991年第5期,第3页。
⑦米歇尔·福柯:《性史》,黄勇民、俞宝发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7页。
⑧吴俊:《新媒介·亚文化·80后——兼以〈萌芽〉新概念作文的个案为例》,《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第91页。





责任编辑:庄亚华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3.010
2016-12-08
李杨(1994— ),男,硕士研究生。
I207.42
A
1673-0887(2017)03-0043-05
——从学科规训视角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