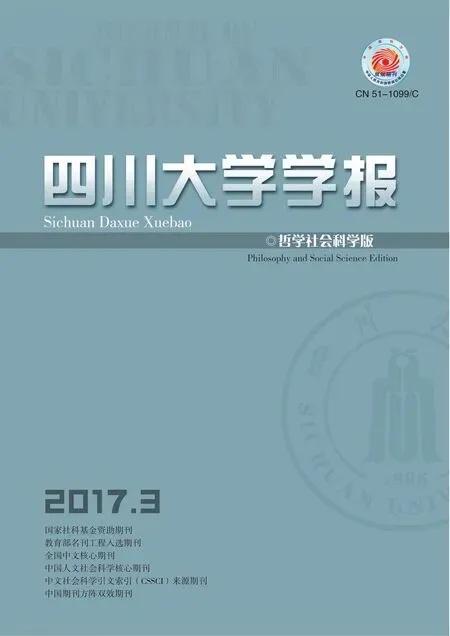Thumos:①跳出理性与欲望的对峙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灵魂三分说的克服
曾 怡
Thumos:①跳出理性与欲望的对峙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灵魂三分说的克服
曾 怡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希腊词thumos正面建构为一个重要概念,且作为灵魂三分法的中介具有多重的功能,调节着理性与欲望的一般对立,并使城邦和个人的正义得以实施。但灵魂三分说自身的分类根据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在应用thumos解释灵魂美德及其实现中的缺憾。由此引发了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并使其在辩证地吸收了自然学家对灵魂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了新的灵魂学说,找到了理性和欲望对立的结构性解决方案,取消了灵魂三分说的必要性,瓦解了thumos概念的中介性地位。同时,也展现了一种不必以灵魂研究为实践哲学奠基的思路,而使得后者完全成为自足研究域。
thumos;灵魂三分法;理性;欲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根据文境侧重的不同,笔者所要讨论的概念thumos可译作“激情”“怒气”“血性”“意气”“心气”“活力”“冲动”乃至“精力”。古希腊荷马(类似的概念如义愤nemesis)、*关于希腊传统非哲学文献中thumos的用法的讨论及其对哲学的影响,参见Olivier Renaut, Platon, La médiation des émotions: L'éducation du thymos dans les dialogues,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2014; Jean Frère, Les Grecset le désir de l'Étre, Paris: Les Belles-Lettres, 1981; Jean Frère, Ardeur et colère: Le thumos platonicien, Paris: Kimé, 2004, pp.13-89.赫希俄德及品达那里这个概念的本义源自“风、风暴”,*Cf. C. P. Caswell, A Study of Thumos in Early Greek Poetry, Leiden: Brill, 1990, pp.51-63.常与攻击性相联,在交战之中被视作直接与战斗相关的斗志,在工作中被视作进取心或争胜心,在悲剧之中被视作不能平息的烦恼源头。所以,一方面,这个概念在前哲学时代意味着与自我形象相关的方面;另一方面,上述情形的共性在于具有thumos的主体所面对的都是或弱或强的竞争(agn)形式,而竞争活动中要解决“凭借什么而争”的问题,就要求建构出一种评判机制。在后一个意义上,thumos在最泛泛而言的意义上涉入哲学性问题,而不止于心理学的范畴:在一种关乎竞争合法性及正当性的评判机制中,这一概念扮演何种角色?
进一步将这个问题具体化,近期的研究中这一概念在实践哲学领域最常被提及:在竞争中关乎荣誉的美德——勇敢(andreia)——与thumos密切相关。*关于与勇气相关的thumos在当代伦理-政治哲学中的讨论,参见Cynthia Fleury, La fin du courage, Paris: Fayard, 2010; Cynthia Fleury, “Le courage du commencement”, Études, Revue de culture contemporaine, Janvier 2014, pp.57-66.我们可以说推动人在智性的对辩之中胜出的动力就是thumos,也就是辩论*我们在这里还无法直接谈及辩证论争(dialectic)和口角之争(eristic)的差异,关于这一区分的形式性方面,参见柏拉图《斐力布》(16e-18d)。中的动力因吗?就像康德所谓的“形而上学冲动”或尼采所谓“求真冲动”?这与上述实践范围内的竞争场景一般无二吗?如那些运用修辞学的场景(庭辩对议、司法辩诉)或战事?那么,这样看来,无论在智性主导的领域抑或实践领域,似乎都有必要先弄清楚thumos的性质及其与灵魂中其他部分的关系。以下,笔者将回顾柏拉图《对话》中率先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回应,继而再现亚里士多德如何重构提问方式,并在针对这些柏拉图式的设置方案提出批评意见之后,回答上述疑问。
一、柏拉图的调节性中介概念
柏拉图对thumos概念的处理并非始终如一,只有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才肯定了它在伦理学及政治学上的积极价值。这一价值又与其对灵魂研究的展开密切相关。近年的研究者对其双重性有一个共识,*在英美学界也有学者如佩内(T. Penner)认为thumos这一概念并无任何重要性,而是柏拉图误置的一个不要紧的概念,他认为柏拉图始终坚持着理性和欲望之间的对立,参见Terry Penner, “Thought and Desire in Plato,” in Gregory Vlastos ed., Plato,N. Y.: Anchor Books,Vol.2,1971, pp.96-118。对此的驳论可参见莫斯Jessica Moss, “Shame, Pleasure and the Divided Soul,”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No.29,2005, pp.137-170。本文所针对的论战的背景性共识可以参见Oliver Renaut, “Le rle de la partieintermédiaire (thumos) dans la tripartition de l'me”, Plato,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to Society, No.6,2006.但对其功能的看法却颇有对立:福莱勒(J.Frère)*Idem.Frère, pp.187-189.http:∥nd.edu./~plato/plato 6issue/contents6,htm认为它不止是灵魂的部分,也许更为本质地和逻各斯一样具有行动(准确地说是大小战事中)的原理性地位。柏拉图的新意就在于将其认可为一种“实现力量”,而在行动中有优先性。在被节制的状态下,它可以作为感受性原理与心胸(phrên)、心官(kardia)并列理解为“心气”,相应于原理序列的则是感受性形式,如悲欢、果敢。也因其原理性地位,thumos概念常常被引申使用。福莱勒就倾向于将之做多义处理,如怒气之心(curencolère)、心的热力(cur ardent)、暴怒(colèreardente)等。相反,雷诺(O.Renaut)则把thumos总结为一种“本能反应”,在三种意义上thumos实现着中介性功能:它是在城邦法与行动之间的沉思的主体性工具;它是客观而言理性对抗欲望的机能;它还是身体与灵魂的中间通途。*参见Renaut, Platon, La médiation des émotions, p.73。因此,thumos概念不能承担规范性尺度建立的主体原则基础,柏拉图强调的还是通过它加入理性灵魂的活动以建立法则,因此它需要被驯化和打磨以联合理性对抗官能性欲望(epithumia)。柏拉图思想的核心奠基于“美德即知识”,它与基于情绪的道德感对立,因而在《理想国》中体现着一种将情绪理性化的思辨进程。他的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道德性不受情绪的牵绊。虽然上述对立意见的交争点在于thumos是否具有优先的原理性地位,但却一致揭示出围绕这一概念,柏拉图的问题焦虑在于调节多方因素使城邦或灵魂实现一种和谐,这一和谐其实就是正义的代名词。Thumos辐射出的问题域也就是关乎主体自身灵魂和谐和城邦的可实行的正义问题。只要看到了这一点,就毫无必要假设集中探讨了这一问题的《理想国》只是纯然否定性或批判性地工作。应该看到,柏拉图一直都在努力建构一个可以使正义得以在人类历史生活中实现出来的学说。


既然存在着彼此差异的部分,而这些差异是对立性的,那么对灵魂进行分部解释就是必然的结果了,这便是灵魂的三分说:“官能性欲望”或“官能层面欲望的部分”(epithumia,437d;epithumètikon,439d),“进行筹算的推理部分”(logistikon,439d)和“使情绪激昂的意气”(thumos,439e)。意气与官能性的欲望最为相似的地方在于它们都是非理性的,不具有推理能力(439d, 441c);然而它们又互不相属,因为同种类的事物间不会有冲突,而它们却可相互抵牾,且意气更倾向于与推理的那部分灵魂结盟。所以,理性和意气才会在发挥自己本然的作用的情况下去领导欲望(442a)。尽管分类已然如此这般建立起来,却留下了一个问题,即“意气的对象是什么”并不如另外两个部分那么明确。这个问题将留在后文予以阐明,在那里,苏格拉底提出,在正义的灵魂或“健康”的灵魂中意气激昂的对象是胜利、优越和荣誉(581a-b)。*Cf. J. M. Cooper, Reason and Emotion: Essays on Ancient Moral Psychology and Eth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73-274.
意气作为介于推理的理性和官能性欲望之间的部分至此已明,它的中介性角色本身并无问题,然而灵魂三分说本是服务于解释美德,尤其要解释正义及其实现的方式,但这一解释却显示出一种不稳定性和交错性(442c-d)。节制是贯穿了整个城邦的,它既存在于统治者身上,也存在于被统治者身上(431e);既专治官能性欲望(430e),又是正义本身(427d),苏格拉底讨论的美德共四种。但要注意在上述表达里,节制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身上的双重存在设置(431e)。
二、柏拉图阐释方案的后果

这里至少有以下几点要注意:一是美德被还原到灵魂层面作解释,而非回到行动或以行动主体的人为原理进行理解;二是具体的美德、智慧和勇敢都以具有科学知识的智性为自身根据,而第三种是灵魂整体的和谐。柏拉图在后文重回对正义的讨论之时,正义才被认为是使灵魂各部分各尽本分的和谐,“引导和命名那些保有和培养其‘和谐’状态是正义且善好的行动,也就把在这些行动中所遵循的科学叫做智慧”(443d-444a);三是正义的行动先行于且又促成了和谐的状态,同时它也遵循科学,也即智慧,但却与其产生的节制在效果上重叠了,两者都产生和谐,而前文(430d)却明确表示要分别对正义和节制进行考察;四是正义与节制的结果重叠了,节制逾越了自身作为官能性欲求适当掌控的本来面目,而在灵魂各部分间产生影响。我们也就不再能坚持此前苏格拉底所坚持的“特定部分针对特定对象了”,灵魂的各部分不只是分别地各尽其份,而是统一地在一个新设入的关系中产生了一种可向高级还原的序列,这个关系即“制定规则和遵循规则”,它对应于“统治和被统治”关系。

那么,综上而论,对于意气而言,在最好的状态下,它应当既要节制,又要以勇气为城邦护持律法,并且它既非欲望,也非理性(441a),且有赖于后者制定的规则获得自身美德的规定性。理性/欲望的一般对立关系在对话中体现为理性/反理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关系最终被意气部分的灵魂介入并调和了。尽管它们仍各自保有独立的性质,但作为两者中介的意气可以在尽其本分的情况下,辅助理性调节灵魂各部分以使其和谐,也即实现灵魂整体的正义。然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代价却是对美德序列解释的结构性破坏——节制和正义之间发生了功能重叠,这显示出有必要重新考察导致这一结论的预设。并且,因为在逻各斯层面的另一个把握事物本质的定义活动在《智者篇》也没有成功建立,那么,就既没有寻找到对“事物本身”进行定义的方式,也没有确立起与其配套的逻辑学,因此意气这一概念时而被作为属性(thumoeidès)去刻画这个中介部分,时而作为灵魂激起愤怒的固有能力(thumos)。所以我们要问:其一,在灵魂中,根据“相似者把握相似者”而对灵魂进行分解的原则本身是否合理呢?其二,如果说苏格拉底是要通过教育使意气成为介质发挥调节理/欲对立的作用的话,这一对立本身是否成立?又是否等价于理性和反理性的对立呢?
三、亚里士多德的批评与thumos中介地位的瓦解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应出现在《论灵魂》中,前文已指出了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给出了一个对于物理学家们对灵魂分部的修正表达。后者的思想被亚里士多德转述为“相似者感知相似者,相似者认识相似者”(《论灵魂》,卷一,410a24-26),其源于恩培多克勒;与之伴随的还有一个观点“感知就是承受某物或被某物推动,而智性活动和认识活动也与之相同”(410a25-27)。苏格拉底仅限定了前一个观点,也就是说,虽然灵魂的特定部分关系特定对象,但特定对象并不必然与灵魂的这个部分有同一性,而仅有相关性,就如关于疾病的科学知识并不等于科学知识本身也有病(439e)。这一澄清可以使他免于亚里士多德对恩培多克勒的部分批评,但仍保留了灵魂的特定部分的性质与其针对的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在苏格拉底对推理部分的灵魂进行划分时,却又从这一点出发,启用了另一种方式,即用推理活动对前一个部分活动的“阻止”来说明,也就是通过与前者比较而言的“活动方面的差异性”来确定新的分类。亚里士多德较之更为激进,他完全取消了在灵魂各部分对应特定对象的划分方式,而通盘采用针对灵魂不同活动及其功能进行探讨的方式。*也许我们会看到《论灵魂》卷三开篇对感官与其相关项进行分析中,亚里士多德也赞同特定感官有其特定感性物的专属对应特征,然而这一分析是服务于解释感官和感觉活动的本质与前人理解的差异,重点已不在于分类,而在与这一活动与非命题性判断的陈述真值的问题。对灵魂进行分部的思路仍被亚里士多德在考察灵魂整体时放弃了。也正因为基于活动方式、功能的效果,他否认了在感知和智性活动、认识活动的同质性。它们之间的区别完全脱离了与身体性相关与否的标准,建立出察识灵魂各机能的另一个标准。这些新标准是亚里士多德在指出灵魂最为特征性的几点时展开的一个比较长的说明,它紧紧回扣并延续着对前人灵魂分部学说的批评,他说道:
所以感知和思想很显然不是一回事。因为如果所有动物都具有前一种,相反则很少具有后一种。智性也一样,其中有对错的形式。正确的形式其实与实践智慧、科学和真意见对应,而错误的形式则对应其对立面。那么这也就与感知不同了,因为如果对特定感性物的知觉总为真且又为一切动物共有,相反,思想则会出错且不属于没有理性(logos)的任何动物。表象(phantasia)自身与思想和信念不同,因为这一感受(pathos)*本文不展开讨论这一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用语里的多义性及其复杂性,但这里近似于近代哲学以降所谓与“观念”相对的“印象”概念,因与后文sumpaskhomen(意为共情、交感、感应)一词呼应,而译作“感受”。可由我们操控的,当我们想要这么做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可以在眼前浮现出影像,就像在人在回忆中做的那样,他们唤起并制造影像。而得出一个意见则不是可由我们操控的。它必然为假或真。再加上,当我们形成对一个可怕的或令人惊恐的事物的意见之时,我们立刻感应到它(sumpaskhomen),如果涉及到令人安心的事物,也是一样。但由表象而来的,我们则像看这些可怕或令人安心的事物的画一样。(《论灵魂》, 427b7-24)
因此,两个新标准分别为:1)是否与真伪问题相关,以及与之伴随的对生物物种间的差异的划分,以及2)其出现是否可由我们左右。这两点划分原则上与前人的不同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灵魂三分法的决定性放弃,也将是他给出新的灵魂学说的起点,其影响还将进一步呈现在意气概念的定位问题上。
由第一个标准,我们可知,感官和感觉也可以使基于其上的陈述具有真值,并且它恒真而无错。这里所谓的“恒为真”不是命题陈述意义上的,而是“分辨”意义上的;*A. Jaulin, Eidos et Ousia, Paris: Klincksieck, 1999, p.63,及同页注76。就如颜色对于视觉而言,红就不是黄;眼睛若错把红色的东西看做黄色的东西,而说“这是黄色”,那是因为我们对着色的东西的判断已经加入了非视觉所特定针对的作为视觉相关项的色彩而作的陈述,因此,我们对着色的载体的陈述可能错,而对色彩本身依旧是能辨别其差异(如红与黄),才能说出“这是红色”或“(把红色的东西)看成了黄色”。因此感觉没有对错之分,它恒真。相反,智性则有对错形式,其为真时,智性把握最初原理、实践智慧把握善、科学知识把握理论的真、真意见表达具有真实性的想法;其为假时则为上述几项的对立面。所以灵魂被基本地分为无所谓真假判断的恒真的领域和可以涉及真假形式的领域,一定要分“部分”的话,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提供了一种灵魂二分说,即非求真部分与求真部分。要注意的是:意见(doxa)涉及真假判断形式,同时它又可以激起恐惧或安定的感受(sumpaskhomen),而意气正是在这种感受下产生作用表达为愤怒的。简言之,意气的激发是与智性相关的意见形成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由标准二,我们可以看到,意见是不在我们能左右的范围内的,而作为可以自主给出印象的表象活动则在我们能左右的范围。也就是说,意见激起的意气的强烈度或客观度要高于(类似于想象或回忆的那种)表象活动。意气的激发并非纯系于主体的意识,其行动性的一面由此可见——因为行动必朝向某种实现(entelekheia),且自身已是一种现实(energeia)。
至此,可以说意气概念已经完全解除了其在柏拉图哲学中的中介性质,而成为了感受(pathos)之客观与智性一面的佐证。既然中介概念已被取消,那么,我们是否可按上述新标准得出一个替代灵魂三分法的新分法了呢?事实上,准确地说,我们不能称这个区分为“灵魂部分”的区分。在陈述了智性与感性的交互活动之后,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卷三继续说道:
马上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谈论灵魂的哪些部分以及其数目。因为在一种意义上它们似乎是无限的,而不只是某些人所做的区分,如推理、意气和官能性欲望,*这里指的正是柏拉图的三分法,段末正式提及对此三分法的否弃。也不仅仅只是另外一些人所说的理性和非理性的部分;*并不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接受灵魂的理性与非理性二分法矛盾,因为在1102a25-32中,亚里士多德对这一二分采取的是一种意见性研究(doxagraphy)的做法,可见理性/非理性的二分法只是众多别的说法之一,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持有的观点,他只是借用其作伦理学的分析的引子。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们划分这些部分所依据的差异,我们就会发现还有其他部分,比我们已经说到过的那些更有明显差异;例如,营养部分,它既属于植物也属于所有动物;感觉部分,我们很难将它分归属于理性或非理性的任何部分;还有表象部分,它本质上与其他都不同,我们很难说它与分部假说中的任何其他部分同一或相反。此外还有欲望部分,无论是在说法上还是在能力上它似乎都是和所有这些部分有区别的,将之加以分划乃是荒谬的,因为在推理的部分中存在着愿望(boulèsis),在非理性的部分中存在着官能性欲望(empithumia)和意气(thumos)。如果我们把灵魂分成三个部分,那么我们在每个部分中都可以找到欲望(orexis)。(《论灵魂》, 432a22-b8)
所以人在求真的析理活动(logismos)主导的时候,灵魂中的感觉(aisthesis)、表象(phantasia)、欲望(orexis)也都起着不同的作用;而人在非求真的感受活动主导的时候,正如此前分析过的意气概念,它可以证明感受(pathos)也可以存在智性参与的部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1103a1.sq.明确补充说明了欲望部分更适合说也是“具有理性的”,只是具有的方式是“如子为父纲般的听从”。任何分部法都困难重重,灵魂三分法最终被瓦解了,*当然我们也知道亚里士多德把灵魂进行过三级化划分,也常说“植物灵魂”或“营养部分的灵魂”,“动物灵魂”或“感觉部分/欲望部分的灵魂”以及为人类独有的“智性灵魂”。但这更多是在1’)的附带特征上针对不同动物的种群进行功能对应的一种说法。这种方法旨在说明灵魂机能由简入繁的嵌套关系,也就是说更为高级的能力包含较低级的于其内,而不是真的以这种区别严格区分物种,也不是反过来以物种确定灵魂的各部分,如:人类灵魂中就集三种灵魂于一体。在类比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也常把人类特有的某些灵魂的能力冠诸某些动物,关于这一点参见贝勒葛兰:《亚里士多德:一种生物政治学?》,载于《欧洲评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春季号),第37-56页。其思路整体地被放弃了,而对灵魂的研究也回到对标志性的各灵魂机能及其活动的分析。求真与非求真的对立也不能对应于理性与欲望的对立,调和二者的中介概念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而作为人的行动动因的冲动(thumos)概念也一样在亚里士多德新的灵魂学说中被欲望的对象(orektikon)取代了。“欲望的对象构成了实践智性的起点,而其最终项构成了实践的起点”(433b16-17),具体展开各个环节则表述如下:“动因在种的意义上数量为一,即欲望性的,而一切欲望性的第一动因是欲望的对象——因为它推动却不被推动——作为智性对象或表象所与,则动因个数为多。存在着三个:一是动因,二是动者,三是被动者,而动因又有二,其一不动,另一则同时为动者和被动者。不动的是实践善,*这里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究竟如前文所说“实践智慧把握善”,还是各欲望对象作为动因都是“实践善”,这两个说法之间看似不一致。这个问题涉及到对“现象上的善”(亚里士多德会说“显得善”)和“真正的善”(“对有实践智慧的人显得善”)之间的分疏的必要,根本而言就是要澄清“凡实践总有目的,而凡目的总是指向善”这一命题。关键在于区分善的尺度建立的一般形式原则和具体的行动者的目的的恶,后者并不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所正面讨论的议题,因为整个伦理学并不服务于“去恶存善”,而服务于阐明实践善的原理及将之付诸践行的机制,毋宁可理解为基于“为善即是去恶”的诠释。本文中就不详细展开这一论题了。而推动又被动的是欲望性的”(433b11-18)。欲望的对象即是某物,作为动因它也同时既为实践的起点,也是其终极。就其为终极而言,它是不动的,就其为起点而言,它同时为动者和被动者。作为动因性中介的冲动(thumos)概念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并且我们再次看到这个枢纽的客观性,它非属于灵魂内部。
那么,作为与愤怒相关的意气(thumos)概念的功能的重要性被降低了,却仍旧保留了说明欲望如何向理性敞开的通途,对之的分析服务于指出感受(pathos)——或说非求真的灵魂活动——中存在着智性因素的事实。但行动者主体中的理性和欲望间在实践中的显而易见的冲突就被取消了吗?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否定的。然而这一对立被确切地表达为智性和官能性欲求的冲突,不是本质性的,而是有限地存在于特定情况中,即人身上的自制/不自制现象。以自制为例,他说道:“然而欲望自身也不是运动的主宰。因为自制的人即便有欲望,有官能性的欲望,也不会实践出他的欲望,而是服从智性(nos)。”(433a6-8)两者间也不存在调和的问题,更无关人心善恶的决定性角逐,两者均处于人具有德性行动与否的临界点上:自制者在最弱意义上保有善,不自制者在最弱意义上为恶。
但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欲望的规定性来自理性,这一点必须强调,它也同时见证了亚里士多德如何脱离了苏格拉底的理智主义思路。因为紧接着对这一冲突的描绘,亚里士多德解释了运动在行动者主体灵魂中的原理层面:“至少这显示出运动就源头而言有两个可轮换的动因,要么是欲望,要么是智性,如果我们把表象也视作某种智性的话”(433a9-10)。所以,事实上,行动的源头兼具两个原理,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则更明确地表达为“欲望着的智性(orektikosnos)和思考着的欲望(orexisdianoètikè),而这就是人类存在的原理”(1139b4-5)。
结 论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研究时提到的,政治学家要引导城邦的善,那就需要对灵魂的本性有所了解,但也不可以模糊实践领域与理论领域的分野;对灵魂的研究不应当像自然学家那样作透彻了解,而只需要了解特定对象以服务于政治学的目的(《尼各马可伦理学》1102a15-25)。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改变了对人之行动原理的解释,也就更新了对实践哲学的划界。也就是说,自然学说不再为实践哲学作任何奠基,也不再发生内容上的直接性关联,它们之间可资贯通的是分析思路的一贯和概念系统的共通。
既然瓦解了前人的灵魂学说,也就必然带来对其所服务的美德理论的重构。亚里士多德对美德的解释也将奠基于灵魂功能(ergon)、活动(energeia)及其所针对的行动目的(telos),而不再如《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有赖于对应灵魂分部而展开的美德学说。在新的结构性的对美德的解释中,节制与正义之间的重叠问题也将迎刃而解。而意气对应的美德,如勇气,其规定性的基础以及由意气激发的怒气究竟为善或为恶,就被归属于与灵魂学说本身旨趣相异的伦理学所考察的对象了。前者只能为后者规划出一个清晰的原理性场域并提供入手的概念工具——指出双原理的存在及灵魂功能和活动的多元及各自属性,但却并不能直接给出善恶判分的基础及其相应的实践原理的特点。
(责任编辑:曹玉华)
Thumos:Jumping Out of the Opposition of Ration and Desire
Zeng Yi
The point of departure of this paper is the inner-Academic polemic concerning the tripartition of soul which is itself constructed by the concept of thumos. Thumos is a Greek word with multiple meanings. Plato, in hisRepublic, has constructed it as an important concept which, serving as the intermediary of the tripartition of the soul, has multiple functions of harmonizing Reason and Desire and ass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justice of both the polis and the individual. But the arguments supporting the tripartition themselves created some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which would be criticized by Aristotle. Starting from dialectically synthesizing the physiologues' theories of soul, Aristotle has developed a new theory of soul which resolve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Reason and Desire, and thus renders Plato's doctrine of tripartition unnecessary. Aristotelian theory of soul will not play such a role of foundation, as Plato proposed, for the ethico-political realm which is indeed autonomous.
thumos, the tripartition of the soul, ration, desire, Plato, Aristotle
曾怡,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讲师(成都 610064)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经费“海外优秀博士科研资助计划”(skyb201303)
B502
A
1006-0766(2017)03-0066-07
§外国哲学研究§
① 鉴于所讨论的thumos这一概念的复杂性,笔者随文加括号译出其侧重的意义,非转换意义重作译文时,不再重新标识;文中凡涉及希腊文重要概念则标记为改写自原文的斜体拉丁拼写;涉及其他西文不标斜体,并统一省去冠词;涉及重要希腊文原文,则摘出原文并保留希腊文拼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