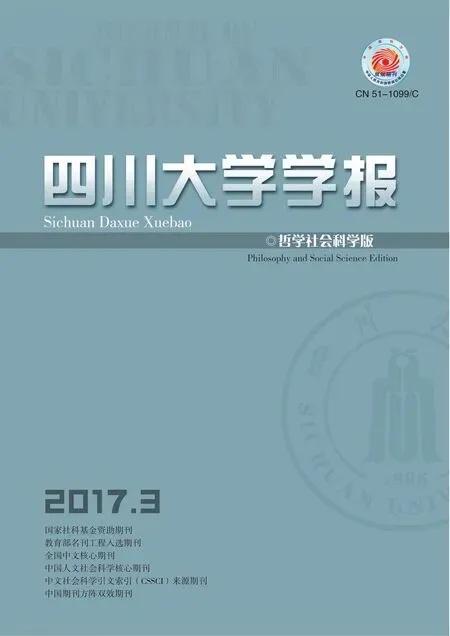从哲学史到思想史
——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
王汎森
从哲学史到思想史
——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
王汎森
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反映了胡适的两种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胡适中年后疏离“哲学”,逐渐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除了受到傅斯年的某些影响外,与时代思潮恐怕也有关联。这个转变使他与哲学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日渐分道扬镳,似乎也因此不能在思想、哲学的战场上与当时的左派思潮作一对抗。第二是胡适在若干重要学术论旨上的巨大改变,如史料批判、疑古精神、东西方哲学互证等等。以胡适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枢纽地位,他上述两方面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注意。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思想史大纲》;哲学史;思想史
本文系根据作者2013年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85周年所庆的专题演讲整理而成。感谢周月峰先生听打整理。由于是演讲稿整理而成,所以保留了演讲的口气,请谅察。
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的《中国思想史大纲》。这份《大纲》是由1554张小纸条所组成的,*这些纸片有的一页只有一行字,多的也只有几行。其中,古代有643页,中古(200B.C.-1000A.D.)有268页,中古宗教(300A.D.-1000A.D.)有237页,理学(1050A.D.-1650A.D.)有326页,反理学(1645A.D.-1945A.D.)有80页。是胡适1944年底到1945年在哈佛的开课大纲,*胡适纪念馆藏号:HS-NK05-209-001。这是他最后一次要写一部《中国思想史》的尝试,但是接着便被早先开始的《水经注》问题盖过去了,没能完成。*这一份《大纲》是1944年秋天到1945年春天胡适应邀在哈佛大学讲课时,写在“拍纸簿”上面,连缀而成的一份大纲。当时上课的情形,杨联陞先生的日记,及周一良、赵元任等先生都有记述。中研院的胡适纪念馆中有一封信可以说明,当时麦克米伦公司曾来函邀约,希望胡适将书交给公司出版。胡适的答信说:“每逢谈到这本书时,我总是非常难为情的。因为它只是一份笔记纸排比而成的大纲而已。”这份《大纲》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之后25年学术工作的一个比较整体的呈现,这中间当然也吸收许多胡适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作,包括《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戴东原的哲学》等。胡适一直想完成一部《中国思想史》,这份大纲应该是他在这方面最后一次的尝试。这份《中国思想史大纲》,与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有很大的不同。
一
这份《大纲》反映了胡适两种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的转变,第二是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到《中国思想史大纲》中,若干观点的转变。这里先谈第一点。我在《汉学研究》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胡适事实上有一个阶段很受傅斯年的影响。*他写《说儒》时,很受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跟《夷夏东西说》的影响,我在文章里面举了很多档案资料,可以看得出来。还有若干方面,其中最后一点,讲到胡适后来对哲学的态度,或许跟这个有关。见《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收入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第309-332页。1944年底到1945年,胡适在哈佛大学演讲,已经强调他所讲的不是中国哲学史,而是中国思想史了(见图1)。事实上,江勇振先生在《舍我其谁:胡适》一书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胡适后来不希望自己被称为哲学史家,而希望被称为思想史家。*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1年,第277、278页。“我有时称我自己为历史家,有时称我自己是一个中国思想史家,但从来就没有自称为哲学家”。他有意淡化主修哲学,对韦莲司女士说“最讨厌抽象的思考方式”。


图1 《中国思想史大纲》原稿
“哲学”原来是一个从西方来的词,日本也是从西方学来的。狭间直树有一篇论文,就是追索日本如何从欧洲学得到“哲学”这个概念。*狭间直树:『西周のオランダ留學と西洋近代學術の移植:「近代東アジア文明圈」形成史:學術篇』,『東方学報』,册86(京都:2011年8月),第131-176页。“哲学”到中国来跟王国维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其实近代的心理学、哲学、美学,这几种学问跟王国维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从《王国维全集》中翻译的部分可以看到,王国维译过不少西方的人文著作。他写过四五篇与哲学相关的文章,主要是在说明,哲学这个东西对我们而言很陌生,但是个好东西。尤其在跟张之洞讨论到学制的时候,他一再强调,哲学是好事情,不要看它好像没有用,可它是一个重要的学科。*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王国维全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2-40页。
蔡元培对哲学兴趣深厚,他根据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写过一本《哲学总论》(1901),早年译过《哲学要领》《伦理学原理》。*後藤延子:「蔡元培の哲学:民国的人間像の行動原理」,『人文科学論集』,号13(1979年3月),第167-168页。他翻译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的《伦理学原理》,后来还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生批语最多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蔡元培所译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现在《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里可以看得出来,当然里面有很多毛泽东自己的想法。蔡元培早期对引进哲学是非常用力的,而且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一般都认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事实上,在胡适之前有两本书,一本是北大的讲义,即陈黻宸(字介石)的《中国哲学史》,另外一本是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谢无量是同盟会的会员,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有很多地方显然是针对谢无量。*胡书批评谢无量,但是他没有提陈介石,可能陈介石的《中国哲学史》在北大当时只是讲义,不像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是印本。谢无量讲哲学,就是从伏羲、神农开始讲起,一路讲下来,胡适认为里面有很多过时的、过度信古的东西。其实谢无量所做的也是受日本影响、受近代西方哲学观念影响的哲学史,但是他不具有胡适那样怀疑批判的角度。
胡适这本书原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后来重印的时候,才改成《中国古代哲学史》。*关于“哲学”在五四前后学科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问题,可参考罗志田:《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事实上胡适在台北版的序言里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他已经放弃哲学史的想法,改写思想史了,所以“下卷”他不要了,就变成《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自记》,《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页。这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会从哲学史转到思想史——后来甚至不太愿意人家称他为“哲学家”。这个转向因为涉及文字的部分,多是在私人书信、日记、未发表的演讲稿中,故有些隐晦,不那样引起注意。
1922年,当胡适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4年后,哥大邀请他去当访问教授,他考虑到要写《哲学史》中、下卷而不去。可见他那时候还是非常投入哲学史的工作。到了1925年,他还出了一本《戴东原的哲学》。可是从1920年代末,可以感觉到胡适对于“哲学”的态度有了一个变化。傅斯年在1926年8月写给胡适一封长信,这封长信大概是因为字迹太草,所以没有被收进《胡适来往书信选》,可是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面有。*已收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第43-52页。傅斯年对胡适说,你写的《哲学史大纲》不是第一流的著作,反倒是你的小说史考证,才是第一流的著作。一方面哲学史的著作当时西方汉学家已经有人写了,但最重要的是你用哲学来讲中国的思想本来就是错误的。中国人没有“哲学”这个东西,中国只有“方术”,任何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讲中国的思想,本身就是错的。傅斯年并说陈寅恪的看法与他是一致的,因为不能用伦理学、本体论、知识论去讲中国的东西。凡要用这些去讲,于古代的思想就有增减。
傅斯年又对胡适说道:“我当方到英国时,觉得我好像能读哲学书,甚至德国哲学书。后来觉得不能懂德国哲学了,觉得德国哲学只是一些德国语言的恶习惯。现在偶然那(拿)起一部Hume来,也不知所谓了。总而言之,我的脑筋对于一切哲学都成石头了。我于这个成绩,也很欢喜。”这代表当时知识界有一种慢慢要疏远“哲学”的倾向。傅斯年在北大学生时期的文字,原来也有很多是牵涉到哲学的,可是慢慢到1926、1927年,受到当时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大概与逻辑实证论有一定的关系,他便开始疏远哲学了。胡适在1926年给他回信,完全同意他。信收藏在史语所的档案里,现在出版了。胡适当时人在巴黎,他说:“你最得意的三件事,我却也有点相像。一、近来每用庞居士临死的遗训劝人:‘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庞居士也许注重在上半句,我却重在下半句。……二、捆人最利害的是那些蜘蛛肚里吐出来自己捆自己的蛛丝网,这几年我自己竭力学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学,不看西洋哲学书,把西洋人的蛛网扫去了不少,自己感觉很痛快,……这一层我很得意。因为我是名为哲学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的吃饭家伙丢了。”*见胡适:《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卷,第435页。
可能受了这一影响,1927年5月胡适访欧回来以后,把他关于中古哲学文雅的标题定为《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此后他慢慢地就不再怎么谈哲学或哲学史,虽然也谈哲学的问题,但是他以后开课的名都是“思想史”了。1929年他在上海大同中学演讲《哲学的将来》,里面说了一些比较决绝的话。这份演讲稿并未发表,一直收藏在家人手上,直到编纂《胡适全集》时才收入。在这篇演讲中,胡适说,“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错误的,或失败了的科学”,“最早乱谈性善性恶的孟子、荀子既可算作哲学家?”(它是问号的),“凡科学已解决的问题,都应承受科学的解决”,“凡科学认为暂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都成为悬案”,“凡科学认为不成问题的问题,都应抛弃”。所以他提到“哲学的根本取消”,“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即使提出解决,也不过是一个待证的假设,不足以取信于现代的人”。他说,“故哲学家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若不如此,但他们不是将来的思想家,只是过去的玄学鬼”,“将来只有一种知识:科学知识。将来只有一种知识思想的方法:科学实验的方法”。所以为什么他不用哲学史,而用思想史,因为“将来只有思想家而无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已证实的便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未证实的叫做待证的假设(Hypothesis)”。*见胡适:《胡适全集》,第8卷,第6-8页。
关于胡适这个重大的转变,我曾在一篇短文中略为讨论过。*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第309-332页。除了傅斯年个人的某些影响外,与时代思潮恐怕也有关。用朱执信的话说:这是个“不去欧洲留学,真没有发言的余地”的时代。*朱执信在《学者的良心》中纪录,章士钊1919年9月间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演说,被四面八方攻击,弄到最后,只好对外表示——用朱执信的话说:“(章氏)从大病以来,已有觉悟,现在不去欧洲留学,真没发言的余地。”见《朱执信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下集,第660页。所以西方思想界的最新动向,往往立刻影响中国知识人的思想。在1930年代前后的西方,的确常见到对传统哲学的诘疑甚至于“取消”之说。胡适所熟悉的杜威(John Dewey)固然主张“哲学之重建”,欧陆也正逢维也纳学派开始集结崭露头角。像《剑桥哲学史1870—1945》中的“The End of Philosophy as Metaphysics”一文中便描述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和逻辑实证论兴起时,带来了哲学是形上学以及“哲学的结束”这样的观念。*这个口号必定给一般人留下重大的印象。相关讨论请参考Simon Glendinning, “The End of Philosophy as Metaphysics,” Rom Harré, “Positivist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lan Richardson, “The Scientific World Conception: Logical Positivism,” in Thomas Baldwi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 1870-1945,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565-577, 11-26, 391-400.不过像胡适这样,认为科学足以完全取代哲学的说法仍然显得极端。杜威认为哲学与科学一样,是一种实验性质的认知方法;维也纳学派认为哲学以逻辑以及语意学的形式,可以继续发挥语言或概念分析的功能。换言之,西方的说法大体上放弃了传统哲学“认识终极真理”的信念,但是仍然给哲学保留一种很谦卑的位置。*这在近代科学初兴的年代已经常见,如Locke说过,哲学家只是负责清理地基,等着如牛顿、波义耳之类的大师负责建造知识大厦。此处请教了钱永祥教授,特此铭谢。由于西方最新的发展,往往就是“真理”之所在。所以胡适不能不敏感察觉到欧洲当时实证主义、逻辑实证论大军压境般的氛围。*参考Leszek Kolakowski, The Alienation of Reason: A History of Positivist Thought, NY: Anchor Books, Doubleday, 1969.尤其是第五章。
胡适的《哲学的将来》一文没有正式发表过,在他同一天的日记里,他把这个演讲的内容录进去了。其中就提到“哲学的根本取消,问题可解决的,都解决了”等等。1929年他废弃《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改写《中古思想史长编》。商务印书馆在1931年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收入《万有文库》的时候,胡适已将书名改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页。并计划将来再重写《中国古代思想史》,这都是重要的信号。
更重要的是,胡适在1930年代,曾经提倡要取消哲学系,取消哲学,宣扬哲学破产。钱穆的《师友杂忆》里有提到说,胡适是北大第一个西洋哲学史教授,而第一个西洋哲学史教授居然提倡要取消哲学系,这在当时是很震动的事情。*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61页。胡适教西洋哲学史很多年了,他的日记里有记载,今天上笛卡尔、上霍布斯,上了很多年,可是此时却主张应该取消哲学系。1934—1938年就读北大哲学系的任继愈晚年接受访问时便有这两段回忆,他说:“胡适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中国哲学不成体系。他贬得太低,所以北大的课叫中国思想史,不叫中国哲学史”,“因为胡适是文学院院长,所以课后他有发言权,课程名称都是他定的”。*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沈阳:辽宁出版社,1999年,第47页。当然不能因此说胡适从此便与“哲学”分道扬镳,或他即不再提到“哲学”。但是,似乎有意无意之间有这么一个分别。“哲学史”与“思想史”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成系统的,后者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
用“思想史”的角度与用“哲学史”的角度是迥然不同的。胡适说用“思想史”则可以写每一个时代,包括道士、佛教,包括他所最鄙夷的很多东西,但是它们都代表那个时代的思想,所以在《清代思想史》遗稿里,他说:“我们注重那代表时代的思想家,而不注重那继承宋明传统的理学家。我们宁可取那编小说的吴敬梓与李汝珍,而不必取那讲理学的汤斌、张伯行。”*见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7册,第38页。
我觉得胡适从哲学史转向思想史的变化,也代表他整个学术观点的一个变化,此后他近史学、汉学而轻哲学、理论。他宣称,我不是哲学史家,我是个思想史家。*见《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9页。有一段时间他在帮人写字时,喜欢写朱熹的“宁烦毋略,宁下毋高,宁浅毋深,宁拙毋巧”,其实指的都是史学性的工作,而不是哲学性的工作。在他没有发表的一个《中国哲学小史》的引论里,他强调以历史治哲学之企图:“我因为不满意于这种没有历史系统的哲学概论,所以想做一部含有历史性质的哲学概论,所以我这部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试验哲学概论是否可以用历史的眼光来做。”*见胡适:《胡适全集》,第7卷,第271页。
二
接着要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到《中国思想史大纲》的转变。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从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改写的。这部论文与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口试教授夏德(Friedrich Hirth)显然意趣相反。夏德偏向孔教派,他给陈焕章那本《孔门财政学》写的序中对之颇为赞赏。《孔门财政学》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刚好是两个极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批判性的、疑古的;而《孔门财政学》是要发扬儒家的现代价值以及在财政方面的智慧的。夏德喜欢的是后者,不是前者。我们一直只注意到杜威,杜威看起来是对胡适的东西很欣赏的,他好几个地方提到,写完以后交给杜威看,杜威也表示赞许。可是夏德喜欢《孔门理财学》这样的东西,所以他跟杜威的看法显然不同。*夏德1911年10月15日为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一书所写的序中说:“Western readers will find in his book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nfucianism from the purely Confucianist point of view by an author who is a Confucianist himself and has had the advantage of sifting his ideas through the methods of western science.”见陈焕章:《孔门理财学》(英文版),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vii页。夏德认为该书出自一个真正的儒者,真正代表了儒家的观点,语气中充满肯定与同情。而《孔门理财学》以晚清今文家的“三统”“三世”说为框架,从伏羲一路讲下来。夏德本人的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o the End of the Chóu Dynasty(New York: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8)也是从伏羲讲起的,此书最开头的部分有一个中心主题是“西来说”的问题,当时西来说甚嚣尘上。中国人自认为中国文明源自陕甘地区,源自本地,并无西来之迹象。夏德此书从盘古、天皇、地皇、人皇、伏羲、女娲、神农、黄帝、仓颉、少昊等(讲起),不过他有一个清楚的观念,认为前述是“神话与传说”,但是无论如何,他认为这是应该传述的历史。而这些与胡适英文的《先秦名学史》显然有所不同。《先秦名学史》从先秦诸子写下来,不提伏羲这些人物,这与夏德、陈焕章他们的书出入很大,但胡适那一篇带有“截断众流”意味的宣言性的序,是1927年他回中国路上短期滞留日本时所写的。其中提到,人们不晓得中国受传统的重压是如何巨大。此外胡适批评《管子》《晏子春秋》还有其他许多可疑的古书,即使《庄》《荀》也是部分接受而已。他说自己刻意不引《尚书》等——除非是他认为可信的篇章,对于经书他基本上全取高度批判性的态度,并说从头到尾,决不引用任何不能确信无疑的古书。这一篇英文序的态度,与胡适在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所宣扬的史料批判观点一致。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痛斥人们高谈“邃古哲学”“唐虞哲学”,“全不问用何史料”,“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有根据,止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尚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见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20-21页。夏德有一份用德文写成的第三人称的简单的自传(Friedric Hirth, “Biographisches nach eigenen Aufzeichnungen”),在这份自传中,并未提及他对儒家或孔教的看法,对他在哥大时期所言亦不多,仅大致说明所开课程,当然亦未有胡适的名字。夏德自传提及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之私交,传中指出康有为在纽约停留期间,常常拜访夏德。此处要谢谢萧高彦兄及杨尚儒代为释读这份德文自传。
蔡元培在一开始就给《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写了一个非常有决定性的序,提到它有四个重点:“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其中在“扼要的手段”中他提道,“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一点很重要,意思是不从伏羲或尧、舜、禹、汤开始讲中国哲学,而是从老子开始讲起。胡适是以史料批判为中心做的哲学史,他在康奈尔大学深受当时西洋哲学史的老师枯雷顿(J. E. Creighton)的影响,这位西洋哲学史老师写哲学史重视史料,重视时代背景,重视思想发展的时间次第,认为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写哲学史是不可靠的。*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一书中说,胡适曾说Creighton(江译为克雷登)“那种客观地对付历史上各阶段的思想史的态度,给我留下了一个极深的印象,也重新唤起了我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兴趣”(第307页)。江勇振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主要受克雷登的影响,不是杜威。克雷登的哲学史课程主题,包括了“本世纪的思辨问题,特别是进化观念的哲学意义及其重要性”(第286页)。所以对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大家都注意到杜威的影响,却忽略了还有枯雷顿的影响。其实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深受当时欧洲唯心论传统的影响。在《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他也列出了自己写这本书时在西方参照哪些东西。其中很重要的还有文德尔班,他还深受文德尔班所写西洋哲学史的影响。所以《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当时看来:第一,这是以西洋的哲学或哲学史的概念,有系统地来疏理古代哲学。*在一开始胡适就对写这本书的用意讲得很清楚,他要谈知识论、谈本体论、谈伦理学、谈教育哲学、政治哲学等。第二,他的史料批判具有非常强烈的疑古精神。他要重现学派的系统、传授和源流,他批评旧书的体例不清,要恢复各家学说的真相。而“乱了学说先后的次序,乱了学派相承的系统”是不行的,《管子》既不是真书,不可以用作管仲时代哲学史料等等。这些东西在谢无量的书里面都没有,在谢无量的书里面《管子》当然就是代表管子了。胡适则认为史料要经过批判。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有一个鲜明的主轴,即进化论。譬如他写庄子的时候提到“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认为这个就是“生物进化论”。当时有人批评马叙伦抄袭胡适这个说法,但马叙伦认为自己是师承章太炎的看法,这在当时的《北大日刊》是一桩公案。*参看傅斯年:《马叙伦著〈庄子札记〉》,原刊《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收入《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4册,总第1420-1425页;马叙伦:《释〈新潮〉中评〈庄子札记〉》,《北京大学日刊》第190、191、192期(1919年1月)。后来胡适在台北版的序言里面讲,他这个说法完全错误,庄子没有生物进化的看法,那是当时他作为年轻人一个大胆的说法而已。前面提到过,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时,深受枯雷顿影响,枯雷顿写西洋哲学史时,非常重视进化论在近代西方哲学上的作用,所以胡适在这本书里面讨论先秦诸子的时候,最重要的共同主题就是生物进化或者进化的思想。他讨论到墨子,讨论到荀子,讨论到其他许多,这都是他其中一个核心的观念。任何学说都是一个发生学的过程,不是一个静止的、不变的东西,它有个过程,一个发生学的过程。*参看胡适:《实验主义》《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全集》,第1卷,第277-323、360-362页。
胡适认为,“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岂可一昧迷信古书。先秦诸子没有一部可靠,“《庄子》一书,大概十分之八九是假造的,《韩非子》也只有十分之一二可靠”,《左传》不足信,“《尚书》是否可作为史料,正难决定,……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的史料”。*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12、22页。这是民国8年出的书。他当时的看法是,东周以前的古书都非常值得怀疑,《尚书》《左传》不可以作史料,所以《中国哲学史大纲》里关于社会背景的描述就变得非常少了,有很多都是引《诗经》的一些话来讲当时的战乱、人民的流离等等。*钱穆在北大与胡适共事时,曾面质胡适这个问题,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8页。但是在1944年的《中国思想史》的大纲中,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因为以前人们没有非常清楚地了解他后期对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看法,所以没有特别去注意。事实上,从其他的痕迹、其他文章也看得出来,但没有这么系统地展现。这份大纲特别讲“发生学的方法”,认为一个学说都有两端,都是一个发生的过程,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东西。不要像古代论述经书,道理是静止不变的东西,所以是一个祖孙的方法。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另外一个特色是西洋哲学的参证。《先秦名学史》是用英文写的,现在也有中译本。《先秦名学史》的序就讲得非常清楚,他有很重要的现实关怀,要用西洋哲学里面的逻辑学方法来复活中国先秦诸子里面的逻辑思想,用很有逻辑的思想来改造这个民族没有逻辑思维的习惯。所以胡适是非常清楚地要用西方的逻辑学来检讨中国先秦的名学思想,他的这本书里面用了很多西方的哲学,用得比较多的比如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康德(Immanuel Kant)。他这时认为东西哲学可以互相印证、互相发明,是因为人类官能心理大概相同,*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28-29页。如认为《老子》是西方的“自然法”,认为先秦诸子各家皆有生物进化论。
一直到胡适担任中研院院长时,还有很多人问他,怎么不把《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卷、下卷写完呢?问他的人一定也不知道胡适的看法变了。事实上,他现在要写的是《中国思想史》,整部的《中国思想史》,而且从胡适所遗留下来的这一份《大纲》看来,他构想中的《中国思想史》观点与《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有变化的。
在1945年英文版的《中国思想史大纲》中,他一开始谈到中国古代的思想跟希腊、罗马、欧洲等等的比较的时候,就提出,“为什么我讲的是history of thought,而不是history of philosophy”?他的言词里似乎表示,如果要写哲学史就得讲在西方哲学标准下能成系统的、抽象的知识论、本体论那样的东西。可是,他写完先秦那部分接着要写下去就不行了,接下去很多都是宗教的,佛教、道教的或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在严格意义上,至少在胡适看起来,并不是“哲学”。
我觉得这份《大纲》有几个特色。跟《中国哲学史大纲》比起来,一个是1919年,一个是1944年。经过25年,胡适的很多看法都变了。*但后来他并非没有写过思想史方面的论文,现在《胡适全集》里面好几册都是思想史方面的。然而,因为这份《大纲》中比较系统地讲,可以比较清楚看出他这25年里的变化。在这里我要举例性地讲几点:首先,胡适对史料持批判的态度这一点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没有像原来那么激烈。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渊源非常长,他非常注意史语所当时在殷墟做的15次挖掘。我觉得这15次挖掘的东西改变了他对古代很多东西的看法。所以他对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对董作宾的研究,对古代东边、西边两个集团的说法都很重视。他其实是用这个背景来重新讲中国古代思想。他也谈到很多考古发现里面可以跟思想有关的东西,而这些都在孔子或老子之前,不像《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一切只能从老子讲起。*他非常不满意冯友兰从孔子讲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出来的时候,杨联陞当时已经在哈佛任教,在美国发表了一个英文书评,胡适给他信说,你下笔太轻了,要再重一点,这本书太糟了。见胡适纪念馆编:《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第99页。由于胡适关怀的重点由哲学史慢慢倾向思想史,所以他很注意那一段时间古代考古发掘方面的思想史意涵的影响。而这使他可以把中国思想从商代的宗教一直讲下来,从人殉等等一直讲下来。
前面提到,《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截断众流”,从老子讲起。但在《中国思想史大纲》中,胡适费了许多笔墨讲老子以前的思想概况。他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一定非常古,不像以前那样宣称,“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22页。他也引用了很多《左传》《尚书》中的材料,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则认为《左传》跟《尚书》不可信(康有为讲《左传》是伪造的)。所以这种看法已经变了。他比较愿意承认,在考古的证实之下,很多东西都可以信了。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关于先秦诸子的起源的问题。《中国哲学史大纲》否定诸子出于王官说,而又不信《尚书》《左传》等书,所以对于先秦诸子之兴起,依《淮南子》说是起于“救世”。而《中国思想史大纲》则颇讲述先秦诸子的宗教与思想背景,但仍未见提到诸子出于王官之论。
当然,这份1554片纸的《大纲》把他过去的几十年的关于思想史的研究观点也吸收进去。不过有一些看法并未改变,如他对佛、道有很多研究,但极尽嘲讽。他非常重视所谓中古的“印度化运动”。胡适在哈佛大学300年的时候,应邀去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讲中国中古的“印度化运动”。*“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Borrowing,” 收入《胡适全集》,第37卷,第328-364页。即使现在看起来,我还是觉得那篇文章很有看法、很有价值,讲中古佛教进来以后,中国人的整个世界观、时间观、人生观等重要的变化。文中他也做了很多比较,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佛教此后变成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反映。
对理学,他当然还是持比较批判的态度。他跟陈寅恪不一样,陈寅恪认为宋朝的思想学术是最光辉、最高明的时代,可是胡适的看法并不相同。他也用美国人所比较了解的词语,譬如讲东周时,他用东罗马帝国来比喻;讲宋代的“新政”、支持“新政”的人时,又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New Deal联系起来。总之,他用了很多当时西方人比较熟悉的词来讲。像讲孔子以前是《旧约》、孔子以后是《新约》的时代等等;我们把理学译成Neo-Confucianism,他不是,他译成Rational Philosophy。不过他讲道学的几个新派时,似乎讲得太无为、太消极。如他认为邵雍、周敦颐都是道家思想家(Taoist Thinkers)。当然他一直讲到清朝,讲到颜元、李塨就结束了。我几年前看了梅光迪的文集,看到他们的通信,才知道原来早期胡适是非常赞赏程朱理学而反对颜元的,而梅光迪在当时则反对程朱理学并且是支持颜元的。后来这两个人在新文化运动里面成为最激烈的敌人,而且他们的思想刚好倒过来。*梅光迪:《致胡适信四十六通》第三函,收入罗岗等编:《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3-116页。胡适很年轻与梅光迪认识的时候,梅光迪就已经认为胡适会是天下第一的人物。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胡适的学术态度仍有其一贯性。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他说以当时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或是他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述古史观书》中所说的,“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顾颉刚编:《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一册,第22页。言下之意是,如果考古学的发现足够,他也未必不可改变想法,而《中国思想史大纲》大量引用考古材料讲北京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等,也说明了这是胡适一贯不变的态度。但因为考古中未出现夏代文物,故《中国思想史大纲》中并未提及夏代。同时也因为商代部分的考古发现丰硕,所以他写商代的部分很多。
从前面的讨论来看,胡适在五四之后的二十几年里面有了重大的变化,它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对哲学的态度,一是对中国古代思想的重估。过去,有人认为胡适没有把哲学史中卷写下去是因为后来被佛教卡住了,没办法像处理先秦诸子那么得心应手。可是现在发现还有一层原因,因为他整个看法已经变了,他已经不再继续写哲学史,而是要写思想史了。当然,还有人困惑,胡适是哲学系毕业的,可他好像变成了汉学家一样,尽管这么多人一再呼吁他:你没有在哲学和思想上作一个大的对抗,使得左派的思想如此蔓延。胡适最后在离开大陆之前,在北平作了一个《水经注》版本的展览。当然也有一些人非常反对,可还是有一批人津津乐道。
胡适原来是以西方哲学的标准与规范来讲先秦诸子,所以出发点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他反复说明:“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哲学。”*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29页。但是东西哲学互相印证、互相发明,并不表示西洋有的我们也有,而由此滋生发扬国光、夸耀自己之念。然而,他最后仍希望东西两支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5页。这是相信有一普遍的哲学的措词,与持“思想史”观点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由“哲学史”到“思想史”显示一种由universal渐变成比较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倾向。不是只要有几个重要的阶段,符合“哲学史”定义的才能写,而是每一个时代的思想都值得写。他说,梁漱溟跟梁启超所讲的正统哲学,只有800年前有,以后就没有了,好像以后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表这些思想。*我觉得后来胡适从哲学史转为思想史,有一个重要的地方跟当时其他做哲学史的不大一样。当时偏向哲学的人,似乎认为既然这些东西都可以用西方的哲学标准来做,所以是有现代价值的。胡适改做思想史,并不表示他认为这些思想都有价值,他主要是在做一个史学家的工作,把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变化写下来。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此后的现实变化是,胡适慢慢疏离了中国哲学圈。其实从《胡适日记》里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中国哲学会(1935)、《哲学评论》创始的时候,他都是参与筹划的人,但后来,可能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到美国去,他就不在哲学圈里活动,而变成史学、汉学圈里面的人了。
当时有人认为,知识界的领导人物群趋考据,疏离了哲学与思想的大问题,是无法对抗左翼思想的一个原因。譬如傅斯年从美国回到中国以后,在一些小的笔记本里面就写过这类反省的话。*参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244-250页。这样的反省,可能与胡适等人慢慢地疏离哲学有关。胡适是当时学界最核心的人物,但他的关怀已别有所在了。冯友兰、贺麟、黄子通等人慢慢变成这个哲学圈的中心,当时哲学学会、《哲学评论》是另外一批人。我觉得两个圈子的慢慢分离,是1930年以后的一个现象。贺麟在《文化与人生》里提到,他认为1930年以后,有另外一个圈子的人(包括贺麟自己)是要讲哲学、讲价值、讲现实人生这些问题的,但学界另有一种非人格(Depersonalization)的趋势。他所指的当然是哲学圈中的人。*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85页。即使在哲学阵营中,冯友兰与其他讲传统哲学者亦不同。任继愈即说:“比如说冯先生讲课,一定要讲得出说得清的才算。但是中国哲学有个直观的体悟的东西,可以意会不可言传,这一部分也是核心部分。……可冯先生就不承认这个。”*林祥主编:《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第46-47页。这使得冯重分析不重体悟,包括《贞元六书》中的《新理学》也表现出这样的特色,这使得他与其他人,尤其是新儒家哲学之间仍有一定距离。
结 论
在以上这一篇短文中,我主要透过胡适后期在哈佛大学讲课的一份英文大纲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胡适中年以后疏离“哲学”,并逐渐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的过程。这个转变,对他的学术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甚至宣布想废除北大哲学系,同时也使得他与这个重要的学术领域日渐分道扬镳,似乎也因此而不能在思想、哲学的战场上与当时的左派思潮作一对抗。第二,是透过比较,爬梳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到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这25年间,胡适在若干重要学术论旨上的巨大改变。以胡适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枢纽地位,他上述两方面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注意。
(责任编辑:史云鹏)
From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o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On the Draft of Hu Shi'sAnOutlineofChineseIntellectualHistory
Wang Fansen
In Hu Shi Memorial Library in Taipei there is a copy of Hu Shi's English draft ofAnOutlineofChineseIntellectualHistory. The shift fromA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toAnOutlineofChineseIntellectualHistoryreveals two critical changes in Hu Shi. The first change is his dephilosiphisation, that is, starting from his middle age years he gradually moved from philosophy towar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 Apart from Fu Sinian's influence, this change of Hu Shi migh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intellectual trends of that time, which turned his attention away from philosophy, and thus rendered him powerless in combating the Left-wing scholars. The second is his change of views on a number of important academic subjects, including criticism concern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doubting attitude on the ancients, and the mutual rectific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As Hu Shi has always remained a key figure i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tremendous influence of his intellectual changes deserves much of our attention.
Hu Shi,A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AnOutlineofChineseIntellectualHistory,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tellectual history
王汎森,(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K26
A
1006-0766(2017)03-0005-09
§胡适研究§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罗志田
专栏导语:2016年是胡适诞辰125周年,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下的胡适研究会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等机构于12月17-18日在北京大学举办了“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因金以林会长的美意,得预现代文化学会事宜,也参与了此次研讨会。学报的原祖杰教授命我在研讨会论文中择优组成一个专辑。作者王汎森(王教授因事未能与会,然惠允我们收入他为会议准备的论文)、章清和张太原分别是所谓50后、60后和70后的优秀学者,他们探讨了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胡适对建构“社会重心”的省思以及胡适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代表了胡适研究的一线成绩。现在不少人以为好题目已经被做得差不多了,然而我们从这些论文可以看到,即使在一些久已深垦的领域,也还大有开拓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