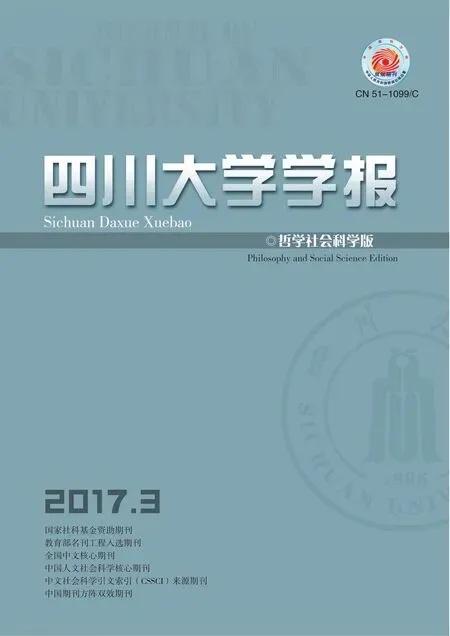“侦查重心主义”研究
——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反思与拓展
秦宗文
“侦查重心主义”研究
——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反思与拓展
秦宗文
“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推进庭审实质化,但庭审实质化仅单向强化了错案过滤功能,加之审判者的深层认知心理因素、证据信息在诉讼进程整合中的有罪强化趋势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实质化的庭审程序仅能适用于少量案件等,其对实体公正的整体保障作用将是有限的。英美对抗式审判仍产生了大量错案即为明证。解说当前改革的两种代表性意见都高估了庭审实质化的作用,提升实体公正水平应贯彻“侦查重心主义”。此概念与传统的“侦查中心主义”不同,可以融入当前改革,并要求深化改革。贯彻“侦查重心主义”要求对侦查行为进行程序控制;防止以虚假供述为主要目标强化辩护人的监督权;并强化侦查录音录像,为还原侦查过程提供可能。
以审判为中心;庭审实质化;侦查中心主义;侦查;司法改革
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任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对改革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明确了“以审判为中心”在当下刑事司法改革中的主线地位。这一改革针对刑事司法多年积弊,与学界讨论多年的“审判中心主义”改革思路也一定程度上契合,研究者反应积极,已有不少成果发表。*代表性论文主要有龙宗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及其限度》,《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朱孝清:《略论“以审判为中心”》,《人民检察》2015年第1期等。这些成果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一是以审判中心主义理论为根基,在肯定当前改革的基础上,提出应进一步推进改革,特别是实现审判对审前程序的控制,建立全面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这代表了理论研究者的理想化路径;二是以诉讼阶段论为出发点,将改革主要集中于审判程序,特别是推进庭审实质化,并以庭审标准指导侦查和起诉工作。这是实务人员对改革方案的解释性意见。
不同视角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当前的改革,但从“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着力实现的保障实体公正、防范冤假错案的目标考虑,两种思路在如何处理审判与侦查的关系上,都有较大的不足。第一种路径强调审判权对侦查活动的程序控制,有利于改革当前的侦查中心主义格局,促进实体公正。但它将审判视为实现实体公正的关键,低估了侦查程序在实现实体公正方面的重要性。第二种路径希望通过单一的庭审实质化改革提升实体公正,不从实质上触及侦查中心主义,更是对审判作用的高估。事实上,不仅我国当前的侦查中心主义诉讼制度下侦查是实体公正形成的真正重心,即使是在西方法治国家的审判中心主义的诉讼制度下亦是如此。审判在实现实体公正、防范冤假错案方面,作用是相对有限的。上述两种改革思路都错置了审判与侦查在实现实体公正方面的位阶。无论以哪一种思路推进改革,都可能造成司法资源配置不合理。承认审判的中心地位,在此前提下确立“侦查重心主义”的观念并进行相应的改革,对保障实体公正、防范冤假错案目标的实现,都更为有利。
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内涵
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内涵,研究者有不同意见。总体上,理论界多倾向于站在“审判中心主义”理论立场进行解读,并期待改革向全面的审判中心主义推进,但一些看法有以理想代替现实之嫌。实务界的解读相对保守,然而一些观点似有部门色彩。回到这一改革的最权威依据——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及相关说明材料,对“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内涵进行解析,特别是阐明与“审判中心主义”的区别,是展开本文讨论的基本前提。
《决定》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全面贯彻证据裁判规则,严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的说明是:“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办案人员对法庭审判重视不够,常常出现一些关键证据没有收集或者没有依法收集,进入庭审的案件没有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要求,使审判无法顺利进行”。 对改革的目的,其解释为,“全会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办案人员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确保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项改革有利于促使办案人员增强责任意识,通过法庭审判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决定〉的说明》,2014年10月28日,http:∥news.qq.com/a/20141028/054014.htm,2016年10月2日。
解析上述文献,“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实现庭审实质化
庭审实质化是此次改革的核心内容,目标是改变既往侦查中心主义导致的庭审空洞化,使“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参见《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第11条、第13条、第14条。“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最高人民法院是主要推动者。*张建伟:《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内涵与实现途径》,《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结合2013年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的精神,对“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实质会有更好的把握。“让庭审实质化,更明确地说让审判成为中心,将成为刑事审判下一阶段最显著的变革”。*赵凌:《庭审“敢于”不走过场,中国法院变革刑事审判》,《南方周末》2014年10月24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95327,2016年10月30日。这清晰地说明,“以审判为中心”基本等同于庭审实质化。
(二)改革的任务是在维持诉讼阶段论的基础上保障审判权的独立行使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当前公检法三机关诉讼关系的建构基础。习近平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对其再次予以肯定,“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制度,必须坚持”。*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决定〉的说明》,2014年10月28日,http:∥news.qq.com/a/20141028/054014.htm,2016年10月2日。“以审判为中心”这一底色使之与审判中心主义有着本质区别。
审判中心主义是要求“法院不仅主导审判程序,而且对审前程序有一定的监督和控制作用。……包括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含令状原则),以及对于权利保护诉求进行判断并实施司法救济的机制”。*龙宗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及其限度》,《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而“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仅是要实现案件实体审理的“以审判为中心”,而不涉及法院对审前程序的即时性程序控制问题。对“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坚守,决定了“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主要效用,是对“侦查中心主义”造成的弊端加以纠正,甚至说是恢复“阶段论”的本意也并不为过。
按照“阶段论”,法院虽不能对审前阶段进行即时性的干预,但它有权对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从事实、程序和法律适用进行独立判断,不受检、警两机关的不当影响。司法实践中形成的侦查中心主义是违背“阶段论”的。“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实际上是法院落实“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下本应享有的权力。宪法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在审判居于程序后位的情况下,即使没有“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只要坚持审判权独立行使,同样可以实现当前改革欲达到的目标,如“促使办案人员树立办案必须经得起法律检验的理念”,“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终围绕审判程序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法发[2015]3号文)。所以,有司法高层人士认为,“要落实‘以审判为中心’”,“首先要把现行的诉讼法实施到位。”*朱孝清:《略论“以审判为中心”》,《人民检察》2015年第1期。从这点看,“以审判为中心”的主旨似乎是找回失落的独立审判权,而不在于将其扩张至审前程序。
(三)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实体公正
“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错案产生”,是“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核心目标。“责任意识”的强化,“程序公正”的提高,仅是实体公正目标的实现方法。在近些年冤错案件频频暴露的背景下,以实体公正作为改革的导向较易解释。冤假错案充分暴露了侦查中心主义模式的弊端,这不但彰显了改革的必要性,也影响到改革目标的设置。“刑事审判最让公众关切的还是冤假错案,这几年连续披露的错案对司法公信力有很大杀伤力”。参加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的学者“在会议上能感受到法院领导的压力,冤错案已经让他们认识到不改不行了”。*赵凌:《庭审“敢于”不走过场,中国法院变革刑事审判》,《南方周末》2014年10月24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95327,2016年10月30日。从时间点和内容上看,《决定》的内容与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联系紧密。以实现实体公正作为改革的核心目标,是对实践问题的针对性回应,与我国重实体的刑事司法传统一脉相承,也与当前社会舆论将案件实体是否公正作为判断司法公正与否的主要标准相符合。*在我国,如果有刑讯逼供,但案件结果是正确的,无论是公众还是执法人员对刑讯逼供都有相当高的接受度。参见林莉红、赵清林、黄启辉:《刑讯逼供社会认知状况调查报告(上篇·民众卷)》,《法学评论》2006年第4期;毕惜茜、李铁军、姜军:《新刑诉法背景下侦查讯问立法完善实证调查与研究》,《政法学刊》2012年第5期。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与学界倡导多年的审判中心主义在整体思路上有一定的契合度,被认为“系中国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建构思想上的一种理性回归”。*龙宗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及其限度》,《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因而,一些讨论“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意见,有意或无意地以审判中心主义为基准,混淆了二者的界限,用审判中心主义的理想,替代了“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原意。实际上,从司法高层的意见看,“以审判为中心”与审判中心主义的内涵相去甚远。*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朱孝清:《略论“以审判为中心”》,《人民检察》2015年第1期。对“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坚持,足以使“以审判为中心”清晰区别于审判中心主义。“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远景可能走向审判中心主义,但至少现实的近景改革规划中,“以审判为中心”仅是法院恢复独立审判的努力而已,*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其内容基本等同于庭审实质化;其对审前程序的影响只是试图以审判的实体标准指引侦查、起诉工作,*《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第3条。避免案件“带病”进入审判程序,“造成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的局面。*孟建柱: 《主动适应形势新变化 坚持以法治为引领 切实提高政法机关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人民法院报》2015年3月18日,第1版。但这种指引是间接的,不是通过即时性的程序干预进行控制。
二、庭审实质化改革对实体公正保障作用的有限性
根据目前的改革构想,实现保障实体公正目标的主要路径是通过庭审实质化提高法庭查清事实真相的能力,并借此将审理标准辐射于侦查、起诉活动,以倒逼机制促使检、警人员按照审判标准办案。但庭审实质化对实现实体公正的作用将是有限的。
(一)庭审实质化的主要作用是单向强化错案过滤功能
刑事诉讼中,建构犯罪事实的任务主要由能动的侦查工作完成。法官的主要任务是审核被起诉的犯罪事实是否成立,过滤和否定控方可能的错误有罪指控,而不是主动建构犯罪事实。而实体公正不仅包括避免冤枉无辜,也包括避免错放真正的作案者。庭审实质化将主要提高法庭过滤有罪错误指控的能力,而对侦查人员取证不充分导致罪疑的案件,法庭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庭审实质化所可能实现的实体公正是单向度的。
(二)经验事实证明,对庭审实质化的纠错能力不宜高估
庭审实质化,英美法庭审判模式具有标杆意义。但事实证明,对侦查阶段事实认定错误的案件,英美法庭的纠错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有美国学者研究认为,联邦调查局所谓的“登记在案的重大案件”里,被起诉与定罪的人中,5%是清白的。*伊丽沙白·罗芙托斯、凯撒琳·柯茜:《辩方证人》,浩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页。另有学者分析了通过“无辜者计划”纠正的错案后认为,1980年代美国最严重的强奸杀人案中,错判率为3.3%至5%。*See D. Michael Risinger, “Innocents Convicted: An Empirically Justified Factual Wrongful Conviction R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 Criminology, Vol.97, No.3, 2007, pp.761-762.在英国,上世纪90年代初,一项官方调查报告表明,“‘有问题的’判决发生率,在法官看来是2%(每年250个案件),在辩护律师看来是17%(约2000件)”。*麦高伟主编:《英国刑事司法程序》,姚永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462页。这些判决都是经正式的审判后做出的。我国当前的庭审实质化改革很难达到英美国家的程度,即使能达到,这种错案比例也显然超出了大多数公众通常可接受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一项美国学者对实际案件的研究表明,被告人在侦查审讯中虚假认罪的案件,86%的案件在审判中被错误定罪。*See Boaz Sangero & Mordechai Halpert,“Proposal to Reverse the View of a Confession: From Key Evidence Requiring Corroboration to Corroboration for Key Evidenc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Journal of Law Reform, Vol.44, Iss.3, 2011, p.526.庭审的纠错能力之低令人吃惊。显然,英美两国的实践表明,对通过庭审实质化改革防范错案不应寄予过高期待。
当涉及隐蔽性证据时,庭审在发现事实真相方面的局限性尤为明显。被告人的口供中包含隐蔽性证据,口供往往被认为是真实的。*对隐蔽性证据特点的分析可参见秦宗文:《刑事隐蔽性证据规则研究》,《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如果隐蔽性证据在侦查阶段发生错误,案件往往被错判。如美国通过“无辜者计划”平反的当初主要依据有罪供述定罪的无辜者中,隐蔽性证据都起到了关键作用。法官甚至因隐蔽性证据而拒绝采信与之矛盾的DNA鉴定意见。*See Brandon L. Garrett,“The Substance of False Confessions,” Stanford Law Review, Vol.62, Iss. 4, April 2010, pp.1054,1057-1058,1061.
如果说我国错案可归因于庭审虚化,而英美两国的错案则显然不能归罪于此。对庭审查明事实能力的局限性,一位法院高层人士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侦查阶段“有无诱导、暗示、引诱辨认人作出辨认,我们是审查不出来的”。*张军主编:《刑事证据规则理解与适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绪论第12页。这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获取其他证据的不当行为。因此,庭审实质化改革实不足以独立承担实现实体公正的重任。
(三)审判者的深层认知心理因素制约着庭审的纠错能力
研究者对制约庭审纠错能力因素的讨论通常忽视了影响法官事实认定的深层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在各国刑事司法中具有共性,即便当前改革能较好地实现庭审实质化目标,它们仍将制约着庭审的纠错能力,且难以克服。
1.口供引发的有罪认知偏见
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人相信自己不会承认没有犯过的罪行——他们相信别人也是如此”。*Saul M. Kassin,“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False Confessions,”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Vol.9, No.1, 2015, p.38.如果犯罪嫌疑人作了有罪供述,人们对供述的真实性一般都持肯定立场,特别是在涉及重大利害关系的刑事案件中更是如此。如果被告人后期翻供,常被视为审讯压力解除后企图脱罪之举。如海南省检察院对黄亚全、黄圣育案的剖析报告认为,酿成错案的原因之一就是承办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先供后翻的案件,往往宁愿相信其供述而不相信其辩解。……承办人错误地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辩解是认罪态度不好”。*《海南省万宁县黄亚全、黄圣育故意杀人案》,2014年12月22日,http:∥www.360doc.cn/article/191726_434767097.html,2016年9月29日。因而,口供可以说是摆在法官面前的最危险的证据,它往往使法官带着预断开始审判,而这种偏见对证据评断的影响,可能是在法官自己都难以觉察的情况下完成的。
口供对审判的关键性影响也得到了试验的证实。美国模拟陪审团审判研究证明,有罪供述对陪审团裁决的影响力超过了目击证人和品格证据。*Kassin,“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False Confessions,” p.38.另一项以132位有经验的法官为对象的研究中,在其他证据较弱时,如果缺乏口供,做出有罪判断的法官仅占17%;如果口供是在低压力下获得的(被告人在口供前仅被讯问了半小时;被告人声称受到了强制,但不能提供具体的强制行为),做出有罪判断的法官达到了96%;即使口供是在高压力环境下生成的(讯问人员拒绝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无罪辩解;讯问进行15个小时后才做出供述;讯问人员以死刑威胁犯罪嫌疑人等),做出有罪判断的法官仍达到了69%,有罪认定的比例是没有口供时的4倍。由此可见,口供在审判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偏见性地主导司法决定的方向。*See D. Brian Wallace & Saul M. Kassin, “Harmless Error Analysis: How Do Judges Respond to Confession Errors?” Law Hum Behav, DOI 10.1007/s10979-010-9262-0, Publish on line: 12 January, 2011.
口供几乎有着难以抵抗的魔力,一旦被告人在审讯中做了口供,很多审判者的首要立场不是客观地审查口供虚假的可能性,而是下意识地以口供为主线组织证据体系,看能否认定被告人有罪,甚至修改对其他证据的已有评价意见,对不同意见则关注不足。如陈夏影三人绑架案中,辩护律师回顾当年的庭审现场,“完全像是走过场,我们律师说的,法院一概不听,只采信检察院的‘一面之词’”。*孙静、赵亚萍、王倩:《男子因“闲聊”卷入绑架杀人案 喊冤18年有望翻案》,《北京青年报》2015年1月29日,http:∥news.163.com/15/0129/03/AH3KC1PP00014AED.html, 2016年9月6日。这种近乎本能性的偏见不但易使法庭降低口供可采性的标准,也往往削弱法庭寻找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的积极性,如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难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此。
这意味着,一旦侦查阶段取得的口供为虚假,其很可能在审判中被作为定案根据并酿成错案。
2.审判者的有罪推定与证实性偏差倾向
刑事司法中弥漫着有罪推定的气氛,这似乎是各国共存的事实。如德肖维茨教授认为美国刑事司法存在13个潜规则,其中 “规则一:事实上,大多数刑事被告人都是有罪的。规则二:所有刑事辩护律师、检察官和法官都了解并相信规则一”。*艾伦·德肖维茨:《最好的辩护》,唐交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1页。现实中,这种有罪推定心态在侦查讯问时就已普遍存在。如一位反贪局长所言:“通过初查认为嫌疑人是极有可能存在犯罪事实的,那么接下来就需要一种‘有罪推定’。”否则,“我们的思维很多时候会被对方影响,或者相信了对方的辩解”,*田骁、朱晓:《一边善用谋略,一边挖掘人性》,《方圆》2013年第1期。因此“不能持以‘或许清白’的疑虑进行审讯”。*浜田寿美男:《自白的心理学》,片成男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48页。有罪推定是制定和实施侦查策略的基础。基于打击犯罪的社会普遍心理,绝大多数被告最终被认定有罪的事实,以及对警察工作的信赖,法官很多情况是以有罪推定为起点开始工作。比如“规则八:大多数初审法官明知警察在说谎,但也装作相信他们。……规则十:多数法官都不相信被告人关于其宪法权利被侵犯的陈述,即使他们说的是真话”。*艾伦·德肖维茨:《最好的辩护》,第11页。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案卷移送制度更强化了审判者的有罪推定心理,有罪推定的普遍性不但在一系列错案中被证实,也为司法高层人士所承认。*参见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6日,第2版。而有罪推定影响下的证实性偏差倾向,使法官更为关注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信息,忽视或贬低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证实性偏差对证据收集与评价的影响可参见秦宗文:《刑事隐蔽性证据规则研究》,《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
如果侦查阶段对事实判断错误,特别是获得虚假认罪口供,审判人员的有罪推定心态和证实性偏差倾向将加大形成错案的风险。
3.审判者的过分自信倾向
执法者往往高估自己识别虚假供述的能力,存在过分自信的现象。许多心理学试验对人们判断真假的能力进行了研究。其通常采用的方法是,让一些普通人,通常是大学生,到实验室来,每人讲一个真的或假的故事,并对此过程进行录像。然后,将录像给被试观看,让他们判断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并给出他们对自己判断结果的自信程度。这些研究表明,普通人对谎言的正确识别率为55%左右,只比抛硬币好一点。另一项研究证明,专业人士在识别谎言方面的能力也远低于预期。侦探和CIA、FBI、军队测谎人员以及法官、精神病医生、特工等所有测试组中,成绩最好的特工人员的正确识别率也仅为64%。*See Saul M. Kassin, “Human Judges of Truth, Deception, and Credibility: Confident but Erroneous,” Cardozo L. Rev., Vol.23, No.3, 2002, pp.810-811.人们识别谎言能力的不足,在对实际案件的分析中也得到证实。有研究表明,存在虚假供述的案件,进行审判程序后,被错误定罪的比例高达86%。*See Sangero & Halpert, “Proposal to Reverse the View of a Confession,” p.526.这一方面反映了供述对判决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司法实务中虚假供述被识破的概率很低。
但参与实验的被试对自己判断结果的自信度普遍高于其实际能力,特别是受过特定技能训练者更是如此。如一项试验中,每个学生看8个讯问录像。一组没有经过培训的学生的平均识别准确率为4.4个;另一组适用“雷德讯问法”培训过的学生的平均准确率仅为3.65%,但他们更自信。为应对该试验对象为非专业人士的质疑,试验设计者将录像给34个警察观看,其平均从业时间是13.7年,有68%接受过专门培训。他们的总体准确度是56%,但他们自我感觉判断准确率平均值为82%,存在明显的过分自信现象。*See Kassin, “Human Judges of Truth, Deception, and Credibility,” pp.812, 813-814.此试验的被试者虽然是警察,但其研究对象是人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带来的判断自信与实际能力的偏差问题,结论对法官也是适用的。
过分自信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但在亚洲范围内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可能是中西方教育方式的差异和亚洲人传统上缺乏概率观念。*于窈、李纾:《“过分自信”的研究及其跨文化差异》,《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
对虚假供述实际识别能力与自信度之间的偏差,可能进一步放大虚假供述诱发的认知偏见,使审判者做出错误判断而不自知。如果过分自信的跨文化现象属实,我国审判者在事实认定问题上可能会比西方同行犯更多的错误。
上述心理因素根植于人的认知机制,庭审实质化只能抑制而很难根除其影响。因上述心理因素引发误判率的高低,更多地与侦查阶段事实错误的机率正相关。减少审判结果的错误,应将重心放在侦查程序。
(四)证据信息在诉讼进程中的整合存在有罪强化趋势
案件的侦查过程,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试错过程,是侦查人员对各种犯罪构想进行验证的过程。当案件最终侦查终结时,参与侦查过程的人员对案件的各种可能性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证据体系的薄弱之处也比较清楚。当案件移送起诉时,他们通常会根据追诉的需要组织证据体系,并对证据的含义作有利于追诉的解释,有时会舍弃或隐匿不利于追诉的证据,*这在安徽余英生杀妻案中表现明显。参见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节目:《检察官在行动:洗冤“于英生杀妻案”》文字版,2015年2月4日, http:∥news.jcrb.com/jxsw/201502/t20150204_1475323.html,2016年9月26日。甚至伪造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日本20个典型刑事错案的产生原因中,警方伪造证据的占13%。参见何宏杰、吕宏庆:《日本预防刑事错案的系列改革》,《人民法院报》2013年5月17日,第5版。检察官决定提起公诉时,会根据追诉需要对证据材料进行优化,并进一步压缩证据材料作其他解释的空间。这一过程也存在将不利于追诉的材料进一步舍弃或隐匿的可能性。当案卷材料最终流转至审判者面前时,证据体系是根据有罪需要来组织的,侦查工作中的漏洞已尽可能得到粉饰,不利于被告人的信息被刻意强调。以这种材料为基础,法官通过阅读案卷在庭审之前往往已形成有罪确信。德国学者研究证明,这种情况下,即使证人按照庭审实质化的要求出庭作证,对庭审结果也几乎没有影响。“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审前程序具有的意义比至今法律政策讨论中认为的要大得多”。*贝恩德·许乃曼:《案卷信息导致的法官偏见:关于与英美模式比较下德国刑事诉讼程序优缺点的实证研究》,刘昶译,载何挺等编译:《外国刑事司法实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2、84页。
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方案,并没有变革案卷移送制度的构想。如果侦查阶段事实认定发生错误,证据信息在诉讼进程中的有罪强化整合过程,使审判很有可能出错。
(五)错案的纠正难度随诉讼进程的责任累积而加大
案件错误发现越晚,程序推进越深入,造成的损害往往也越大,牵连的公检法人员也越多,在当前办案责任制下,累积的追责任务也越重,纠正错误面临的阻力一般也越大,更可能出现将错就错、知错不改的现象。这一点在聂树斌案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从这点看,将实体公正的重心向侦查程序倾斜,尽可能在早期的侦查阶段发现错误,比在审判阶段发现错误,更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
(六)实质化的庭审程序仅能适用于少量案件
通过庭审实质化改革保障实体公正的前提,是案件能够适用实质化的庭审进行审理。但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案件进行程序分流,提高简易程序处理案件的比例,就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方向。当前以简易程序处理的公诉案件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如2012—2014年,黑龙江省全省简易程序总体适用率为 49.30%;*贾志强、闵春雷:《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实践困境及其出路》,《理论学刊》2015年第8期。2013年西宁市基层法院的刑事简易程序适用率达到了86%。*李雪、赵元智:《刑事简易程序适用机制探讨——以西宁市基层检察院和法院为样本分析》,《法制与社会》2014年3月(上)。司法改革力推的刑事轻微案件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机制等,将进一步降低通过实质化庭审处理的案件比例。从国外情况看,少量案件以实质化的庭审审理也是以其他案件的程序简化为前提的。如美国的对抗式庭审是以绝大多数案件通过辩诉交易处理为前提的。美国联邦法院定罪的案件中,97%是通过辩诉交易完成;州法院定罪的案件中,94%是辩护交易的结果。*See Yale Kamisar, “The Rise, Decline, and Fall(?) of Miranda,” Washington Law Review, Vol.87, No.4, 2012, pp.1022-1023.2001年,经过程序分流,德国只有15.6%案件进入法庭审理程序。*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趋势和冲突领域》,樊文译,载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41页。如果要完成庭审实质化改革,我国必须进一步强化程序分流,以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比例应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第21条第一次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列为选择关系,改变了刑事诉讼法第208条适用简易程序应同时具备“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和被告人认罪两项条件的要求。这意味着只在被告人认罪,即使案件事实不清,也可不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由于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被告人审判时都表示认罪,我国未来可能只有极少数案件通过实质化庭审程序进行审判。
这意味着,即使按照当前计划对庭审进行实质化改革,能适用该种程序的也只能是少数案件。案件实体公正的保障将更依赖于审前程序的工作成果。如果审前程序,特别是侦查程序出错,以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酿成错案的机率将更高。
三、提升实体公正应实行“侦查重心主义”
(一)什么是“侦查重心主义”
侦查重心主义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其含义可通过与侦查中心主义的比较得到更清晰的理解。“侦查重心主义”不同于惯用的“侦查中心主义”。所谓侦查中心主义是指侦查活动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侦查过程基本不受检察官、法官的干预,并且侦查结果通常可得到检察官、法官的认可,实际上左右着起诉、审判活动的结果。这使整个诉讼过程以侦查为中心进行,起诉和审判趋于形式化,丧失纠错能力,其结果就是“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由于侦查思维具有很强的有罪推定倾向,侦查中心主义使整个刑事司法充溢着重打击、轻保护的色彩,更可能冤枉无辜而非错放罪犯。我国错案的频繁暴露与侦查中心主义的诉讼机制密切相关。提高我国刑事司法的实体公正性,防范冤假错案,必然要求否定侦查中心主义。
侦查重心主义认为,在刑事诉讼的各阶段中,侦查是决定案件实体公正的最重要阶段。起诉、审判对实体公正可起到一定的审核、纠错作用,但对其功能不宜高估。一旦侦查阶段事实认定错误,通过起诉和审判程序纠正这种错误将面临很大难度。因而,就实体公正而言,应将侦查作为实现实体公正的重心,尽可能减少侦查结果的错误,而非寄希望于通过审判实质化纠正错误。侦查重心主义强调侦查在保障实体真实方面的重要意义,事实上也会出现审判结果大多数情况下与侦查结果一致的局面,但这不是法官对侦查结果的无奈接受,而是在法官可对侦查活动进行即时性程序性控制、对侦查结果独立判断后对侦查结果的认同。这一点与侦查中心主义完全不同。
(二)为什么应实行“侦查重心主义”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主要针对的是庭审虚化问题,意图通过庭审实质化提升审判的纠错能力。这是有意义的。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此思路高估了庭审在保障实体公正方面的作用。庭审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克服的,即使庭审实质化改革完成时也是如此。这是实行“侦查重心主义”最重要因素。
实行“侦查重心主义”也是对实践理性的承认。“侦查重心主义”虽然是新概念,但其实际上是对司法实践的一种现状描述。且不论我国侦查中心主义之下事实形成以侦查阶段为重心,即使在西方法治国家的审判中心主义诉讼制度下也是如此。从各国实践看,审判中心主义主要体现为审判权对程序正当性的保障作用,包括审判权对审前程序的程序性监控,而在实体形成方面,真正的重心在侦查程序。当然,由于各法治国家中审判权对审前程序,特别是对侦查活动有较强的程序控制权,包括对强制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以及对于权利保护诉求进行判断并实施司法救济的权力,各法治国家刑事诉讼制度仍可称为审判中心主义。但其与传统的将审判视为实体形成关键阶段的审判中心主义概念已然不同。或者说,从侦查结果对案件事实形成的影响看,理想的审判中心主义可能从未真正出现过。而近几十年来程序分流措施在各国的大量适用,则进一步加速了刑事案件事实形成的重心转移趋势。如在德国,由于程序分流,很多案件不再进行审判程序,以及“侦查程序的结果对庭审的影响”,“实际上长期以来,重心已经移向了侦查程序”。*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趋势和冲突领域》,载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第241页。日本的精密司法和案卷的重要作用,也使其刑事案件事实形成的重心在侦查阶段。美国绝大多数案件都通过辩诉交易解决,而交易的基础就是侦查的结果。即使是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侦查结果仍发挥着重要影响,因为作为刑事司法的潜规则,“所有的刑事被告辩护律师、检察官和法官都知道和相信”“几乎所有的刑事被告实际上是有罪的”,“大部分一审法官都明知警察在撒谎还相信他们的证词”。*艾伦·德肖维茨:《最好的辩护》,第11页。侦查结果是否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对审判最终结果起着重要作用。侦查程序也是美国刑事案件事实形成的真正重心。
“侦查重心主义”要求将事实形成的重心放在侦查,这一方面要求司法资源的配置向侦查活动倾斜,避免因资源投入的不足造成取证不足,给接下来的起诉、审判活动留下隐患;另一方面,既然意识到侦查是事实形成的重心,形成错误将难以纠正,基于权力独断易于滥用的一般原理,应防患于未然,在侦查活动中应通过外力的介入提高侦查质量。这为检察官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法官对侦查活动进行程序性控制提供了正当性根据。高质量的侦查将为起诉、审判的顺利进行和防范冤假错案提供扎实的基础。
当前两种改革思路都将实现实体公正重点寄托于审判程序的改革,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诉讼实际。“侦查重心主义”概念是对上述思路误区的矫正,以厘清改革的切入点。“侦查重心主义”首先是一种心理认知,明白侦查是实体公正的关键,审判仅能起到有限的纠错功能。因而,制度上虽不应忽视审判程序改革的重要性,但更应着力于侦查程序的完善,从起点上防止案件事实形成的错误,而不宜将重心放在事后的纠错上。
(三)“侦查重心主义”与“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关系
“侦查重心主义”与“以审判为中心”在促进实体公正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一方面,庭审实质化改革有助于提高法庭查明事实真相的能力,一定程度上纠正侦查阶段的事实误认。另一方面,庭审实质化所要求的一些改革,如非法证据排除、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等,可反射于侦查工作,督促侦查行为合法进行,防范错案发生。
但侦查重心主义认为,基于侦查在事实形成中的关键作用,及侦查权的不当使用造成案件事实错误的可能性,将“以审判为中心”改革局限于庭审实质化,放弃审判权对侦查权的即时性程序控制,仅欲以“倒逼”方式促成侦查质量的提升,是审判权的过分谦抑,也高估了庭审发现真相的能力。“侦查重心主义”要求对“以审判为中心”改革内涵进行扩张,除审判程序自身的改革外,还应由审判权对侦查活动进行程序控制,并对权利保护的诉求进行司法救济。
“侦查重心主义”是扩充内涵后的“以审判为中心”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之平行的概念,更不是像侦查中心主义一样是与之相对立的概念。侦查中心主义不仅是对侦查在案件事实形成中占据核心地位这一事实的描述,还包含侦查机关的强势地位,侦查结果主导诉讼进程,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决定诉讼结果等诉讼关系层面上的因素。而“侦查重心主义”是对刑事案件事实形成过程的客观描述,不包含侦查在诉讼关系中占强势地位的要求。为防止侦查权滥用可能造成事实错误,“侦查重心主义”反而要求更具中立性的审判权对侦查活动进行程序制约。因而,“侦查重心主义”与“以审判中心”改革不冲突,而是要求深化这一改革。
四、“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中如何贯彻“侦查重心主义”
贯彻“侦查重心主义”,就是要将侦查作为实现实体公正的关键阶段来看待,并采取措施提高侦查活动产出正确结果的能力。这主要有三个路径:一是提升侦查人员的取证能力。包括变革侦查方法、提高侦查人员素质等。二是防止侦查人员违法取证。“司法实务中暴露出的许多冤错案件,往往都与侦查阶段的违法取证行为直接相关”。*沈德咏、何艳芳:《论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科学构建》,《法律科学》2012年第2期。因此,遏制违法取证是提升侦查质量的重要环节。三是为还原侦查过程提供可能。侦查过程通常只有控辩双方在场,审判中双方对某些事项发生意见分歧,往往陷入无解的“发誓竞赛”。如能采取措施还原讯问现场情景,将有助于法官准确判断。第一类措施虽然重要,但与“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关联性相对较弱,此处暂不讨论。
(一)“以审判为中心”对侦查行为进行程序控制
从我国近年来已暴露的错案情况看,违法取证根源于对侦查活动的程序制约机制不足。违法侦查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如果能强化程序审查和权利救济,其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被遏制的。这是提升侦查阶段实体公正的关键。
我国当前的强制侦查措施,除逮捕由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都由侦查机关自行掌握(检察机关自侦案件,逮捕也由检察机关自行掌握)。这使侦查合法性的保障主要依赖于侦查机关的自律。利益的一致性使侦查机关内部上下级间的监督常流于形式,其自律监督整体上是不成功的。这在暴露的错案中有明显体现。一种观点认为可由检察机关承担对强制侦查行为的程序控制任务。且不论自侦案件的自我监督问题,即使是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也往往不是合格的监督者。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同为追诉者的身份,使检察官客观义务在多年的实践中多流于纸面。检察官对警察的违法侦查行为通常宽容多于苛责。相对而言,审判权更为中立,由其对强制侦查行为进行程序控制更为适宜。控制方式包括对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和对权利保护诉求的司法救济。同时,由法官对强制侦查进行程序审查,不仅仅是针对实际问题的对策性考虑,更是调整侦查权与审判权关系、完善权利程序保障机制的“战略需要”。*孙长永:《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与司法审查》,《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将压缩违法侦查的时间与空间,减少侦查阶段案件事实出错的可能性。其成效在地方庭审实质化试点中已有体现。如成都地区法院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后,切实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程序,警察出庭作证,倒逼侦查机关取证更加规范。*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成都法院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工作调研报告》,载南英主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3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第200页。这对于提高侦查质量显然有积极意义。
对审判权向审前程序延伸的必要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领导的论述中也有涉及。如沈德咏认为,“以审判为中心”改革的“中景目标,应当是通过深化司法改革,进一步优化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以实现审判对侦查及公诉活动的有效制约”。*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但笔者认为,基于侦查重心主义,为实现改革所追求的实体公正目标,“以审判为中心”对侦查行为进行程序控制和权利救济,应作为近景的现实措施,而非作为理想的中景目标。
(二)以防止虚假供述为主要目标强化辩护人的监督权
非法取证的主要目标是取得口供,已暴露的错案基本都与虚假供述有关,提升侦查阶段实体公正的重中之重是解决虚假供述问题。这方面,司法审查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对控方提出的强制侦查申请进行审查外,司法审查的启动更依赖于辩方的权利救济申请。受犯罪嫌疑人法律素质不足、高羁押率等因素的影响,犯罪嫌疑人行使救济权往往需要律师协助。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程度影响着辩方启动司法审查的能力。
律师侦查阶段介入诉讼,当前还存在不少问题。实践中,一些侦查人员担心律师介入影响侦查效果,以多种方法对律师活动进行限制;与西方法治国家比较,我国立法出于保障侦查有效性的考虑,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也限制颇多。这一方面源于我国将犯罪视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斗争,甚至将律师辩护看作为坏人说话的传统思维。在这种“斗争”思维下,削弱对手无疑是保障胜利的重要方法。作为取证的关键阶段,限制律师介入侦查程序就显得理所当然。另一方面,“平等武装”理论也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难度。这一理论近二十年来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影响广泛,它为提高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但它也是一种“斗争”思维,只不过与我国传统思维方向相反而已。其虽然有助于唤醒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关注,但没有能有效推动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特别是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相关立法。因为它将律师介入侦查视为强化犯罪嫌疑人对抗能力的手段,而以此为出发点设置的辩方权利很可能损害控方的取证能力,典型的如律师讯问在场权。由于我国刑事司法对实体真实的重视,保障侦查有效性被置于优先地位,强化辩方对抗能力的理论见解与实务部门的观点形成尖锐冲突,增加了立法阻力。对抗思维也增加了辩护律师的职业风险,使一些优秀的律师视刑辩为畏途,不愿从事刑辩业务。*这在地方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中仍无显著改观。参见徐建新、任国权、吴程远:《温州法院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工作调研报告》,载南英主编:《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3集,第224页。“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方案再次肯定了实体公正的优先地位,这意味着至少在一定时间内,在侦查程序中强化辩方对抗能力的改革思路将难以落实。
在实现实体公正已成为“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主要目标,并且侦查机关主导侦查的局面短期内难以变动的情况下,律师介入侦查程序更具可行性的制度设计,应立足于监督侦查人员合法行使职权,以防止虚假供述为主,而不是帮助犯罪嫌疑人与侦查人员对抗。对抗与监督二者有重合之处,但侧重点则不同。以律师讯问在场权为例,如果将律师定位于协助犯罪嫌疑人对抗讯问,律师在场可以指导犯罪嫌疑人应对讯问,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心理支持,这一权利是合理的;如果将律师定位于监督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律师可以通过同步录音录像或在其他房间观看讯问过程,而不必在场。二者都可监督侦查人员,防止违法取证,但律师在场将打破侦查的空间封闭性和信息秘密性,强化犯罪嫌疑人的对抗能力,增加侦查人员的取证难度;通过同步录音录像或在其他房间观看讯问过程则仅打破信息秘密性,无损空间封闭性,对取证有效性影响较少。
将律师定位为监督者还是对抗者,对律师参与侦查程序的空间拓展有重要影响。在国家对侦查有效性仍极为关注的情况下,以强化辩方对抗能力为诉求的改革极易遭遇阻力;若以防止虚假口供为目标,以监督者身份定位辩护律师,能更好地平衡防范违法取证与维护侦查有效性的关系,贴合当前司法改革的目标,将有利于化解刑事辩护面临的阻力。
(三)完善侦查录音录像,为还原侦查过程提供可能
司法审查和律师监督可使侦查程序一定程度上公开化,但各国为保证侦查的有效性,侦查秘密进行仍是基本原则。即使法律规定应公开的事项,实践中侦查人员仍有将其秘密化的倾向。如在美国,根据米兰达规则,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可以要求律师在场,但警察“发明了多种规避、限制、架空,有的时候甚至违反米兰达规则及相关判例的策略,米兰达规则对警察审讯的约束微乎其微”。*理查德·A·利奥:《警察审讯与美国刑事司法》,刘方权、朱奎彬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一项实证研究证明,讯问中平均78%的犯罪嫌疑人放弃了米兰达权利的保护。其中无犯罪前科的犯罪嫌疑人放弃的比例更高达92%。*See Richard A. Leo, “Inside The Interrogation Room,” Th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 Criminology, Vol.86, No.2, 1996, p.286.此外,其他原因也可能导致打破侦查秘密性的努力受挫。如犯罪嫌疑人要求律师在场,但一大早进行讯问,律师不愿意到场。*See Wayne T. Westling and Vicki Waye, “Videotaping Police Interrogations: Lessons from Australia,”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Vol.25, No.3, 1998, p.540.在侦查秘密化之下,如果发生违法取证,将难以被发现。有时,事实错误甚至是在侦查人员都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位侦探回忆了口供如何在无意中被污染:“为证明已掌握确实的证据,我们向嫌疑人出示了证据,无意之间透露了一些她不知道的细节,以致于她随后能复述这些信息。”促生了虚假供述。*See Garrett,“The Substance of False Confessions,” p.1075.对这类口供被污染的情形,若控辩双方审判对口供真实性发生争议,往往演变为“发誓”比赛,事实真相难以查明。
这说明,依靠外力介入打破侦查秘密性、保障实体公正有较大的局限性。为解决控辩双方对侦查行为,特别是对口供真实性的争议,一些国家开始对侦查活动,特别是讯问活动进行录音录像。如纽约Bronx地方检察官在1975—1983年间,主动对3000个讯问过程进行了录像,以反驳讯问违反米兰达规则及其他警察违法行为的指控。*See Corey J. Ayling, “Corroborating Confes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Legal Safeguards against False Confessions,” Wisconsin Law Review, Vol.1984, 1984, p.1191.1985年,阿拉斯加州开始要求在重罪案件中对会见和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进行录像。美国司法部最近也改变长期的反对立场,要求FBI和其他联邦执法机构对重罪羁押性讯问进行录像。*Kassin,“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False Confessions,” p.42.2002年,英国立法上正式确立了讯问同步录像制度。*瓮怡洁:《英国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现代法学》2010年第5期。日本2015年通过法案,对部分案件的讯问活动进行录音录像。*马丽:《日本众院法务委通过规定审讯可视化的法案》,《环球时报》2015年8月6日,http:∥tthz.huanqiu.com/viewTouTiao.html?newId=6496533&f,2016年9月10日。讯问录音录像一方面克服了律师某些情况下难以在场,或警察规避律师在场的情形,对侦查活动进行全程记录,形成心理威慑,防范违法取证;另一方面可生动、全面还原侦查过程,有助于法官根据丰富的背景信息,如犯罪嫌疑人的语气、表情、对话过程等,查明事实真相。如上述侦查人员无意中污染口供的案件中,污染行为之所以能被发现,就在于“对讯问进行了录像,从而避免了可怕的错误。这是典型的虚假口供,若无录像,我们将永远也不会意识到这一点”。*See Garrett,“The Substance of False Confessions,” p.1075.讯问录音录像已成为一些国家促进侦查公开、防范错案的重要举措。
在吸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我国立法上正式确立了讯问录音录像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要求,所有职务犯罪案件的讯问都要录音录像。*参见201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公安部要求2017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刑事案件的讯问进行录音录像;*参见2014年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 录音录像工作规定〉的通知》。自2016年7月1日起,对刑事案件的现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辨认、扣留等执法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参见2016年公安部《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在规范意义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刑事执法录音录像范围要求最广的国家。在不允许以律师为代表的外力充分介入侦查过程的情况下,侦查活动录音录像几乎是解决控辩双方“发誓竞赛”的唯一方法。
理论界和立法者都对侦查录音录像寄予很高期望,期待其成为打破侦查封闭性,解决违法取证,特别是刑事逼供问题,查明事实真相,挽救刑事司法公信力的有力工具,但从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实践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异化为侦查机关掩盖刑讯逼供的巧妙手段”。*参见毛立新:《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缘何异化?》,《财经》2014年第14期。讯问录音录像当前的信誉危机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源于其从制作至使用,都缺乏外部监督,很大程度上沦为侦查机关自娱自乐的工具,缺乏公信力。
要真正发挥侦查录音录像保障实体公正的功能,应确立录音录像资料的证据地位,建立录音录像资料随案移送制度,由法院审查录制是否完整、真实,并确立录音录像资料缺失、不完整时不利于控方的推定规则。其中不利推定规则最为重要。英国、澳大利亚的警察发现,在心理学讯问方法不变的情况下,讯问录音录像没有改变讯问过程的权力关系,警察仍然可以操纵讯问过程,不会影响讯问的有效性。*See Tracey Green, “The Future of Investigative Interviewing: Lessons for Australia,” Australian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Vol.44, No.1, 2012, p.33.这一点对我国侦查录音录像制度有重要启发意义。它意味着,如果不以违法方式执法,录音录像基本不会影响侦查的有效性。此种情况下,若一些侦查人员仍规避录音录像,可以反推侦查行为违法的可能性极大。结合我国错案与违法行为之间的纠葛关系,此时案件事实错误的可能性较高,应排除相关证据。这种“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安排可克服当前录音录像制度的不足,将“侦查重心主义”与“以审判为中心”二者协调统一。
(责任编辑:魏 萍)
Taking Investigation as the Focus of Fact-finding in the Lawsuit System Reform Centered on Trial
Qin Zongwen
Promoting the substantiation of court hearing is the main content of lawsuit system reform centered on trial. However, the substantiation of court hearing can only help filter misjudged cases unilaterally. Evidence integration strengthens the possibility of “guilt” conviction in lawsuit procedures, and court hearing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factors of judges. Besides, substantiated court hearing can only be applied in very few cases, thus playing a limited role in ensuring substantive justice, which is proved by the fact that many misjudged cases have been produced in the adversary criminal trials of common law system. Both of the current two representative views of the reform fail to recognize this limitation. To promote substantive justice, we should take investigation as the focus of fact-finding,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aking investigation as the center of lawsuit procedures, and thus it can be adopted to promote the current reform. Taking investigation as the focus of fact-finding, we need to control investigation in the judicial procedure, to strengthen defender's right of supervision over the use of false confession, and to use audio-video recording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gation,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to revivify the investigation process.
trial-centered, substantiation of court hearing, centralism of investigation, investigation, judicial reform
秦宗文,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南京 210093)
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隐蔽性证据虚假补强问题研究”(15BFX096)
DF718
A
1006-0766(2017)03-0141-12
§人权保障与司法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