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法家艺术观简议
孔 涛
(淄博市博物馆, 山东 淄博 255000)
《韩非子》的法家艺术观简议
孔 涛
(淄博市博物馆, 山东 淄博 255000)
《韩非子》虽然对艺术总体上有否定倾向,但他对艺术理论的诸多方面均有所涉及。在艺术发生论、艺术本体论、艺术认识论和创作论、艺术功能论以及审美标准上分别主张“模仿说”、 重质主义、先实后虚说、实用主义和等级主义以及客观主义。尽管它的艺术观深受道家影响,但与老、庄差别很大,其法家式的极端主义特征仍然非常突出,其中某些观念具有积极进步的一面,而更多的则是消极的。
艺术发生论;本体论;创作论;功能论;审美标准
《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虽然对文艺总体上持否定态度,但它对艺术的起源、本质、创作与鉴赏、审美标准、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虽然这些观点绝大多数都是作为论证其法家理论的论据而存在,但从中仍可以窥得法家艺术观的极端主义特征。《韩非子》主要以黄老之学为哲学基础,因此它的艺术观带有相当浓厚的道家色彩,但二者又有很大不同。下面分别对《韩非子》在艺术发生论、本体论、创作论、功能论、审美标准等方面的思想观点逐次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艺术发生论上的“模仿说”
《韩非子》的艺术发生论属于“模仿说”,认为艺术起源于对自然物形体的模仿。《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
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1]270
画犬马最难,鬼魅最易,依据就是绘画对象有没有可为人所认识和把握的客观形体的存在,因此把这段话理解为对形似的追求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这段话之所以这样表述,是因为韩非常用的那种极而言之的逻辑论证方法。他未必没有认识到“犬马”并非最难,人的表情、动作、形体最为复杂,岂不明显比“犬马”更难?“犬马”和“鬼魅”作为事物的两个极端,在普通人眼里,一个低等、一个高等,但画起来却是低等的难,高等的易。韩非子正是通过这样鲜明的反差和对比,来隐喻“法”的客观性、有效性及可依赖性。
从形神关系的角度上看,韩非的“模仿说”还仅停留在对艺术对象的外在形态的模仿上,他虽然多次论及“神”这一概念,但取的都是鬼神、精力、智识义,都不是从形与神的内在辩证关系着眼的。这是他始终关注政治的外向型思想取向决定的。这一点上《韩非子》与《庄子》迥然有别。虽然《庄子》也否定文艺,认为“擢乱六律,铄绝竿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庄子·胠箧》)[2]45,但它否定文艺的原因在于文艺妨碍了人的“聪”和“明”,破坏了人内在精神的自然天真和自由完满。精神和心灵的绝对自由成了《庄子》的终极价值追求,《庄子》由此完成了道家的内向转化,反而表现出极为浓厚的文艺美学特征。这种内向转化反映在形与神的关系上,就是重神轻形。《庄子·知北游》:“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就指出“神”是比“形”更为根本的东西。《庄子》还赞美过很多形残而神全的人物,如形若槁木的南郭子綦、受过刖刑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相貌奇丑的哀骀它等等,也都印证了这一美学主张。《韩非子》的形神论虽然没有达到那样的理论高度,但它追求形似的“模仿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反映着战国晚期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因而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考古发现来看,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的《仕女龙凤帛画》和1973年5月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人物御龙帛画》是目前所见最有代表性的两幅战国晚期帛画,二者都属引导墓主人升天成仙的旌幡,其画面具有浓厚的图式象征意义。《仕女龙凤帛画》造型简劲爽利,以勾线和色彩平涂为造型方法,凤鸟引颈张喙,做向前飞扑状;夔龙取大蛇状,形象较为逼真,身上装饰着环状纹路,双足张举,作蜿蜒升腾状;仕女取侧面剪影,发髻盘脑后,双手合掌,身着凤纹宽袖细腰长袍,形体比例精当,但人物面部刻划较为粗略,图案装饰意味很强。《人物御龙帛画》上画一有须男子,侧身佩剑,手执缰绳,驾驭着一条船形巨龙。男子形象与《仕女龙凤帛画》中的仕女相比,虽同为侧影,但脸部器官比例更为准确,也更为鲜活有生气。尤其龙尾上部站着的一只鹭鸟,圆目长喙,意态悠闲,栩栩如生,左下角的鲤鱼造型逼真精确,似有游动之意。不仅如此,线条的轻重刚柔变化更为多样,设色也更为丰富,在单线勾勒后,平涂与渲染并用,其中一些地方还加用了金、白粉,可以看到当时绘画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3]42-61。
这两幅帛画在表现真实存在的动物时,形象都显得更为生动传神,虽然图案装饰性、图式象征性的成分还很浓重,但刻画内容开始从龙凤、神兽这些虚拟的物象转向客观存在的物象如蛇、白鹭、鱼等。韩非子“犬马最难、鬼魅最易”的“模仿说”是战国时期艺术思维开始由图式象征转向客观写实这一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反映了战国晚期艺术逐步摆脱当时仍然盛行的巫术思维的影响而独立发展的时代需要,体现了人文理性精神在艺术领域中的逐步成熟和扩张。
二、艺术本体论上的重质主义、艺术认识论上的先实后虚说
艺术本体论揭示艺术的本源、本质和意义,对艺术认识论和创作论以及艺术形式的选择起着支配性作用。文质关系是中国艺术本体论的重要内容,《韩非子》继承了《老子》的重质轻文、抱朴守拙等思想观念,在艺术本体论上主张重质主义,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推崇素朴无文。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在韩非看来,美质不饰,饰质不美,“和氏之璧”和“隋侯之珠是“质至美”者,它们无须“饰”,“质”完全可以独立于“文”而存在,“文”则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韩非关于文质关系的这种极端论调是与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4]176一脉相承的。韩非的重质主义,是他实用主义的学说特色在艺术观上的反映。这一点将在后文详述。《韩非子·扬权》:
谨修所事,待命于天,毋失其要,乃为圣人。……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参鞠之,终则有始。虚以静后,未尝用己。
《韩非子》的这段话,虽是谈圣人之道和治国方略的,但同样适用于艺术认识论和创作论。圣人、君主应“谨修所事”,为更好地履行职事,必须“待命于天”“毋失其要”,即必须把握天道规律和要点。“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参鞠之,终则有始”意思是做事应该宏观上顺应自然的普遍规律,微观上探析事物的具体道理,深入观察,交互验证,寻根究底,终而复始。这段话是讲“有为”,讲实践功夫的。等到真正具备了“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的能力后,“虚以静后,未尝用己”,即抱虚守静,与道合一,动辄就能与“道”与“理”若合符节,就可以避免经常为不成熟、不可靠的主观看法所左右、所干扰的处境。这个“未尝用己”绝不是否定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认知精神,而是说通过不断认识、不断实践,最终把握住真理,实现对个人主观意识的不确定性、有限性的超越,从而无所不能。这是讲“无为”,讲虚静的,而这种“无为”根本目的是为了“无不为”。
从这段话看,《韩非子》虽然在艺术本体论上与《老子》同样重质轻文,但它的认识论充满着辩证的、积极能动的认知精神,与《老子》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那种消极不作为的认识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韩非子》先实后虚的艺术认识论和创作论。艺术家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门类,对所再现或表现的艺术对象,首先应“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参鞠之,终则有始”,经过不断由感性认识升进成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归到感性认识的辩证循环,这样一来,艺术认知、艺术技法和艺术境界就会日臻完善。在此基础上,返璞归真,抱虚守静,“未尝用己”却能动辄合道,艺术之美便在艺术家手下如行云流水般自然流淌而出。这里的“未尝用己”看起来似乎完全抹杀了艺术个性,其实是对个体艺术认知的幼稚肤浅的超越。而且,从逻辑上说,既然《韩非子》承认个体的认知能动性,他再怎么强调“法”的整齐划一,也不可能完全抹杀个体的个性差异,相反,他积极的辩证认知精神,反倒为艺术的存在留下了较大的空间,至少跟《老子》相比是如此。
三、艺术功能论上的实用主义和等级主义
审美功能是艺术赖以存在的核心功能,《韩非子》曾多次将君王痴迷艺术,耽于声色作为反面教材来立论,这说明他是认同艺术的审美功能的,只是他认为君王应该将对艺术的审美享受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以免陷入众叛亲离、人亡政息的境地。《韩非子》主张变革除弊、反对因循复古,宣扬君主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因此他的艺术功能论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和等级主义色彩。
宋王与齐仇也,筑武宫,讴癸倡,行者止观,筑者不倦。……王召射稽使之讴,行者不止,筑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筑者知倦,其讴不胜如癸美,何也?”对曰:“王试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坚,癸五寸,射稽二寸。(《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客有为筴周君画荚者,三年而成。……画荚者曰:“筑十版之墙,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周君为之,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周君大悦。此荚之功非不微难也,然其用与素髹荚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故不乘天地之资,而载一人之身,不随道理之数,而学一人之智,此皆一叶之行也。(《韩非子·喻老》)
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以上是《韩非子》借艺立论的例子。实用主义的艺术功能论是他唯质主义的艺术本体论决定的。韩非反对以文害用,反对华而不实,主张以艺术的实用功能作为衡量艺术高下的尺度。
虽然在行者、筑者甚至宋王看来,讴癸的老师射稽唱得不如讴癸好听,但讴癸之所以认为其师唱得比他好,是因为听老师唱歌的人所筑的宫墙更厚、更坚硬。为周君画荚者虽然画得“尽成龙蛇禽兽车马,万物状备具”,艺术水准不可谓不高,但画得再好,用途却与光素无文的髹筴相同,并无任何实用价值。宋人雕刻楮叶,虽然巧夺天工,几可乱真,但三年才成,楮树一年长出的楮叶,何止亿万?浪费了如此多的时间不说,还没有任何用处,君主却被蛊惑得忘记了“天地之资”和“道理之数”,不唯无用,甚至有罪了。买椟还珠这一寓言则比喻人们往往为外在的浮文丽辞所迷惑,坠入舍本逐末的境地而不自知的可笑,进而说明以文害用的现实危害性。
在这些例子中,除第一例承认歌唱艺术的实用价值外,其他似乎都有否定艺术存在之价值的思想倾向。其实解读《韩非子》的艺术观念,不能望文生义,他对画荚者、 为楮叶者、买椟还珠者的看法仅是一种比喻性的论证方法,目的是为了使他的重质轻文、重内容轻形式的结论更形象生动,不能因此就认定韩非是个彻底的唯质论者、反艺术论者。《韩非子》虽是哲学著作,词锋犀利,逻辑严密,同时又文采斐然,气势如虹,尤擅用形象化的寓言故事、历史掌故或传说将抽象的道理说得引人入胜,是先秦散文的重要代表之一。这本身就说明了韩非对文质关系的真实看法,他的重质轻文的实用主义态度其实是对当时重文轻质、“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社会现实的矫枉过正。
除实用主义外,《韩非子》出于维护和强化君权的需要,认同并接受了周礼正名分、明等级的作用,主张等级主义的艺术功能论,认为艺术在现实性和象征性上都不能逾越贵贱有别的身份等级和社会地位,否则就动摇了艺术存在的基础。
孔子侍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之闻也,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赵简子谓左右: “车席泰美。夫冠虽贱,头必戴之;屦虽贵,足必履之。今车席如此,大美,吾将何屩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义之本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齐宣王问匡倩曰:“儒者博乎?”……对曰:“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弋者从下害于上者也,是从下伤君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弋。”……夫瑟以小弦为大声,以大弦为小声,是大小易序,贵贱易位,儒者以为害义,故不鼓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韩非竭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立场不唯与儒家一致,甚至远比儒家极端。这三段话虽是借孔子或儒者之口说的,但其实是韩非为了立论的需要自己编造或演绎的历史传说。孔子之所以先吃了鲁哀公赏给他擦桃子的黍子,是因为黍子是五谷之首,是祭祀先王的上等祭品,而桃子是瓜果中最下等的,贵贱悬殊,所以不敢先吃桃子,否则就违背礼义。同样地,帽子虽贱,一定要戴在头上;鞋子虽贵,一定是踩在脚下。如果车上铺的席子过分地华美,那该用什么鞋子踩在上面呢?“美下而耗上”,同样有违道义。至于匡倩所说的儒者不博戏、不射鸟、不弹瑟,原因在于博戏必定要杀掉尊贵的枭,象征以贱害贵,射鸟以下射上,象征臣下伤害君主,弹瑟小弦发大声,大弦发小声,象征大小贵贱易位,虽有牵强附会之嫌,但也充分说明,《韩非子》所主张的艺术功能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审视的,这种艺术功能论极力维护君权至上的封建等级主义,本身就是实用主义的体现。
除此之外,从艺术他律的角度上看,《韩非子》艺术功能论上的等级主义还体现在君主对审美评判权的绝对控制与支配上。
上下清浊,不以耳断而决于乐正,则瞽工轻君而重于乐正矣。治国是非,不以术断而决于宠人,则臣下轻君而重于宠人矣。人主不亲观听,而制断在下,托食于国者也。(《韩非子·八说》)
田连、成窍,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连鼓上,成窍擫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人主安能与其臣共权以为治?以田连、成窍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与其臣共势以成功乎?(《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韩非子》认为君权凌驾于专业权威之上,乐曲的高下清浊,最终评判权掌握在君王而不是专业的乐正的手里,如若不然,奏乐的盲人们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乐官。治国的是非得失,如果取决于宠臣,臣下就会轻视君主而尊重宠臣。所以,君与臣难以“共权”“共势”,就像田连、成窍这样高明的乐手也不能共用一琴而成曲一样。为避免君权旁落,君主必须亲操权柄,以“术”来判断事物的是非曲直。艺术审美由此纳入了君主的“势”和“术”的作用范围。
“势”“法”“术”是《韩非子》学说的核心。“势”指君主拥有的威慑和支配臣民的无上权力,分“自然之势”和“所得而设之势”两种,前者是君主自然天授的权力,后者指君主用智慧人为营构的威权,韩非的学说侧重后者。为实现“所得而设之势”,必须用“术”,即君主统御和威慑臣下的方法。用“术”的要诀在于虚静无为,深藏不露,让臣下难以捉摸,无从钻营从而畏君守法。在韩非看来,艺术同样如此。艺术作品的清浊、高下、优劣、美丑等审美标准并不理所应当地取决于艺术自身,而更多地取决于外在的君权,不同的时间、场合、心境,君主对艺术的品鉴结果也会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这样一来,艺人们便不能出于草率应付或迎合谄媚的目的去创作或表演,只能恪守既有的艺术规则和标准(即艺术之“法”)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四、审美标准上的客观主义
从艺术自律的角度上看,《韩非子》也涉及到了艺术自身的审美标准问题。其实,不论是《韩非子》的“模仿说”、重质主义还是先实后虚论及实用主义,都表现出了以实体存在为逻辑起点、以客观主义为哲学根基的思想特色。《韩非子》的艺术审美标准同样如此。
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议言之士,计会规矩也。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故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则事无不事,功无不功。(《韩非子·解老》)
既然“万物莫不有规矩”,“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那么,符合“规矩”与否、符合“规矩”的程度也就成了艺术自身的审美标准,而这个规矩的本质就是“理”,也就是事物固有的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等客观物理属性。韩非子的“模仿说”正是以再现艺术对象为最终目的,他的审美标准必然是以客观主义为指归的。
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使人视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故以詹子之察,苦心伤神,而后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韩非子·解老》)
实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释法而任慧者,则受事者安得其务?(《韩非子·制分》)
在《韩非子》看来,詹子虽然成功地预测了门外的黑牛用白布包着角,但这种主观判断因为没有任何依据,预测对了也纯属侥幸,除了苦心伤神外,并无丝毫实用价值,还不如让一个孩童去门口眼见为实来得可靠,因此是最愚蠢的行为。《韩非子》所反对的,是指“先物行先理动”的“前识”即没有实在依据的主观臆断,而并非人的主观能动性本身,他认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建立在业已显现的客观依据之上。同理,艺术创作也不能凭空臆想,这和他的“画鬼最易”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二段话虽是讲依法为政的,但同样可以说明《韩非子》对主观主义的拒斥和对客观主义的坚守。人的贤愚有别,主观看法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标准,处理政务如果“释法而任慧”,舍弃客观标准,全凭主观好恶,必然会导致混乱。
综上所述,《韩非子》的法家艺术观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以艺术发生论上的“模仿说”、艺术认识论和创作论上的先实后虚论、审美标准上的客观主义为代表,表现出很强的辩证理性精神,有利于艺术摆脱巫术思维的影响而依照自身的规律独立发展;但更多的是消极的一面,以艺术本体论上的重质主义、艺术功能论上的实用主义和等级主义为代表,这些主张又在很大程度上钳制了艺术想象的翅膀,使艺术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君权的奴婢,这是由《韩非子》的法家本色所决定的。
[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王先谦.庄子集解[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3]穆益林.中国帛画[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
[4]冯达甫.老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张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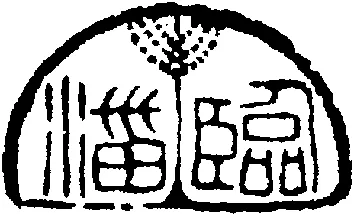
2016-10-19
孔涛(1971—),山东曲阜人,山东大学专门史专业博士,现就职于淄博市博物馆,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艺术史论。
B226.5
A
1002-3828(2017)01-0062-05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7.0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