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致胜逻辑与文化根基
姚振文
(滨州学院 孙子研究院,山东 滨州 256603)
齐兵学与古代军事文化
《孙子兵法》的致胜逻辑与文化根基
姚振文
(滨州学院 孙子研究院,山东 滨州 256603)
《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兵学著作,奠基于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从实用理性、用知求变、辩证法则、守度持中、悟性思维、道胜境界等六个方面,归纳出孙子兵法指导战争的致胜逻辑,以便于人们能够准确地把握《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更好地发挥《孙子兵法》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和价值。
孙子兵法;致胜逻辑;文化根基
《孙子兵法》是研究战争制胜规律的学说,具有完整的理论思想体系,而这种理论思想体系本身蕴含了一种内在的战争致胜逻辑。对此,前人已做过很多研究,相关结论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笔者看来,《孙子兵法》的致胜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及主要特点是密切相关的,它所反映的是农耕文明基础上中华民族对待生存和竞争问题所表现出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理念。因此,研究《孙子兵法》的致胜逻辑应该充分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特点去发掘和讨论。以下从六个方面,想谈谈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一、“实用理性”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 在古代,“祀”的活动主要体现的是宗教信仰理念,而“戎”的活动则更多培育了理性精神。因为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激烈程度的提高,人们基于对战争残酷性和战争破坏力的深刻体认,不断对战争活动和战争行为进行反思和总结,从而使得注重现实和关注功利的实用理性精神得以突出表现。《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兵学文化的经典之作,其指导战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实用理性”,这种“实用理性”原则可以说是整个《孙子兵法》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
首先,孙子主张理性用兵。他在《计篇》开头即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要求人们站在国家兴亡和民众生死的高度来理性认识和对待战争。其在《火攻篇》又谈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这是从克服人类本性好名、贪婪的弱点出发,要求君主和将帅立足于客观实际进行理性决策。在十三篇其他内容中,这种理性之言与警示之语,也处处可见。如《作战篇》认为:“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军争篇》亦言:“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九变篇》则谈到:“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总之,“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哀憎和任何观念上的鬼神天意来替代或影响理知的判断和谋划”[1]41-52。
另一方面,孙子以追求战争的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宗旨,极力追求用兵中的实用与实效。他主张善战、易胜和全胜,其目的就是为了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而由此产生的对将帅的最高要求则是:“故善战者之胜也,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孙子兵法·形篇》,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在孙子看来,衡量一位将帅的功绩,不仅要看他是否战胜了敌人,更要看他取胜的方法是否高明,看他是否是在最省力的时候和最省力的条件下战胜了对手。正如《谋攻篇》所讲:“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概而言之,孙子是“利本主义”者,“利”是孙子兵学思想暗含的一条主线。
孙子“实用理性”的战争指导原则,一方面是出于战争实践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注重现实生活的民族,其群体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内容即表现为对现实利益的过度关注,它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气质性格、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并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种“实用理性”精神在中国先秦时期主要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中都有体现。道家学派的老子为中国古代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其关心的重点依然是“君人南面之术”,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五十七章)儒家学派也强调学以致用,非常关注现实的价值。比如,孔子对于生死与鬼神的态度就是:“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在这里,对于生死,孔子关心的是今生而不是来世,是此岸而非彼岸;对于鬼神,则是既“敬之”又“远之”,既不否定也不肯定。这些话语所表现出的都是一种非常理性的现实主义的态度。
二、用知求变
既然以“实用理性”为基本原则,孙子在研究战争的过程中就非常重视“知”,同时又特别强调“变”,其目的是为了将战争认知和战争行动建立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使己方的战略战术方法更能做到实际、实用和实效。
“知”是孙子兵学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孙子对于“知”的论述和研究是对中国兵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杰出贡献。其一,他第一次将古代人们停留在初级经验阶段的关于“知”的认识上升到理论层次,提醒人们注重信息情报的重要性,促使人们在“知”的运用过程中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感性阶段过渡到理性阶段。其二,他最终构建出一个丰富而完整的关于“知”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一体系既包括有关“知”的各方面的具体内容,如“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知常知变、尽知全知”等,又包括有关“知”的各种具体方法与途径,如“庙算分析、相敌、用间、战略试探”等。其三,孙子还从知行统一的基本原理出发,将“知”的问题上升到了唯物论的高度。如孙子在《地形篇》中谈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在这句话中,“知”是“胜”的前提,“胜”是“知”的目的,这无疑是立足于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以把握“知”的作用和价值,并由此实现了战争认识论与战争实践论的高度统一。
在强调“知”的同时,孙子又非常重视“变”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变”也是孙子兵学思想体系的一个核心内容,整个《孙子兵法》可以说就是一部用变与处变的学说。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十三篇”,就会发现它几乎每篇都讲“变”,几乎处处都讲“变”,而且是从不同的角度予以阐发。比如:《计篇》所言“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是强调要根据自身的优势而变;《势篇》所言“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是强调依据常规和非常规的辩证关系而变;《虚实篇》所言“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是强调要根据对手的反应而变;《九变篇》所言“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是强调要突破思维的定势和惯性而变;《虚实篇》所言“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是强调变化的创新性、连续性和无限性;《九地篇》所言“践墨随敌,以决胜负”是强调在变化中坚持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孙子“重变”的思想内容及“用变”的思想方法,大多是依据战争活力对抗的基本特点而论,因时而变,因地而变,更重要的是因战争双方指挥者的心理变化和互动博弈而变,毕竟人的智力活动和思维活动是最难揣摩和判定的。
战争中的“用知”“求变”自然是战争指导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规律,但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兵学和兵家重视这一问题,又是基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相比较,中国人是一个更注重知行合一和灵活变通的民族。例如,《周易》的“易”字,本身就包含有变化的意思。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易·系辞上》),所谓“介于石,不终日”(《易·豫卦》),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系辞下》),这些内容都是强调了“变”的重要性,由此也演绎出儒家的变易思想。而就道家思想而言,它所推崇和重视的“变”是基于其对宇宙世界变化规律的独特认识而言的。“中国道家哲学强调一切事物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不一定有预定的答案。答案和意义形成于千变万化的互动关系和不确定的无穷可能性之中。”[2]
三、辩证法则
用兵打仗讲求“知”与“变”,但“知”并不是直接的表面的“知”,“变”也不是毫无规律、杂乱无章、随心所欲的“变”,这二者都要建立在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之上。
从“知”的角度讲,孙子“知胜”思想体现了深刻的辩证哲理。在孙子看来,战争双方是对立的但又是不可分离的矛盾共同体。知胜既要了解自己,也要了解对方。孙子讲:“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谋攻篇》)孙子还谈到:“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 (《地形篇》)从现代军事理论角度讲,信息本身就是充满了对抗性的领域,任何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首先是围绕着“知”的对抗。如果一方在制定战略目标和计划时,能够打破信息与认知的平衡,使其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就奠定了其在战争中取胜的基础。
从“变”的角度讲,孙子的用兵思想更建立在辩证法原理的基础之上。孙子重“变”,但其“变胜”思想的核心和精华则在于对“攻守、虚实、迂直、奇正、专分”等兵学范畴的活用。为了达到出人意料的最高目的,孙子将这一系列的古代兵学范畴转化为具体战争指导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进而成为种种达成致胜目的的用兵艺术手段。之所以能“攻而必取”,是因为“攻其所不守也”;之所以能“进而不可御”,是因为“冲其虚也”;敌人判断我应抄近直之路,我却偏要走迂回之途;敌人判断我会出奇兵,我却偏要用正兵。总之,正是因为主要的谋略和用变都是依据了辩证原理,才能做到取胜方法之“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才能使指挥者在战争中“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地形篇》)。可以说,整个《孙子兵法》思想内容中活的灵魂就是这种辩证哲学。
孙子用兵对辩证哲理的应用也与中国古代早熟的辩证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形成了辩证地认识和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如《易·系辞上》记载“一阴一阳之谓道”,也就是说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整个世界的形成,便是阴阳二性相互作用又相互渗透的结果。这种辩证思想的产生又是源于农耕文明的客观需求,农业生产需要顺应天时,人们为此十分注意观察太阳、月亮运行及四季交替的自然规律,“寒来则暑往,暑往则寒来”(《系辞传》下)、“日盈则昃,月盈则食”(《丰卦·彖辞》),不断对这些规律进行观察、认识和总结,进而推动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成熟和完善。
四、守度持中
辩证法则在战争中的运用,其关键之处又表现为指挥者对战争活动转化过程中“节”与“度”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战争活动本身是有规律的,战争中的节奏与行动发展到一定条件下,总是会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因此,对于战争指挥者来说,很重要的一点便是把握“度”的问题,即随时随地观察和分析形势,时刻掌握战争中各项活动变化的临界点,不断调整谋略计划的实施时点和范围,做到收放自如,攻守兼备,正所谓“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军争篇》)。
《孙子兵法》中没有出现“守度”这个词,但其许多兵学思想却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基本精神。比如,《孙子兵法》中最受推崇的“全胜”思想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守度的把握。战争是实力的角逐和暴力的运用,然而如果将实力和暴力运用到极端,就会增大战争带来的损失和灾难,最终造成“杀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残胜”局面,这是明智的战争指挥者所不愿看到的。而孙子提倡“全胜”实际上就是在实力和暴力的运用上依据守度原则进行战争控制,既要展示实力和运用实力,又要对实力的运用把握好分寸,如此既能达到战争的预期目的,又能最大限度避免战争带来的巨大危害。
孙子在《九变篇》中曾总结有“将有五危”的基本理论:“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在这段话中,“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等内容,都是将帅对某些战争问题处理极端化的表现,相应的分寸和尺度没有把握好,于是成为将帅性格的缺陷,在实践中可能会带来“覆军杀将”的严重后果。
孙子在《军争篇》中还总结了“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三个基本的用兵原则。敌人撤兵不能拦截,包围敌军却留下缺口,敌人陷于困境而不猛攻,这些内容在常人看来都不能理解,似乎都违背了战争的基本常识。事实上,这些都是孙子在指导战争方面把握“守度”原则的体现。人都有求生的本能欲望,如果把敌人的生路都断绝,他们就会拼死作战、孤注一掷,这必然使我方付出更大的兵力消耗和资源损失。所以,孙子极力主张不要把敌人逼到此种极端状态上,进攻行动要有张有弛,有急有缓,避免眼前的胜利在极端的情况下走向反面。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就是“守度”和“持中”。“度”的核心是一个“中”字,它寓意为人的行为的最佳方式及事物存在的最佳结构和最佳状态。冯友兰在解释《易经》时曾谈到:“事物若要臻于完善,若要保住完善状态,它的运行就必须在恰当的地位,恰当的限度,恰当的时间。《易》的卦辞、爻辞,把这种恰当叫做‘正’、‘中’。”[3]202追求和谐、守度持中、顺其自然、恰到好处,这可以说是浸透中国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指导世人不要太趋向和执着于某一端,做人做事充分留有余地,不偏不倚,适中得当。正如孔子所言:“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五、悟性思维
在战争实践中“守度”,在用兵过程中“持中”,往往很难通过具体量化的方式把握某一事物的最佳尺度,而是需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根本性质和特点,这就需要一种悟性思维来实现。
战争的对抗性和多变性,使得孙子论兵非常注重这种悟性思维。在战略决策方面,孙子主张“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计篇》)一个“索”字,体现了孙子对战略决策和判断的深刻认识和精准把握。它要求战略统帅不能单纯凭靠自身已有的知识、经验或者对眼前情报材料的直接认知去分析战争形势,而是要将自己头脑中的原有经验与现实的情报信息融汇在一起,调动各种心理因素,将整个身心投入其中,进而全方位地对战略环境进行悟知、谋划和构想,最终达到所谓“以近视远,以一知万”(《荀子·解蔽》)的战略理想境界。
在情报信息搜集和处理方面,孙子主张:“非圣不能用间,非仁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用间篇》)何谓“微妙”?“微妙”就是敏锐的直觉和悟性,它是一种智能和灵性的发挥过程,能够对情报信息形成强大的穿透力,能够透过复杂的表象直击战争事物的本质,进而预测战争活动未来的发展趋向,并及时捕捉战场上转瞬即逝的作战良机。同时,悟性思维又具有模糊性特征,它不能构成清晰的具象思维或完全的抽象思维,而是一种若明若暗、若隐若现、变幻飘忽的相对虚化形态。所以,孙子才讲“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
值得强调的是,《孙子兵法》中有一句名言,叫“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计篇》)。为什么说不可先传呢?因为每一个战场的构成都涉及太多的因素和变化,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故而兵家制胜的诀窍,不能通过照搬兵书中已有的理论去得到,一切都要靠将帅在实践中去感悟。楚汉战争时期的韩信是战争天才,他指挥每一个战役,都能凭自己的悟性恰到好处地将战场上天、地、人及各方面的因素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最终形成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西汉名将霍去病并没有读过兵书,但却能够“暗与孙、吴通”,不断创造出新的战法,将兵法谋略运用的淋漓尽致。宋朝岳飞是一代名将,他对古代阵法和兵法的理解是:“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太平天国的杨秀清,识字无多,但却能在战争中玩转“乘隙蹈虚”式的战略艺术。欧洲历史上的拿破仑没有写过兵书,但他对战争硝烟有着敏锐的嗅觉,迅速扑捉战场上的作战机会,迅速集中和分散兵力,是他指挥作战的最大特点。总之,战争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在运用兵学理论时,必须要做到“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而这势必要求通过一种弹性的心灵和高度的悟性才能实现。
孙子论兵的这种悟性思维方式与中华民族农耕文明基础上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关。农民从事农耕的活动比较现实和有规律,有春耕就有秋收,有秋收就有收获,“天上的仙鹤比不上手中的麻雀”,因而他们的认知更注重实际和应用,同时也十分强调自身的直接感悟与体验。与此相对应,中国传统哲学重整体、重宏观、重感悟,其对真理的发现也是一种直接把握或觉悟,非语言所能表达和交流,“道”不可言,只能暗示。这在儒家的“格致”、道家的“玄览”及中国佛家的“了悟”等理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六、道胜境界
辩证思维基础上的守度持中与悟性思维达到极致足以使孙子的兵学思想进入“道”的境界。
什么是“道”?《孙子兵法》的直接解释是:“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计篇》)在这里,“道”乃是指政治因素,意在强调民众和民心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然而在笔者看来,《孙子兵法》中还有更深层次的“道”的内涵,那就是“战争规律”。
《孙子兵法》作为兵学圣典,研究的就是战争制胜的基本规律。一方面,孙子在创立一系列的兵学范畴和原则的前提下,注重信息情报的运用,强调“五事七计”的科学性,将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认知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之上。进而从表象到本质,从暂时到长远,从局部到整体,深刻地揭示出战争过程的基本轨迹,构建了中国兵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有专家指出:“《孙子》一书建立的许多古典军事学的概念和范畴,不仅是对中国古典军事学的一种科学化和完善化,而且还使我们从这些概念范畴体系之间的普遍联系中,看到了战争制胜的最一般规律。如《孙子》中的彼己、虚实、强弱、形势、奇正、分合、知与不知等,都是用来揭示战争制胜的普遍规律的。”[4]
另一方面,孙子注重兵学思想的灵活变通,强调“兵者诡道”原则之下的奇正相生、虚实相依、专分相变,进而“因形任势”如“率然之蛇”,而其最终的目的则在于探索战争和战略指导的至高境界。《势篇》中讲:“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虚实篇》谈到:“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九地篇》中又说:“率然者,恒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九地篇》)等等。这些内容都是孙子领悟战略战术奥秘的艺术境界,也是他力求把握战争规律的突出表现。
道胜境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古代圣人先贤做人做事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道”的本义是“道路”,后来,中国古代思想家将其提升至哲理的高度,并引申出本体、规律和道德等方面的涵义。作为“规律”的“道”而言,要求人们依乎天理,顺应天时,思想和行为都与自然规律合拍,最终趋向“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易·乾·文言》载:“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庄子·说剑》对“天子之剑”的论述也是这样一种“道胜”境界:“天子之剑,以燕溪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魏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夹;包以四夷,裹以四时;绕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另外,作为道胜思想的实施主体而言,则是需要大智慧之人,他要做到总揽全局、把握大势、且通权达变、举重若轻,最终能够游刃有余地战胜自己的对手。
[1]李泽厚.孙、老、韩合说[J].哲学研究,1984,(4).
[2]乐黛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重构 [J].文史哲,2008,(3).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4]陈学凯.论《孙子兵法》对古典军事学的贡献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4).
(责任编辑:王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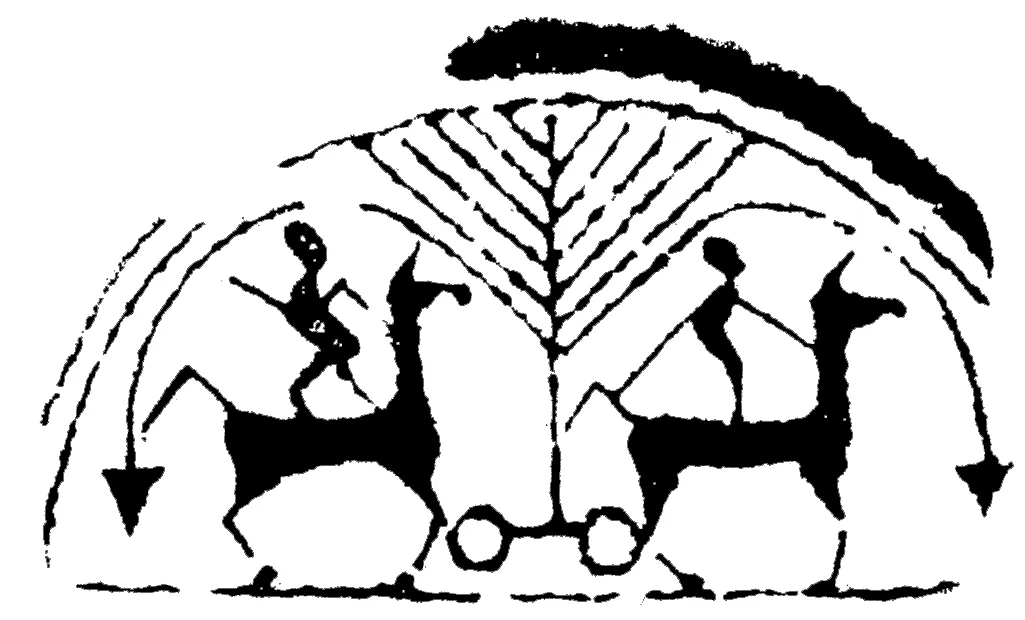
2016-07-2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中国古代兵儒关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立项号:15CLSJ03;滨州学院重大招标课题“孙子兵学与儒家思想的冲突与融合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立项号:2013ZDW01。
姚振文(1966—),男,山东邹平人,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先秦史及孙子兵法研究。
E892
A
1002-3828(2017)01-0041-05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10.19321/j.cnki.gzxk.issn1002-3828.2017.01.007
——刘家文
——徐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