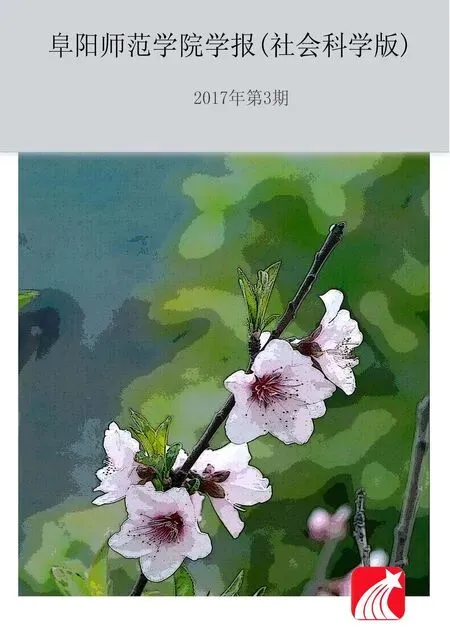陈祖武的顾炎武研究述评
张光华
陈祖武的顾炎武研究述评
张光华*
(阜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阜阳 236032)
陈祖武的学术生涯始自顾炎武研究,其相关学术成果在该领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顾氏生平方面,他澄清了顾氏抗清、北游等事迹中的诸多疑点,并依据确凿史料做出合理的推测。在顾氏学术方面,他指出顾氏之学已突破程朱陆王框架而有新的内容,其哲学思想虽然零散但自成体系,其政治思想的特质是忧国爱民,其历史地位在于开启学风、示范方法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陈先生在研究过程中体现出的多闻阙疑的求实精神和不拘成说的创新精神,尤可树为学界的榜样。
陈祖武;顾炎武研究;学术贡献
陈祖武先生的专业领域集中于清代学术史,著有《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学案史》《清儒学术拾零》等享誉学界的著作。而对顾炎武的研究,乃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祖武之治清代学术史,即自读顾亭林先生书起步。”[1]前言其《黄宗羲、顾炎武合论》《顾炎武哲学思想剖析》《顾炎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顾炎武评传》《顾炎武与清代学风》《亭林学案》等多种论文专著,对顾氏生平、著述、学术思想等各个侧面都有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拟对陈先生在这方面的成就与贡献略作梳理,敬请批评指正。
一、对顾炎武生平的研究
关于顾炎武的生平,陈祖武著有《顾炎武》和《顾炎武评传》两种著作。前者出版于1980年代,属于《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一种。该书篇幅不到四十页,以极为平实的语言,突出顾炎武的高尚人格、求实学风和爱国主义精神,对历史知识的普及贡献良多。但也因为篇幅限制和普及性考虑,顾氏生平中的诸多问题,均没有展开讨论。或许是为了弥补上书的不足,陈祖武又于1999年著成《顾炎武评传》。该著作分十四讲。前两讲分述晚明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状况,便于学者了解顾氏行迹与学术思想产生的背景。第三至十讲以时间为序记述顾炎武一生,作者以核心事件为中心展开论述,普通事件则一笔带过,在突出重点的同时亦保证了其事迹的完整性。第十一至第十四讲,以《广师》《日知录》和顾氏礼学为中心,集中探讨顾炎武学术思想,既避免了事迹叙述中横生枝节,又展现出顾氏深厚学养。尤为重要的是,陈祖武对顾氏生平中的诸多疑点,进行了深刻辨析。
这些疑点的产生,一是源于猜疑:在清廷高压政策下,顾炎武本人及其嗣子顾衍生、门人潘次耕都曾有意识地删略、修改部分容易引发忌讳的内容,给后人留下较多的猜想空间。二是源于深藏在学者内心的某种“顾忌”:顾炎武既然已经成为学术楷模、人生的的榜样,那么任何“不利于”顾炎武的事迹都是“不应该”有的。一疑一忌,便导致了对材料的错误解读,许多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反都成了聚讼不休的问题。陈祖武摒弃疑、忌,以客观公正的态度真实再现了顾炎武的本来面目。
顾炎武是否参与了昆山抗清活动?先是其嗣子顾衍生含混其辞,继有全祖望、吴映奎、徐世昌等人的揣度,昆山抗清便成了顾氏生平中的一大疑点。张穆《顾亭林年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王冀民《顾亭林诗笺释》亦深疑顾炎武未亲与此役,但两者均言之未详。陈祖武详考顾炎武诗文、书札,并没有发现顾炎武参加昆山抗清的迹象。相反,其《常熟陈君墓志铭》则提供了没有参与此役的确凿证据。顾炎武说:“未一岁而戎马驰突,吴中诸县并起义兵自守,与之抗衡。而余以母在,独屏居水乡不出。自六月至于闰月,无夜不与君露坐水边树下,仰视月食,遥闻火炮。”[2]161这段文字,表述清楚,几无任何疑义,而且“顾炎武为人,诚笃不欺,其所记当属最可信据”[1]40。据此,陈祖武得出结论:顾炎武并没有参加昆山抗清活动。在这一问题上,学界讨论颇多。最大的不足在于置顾氏留下的第一手材料于不顾,反而寻找二手、三手资料否认原始资料价值,甚至把顾氏留下的资料说成是他自己有意识地隐晦。但隐晦之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顾炎武即不隐晦此前的“从军于苏”,为何要隐晦“昆山抗清”?“从军于苏”不能带来灾祸,昆山抗清会带来灾祸?这在逻辑上已经陷入自相矛盾。
昆山之外,顾炎武的其他抗清活动,也由于史料缺乏而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陈祖武始终坚持“存疑”原则。他说:顾炎武往还淮上,“或当另有所谋”,“他日若有相关史料爬梳而出,此一揣测之确否或可得以澄清。因此,关于顾炎武此数年间,乃至其后一段时期的若干重要往还及其真实的目的,似以存疑为宜”。不过,这并不妨碍依据确凿的史料,作出合理的推测,为后人的研究提供线索和指引。薙发以后几年,顾炎武奔走于大江南北,虽无确凿史料证明其从事抗清事业,但“非同寻常漫游”则是可以推断的。陈祖武列举了三条证据:“屡谒明孝陵”“同明遗民频繁往还”“关心湘黔战局”。特别是湘黔战局的进展,顾炎武了如指掌。“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顾炎武能够如此准确地获知前方战况,恐或有专门联络渠道。至于这一渠道存在与否,以及具体情况,史料无征,只好存疑。”此外,陈先生还把顾炎武的行踪置于江南的复明运动中去考察,于“非同寻常漫游”增加新的证据。借助顾炎武诗文,陈祖武发现,张名振遥拜孝陵之后,顾炎武则卜居孝陵所在的神烈山;张名振二次入江抵仪征,顾炎武则有《真州》诗专述其事;张名振三次入江抵燕子矶,顾炎武则居于燕子矶僧院中。“张名振军三入长江,顾炎武亦步亦趋,形影相随,这难道仅是其行止的暗合?”[1]50-53虽然有此疑惑,陈祖武并不把猜测当成史实。傅斯年当年大声疾呼,研治史学要“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陈祖武无疑是这一原则的坚守者。
顾炎武一生,北游长达二十五年。其目的以及其间的种种活动,是顾氏生平中最为神秘的部分,学界争议也最多。陈祖武将其北游分成想法初萌、起身北上、北游不归三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他发现,顾氏北游的想法,早在顺治五年秋的《偶来》和是年冬的《将远行作》两诗中就已有明确表露。只是因为没有薙发,加上江南此起彼伏的抗清形势,北游迟迟未能成行。但其“辙环非是为身谋”的诗句,已表明他“决计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坚守初志,辙环四方”的远大报负[1]46。陆恩案发后,顾炎武起身北上。对于其原因,陈祖武依据顾氏《赠路光禄太平》和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等材料指出,顾氏“此次离家北游,确实就是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并没有更复杂的因素存在其中[1]66。至于北游之后迟迟不归,学界争议极大。梁启超曾说:“他本是性情极厚、守礼极严的君子。他父母坟墓,忍着几十年不祭扫。夫人死了,也只临风一哭。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这个哑谜,也只好让天下万世有心人胡猜罢了。”[3]51其后,学界各种猜测风起,最典型的莫过于“消极避祸”和“寻求抗清根据地”两说。对于前者,陈祖武指出:“顺治十四年顾炎武的山东之行,固属避仇。然而三年多过去,仇家已去,旧怨不存,复有挚友苦苦劝归,炎武依然旅途,不返乡里,抑或就不是‘避仇’二字所能够赅括的了。”[1]79对于后者,他认为:“‘谋求抗清根据地’之说,有失牵强,不足为据。”“顾炎武之北游,乃是采取以游为隐的方式,寄寓故国之思,以至死不合作的态度,曲折地与清廷抗争。”[4]目前来看,抗清根据地之说大多都是依据其诗文进行的揣测。诗文固可证史,但把文学色彩的描述铺陈视为事实,把雄心壮志的抒发等同于行动,无疑违反了治史的基本原则。综观《评传》对北游历程的记述,一方面是顾氏与友人的交往唱和,而更多的则是突出他北游的学术目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决意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著述事业。”[1]86“常年往来于直、鲁、秦、晋间,志在九州,著述经世,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1]118至于是否为建立抗清根据地奔波,除引用顾氏诗文展现其悼古伤今与家国之思外,陈先生并没有在史料之外有一丝多余的话语。
二、对顾炎武学术思想的研究
学界对顾氏学术的研究,是从区分其学术派别开始的。从唐鉴《清学案小识》把顾炎武归入“翼道学案”,加上顾氏晚年曾倡导修建朱子祠堂和考亭书院,其后学者多以程朱之学目之。民国时期,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将其径直归入“程朱学派”。虽然觉察到两者有所区别,并将其称为“程朱派之考证学者”,但所看到的仍然只是表面[5]4。陈祖武指出,顾炎武之学“既非朱、王学所能拘囿,亦非汉、宋学所能赅括。乾嘉汉学家之推崇顾炎武,以及唐鉴之斥王是顾,无非买椟还珠,强人就我的门户之见,毫不足取”[4]。为了证明这一观点,陈先生从四个侧面分析了顾氏学术与程朱的区别。首先,对“理”的理解不同。程朱之学的最高范畴“理”,“似乎是脱离具体事物而存在的”。而顾氏“是把它同‘验于事物’结合起来谈的”“不仅同标榜‘心即理’的陆王心学分道扬镳,而且与鼓吹‘性即理’的程朱之学亦泾渭判然,其唯物主义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其次,对性与天道的态度不同。程朱陆王大谈性与天道,而“顾炎武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不讲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而终日陷于‘性与天道’的辩难之中,断非孔孟的儒学正统”。再次,在学术的走向上,“他并没如某些人所说的‘由王返朱’,而是断然选取了经学,提出‘理学,经学也’的命题”。在这一命题之下,“心学也罢,理学也罢,统统作为‘不知本’的‘后儒之学’而被摒弃了”。最后,顾氏对程朱之学的直接批评,更能显示出其与程朱之学的异趣。陈祖武引用《下学指南》与《内典》等篇章指出,虽然没有明确地站在程朱的对立面,“但留意辨析,那种对程朱之学的隐晦曲折的批判,依然是不乏见到的”[6]。陈先生的这些论证,抛开细枝末节与程朱的表面相似,从深层和整体对顾氏学术进行深入剖析,其结论当然也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顾炎武的政治思想,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晚清反满革命起,历经民国,一直到今天,出现了高良佐《清代民族思想之先导者》(1933年)、谢兴尧《爱国主义者顾亭林》(1951年)、冉昭德《坚持反清斗争的爱国学者顾炎武》(1964年)、赵俪生《爱国主义思想家顾炎武的反清斗争》(1981年)等大量的论文与著作。对顾氏政治思想特质的阐发,逐渐形成了忠君说、爱国说和反清复明说等几种不同的观点。陈祖武反对忠君说和反清复明说,有限认同“爱国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顾炎武社会政治思想的特色,或者说本质,就是忧国爱民的救世思想。”这一结论,不仅涵盖了爱国说的基本内容,而且将顾氏政治思想中关注民生疾苦、关心民族未来的特质表述得更为清楚准确。与此同时,陈先生以历史主义为指导,批评了研究中的几种不良倾向。部分持爱国说者“对顾炎武做了过分的褒扬,甚至将这一历史人物现代化,我们也不赞成”。对于顾炎武忠君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他指出,“应当将历史问题摆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进行分析”,这是“清初特定的历史环境给那个时代的理论思维留下的印记”,“不能因为今天要批判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便将在一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并且产生过积极作用的民族意识,以及可以批判继承的民族气节概然否定”。而部分持忠君说者,“仅仅依据顾氏思想中的某些糟粕,便否定了顾炎武的代表作《日知录》及其忧国爱民思想,并进而否定了顾氏晚节,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显然是“对历史人物的苛求,而且也是违背历史真实的”[7]。
关于顾氏哲学,学界的相关研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一直没有起色。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在于学者对于顾氏哲学的不当认识。有学者曾言,“顾炎武的哲学思想是比较贫乏的”[8]。也有学者认为,“顾炎武不是哲学家”,他“以实学取代哲学”,是“哲学取消论者”[9]249-250。这些观点,否认顾氏哲学的历史地位,同时也不利于对顾氏哲学的深入探讨。陈祖武指出,顾氏哲学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只是散见于其论文书札之中”。虽然不像王夫之那样严密博大,但“却也能自成体系,绝非人云亦云”。不仅如此,顾炎武“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上,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其研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基于这一认识,陈先生从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三个层面对顾氏哲学进行了深层次剖析,并归纳出顾氏哲学“朴素唯物主义倾向”这一基本特征。在本体论方面,顾炎武所走的是与程朱陆王相反的“唯物主义思辨路径,自然较之接近真理”,其道器之辨的内涵是“道是寓于器中的,精神是寓于物质的”;其“盈天地之间者气也”的命题,把宇宙描述成“一个充满了气的物质实体,而不是唯心主义理学家所说的不可捉摸的精神世界”。在认识论上,顾氏一反理学家知先行后的认识模式,“强调后天的知识积累,主张学而知之”。其学“不单纯是向书本求知,而且还含有实践意义后天知识积累”。也正是“这种在实践中求知的认识精神,使顾炎武获得了学术上繁富的成果,以一代儒宗而为后世景仰”[6]。陈先生的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顾氏哲学的内涵,更重要的是纠正了学界轻视顾氏哲学的态度,启导后学在这一领域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其后,南京大学的周可真先生完成《顾炎武哲学研究》学术专著,对顾氏政治哲学、伦理哲学等各个层面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一成就的取得,和陈祖武的倡导是分不开的。
准确把握顾炎武的历史地位与学术地位,是陈祖武的又一贡献。陈先生把清初学术看成中国学术史上“承先启后,开辟路径的重要阶段”,且“足以同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后先媲美”[10]。而顾炎武毫无疑问是这一时期最关键的人物之一。整体而言,他是“中国学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宗师”。分而述之则体现为树立学风、示范方法、精神品格等诸方面。虽然清代有汉宋分野、经今古文之争,但“顾炎武学风的影响,却是始终有辙迹可循的”[11]267。顾炎武“当宋明理学衰微之后”,“以他‘明道救世’的实学思想,为当时及后世示范了一种严谨健实的新学风”[12]23。在方法上,顾炎武“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努力,尤其是训诂治经方法论的提出和示范,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历史贡献”。清代学人汲取这两面的营养,才“不惟使古音学研究由经学附庸而蔚为大国,而且还形成了主盟学坛的乾嘉学派,产生了全面总结、整理中国数千年学术的丰硕成果”。如果说,这些成绩的影响还仅限于学术界,那么,其高尚的精神品格便是顾氏影响及于社会全体的关键。梁启超当年深信“顾炎武不仅是经师,而且是人师”,并希望后人“用点功夫,多参阅些资料,以看出他的全人格”[3]51。陈祖武则从两个方面进一步阐释了这种“人师”的品格。一在于他“准确而深刻地阐释了孔子所言二语八字(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而且还在于前无古人地将二者合为一体,提升至圣人之道的高度而大声疾呼”。其二“恐怕当属先生始终如一的高度社会责任意识”,其“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经后世学人归纳,就成了掷地有声的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顾氏留下的精神财富中“最具永恒价值”的部分[13]。时至今日,这八个字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每当中华民族面临危机之际,这句话便成为激励国人奋起抗争的精神支柱。
结语
除了顾炎武生平和学术思想的研究外,陈祖武对顾氏文献研究也有贡献。1981年,陈先生在浙江图书馆见到《甲申野史汇钞》转写本,题“古吴亭林老人辑”。经考订后认定为托名伪作。1982年前后,他又在北京图书馆“得见一无序跋且目录亦略有残缺的八卷刻本《日知录》”,经考证后认定为康熙九年刻本[14]。这些对后世编纂顾炎武作品集、认识其学术思想的真实面貌都提供了可资信据的重要资料。总而言之,陈祖武对顾炎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澄清了顾氏生平中的诸多疑点,对其学术特点、学术思想和学术地位更有许多超越前人的精到阐发,很多观点已被学界公认。尤为重要的是,他在顾氏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求实精神和不拘成说的创新精神,为学术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1]陈祖武.顾炎武评传[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2]顾炎武.常熟陈君墓志铭[M]//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4]陈祖武.顾炎武、黄宗羲合论[J].贵州社会科学,1984(5).
[5]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6]陈祖武.顾炎武哲学思想剖析[J].社会科学战线,1983(2).
[7]陈祖武.顾炎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1(6).
[8]华山,王庚唐.论顾炎武思想(下)[J].文史哲,1963(3).
[9]王茂.清代哲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10]陈祖武.论清初学术的历史地位[J].清史研究,1991(1).
[11]陈祖武:顾炎武与清代学风[M]//清史论丛(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陈祖武.论17世纪的中国实学[M]//中韩实学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13]陈祖武.高尚之人格,不朽之学术——纪念顾亭林先生四百年冥诞[J].文史哲,2014(2).
[14]陈祖武.《日知录》八卷本未佚[J].读书,1982(1).
Commentary on Chen Zu-wu’s Research of Gu Yan-wu
ZHANG Guang-hua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College,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2 Anhui)
The research of Gu Yan-wu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Chen Zu-wu’s academic life. In the aspect of Gu’s life, he clarified many doubtful points and made some reasonable speculations based on authentic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aspect of Gu’s academy, he pointed out that Gu’s theory had broken the limit of Cheng Zhu and Lu Wang, his philosophy was fragmentary but systematic, the particularity of his political ideas was the anxiety of the nation and common people, his historical status lied in initiating new style of study, demonstrating new academic method and stro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Mr. Chen’s matter-of -fact attitude and initiative spirit also set an example for the academic circle.
Chen Zu-wu; research of Gu Yan-wu; academic contribution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3.26
K27
A
1004-4310(2017)03-0133-05
2017-02-25
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史通文献集成与研究”(14BZS001)。
张光华(1972- ),男,安徽砀山人,历史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