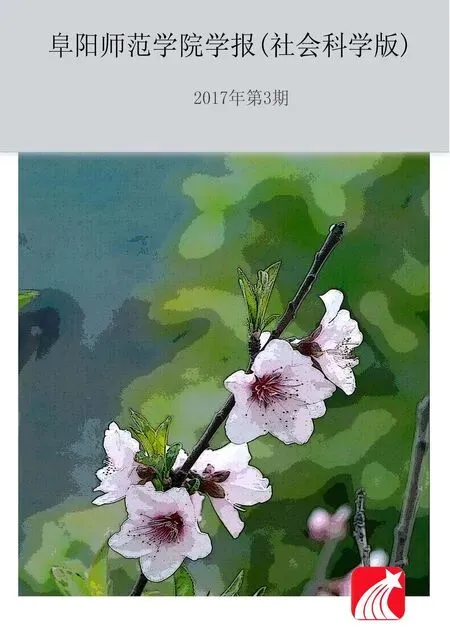《淮南子》礼乐文化述论
张良宝
《淮南子》礼乐文化述论
张良宝*
(淮南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安徽淮南 232038)
《淮南子》是西汉初期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一部著作,其中论述礼乐文化的文字虽然散见于不同的篇章,但认识独到,论证全面,运用灵活,值得加以研究。本文主要从礼乐的产生及其社会功能、礼乐之“情”与礼乐之“和”、礼乐应因时因地而制宜等方面,集中论述了《淮南子》中的礼乐文化。
《淮南子》;礼乐;道德;雅颂之乐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系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招集宾客集体创作。《淮南子》全书共有二十余篇,体系庞大,内容丰赡,涉及天地万物、事态风情以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淮南子》博奥深宏的论说中,对于礼乐文化的论述有很大的篇幅,尽管这些论说散见于不同的篇章,但论述深刻而精辟。笔者从事音乐理论研究,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孜孜以求,本文意在整理散见于《淮南子》中的礼乐文化方面的论述,并主要从礼乐的产生及其社会功能、礼乐之“情”与礼乐之“和”、礼乐应因时因地而制宜等方面,分析研究《淮南子》中的礼乐思想。
一、礼乐与仁义的产生及其社会功能
仁、义、礼、乐是中国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礼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礼制或礼俗仪式相须固化为用的乐舞形态”(1)。
《淮南子》以道家思想为主旨,提出了对《老子》《庄子》中的“道”论及“无为”论的个性化解释,明确提出“无为”并非无所事事、无所作为,更不是违背自然之理的主观妄为,而是应该“循理而举事”,即顺应自然和人类自身及社会规律行事,强调天地“合和”的思想旨归。《淮南子》在论及礼、乐的产生与社会功能时,是将其与仁义、道德等文化现象结合在一起来综合阐发的。《本经训》说:“天地之合和,阴、阳之陶化万物,皆乘人气者也。”指出天地之间的气体相互融合,阴阳之气和化为万物,一切都顺应天地的合和之气,因此“古之人同气于天地,与一世而优游。当此之时,无庆贺之利、刑罚之威,礼义廉耻不设,诽誉仁鄙不立,而万民莫相侵欺暴虐,犹在于混冥之中”。正是由于古代圣人与天地同气,故能在一世间悠闲遨游,如同生活于大冥之中,无利益纷争、无刑罚之威、无礼义廉耻,也无诽谤赞誉和仁慈卑鄙之念,这是以道家“天道”的观念解读世界,反映了《淮南子》崇尚合和的理想境界,体现出自然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哲学特点。
探究礼乐之本,须溯礼乐之源。礼乐文化产生于远古时期的祭祀活动及其相应的礼俗仪式与礼乐活动,西周时期,宗教性礼乐让位于政治性礼乐,礼乐从此由神坛进入人间,礼乐之道成为治国之道。关于仁、义、礼、乐的产生,《本经训》说:“逮至衰世,人众而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于是忿争生,是以贵仁。仁鄙不齐,比周朋党,设诈諝,怀机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贵义。阴阳之情,莫不有血气之感,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是以贵礼。姓名之情,淫而相协,以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是故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淮南子》认为:仁、义、礼、乐产生于“衰世”,古代圣人因与天地同气,因此不需要仁、义、礼、乐。只有在衰败之世,才会因纷争而产生对仁爱的期盼,因纯真本性的丧失而产生对道义的追求,因人有阴阳二气交汇充满了血气的冲动,便提倡尊重礼节,因人性中情欲失调,便提倡乐教。《淮南子》还认为:对仁、义、礼、乐的提倡与规定,只能补救暂时的混乱,而不能解决天下的根本问题。《淮南子》肯定仁义礼乐是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道衰落之时可以“救败”。《本经训》认为:“夫仁者,所以救争也;义者,所以救失也;礼者,所以救淫也;乐者,所以救忧也。”《淮南子》指出了仁、义、礼、乐的社会作用:仁爱可以用来制止互相争斗;大义可以用来解救本性的丧失;礼节可以用来制服相互淫乱,乐教可以用来解救忧愁。由此可见,《淮南子》对于与“道”的内涵相同或密切相连的仁、义、礼、乐是予以赞同的,而对于脱离了“道”的实质与根本、作为“文饰”的仁、义、礼、乐是持否定态度的。如果说衰世会产生仁、义、礼、乐,虽然“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那么只有重返“同气于天地”的“大道”世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治理天下的问题,因此,《本经训》说:“神明定于天下,而心返其初;心返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阴阳从而包之,则财足;财足而人瞻矣,贪鄙忿争不得生焉。由此观之,则仁义不用矣。道德定于天下而民纯朴,则目不营于色,耳不淫于声,坐俳而歌谣,被发而浮游,虽有毛嫱、西施之色,不知悦也;《掉羽》《武象》,不知乐也;淫泆无别,不得生焉。由此观之,礼乐不用也。”
“道德”与“仁义”是《淮南子》一书中的核心范畴。关于道德,《淮南子》说:“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认为“道”就是要依循本性而行事;“德”就是要得到天然的本质或属性。《淮南子》在广泛运用“道德”范畴的同时,并常将“道德”适配“仁义”。《淮南子》主张以“道德”来统领仁义礼乐的施用过程。《淮南子》认为,只有“神明、道德定于天下”才是解决治理国家问题、实现盛世的根本,并强调“神明”的缺失会导致德衰、行沮、和失、礼淫。“是故德衰然后仁生,行沮然后义立,和失然后声调,礼淫然后容饰。是故知神明,然后知道德之不足为也;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之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之不足脩也。”意思是说:“仁”生于“德衰”,“义”立于“行沮”,“乐”生于“和失”,“礼”生于淫乱。《淮南子》在要求人们恪守道德的同时,强调了“仁义礼乐”对于“德衰”“行沮”“和失”“淫乱”具有规范与制约的作用。《淮南子》强调:“今背其本而求于末,释其要而索之于详,未可与言至也。”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既指出了社会发展中“舍本求末”的问题,认为仁义礼乐是衰落之世的必然产物,提醒为治者要正视这一事实,并尽力纠偏救弊,同时表达了“不先物为”“不易自然”“循理而举事”的治国主张。《原道训》说:“是故不得于心,而有经天下之气,是犹无耳而欲调钟鼓、无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胜其任矣。”这里是说,治理天下,心中必须有大道的主宰,否则就如同无耳之人为钟鼓调音,亦如同无目之人喜欢文采。
关于仁、义、礼、乐的用法,《淮南子》有时将四者合称,有时各自独立使用,还有时将仁义或礼乐连用,而且对仁、义、礼、乐所秉持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有时正面赞许,有时又负面讥讽或严厉批评。《本经训》说:“立仁义,修礼乐,则德迁而为伪矣。及伪之生也,饰智以惊愚,设诈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对于鼓吹仁义礼乐造成的饰智求诈、伪匿不实的风气,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仁义礼乐蒙蔽了人的恬淡清净的本性,并强调缘饰礼乐会导致劳民伤财的后果。《齐俗训》说:“性失然后贵仁,道失然后贵义。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礼乐饰则纯朴散矣,是非形则百姓昡矣,珠玉尊则天下争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业,末世之用也。”《淮南子》认为,仁义礼乐是衰落之世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纯朴消失,人们争斗不休,道德沦丧,失去了人性的根本,提醒为治者要正视这一事实,并尽力纠偏救弊。
二、“礼乐之情”与“礼乐之和”
先秦时期的“礼乐”文化形成为完备的典章制度(主要是君臣、父子、贵贱的等级制度)、道德规范(主要包括忠、孝之道)和各种礼仪形式的综合。孔子把以“仁”为核心的礼乐精神引向人的内心世界,要求音乐的思想情感表达必须符合礼制,把礼乐的应用范围从贵族统治阶级扩大到全社会,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根基。《礼记·乐记》说:“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主流是礼乐思想,它要求音乐受制于“礼”,将音乐社会现实以及政治兴衰紧密相连,《乐记》的音乐思想对后世的音乐创作与音乐理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淮南子》认为:性生欲,欲生情。人的本性中存在各种欲望,并不断寻求欲望的满足,而在欲望满足的过程中,人的性情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主要表现为“乐”与“怒”两类性情范畴。人的欲望,本然地希望“心和欲”,以求自得之乐,这些取决于外物的影响,亦即“触物生情”,正如《俶真训》所言:“且人之情,耳目应感动,心志知忧乐……所以与物接也。”因“与物接”,人自然便会“知动”“神应”。“神”即“情”,在“知动”“神应”的过程中便会有情的自然产生。故《本经训》说:“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歌舞节则禽兽跳矣。”人“心和欲”便会产生一种自然的“乐”的情感,并以“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的形式来表现“乐”,这既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人的感性欲求,又简洁地概括了人通过自身的肢体语言与发声来寻求自然情感的表达,呈现出艺术情感表达的过程。
若“与物接”而“不和欲”,则人会哀、怒。《本经训》说:“人之性,有浸犯则怒,怒则血充,血充则气激,气激则发怒,发怒则有所释憾矣。” “夫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所以饰喜也;衰絰苴杖,哭踊有节,所以饰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钺,所以饰怒也。”由于外物的影响,人可生“情”,情的表达要通过“饰喜”“饰哀”“饰怒”等礼仪手段而“形行于外”。《修务训》说:“夫歌者,乐之徴也;哭者,悲之效也。愤于中而应于外,故在所以感。”《泰族训》也说:“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经哭踊之节。”指出人表达情感可以通过自然与人文饰物来表现。
《淮南子》认为,音乐因人性而生,反之,音乐也可以影响人的性情,即“声色之乐”使人乱性。“声色之乐”是满足于生理性快感的音乐,它属于“淫”乐的范畴。《精神训》说:“耳目淫于声色之乐,则五脏摇动而不定矣。五脏摇动而不定,则血气滔荡而不休矣。血气滔荡而不休矣,则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则祸福之至,虽如丘山,无由识矣……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哗耳,使耳不聪。”《淮南子》对于这种使“精神驰骋于外而不守”的“声色之乐”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该类音乐“五声哗耳,使耳不聪”。正是因为音乐会使人乱性,因此极力反对音乐的淫而不和,反对听者纵欲而失性。《齐俗训》说:“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夫纵欲而失性,动未尝正也,以治身则危,以治国则乱。”《泰族训》说:“乐之失淫。……今目悦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声,七窍交争以害其性,日引斜欲而浇其天和,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此,《齐俗训》说:“乱国……乐优以淫……是故圣人废而不用也。”淫乐可以“害性”,会“日引斜欲而浇其天和”,甚至可能“乱国”,因此,圣人对淫乐的态度是“废而不用”。
《淮南子》认为,从事音乐活动者必须通达礼乐之道,制礼作乐是为了避免人情的“外淫”,因此,明确强调“通于礼乐之情者,能作音”(《氾论训》),意思是说,制作有教化功能的音乐,必须懂得礼乐之情;反之,不通礼乐之情者,则不能作“音”,这是从教育的角度,提出了“作音”的条件。《淮南子》主张好的音乐可以“致和”。《本经训》说:“乐者,所以致和。”《原道训》说:“圣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提出音乐应该“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乱情”,明确指出,有道德的人,不会让外物支配自己,不会让外物扰乱自己的天和。《原道训》说:“目观《掉羽》《武象》之乐,耳听滔朗奇丽激抮之音,扬郑卫之浩乐,结激楚之遗风……此齐民之所以淫佚流面。圣人处之,不足以营其精神、乱其气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本经训》说:“性命之情,淫而相协,以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圣人顺应人们对音乐的喜爱,出于使社会秩序和谐的目的而制礼作乐,意在使社会和顺,使秩序畅达。故《本经训》说:“古者圣人在上,政教平,仁爱洽……夫人相乐,无所发贶,故圣人为之作乐以和节之。末世之政,田渔重税,关市急征……愚夫蠢妇皆有流连之心,凄怆之志,乃始为之撞大钟、击鸣鼓、吹竽笙、弹琴瑟,失乐之本矣。”政治和顺,人心愉悦,音乐使人和乐。反之,政治乖逆,人心悲苦,音乐使人凄怆。
《淮南子》重视《雅》《颂》之乐,将《雅》《颂》之乐作为标准而加以提倡。《泰族训》说:“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仪;言不合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音不调乎雅颂者,不可以为乐。”《淮南子》在此强调,不管是表现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音乐都应该合乎《雅》《颂》的要求。《泰族训》说:“民有喜乐之性,故有钟鼓管弦之音……今夫雅颂之声皆发于词,本于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亲。故《韶》《夏》之乐也,声浸乎金石,润乎草木。今取怨思之声施之于弦管,闻其音者不淫则悲,淫则乱男女之辨,悲则感怨思之气,岂所谓乐哉?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作为山木之讴,闻者莫不殒涕。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发植穿冠。因以此声为乐而入宗庙,岂古之所谓乐哉?”这有三层意思:一是说明“钟鼓管弦之乐”可以文饰人的喜乐情感;二是“雅颂之声”因其“本于情”,所以君臣和睦,父子相亲;三是通过反问的手法,指出“怨思之声”和“易水之声”因为不能“致和”,所以均不符合礼乐的标准。故《泰族训》说:“因其喜音而正《雅》《颂》之音,故风俗不流。”
三、礼乐应因时因地而制宜
作为一种文化范畴,礼乐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淮南子》以发展的眼光,在总结三代礼乐文化历史演进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礼乐文化的历史性与时代性,主张礼乐应“因时而变”。《齐俗训》说:“有虞氏之礼,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亩,其乐《咸池》《承云》《九韶》,其服尚黄;夏后氏之礼,其社用松、祀户,葬墙置翣,其乐《夏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礼,其社用石,祀门,葬树松,其乐《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礼,其社用粟,祀灶,葬树柏,其乐《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礼乐相诡,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亲属之恩,上下之伦。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传代之俗,譬由胶柱而调瑟也……是故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故圣人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世。”《淮南子》陈述了虞氏、夏后氏、殷人、周人的礼制与用乐制度,强调尽管“礼乐相诡,服制相反”,但“皆不失亲属之恩,上下之伦”。因此不同时代的礼乐在内容与风格上是不同的,肯定不同时代音乐制度的变化。《氾论训》说:“尧《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汤《大濩》周《武象》,此乐之不同者也。故武帝异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淮南子》由此推而广之指出,圣人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论世而立法,随时而举世”。这一观念的提出,既是对抱残守缺的礼教思想的批评,也是对当朝皇帝治国理政方法的提醒与忠告。
《淮南子》认为礼乐应“因时变而制宜适也”,强调礼乐的时代性。在反对崇旧循古的同时,《淮南子》不仅认为“礼乐未始有常制”,主张辩证地看待礼乐文化,应该因时因地制宜,而不应该生搬硬套、死板教条,同时主张礼乐的制定应该以利民为本。《氾论训》说:“先王之治,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苟利于民,不必法古;敬周于事,不必循旧。……故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变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在此,《淮南子》认为礼乐盲目法古是不可取的,法与礼应当与时俱进,对于法制和礼乐制度“不宜则废之”。同时认为,制订礼乐要适合本时代人民生活和社会实践的现实需要,这反映了《淮南子》非常开明的民本思想。“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这体现了作者的进步的历史观。在礼教纲常走向严酷的时代,《淮南子》大胆提出“因时变而制礼乐”“先王之治,不宜则废之”“苟利于民,不必法古”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结语
礼乐文化脱胎于原始礼乐,经过西周王朝礼乐文化的渐进培育和先秦儒家文化的丰富与强化,并在后世官方和民间的推助下,成为贯穿于中华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基本精神,对于铸造民族精神影响深远。“滥觞、发展自先秦的礼乐文明,不仅作为一种单纯的文化事象而存在,更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价值体系,深植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成为影响华夏民族道德信仰和民族精神的重要因素。”[2]《淮南子》融道、儒、阴阳等诸家思想于一体,论述了仁义礼乐产生的本质及其伸展蔓延的缘由,强调仁义礼乐并非治国理政的根本方法,主张重返“同气于天地”的“大道”世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治理天下的问题。在音乐的主与客、内与外的论述中,指出了“声色之乐”虽然可以实现人性的宣泄,但是也可以导致纵欲失性的后果,提出《雅》《颂》之乐的制乐标准,重视雅乐对于人的教化作用以及纯化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淮南子》承继三代及先秦礼乐的变通的特点,强调礼乐应该因时而制、因地制宜,体现了鲜明的“亲民”诉求。
“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各个民族对其原生文明的深刻反思,从来都是在各个时代发挥创作力的精神宝库。”[3]《淮南子》中至于礼乐文化的论述,不仅是对三代以来礼乐文明发展的梳理与荟萃,更是站在特定的历史憧景下对治理国家重大问题学理性思考的重要成果。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在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下,深入研究包括《淮南子》在内的经典著作中蕴含的优秀文化基因,弘扬传统社乐文化,不仅有助于加强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认识与理解,更重要的是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启示与参照。因此,深入研究《淮南子》中礼乐文化对于当下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1]项阳.“礼乐文明”的困惑[J].中国音乐学,2015(1):6.
[2]李宏峰.传统礼乐文化的内在张力结构[J].中国音乐 学,2007(4):5.
[3]张炯.一部波澜壮阔的帝国史诗——评《大秦帝国》[N].光明日报,2013-12-08.
On the Music Culture in
ZHANG Liang-bao
(School of Music and Dance,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232038, Anhui)
is a book compiled by Liu An, the Huainan king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which discussed the music culture in different chapters. Though scattered but unique, flexible with comprehensive demonstration, those words on music culture are worth studying.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music culture infrom the origin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music, “love” and “ritual” in music, and adaptation to the times.
; music; moral; Ya Song Music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7.03.03
J60
A
1004-4310(2017)03-0010-05
2016-12-28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淮南子》中的礼乐文化研究”(AHSKY2014D129)。
张良宝(1969- ),男,安徽灵璧人,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学。